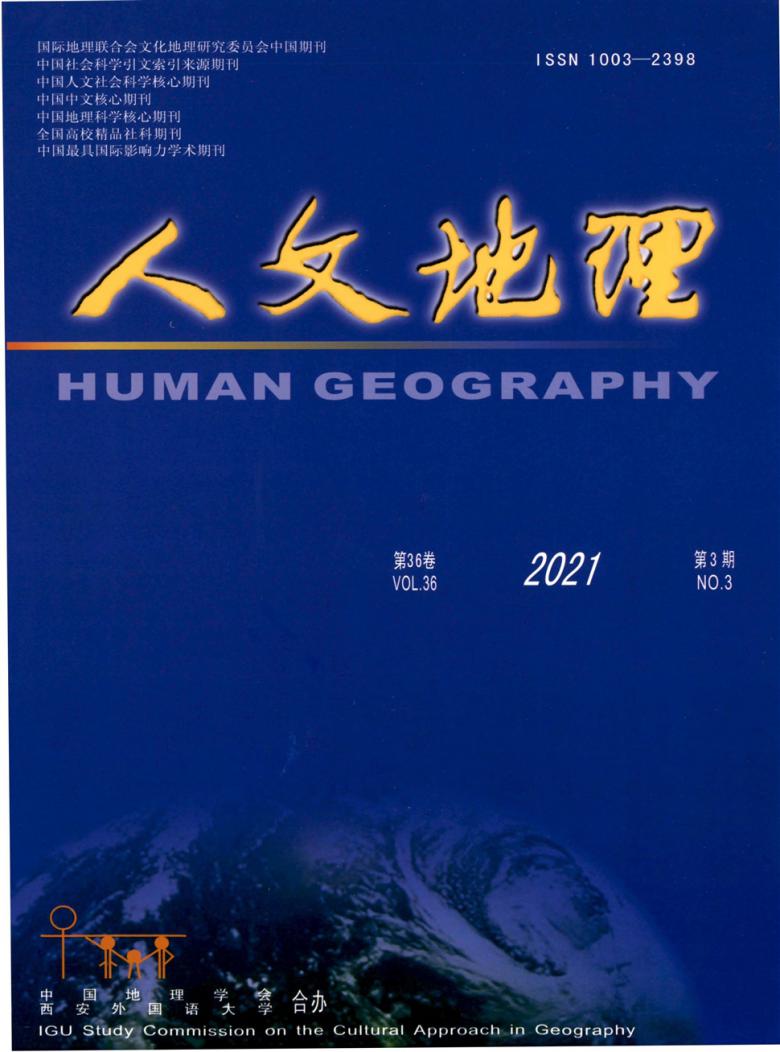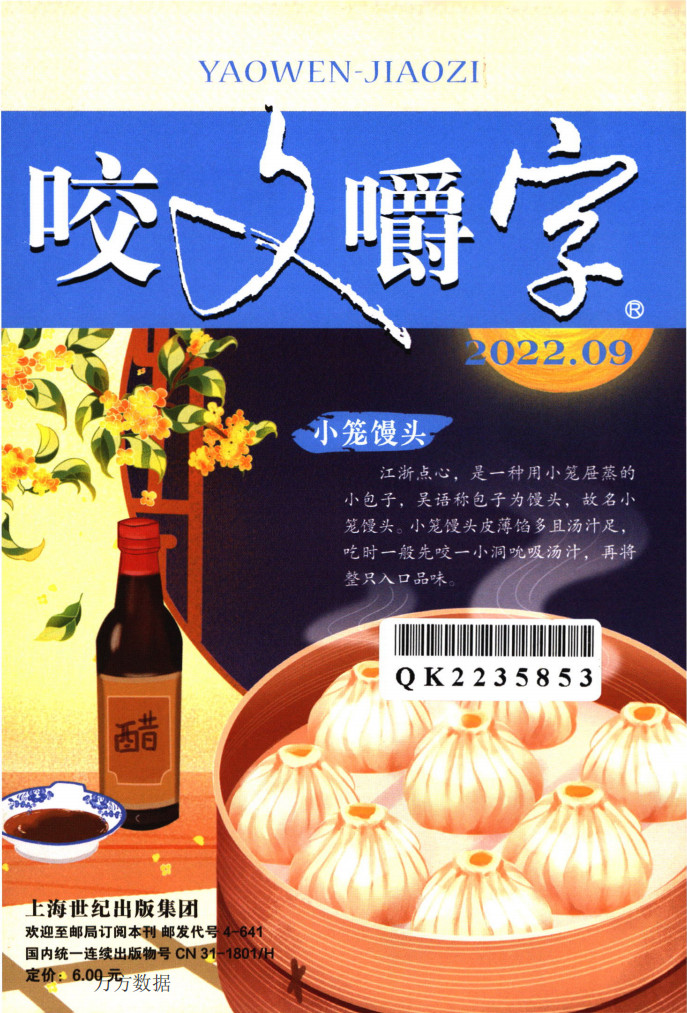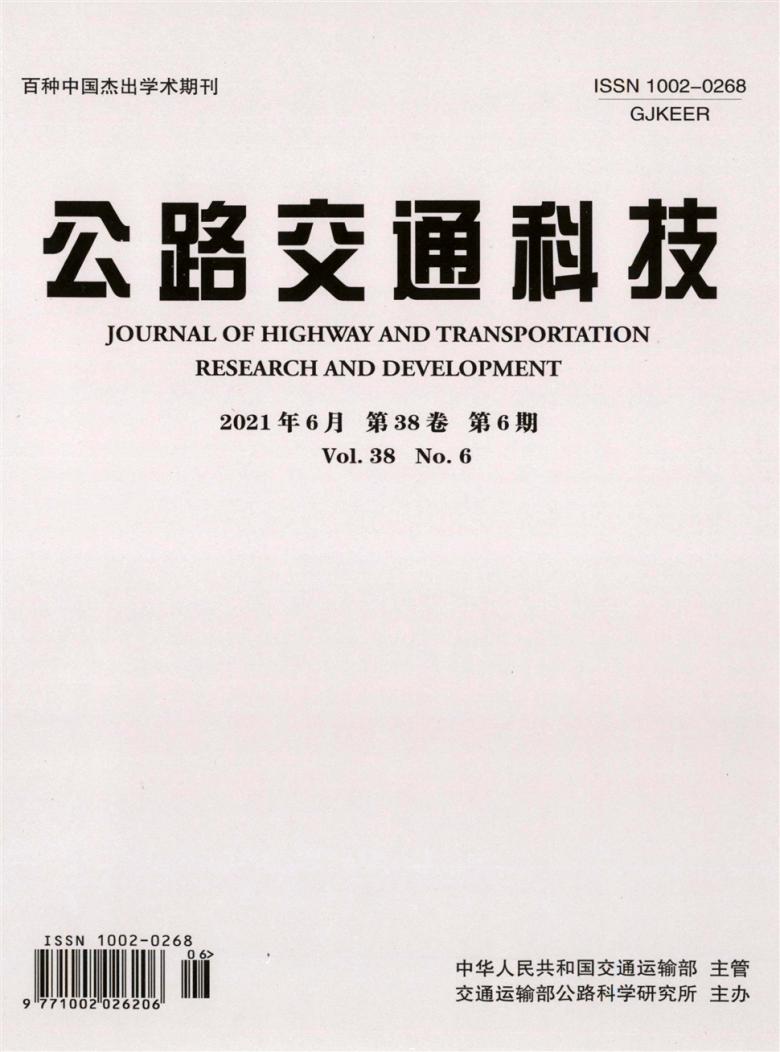二元社會視野下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宏觀透視——新民主主義革命發生發展的歷史根據
張福記
[關鍵詞] 二元社會 新民主主義革命 歷史根據
[摘 要] 革命是少數精英主觀鼓動的結果還是歷史演化的必然選擇,是阻礙了社會現代化進程還是為現代化的大規模展開開辟道路,問題的求解需要我們以馬克思主義唯物史觀為指導,從近代中國社會基本的二元格局出發,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尋找答案。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生發展從根本上講源自生產力的內在要求,是近代中國社會生產力與落后腐朽生產關系沖突的結果;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也正是為了解放與發展生產力。這一切表明,中國共產黨是中國社會先進生產力的真正代表。
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是近代中國社會演化的結果,探求其發生發展的合理的歷史根據,也必須從近代中國社會演化的視角去考察。近代中國社會變遷的最明顯表現為二元社會格局的出現:一方面,孤島般、畸形繁榮、新事物紛然出籠的通商大都市崛起,另一方面則是作為中國社會主體之鄉村的發展遲滯、日漸貧困、掙扎于生存危機。這種二元格局從不同的層面制約著中國近代社會的政治變革,也許只有從城鄉二元及其內在關系的維度才能更為全面而深刻地理解新民主主義革命發生發展的歷史意蘊。本文主要從城鄉生產力的解放與發展的角度,考察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歷史必然性。
一、鄉村危機·土地革命及其現代意義
近代中國90%以上的人口為農民,農業在國民經濟中始終占著主要地位,且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主要內容之一為土地變革,毛澤東也在不同的場合多次說過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實質是農民革命,故要研究新民主主義革命合理的歷史根據必然離不開對農村演化的分析。過去分析新民主主義革命時,都重點分析了農村的狀況,本文認為這種分析是必要的,但需指出的是,新民主主義革命決不等于農民革命或土地革命,土地革命具有多重意義,既有發展農業生產、解決農民生存危機、進而動員廣大貧苦農民參加反帝反封建的直接動因,更有從根本上為中國先進的生產力開辟道路最終完成從農業向工業國轉型的偉大目標。土地革命僅是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項重要內容,它服務于實現民族獨立和建立公平與現代化社會的歷史使命。
近代中國鄉村情況如何?至今沒有統一的意見。過去一般認為近代中國農村農業落后農民生活困苦,沒有什么進步。近幾年又出現一些稍新的觀點,認為近代中國鄉村有一定發展,而不是一直蕭條。本文則基本傾向于傳統的觀點,并用鄉村危機來概括近代中國農村社會的基本狀況,且堅信這是比較符合歷史事實的。
鄉村危機早在乾隆中后期就已開始,鴉片戰后,外國的入侵激化了本已尖銳的社會矛盾,最終釀成中國歷史上規模最大的舊式農民大起義。但太平天國運動沒有導致王朝的更替,封建大土地所有制仍然存在,也未造成政府休養生息政策的執行,只是部分緩和了過去極為緊張的人地關系。隨后,由于對外賠款的增多、政府舉辦洋務的展開等種種因素,鄉村一直處于危機之中,從過去的周期性爆發轉變為持續性存在,不僅有絕對的生產不足而出現物質匱乏,且有一定程度的生產過剩危機征象,成為世界經濟危機的一部分。(《王亞南文集》第3卷,第283頁,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
近代鄉村危機主要表現在以下兩個方面:(1)農業生產的落后和發展遲滯。近代中國農業經濟雖然局部地區呈現一定程度的商品化、區域化格局,但從總的來講,近代中國農村的生產力沒有多少質的進步。農村基本仍沿用傳統的生產工具和耕作方法,即使在中國相對先進的通商口岸地區,“古老的耕作方法依然占支配地位,復種輪作沒什么創新,農民普遍使用的仍是浪費體力的古老農具,農民依舊依靠傳統農家肥,改良種子和新品種的引進有名無實”,“新式農具、化學肥料和新品種的采用等新因素所起作用微不足道。” (章有義:《海關報告中的近代中國農業生產力狀況》,《中國農史》1991(2)。)農作物產量從總體上講,部分年份有所增加,但單位畝產量并未提高,相對于鴉片戰爭前夕,總體上看有下降的趨勢。若以1821~1830年間畝產量指數為100,1831~1850年則為92,1871~1890年為80,1891~1911年為78。(珀金斯:《1368~1968中國農業的發展》,第31頁,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1931年糧食作物畝產量平均僅為270.09斤,比清代中葉的367斤下降了26.2%,1947年的畝產量甚至低于漢代264斤的水平。(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量研究》,第205~206頁,農業出版社,1985。)總產量的增加主要靠耕地的增加(開墾東北及西南邊疆等)及玉米、甘薯等高產作物的種植。農業的衰落還表現在大批無地農戶無力租種土地,導致廢荒耕地不斷增多。耕地荒廢面積的增加率若以1914年為100,1930年則已達323。(《王亞南文集》第3卷,第277頁。)具有資本主義性質的經營式農場,不僅稀少,且在30年代逐漸衰落。總之,近代農業生產在諸種因素阻礙下,仍維持傳統落后的生產方式,沒有出現什么質的進步。(2)農民生活貧困化加劇與流民增多。近代農業的稍許進步所得并沒有歸勞動人民所有,而是通過種種剝削流進了地主、商人、官僚、資本家及外國侵略者手中,且農村貨幣不斷流入城市,導致近代農村金融枯竭,缺乏進一步發展的物質力量。近代中國農民負債者不斷增加。三十年代中央農業實驗所對全國22省850縣所做的調查表明,借錢戶占全體農民戶數的56%,借糧戶占48%。(張培剛:《民國二十三年的中國農業經濟》,《東方雜志》第32卷(13)。)當時高利貸盛行,貧困的農民在惡性循環中難以擺脫困境。許多農民在難以生存的情形下,走上背井離鄉、出外謀生的道路。據1933年21省有報告資料的縣份計,離村農戶均占該縣農戶總數的4.8%,高者達12.2%。(趙德馨主編:《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教程》,第267頁,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由于近代工業不發達,進城而難以發生角色轉換的農民,或淪為乞丐與娼妓,或加入黑社會擾亂一方。也有不少青壯年男子進入部隊充當士兵,更有一些破產農民結伙為盜、占山為匪,成為社會的贅瘤。廣大農民處于生存危機之中,為生存而斗爭構成起伏不斷的農民運動的主題。
阻礙近代農村生產力發展導致農村發生危機的因素是多重的。帝國主義對華勒索巨額賠款及其商品剝削、歷屆反動政權對農村征收沉重的賦稅和攤派徭役、腐敗統治下頻繁的天災人禍以及一直存在的人地緊張關系等,都構成近代鄉村不斷走向衰落的重要原因,這里主要對導致農村危機的根本障礙封建大地主土地所有制對農村生產力阻礙做些說明。
中國自秦漢以來,就形成了在土地私有制基礎上以地主大土地所有制為主的封建土地制度。大土地所有制與個體租佃小農經營體制的結合,構成中國農村社會的基本生產方式。這種生產方式存在著內在的矛盾,極不利于農村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一方面在土地買賣兼并的過程中,耗費了大量的社會貨幣,以致土地所有者難以向農業生產進行大量投資,同時由于大土地所有者采取租佃經營,只重視農業產品的再分配而不重視農業的再生產,不愿對生產進行投資;另一方面,土地耕作者,在沉重剝削下,缺乏再生產能力,勞動積極性也受到打擊。因此,這種土地制度在中國商品經濟極不發達及生產力極其落后的社會條件下出現,可說是一個怪胎,構成中國社會發展遲滯的總根源,使中國長期徘徊于治亂循環的周期性危機之中。進入近代以后,封建土地制度沒有改變,軍功地主增多下土地兼并仍有不斷加劇之勢,導致無地農戶增多,這在東南沿海省份表現得更為突出。以1905~1924年江蘇昆山為例,1905年自耕農(包括地主和富農)占各類農戶的比例為26%,1924年則下降為8.3%;佃農則由1905年的57.4%,上升為1924年的77.6%。(嚴中平等輯:《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276頁,科學出版社,1955。)土地集中并未帶來經營方式的變化,相反,由于廣大農民日益貧困,無力耕種更多的土地,以致土地使用日益分散。據1922年對浙江等五省九縣田場大小的統計,平均使用10畝地塊以下的農戶,竟占全體農戶的58.1%,11~25畝的占24.1%,26~50畝的只有9.4%,使用51畝以上的農戶僅為8.3%。(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第2輯,第381頁。)近代以來,中國人地比例一直處于緊張狀態,出現競租現象。據章有義的最新研究,中國人均耕地從未超過3畝,1928~1936年僅為2.77畝。(章有義:《近代人口與耕地的再估計》,《中國經濟史研究》1991年第1期。)耕地的增長速度跟不上人口的增長速度。在競租耕地及其他因素的影響下,形成地租上漲趨勢。據江蘇9縣調查,1922~1927年間,實物定額租增長了37%;蘇、皖兩省4縣的調查,分成租額增長了172%。據江蘇27縣調查,1922~1927年間貨幣地租增長了129%。(嚴中平等輯:《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304~305頁。)近代中國的地租一般占產量的一半左右,有的高達八成甚至100%以上。如昆明三村租額為107%,浙江義烏為121%,福建長汀為100%。(嚴中平等輯:《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第304~305頁。)在商業性農業區,地主往往提高種植經濟作物土地的地租率,將佃農通過增加投資和勞動所得的收益剝削去大部分,影響著農民生產積極性的發揮。地主還通過押租、預租以及各種附加租和勞役等手段, 加強對一般農民的剝削,將廣大農民推向生存危機的境地。由于高地租的影響,一方面導致各色地主將農民勞動成果大部剝削歸己,嚴重影響直接生產者小農的擴大再生產甚至簡單再生產,從而阻礙了農村生產力的進步,同時也導致社會大量貨幣向土地轉移,或將地租轉化為高利貸和商業資本,而不是投入到現代產業中去。
可見,近代中國農村生產力與封建的生產關系存在著尖銳的沖突,要發展農村生產力,促進農村經濟的進步,必須徹底改變封建的土地制度和地主階級的統治。把農民從大地主土地所有制下解放出來,實現耕者有其田,是當時促進農業發展的最基本的舉措。中國共產黨領導的土地革命正是將廣大農民從封建制度下解放出來,最大限度地調動農民生產的積極性,解放農業生產力,促進農業經濟的發展,進而為中國工業化的大規模展開奠定基礎。
鄉村危機構成了新民主主義革命的基本背景,但以土地革命為中心內容的新民主主義,不是一般的農民革命。在近代中國工業化不斷發展的背景下,它已與中國社會現代化相聯,是促進中國工業化進步的必要前提。因此,土地革命的性質與作用決不是傳統的農民革命所比擬的。土地革命只是中共新民主主義革命的一部分,是中共實現民族獨立、國家統一、建立新型制度、完成工業化、最終實現中國社會現代化的革命道路和手段。關于土地革命對解放生產力的意義,中國共產黨雖然出現過錯誤的認識,但以毛澤東為代表的領導人則對此認識不斷深入。早在1927年毛澤東就指出土地革命的意義在于“農民得解放”、“增加生產力”、“保護革命”。(《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3頁,人民出版社,1993。)1936年他在與斯諾的談話中,明確指出土地革命是“資產階級性質的革命。它有利于資本主義的發展”。(《毛澤東文集》第1卷,第410頁。)1944年毛澤東在同英國記者斯坦因的談話中更為明確指出:“在沒有進行土地改革的中國其他地區,仍然是封建土地所有制下的分散的個體小農經濟,農民被土地束縛著,沒有自由,彼此很少往來,過著愚昧落后的生活。這種經濟是中國古代封建主義和獨裁專制的基礎。未來的新民主主義社會不可能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中國社會的進步將主要依靠工業的發展。但為了發展工業,必須首先解決土地問題。沒有一場反對封建土地制度的革命,就不可能發展資本主義”。(《毛澤東文集》第3卷, 第183~184頁,人民出版社,1996。)事實上,近代中國農村的狀況與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工業的盛衰有著根本關聯,限于篇幅,這里不準備詳談。
二、現代化與革命的內在互動
真正理解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發生、發展及其性質,如果僅從衰落的農村一元去觀察是極不全面的,還必須考察擁有現代生產方式及新的思想價值觀念、代表時代發展潮流的城市,從根本上講,正是后者的參與,才使得中共革命成為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導致革命發生及其性質變化的更為根本的因素是現代生產力及在此基礎上社會諸領域現代化因素的不斷發展與壯大。革命與現代化的關系不是對立的關系,歷史的事實是:現代化因素的不斷積聚及其受壓,是導致革命發生的最本質因素,革命又是為社會現代化開辟道路。這里主要從20世紀二三十年代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及其障礙作些分析,以考察新民主主義革命與新式生產力的互動關系。
不斷發展的新生產力與占統治地位的舊生產關系之間的沖突是革命發生發展的根本原因與條件,也是一場先進的革命發生發展的最根本的歷史根據。對此,馬克思等經典作家做過大量的論述。(張福記:《馬克思等經典作家政治革命觀的重新理解》,《山東師大學報》1998(4)。)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曾做過經典性的概述:“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過程。……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運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2卷,第32—33頁。)這一段話論述了研究革命的基本方法,明確指出了生產力的不斷發展是革命產生與發展的始動因素,只有在生產力不斷發展,并與現存的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發生沖突的基礎上,革命才有可能發生,并取得發生發展的合理的根據。
20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從總的趨勢看一直處于曲折發展之中。具體來說,1911~1922年不斷發展,1923~1925年發展出現一些危機、1925—1931年是相對發展較快的幾年,1931—1935的四年間,由于種種原因,不少民族資本企業陷入困境,不過自1935年底始,大部分民族資本主義企業走向恢復發展的階段,1936年及1937年又有較大的發展,隨后則由于日本的大規模侵略而打斷中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進程。從部門上看,一些新興的行業得到較大的發展。如化學工業中的橡膠、酸類制品發展極快,機器造紙業、水泥、火柴業、電力、通訊、交通運輸、金融、現代商業等基本處于較順利的發展之中,沒有出現很大的波折,但過去一向發展較快的幾個行業如棉紡織業、絲織業、卷煙業等基本陷入困境中,但在曲折中也仍有一定的發展。所以,這十年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并非全面的蕭條與破產,從整個來看,是資本主義經濟發展較快的時期。
外國在華的產業資本及官僚資本在總的數額上仍超過了民族資本,不過民族資本在1920—1936年間,雖然經歷了三十年代的經濟危機,但其產業資本的增長率仍達8.21%,專就工業而論則達9.37%,比外國在華產業資本的增長率4.31%和官僚資本的增長率7.78%(均不計東北)都高。(許滌新、吳承明主編:《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726—727頁。)
但是,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卻異常的艱難,面臨種種障礙,其中根本障礙還在于外資在華企業及外國商品的競爭與沖擊和國民黨政權對民族私人資本的壓制,自然也包括前面所述的封建土地制度及鄉村危機。
雖然外資在一定時期曾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產生與發展起過刺激和示范作用,但隨著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逐步發展,刺激示范作用逐步為壓迫與競爭所代替,尤其是1929年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爆發經濟危機以后。西方國家一方面大力向華傾銷剩余商品,另一方面則提高進口關稅,以保護國內工業的發展。在中外貿易中,中國入超值日益增大。1931年入超升至81641萬多元。(《財政年鑒》上冊,第444、463~476頁。)二三十年代,在華外資在煤礦、鋼鐵、石油、電力及卷煙等許多行業占有絕對優勢和壟斷地位,(詳見嚴中平等輯:《中國近代經濟史資料統計資料選輯》,123~124、127~128頁。)從而構成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進一步發展的重大障礙。中國發展較快的新興行業,也多是在與外資拚死競爭下求得一定發展的。如范旭東創辦的永利制堿公司,在發展的過程中就是歷經磨難才有所進步的。而一度發展的民族橡膠業,則在日資企業及走私制品的打擊下瀕于破產。(《上海民族橡膠工業》, 第35頁,中華書局,1979。)
脆弱的民族資本企業面臨強大外資企業的競爭,亟需政府的大力扶植,但南京國民政府并未表現出應有的熱情。國民黨政權與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的關系是值得深入研究的一個問題,但據現有研究成果看,該時期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從根本上講不能歸功于國民黨政權,盡管它也起到過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比較起來阻礙作用更大。縱觀國民政府十年的所作所為,它不僅無力解決中國社會所積聚的各種社會矛盾,全面推進中國社會的現代化,而且在根本方面排斥著民族私人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
收回關稅自主權是全國人民的要求,也符合國民黨政權的利益,但是并未完全達到有效保護民族資本的目的。當時日資是中國民族工業發展的最大障礙,但國民黨為了盡快實現關稅自主的目標,不惜犧牲民族利益與民族資本的利益,與日本妥協,答應日本的一些特殊要求,以換得日本對中國關稅自主形式上的承認。在關稅稅率的制訂方面,國民政府對日本棉織品、面粉、海味等62種產品,在1~3年內保持了原有低稅率;再就是關稅改革以增加政府財政收入為主要目的,對奢侈品等稅率提高較少,而對中國民族資本工業發展需要的機器產品等卻加以重征。1932年生活必需品的進口稅率水準約為從價的30.3%,奢侈品的進口稅率為從價的32.4%,而1933年必需品的平均稅率提高到53.9%,奢侈品只不過為34.3%。1936年,前者為83.7%,后者仍只有38.1%。(鄭友揆:《我國關稅自主后進口稅率水準之變遷》, 第30頁,商務印書館,1939。)所以國民黨政權幾次修訂稅率,主要的著眼點是保證關稅收入的增加,并不是真誠地、盡力地利用關稅稅則保護本國民族資本工業的發展。
從國內稅收政策來看,1927~1937的十年中,民族資本企業的稅負呈不斷增加的趨勢,超過了北洋時期。裁撤厘金本是為廣大工商業者所歡迎的,但為補償裁厘而帶來的政府稅收減少問題,國民政府設立了特種消費稅。特稅消費稅種類繁多,節節設卡,成了變相的厘金。統稅的實行,從理論上講,簡化了收稅手續,可以避免苛捐雜稅的泛濫,且外貨除納進口稅外,也要同樣交納統稅,這將有利于國貨的競爭能力。但問題的關鍵在于稅率的高低。實行統稅的行業,稅負較過去普遍加重。以卷煙統稅來說,1928年開征統稅后,起初稅率為22.5%,以后不斷提高,至1931年增加到50%。在這3年期間,稅率提高了100%以上。(捐稅繁重與民族產業之沒落),《東方雜志》第31卷第14期。)火柴統稅高達成本的60%,水泥稅捐占售價的53%。(《財政年鑒》第1編,上冊,第949頁。)國民政府的統稅收入不斷增加,并在國民政府稅收中所占的比例不斷上升。1927年統稅占國民政府所有稅收的比例為2.9%,1931年則占14.4%,1934年1935年分別為27.6%和39.6%,而民族資本企業此時正處于發展危機之中。(楊蔭溥:《民國財政史》, 第47頁,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
還需注意的是,對于該時期國民黨政權采取的一些曾對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有促進作用的政策與措施, 諸如關稅自主、裁厘改統、幣制改革等,不能孤立在去考察,應把握國民政府經濟政策中影響全局的主導傾向,從而把這些政策放在總的傾向中作整體分析與評價。縱觀國民黨政權的十年經濟政策,其主導傾向是大力發展國家壟斷資本主義,只有從這一總體傾向出發,去理解國民政府的諸多政策,才可能得出一個客觀公正的評價,也才會明了,那些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措施,同時也是國民黨政權壟斷全國經濟諸政策中的一個組成部分和一個步驟,而不是從根本上為民族資本主義發展掃清障礙,開辟道路。(詳見杜恂誠:《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 第256~283頁,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正因為有不同的主觀動機,才使得一個具有多種作用與影響的政策,在實施的過程中,日益朝著不利于民族資本主義進步的方向發展,而逐步成為國民黨政權擴張官僚壟斷資本主義方案中的實際步驟。
總之,以蔣介石為核心的南京國民政府,是一個失去革命精神、維護少數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的軍事獨裁政權。雖然它容納了一些民族資產階級人物,但在當時多是蔣介石為方便獲得軍費或裝點門面而采取的權宜之計,在國家決策中不起作用。蔣介石政治上依靠傳統的姻親關系、地緣關系、師生關系等,結成幫派,大力發展軍事力量,實行封建的家族式的獨裁專制,經濟上則依賴對民族資本的剝削及發展國家壟斷資本,在農村則繼續維護封建的大地主土地所有制,所以它所維護的是代表大地主大資產階級利益的舊制度,與新質的生產力發展的要求背道而馳,沒有也不可能從根本制度上為民族資本主義的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社會發展環境。
正是由于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不斷發展,先進生產力的代表者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力量才日益壯大,才有可能由日益不滿國民黨的反動統治而敢于與之抗爭。中國民族資產階級對南京國民黨政權經歷了了一個由信任至失望、由依附到抗爭的過程;而無產階級及其先進代表中國共產黨則在革命聯盟破裂后,堅持革命精神對反動制度進行了全面的革命。自然一種新的生產方式還會促進新式教育的發展,導致生活方式的變革,促發新的價值觀念的生長與發展,這一切都會形成對占統治地位的舊制度、舊風俗、舊道德的沖擊,構成中國革命的社會基礎。限于篇幅,下面主要從民族實業資產階級不滿國民黨的專制統治、要求參政與政的歷史事實中,加深理解新民主主義革命代表先進生產力發展要求的進步性。
中國民族資產階級為維護自身權益曾進行過不同方式的抗爭。在北洋政府統治時期,以商會等組織為依托,民族資產階級積極參政議政,曾一度在政治舞臺上叱咤風云。國民黨當政后,民族資產階級一度幻想在新政權中占有一定席位,但歷史很快證明,國民黨政權實行的是一黨專政,不容其他階級與階層分享政治權力。民族資產階級的斗爭主要表現在抵制國民黨政權增捐加稅、要求參政預政、反對帝國主義侵略等幾個方面。
1927年后民族資產階級一度將自己的希望寄托于蔣介石身上,但是,民族資產階級從投靠蔣介石集團的第一天起,就背上了沉重的經濟負擔,其后稅負不斷增加的事實不斷打破民族資產階級人物的幻想,抵制國民黨政府及各地軍閥增捐加稅,就成為資產階級各類團體所從事的主要活動之一。早在1927年,不少企業就對蔣介石的一次次財政攤款進行了抵制,拒絕認購庫券。為此蔣介石采取殺雞給猴看的方法,以榮宗敬甘心依附孫傳芳為由,查封其產業,并通令各軍偵緝,直到榮氏認購庫券50萬元才取消通緝令。(《榮家企業史料》上冊,第196~197頁。)民族資產階級不滿于國民政府的對日妥協,上海市商會等團體曾掀起反對1934年國定稅則的運動。(《四川經濟月刊》,第2卷,第1期,1934年7月。)這一時期,有關實業界向政府請愿要求降低稅率活動的記載特別多。可見,1927~1937的十年間,雖然國民政府在實現關稅自主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離民族工商業者的要求相差很遠。
為從根本上創造有利于自己發展的優越環境,民族資產階級以各種形式進行了爭取民主參政權利的活動。一個突出的例子是1928年全國商會聯合會獨自預選10名立法委員,請求從中遴選5人。(《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28~1937), 第566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該事件顯示了民族資產階級強烈的參政與政愿望,這自然為實行一黨專政的國民黨政權所拒絕。民族資產階級各團體為爭取商會的選舉權,也一度與國民黨政權展開了斗爭。(《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28~1927),第576頁。)九一八事變后,民族危機加深,國內要求民主的呼聲日益高漲,民族資產階級及其報刊紛紛抨擊國民黨政府的“一黨專政”,要求實行憲政,還基于自身的利益和民族的前途,積極參加了一系列反帝愛國與抵制內戰運動。一二八事變爆發后,上海一大批民族資本企業毀于炮火,對國民黨政權的不滿日益增加。他們更加積極地投入到反對國民黨專制獨裁及抗日行列中。1932年4月,上海成立的中社開會討論參加國難會議之事,黃炎培、史量才、劉鴻生、榮宗敬等多人,宣布不參加國民黨主持的國難會議,以示抗議,同時要求國民黨政府確保人民之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之自由,承認各政黨得并立自由活動,實行地方自治,籌備憲政,限八個月制定民主主義之憲法宣布之。(《救亡通信》第11號,1932年4月22日。)集中反映了當時廣大民族資產階級乃至全國人民的政治主張,表達了民族資產階級追求獨立、自由、民主的理想與愿望。1932年5月,在上海的全國商聯會和市商會、銀行公會等發起組織“廢止內戰大同盟”。
雖然民族資產階級認識到一些問題的實質,但他們還是不敢參加革命,只能提出一些一廂情愿的改良的辦法,自然難以實現。但是基于自身發展的種種困境及國民黨政權對外妥協對內壓榨的政策,民族資產階級的思想認識有了極大的提高。身為國民政府官員的民族實業資本家穆藕初思想的變化,具有一定的代表性。1930年在國立暨南大學演講中指出中國棉業不發達的致命傷為帝國主義的經濟侵略。(《穆藕初文集》,第332—337頁。)對農村衰落也有較深的認識,指出中國農民的致命傷在于全國農村中之農蠹。(《穆藕初文集》,第468頁。)在這里,對“農蠹”即農村的土豪劣紳的封建剝削與壓迫是導致廣大農村衰落的根源有了一定的認識。1932年發出了改良政治的呼聲。“非改良政治不足以抵抗帝國主義列強之侵略,不足以保護我尚在幼稚時期之紡織工業。”(《穆藕初文集》,第352—353頁。)以后又提出,中國進行生產建設,必須先解決一些先決條件,“對內急應鏟除建設之各種障礙,對外則應解除帝國主義對中國之束縛是也。”(《穆藕初文集》,第483頁。)至此,身在官場、且以實業救國為志的民族資產階級人物,經過多年的觀察與思考,對中國社會問題的認識達到了一個高度,認識到國民黨政權與北洋軍閥毫無二致,其對國民黨政權所抱的幻想日漸破滅,得出了要發展實業,必須首先掃除經濟發展前進的一切障礙,必須推翻帝國主義的統治。資產階級實業家兼民主派人士章乃器的思想認識更為徹底。在《改造中國經濟的正路與歧路》一文中指出:帝國主義與封建勢力,利害相同,阻礙民族中心經濟建設的進行,要搞經濟建設,就必須解決一個前提即先消滅帝國主義和封建勢力。(《章乃器文集》上卷, 第186頁,華夏出版社,1997。)1937年撰文指出:“農村的破產和中產階級的沒落,表明中國的社會必然的要發生革命,也可以說革命早已經開始。”(《章乃器文集》第107頁。)
這些資產階級人物通過對中國社會的分析及對國民黨政權統治的觀察,得出了與中國共產黨人基本一致的認識,值得深思。可見在舊中國,要發展生產力,首先要實現政治變革,這是歷史的必然要求。由此也可明了,中共領導的革命決不是少數人主觀意志的產物,而是中國生產力發展的內在要求,從根本上符合民族資產階級的愿望與利益。不過,由于中國民族資產階級一直在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的夾縫中生存,其自身有難以克服的缺陷,不愿也無能力領導中國革命的主力軍農民與工人,在反帝反封建的戰場上沖鋒陷陣。近代中國的國情決定了,推翻帝國主義封建主義與官僚資本主義,為中國民族資本主義和鄉村生產力發展開辟道路的歷史使命,只能落在先進的無產階級身上。無產階級領導的旨在推翻帝國主義與封建主義統治的民族民主革命,實際上正是在完成民族資產階級想完成而靠其自身而無法完成的使命,從而為當時中國先進的生產力–––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掃除障礙,開辟道路,使其由依附被動的發展狀態,導向獨立自主的發展軌道。也正是由于以上所述的理由,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民主主義革命有了其繼續進行的內在根據。
自然,中國共產黨人對于當時歷史賦予自己的使命––––為發展受阻的現代生產力開辟道路、更快地實現中國社會現代化,經歷了一個曲折的認識歷程,一度犯了左傾錯誤,但此時革命的基本點始終未偏離反帝反封建這一根本任務,同時這一時期以毛澤東為首的一批共產黨人對革命的性質與意義也不乏清醒而正確的認識,使得左傾錯誤得到一定的限制。因此,并不能因左傾錯誤的發生而否定其為生產力開辟道路的歷史作用。
總之,新民主主義革命既與傳統社會的危機有關,更與社會現代化因素的進步相聯,是鄉村生存危機與新生產方式不斷進步及受阻綜合作用的產物。把新民主主義革命理解為單純的農民運動或者純粹的資產階級革命甚至社會主義革命都難尋其本質。基于中國國情而進行的新式資產階級革命,既是為了消除傳統生產方式內在的矛盾,最大限度地推進農業發展及農村社會的重建,同時又為新質生產力和生產關系順利成長開辟道路。因此,新民主主義革命是中國歷史的必然選擇,是為了解放與發展生產力和實現社會的現代化。在當時歷史條件下,中國共產黨領導的革命最大限度地將二元對立的社會整合在一起,最終實現了民族獨立和國家統一,建立了一個人民當家作主的注重公平的新民主主義政治制度,為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張靜如. 唯物史觀與中共黨史學[M],長沙:湖南出版社,1995.
[2]章有義. 海關報告中的近代中國農業生產力狀況[J],中國農史,1991(2).
[3]珀金斯.1368~1968中國農業的發展[M],上海譯文出版社,1984.
[4]吳慧.中國歷代糧食畝產量研究[M],北京:農業出版社,1985.
[5]王亞南文集[M],第3卷,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8.
[6]趙德馨.中國近代國民經濟史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
[7]嚴中平.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M],科學出版社,1955.
[8]章有義.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M],第2輯,三聯書店,1957.
[9]毛澤東文集[M],第1卷,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996.
[10]馬克思恩格斯選集[M],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
[11]楊蔭溥.民國財政史[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85.
[12]杜恂誠.民族資本主義與舊中國政府[M],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1.
[13]天津商會檔案匯編(1928~1937)[M],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
[14]趙靖.穆藕初文集[M],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
[15]章立凡.章乃器文集[M],上卷,北京:華夏出版社,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