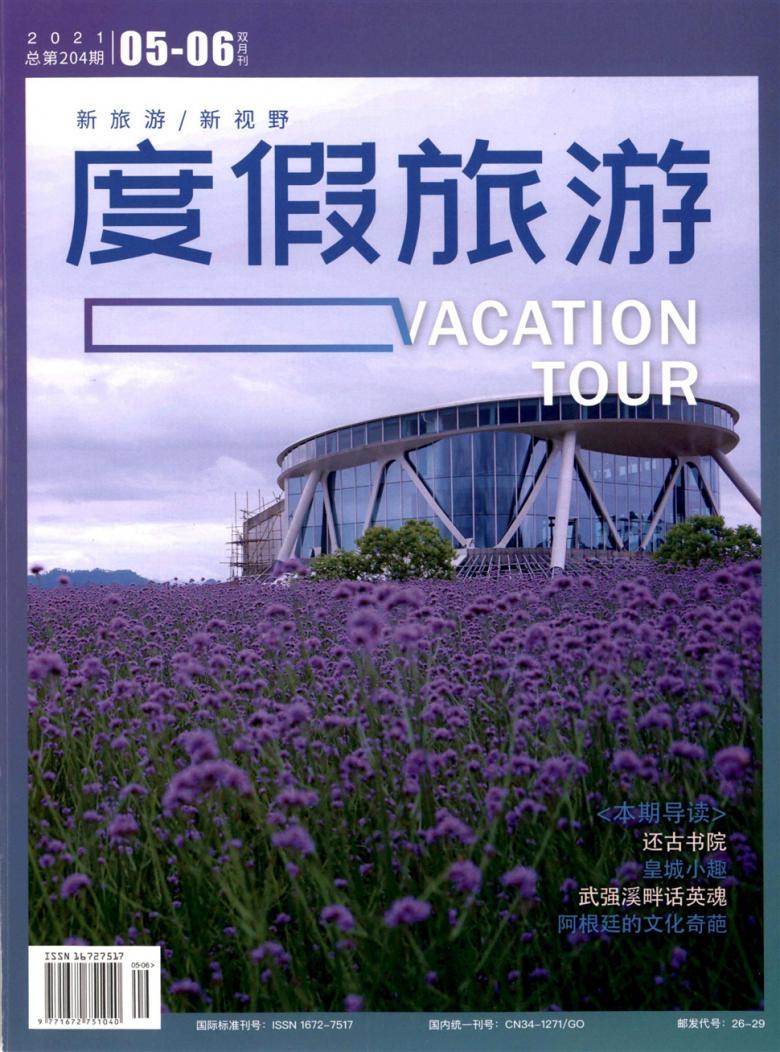封建地主制下的小農經濟(二)——傳統農業與小農經濟研究述評(下)
葉茂 蘭鷗 柯文武
四.小農經濟與商品經濟
八十年代初,有的同志提出:在歷史上和理論上,都有兩種小生產。一種是自然經濟的小生產,曾構成漫長的封建經濟的基礎,特點是自給自足,馬克思《路易·波拿巴的霧月十八》中分析的法國小農等,即屬此類。另一種是商品經濟小生產,其歷史雖可追溯到原始社會瓦解時期,但在整個古代社會只處于占統治地位的自然經濟的縫隙中,直到封建社會后期,才獲得典型的形式,《資本論》中論述的作為資本主義產生的直接前提而為資本主義剝奪的小生產即屬此類。只有商品經濟的小生產的充分發展才能走向社會化大生產。混淆兩類小生產,否認小商品經濟的合法性和進步性,是導致左傾經濟理論的根源之一。[19] 當時也有人提出質疑,認為從小生產的地位和性質看,均無劃分兩種小生產的必有。馬克思的《霧月十八》和《資本論》提到的小農并無本質區別。小商品生產從來沒有也根本不會取得統治地位。它大量存在于自然經濟向商品經濟過渡時期,但在價值規律作用下又會不斷分化。[55]不過,兩種小生產區分還是被不少學者所接受,并作為分析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的一種工具。但在我國封建地主制中,尤其是它的后期,何種小生產占居主導地位,商品經濟小生產是否構成過獨立的發展階段,則有不同的認識。
陳家澤認為,“在歐洲中世紀后期,商品經濟小生產得到了幾乎是純粹的自身形態的發展,而在中國封建社會中,則始終只是作為自然經濟的一種補充而存在”。但占主要地位的自然經濟小生產又呈現出不完整不純粹的形態。這是因為中國封建社會以一家一戶為基本生產細胞,自給程度遠遜于西歐中世紀莊園,故小商品生產很早就作為自然經濟小生產的補充而存在。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的這種不完整性和變通性導致商品經濟的早熟及其對自然經濟的依附和從屬。他認為這種商品經濟完全不受價值規律的支配,是“非商品生產的商品經濟”。[47]龍登高認為宋代隨著個體性綜合型生產力趨于成熟和小農家庭獨立經營能力的加強,小農與市場聯系更密切,代替了前此與鄉里宗族的聯系而成為小農再生產的外部條件。但在小農經濟基礎上形成的農村市場屬于商品內循環類型,并不能誘發個體家庭突破自給性生產,在某種程度上還制約了農民從事商品生產的動機。[16ab]薛虹贊成“小農經濟是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相結合”的提法,但強調明清小農經濟中小商品經濟的普遍性及其在整個社會經濟結構中的決定性作用。他認為明清以前小農經濟的商品生產基本以生產使用價值為目的,商人資本尚未進入小農經濟領域,可視為自然經濟產物.自給性生產的補充;明清商業資本進入小農經濟領域,控制小農生產,價值規律起支配作用,已超出自然經濟范疇,不能再視為自然經濟的補充。他認為明清小農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封建剝削苛重.商業資本滲入農村和人稠地少相互誘發促成的,是由于農業生產不足追求的補償。其運營總趨向是下滑的傾勢,是生產投入增長率遞增而產品價值增長率遞減的二律背反的生產。在這基礎上中國不可能發展為資本主義。[90]陳慶德不同意把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相對立作為劃分資本主義和封建主義的基本標志之一,不同意把清代商品性手工業簡單劃歸自給性典型的耕織結合,他認為油價農業生產向商品生產轉化,手工業商品生產向農村家庭化擴展,兩個過程融合在一起,把中國的小農毫無例外地卷進商品經濟的體系中。它的根本動力是日益深重的農業危機,即人口激增形成對土地的沉重壓力下,為補充農業生產不足維系小農生存而發展起來的。“這種與自然性農業結為一體的商品生產正是個體地域性經濟中商品經濟形式發展的歷史特點。”陳鏗則強調了封建社會中從自然經濟到資本主義商品經濟之間小商品經濟形態的獨立存在和歷史進步性。[44]柯建中也論述過明清從自然經濟到小商品經濟的轉化。[61]
在小農經濟中,區分自然經濟小生產和商品經濟小生產是有一定意義的,但如把這種區分絕對化,則無論在理論上或實際上都未必妥當。一般而言,小農經濟自始至終包含著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兩種經濟成分,不過在不同國家.不同地區.不同時期.不同階層,兩者的比例各不相同罷了。根據這種比例的不同,我們可以把小農經濟區分為不同類型。總的發展趨勢是小農經濟中自然經濟成分的縮小和商品經濟成分的增加,相應地是自然經濟小生產類型的縮小和商品經濟小生產類型的增加,但終封建之世,小農經濟并沒有完成從自然經濟小生產向商品經濟小生產的轉化。《資本論》論述的小塊土地所有制的農民經濟(自耕農),從其農產品大部分供自身消費,谷物價格不受平均利潤率的支配看,也并沒有完全擺脫自然經濟的性質。我國封建社會后期小農經濟中的商品經濟成分有較大發展,但是否已構成受價值規律支配的獨立的小商品經濟的階段,仍然需要更多的研究和論證。我們下面的介紹還將涉及這一問題
在海外學者中,黃宗智對華北和長江三角洲的小農經濟的研究是影響比較大的。他著重批評了認為商品化與小農經濟不相容和必然導致近代化的觀點。他在《華北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書中指出中國近代農村演變型式不同于西方,西方小農分化過程歸結為農村經濟的全面轉化;中國則在小農經濟范圍內發展,它所導致的不是資本主義的工業經濟,而是一個分化了的小農經濟。他認為家庭式農場(按,黃氏所說“家庭式農場”大體相當于我們所說的小農經濟)由于規模狹小和地租高利貸剝削的苛重,要依靠家庭手工業和傭工作支撐。但他不同意把中國家庭工業與小農耕作的結合視為自給自足自然經濟的基礎。他認為18世紀華北平原已高度商品化,小麥成為一種商品作物,棉花已廣泛種植,手工業在許多方面已超出為自家消費而生產的“自然經濟”階段,而成為市場經濟一部分。不是自足的自然經濟,而是商品化了的手工業對近代工業的入侵作了頑強的抵抗。這種商業化了的手工業,與其說是過渡到資本主義工業的跳板,不如說它是資本主義發展的障礙。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中進一步明確指出:商品化帶來的不是家庭單位的削弱,而是它的更充會完善和強化。它把更多的婦女和其它家庭成員吸收到生產領域,從事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男耕女織”實際上反映了家庭生產在商品化推動下的這種完善和加強,明清以來蓬勃發展的商品化為什么沒有導致近代化?黃宗智認為這是因為明清時代中國的商品化是在人口壓力推動下的過密型的商品化,不同于推動近代化發展的質變性的商品化。這種過密型商品化導致的過密型家庭生產,使用低報酬的勞動(低于市場上男勞力的工資)的家庭勞動力,形成一個依賴雇傭勞動無法與之競爭的生命力極強的生產體系,雖可提高總產量與總產值,每個勞動日的報酬則是逐漸遞減的。[93ab]
與上文提到的特定類型自然經濟論相比照,黃宗智的觀點可稱為特定類型的商品經濟論。除此之外,又有即區別于自然經濟又區別于商品經濟的交換經濟論。
崔曉黎通過對1929—1949年無錫清苑農戶家庭經濟及其與外部市場關系剖析,提出傳統農業是交換經濟的觀點。據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調查材料和老農對解放前生活的回憶,當時糧.肉.油.棉等能自給自足或大部自給,燈油.煤炭.煙.酒等則需用貨幣購進或支出。生產資料投入(種子.農家肥等)基本自給,靠貨幣購買的為數極少。農戶貨幣收入占總收入的比例,清苑為45.5%,無錫縣為70%。他把一個或幾個與農民日常生活最密切的市場所覆蓋的區域范圍稱為“市場社區”,反過來把這一區域內的市場稱為“社區市場”。清苑縣一個4000戶左右的市場社區貨幣流通總量約為一百萬元,在社區內和社區外流通部分各占64%和36%。在與社區外的貨幣流通中,30—35%為工業品。進入傳統農村社區市場的三大工業品是棉布.煤油和煤炭。洋布受到農戶中利用機會成本接近于零的家庭剩余勞動力生產的土布的頑強競爭,發展緩慢。煤油已基本代替農戶的食用油照明,因它物美價廉,且可省點地種別的。清苑燃料短缺,故廉價的煤炭有相當發展。崔曉黎在分析了這三種工業品替代傳統產品不同方式后指出:農民的生產.交易行為確實是處于一個大的廣義市場環境約束之下。傳統集市市場形成與人口發展同步,屬“人口密集成因”。市場有明顯歷史沿襲性,長期不變,表明農民對市場的內在依賴很高,農戶家庭經濟的自身運行,是建立在時時刻刻的比較利益之上的。因此,傳統農村社區經濟是一種交換經濟,它不同于工業社會的商品經濟在于它是一非利潤約束市場,沒有平均利潤率制衡機制,交換的實際上是使用價值等等。從原始社會的比較經濟,到農業社會的交換經濟,再到工業社會的商品經濟的發展是基于一種比較效益的意識和行為。馬克思說農業社會是自然經濟,這是與工業社會相比較,從農業內部低商品率.農民自給自足部分很大這樣一個角度提出問題,而不是社會發展內在動務角度提出問題。所以自然濟與交換經濟提法并不矛盾。
五.商品率與剩余率
對我國小農經濟的商品率也有不同的計算。茲略舉數例:李文治最近估算明清各類地區各類農戶商品率:一.買布而衣地區30—50%;二.產糧為主兼植棉紡織地區,黃河中下游自耕農,售麥售布者約35—40%,只售麥類或只售棉布者,20—30%,租佃農交實物租者略減,交貨幣租者30%以上;長江流域自耕農約30%或更多,租佃農約20%,交貨幣租者超過30%;三.植棉紡織專業區或專業戶,低者60—70%,高者80%以上;四.棉蠶以外其它經濟作物與糧食作物混合種植區,多為50—60%。他據此對該時期地主制經濟是否仍用自然經濟這一術語概括提出疑問。[35c]二十世紀三十年代的社會調查,農家經濟商品率常達50%以上。近年杜昌修整理發表1936年對定縣.南京.肖縣農村的調查材料,其農民經濟商品率分別為64.4%,62.04%.66.96%。[48]曹幸穗對舊中國蘇南家庭農場經濟研究的結果則是:糧食商品率約為收獲量的25%,棉花商品率達90%以上,實物收入與現金收入各占50%左右。[81a]上述農家商品率,均系指農副產品中出售部分占總產量或總產值的比例。對于近世學者調查或估算的相當高的農家商品率,不少學者指出其中包含了虛假成分。如盧鋒指出:農產品商品化的發展應以勞動生產率的提高.生產者剩余產品量的提高為前提。但近代中國往往是耕作規模較小.勞動生產率較低的農戶,商品率水平反而比較高。這是因為他們為生活所迫,不得不出售自產細糧,換回粗糧充饑;為了完租還債,又往往在收獲時賤價出售農產品,冬春青黃不接時又要買回農產品維持生活。這種同一生產者對同類產品賣出復買進的市場行為,雖然在統計上增大農產品交換比重,卻不能真正提高農產品商品化水平。[14]有人稱中國近代農村商品經濟為“饑餓的商品生產”.“虛假的商品流通”。[1]或提出應將這類與剩余產品無涉的商品交換排除在商品率之外。吳承明對國內市場商品量與商品率的估算方法與此不同。以糧食為例,其商品量是非農業人口用糧,經濟作物區人口用糧與商業用糧(釀酒.上漿等)的和,商品量除以總產量為商品率。這樣算出來的糧食商品率,基本排除了農民之間在地方市場上的品種調劑和余缺調劑,以及為完租等被迫出賣.日后仍需反銷的口糧,比較接近商品經濟發展的實際水平。按此法估算,鴉片戰爭前糧食.棉花.棉布和絲的商品率分別為10.5%.26.3%.52.8%.92.2%。在國內市場中商品值比重前三位分別為糧食.棉布和鹽。吳承明認為,鴉片戰爭前的國內市場是一種以糧食為基礎,以布和鹽為主要對象的小生產之間交換的市場模式。作為農村自然經濟解體的基本指標的糧食商品率僅有10.5%,經調整(排除引起產品單向流動的租賦等因素)后不到10%,商品糧中用于遠距離運銷的只占20%左右。棉布商品量雖大,但主要是農家自用有余的布,農村中的糧布交易屬農家間的品種調劑,是耕織結合的另一種形式,未脫離自然經濟范疇。總之,當時農村基本上仍處于自然經濟狀態。[28]徐新吾也認為,近代農產品的商品化雖有發展,但在農業生產領域中,自然經濟始終占優勢。據他的估算,農業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的比例,1920年為38:62,1936年為44:56。舊中國農村已以市場經濟為主的說法難以成立。近代中國農產品的商品化,受糧食生產長期停滯以至下降趨勢的嚴重制約,和出口貿易興衰的支配,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貧困的商品經濟”。解放后糧食產量雖然增加,但由于農民生活改善和飼養業的發展,糧食商品率反而下降,即其反證。[71b]
有些世界史研究者根據他們對歷史唯物主義的新理解,強調以勞動者為主體的現實的人的物質力量 與精神力量的發展是歷史前進的終極原因,倡導開展中外封建社會勞動者狀況的比較研究,也對我國封建社會小農的勞動生產率.凈余率和商品率作出估算。龐卓恒認為中國封建時代的農民,以他們的能力可能達到的程度而言,勞動生產率是相當高的。他據《管子·治國》“一夫為粟二百石”推算,西漢一個全勞力已能年產糧2700公斤,高于12—13世紀英國全份地農奴的勞動生產率(2300公斤),以“中農挾四”算,一個全勞力剩余產品已達80%,也高于英國全份地農奴(77%)。但英國平均地租率為21%,凈余率為26%,中國農民除唐代受田農民有10%的凈余率外,大部分時期,剩余產品全被剝削掉了,僅能勉強維持簡單再生產,無力掀起促成自然經濟解體.封建制度向新的社會制度過渡的歷史變遷。[61b]侯建新根據他對鴉片戰爭以前浙江地區農民家庭收支的計算,得出商品率11%,擴大再生產部分及凈余率為7%的結論。(以后又調整為商品率14%,儲蓄率6.7%)它大大低于英國十三.四世紀的水平(商品率53%,后調整至45%)的水平,根本無法沖破封建自然經濟結構。[65ab]這里的凈余率為收支相抵的余額,商品率為進入市場部分。據侯建新計算,農戶收獲糧食除地租.口糧和生產性支出外無剩余,能進入市場者僅為部分棉布,故與李文治等人估算相去甚為懸殊。簫少秋和陳景彪也具體分析了15—17世紀蘇松地區的農戶生活狀況,據他們計算,16世紀蘇松農戶凈余率為4—30%,出現了稀疏的資本主義萌芽,17世紀米貴布賤,加上賦役地租率上升,各類農民均無剩余,農村商品經濟的資本主義萌芽遭到滅頂之災。[78]
王家范.謝天佑對我國封建社會自耕農的收支情況作過估算,其中農民占有剩余勞動余額一項與上述學者所言之凈余率一致,亦可供參考。茲將其估算表列如下:
五口之家 漢 代 唐 代 清 代
(二大三小) 收支 占總產% 收支 占總產% 收支 占總產%
面 積 50(漢大畝) 30(唐畝) 10畝
總 產 3×50=150 100 1.5×30=45 100 3×10=30 100
口 糧 90 60 28 62.2 20 67
農 本 10① 6.7 3.8③ 8.5 4.5 15
賦 租 19② 12.6 7④ 15.5 5 16
(衣著) (15) 10 (3.5) (7.8) (2.34) (7.8)
衣著不算 31 20.7 6.2 13.8 0.5 2
扣除衣著 16 10.7 2.7 6 (-1.84) (-5.8)
① 包括種子飼料等。
② 包括田租.口算賦.更賦.芻藁.未包括徭役
③ 包括種子.飼料.農具損耗等。
④ 包括田租.庸調.地稅
上表表明,每一朝代自耕農的實際占有土地面積與最低必要耕地限量幾乎相同,在影響自耕農占有剩余勞動量多少的諸變量(畝積.畝產.口糧.農本.法定賦稅)中,雖然單產有所增長,但由于畝積縮小.法定賦稅量增大,綜合的結果是農民占有的剩余勞動余額反趨下降。[8]
對龐侯等人的估算和比較,學術界有不少不同看法。如畢道村按宋代畝產309市斤.每戶占地30畝計算,得出每個農戶年產糧8343市斤,為十四世紀英國中等農戶的1.8倍。佃耕30畝的客戶,扣除50%的地租和口糧.種子后,有余糧1521斤,為其收入的36%,遠遠超過西歐中等農戶。明清農民的境況惡化是人口增加.耕地不足.土地兼并等因素導致的。[25b]就我國封建社會實際情況看,農民出售的農產品往往不僅僅是他們生產生活消費后剩余的部分,而農民交納的地租賦稅,也會有部會轉化為商品,因而,按農民“凈余率”推算商品率會出現誤差,但以勞動生產率和凈余率作為商品經濟發展的真正基礎,仍不失為觀察這一問題的有意義的視角。
六.價值規律與勞動消費均衡公式
為了正確判斷封建地主制下的小農經濟中商品經濟的發展程度及其性質,除了要對農民經濟的商品率作出量的估計外,還應進一步研究小農經濟的有關運行機制,考察價值規律對小農經濟作用的范圍.程度和特點。
對于封建地主制下價值規律的作用,胡如雷作過比較系統的分析,他認為封建社會雖然 自然經濟占支配地位,但始終存在簡單商品生產,價值規律不但對商品生產的商品,而且對非商品生產的商品,即對整個商品經濟領域起著制約作用。但商品價值通過價格的擺動而測定,需要一個相當長的過程,而價值規律對商品經濟所發生的作用,又受到很多封建特權和其他因素的干擾和阻礙。如農民豐收時低價出售糧食,歉收或青黃不接時,不計成本低價出售手工業品以換取谷食,又如貨幣征稅遠遠超出商品經濟的實際水平時,納稅人被迫出售產品,造成供過于求和谷價病態下落,都會對價值規律的作用產生干擾和破壞。價值規律能對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在各經濟部門中的分配起到一定的調節作用,但這種作用也受到很大限制。當農民為出賣而生產一部份產品時,不可能不考慮市場的價格而決定自己的生產安排,盡量選擇價格對己有利的生產項目,并根據各種商品價格的變動調節各項生產比例。但農民經濟中占大頭的自給性生產,則完全取決于自己的實際需要,不受價值規律的任何影響。[67]方行根據清代前期的史實,對價值規律在封建社會農民生產中的作用作了探討。他指出清代前期棉.絲.煙.蔗等商品性農產品和棉紡織.絲織.造紙.榨糖.編織等家庭手工業商品生產有頗大發展,根本原因在于它們比種糧有利,體現了價值規律對農民商品生產的調節作用。但封建社會中價值規律作用受到種種限制。如用作租賦的糧食生產,農戶經濟中的自給性生產都不受價值規律制約。農民不論從事自給性生產或商品性生產,均由家庭勞動力負擔,就自給性生產而言,只要能養家糊口,即會耕種土地,是否有剩余產品,不表現為經營土地的界限。就商品性生產而言,家內勞動力的生活費用是可以不予考慮的固定開支,只要家庭手工業產品能收回原料費不略有盈余,這種生產就會繼續下去。而其商品的市場價格根本不必提到與其相等的水平。因此,價值規律對農民商品生產的調節作用,是十分遲鈍的。氣候.土壤和耕地面積等不優裕的自然條件,也成為價值規律發生作用的限制的因素。方行認為“從封建社會小農經濟的整體看,農業生產中土地資源和勞動力資源的配置,還主要是取決于農民對直接使用價值的需求結構與數量,而不是取決于價值規律。”但他又認為,全部農民的自給生產與商品生產的比例關系,是由價值規律來實現的。[10d]
一些主張秦漢是古典經濟的學者認為漢代價值規律已能發揮其調節生產并維持社會分工的作用。如秦暉認為,“價值規律的調節作用是通過利潤率的平均化來體現的,整個經濟在動態平衡中形成平均利潤率,并借以維持社會分工不致失常”。《史記·貨殖列傳》:“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就是漢代已形成平均利潤率的明確記載。[73]薛平栓不同意這個看法。他指出漢代和后世都存在農民“棄本逐末”現象,這是因為市場機制尚不建全,沒形成平均利潤率,致使商業利潤高于農業利潤的緣故,“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就是這種情形的反映。[88]
關于上述諺語,也有人認為是反映了價值規律發生了調節勞動力和生產資料分配的作用。胡如雷對此亦有分析,認為經營工商業比經營農業有利是各種因素造成的(如經營農業所需墊支較大,生產周期較長,稅負重而難以逃避等),基本上與價值規律無關。[67]葉茂則指出:“由于商品經濟既有發展又不夠發展,由于流通在相當程度上獨立于生產,沒有能夠形成發達商品經濟社會那樣的支配整個社會經濟的平均利潤,農民經營既沒有平均利潤為最低界限,商人贏利亦不受平均利潤的制約,商品價格遂在農副業生產和商品流通兩端發生了方向相反的對價值的偏離;農民出售農副產品利益經常受損,商業利潤卻居高不下。農工商之間這種比較利益差距與其說反映了價值規律起作用,毋寧說反映了價值規律的作用被扭曲,無法發揮其正常作用。”[15]
以上是主張中國封建地主制經濟以自然經濟為主的學者的有代表性的意見。這種意見與自然經濟主導論完全一致,是不言而喻的。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主張明清以后我國商品經濟有了很大發展,或者徑已進入商品經濟階段的學者,也并不認為價值規律在當時社會經濟中已起支配作用,他們把謀生而不是謀利作為小農經濟活動的第一原則。下面舉兩個例子:
陳春聲.劉志偉認為,清代太湖流域.珠江三角洲等地區,商業性農業已有相當程度的發展,農產品商品率達到較高水平,許多農戶的生計已同市場有較密切聯系;十八世紀廣東區域市場結構的有機性和市場功能的有效性,甚至可以與同時代的法國相媲美。但即使是與市場聯系最密切的農戶,其生產經營活動也仍是以生活上的滿足和群體和諧為根本目的。市場上某種農產品較優裕的價格,或者也會對他們產生一定吸引力,使他們改種這一作物。但他們作出這一選擇的內在驅動力,不是這種作物作為商品投入市場后可能帶來的利潤,而是維持家庭生計的需要。農戶收益要經過市場交換才能實現,收益大小也取決于市場價格,但對生產資料的撥付使用和勞動力的投入,卻沒有也不必要根據市場價格來核算。土地收益率的提高是以更多的物資和勞動力投入來獲得,至于由此而可能導致的勞動生產率降低或利潤(如果有的話)下降,則一般不會被考慮。這種現象,陳.劉稱之為“農戶經濟活動的非市場導向性”,把它和所謂“整體市場活動的非經濟導向性”作為清代經濟運作的兩個特點。并認為這些特點的形成不能單從經濟層面.而應從我國傳統文化中尋找其根源。[45]
如前所述,黃宗智認為明清以來的中國小農經濟已充分商品化,但他也強調小農經濟是維持生計而不追求利潤的經濟。在《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一書中,黃氏提出區分不同階層小農的綜合分析法,自稱綜合了以舒爾茲為代表的形式主義.以蔡雅諾夫為代表的實體主義和馬克思主義三種農民學理論。認為革命前的中國小農具有三種面貌,既是追求利潤者,又是維持生計的生產者,當然更是受剝削的耕作者。富農與經營式農場主較象前者,佃雇農更像后者,而自耕農則以中者相似。認為馬克思只談階級斗爭,自然是一種誤解,經營式農場主也難以劃入小農經濟范疇,而自耕農和佃雇農在某種意義都是維持生計的生產者。在《長江三角洲小農家庭與鄉村發展》一書中,黃氏進一步指出:“長江三角洲農村經濟的商品化不是按照舒爾茲的邏輯,而是按照蔡雅諾夫的邏輯推的。”[93ab]
以西奧多·舒爾茲為代表的經濟學家認為傳統農業的小農是理性的,他們追求利潤最大化,對價格反應靈活,資源配置有效率,象特定條件下的資本主義企業家那樣行事。舒爾茲的理論在中國學術界有較大反響,農經界自不必說,史學界也有嘗試應用他的理論重新認識小農經濟的。如樊樹志即根據舒爾茲關于理性小農的論述,指出小農是在傳統農業范圍內有進取精神并對資源能作最適度運用的人。把小農和小農經濟描寫成一切陋俗惡俗的淵藪,未免有失偏頗。[88]不過,舒爾茲等的理性小農論實際上是以資本主義已有相當發展的條件下的小農為模特的。我國傳統小農是聰明的,有經營頭腦的,但很難認為他們象資本主義的企業家。故有人根據韋伯理論提出“廣義理性原則”。根據這一原則,傳統小農不是追求利潤最大化,而是以利益和效用的追求為其經濟活動的目標,具有創造性和在一定范圍的整體中尋求均衡的傾向。[40]
蔡雅諾夫的農民理論是以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國農村中廣泛存在的家庭農場為理論原型的。他認為勞動家庭經濟單位類型是獨立的經濟關系類型,不適合于反映資本主義經濟關系的古典經濟學等理論。其特點是不使用雇傭工資勞動,完全依靠家庭成員從事生產,以滿足自身消費為目的。它包括完全自然經濟的家庭單位和與市場交換有聯系的家庭單位。前者固然以家庭需求的滿足為經濟活動的依據,后者更關心取得最大的勞動報酬,但仍以滿足自身需求為最后原則,而遵循“勞動—消費”均衡公式。所謂“勞動—消費”均衡公式,是指以家庭內部勞動辛苦程度和消費滿足程度的評價為決定家庭經濟活動的準則。消費需求沒獲得滿足,即兩者未達到均衡。這時對勞動辛苦的評價低于滿足消費的意義,勞動投入將繼續,哪怕以降低勞動生產率或以在資本主義意義上的虧損為代價;相反,一旦需求已基本滿足,即達到均衡點,則任何進一步的勞動消費都是無意義的。家庭消費需求是家庭經濟活動的第一原則。[72a.49.73b]蔡雅諾夫認為,代役租農奴經濟接近于勞動家庭農場,基本上適用“勞動—消費”均衡的原則。蔡雅諾夫理論的出發點是既作為生產單位又作為消費單位的個體家庭,亦即物質再生產與人口再生產相結合的小農家庭。小農經濟的自然經濟性質很大程度上正是由這種結合決定的。其理論對自然經濟或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小農經濟是有普遍意義的。蔡雅諾夫注意到小農經濟中經濟再生產與人口再生產的關系,注意到由家庭人口自然發展所決定的家庭規模與構成及其對家庭經濟發展變化的重要影響。但他忽視小農庭與外部社會的聯系,忽視在社會上占主導地位的生產關系對小農經濟的影響,因而這種理論難以全面準確地闡明不同國家不同時代的小農經濟的發展規律。但他所揭示的小農家庭的特點和運行機制,對于自然經濟和以自然經濟為基礎小農經濟來說,恐怕是難以移易的準則。
李根蟠把“勞動一消費均衡公式”視為“自然經濟決定的原則與機制”,并以此分析《管子·國蓄》中“谷貴則萬物必賤,谷賤則萬物必貴”的話。“當糧食豐收時,谷價雖賤,農民有較多糧食可賣,收入足供所需,其副業生產可以收縮,或把較多產品留作自用,產品投放市場數量較多,故谷賤萬物貴。當糧食歉收時,谷價雖貴,農民沒有什么糧食可賣,收入不足抵償其各項開支,甚至還要買進口糧,這樣,只好增加副業生產,把較多產品投放市場,以彌補生計之缺,故谷貴萬物賤。這說明在當時地主制下的小農經濟,商品生產是自給生產的補充,副業生產是糧食生產的補充,其農副產品投放市場的多寡,主要不是取決于自身的需要,而是取決于自身的需要,即以足夠換取自己不能生產的那部分物質資料和交納貢賦為度,其副業生產規模及其產品投放市場的數量,則依據糧食生產滿足上述要求的程度來調節。”“由此可見,在地主制下的小農經濟中,由自然經濟所產生的思想觀念.行為方式和活動機制,仍然起著決定作用。”[34b]
現在我們再回到小農經濟與商品經濟的關系上。
從上面的敘述中可以看出,我國封建地主制下的小農并非完全自給自足,他們與市場已有較多聯系,小農經濟中可以容納商品經濟的成份,在整個地主制經濟時代,尤其是明清時代,商品經濟有較明顯的發展。——這是多數學者所公認的事實,但解釋各有不同。一種意見認為,這種商品經濟繁榮的表象和它實際達到的水平之間有很大差距,相當部分帶有自然經濟的痕跡,從總體看,當時的小農經濟仍屬自然經濟范疇;或因其既包含商品經濟成分,又仍以自給性生產為基礎或依托而稱之為“不完全的自然經濟”。另一種意見認為我國小農經濟中商品經濟的這種發展已使它脫離自然經濟的范疇,而屬于商品經濟中的一種類型;但這是建立在勞動生產率低下,小農經濟貧困化基礎上的特定類型的商品經濟。在這種商品經濟的基礎上,新的生產方式難以建立。——在這一點上兩種意見又趨向接近,不過,我國封建地主制下商品生產的發展,能否最終導致資本主義的建立,則不但在兩種意見間,而且在兩種意見內部,也存在著實質性的分歧。
如果光從小農經濟產品進入市場的數量和比例看,的確很容易得出我國封建社會小農經濟已經商品化(或已脫離自然經濟)的結論,但若從社會分工發展程度,農民勞動生產率和他們所能掌握的剩余產品作些分析,這種商品經濟的實際水平就值得考慮了。如果進一步考察小農經濟的運行機制,上述結論恐怕就難以成立了。陳春聲.劉志偉所說的“農戶經濟活動的非市場導向性”,撇開概念表達的歧異,與蔡雅諾夫所揭示的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農戶經濟活動的原則,并無本質的區別,似乎也不需要到傳統文化中去找尋清代經濟運作特殊性的根源。黃宗智既然承認中國明清以來小農經濟的發展是依據蔡雅諾夫的邏輯來推動的,則他所謂明清以來小農經濟已高度商品化的結論就可以商榷了。把維持生存放在首位,不正是可以理解為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經濟原則嗎?個體小農之所以能在邊際報酬低于正常工值的條件下投入家庭勞動從事家庭手工業生產,并以其低廉價格獲得在市場上的競爭力,不正是因為有自給性生產作了它的底墊的依托嗎?正如有些日本學者所指出的,中國土布之所以能維持低廉的價格,其“秘密就在于它不是基于商品生產,而是以自給自足為基礎的,將支出壓至最低限度而幾乎不考慮工資部份,才使低價格成為可能。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認為,低價格是完全無視‘商品’化相對應的價值問題,基本上是‘勞動力浪費體制’才得以實現的。”[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