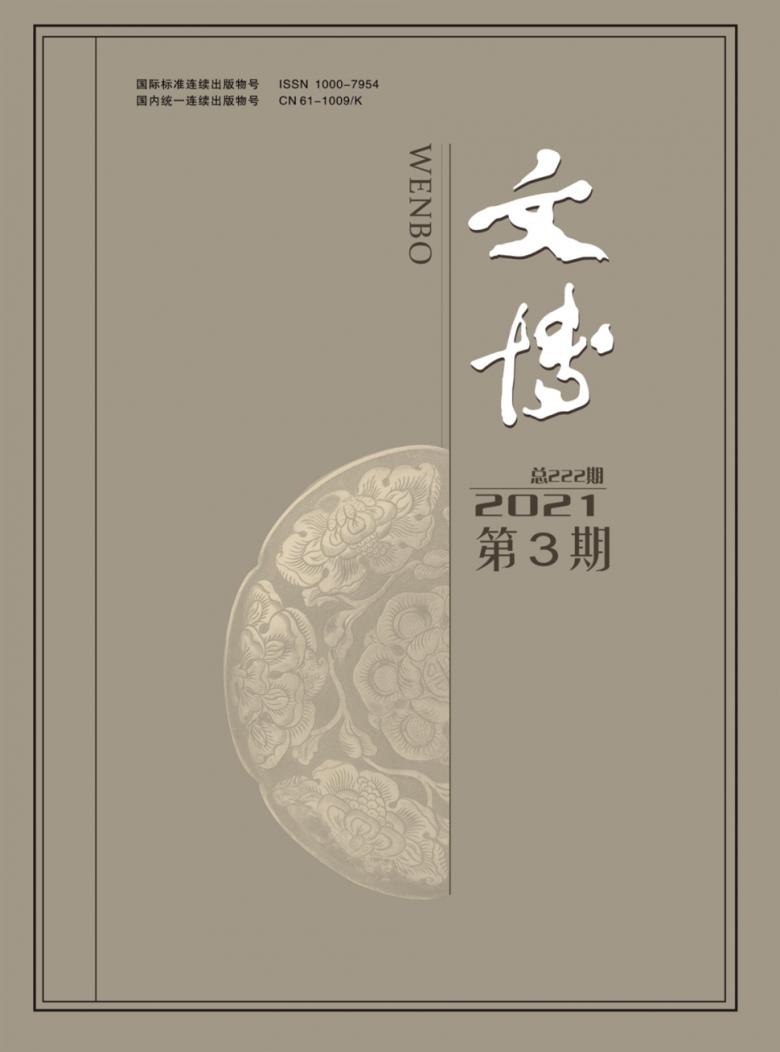封建地主制下的小農經濟(一)——傳統農業與小農經濟研究述評(下)
葉茂 蘭鷗 柯文武
關于小農經濟的界定,學術界有各種表述,[37a.41.85b]觀察角度和側重點各有不同;但基本精神大體一致。小農經濟是農業領域的與手工工具相聯系的個體經濟,它最本質的內涵,一是以個體家庭為生產和消費單位,即把物質再生產和人口再生產結合在個體家庭之中;二是以直接生產者的小私有制為基礎,這種小私有制包括對土地.農具.耕畜和其它生產資料程度不同的所有權。小農經濟經營規模狹小,以滿足自身消費為生產的基本目的,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相結合,受社會上占主導地位生產關系的支配,對地主.鄉族.國家存在不同程度的依附,既脆弱又頑強,易分化亦易再生等等特點,均由此而派生。根據小農與生產資料關系的不同,小農經濟可以區分為自耕農經濟.佃農經濟.份地農經濟等。有的學者所說的小農經濟,是指自耕農而言。[21]自耕農是典型的.但又是狹義的小農經濟;不應以此否認佃農.份地農之為小農經濟。又有的學者把“經濟地位上升的,雇傭長工以及生產有相當剩余的富農或經營式農場主”作為小農的一個階層,[93a]或者把地主和自耕農.佃農并列為“小農家族經濟”的三種類型[83],都背離了小農經濟的科學界定[56]。
中國小農經濟形成于何時,學術界有不同意見。一種流行的觀點認為,春秋以前尚盛行集體耕作的耦耕方式,春秋戰國時期鐵農具的推廣使一家一戶為單位的個體經營成為可能,小農經濟由此出現,封建地主制亦由此形成。[52a.57]也有不少學者指出,小農經濟并非封建社會所專有,它存在于從原始社會末期到資本主義時期的不同歷史時代中。[68.85b]亦有人根據我國考古發現,分析了個體家庭的分散勞動和獨立經濟早在原始社會末期即已出現,周代耦耕是農村公社中擁有獨立經濟的個體農戶之間的協作,春秋戰國鐵器的推廣只是加強了小農經濟的獨立性[34a]。不過,我國封建地主制確實形成于戰國,封建地主制下小農經濟諸特點,也是戰國以后才逐步顯露的,因此,上述分歧對我們所要談論的主題來說是無關宏旨的。
一、 小農的構成與身份
我國地主制下小農經濟的特點,可以從生產關系和生產結構這兩個方面進行分析。前者即地主制下小農的構成和身份有關。
我國地主制下的小農包括自耕農和佃農,不同于西歐中世紀主要為份地制農奴,這點各家意見大體一致。有人認為還應包括依附農。[17]不過所謂依附農實際不過是對地主有著比較嚴格關系的佃農,有時還包括部分自耕農。
我國封建地主主要采取分散租佃方式經營其土地,佃農是地主土地上的主要勞動者。中國古代佃與西歐中世紀農奴有明顯區別,它從未擁有固定份地,向地主交納的是實物地租,由于地主制下政治統治權與土地所有權的分離,以及土地可比買賣,地權經常轉移,在大多數情況下佃農并未對地主形成固定的.世襲的人身依附關系,且主佃間的依附關系在封建社會后期愈趨松弛。對這個問題,大多數學者的意見基本一致或接近[67]。但有些學者(如傅筑夫)認為佃農與地主只有契約關系,沒有人身依附關系[84b]。魏晉封建論者則只承認魏晉以后佃農對地主的依附關系,秦漢佃農被認為是古典式的自由佃農。[42]有些學者針對這種觀點作了批評,指出漢唐間封建租佃關系的主流是隸屬性嚴格的租佃制,這時也存在人身依附關系比較松弛的佃農,但這只是反映了佃農中人身不自由程度的等差。唐宋以后契約型租佃關系占主導地位,但主佃雙方仍非平等關系。主佃間的人身依附關系,既可在契約中明確規定,亦可僅靠傳統來維持。[58]不過,佃農對地主的人身依附,似乎有一個先是逐步強化,而后又逐步削弱的過程,有些學者著重論證了封建社會后期(明清)佃農人身依附關秒的全面松解。[35b]
中國封建地主制下又經常存在數量較多的自耕農,每一新王朝初建時尤其如此,這是中國封建社會的主要特點之一。[67.36.54]這也是大多數學者公認的。對自耕農的身份則有不同看法;這些不同看法是與對我國封建土地所有制性質的不同認識相聯系的。分歧的焦點,一是他們是小塊土地私有者呢?還是國家佃農;二是他們是自由農民呢?還是非自由農民。
封建土地私有論者無不認為自耕農擁有他們耕作的小塊土地的私有權,向國家交納的是賦稅而非地租。這也就是通常理解的“自耕農”,可不多說。封建土地國有制論者的理解不同,如郭庠林認為自耕農占有的耕地是國家給予的,其目的是為了利用農民開荒,從而向農民征收賦役,封建國家仍可任意處置這些永業田。因而永業田屬國家所有,自耕農只有世襲的使用權,他們實質上是國家佃農。[77]也有認為中國自耕農的土地所有制既是直接生產者占有小塊土地的小塊土地所有制,又是封建國家占有剩余勞動的封建土地國有制,即兼有兩者特點的變態封建所有制,[76]龐卓恒也有類似觀點,認為國家編戶制下的個體農戶,擁有相對獨立的土地所有權,但最高土地所有權或支配權仍屬國家,其突出表現是編戶農民征收與地租合一的賦稅和勞役。[61a]
認為中國封建地主制下自耕農是自由農民的,既有封建土地私有制論者中的某些人,也有魏晉封建論者,后者把戰國秦漢時代的自耕農視為古典時代的自由農民。主張自耕農為非自由農民的,既有封建土地國有論者,也有封建地主私有論者,前者如王毓銓,認為中國封建時代農民被編制在官府的戶籍中,什伍連坐,不得隨意遷移,為官府納糧當差。差糧征發實際以人戶為本,被征課者人身隸屬于皇帝,其土地可稱為“當差地”.“糧飯地”,其人身無“自由”“獨立”可言。[7]后者如湯明,指出“戶籍制的目的是為了征役,因而必然把土地占有和人身奴役連鎖在一起”;“力役在中國封建社會始終是廣大小農最沉重的負擔,這種以勞動的自然形態而提供的力役體現著極大的人身束縛”。他反對把編制在封建政權戶籍制度下的小農稱為“自由農民”。[27]楊國楨則從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特質來論述相似的觀點。他認為中國封建社會的自耕農雖不能稱為國家佃戶,但封建私人所有土地上也包含了鄉族和國家的部分所有權,賦稅既是國家政權的經濟實現,也部分帶有地租性質。“專制國家在自耕農土地上攫取了部分地租的轉讓,顯示了國家土地所有權的現實存在,自耕農隨之而來承擔一定的經濟義務,因而也就存在一定的封建依附關系。在這層意義上,他們又不是自由農民”。[53]針對魏晉封建論的觀點,李根蟠指出:“古希臘羅馬的公社是在原始社會向階級社會過渡期間解體的,這是自然發生的公社,公社解體后出現的是自由村社社員演變而來的自由小農。我國古代公社是春秋戰國之際解體的,這時我國進入階段社會已久,公社發生了質變,已打上剝削和壓迫關系的深刻烙印,公社社員已不是自由身份的社員,公社瓦解后出現的自然是對封建國家存在嚴重依附關系的自耕農。”[34c]戰國秦漢自耕農與其說象希臘羅馬的自由小農,毋寧說更象我國唐宋自耕農以以后的自耕農,從賦與役之比重看,其對封建國家的依附比后者更甚。看來,雖然應該承認地主制下的自耕農是小塊土地所有者,但把它們等同于古希臘羅馬的自由農民或西歐中世紀晚期擺脫了封建依附 關系的自耕農,都是不妥當的。不過,隨著封建地主制的自我調節,封建社會晚期的自耕農的土地所有權更為完整,其對封建國家的依附關系也有較大的松動,不少學者對此均有論述。
關于自耕農.佃農和農奴地位優劣之比較,胡如雷的分析頗有代表性。他認為自耕農優于佃農。因為自耕農農擁有私有土地,承擔課役而不必交租,在經營相同面積土地的條件下,自耕農會比佃家多占有一個凈租量,不但可以改善生活,而且可以投入再生產。與此相聯系,自耕農的最低必要耕地限量[=最低必要勞動總額/(畝產量-畝賦稅量)]可以比佃農的最低必要租地限量[=最低必要勞動總額/(畝產量-畝地租量)]低,最高耕地限量可以比佃農的最高租地限量高,因而有更大的適應性和靈活性;生產集約化程度可以更高,由于耕種自己的土地,利用土地時能長遠打算,注意提高土地豐度。但自耕農經濟比之佃農經濟更不穩定,除了經濟上的孤立性和經濟力量的薄弱以外,重要原因之一是國家役的增減幅度遠遠超過私租的增減幅度。中國的佃農則優于西歐的農奴。因為佃農避免了比較原始的勞動地租,比農奴有較多的人身自,刺激了生產積極性,招佃競爭又可導致剝削率下降等。但比起份地制下的農奴,在經濟上缺乏保障;地主不關心佃農勞動力的再生產,總是最大限度地提高地租剝削率;而地主奪佃.改佃時,又掠奪了佃農改良土壤.興修水利等提高土地豐度的成就,妨礙了農民發展生產積極性的發揮。而總的來看,中國封建地主制下的小農經濟優于西歐中世紀的農奴經濟。[67]任何事物都有正面和負面。有的學者強調了負面,對中西小農經濟的優劣提出相反的意見。如傅筑夫認為領主經濟農民經濟的存在為條件,其剝削率以不打破農奴經濟的再生產為度;地主經濟則不以農民經濟的存在為條件,地主對佃農的剝削不受任何限制。自耕農賦銳負擔亦不比佃農輕。[83ab]李運元也強調我國作為封建經濟細胞的個體農戶受剝削比西歐農奴重,由引造成兩千年來小農經濟的劇烈波動和極不穩定。[31]劉昶則認為中國的小農經濟不同于西歐莊園制大生產。小農經濟(按指自耕農)必然要分化;封建化是在小農分化基礎上實現的。西歐完成了封建化,形成了莊園經濟;中國沒有完成封建化,小農經濟仍廣泛存在。莊園經濟能在較大范圍和程度上集中人力物力,發展公共經濟,擴大再生產,實行進一步分工,因而優于小農經濟。中國則因不穩定易分化的小農經濟之廣泛存在,而陷于治亂興衰的輪回之中。[21]針對上述一些觀點,馬克垚指出西歐莊園也是小生產,而不是大生產:地主對佃農的剝削不可能沒有限度;中國佃農和西歐農奴都無土地所有權,很難說誰的土地更有保障,誰受的剝削更重;在中國歷史上,自耕農地位往往不如佃農,這就是歷代投存蔭冒之由起[3]。
關于自耕農和佃農的比例,流行的觀點認為,中唐以前自耕農占主要地位,中唐以后地主土地私有制和租佃制進一步發展,佃農逐漸占居主要地位。近代則有“占鄉村人口不到10%的地富占有70-80%土地(按,由于地主主要實行租佃制,設佃農與自耕農經營規模相仿,則佃農亦應占總戶70%),而占鄉村人口90%以上的雇農.貧農.中農只占20—30%土地”之說。晚近的一些研究動搖了這種看法。宋代的情形,漆俠《宋代經濟史》估計佃農(“客戶”中的主要部分)在總戶數中所占比例,北宋初為40%,以后逐年下降,最低是神宗熙寧年間的30%,轉而回升,南宋初為36%。南宋末達45%。自耕農(“主戶”中的四五等戶),北宋時約占50%左右,南宋時有所下降。崔瑩引用了這種意見。[79]馮爾康則認為宋清自耕農約占農村人口1/3,而自稱這是比較保守的估計。[18]章有義對本世紀二三十年代的地權分配作了重新估計,指出:“大體說,無產戶占鄉村總戶數的30%至40%,在有地戶中,地主富農占有土地50—60%,中貧農占40—50%。”,這和1091—1099年客戶占總戶數32.33%的比例基本一致。章氏呼吁要正確估量自耕農民小土地所有制在舊中國土地關系中所占的地位。他認為在地主所有制下,對地權分配長期起作用的兩個基本因素是土地買賣和遺產多子均分制,前者促進地權集中,后者導致地權的分散。此外,農民起義和新王朝保護小農政策也促進了地權的分散。種種長期和短期的因素交織在一起,于是在長期上,整體上形成地權的階級分配的某種常態,即地主農民占地的比率大體穩定。[82a]當然,這種長期趨勢的大體恒定是通過經常的變動不居來實現的,而在不同時段和不同地區呈現不平衡。如王朝初期自耕農較多,王朝后期佃農較多(這大體與土地兼并的周期變化有關);近世北方多自耕農,南方多佃農(楊國楨以在商品經濟發展程度不同地區封建私人土地所有權不同的變動態勢來解釋它[53])。
在這里產生了一個問題,既然自耕農始終大量存在,數量甚至往往超過佃農,這種社會還能稱為封建地主制嗎?美籍華裔學者趙岡正是根據章有義的文章導出否定封建地主制存在的結論的。[94b]這是對章氏觀點的一種誤解。國內也有學者認為“自耕農是一個與地主佃農沒有本質聯系的社會集團”。[18]戰國以后的自耕農經濟當然不同于地主經濟,但它并非游離于地主經濟體系以外的經濟成份。吳承明曾指出封建社會里存在著本質的.非本質的和異質的東西。[38e]封建地主制作為一個經濟體系可以把本質的.非本質的.異質的東西結合在一起。在地主制經濟體系中,正如佃農和地主相互依存一樣,自耕農和地主也是相互依存的。自耕農的分化為地主經濟的形成提供了土地和勞動的來源;地主家庭的析產和破落又不斷補充自耕農隊伍。說明“自耕農小土地所有制不單單是大地主土地所有制的附庸,而且是它必然的伴生物;它的存在是地主土地 所有制形式和發展的必要條件”。[34c]另一方面,不論自耕農經濟或佃農經濟,其發展均受地主經濟的制約。封建地主制經濟的性質正是由這一點決定的,而不在于佃農是否在生產者中占多數。正如奴隸制社會的性質取決于奴隸主經濟所占的支配地位,而不在于奴隸是否在生產者中占多數。
二.耕織結合
我國封建時代農區的小農經濟一般實行以糧食生產為中心的多種經營,把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結合在一起,人們一般用耕織結合來概括這種生產結構。這種結合十分牢固,以至成為資本主義萌芽發展的障礙,導致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基本要素。對這個問題,學術界歷來無異辭。近年來,一些學者對我國耕織結合不同于西方的特點,我國小農耕織結合形成和發展的過程,以及它所以特別堅固的原因,從不同角度進行了新的探索。
吳承明指出,男耕女織,是一種自然分工。凡是自然經濟占優勢的地方,都是存在的,并非中國或東方獨有。但西方畜牧業較發達,人們食品和衣著的構成也與中國不同,耕織結合常反映為耕牧結合。中國的耕織結合則以種植業為基礎。西方耕織結合不完全體現在個體家庭中,村社保留了較多的公有經濟。中國耕織結合則以家庭為本位。[38a]吳承明認為,東西方在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結合方面的程度差異,在向資本主義生產方式過渡時期,才變得重要起來。這種概括,代表了一種比較普遍的認識。
對耕織結合不能作機械的理解。不一定每個農家都從事紡織生產,但每個農家在糧食生產之外,必定兼事其他生產項目,以解決家庭消費的多種需要。在某種意義上,似乎也可稱為“農副結合”或“主副結合(指不以糧食生產為主業的農戶)”。李躬圃提出“中國古代農家綜合型生產力”的概念,[32a]這一概念未必確切,實際上只是指個體農戶以農耕為主多種經營的生產結構,并未能包攝生產工具,生產技術等生產力的重要內容。他又根據《亨萊農書》指出,十三世紀英國農家生產內容包括種植業.畜牧業.養殖業.奶制品業及建筑業,而無紡織業;紡織業生產主要在莊園作坊中進行。英國古代農家經濟屬農牧結合型,與中國有顯著區別。[32b]
龍登高不贊成籠統說小農家庭經營方式是“耕織結合”,他認為小農家庭經營由個體性綜合型生產力決定,有不同的發展階段。春秋中后期鐵刃農具初步推廣,始形成個體綜合型生產力,這時個體農戶獨立經營已出現,但幼弱而不完整,耕織并沒有統一于一個家庭中,不少農民要購買衣服,不購買衣服的農民其紡織生產也不完全在家內進行,解體中的村社共同體或自發的再生共同體仍在農民再生產中起作用。秦漢時期個體家庭獨立經營才真正形成,但對宗族與鄉社仍有一定依賴。西漢中期后耦犁的出現促進了群體勞動和協作勞動的發展,北魏以后生產力又向個體綜合性回歸,個體小農家庭經營經歷了獨立性減弱.依附性加強到復蘇的曲折過程。中晚唐以后,隨著鋼刃熟鐵農具等的出現,個體綜合型生產力趨于定型和成熟,個體家庭經營能力增強,實行耕織結合.多種經營,經濟結構日趨緊湊合理。[16ab]在這里,某些概念和表述尚可商榷,但把小農經濟的生產結構看作發展的過程無疑是可取的。
關于我國小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結合特別牢固的原因,有各種不同解釋。茲舉要如下:
1.強調地主階級的殘酷剝削。這是流行已久,至今仍為不少人贊同的觀點。如傅筑夫說:“由于地主階級及其國家的剝削非常殘酷,農民不能完全依靠租來的或自有的少量土地來維持生活,而必須經營一些可能經營的家庭副業,用以一方面滿足自己的需要,另一方面還可以把多余的一點產品出賣,來補助生活。……于是這種由小農業與手工業相結合的經濟形態,遂成為中國社會經濟結構的基本核心。”[84b]于素云也認為“苛重的剝削使農民必須以家庭手工業作為農業的補充”。[2]進行中外比較研究的一些學者如龐卓恒也強調這一點。認為地主階級級剝削的異常殘酷,使小農雙手緊緊抓住“耒耜與機杼”不放,農民越窮就越要依靠副業“與耕助織”。[61ab]吳承明對這種觀點提出批評,他指出,耕織結合的加強主要是明清以后的事,但很難說明清比前代剝削加重,近代剝削的確有所加重,但卻是耕織結合的自然經濟受到破壞的時期。用剝削加重來解釋耕織結合這樣一貫串整個自然經濟時代的歷史現象,是不夠的。[38a]
2.強調紡織原料的變化和紡織工具的落后。吳承明認為,在我國紡織原料經歷了以用麻為主時代向以用棉為主時代的演變,耕織結合的程度也發生了相應的變化。由于麻的御寒力較差,種植欠廣,原料加工運輸不便,用麻時代并非家家戶戶都能輯麻織布。棉取代了麻以后,棉花種植廣.運輸便.適應其纖維短而使用的小紡車,家家可置.老弱能用,紡紗遂真正成為家內婦女的事。他指出,王禎農書中已載有五綻腳踏紡車和32綻大紡車,植棉推廣后,重新使用單綻手搖車,幾乎回到漢代水平;生產力落后才是明清耕織結合更為緊密的根本原因。[38a]他又具體比較了解了棉紡織業中紡紗和織布的勞動生產率和收益。認為由于紡紗工具落后于織布工具,紡紗的生產率和收益均低于織布,“每一工作日紡紗收益10文,而織布可收益100文”,若農民單事紡紗,只能補償工食,故農民不能棄織專紡,耕織因之難以分離。[38b]孔涇源在吳承明理論基礎上作了發揮。他認為宋元出現的多綻紡車標志著家庭紡織業獨立化的技術基礎已經具備。但普遍存在的小農經濟的自然經濟性質,規定其生產目的是滿足家庭本身的消費需求,即直接使用價植的追求。棉花之保暖性能優于麻織品,更符合地處溫帶的小農的需要,故宋元之際一經傳入,農民家庭便以不計勞動消耗和犧牲技術進步為代價,舍麻取棉,中斷了紡織技術的演進過程,妨礙了耕織的分離,從而使資本主義萌芽難以發展。[11a]對王禎農書所載大紡車后世何以不見使用,歷來眾說紛紜,李伯重曾予評述并提出自己看法,[37b]于此不贅。趙磊曾對吳承明觀點作了批評,然未中肯綮。[64]
3.強調中西社會基導組織的差異,徐新吾認為西歐領主制下雖有小農生產,但以莊園大生產為社會基層組織的生產結構,而莊園有比較發達的專業分工,在一定條件下較易獨立分化。中國地主制則以個體小農經濟為社會基層組織的生產結構,小農經濟具有較高的獨立性,利于農業生產發展,但以自然分工為主,農業手工業緊密結合,故具有更大的凝固性,難于分化瓦解。[71a]蕭國亮的觀點與此相似,而更強調家族血緣紐帶的作用。他認為西歐農業與手工業結合以莊園經濟為主體,以莊園內部的勞動分工為基礎,莊園衰落時較易轉化為社會分工。中國傳統社會農業與手工業的結合以家族經濟為主體,實行家族內部的自然分工,由于家族血緣紐帶作用,兩者難以分離。[83]畢道村不同意徐新吾的觀點,他指出西歐莊園經濟仍是一種小生產,西歐十一.二世紀莊園的各種手工業并沒有發現不同于中國的獨立分化和專業分化,相反,其分化程度不及中國農村。他甚至說,西歐農家耕織結合不是低于而是高于中國。他認為西歐十一至十三世紀農業手工業分離的真正原因是市場與城市的發展。不應從農業與家庭手工業中的結合尋找中國封建社會長期延續的原因。[25a]
4.強調我國小農經濟對商品經濟一定程度的包容性。方行指出我國封建時代小農比之西歐中世紀農奴有較多的獨立性和自主權,有利于在自有經濟中發展商品生產。明清時代自給性耕織結合的小農經濟仍占優勢,但許多農民已分別在農業的一極或家庭手工業的一極部分地轉化為商品生產,而以自給性農業和商品性手工業的結合尤為普遍。農民通過家庭手工業的商品化獲得較大收益,從而增強了對封建剝削的負荷力,對人口增長的適應力,對新生產方式的排斥力,以至對機器工業產品的抵抗力。方行還談到這種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體隨著人口的自然增長,通過農民多子分居,象細胞分裂式地再生和復制著自己,使之形成汪洋大海;商人對農民小生產的控制也反過來使它能長期保存。所有這些,就是這種經濟結構堅韌性的全部秘密所在[10a]。
以上各種解釋各有其理由,亦各有不足處;相互補充,當可更為完整。剝削苛重,小農不得不“以副養農”“以織助耕”,這種情況確實是存在的,但它難以解釋耕織結合的發生,也難以圓滿解釋其強化。對于中西農家耕織結合形態的差異,徐新吾的說法恐怕比畢道村的說法更符合實際,不過差異的本身并不等于差異原因。吳承明指出耕織結合在封建社會后期強化的事實和紡織原料更替所起作用,甚有見地。但謂麻的時代耕織結合并不普遍,則屬可商。麻和絲是并行的。自曹魏實行租調制,長期以來絲麻織品是政府對農民的主要課納物品之一,農民豈能玩忽!用棉時代織布農戶與買布農戶約略相當的局面恐怕只有在這種課稅制度發生變革以后才能出現。作為課納物品的絲麻織品生產屬自給性生產范圍,這時的耕織結合雖已包含商品生產成份,但以自給生產為主。一條鞭法實行后,原自給性家庭手工業生產可能部分地轉為商品生產,農家耕織結合中商品經濟成份增加。我國封建社會后期耕織結合的強化,不但由于棉紡織生產更適合農家小規模手工生產,而且由于農家經濟中商品生產成分的增加使耕織結合的生產結構產生更強的生命力。從這個角度看,方行的解釋似乎更接近事物的本質。
三.封建地主與自然經濟商品經濟的關系
八十年代曾發生封建地主制與自然經濟.商品經濟關系的討論。由于小農經營是封建地主制的主要特點之一,因此討論中實際上也涉及小農經濟與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關系問題。
馬恩曾分析了西歐中世紀社會的自然經濟性質。以前國內史學界一般認為中國封建社會也是自然經濟占主要地位,小農經濟的耕織結合正是自然經濟的基礎和標志。但中國自春秋戰國以來,商品經濟比西歐中世紀發達得多,小農經濟的商品率頗高,這種情況封建社會后期又有所發展;同時,中國封建社會雖有相當繁榮的商品經濟,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卻遲遲建立不起來。如何解釋這些現象,出現不同思路和理論。
一種思路以吳承明為代表。吳承明看到東西方的差別,指出西歐中世紀在一個莊園或馬爾克鄉區范圍內,經濟上是高度自給自足的,但共同體內存在較多的分工.協作和勞動交換;中國封建社會以家庭為本位,個體家庭在經濟上的獨立性比西方大,但自然經濟并非更完整,中國封建商業與商業資本的發展超過西方。但他認為我國經濟史特別是近代史研究中有夸大商品經濟的傾向;同時自然經濟的觀念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仍然這樣或奸樣地表現出來。有鑒于此,他對“自然經濟”的含義作了“引申”。他認為家庭的自給自足只是自然經濟的第一層含義,但家庭實際上不能做到完全自給自足。自然經濟還應包括農民為剝削者直接消費的生產。根據政治經濟學的解釋,自然經濟是指在一個經濟單位內自我完成的再生產,這種經濟單位,在中國地主制經濟中大體相當于過去一個采邑的鄉里或邑縣,包括其中的地主.農民.各種工匠.手藝人.還有小商人,他們依靠在地方小市場上進行品種調劑和余缺調劑,互相取得原料和成品完成再生產。而廣義說,凡以使用價值為目的的生產和交換,都屬自然經濟范疇,因為這種生產和交換,盡管也會造成市場的繁榮,卻又常成為自然經濟的補充。地主制經濟利用它鞏固了自己。[37c]他又指出,傳統市場理論認為社會分工是商品經濟的基礎,但考之歷史,原始公社間的交換,地方小市場,剝削引起的交換,基于地區自然分工的長距離販運貿易等,都不是基于社會分工的交換。“歷史上可以有不同性質的交換,乃至有不同意義的商品。馬克思講的分工,是表現為價值的分工,無論有多大市場,只要沒有專業戶,即沒有生產交換價值的分工,就不算(本來意義的)商品交換。”[37d]
吳承明對“自然經濟”概念的拓寬曾引起一些人的批評,認為混淆了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界限。但持類似觀點的也不乏人。如湯明檖認為中國自然經濟不但表現在小農家庭,而且表現在地方基層組織的自給自足性。[27]章有義則認為:“小商品生產實質上以交換價值的形式的使用價值生產,成為自給性生產的組成部分”。[82b]孔涇源則強調了自然分工與自然經濟的關系。他說:“在農耕民族中,男耕女織的自然分工成為社會的基本生產方式,基于地域之間自然物產的差異性或勞動產品的多樣性進行的交換活動,又構成這種生產方式的補充要素。自然分工一方面使自然經濟的生產與消費直接結合的本質屬性得以確立,另一方面又使商品經濟因素潛在于這種自然經濟的機體之中。”他肯定耕織結合的自然經濟性質,認為自然經濟的真正分解,最初只能從耕織結構的內部開始。[11b]
另一種思路的代表是經君健。他對“中國封建社會自然經濟始終占主要地位”.“耕織結合是自然經濟的典型表現”的觀點提出批評。他認為作為自然經濟主要特征的自給自足是指“使用價值形態的自給自足”,而不是指“價值形態的自給自足”。一個經濟單位內生產品和消費品品種和數量的一致,是自然經濟的前提,他稱之為“自然經濟平衡律”。他列舉了一個經濟單位要滿足這一平衡律所必須具備的條件。他認為西歐中世紀莊園具備這些條件,因而屬自然經濟。中國封建地主制下無論地主經濟或小農經濟都滿足不了這些條件,都存在使用價值形態收入的單一性和需求多樣性的矛盾。這矛盾不可能在本經濟單位內解決,必須與外單位進行商品交換,這就決定了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有著本質的聯系。耕織結合的小農也得籍助于商品交換。“不要看到哪里有農業與家庭手工業的結合就認定那里必定是自然經濟;事情可能相反,恰恰那種結合正是商品經濟的表現,它跟商品經濟的發展成正比,甚至可以說,中國封建社會的大商品量的主要依據之一就是小農的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的結合。”他不同意把地方小市場劃歸自然經濟范疇,也不同意說地主制下的經濟單位是鄉邑,個體家庭只是生產單位。經君健又指出,盡管地主制經濟以商品經濟為條件,但商品生產仍停留在簡單商品生產階段,商品流通從屬于地主經濟,為地主經濟服務,成為地主商人高利貸者聯合對廣大農業勞動者進行剝削的工具,資本主義之芽難以在這基礎上萌生成長。[66]在此以前,盡管國內也有學者談到商品經濟在封建地主制形成發展中的作用,如李埏就把商品經濟的發展作為地主階級更新的條件之一;[33]吳太昌認為商品經濟也是封建地主制的基礎之一。[39a]但明確指出封建地主制與商品經濟有本質聯系,而不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在國內馬克思主義研究者中,經君健無疑是第一人。
不過,在港臺海外的經濟史研究中,主張中國傳統經濟為市場經濟的并不乏人。許倬云論述漢代農業,其模式是人口壓力—精耕細作—市場經濟。謂因精耕細作,多勞集約,產生勞動力的季節閑置,這些勞動力被用于從事工副業,發展了商品生產。故中國傳統農業并非都由自給自足的村落組成。[95]又如趙岡.陳鐘毅認為,中國至遲戰國開始,已在私有產權和小生產單位的基礎上形成市場經濟。眾多具有私有產權的經濟單元在既有的制約下作最合適的選擇,以獲得最大的經濟利益。他們合著的《中國經濟制度史論》一書,即按市場經濟的體系編篡。[94a]趙岡在《地主經濟制質疑》一文中,又提出租佃制與自然經濟不相容的觀點。[94b]
在上述問題討論中,不少學者既承認地主制經濟與商品經濟有本質聯系,又承認地主制經濟與自然經濟有本質聯系,何者為主則依各人理解為異。同時又往往從小農經濟的兩重性尋找地主制經濟兩重性的根源。
魏金玉認為從封建經濟單位的生產和消費的整個運行考察,封建經濟與商品經濟有本質聯系,但從封建土地所有者與農民的關系來考察,則封建經濟與自然經濟有本質聯系。他指出小農不但是獨立經營者,而且是地租交納者,往往要納稅后才能考慮家庭消費的需要,這是一種為滿足納租需要的生產,是一種使用價值的生產。他強調了封建社會中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相互補充的一面。封建社會中自給生產與商品生產相結合的單位,生產目的仍是使用價值,商品的使用價值制約著商品的交換價值,形成封建經濟特殊的計量概念和方法。經營者一方面盡量減少貨幣支出,另方面盡量增加貨幣收入,二者統一到增加贏利上。[91]
方行指出,我國封建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結合,兩者既相互排斥,又相互補充,不能只強調一個方面。他是從小農經濟的發展來論述這一點的。他指出農民“再生產所需的生產資料和生活資料,除自己以實物形態滿足外,其余部分要通過市場進行價值補償和物質替換,農民家庭并不是單純的自我完成再生產的經濟單位,而是一個包含有一定程度的以流通為媒介的再生產的經濟單位。農業和手工業.自給性生產與商品性生產的雙重結合,是小農經濟在生產上的基本特征,它已成為農民生產的內在結構。”他把小農經濟劃分為自給型.半自給型(以上屬自然經濟范疇)和交換型.以贏利為目的的交換型(以上屬商品經濟范疇)等四種類型,封建前期以前者為主,封建后期逐步向后者轉化。但絕大數農民仍保留或多或少的自給生產部分,從總體看自然經濟仍占主要地位。[10abcde]
李根蟠表示不同意“自然經濟平衡律”的提法,也不同意把小商品生產歸入廣義自然經濟范疇。他認為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本質區別不在于產品進入流通領域之有無或多寡,而在于生產要素在再生產中的不同運動方式,在于流通是否成為生產過程中的要素對生產起支配作用。以此衡量,前資本主義社會商品經濟雖已出現并有一定發展,但自然經濟仍占統治地位,這種二重性根源于個體經濟的二重性。中國封建地主制有比典型封建領土制發達得多的商品經濟,流通不但是物質資料再生產中的必要環節,而且是生產關系再生產過程中的必要環節。地主制經濟是商品經濟與自然經濟相結合的二重性經濟。但商品生產仍以自給性生產為基礎和依托,流通仍未控制整個生產過程,價值規律作用有限,仍受制于基于自然經濟的原則和機制。因此,從主導方面看,地主制經濟仍屬自然經濟的范疇,但已是一種“不完全的自然經濟”它是自然經濟的一種類型,而不是意味著自然經濟的解體。地主制經濟之所以能包含較多商品經濟的成分,與地主制下小農經濟的特點有關。在典型的領主制下,農奴經濟與領主經濟之間,農奴經濟與農奴經濟之間有直接聯系,共同構成自給自足程度頗高的半封閉的經濟實體。中國封建地主制下,個體農民之上一般不存在這種經濟實體,地主經濟與農民經濟是兩張皮,個體農戶不能自我滿足的那部分需要,常常要從市場求取解決,故農民經濟中一般包含部分商品生產,這是地主制下商品經濟的主要基礎。[34b]
吳太昌把中國封建制社會分為領主制和地主制兩個階段,強調了第二階段自然經濟的不完整性,強調了作為自然經濟必要補充的城鄉小商品生產的高度發展,以及商業的繁榮。這種與地主經濟伴生的商品經濟雖然始終處于對封建自然經濟的依附和從屬地位,但它的發展終究是社會生產力發展.社會分工和交換擴大的結果。自然經濟和商品經濟相互依存,相反相成,擴大了中國封建地主制的經濟基礎。[39ab]
閻守誠也認為封建地主制社會中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具有同一性。其重要表現之一是以自然經濟為主體的農業經濟中包含了商品經濟的成分,不管個體農民經濟或是地主經濟,均與商品經濟有必然聯系。[74]蕭國亮也主張小農家庭經濟是自然經濟與商品經濟的混合物,但強調土地買賣的作用。他認為小農家族之所以經營部分商品生產,是為了追求貨幣以購買土地。[83]
有關論述還不少,恕不一一列舉。
關于這一問題,似乎可以區分為兩個基本方面:一是封建地主與商品經濟是否有本質的聯系,或者說,封建地主制是否以商品經濟為其基礎之一;二是從主導方面看,封建地主制經濟究竟屬于自然經濟范疇,還是屬于商品經濟范疇?對于第一個問題,討論中多數人作了肯定回答,承認封建地主制下有比領主制社會更發達的商品經濟。關于第二個問題,有些人強調了這種商品經濟成分對自然經濟的依附,從而認為自然經濟仍占主導地位;另一些人則強調了商品經濟的獨立發展和重大作用,而不認為地主制經濟與自然經濟也有本質聯系。而地主制經濟之所以包容較多的商品經濟成份,則無疑與地主制下小農經濟的特點有關。讓我們進一步看看有關討論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