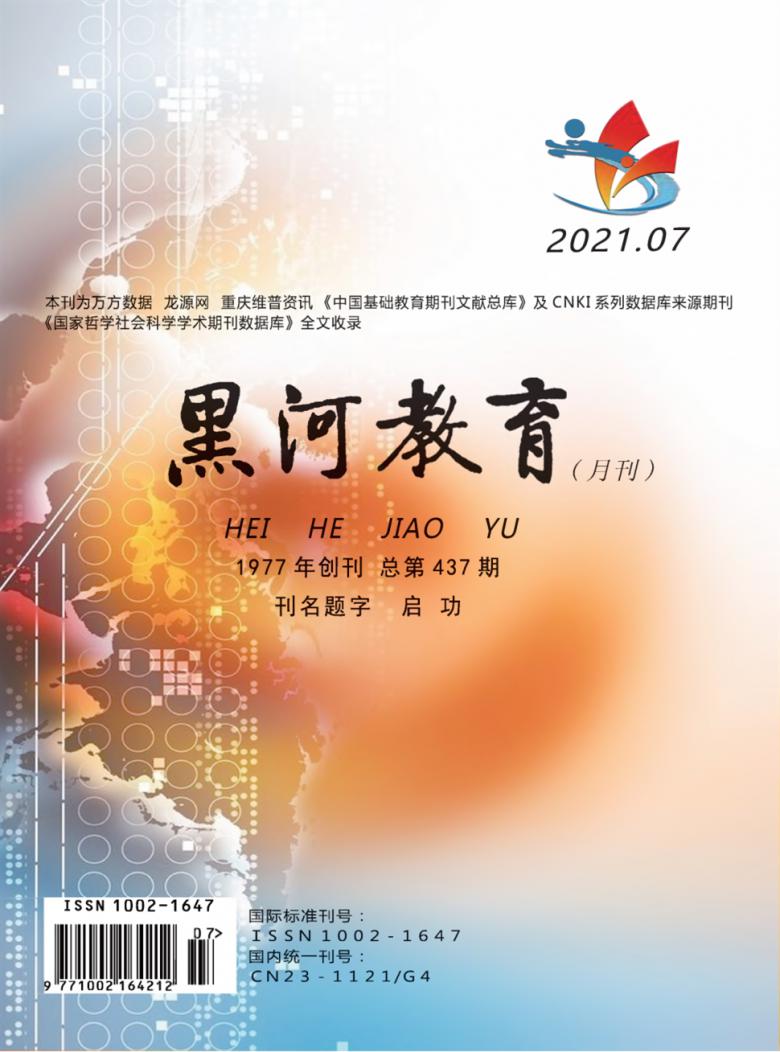農業科技投入增加的制約條件與相關因素分析
佚名
摘要:以糧食為基本對象,分析了當前農業問題的相關背景,闡述了與技術進步相關的條件制約因素,并分析了農業技術進步和政府投入的國情約束和制度障礙。指出中國的農業技術和投入政策研究,不能遵循國際通行的農業現代化理論,當務之急還是大包干以后提出,但至今沒有解決的“有中國特色”的老問題:即如何重新建立適合小農村社會經濟基礎的科技服務系統。
關鍵詞:農業;科技 ;投入; 條件;分析
進入新世紀的第一年,中國有兩個重要情況引起人們的普遍關注。
一是中國加入WTO談判曾經在2000年初受阻于農業補貼,引發爭議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在國內價格高于國際市場的情況下對糧食的補貼出口。同期,糧食占壓信貸資金和政府財政對庫存虧損補貼大幅度增加的問題,不僅引發了國內政策研究領域的反思,也導致了糧食購銷體制改革的進一步深化。
二是由于包括糧食在內的農產品長期賣難和農民收入連續4年增長速度下降,反映出農民群體在中國加入全球化的進程中,逐漸表現出“邊緣化”趨勢,因此,人們關于“三農(農業、農村、農民)”問題的討論也成為新的熱點。
以上兩個重要情況,對政府加強農業投入政策和對農業的科技進步的評價,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因為,中國小農經濟條件下的農業,表現出一種用“農業現代化”和“農業科技進步”等話語體系無法解釋的矛盾:
一方面,20世紀90年代以來農業的物質技術投入增加幅度顯著高于80年代,據測算其中農業的科技貢獻度超過40%;這往往被作為農業的重大進步而予以宣傳。
另一方面,農業的直接成本上升超過10%,包括技術在內的服務成本上升9%,其中,不僅家庭經營條件下的種植業投入產出已經是負效益,而且基本農產品也已經因為成本上升而喪失國際競爭力。
有鑒于此,中國的所謂農業技術和投入政策研究,顯然不能遵循國際通行的農業現代化理論,當務之急其實還是大包干以后就提出、但至今沒有解決的“有中國特色”的老問題:如何重新建立適合小農村社經濟基礎的科技服務系統。
為了方便討論,本文以糧食這個農業主產品為基本分析對象。
一 當前中國農業問題的討論與相關背景分析
人們在分析1996年以來糧食高產和庫存超過2億5千萬噸的問題的時候,對造成糧食過剩的背景討論不夠。并且,有關部門在提出解決“三農”問題的政策建議時,也仍然強調舊有的“增加投入”的思路。盡管其中增加科技投入的建議,可能在一定條件下還具有相對積極的政策意義,但技術部門的知識局限難以解釋農業的物質技術裝備系數提高的同時、效益卻在下降的道理。因此,需要從經濟角度討論與技術進步相關的條件制約。
(一)中國糧食增產的不同階段及其相關因素的討論
中國改革的20年中,糧食增產分3個階段,其階段性特征明顯,相關的不同意見討論,主要集中在制度和物質這兩種影響因素何者為主的分析上。農業部最近的研究,把糧食增產分四個階段(參見表1、表2)。
(1)其他物質投入,包括種子、農機、農膜、農藥等
(2)此處指廣義的技術進步,包括技術措施、制度變革和經營管理等內容
第一階段是在1978-1984年的6年中,我國糧食從1978年的3047.6億公斤提高到1984年的4073.1億公斤,總量增長32.6%,最為顯著的是單產從168.5公斤/畝增加到240.6公斤/畝,增長42.8%。對此,北京大學林毅夫教授的研究認為,以農村大包干為主的制度創新因素的貢獻度占40%。不過,后來的研究有所不同,主要是在價格刺激和物質投入兩個方面,補充、或者修改他的結論:
其一,1979-1982年政府把糧食綜合價格提高了49%。人們指出,這是在約20年不變的長期計劃價格壓抑下,在單一糧食產業上具有突破意義的短期價格調整,因此,必然對農民的生產積極性有特別大的刺激作用。
其二,據農業部的研究,這個階段糧食產量大幅度增加,其中的物質投入的作用是重要的。例如,化肥增加了100多萬噸,其中僅1982-1984年期間化肥在增產中的貢獻度就達到49%;用電增加30多億千瓦,農機總動力增加1000多萬千瓦,這些物質投入的貢獻度是26%;技術進步的貢獻是31%。
以上補充雖然可以被認為是不同意見,但由于提高價格也屬于政策變動,因此,人們至少在公開場合都仍然承認,農村改革是第一階段增產的主要因素。
第二階段是1985-1993年的9年,期間,由于1984年糧食產量大幅度增加,出現了嚴重的供給過剩,1985年農民調整種植結構,自發地減少了7千萬畝糧食播種面積,糧食產量下降2700萬噸。由此導致政府轉變了繼續深化改革的政策取向,而主要采取了加強投入和部分恢復以“合同定購”為名的強制收購政策。據農業部資料,這9年中,有效灌溉面積年遞增1%以上,化肥年遞增6.8%,貢獻度達到47%;農電年遞增11.6%,農機年增5.6%,這些物質投入的貢獻度為13%;技術進步的貢獻度是33%;財政資金年增13.5%。
但是,盡管物質技術投入比第一階段大幅度增加,由于糧食的需求彈性小,容易受到市場抑制,其產量還是“長期徘徊”;尤其是單產,9年中僅從240.6公斤/畝增加到275.4公斤/畝,僅為14.5%,比上個階段下降了28個百分點。直到1992年中國經濟進入高漲期,糧食才隨需求拉動造成的價格上漲,而出現比較明顯的增產,達到4564.8億公斤,增長幅度為12%。
第三階段是1994-1996年的3年內,糧食產量從4564.8億公斤迅速增加到5045.3億公斤,增長幅度為10.5%;不過,單產僅增長到298.9公斤,幅度僅為8%。進一步值得討論的問題是:這個階段的大幅度增產與投入和科技貢獻并不相關。據測算,化肥+6.7%,農電+13.4%,農機+6.6%,財政+16.7%。與上一階段相比,物質投入增加的幅度沒有明顯增長;而且,科技進步的貢獻度明顯下降到17%,氣候的貢獻度卻高達31%。
盡管有關部門測算的結果仍然表明了物質技術投入的重要性,但這些投入與產出和效益之間是否顯著相關,還有待于進一步證明。其實,在此期間內,人們公認的最有影響的重要因素既不是制度,也不是物質技術,更不是市場需求,而是政府。因為政府不僅在因豐收而形成的供給增加的3年內,兩次大幅度提高糧食收購價格(1996年與1993年相比提高幅度達105%),導致農民拋售存糧;而且還在此后連續3年強調全額收購。
通過對20年的三個階段糧食增產的因素分析可以看出:第一階段的主要增產因素是制度;第二階段產量徘徊的影響因素是市場;第三階段產量過快增長的推動因素是政府價格和相關政策。可見,物質技術投入至少在近期內還難以成為主要影響因素。
(二)農業投入的負作用
據農業部最近的研究成果,物質投入不僅已經表現出邊際報酬遞減規律,而且導致成本收益率逐漸下降,小農經濟條件下的糧食生產已經變成負效益。
統計數據顯示,1978年到1996年糧食產量從3000億公斤到5000億公斤的增長中,物質投入增加的作用是明顯的:在播種面積下降6.7%、減少803.9萬公頃的條件下,有效灌溉面積+12%、達641.6萬公頃;化肥+333%,施用量增加2943.9萬噸;農電+615%,1559.6億千瓦時;農機+228%,總動力增加26797萬千瓦;農業財政支出+364%、增加549.77億元。
其中雖然有不可比因素,但這種農業投入的顯著增加,在創造出高產量的同時,也使得物質成本不斷上漲,20世紀90年代農業成本增加幅度超過10%。而由于同期農業勞動力轉移困難,農業的勞動生產率并沒有提高。
在這種高投入的促進作用下,我國1996年糧食產量超前4年達到2000年的目標。但是,在人口以及與人口高度相關的、彈性很小的糧食消費需求卻不可能超前增加的壓抑下,就必然導致供給過剩和價格下跌;連帶發生農民收入增長困難的問題。可見,價格提高和投入增加這兩個被一般人看作是“好政策”的實際作用,在現行體制下恰恰是負面的。
上述情況,也是近年來糧食積壓造成財政補貼和銀行壞賬增加問題,并且引起全社會大討論的背景。
二 農業技術進步和政府投入的國情約束和制度障礙
在最近的研究中我對自己的觀點作了重要修改:我曾經認為20世紀80年代農村以“大包干”為名的改革,其實質是“農民得到了從集體經濟的退出權”。90年代以來的經驗過程表明,農村之所以能夠改革,其實是“政府退出農業生產領域”,這是由于集體經濟條件下農業低效益、高負債。
這個觀點也用于可以解釋大多數農業技術部門在大包干以后的20年中都面臨的困難局面:由于政府退出而導致的農技服務體系衰敗。
(一)技術和投入的體制障礙
如果上述觀點成立,那么隨之產生的問題就是,在農業、特別是種植業已經屬于負效益產業的情況下,政府難道能夠重新進入嗎?答案顯然是不樂觀的。本文因此希望重新以下討論人們習慣接受的政策建議:
第一,要“靠技術創新提高農業效益”。這個一向不容置疑的提法有兩個被有意無意繞開的問題:其一,一般情況下都是技術替代勞動,這使得大多數被專家們在實驗室里欣賞的技術,因為與我國的國情不符而導致其應用率難以提高。其二,任何一項技術都需要前期成本,改革前這些前期成本由國家支付,現在誰來付?因為前期成本高才要知識產權,所以人們講知識產權保護,在市場經濟體制下,技術是要拿來賣個好價錢的。更何況,在我國分散的小農經濟條件下,哪個小農戶能夠成為這種技術和投入的載體?
第二,提高產業層次,靠產業化解決農業的出路。當然,這是一個靠提高外部規模解決小農經濟問題的很合理的辦法。但也需要考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