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北魏的畜牧業(yè)
王磊 張法瑞 柴福
[摘要]北魏的畜牧業(yè)特別是國(guó)營(yíng)畜牧業(yè),在我國(guó)畜牧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它的生產(chǎn)技術(shù)水平相當(dāng)之高,這在《齊民要術(shù)》中得到反映,其中又以《養(yǎng)羊篇》所載的成就為最高,給后世養(yǎng)羊業(yè)的發(fā)展帶來(lái)了深遠(yuǎn)的影響。本文分析了北魏農(nóng)牧結(jié)構(gòu)的變動(dòng),農(nóng)牧業(yè)的此消彼長(zhǎng)的原因,并且還就這一時(shí)期以畜牧業(yè)為主的生產(chǎn)方式對(duì)諸如水土保持等有關(guān)生態(tài)方面的積極影響,進(jìn)行了探討。
[關(guān)鍵詞]北魏 畜牧業(yè) 齊民要術(shù) 農(nóng)牧結(jié)構(gòu)
北魏是繼十六國(guó)分裂局面之后重新統(tǒng)一北方的封建王朝,是我國(guó)歷史上民族大融合非常重要的一個(gè)時(shí)期。由鮮卑拓跋珪于公元386年建立,歷十二帝二王,至公元534年分裂為東魏和西魏截止,共經(jīng)歷一百四十九年。其間通過(guò)不斷對(duì)其他游牧部族及南朝劉宋政權(quán)的掠奪進(jìn)攻,于公元439年,完成了黃河流域的統(tǒng)一,從而結(jié)束了一百多年來(lái)北方分裂割據(jù)的局面。至公元449年,北魏的疆域已北至大漠,西至新疆東部,東北至遼河,南至江淮,達(dá)到鼎盛時(shí)期。作為一個(gè)由游牧的鮮卑族建立起來(lái)的國(guó)家,北魏的畜牧業(yè)生產(chǎn)相當(dāng)繁榮,在我國(guó)畜牧史占有顯著的地位。探討這一時(shí)期的畜牧業(yè)的發(fā)生發(fā)展、生產(chǎn)水平、結(jié)構(gòu)變動(dòng)及產(chǎn)生的影響,是一項(xiàng)頗有價(jià)值的工作。本文將就此略作說(shuō)明,不妥之處,敬請(qǐng)指正。
一、 北魏畜牧業(yè)的發(fā)展
來(lái)自北方草原的鮮卑拓跋部,在北魏建立以前,還處于“畜牧遷徙,射獵為業(yè)”[1]的原始游牧社會(huì),從事著單一的游牧經(jīng)濟(jì)。掠奪和自然繁殖是主要的生產(chǎn)方式,為其提供皮、毛、肉、酪等畜產(chǎn)品以維持衣、食、住、行的需要。公元386年,道武帝拓跋珪建立北魏,同時(shí)加快了對(duì)周邊敕勒、柔然等游牧部族的征討,并取得了節(jié)節(jié)勝利。戰(zhàn)爭(zhēng)掠奪已然成為獲取財(cái)富的重要手段。據(jù)初步統(tǒng)計(jì),從北魏建立至公元439年北方統(tǒng)一這五、六十年間,共發(fā)生針對(duì)別的部族的掠奪戰(zhàn)爭(zhēng)不下十五起,而且規(guī)模是越來(lái)越大[2]。戰(zhàn)爭(zhēng)不但使得其軍事實(shí)力不斷增強(qiáng),而且促使北魏的畜牧業(yè)經(jīng)濟(jì)取得了很大發(fā)展,為后來(lái)的統(tǒng)一北方打下了堅(jiān)實(shí)的基礎(chǔ)。像公元429年,太武帝北征柔然,一次性掠獲戎馬500萬(wàn)匹,呈現(xiàn)出畜牧車(chē)廬,彌漫山谷的景象。這一時(shí)期,除去自然繁殖以外,掠奪在北魏的畜牧業(yè)生產(chǎn)中占據(jù)非常重要的地位。正是為了安置這些掠奪而來(lái)的馬牛羊等戰(zhàn)利品,同時(shí)也為了頻繁而又長(zhǎng)期的統(tǒng)一戰(zhàn)爭(zhēng)的需要,加之北方地區(qū)一百多年來(lái)長(zhǎng)期處于戰(zhàn)亂分裂的局面,人煙稀少,土地荒蕪,于是在北魏畜牧業(yè)中占有極為重要地位和影響的國(guó)營(yíng)牧場(chǎng)便應(yīng)運(yùn)而生了。
表1:北魏四大國(guó)營(yíng)牧場(chǎng)
————|建立年代|撤消年代|位置|牲畜頭數(shù)|牲畜來(lái)源|功能
代郡牧場(chǎng)|公元399年|不祥,可能保留至北魏滅亡|南起臺(tái)陰,北距長(zhǎng)城東包白登,西至西山[3]|馬35萬(wàn)余匹,牛羊160余萬(wàn)頭|掠奪|供應(yīng)戰(zhàn)馬皮毛等軍資,作為統(tǒng)一北方戰(zhàn)爭(zhēng)的需要
漠南牧場(chǎng)|公元429年|公元433年|東至濡源,西暨陰山,東西三千里[4]|馬牛羊600余萬(wàn)|掠奪|向政府交納貢賦
河西牧場(chǎng)|公元439年|約公元529年|涼州到黃河河套地區(qū)[5]|馬200余萬(wàn)匹,駱駝100余萬(wàn)峯,牛羊無(wú)數(shù)|掠奪|畜牧業(yè)的產(chǎn)源地
河陽(yáng)牧場(chǎng)|公元494年|不祥,可能至北魏滅亡|以汲郡為中心,東至東郡的石濟(jì),西至河內(nèi)郡,南距黃河十里[6]|戎馬10萬(wàn)匹,每年還從別處遷入|從代郡牧場(chǎng)和河西牧場(chǎng)遷入|京師警備及畜牧業(yè)的產(chǎn)銷(xiāo)地
本表?yè)?jù)朱大渭、張澤咸主編的《中國(guó)封建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史》(齊魯書(shū)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第56-59頁(yè)資料制成。
代郡牧場(chǎng)是北魏建立的第一個(gè)國(guó)營(yíng)牧場(chǎng),曾于泰常六年(421)進(jìn)行擴(kuò)建。北魏遷都以后,大多數(shù)牲口都移往了河陽(yáng)牧場(chǎng),只保留了一小部分于此。后來(lái)北齊恒州的代郡牧場(chǎng),便是沿襲北魏該地而來(lái)的。漠南牧場(chǎng)的經(jīng)營(yíng)方式與代郡牧場(chǎng)有所不同,它保留了被征服部族的原部落組織,“使其耕牧,而收其貢賦”[7]。漠南牧場(chǎng)人畜眾多,畜牧業(yè)生產(chǎn)繁榮,以致于“歲至獻(xiàn)貢,由是國(guó)家馬及牛羊遂至于賤,毛皮委積”[8]。河西牧場(chǎng)的規(guī)模最為龐大,并且存在時(shí)間也最長(zhǎng),將近90年,在北魏的畜牧業(yè)生產(chǎn)中占有顯著地位。河陽(yáng)牧場(chǎng)距黃河僅10里,位于中原腹地,是遷都以后,鑒于代郡牧場(chǎng)和河西牧場(chǎng)距京都較遠(yuǎn),為滿(mǎn)足京師警備及畜產(chǎn)品消費(fèi)而興建的。
從以上對(duì)于四大國(guó)營(yíng)牧場(chǎng)的介紹及表中的數(shù)據(jù)可以看出,國(guó)營(yíng)牧場(chǎng)在時(shí)間與空間上的變化與北魏拓跋鮮卑的南下逐步統(tǒng)一整個(gè)黃河流域最終定都洛陽(yáng)始終保持一致的,亦反映了北魏畜牧業(yè)在時(shí)空上的變化。即整個(gè)社會(huì)在向中原定居的農(nóng)耕社會(huì)轉(zhuǎn)變,畜牧經(jīng)濟(jì)的下降是必然的。這四大牧場(chǎng)前三個(gè)牧場(chǎng)的牲畜來(lái)源全靠戰(zhàn)爭(zhēng)掠奪而來(lái)的,而河陽(yáng)牧場(chǎng)的牲畜則是從代郡和河西主要是河西牧場(chǎng)遷入的,說(shuō)明在北魏中前期,掠奪在畜牧業(yè)經(jīng)濟(jì)中占了非常重要的地位。隨著北魏太武帝統(tǒng)一北方,也即河西牧場(chǎng)建立年間,大規(guī)模的掠奪已達(dá)到了頂點(diǎn),國(guó)力亦達(dá)到最高峰,此后掠奪戰(zhàn)爭(zhēng)隨之減少,國(guó)勢(shì)也漸漸衰弱。值得注意的是,河西牧場(chǎng)的牲畜遷往河陽(yáng)的過(guò)程中,“每歲自河西徙牧于并州,以漸南轉(zhuǎn),欲其習(xí)水土而無(wú)死傷也”[9],然后再轉(zhuǎn)牧于河陽(yáng),這也從側(cè)面反映了北魏的畜牧業(yè)生產(chǎn)水平。從每個(gè)牧場(chǎng)牲畜驚人的數(shù)量可以看出北魏的畜牧業(yè)生產(chǎn)規(guī)模之大。唐代最大的國(guó)家牧場(chǎng)的牲畜總數(shù),也僅為河西牧場(chǎng)的三分之一。可見(jiàn),北魏的畜牧生產(chǎn)規(guī)模及水平,繁榮程度,不但超越了以前歷代,就連后來(lái)以馬政最為著名的唐代甚至也難與之相比。
不但國(guó)營(yíng)畜牧業(yè)如此,北魏的私營(yíng)畜牧業(yè)也是比較繁榮的。那些受封牧地的世家大族像爾朱羽健、越豆眷、提雄杰等,他們的牧地面積多達(dá)上百里甚至幾百里,所養(yǎng)從事放牧的“牧子”就數(shù)以千計(jì),而牲畜的數(shù)量更是難以估算。明元帝拓跋嗣(409~423)年間,政府制定了征收牲畜稅的政策,規(guī)定:“調(diào)民二十戶(hù),輸戎馬一匹”“六部民羊滿(mǎn)百口,輸戎馬一匹”[10],以馬作為征收對(duì)象,以羊的數(shù)量作為征稅標(biāo)準(zhǔn),如果沒(méi)有發(fā)達(dá)的私營(yíng)畜牧業(yè)是不可能的。孝明帝(515~528)時(shí),恒州刺史“私家有馬千匹者,必取百匹,以此為恒”[11]。北魏《齊民要術(shù)》中提到養(yǎng)羊生產(chǎn),羊的數(shù)量往往以“千口”計(jì),“羊一千口者”“用二萬(wàn)錢(qián)為羊本,必歲收千口”,想必當(dāng)時(shí)在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單個(gè)家庭飼養(yǎng)千口羊的規(guī)模也不罕見(jiàn)。值得一提的是,《齊民要術(shù)》的作者賈思勰本人就曾養(yǎng)了200只羊。所有這些,都表明了當(dāng)時(shí)私營(yíng)畜牧業(yè)在北魏的畜牧業(yè)中也占有相當(dāng)重要的地位。
二、 從《齊民要術(shù)》看北魏畜牧業(yè)生產(chǎn)水平
《齊民要術(shù)》成書(shū)于北魏末年,是一部系統(tǒng)總結(jié)北魏及其以前的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經(jīng)驗(yàn),特別是北方黃河流域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綜合性農(nóng)學(xué)著作,在我國(guó)農(nóng)業(yè)發(fā)展史上占有相當(dāng)重要的地位。《齊民要術(shù)》第六卷專(zhuān)講畜牧,內(nèi)容涉及馬、羊、牛等家畜,有關(guān)技術(shù)內(nèi)容則遍及選種繁育、飼養(yǎng)管理、疾病防治、畜產(chǎn)品的加工等諸多方面,其水平之高,充分反映了北魏畜牧業(yè)所取得的成就,對(duì)后世的畜牧生產(chǎn)具有很大的影響。雖然這一部分只有一卷且僅占全書(shū)的十分之一,“但在中國(guó)古代綜合性農(nóng)書(shū)中都是空前的,也是絕后的”[12],由此可見(jiàn)其地位與重要性了。而這部分,據(jù)游修齡先生統(tǒng)計(jì):敘述馬的字?jǐn)?shù)占全部畜牧字?jǐn)?shù)的45.45%,羊占25.75%,馬和羊合占71.20%,是絕對(duì)多數(shù)[13]。出現(xiàn)這種情況并不是偶然的,它具有深厚的草原文化的烙印,也充分說(shuō)明了馬和羊在北魏畜牧業(yè)生產(chǎn)中的地位。
馬對(duì)于來(lái)自北方草原的拓跋鮮卑來(lái)說(shuō),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在北魏的畜牧業(yè)生產(chǎn)中占據(jù)首位,主要是馬的軍事意義大于經(jīng)濟(jì)意義,包括別的朝代也是如此,而且專(zhuān)辟馬政。這從中國(guó)古代畜牧獸醫(yī)方面的書(shū)中也可以看出,涉及到馬的書(shū)占了絕大部分,且大多是以專(zhuān)書(shū)的形式出現(xiàn)的。《齊民要術(shù)》中關(guān)于馬的飼養(yǎng),認(rèn)為飲食上應(yīng)當(dāng)遵循“三芻”即饑時(shí)喂粗料,飽時(shí)喂精料,引誘多吃和“三時(shí)” 即朝飲少量,晝飲酌量,暮飲足量;在繁育上,馬驢的雜交,需要父強(qiáng)母壯。另外,還提出了軍馬的臨時(shí)強(qiáng)健法等等。
但是,《齊民要術(shù)》畜牧部分有關(guān)養(yǎng)馬的內(nèi)容,繆啓愉先生認(rèn)為“《要術(shù)》所載相馬內(nèi)容,頗為繁瑣、零亂重復(fù)既多,也間有出入,與他篇大不相同”,“懷疑其中大部分是后人插進(jìn)去的”[14],所以它并不能較為深刻系統(tǒng)地反映出當(dāng)時(shí)畜牧業(yè)的技術(shù)水平。而真正能代表畜牧生產(chǎn)水平與成就并對(duì)后來(lái)產(chǎn)生很大影響的便是《齊民要術(shù)》中的養(yǎng)羊篇。
作為北魏統(tǒng)治者拓跋鮮卑這樣的游牧民族,羊的皮毛、肉酪可以滿(mǎn)足他們的衣、食、住等方面需求,所以羊在游牧民族的生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隨著拓跋魏的入主中原,“一向?qū)τ谌轭?lèi)沒(méi)有多大興趣的漢民族,似乎由于學(xué)習(xí)北方民族的風(fēng)尚,大量養(yǎng)羊”[15],飲食方面漸為“胡化”,羊肉酪漿已然成為“中國(guó)之味”[16],并且做氈及制作酥酪等畜產(chǎn)品的加工已開(kāi)始盛行,社會(huì)的需求儼然促進(jìn)了養(yǎng)羊業(yè)的發(fā)展。所以《齊民要術(shù)》養(yǎng)羊篇反映的當(dāng)時(shí)生產(chǎn)技術(shù)成就的出現(xiàn),并不是偶然的。
表2:《齊民要術(shù)》養(yǎng)羊技術(shù)要點(diǎn)
————|技 術(shù) 要 點(diǎn)
選種繁育|“常留臘月,正月生羔為種者,上;十一月、二月者,次之”這個(gè)留冬羔作種的原則至今仍在沿用
飼養(yǎng)管理|“牧羊必須大老子、心性宛順者,起居以時(shí),調(diào)其宜適。卜式云:牧民何異于是者”[17],這是對(duì)于牧羊人的選擇。“既至冬寒,多饒風(fēng)霜;或春初雨落,青草未生時(shí),則須飼,不宜出牧”,舍飼與放牧應(yīng)結(jié)合起來(lái)
飼草儲(chǔ)存|“積茭之法:于高燥之處,豎桑、棘木,作兩圓柵,各五六步許。積茭著柵中,高一丈,亦無(wú)嫌”,即保存過(guò)冬牧草的方法
制酪做氈|“于鐺斧中緩火煎之”,“四五沸便止”,“以張生絹袋子,濾熟乳著瓦瓶子中臥之”,制酪應(yīng)慢火煎,瓦罐盛。做氈“秋毛緊強(qiáng),春毛軟弱”應(yīng)該混用,并且“不須厚大,唯緊薄均調(diào)乃佳耳”
疾病治療|“羊有疥者,間別之”當(dāng)時(shí)已經(jīng)認(rèn)識(shí)到通過(guò)隔離以防止疾病的傳染。“當(dāng)欄前作瀆,深二尺,廣四尺,往還皆跳遇者,無(wú)病;不能過(guò)者,入瀆中行過(guò),便別之”以此來(lái)檢驗(yàn)羊的健康狀況
《齊民要術(shù)》養(yǎng)羊篇所總結(jié)和反映的北魏畜牧業(yè)的生產(chǎn)技術(shù)成就,在中國(guó)的養(yǎng)羊史甚至于畜牧史上都具有非常大的價(jià)值和影響。它是“保存到現(xiàn)在的最古我國(guó)養(yǎng)羊技術(shù)資料”[18],并且“要了解古代養(yǎng)羊的實(shí)際方法,應(yīng)以《齊民要術(shù)》的記載為最有價(jià)值”[19],這是對(duì)《齊民要術(shù)》養(yǎng)羊篇最好的評(píng)價(jià)。
更為難能可貴的是養(yǎng)羊篇所載的方法內(nèi)容,很有可能并不像別的卷篇那樣包含了對(duì)以前的技術(shù)經(jīng)驗(yàn)的總結(jié),而是在北魏這一特定歷史時(shí)期黃河中下游地區(qū)勞動(dòng)人民自身在生產(chǎn)實(shí)踐中總結(jié)提煉,并且借鑒北方畜牧生產(chǎn)的經(jīng)驗(yàn)方法的結(jié)果,是農(nóng)耕民族和游牧民族在社會(huì)經(jīng)濟(jì)文化上不斷交匯融合的產(chǎn)物。日本農(nóng)史學(xué)家天野元之助在其《后魏賈思勰的齊民要術(shù)研究》一文中就曾指出“《要術(shù)》卷六畜牧加工部分是吸收了拓跋族的生產(chǎn)經(jīng)驗(yàn)。僅從其記敘字?jǐn)?shù)就不難看出,有關(guān)羊的飼養(yǎng)比重已遠(yuǎn)超出此前占優(yōu)勢(shì)的豬。從而可見(jiàn)此一時(shí)期,華北農(nóng)民對(duì)羊的飼養(yǎng)已處于優(yōu)勢(shì)地位。羊的飼養(yǎng)跟農(nóng)戶(hù)的活動(dòng)有密切相關(guān)的諸多問(wèn)題,在《要術(shù)》養(yǎng)羊第五十七中,大體可以窺之,而體現(xiàn)這些經(jīng)驗(yàn)的記述,只能是依據(jù)直接經(jīng)驗(yàn)者,其中理應(yīng)包括有些是從北方民族學(xué)來(lái)的”[20]。“要術(shù)最重要的優(yōu)良作風(fēng)之一是引書(shū)都注明出處”[21],而本篇標(biāo)明出處的僅有一處,即引用《家政法》中的有關(guān)內(nèi)容,“養(yǎng)羊法,當(dāng)以瓦器盛一升鹽,懸養(yǎng)欄中,羊喜鹽,自數(shù)還啖之,不勞人收”等。由此看來(lái),養(yǎng)羊篇所反映的成就可能是那一時(shí)期獨(dú)創(chuàng)的。
中國(guó)古代農(nóng)書(shū)中關(guān)于畜牧獸醫(yī)方面的,以馬、牛為最多,駝、豬次之,但有關(guān)養(yǎng)羊的專(zhuān)著,則幾乎就沒(méi)有。同時(shí)“屬于畜牧學(xué)性質(zhì)的著作,除去相牛經(jīng)、相馬經(jīng)之類(lèi)而外,專(zhuān)講育種、飼養(yǎng)的可說(shuō)是寥若晨星。反之,獸醫(yī)書(shū)卻很不少。在這些著作中,關(guān)于家畜的飼養(yǎng)管理的知識(shí)淪為附庸”[22]。可見(jiàn)《齊民要術(shù)》養(yǎng)羊篇在養(yǎng)羊史上屬于一篇非常有分量的著作,并對(duì)后世產(chǎn)生了非常大的影響。我國(guó)現(xiàn)存最早的元代官頒農(nóng)書(shū)《農(nóng)桑輯要》中涉及到養(yǎng)羊的部分幾乎全部引自《齊民要術(shù)》。另外一本元代三大農(nóng)書(shū)之一的《王禎農(nóng)書(shū)》中的羊養(yǎng)技術(shù)方法,一字不差全部抄自《齊民要術(shù)》。
《齊民要術(shù)》中除了馬、羊,對(duì)于其它家畜諸如牛、驢、騾、豬、雞等均有所論及。從書(shū)中的記載我們可以看出驢騾這兩種由北方傳入,中原地區(qū)以前沒(méi)有的動(dòng)物,在那時(shí)已經(jīng)成為很重要的役畜了。書(shū)中關(guān)于豬和雞的飼養(yǎng)管理,也都設(shè)立了單獨(dú)的篇章,材料很多,論述很有價(jià)值。 三. 北魏農(nóng)牧結(jié)構(gòu)的變動(dòng)
當(dāng)北魏的畜牧業(yè)經(jīng)濟(jì)不斷發(fā)展壯大直至達(dá)到頂峰的時(shí)候,對(duì)于作為統(tǒng)治者的拓跋鮮卑來(lái)說(shuō),農(nóng)業(yè),這個(gè)在黃河中下游地區(qū)有著更為悠久歷史的經(jīng)濟(jì)部門(mén),也得到恢復(fù)進(jìn)而不斷發(fā)展,最終取代了畜牧業(yè)經(jīng)濟(jì),在國(guó)家經(jīng)濟(jì)中重又占據(jù)首要地位。
來(lái)自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鮮卑拓跋部,早期很少?gòu)氖罗r(nóng)業(yè)生產(chǎn)活動(dòng)。到了道武帝拓跋珪(386~408)時(shí)期,隨著與中原農(nóng)耕民族不斷沖突交往過(guò)程中,統(tǒng)治者開(kāi)始漸漸意識(shí)到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重要性,并開(kāi)始采取相應(yīng)的促進(jìn)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的措施,像“幸定襄之盛樂(lè),息眾課農(nóng)”[23]、“給農(nóng)器,記口受田”[24]等等。但是從建國(guó)至北方統(tǒng)一的這一個(gè)時(shí)期,在推行農(nóng)業(yè)的過(guò)程中,由于受到來(lái)自游牧貴族的阻力,加之采取的措施僅具有權(quán)宜應(yīng)急性,所以農(nóng)業(yè)發(fā)展緩慢,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所占的比重非常小。畜牧業(yè)經(jīng)濟(jì)無(wú)論是在規(guī)模還是在水平上都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仍然占據(jù)著主導(dǎo)地位。
太武帝拓跋燾(424~452)完成統(tǒng)一北方大業(yè)以后,通過(guò)頒布政策措施,農(nóng)業(yè)取得了很大的發(fā)展。加之隨后進(jìn)行的戰(zhàn)爭(zhēng)越來(lái)越少,規(guī)模也越來(lái)越小,這使得以掠奪為主要來(lái)源的畜牧業(yè)的比重在有所下降,但比起種植業(yè)來(lái)還具有相當(dāng)大的優(yōu)勢(shì)。此時(shí)北魏統(tǒng)治集團(tuán)內(nèi)部仍有人聲稱(chēng)“國(guó)人本著皮套,何用棉帛”[25],可見(jiàn)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結(jié)構(gòu)尚待全面進(jìn)行調(diào)整。
從孝文帝拓跋宏(471~499)太和九年(485)實(shí)行均田制到北魏末年,迫于人口激增,對(duì)衣食需求的加大,從而進(jìn)入了農(nóng)牧并重平行發(fā)展并最終農(nóng)業(yè)超過(guò)畜牧業(yè)的一個(gè)時(shí)期。特別是旨在“勸課農(nóng)桑,興富民之本”[26]的均田制的提出與大力推行,使得土地與勞動(dòng)力有效地結(jié)合起來(lái),在客觀上為北魏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發(fā)展開(kāi)辟了道路。隨后產(chǎn)生的三長(zhǎng)制,即設(shè)立鄰長(zhǎng)、里長(zhǎng)和黨長(zhǎng),三長(zhǎng)負(fù)責(zé)檢查戶(hù)口、收繳賦稅、征發(fā)徭役以及督促生產(chǎn),它使得農(nóng)業(yè)成為國(guó)家收入的主要來(lái)源,從而在根本上實(shí)現(xiàn)了從畜牧業(yè)經(jīng)濟(jì)向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的轉(zhuǎn)變。如果說(shuō)均田制的實(shí)行是北魏進(jìn)入農(nóng)耕社會(huì)的標(biāo)志的話(huà),那么三長(zhǎng)制的創(chuàng)立則是北魏“漢化”深化的重要標(biāo)志。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此時(shí)已占據(jù)了優(yōu)勢(shì)地位,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成為社會(huì)生產(chǎn)的主要方式,所以《齊民要術(shù)》出現(xiàn)在北魏的這個(gè)時(shí)期并不是偶然的。值得一提的是,這個(gè)時(shí)期畜牧業(yè)的比重在逐漸降低,但“如果說(shuō)鮮卑拓跋部的游牧經(jīng)濟(jì)已不復(fù)存在,那是錯(cuò)誤的”[27]。河陽(yáng)牧場(chǎng)的存在,至少是個(gè)例證。
四、北魏畜牧業(yè)經(jīng)濟(jì)的生態(tài)影響
北魏中前期畜牧業(yè)經(jīng)濟(jì)占主導(dǎo)地位,以畜牧業(yè)作為主要的生產(chǎn)方式,對(duì)于生態(tài)環(huán)境的影響也值得關(guān)注。它的主要效益是減少了黃河流域的水土流失,從而減少了黃河決口泛濫所帶來(lái)的災(zāi)害。這也是北魏統(tǒng)治者得以把河陽(yáng)牧場(chǎng)修建在黃河邊上的原因。北魏最后一個(gè)大型國(guó)有牧場(chǎng)河陽(yáng)牧場(chǎng),靠近黃河北岸,距離黃河僅10里,沿黃河呈條狀分布。作為亦農(nóng)亦牧的地區(qū),在這之前畜牧業(yè)就已有之。《晉書(shū)·束皙傳》中記載,“州司十郡,土狹人繁,三魏尤甚,而豬羊馬牧,布其境內(nèi),宜悉破廢以供無(wú)業(yè)”,“故謂北土不宜畜牧,此誠(chéng)不然”[28]。這里的“州司十郡”即包括黃河中游南北兩岸境。河陽(yáng)牧場(chǎng)常備戎馬十萬(wàn)匹,不但肩負(fù)著京師的警備要?jiǎng)?wù),同時(shí)還要為京師提供肉酪等畜產(chǎn)品,可見(jiàn)其對(duì)于北魏統(tǒng)治者來(lái)說(shuō)是何其重要了。
從公元70年的東漢初期至九世紀(jì)末的唐朝時(shí)期,黃河出現(xiàn)了大約有八百年相對(duì)穩(wěn)定的時(shí)期。據(jù)記載,整個(gè)魏晉南北朝一共只發(fā)生過(guò)六次河患,而北魏僅有兩次,且這兩次也都發(fā)生在道武帝統(tǒng)一北方之前,分別為“泰常三年(公元418年),八月河內(nèi)(今豫北)大水(一作雁門(mén)河內(nèi)大雨水);神麚四年(公元431年),魏南鄙大水,自山以東,遍遭水害,民多餓死”[29]。如果我們?cè)侔褮v史推進(jìn)到500年后的北宋,就會(huì)發(fā)現(xiàn),雖然長(zhǎng)期動(dòng)亂分裂的局面結(jié)束了,但是黃河河患決口卻更甚從前,平均每1.5年便決溢一次[30]。這種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并不是偶然的。當(dāng)黃河流域畜牧經(jīng)濟(jì)占主導(dǎo)地位時(shí),它對(duì)于生態(tài)破壞的程度遠(yuǎn)遠(yuǎn)小于農(nóng)耕經(jīng)濟(jì)。“歷史時(shí)期某一地區(qū)的植被破壞情況如何,又主要取決于生活在這地區(qū)內(nèi)的人們的生產(chǎn)活動(dòng),即土地利用方式”[31]。農(nóng)耕對(duì)于植被的破壞是相當(dāng)大的,而畜牧經(jīng)濟(jì)只要不過(guò)度放牧,草原植物基本上就不會(huì)受影響。而植被的破壞與否,特別是對(duì)于黃土高原來(lái)說(shuō),直接關(guān)系到水土流失的程度以至河道淤積,黃河泛濫。所以當(dāng)畜牧經(jīng)濟(jì)轉(zhuǎn)向更為“文明先進(jìn)”的農(nóng)耕經(jīng)濟(jì)時(shí),從整個(gè)黃河流域來(lái)看,會(huì)發(fā)現(xiàn)是得不償失的。比較北魏和北宋黃河決口的次數(shù),當(dāng)可說(shuō)明這一點(diǎn)。即畜牧業(yè)處于主導(dǎo)地位時(shí),黃河泛濫決口次數(shù)就少,當(dāng)農(nóng)耕經(jīng)濟(jì)占主導(dǎo)地位時(shí),黃河泛濫決口次數(shù)則偏多。正是由于北魏中前期畜牧業(yè)的發(fā)達(dá),才使得黃河中游較大水患僅發(fā)生兩次,以致北魏出現(xiàn)了長(zhǎng)達(dá)九十年的安定局面。譚其驤先生在《何以黃河在東漢以后會(huì)出現(xiàn)一個(gè)長(zhǎng)期安流的局面》中指出:“東漢以后,由于黃河中游地區(qū)的土地利用方式變成以畜牧業(yè)為主,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減輕,這是下游之所以會(huì)出現(xiàn)長(zhǎng)期安流局面的決定性因素”。
1. 董愷忱、范楚玉主編:《中國(guó)科學(xué)技術(shù)史·農(nóng)學(xué)卷》,.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2000。
2. 韓國(guó)磐:《南北朝經(jīng)濟(jì)史略》,.廈門(mén),廈門(mén)大學(xué)出版社,1990。
3. 石聲漢:《中國(guó)農(nóng)學(xué)遺產(chǎn)要略》,北京,農(nóng)業(yè)出版社,1981。
4. 王毓瑚:《中國(guó)畜牧史資料》,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1958。
5. 謝成俠:《中國(guó)養(yǎng)牛羊史》,.北京,農(nóng)業(yè)出版社,1985。
6. 張仲葛、朱先煌主編:《中國(guó)畜牧史料集》,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1986。
7. 中國(guó)農(nóng)業(yè)遺產(chǎn)研究室編:《中國(guó)農(nóng)學(xué)史》,上冊(cè),北京,科學(xué)出版社,1959。
8. 鄒逸麟主編:《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
9. 吳于廑:《世界歷史上的游牧世界與農(nóng)耕世界》,《云南社會(huì)科學(xué)》, 1983,1期。
注釋?zhuān)?/p>
[1]《魏書(shū)》卷1《序記》。
[2] 參見(jiàn)唐啟宇:《中國(guó)農(nóng)史稿》,農(nóng)業(yè)出版社,1985年,第399-400頁(yè)。
[3] 《魏書(shū)》卷2《太祖紀(jì)》、卷103《高車(chē)傳》。
[4] 《魏書(shū)》卷4《世祖紀(jì)》上、卷103《高車(chē)傳》。
[5] 《魏書(shū)》卷110《食貨志》。
[6] 《魏書(shū)》卷44《宇文福傳》。
[7] 《魏書(shū)》卷103《高車(chē)傳》。
[8] 《魏書(shū)》卷103《高車(chē)傳》。
[9] 《魏書(shū)》卷110《食貨志》。
[10] 《魏書(shū)》卷3《太祖紀(jì)》。
[11] 《魏書(shū)》卷18《廣陽(yáng)王元深傳》。
[12] 李根蟠:《從〈齊民要術(shù)〉看少數(shù)民族對(duì)中國(guó)科技文化發(fā)展的貢獻(xiàn)》,《中國(guó)農(nóng)史》2002年第2期。
[13] 游修齡:《〈齊民要術(shù)〉成書(shū)背景小議》,《中國(guó)經(jīng)濟(jì)史研究》1994年第1期。
[14] 繆啓愉:《〈齊民要術(shù)〉校釋》,中國(guó)農(nóng)業(yè)出版社,1998年,第387頁(yè)。
[15] 石聲漢:《從〈齊民要術(shù)〉看中國(guó)古代的農(nóng)業(yè)科學(xué)知識(shí)》,科學(xué)出版社,1957年,第59頁(yè)。
[16] 楊衒之:《洛陽(yáng)伽藍(lán)記》卷3。
[17] 卜氏語(yǔ)見(jiàn)《史記·平準(zhǔn)書(shū)》,此處是賈氏意述,不是原文。原文為“非獨(dú)羊也,治民猶是也,以時(shí)起居;惡者輒斥去,毋令敗群”。
[18] 鄒介正:《我國(guó)養(yǎng)羊技術(shù)成就史略》,《農(nóng)業(yè)考古》1982年第2期。
[19] 謝成俠:《中國(guó)養(yǎng)牛羊史(附養(yǎng)鹿簡(jiǎn)史)》,農(nóng)業(yè)出版社,1985年,第156頁(yè)。
[20] 天野元之助:《后魏賈思勰〈齊民要術(shù)〉研究》,山田慶兒編《中國(guó)的科學(xué)和科學(xué)者》,京都大學(xué)人文科學(xué)研究所,1978年,第548-550頁(yè)。
[21] 石聲漢:《齊民要術(shù)今釋》,科學(xué)出版社,1958年,第356頁(yè)。
[22] 王毓瑚:《中國(guó)農(nóng)學(xué)書(shū)錄》,農(nóng)業(yè)出版社,1964年,第346頁(yè)。
[23] 《魏書(shū)》卷3《太祖紀(jì)》。
[24] 《魏書(shū)》卷3《太宗紀(jì)》。
[25] 《資治通鑒》卷125《宋紀(jì)》元嘉27年。
[26] 《魏書(shū)》卷7上《高祖紀(jì)上》。
[27] 張維訓(xùn):《論鮮卑拓跋族由游牧社會(huì)走向農(nóng)業(yè)社會(huì)的歷史轉(zhuǎn)變》.《中國(guó)社會(huì)經(jīng)濟(jì)史研究》,1985年第3期。
[28] 李劍農(nóng):《中國(guó)古代經(jīng)濟(jì)史稿》,武漢大學(xué)出版社,1990年,第41頁(yè)。
[29] 周魁一:《中國(guó)水利史稿》上冊(cè),水利電子出版社,1979年,第250頁(yè)。
[30] 鄒逸麟:《黃淮海平原歷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第103頁(yè)。
[31] 譚其驤:《長(zhǎng)水集》下,人民出版社,1987年,第8頁(yè)。
Animal husbandry in the North Wei dynasty
Abstract: Livestock farming in the North Wei dynasty, especially its state-owned farming, plays a very important role in the history of China’s animal husbandry. The production and technology was much developed then, which was reflected in the book of “Qiminyaoshu” (Key skills for ruling the people). Sheep farming was the most developed one and had profound influence on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this industry. Close attention is also paid on change in agricultural structure in terms of composition of crop farming and livestock farming in the North Wei dynasty. Also discussed in the paper are the positive impacts of the livestock farming dominated agriculture on the environment such as soil and water conservation.
Key words: North Wei Dynasty, livestock Farming, Qiminyaoshu, Agricultural Structure
學(xué)研究.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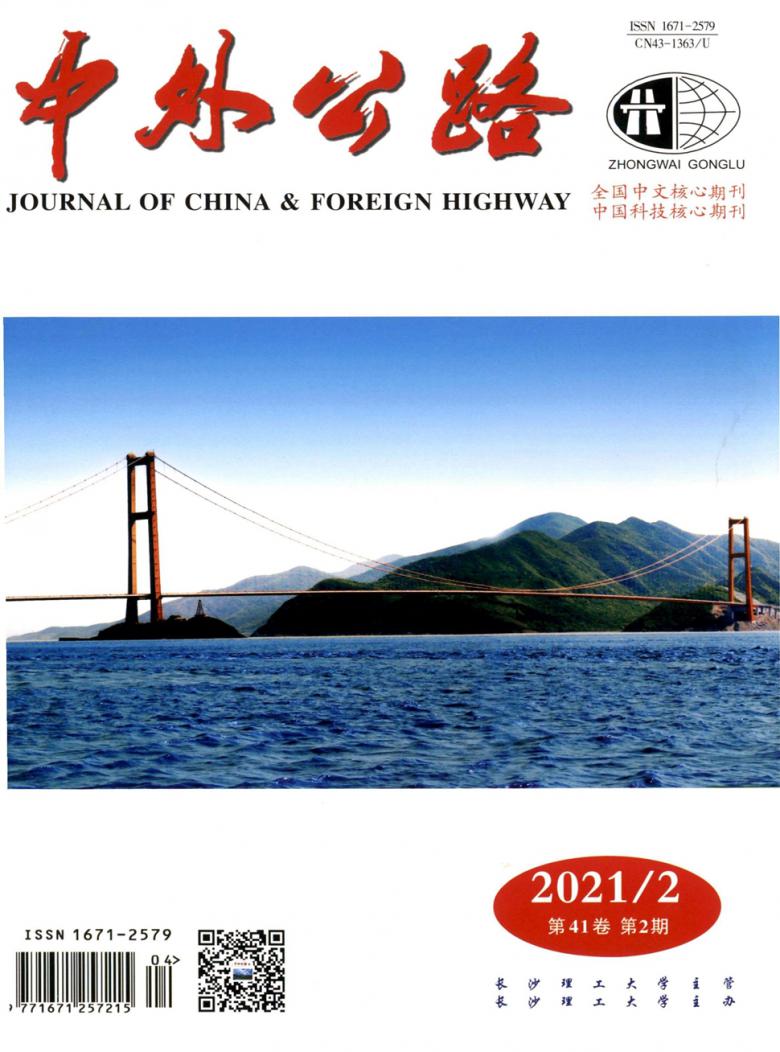
代特殊教育.jpg)
.jpg)
全科醫(yī)學(xué).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