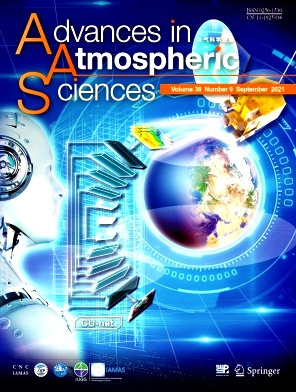日本國際制造業產業轉移分析及對我國的啟示
劉晶
關鍵詞:日本,國際制造業,產業轉移
一、國際制造業產業轉移的理論發展綜述 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推進,國際產業轉移方興未艾,如何更好地抓住這個機遇,提升我國的整體競爭力,是我們要深入研究的課題。國際產業轉移,主要指發達國家或地區通過國際貿易和國際投資等多種方式,將產業(主要是制造業或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到次發達國家或地區以及發展中國家或地區,帶動東道國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優化升級。日本經濟學家以發展中國家的立場,從不同的視角闡述了這個問題。關于國際產業轉移歐美學者較早地展開了研究,日本學者后來追上,他們從不同角度出發,闡述了自己的觀點。
阿瑟·劉易斯(1984)認為,引起20世紀60年代非熟練勞動密集型產業由發達國家轉移至發展中國家的主要因素,是二次大戰后發達國家人口的增長幾乎為零,而工業的增長速度又前所未有引致的非熟練勞動力的不足。劉易斯的觀點,實際上是建立在赫克歇爾—俄林的要素稟賦理論基礎之上。由于當時國際產業轉移主要發生在勞動密集型產業方面,因而影響轉移的因素主要是上述兩類不同國家間在非熟練勞動力豐裕程度方面的差別。
弗農(1966)提出的產品生命周期理論,則以產品生命周期的變化來解釋產業轉移現象。他認為,企業為順應產品從新產品階段到成熟階段再到標準化階段的生命周期的變化,而在要素豐裕程度不一的地區之間轉移產業,以規避生產上的比較劣勢。
在產業區域轉移的微觀層面的研究上,鄧寧(1976)用0-L-I模型來說明發達國家的跨國公司的對外投資和擴張行為。他指出,產業組織決定的所有權優勢,要素賦存結構決定的區域特定優勢,交易成本決定的內部化優勢,是解釋企業對外直接投資和跨國經營的主要原因。
日本經濟學家以發展中國家的獨特視角,結合本國的實踐經驗。從不同的視角闡述了這個問題。
筱原三代平提出了著名的“動態比較費用論”。他認為,如果按照李嘉圖的理論,發達國家將其重點工業放在重工業等收入彈性高的工業,而發展中國家只發展農產品等收人彈性低、技術進步率低的初級產業。這種國際分工持續下去就會使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收入差距進一步加大。因此對日本來講,如原封不動地接受這種靜態比較成本學說,是無法趕超歐美發達國家的。從發展和動態的角度來看,對那些有發展潛力,又對國民經濟有重要意義的產業,只要經過10—15年的積極扶持,是可以成為強有力的出口產業,能夠取得動態的比較成本優勢的。
在實踐中,日本學者赤松要等人從日本國情出發,立足于東亞這一國際區域展開研究,提出了著名的“雁行形態論”。該理論反映了國際間產業轉移由消費資料產業向資本資料產業、輕工業向重工業、原材料工業向加工、組裝工業演化。這種結構演進趨勢,同工業先行國突破一國限制,在全球范圍內進行結構調整的趨向吻合。國際產業轉移實際上是工業先行國在全球范圍內進行國內產業結構調整的一種手段。小島清(1979)提出“邊際產業擴張論”,修正并完善了“雁行形態論”。
我國學者對產業區域轉移的研究,由于實踐的滯后,還處于初始階段。盧根鑫從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產品價值構成的角度出發,認為產業轉移的經濟動因在于重合產業的產品技術構成相似而價值構成相異,這樣導致了產業從高成本國家和地區轉移到低成本國家和地區(盧根鑫,1997)。陳建軍認為,中國現階段出現的產業區域轉移現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市場的擴張、產業結構的調整、追求經營資源的邊際效益最大化以及企業成長的需要。
這些理論從不同的層面解釋了國際產業轉移問題,但必須要結合我國的具體國情才能解決目前的一些問題,不能孤立、片面地模仿。我國是一個人口眾多、區域經濟發展差距大的發展中大國,不是所有產業都能套用國際經典理論的模式。筆者認為,我國現階段應在充分發揮比較優勢、更深入參與國際產業分工、承接國際制造業轉移的同時,建立競爭優勢,對于我國具有比較優勢的產業,要大膽實施“走出去”的發展戰略。同時結合中國國情,將產業轉移、產業結構調整和區域經濟整合結合起來,建立有利于東、中、西部協調發展的國內區際產業轉移模式,提升國家的整體競爭力。在下文中,筆者將借鑒日本國際制造業產業轉移的理論與實踐經驗,并結合我國國情提出一些建議。 二、日本承接國際制造業產業轉移的動因 二戰后由美國實施的“道奇計劃”。為日本經濟復蘇提供了充裕的資金和技術;1950年爆發的朝鮮戰爭使日本得到了大量美國的軍需訂單,國內需求嚴重不足的狀況得到改變。布雷頓森林體系與固定匯率制為日本營造了良好的國際環境,使日本的貨幣政策、貿易政策的政策效力大大加強。美日之間的不對稱合作使得日本產品在美國市場長驅直人的同時有效地保護了相對軟弱的國內市場。
20世紀50—60年代,日本政府通過《外資法》、《外匯法》、政府資金、租稅特別措施等產業政策的實施,成功地將吸引的海外投資及國內的私人資本引向大型工業設備領域。憑借積極的設備投資,日本經濟的產業結構迅速轉化為以高附加值生產領域為核心的結構形式。產業結構也發生了重大變化。日本經濟的產業結構變化速度之快,無論是從整個產業還是從制造業,日本產業結構的變化系數都遠遠高于歐美主要國家,說明其結構變化劇烈。
并且,在制造業比例居高的條件下(1960年制造業附加值占GDP比重為33.8%),轉向了具有高附加值生產率的金屬工業、化學與機械工業,即形成了以重化學工業為核心的產業結構。
日本廣泛引進外國先進技術,引進速度成幾何級數增長的強勁增長勢頭,其中80%以上是基礎工業技術,主要來自美國,也有西歐和其他地區的。日本從引進的技術中廣泛吸取各國之長,并且加以消化、吸收、企業化,迅速縮短了與世界先進水平的差距。20世紀60年代后半期,日本在繼續大量引進外國先進技術的同時,加快本國獨立研制工藝技術的步伐。技術革新取得的突破新進展。這一點對日本從經濟上、技術上全面趕超世界先進水平起到決定性作用。
在經濟高增長期,日本的出口產品結構也隨之做出了快速反應。最初,纖維制品、棉制品等天然纖維以及雜貨制品所占比例很高(20世紀50年代初該項出口額構成比為13.7%,20世紀60年代后期該比例縮減為3.9%),而后重心轉移向鋼鐵制品、船舶等重化學工業,并向機械、電子器械領域廣泛延伸(20世紀50年代初該項出口額構成合計為35.5%,20世紀60年代后期該比例增至52.8%)。這一變化意味著日本出口主要集中在需求收入彈性高的產品領域。 三、日本制造業產業國際轉移的演進 20世紀60—70年代,日本的鋼鐵、電力、機械和石油化學等基礎工業設備投資向巨型化、大容量化發展,增強日本工業產品的國際競爭力。同時,日本獨創的新產品、新技術、新工藝日益增多,在民用消費品領域(特別是高檔家用電器等)尤為明顯。到20世紀70年代初期,日本在生產技術上達到了世界水平。1965年以后,日本的對外貿易繼續大幅度增長,在對外貿易方面已基本上可保持順差局面,并呈穩定增長趨勢。外貿順差的結果導致了日本資本輸出的迅猛增長。
為了降低生產成本,促進國內產業結構升級,日本資本輸出主要集中在亞非拉第三世界國家,投資范圍遍及輕紡、化學工業等,由于日本資源匱乏,缺乏重工業發展所需的礦產品,所以,對采礦業的投資比重最大。日本向礦產資源豐富的第三世界國家轉移先進的采礦技術和資金,再將生產出的礦產品返出口到日本國內,扶助重工業的發展。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日本企業對海外的直接投資開始快速增長。這其中包含了多方面的原因:一是“尼克松沖擊”、石油危機、總需求增長的減速使日本國內維持高速經濟增長的條件逐漸喪失。日本重工業遭嚴重打擊,耗能型的重工業向節能型改進,同時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下降。勞動密集型的組裝加工產業在產業結構中的比重上升。二是由于貿易摩擦,如北美和歐洲汽車市場的案例,而將生產轉移到海外。三是由于日元匯率走高而將生產向海外轉移,特別是電氣和電子產品的生產商,為尋求高質量、低成本的勞動力紛紛將生產轉移到東南亞和中國。四是為了開拓需求增長潛力大的市場(如中國)而將生產設施轉移到其他國家。這一時期日本的海外直接投資大部分流向北美和歐洲。
20世紀80年代,隨著日本人口高齡化社會問題加深,勞動力老化現象日趨嚴重,國內勞動力成本上升,消費品市場增長乏力,日元升值且在國際匯率市場上幣值極不穩定。上述種種因素導致老的組裝加工業在日本漸失生存與發展的比較優勢。制造業的重要組成部分——組裝加工業開始加快向海外轉移步伐,轉移的方向是歐美和東亞。
進入20世紀90年代,日本直接投資的重心已轉移至東亞和中國。與20世紀80年代相比,日本對歐美投資不斷減少,對東亞投資卻逐年上升。自1993年開始直接投資表現為“清一色亞洲格局”。日本對亞洲的投資雖然在整體規模上不如其在美、歐的投資,但始終保持比較平穩的上升態勢。這是因為日本在美、歐的投資存量很高。日本對亞洲海外投資的案例數在整體上高于日本對美、歐的投資案例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