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代文化的眾聲喧嘩1.浪漫倫理與現代消費主義精神2.當代中國娛樂文化的三大新變(上)
柯林·坎貝爾
[摘要]本文為英國社會學家柯林·坎貝爾《浪漫主義倫理與現代消費主義精神》的導論部分。此書從標題到研究思路沿襲了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通過對18世紀英國工業革命時期伴隨而來的消費革命的梳理與分析,探尋現代消費主義的起源,試圖將文學浪漫主義與現代工業社會的“獲取與花費”相聯接。通過對文學、歷史、社會學、經濟學等學科的例證,坎貝爾提出現代社會消費主義的特征不僅源于工業資本主義的市場力量,也與獲取快感和白日夢的浪漫藝術相關。此書是西方消費文化研究的經典作品,也是研究消費文化的必讀書目。此書在消費文化研究、大眾文化研究等領域影響深遠。在導論一節中,作者主要介紹了研究的方法、方法論及其思路形成過程。
[關鍵詞]浪漫/消費(主義)/現代化/馬克思·韋伯
牛津英語辭典對浪漫的定義是“標志為、暗示為、賦予為羅曼史的,想象的,遠離經驗的,幻想的,以及(與文學與藝術方法相關)指高貴或是激情或是不尋常的美”。這些注釋與冠以“消費”之名的行為看上去沒有關系。① 恰恰相反,除了極個別的情況,例如我們購買大件物品,如房子和汽車,我們通常將挑選、購買與使用商品和服務全都視為無趣和平淡的日常行為。消費作為經濟行為的一種形式,在生活中通常被放在我們所認定的“浪漫”的對立面。這種對立的合理性很容易掩人耳目,然而,一旦我們認識到有一種重要的現代現象將兩者直接相聯,事情就變得明晰了。
這種現象就是廣告,只要粗粗瀏覽幾頁時尚雜志,瞅上幾眼商業電視,就會發現有多少廣告與“浪漫”主題相聯,多少影像和拷貝與“遠離日常經驗的”、“想象的”、暗示為“高貴或是激情”的場景相聯。在涉及香水、香煙或是女式內衣的廣告中,狹義的浪漫表現得特別明顯,在有些圖像與故事中,更典型地使用著異國情調的、想像的、理想化的等廣義的浪漫。而廣告的實際目的當然是誘使我們購買它們所表現的物品,換句話說,就是消費。② 基本的“浪漫”文化物質通常以這種方式用于廣告,這一點經常被注意到,因此,可以說,對“浪漫主義”與“消費”之間聯系的共識業已存在。在包括社會科學學者在內的學者與知識分子中流行一種設想,即認為正是廣告商出于他們所代表的生產商的利益,決定了物品的用途,因而,應當認為在這種關系中,“浪漫的”的想法、靈感與態度對“消費社會”(consumer society)③ 的利益有用。本書稍后將挑戰這種觀念(不過沒有拒絕),本書主張在將文化的“浪漫”因素(romantic ingredient)視為現代消費主義本身發展的重要部分的同時,也對相反的關系加以詳察。其實,消費(consumption)可以決定需求(demand)和需求供給(demand supply),可以認為, 浪漫主義本身在推動工業革命時地位突出,在現代經濟特征中擁有一席之地。這是一個雄心勃勃的主張,因而,我一開始將解釋我是如何到達這一立場的。
發生在20世紀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的一些事件導致了本書寫作。如同眾多的歐洲與北美學者,特別是社會科學學者,我認為那一時期動蕩不安、充滿挑戰,有時甚至振奮人心。大學校園處于代際戰爭的前沿,在這場戰爭中,擁有特權和受過教育的年輕人仿佛將歷史的進程偏移到前途未卜的軌道上。沒有學者,至少沒有社會學家,能經歷這一場知識(intellectual)與文化的動亂,而不促使自己反思并重驗指導他們專業與個人行為的假想。我的有些同行,經過適當的自我權衡,決定加入年輕的“反文化者”(counter-culturalist), 然而有些人對他們稱之為年輕人反常規的瘋狂(youthful antinomian madness)④,采取了更加頑固的立場(entrenched position)。我本人,對于給個人帶來兩難困境的現象更為興趣盎然;對我不能完全理解的事情,我在寬容(condone)與聲討(condemn)之間難定取舍;我將更多的精力用于令人不知所措的文化劇變的研究。盡管一開始,這只是一個個人調查,對于它很快成為具備專業觀照的事情,實際上,我后來發現,它對我的專業意味更多。 在后來幾年中,我的研究主要采取了閱讀文獻方式,我不僅閱讀“水瓶座時代”⑤ 的先驅們所炮制和青睞的文獻,甚至閱讀比他們更早一些的衛道士們的作品。我力圖通過閱讀這兩者來更好地理解他們的世界觀。⑥同時,我也考慮到了數量有限,然而日益增長的社會學專論,它們也聲稱將闡釋這一令人不知所措的新現象。⑦ 二戰后既有的社會學常識(其實是此前一代)建立的基礎是認定現代社會將繼續沿著理性、唯物主義和世俗的道路演進。這使得后者格外困難。讓人預料不到也無法解釋的是,相當一部分受過教育的中產階級年輕人轉向了巫術、神秘事物與海外宗教,明顯地偏離理性文化,堅決地反清教徒主義。對此現象的敘述是相當困難的,而且沒有直接挑戰長期“理性化”(longterm“rationalization”)的大前提。由于現代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理性,是學科創始人以及他們現在的大多數執行者堅持的原則,即使解釋對這種假想的挑戰,已經是對原則的質疑了。
不久前,我才確信類似的文化革命曾經發生過,反文化者所支持的世界觀只有用“浪漫”來修飾才充分。我并不是唯一持這種觀念的人,在上一輪“浪漫熱”(romantic fever)爆發時已經有支持者與批判者偶爾比較過浪漫運動了。⑧ 不過看起來,我是唯一將這種同一性(identification)當作問題延伸而非問題答案的人。浪漫主義作為一種現象,一向引發強烈的情感,很明顯許多評論者能夠給反文化戴上如此標簽不僅僅是去除它的神秘色彩(demystify),而是解決如何評價它的問題。這種比較值得注意之處在于, 他們試圖通過對語境的分析來討論當代文化變遷(也就是說,可以回指到浪漫的對應物,或是將第一次浪漫運動的信念與態度投射到后繼者的觀念上),這種被認定的同一性的后果卻幾乎沒有論及。由于我能找到的對浪漫運動的這些“解釋”在形式上側重探究歷史,強調法國革命和工業革命之類的特殊事件,將反文化認定為“浪漫”并不能解釋它為何發生。
并不是說,學者們對于浪漫運動、浪漫主義者及其作品缺乏學術興趣,恰恰相反,這類作品多得驚人。另一方面,相當數量的作品在形式上是文學、美學和哲學的,另外附上些社會政治史或知識分類史(intellectual variety),盡管我發覺很多學者的工作是無法估價的,然而并沒有像樣的社會學討論。也就是說,學者們至少將浪漫主義視為社會文化運動,將其在功能上與新興的工業社會相聯系,然而,我卻找不到任何對所謂現代生活的“浪漫因素”的檢視,將“浪漫”與“理性”相對。如果60年代和70年初的事件僅僅被作為浪漫主義的最新宣言來看待,很明顯,它需要被理解為現代文化一個持續的元素。
我發現浪漫思想對于社會學的影響經常被討論,但是很少有相應的浪漫主義社會學來加以平衡。浪漫思想與啟蒙⑨ 運動的觀念和態度(至少部分地作為一種反動),是將社會學造就為一門學科的主要知識材料。這門學科的大部分創始人仿佛超越了他們自己的浪漫趨向,采取了進步論的歷史觀,將浪漫主義視為不同于現代生活中的任一“反動”因素,視為一種植根于過去而為文化和社會的理性因素之手滅絕的現象。正如曼海姆闡述的,這已經被當作一種既定的常識。 當這些想法在我腦海中結晶的那些年,我的精力轉向研究新、舊的浪漫主義,與此同時我教授宗教社會學的課程,那是我興趣所在的主要領域,我的社會學事業也從此起步。很自然地,我開始關注與韋伯作品相關的問題,“清教倫理論”成為我研究的天然焦點。在我教授這一課程期間,我對倫理的命運產生了興趣,隨著時間流逝,這個論題的問題意識越來越強。盡管社會學家并未將此作為詳細研究的對象,其他領域以及理由充分的大眾常識卻提出了要求,共同致力創建一種觀點,韋伯所確定的倫理,在現代西方工業社會已不再是主流的社會倫理,取而代之的是與之相對的“其他方向的”、“社會的”或是“表現性”的倫理。我一開始并不傾向挑戰“清教倫理論”,我只是被這個論題所呈現的眾多困境和矛盾所困擾。
首先,那些被當作支持“新教倫理衰落論”(decline of the Protestant ethic thesis)的研究很大程度上表現出僅憑印象和新聞式的特征。更令人困擾的事實在于,正如懷特(White)所說,大部分的作者涉入發展一種“知識意識形態”(intellectual ideology),他們涉及的是對文化變遷方向的悲嘆而不是描繪。其次,任何研究必然存在著方法論的困境,盡管它本身在時間上僅僅只是一張“快照”,卻被用作評述歷史過程,由于缺乏適當的縱向研究,必然導致對過去和現在的假設。似乎這些困境仍不足夠,此后許多爭論顯示極少有討論是關于新教倫理如何甚至何時在想像中被推翻的。曾經有人宣布關于眼前的和即將到來的新教倫理之“死”一系列聲明,奇怪的是,另一天它又活過一次,死去一回。更有甚者,倫理是如何被斬盡殺絕,到底是社會經濟還是文化該對“謀殺”倫理承擔更多責任,存在相當的觀點差異。此外,從16世紀初新教倫理首次被闡明到20世紀它被宣布推翻存在令人困惑的歷史脫節問題。難道它真的在四百年間始終絲毫也未受到挑戰?由于這些原因,我開始越來越懷疑既定的觀點,開始傾向于覺得無論什么力量致力于挑戰新教倫理,它們不可能僅是存在于現在,而是回溯到20世紀以前的系譜。歷史紀錄中的鴻溝,使我感覺到需要更新韋伯的分析,也就是說,我認為需要繼續他關于西方宗教傳統發展以及它與社會、經濟生活關系精致詳實的討論,跨過《清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所表現的時間線,這條時間線某些社會學家認為在1920年前后,而我認為早至1620,最好在1720年。
大約正在這時,我的兩大興趣首次會師,本書的觀點在我頭腦中開始構思。對我而言,如果文化反清教力量可能本質上是“浪漫的”,它們也與消費相關;如果在60年代,消費與浪漫主義相關;那么它們可能一直如此?可能,存在一種“浪漫倫理”致力于促進“消費主義精神”,正如同韋伯曾經假定“清教”倫理促進了資本主義精神?當然,正是“浪漫文化運動”時常被作為清教主義的“天然敵人”。
這種觀點足夠促使我以一種新的視角觀察浪漫主義,同時著手查找消費以及消費者行為的材料。不久后,我讀到麥克·肯德尼克(McKendrick)、布魯爾(Brewer)、普拉姆(Plumb)的書,我所讀到的內容激勵我深化這一論題。我將在第二章討論此書。
此書作者們繼續使用“消費革命”一詞,用以指代他們所評注的明顯與浪漫運動同時的變遷。我此時不僅認為,既然有必要在細節上檢驗兩者的聯系,本書的標題也自然地浮現在腦海。除了將它稱為“浪漫倫理與現代消費精神”,我還能起別的什么名字呢?
此時,我的論題證據積累希望十足,不幸的是,我碰到了最麻煩的障礙。那就是,仿佛并沒有理想的現代消費主義理論。
韋伯的論題建立在一個假想之上:工業革命構成了人造產品生產體系最重大的劇變,這種劇變史無前例,與現代資本主義的產生相關。在他的時代這不是韋伯一個人的假想,大部分社會理論家持有這種假想,它也是可觀的研究與討論課題。論爭主要rage它的原因,而不是它的形式,然而對于生產性資本主義構成卻存在共識。對于消費卻不是這樣。如果如今看起來是這樣,經濟史學家開始持有觀點,工業革命也見證了消費的重大革命,至于“現代”消費的本質是什么沒有確切的理論。
這主要是因為消費行為的對象完全被經濟學家獨占,他們典型的研究是通過非歷史的假想框架,認為消費行為對于任何人任何時間都是基本相同的。我很自然地求助于那些將注意力轉向消費的社會學家們,主要是凡勃倫(Veblen Thorstein,也譯維布倫,1857—1929,美國經濟學家和社會學家)和桑巴特,然而我發現很少有人真正從事這個問題關鍵之處。我只能獨自面對令人畏縮的重任,力圖創建一套現代消費主義理論。正是因為這個原因,在這個課題上韋伯僅用了十多頁(現代資本主義精神),我卻用了四章來討論。首先,創建現代消費行為理論是必需的;其次,經典的經濟學和凡勃倫都沒有提供一套合適的理論;第三,享樂主義的社會行為理論完全不同于當前經濟學的實用主義為基礎的視角;第四,現代享樂行為理論確實可以說明現代消費行為的獨特之處。
由于我并不急切地斗膽涉足其他學科,我并未毫不遲疑地著手這一野心勃勃的行為。我對肯德尼克、布魯爾與普拉姆對18世紀消費革命的敘述的檢視,使我確信,他們在闡釋上的無力是直接源于缺乏準確的理論,這并不只是代表在經濟學部分的失敗,而是包括社會學家在內的所有社會科學家的罪過。而且,從他們提供的材料以及我關于60年代和第一次浪漫運動的研究可以清楚發現,諸如時裝、浪漫愛情、品味與小說閱讀等現象被社會科學家們所忽略。這些現象深深地暗示著消費革命與現代消費行為。
這些課題為人忽略,這一事實在我看來是一個重大的遺憾,盡管有些現象,比如時裝與浪漫愛情,對社會學家缺乏吸引力是因為有影響的理論視角來suggest它們的重要性,它們在現代社會的無處不在已經足以不言而喻了。社會學家們的忽略基本上可以被視為源自偏見,源自假想先于調查的潮流,認同這些現象在某種方式上是微不足道的,是不值得認真研究的。有一種觀點部分地是從生產論(productionist)經濟學偏見派生出來而彌漫到整個社會科學界,這種觀點與潛在的禁欲清教主義態度相關。這些課題未被適當地研究應當歸因于這種偏見的因與果。毋庸置疑,如果社會科學家們許久以前就將注意力轉向對這些現象的認真思索,現在偏見也不會在各個學科中流行。在凡勃倫的作品中,縱容教化消費實踐的趨勢非常明顯。他的后繼者也是一樣,里茲曼(David Riesman, 哈佛大學社會學教授),加爾·布雷思(John Galbraith)則將此鼓吹為一項美德。即使意見相左的兩位當代大師赫伯特·馬爾庫斯(Herbert Marcuse)與丹尼爾·貝爾(Daniel Bell)也成為相同的趨勢的例子,傾向批評與譴責而不是調查和解釋。
然而,此時另一個同樣令人困惑的問題浮現出來。如果,按我所想像的,浪漫主義有利于18世紀末19世紀初英格蘭現代消費行為的出現,有利于“消費倫理”的合法有效,那么從新教主義派生,又與“生產倫理”相悖,如何能夠在同時同地運作?是否真的存在兩種社會倫理,它們在形式上相對,卻又并肩相存,一個支持生產,一個支持消費?如果是這樣,是否有兩個社會群體(group)分別擔當文化載體?韋伯的論題明顯與生產倫理和新興資產階級相聯,那么有可能消費倫理與貴族相聯?然而事實證明需求的新潮流來自新富(nouveaux riches)。可以得出結論, 資產階級同時擁有清教倫理與消費倫理,這一觀點與我認定浪漫運動主要與中產階級特征有關相吻合,不過這帶來新的社會學迷惑。
我逐漸開始感到消費文化研究中的一個歷史問題:如果沒有解決潛在的理論問題:特別是關于現代消費主義核心的變遷機制,就無法成功地解釋消費革命來源。這一變遷機制無論如何轉變,都暗示著文化過程。因而,正如同韋伯從事他關于生產革命來源的原創研究時關注歷史、經濟與社會學問題,我開始關注到這些密切相關的問題。
正是在此時,我認識到我正在寫作的論文對于現代工業社會及其文化的出現的傳統既定觀點是怎樣一個激進的修正,遠超于我原先的想像。首先,在工業革命名義下的巨變應當被視為集中于消費的革命,正如集中于生產的革命。很大程度上,這一點是由經濟史家提供的證據清楚顯示的,他們仿佛是漸漸改變主意形成這個觀點。如果,他們在這一點上是正確的,那么在他們覺醒后會緊跟有一系列其他結論。例如,“消費倫理”必須一開始就存在于工業社會,而不是后來出現的,這當然暗示著新教倫理與無論哪一種被倫理合法化的消費很大程度上是同時的現象。這引發以下的想法,可能清教與浪漫互為文化替換物(cultural alternatives),正如社會學家通常視為的那樣,這種想法不僅挑戰了流行的“文化矛盾”(cultural contraction)論,也質疑了被廣泛接受的假想:“理性化”是資本主義與現代文化的主要特征。所有這些推論仿佛都拒絕廣泛流傳的錯誤,將工業革命僅僅當作以生產為手段構成的激進轉變。這當然,由于韋伯采取了狹隘的觀點,將清教主義的理性與美學特征挑出作為至關緊要的影響:如果,他錯在明顯忽視了相伴的消費革命,基督教傳統的其他因素可能會對現代經濟產生重大影響嗎?這些都是我開始著手此書時腦海中浮現過的想法,我轉向韋伯的原文以便啟迪與指導我的任務。
馬克思·韋伯作為學者和社會學的“創始人”在社會學家中享有盛譽,社會學家們更多的是書寫他以及他的作品,而不是仿效他。也就是說,有一個巨大的韋伯產業,而沒有人對他開創的文化社會學付諸努力。有可能沿著他的足跡這一任務本身明顯令人畏懼,除此之外,很難說清事情為什么會這樣。在韋伯那個時代,由于他那淵博的學識沒有學者可以成功地仿效他,自從世紀之交以來學術界日漸學科專業化,他那種范圍廣、多學科的風格實際上更不可能被任何人效仿。這并不意味無法嘗試,正如韋伯本人描述的,對現代社會的社會文化變遷的洞見可能只能通過不同領域的探尋才能獲得,諸如宗教與經濟,通常被認為是沒有聯系的,這種洞見因而也可能只是刻意打破傳統的學科界限。即使其他學科的學者會對這些不當行為側目以視,社會學家并不是太過羞怯去越界。部分的答案在于,許多高度贊賞韋伯的社會學家在研究文化時,實際上選擇跟隨馬克思,所關注的不是韋伯成功運用的獨特類目,而是關注“意識形態”的概念。
反諷的是,另一個主要的原因可能正是對韋伯作品及其所蘊含的世界觀的尊敬,他所贊成的理性世界觀(rationalistic Weltanschauung)想像出了他終生致力研究的現象的實際消失。盡管韋伯的興趣廣泛,包括機制例如科層制,勞動分工,法律與國家這些仍是現代社會的重要部分,然而他主要的興趣還在于宗教,如果不是這一現象確實消失,他對于去魅(disenchantment)和理性化整體過程的強調就失去了影響力。對于現代社會誕生的主要特征,他的觀點看上去,宗教的助產士功能是不容置疑的,接著它在世界舞臺不再有任何重要作用。To the extent, 社會學家接受了韋伯式(weberian)的觀點(當然不僅僅限于韋伯的觀點),他們可能原諒了假定從事他所擅長的特定形式文化分析沒有什么意義(point),因為韋伯采用的很多概念,比如神正論、禁欲主義與預言看起來僅僅適用于信仰與價值的“宗教”體系。
稍作反思,就能暴露這種假想的錯誤,然而,正如韋伯使用和發展了術語,與宗教的必然聯系并不多于超凡魅力(charisma),是在韋伯所有的術語中最明顯突破了概念窠臼的。當然,韋伯的分析風格對當代文化現象看起來并不比他曾研究過的宗教的歷史形式更有用。這也是本書潛在的假想。
但是那些以宗教作為特定研究領域的社會學家通常對他們的研究對象會采取奇怪的含混態度,在研究現代時具有涂爾干的特色,在回顧過去時卻是韋伯式的。也就是說,他們自作聰明,在尋求當代行為與機制時,采取涂爾干式對“宗教”功能和本質的洞見,當作富于洞察力的時尚;而研究過去時,他們緊隨韋伯,采取傳統的被視為“宗教現象”的觀點。韋伯雄心勃勃的計劃是研究世界宗教及其截止于他那個時代的歷史發展。
然而由于韋伯沒有將他對神學體系演變的研究繼續到18世紀,在文化社會學出現了一個尷尬的時代陰影。這段時間將封建和前現代社會與當代社會分開,那時可以想見所有重要的社會政治與文化運動可能以“宗教”的形式被宣告,并伴以被認可的神學。在當代社會中則是相反的假想大行其道。在中間這段時間——在1650至1850的關鍵時期,韋伯的“新教倫理論”已經談得十分清楚。不幸的是,太容易忘記韋伯的論題是針對特定問題而闡發,即現代資本主義為什么會首先在西歐出現,因而,不能對直到現代的西歐宗教思想發展嘗試做一完整而全面的敘述。
本書表明,對偉大人物表示敬意最好的方式不是僅僅贊揚他,而是仿效他,本書既是對學者的贊頌,也是對他名作的完善。本書不是作為《新教倫理和資本主義精神》的姊妹篇,也不是對它的注釋,或許它同時含有這兩種風格。本書主要觀點事實上目的是對韋伯完善,效果上是他觀點的鏡像,從這個意義上說,它是一本姊妹篇。韋伯關注新教主義與資本主義本質聯系的主張并沒有被否認,但是拓展了宗教理性禁欲(raional ascetic)與感傷虔誠派(sentimental Pietistic)兩方面對于現代經濟發展的貢獻。為了實現更具雄心的整體敘述,本書對韋伯的觀點作了些改進,特別是關于他對待新教主義的方式和對待新教主義“倫理”的合理構成的方式,以及對待它命運的方式。對韋伯的修正并不是對他主張的毀滅,恰恰相反,這些修正是為了解決接受他的論題所帶來的長期存在的問題。 本書依照韋伯的榜樣,第一部分勾勒出“消費精神”,接下來第二部分討論“新教(浪漫)倫理”,這一步驟由于需要以一定篇幅討論現代消費主義的本質而變得復雜。最后,它的精神具體到自給(automonous)自我想像(self-illusory)的享樂主義,這樣便可以轉向勾勒出推動它產生的文化倫理。
在對待方式上的不同是韋伯自己作品的直接后果。因為,他認為新教說教影響了對于資本主義精神有益的倫理發展,當他專注于勾畫出那些新教說教時,必須從那些self-same的說教中清理其他倫理的來源。用于證明消費合法的倫理規范(ethical code)的基礎很大程度上可以被描繪為一個從韋伯描述的“新教倫理”區分出來的過程。盡管有這些差異,本書潛在的結構盡力與韋伯相對應,強調“文化倫理”在引入經濟行為的“現代”模式時的中心地位。展示它們的一致(congruence)與它們的心理與文化聯系。
這并不是傳統意義上的對觀點史的運用,卻像韋伯的作品,推行某種意味的取向(approach),這并不只是贊成思想(mind)與精神(spirit)是歷史發展最終力量的一面之詞,而是承認,當觀念運動構成受人重視的人們的“活的信念”(living faith)或是(formulated aspirations)之時,觀念運動是社會變遷的主要原因,依照韋伯的榜樣,由既定信仰而產生的行為的真正本質被視為有問題的(problematic),它本身也是研究所關注的中心。因而,本書最主要的關注在于追蹤社會風俗(manner),正是在社會風俗中,社會真、善、美觀念的變遷影響行為模式(patterns of conduct),不是任何直接約定俗成的時尚(prescriptive fashion),而是觀點為確認特質的行為(characterconfirming conduct)給出了方向。雖然本書并不追隨物質力量對于觀念構成與接納的影響的觀點,但也不忽視這一觀點。
諸如聲名赫赫的阿瑟·洛夫喬伊⑩ 與觀念史更為相近,他關注的是默許假想和預設形式的觀念與“思想”及外在的信仰體系。洛夫喬伊稱之為人們的“無意識的精神習慣”(unconscious mental habits)可以清楚而意味深長地理解為他們的倫理行為(ethical conduct)與公然的信條(professed creeds),正是在這種語境下文學批評的材料被認為特別有價值。與此同時,從術語的完整意義上如同知識史(intellectual history)而非文化史,存在一個忽視大眾(popular)與民間(folk)信仰的趨勢,以便集中更高雅(higer)文化, 如果不是僅僅集中高雅文化(high culture)。對此的論證(justification)有賴于更大的影響,后者建立在總體思潮,特別是倫理理想的闡述(formulatin of ethical ideasls)上。正是由于這個原因,在此后的篇幅中,幾乎沒有涉及工人階級。 與此同時,本書的調查分享了觀念史的跨學科特性,充分利用了洛夫喬伊認為用來建造“分離學科圍墻”的“大門”。它有一種紋理不規則特征,不僅是源自從通常的學科語境之外檢驗課題,也源自使課題與拒絕它們的意義達成一致。傷感主義(sentimentalism)被視為重要的社會倫理(socioethical)運動,而不是僅僅影響了浪漫主義的不走運的文學潮流;類似地,時尚被視為顯示了現代中心價值的一個重要的社會美學現象,而不僅僅是精巧宣傳的銷售詭計。本書涉及了一定數量對現代社會誕生傳統說法的言外之意的閱讀,不僅挑戰了歷史和社會科學中生產論偏見,也挑戰了現代文化發展具有不斷增長的理性化特點的假想。
當然,任何人承認這種“完善”韋伯的主張,都會引發對將兩個論題整合的整體更深的思考。如果承認,平行的文化進程與現代生產相聯而產生,又與現代消費相聯而產生,那么等式兩邊到底有什么聯系呢?如果生產論偏見影響了韋伯關于工業革命的觀點需要修正,那么它應當被消費論取代嗎?還是存在對現代經濟的產生有完整的“平衡”的論述,從而避開這個問題的兩者取一?這個問題饒有興趣,有待于其他后繼的作品來思考。
注釋: ① 牛津英文詞典1969年版,“浪漫”詞條(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1969,s.v.“romantic”)。 ② 不是所有的廣告都使用“浪漫”版本,當然不是所有的消費具有“現代”特征。 ③ 可以在皮斯關于現代廣告的產生中找到此類觀點。參見奧梯斯·皮斯:《美國廣告的責任:私人控制與公眾影響,1920—1940》(The Responsibilities of American Advertising: Private Control and Public Influence, 1920—1940, New York: Arno Press 1976, pp.40—41)。 ④ 這一類反應的例子可以在大衛·馬丁(David Martin)的《無政府與文化:當代大學問題》(Anarchy and Culture: Problems of Contemporary University),London:Routledge and Kegan Paul,1969)中找到。 ⑤ “the Age of Aquarius”,水瓶座時代,占星學名詞,可能由于BEATLES的同名歌曲(1962)而風靡一時,指1960年。當時有一批人根據占星學分析而表示,水瓶座時代即將降臨,在這個時代中,人類的精神層次將會提升,愛與和平將降臨大地。從而興起了所謂“新時代運動”,也稱水瓶時代運動,是一群西方的知識分子,對于過去過于重視科技與物質,而忽略心靈與環保的一種反動。 ⑥ 我見到格外有用的匯編包括約瑟夫·伯克(Joseph Berke)編輯的《反文化》(Counter Culture, London: Peter Owen, 1969);杰里·霍普金斯(Jerry Hopkins)編輯的《嬉皮檔案:地下報刊筆記》(The Hippy Papers : Notes from the Underground Press. New York: Signet Books,1968);彼得·斯坦西爾(Peter Stansill)與大衛·扎恩·麥羅(David Zane Mairowitz)《BAMN:反判宣言與曇花一現1965—70》(BAMN: Outlaw Manifestos and Ephemera 1965—70.Harmondsworth, Middx: Penguin Books,1971)。 ⑦ 主要的文本為肯尼斯·維斯修斯(Kenneth Westhues)編輯的《社會的陰影:反文化社會學研究》(Society's Shadow: Studies in the Sociology of Countercultures. Toronto: McGraw-Hill Ryerson,1971),與弗蘭克·穆斯格魯夫(Frank Musgrove)《癡迷與神圣:反文化與開放社會》(Ecstasy and Holiness: Counter Culture and the Open Society. London: Methuen, 1974 )。 ⑧ 這種對比可以在布克(Booker)的作品中找到,他評述了20世紀60 年代和第一次浪漫主義之間氛圍上“封閉的平行”(Close parallel)。 ⑨ 關于浪漫主義在現代思想的發展中所起作用可見H. Stuart Hughes《意識與社會》(Consciousness and Society. Brighton: Harvester Press, 1979)。 ⑩ Arthru Lovejoy,1873—1962,美國哲學家。以對觀念史和知識論的研究而著名,主要著作為《存在的巨大鏈條:觀念史研究》(1936),《觀念史論文集》(1948),《反對二元論》。他的晚期作品《對人性的思考》(1961)、《理性、悟性與時代》(1961)都和浪漫主義相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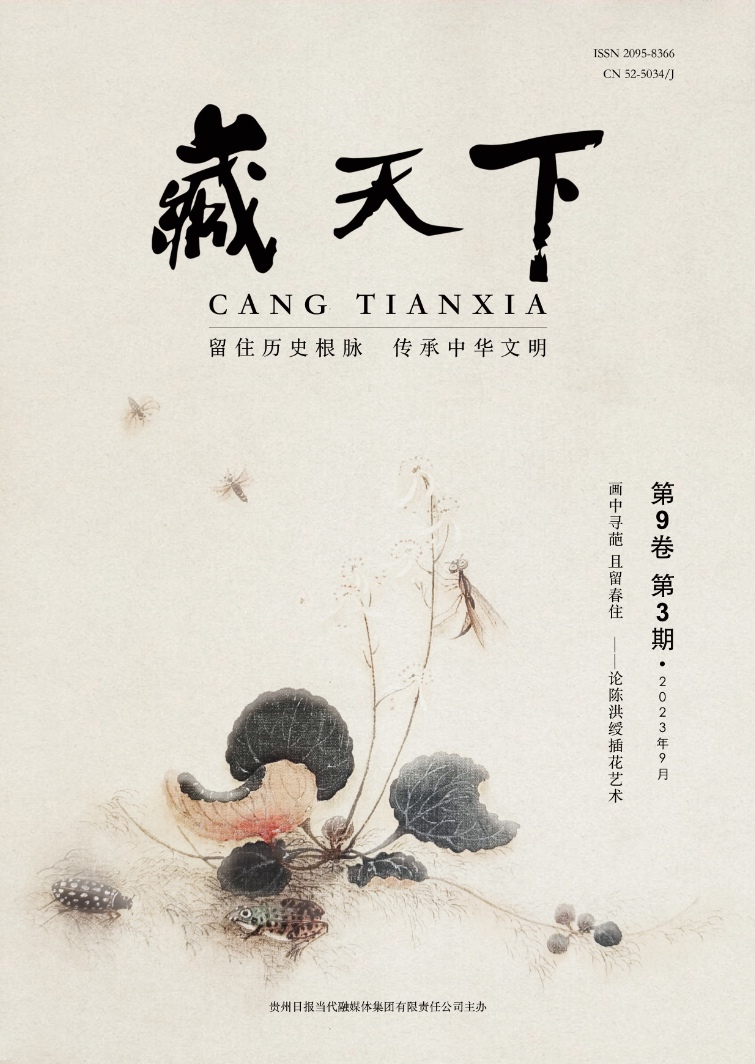

.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