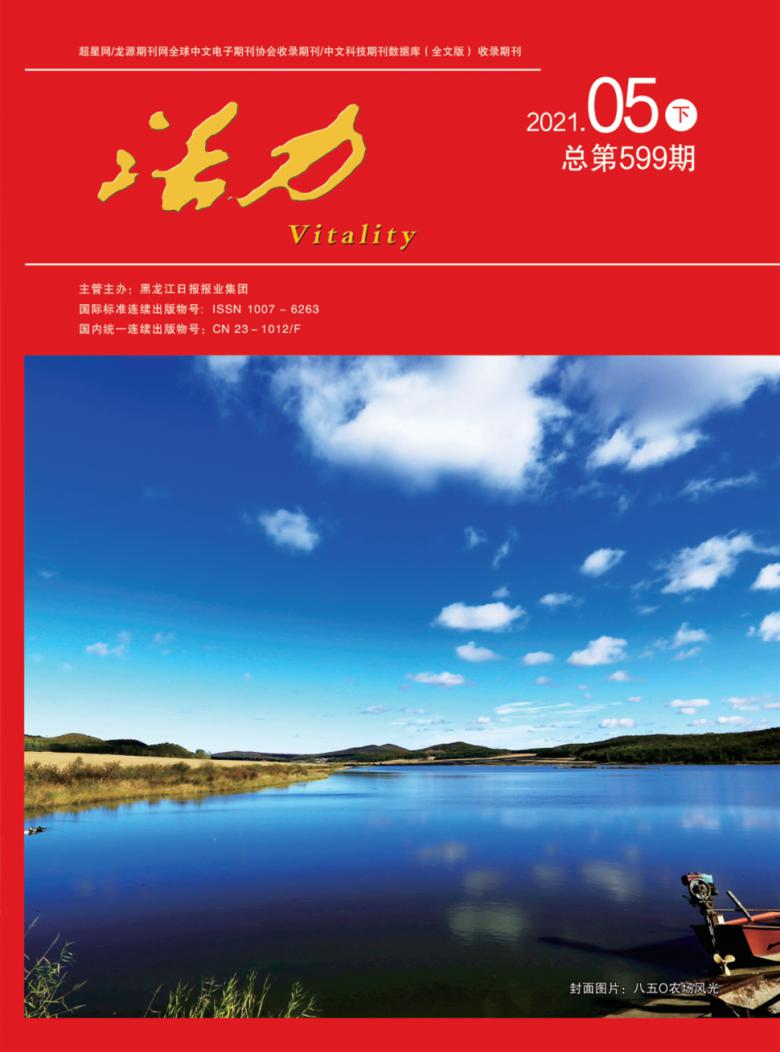從民營企業的角度看WTO
陳江淮
去年12月11日在卡塔爾首都多哈,我們的中央政府與世界貿易組織達成了準入協議。和任何個人新加入一個組織的興奮心情一樣,全國上下的輿論在那陣子也是極為亢進的。然而仔細梳理一下這段時間的新聞報導以及背景分析,可以發現其中的反應又是矛盾的,一種宣傳調子的色彩可謂是歡欣鼓舞:十五年的漫長期盼終于變成了現實,我們即將步入全球自由貿易的“歡樂之谷”。另一種調子則是憂心忡忡,擔心要“變天”;認為迎接我們的將是一個殘酷無情的“動物兇猛世界”,一時間諸如“與狼共舞”、“來勢洶洶”、“大浪襲來如何應對”之類帶有點血腥味的字眼充斥著大小媒體,氣氛渲染得不說讓人恐慌,至少也是使人的皮膚發緊。搞得似乎咱們這個多災多難的國家剛過上幾天好日子就要像羊羔落入虎狼之口一樣,令人不寒而栗!
多少年的實踐證明,說得太美好的事情無論對國家、對企業、對個人都不會有的,因為天上不會憑白無故地掉餡餅;描述得太壞的事也未必很多,假如加入WTO算是的話,相信我們的政府絕不會自己設套子自己往里鉆的。
需要提醒人們注意的是,WTO有它自己非常準確的界定含義,入世對我國的影響無論如何不是一個無限大的含義。WTO的職能主要體現在制定規則、開放市場、解決糾紛三個方面,因此挑戰首先是針對政府的。世貿組織主要管政府,對企業沒有太直接的影響,有影響也是間接的。
當然我們不能以為影響是間接的就可以等閑視之。WTO的一個主要要求是在貿易方面實行國民待遇,即要求對各類企業都要同等待遇,這樣的規則對廣大中小企業較為有利。倒是那些長期以來倍受國家保護、照顧的企業,往后的日子反而是有點那個了。
但即便從企業的角度看,雖然“與狼共舞”是入世后人們使用最多的一個詞匯,考慮到目前中國500強企業的年平均銷售額僅為世界500強的2%,說句老實話,我們暫時還沒有上升到和人家共舞的層面,現在就說“過招”只能是抬舉自己。
更況且體系規則的建立并不會自動地實行,市場經濟需要建立在誠實守信用的道德基礎之上,這也同樣需要時間的熏陶。
人在同陌生人初次打交道時一般都很謹慎,心理上很戒備,這是正常的。國家之間也差不多。因此當我們乍接觸一個名叫“WTO”的玩意,在預測它闖進來后對原有經濟秩序的沖擊時,難免有些過激反應,這是我對前一階段WTO熱的一個大致看法。何況許多人對WTO的實質并不懂,只是把別人的觀點不加思考地拿過來套用,其結果只會起誤導作用。
其實WTO對不同性質企業的關聯度是不同的,民營企業在未來WTO背景下的前景如何呢?下面我試著談一點學習體會。
必須認識到,經濟全球化是一種大勢所趨,雖然其間交織著各個國家和地區錯綜復雜的利益關系和激烈的競爭,必然要經過許多曲折和反復,但這種潮流是任何人也無法阻擋的。
不管經濟全球化給各國帶來什么樣的后果(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人們只能是接受而不是逃避。中國現在的首要任務是加速向現代化邁進,其中進一步融入經濟全球化進程就是實現現代化的一個必備條件,而WTO正好是為我們提供了一個盡快融為一體的可能性。
打個比方說,加入WTO猶如給我們提供了在世界舞臺上演戲的機會。但舞臺和演戲不是一碼事,它并不足以保證演出成功,演砸鍋也是可能的。
也就是說加入WTO只是讓我們獲得了擠身于世界經濟繁榮的入場券和參賽資格,并不能保證我國經濟將順利發展。那種以為一經加入就萬事大吉的想法是幼稚的,也是不切題的。我們只能說相反的命題——如果不加入麻煩更多——成立。
我想以上這個判斷對國家對國企對民企都適用,因此比機會更加重要的是能力。與其臨淵羨魚不如退而結網,要想生存下去,關鍵還是要利用加入WTO后的過渡時期苦練內功,以全力提高我們自身的競爭力為第一要義。
時下人們經常在議論入世后對哪些產業有利、對哪些行業沖擊更大。這些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加入世貿組織為中國奠定了進一步改革的制度基礎。在當前中國各項改革都到了一個瓶頸(甚至騎虎難下)的時候,其意義一點也不亞于1978年著名的中共中央十一屆三中全會。
回顧歷史,前二十年的改革特征概括起來可以說是“摸著石頭過河”,雖然也同樣是沒什么經驗,但基本上是還原和矯正在之之前被錯誤地扭曲的東西,是“撥亂反正”,因此并不是毫無軌跡可尋。但以后的路怎么走,人們首先在理論上就遇到了極大的困難。年紀大一點的人也許還記得,前總書記趙紫陽曾經公開坦承“社會主義到底是什么,我們也搞不清楚”。我在這里重提這句話不是為其翻案(這句話當然還是錯的),而是說明中國的改革只有撇開一些目前暫時看不到結果的爭論,通過融入全球化,依靠廣大人民的實踐、依靠經濟活動自發的改革趨向去尋找進一步的發展,這才是沒有最好辦法的最好辦法。
清醒的事實告訴我們,中國的經濟問題、制度問題、利益集團問題以及地方保護等等問題目前制約著改革的前進。漸進式改革雖然較為穩妥,但也固化了人們的利益關系,某些部分甚至構成了繼續深化改革和擴大對外開放的阻礙。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上一直都有在迫不得已的情況下借助外力求發展的先例,這一次也不例外。
加入WTO后,通過承諾在一定的過渡時期后實施世界貿易組織基本原則,這種外部要求自然成了成為推動國內市場完善,使之朝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一既定目標前進的動力。也就是說,加入WTO之后,我國改革的動力不僅要依靠生產力的內部釋放(通過調整生產關系和上層建筑),而且也將由強大的外部力量所推動。
WTO的根本原則要求其成員國必須全面實行市場經濟。作為改革開發的產物,民營企業是市場經濟的天然朋友。由于它從來不屬于嫡系,雖然沒有得到過什么好處,也沒有什么“原罪式”的負擔,因此越是繼續開放越是有利。因此對于WTO的到來,民營企業自然持熱烈歡迎的態度。
首先應該認識到,我們討論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得與失是站在企業立場看問題的,對于老百姓來說其實是增進福利的事情,這是兩個不同的境界。
其次要看到,世界貿易組織是一個擁有142個國家和地區的大家庭,其中比中國經濟落后的發展中國家占絕大多數。既然它們在世貿組織(以前是關貿協定組織)中已生活了很多年,其國民經濟不僅沒有被沖跨,相反還從中受了不少益處,中國這個世界貿易排名第七的大國還擔心什么?!
記得美國經濟顧問委員會代表團1997年訪華時,曾到北京大學的中國經濟研究中心與中方學者進行了一次座談。會上他們問了一些很直接的問題,反映出在是否接納中國這件事上美國人有顧慮。他們怕什么?怕的是中國的改革方向是不是會繼續朝著市場經濟進行下去,中國的國有企業會不會在加入世貿后因為特殊的身份在國際市場進行不平等的競爭等等,所以說感到擔心的不僅僅是咱們自己。(關于對立雙方互相防范的心理,央視“實話實說”節目曾經播過這樣一個案例,拾金不昧者與失主之間在還錢過程中一開始就生波折,雙方都十分警惕,都在干防止對方敲詐的事情。這個故事很經典,企業也經常有此類事情發生,打工者和雇主的心都是懸著的。)
又比如,在WTO談判過程中我方一直強調中國是發展中國家,而西方卻總是要求我們盡可能地開放市場,雙方的立場和邏輯在很長一個時期看上去不能統一,其實這里面既有利益的分歧,也有溝通的問題。記得美國前首席談判代表巴舍夫斯基說過,他們從來沒有認為中國不是發展中國家,但由于中國是大國,在國際貿易中,大國(哪怕是發展中國家)同樣可以影響國際貿易價格,所以中國不能適用一般發展中國家的條件。另外值得一說的是,不要以為在談判中讓步就是吃了大虧什么的,其實談判就是一個讓步和妥協的藝術,讓步有時候并不是以犧牲自己利益為代價的,而是在整個談判過程中形成共識的一個手段。只有善于溝通,才能找到利益平衡點,才能達成協議。
既然世界上大多數國家的生活是極其相似的,人的心理反應也差不多,加入的一方和接納的一方心存疑慮也就不難理解了。所以說憂患是正常的(“生于憂患,死于安樂”嘛!),恐懼則毫無必要。厲以寧教授說得好,只有夕陽企業,沒有夕陽產業。即便是那些暫時受打擊比較大的企業,關鍵也還是在于應對措施的正誤,不要把企業的興衰簡單地歸罪與人。
再舉一個例子。日本戰敗初期是接受盟軍的全面管制,為了保證盟軍司令部制定的“以日本經濟的獨立作為目標的企業合理化和經濟安定九原則”方針的完全實現,總司令部請來了原美國底特律銀行總經理道奇公使。道奇來了,在經過一番調研之后,他指出:
“日本當前的經濟是由美國的援助和日本政府的國家補助金構成的兩只腳的高蹺經濟。”
“除非切斷這兩只腳,靠自己的腳站起來,否則日本的經濟就難以重建。因此即使發生摩擦也應實施九原則,切斷虛假的腳——高蹺。”
在這種見解下,他指令日本政府設法把包括特別會計、公團、復興金融金庫在內的預算收支做平衡,廢止由復興金融金庫融資和貿易資金操作的補助金。一開始人們認為這會給日本的企業帶來危機,許多人心存疑慮,但后來的許多經濟史學家都承認,盡管當時一度出現了既不是通貨緊縮又不是通貨膨脹的所謂“模擬式通貨膨脹”,這一政策成了日本經濟獨立的基礎。
中國現在的經濟形勢在某種意義上與上述情況有點類似,WTO的到來也許短時間內要和一些企業“作對”,長遠地看問題,利國利企利民。
對中國的民企來說,入世意味著獲得了在中國國內市場乃至國際市場上與同行平等競爭的機會。有數據表明,此這之前國家對個體私營經濟在經營范圍上有限制的規定高達60多項。從產業領域來看,目前限制個體私營經濟進入的領域只有極小一部分關系到國計民生,大部分是眼下市場投資回報率較高的行業,如電信、保險和金融機構,而入世后這一部分有相當多的已被列入逐漸對外開放的領域。
根據國民待遇原則,既然對外開放了,對內當然也放開了。以前民營企業在諸如市場準入、上市融資、進出口等方面的不平等待遇將會逐步取消。至于那些希望謀求海外發展的民營企業,出口通道也更加暢通了。
但我為什么要說民營企業是“理論上”拓寬了生存空間呢?因為要考慮到中國的國情。實際情況表明,在很多領域,對內開放要落后于對外開放,民營企業在未來的市場開放中也許不會比以前更容易搶占先機。說不定在入世以后,呼吁國民待遇的不再是外資企業,而是我們的民營企業。
關于這一點,我們目前能夠說的大概只有“拭目以待”了。但即使出現這種現象,我想也是過渡性的。
民營企業的成功依靠的什么?粗算起來大概有創業者吃苦耐勞、比國營企業更加廉價的勞動力、經營手法相對靈活、人際網絡優勢這些方面(說不出口的內容可能還包括逃稅等不太光彩的事情)。加入WTO之后,這些維持企業存在的東西可能面臨很大的困難。另一方面。國有企業原先沒有得到充分發揮的能量反倒有可能被釋放出來。
民營企業和市場經濟是天然的結合,但國有制企業與市場經濟也是可以結合的。在與集體、民營企業競爭中,國有企業在生產成本和市場營銷方面不具備優勢,這是其缺點,但國有企業的研發能力強,員工綜合素質高,這些方面民營企業是無法望其項背的。
經濟學家張維迎認為,從一個企業的長遠發展來講,有三點非常重要,第一是如何積累互補性的知識,這是企業的核心競爭力與動態競爭力;第二是如何建立一個良好的信譽,這是企業的價值所在。最后,企業要學會從競爭戰略到合作戰略的思維轉變。前兩點我十分贊成,第三點我覺得改為“企業要學會把發展戰略細化實施的本領”似更好。
為什么現在的許多企業沒有積極性去積累互補性的知識,這與企業的產權制度有關。各級經理人員因為可以理解的原因(缺少起碼的職業安全感),都在積累如何使企業依賴于自己,而不是自己依賴于企業,這樣他們就很難有積極性去積累這種互補性的知識。以上三個問題看似國有企業做得不好,實質上許多民營企業也做得不怎么樣。
在WTO到來之前,各種不同性質的企業有不同的規矩制約著,還有許多規則管不到的地方。現在大家實行一個規則了,對民營企業既是好事也可能是“壞事”。規矩執行起來也有它比較利害的一面,我以一個小故事為例。
中國WTO談判首席代表龍永圖(現任外貿部副部長)當年在英國進修時經常同他的指導導師“抬杠”。
在有一次“吵架”中,那位英國老頭冷不防問龍永圖一句題外的話:“請問在你們中國,水是從低處往高處流還是從高處往低處流呢?”
龍永圖不敢撒謊:“高處向低處”。
老師隨后意味深長地說:“正如不論在世界何處,水都是從高處往地處流一樣,難道在你們中國水是從低處往高處流嗎?作為整個經濟的運行規律來講,應該說只有一個,就是市場經濟的規律。”
當時的龍永圖是不服氣的,但十來年以后,他終于愉快地承認老師當年的話是對的。
入世后人們的規則意識肯定會大大加強,市場經濟就好比是籃球比賽,企業就好比是場上的運動員,在正常情況下,運動員會互相配合打球,對裁判的信號會有合乎邏輯的反應,但如果有的運動員在場上專門踢人家的腳、老是走步犯規、投自家藍筐,那這場球就無法打。
有的民營企業過去能夠成功,也有巧妙借助規則漏洞的成分。入世以后,隨著外資企業更多的進入,他們的法制觀念、知識產權意識是非常強的,屆時那種“遇到黃燈抓緊走、碰見紅燈繞路走”的現象恐怕會越來越少了吧。對于民營企業來說,這是利好、還是利空呢?
縱觀二次世界大戰之后世界經濟的發展軌跡,我們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先是由于拉丁美洲國家的經濟衰退才有了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崛起,而隨著1988年日本經濟的被淘汰出局(一直到現在日本都還在苦苦追尋經濟重新持續增長的“生長點”),這才給了中國一個機會。原先日本是世界制造業大國,如果不是它的“主動退卻”,中國雖然也在發展,但肯定不會像現在這樣的飛速發展。
如今機遇終于來了,中國的全球制造業中心地位已初步形成,沿海經濟帶正在成為世界產業鏈條中的一個重要環節。伴隨著世界500強跨國公司全球網絡的三大基地——生產中心、研發中心、管理運營中心——紛紛落戶中國開辦“分店”,全球化的經濟大潮勢必要席卷到中國社會的每個角落。
從國家的角度講,中國加入WTO的目標肯定不是僅僅停留在過渡時期的承諾上,而應該是借助WTO打造最強的企業和為國民提供美好的生活,這是我們加入WTO的最終原則和最終意義。
在這場絲毫不亞于一場革命的巨變當中,民營企業的天地是廣闊的,是應該可以大有作為,這樣的機遇應該要抓住。不過機遇往往只垂青于那些早有準備的人,我們準備好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