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鄉(xiāng)二元經(jīng)濟結構剛性的原因分析
李啟登
摘要: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已經(jīng)逐步認識到了要改變城鄉(xiāng)二元經(jīng)濟結構的重要性,并為之采取了一些措施,但并未有效改變二元經(jīng)濟結構,這一方面說明政策的不到位,另一方面也說明我國的二元經(jīng)濟結構存在一定的剛性,分析存在這種剛性的原因,并提出一些軟化對策。
關鍵詞:二元經(jīng)濟結構;剛性;軟化對策
一、二元經(jīng)濟結構的一般理論
“二元經(jīng)濟”最初是由伯克(Boeke,1953)提出的,他在對印度尼西亞社會經(jīng)濟的研究中,把該國經(jīng)濟和社會劃分為傳統(tǒng)部門和現(xiàn)代化的資本主義部門。關于發(fā)展中國家經(jīng)濟二元性系統(tǒng)的理論則出自于美國著名的經(jīng)濟學家阿瑟·劉易斯(Lewis,1954),劉易斯認為,發(fā)展中國家在經(jīng)濟發(fā)展過程中,必然會出現(xiàn)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部門和現(xiàn)代工業(yè)部門并存的狀況。在傳統(tǒng)農(nóng)業(yè)部門存在著邊際生產(chǎn)率為零甚至為負的大量剩余勞動力,他們在最低的工資水平下提供勞動,存在無限的勞動供給,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率低,技術水平落后。而在現(xiàn)代工業(yè)部門,生產(chǎn)率高,工資率比農(nóng)業(yè)部門高,從而誘使農(nóng)業(yè)剩余勞動力向現(xiàn)代工業(yè)部門轉移。農(nóng)業(yè)剩余勞動力轉移一方面會推動現(xiàn)代工業(yè)部門繼續(xù)擴張,推動經(jīng)濟發(fā)展,另一方面會促使農(nóng)業(yè)部門勞動的邊際生產(chǎn)率提高,并逐步與現(xiàn)代工業(yè)部門一致,此時經(jīng)濟的二元結構將消失。由于劉易斯二元經(jīng)濟結構模型存在與發(fā)展中國家現(xiàn)實不一致的“理想化”的現(xiàn)象,此后的經(jīng)濟學家費景漢、拉尼斯(Ranis,1964)、喬根森(Jorgenson,1967)、哈里斯特和托達羅(Harrist,1970)等相繼修正了劉易斯假設,并對劉易斯模型進行了拓展,但是這些拓展都難掩劉易斯模型的光輝。劉易斯模型比較簡單明了地刻畫出發(fā)展中國家經(jīng)濟發(fā)展過程中的情景,是對發(fā)展中國家早期發(fā)展階段的客觀描述,是分析二元經(jīng)濟結構問題的經(jīng)典模型。農(nóng)業(yè)剩余勞動力的非農(nóng)化促使二元經(jīng)濟結構消減,這是劉易斯二元經(jīng)濟理論為發(fā)展中國家二元經(jīng)濟結構轉化提供的基本路徑,這對認識中國二元經(jīng)濟結構轉換按照劉易斯模型的刻畫,中國是一個具有典型的二元經(jīng)濟結構特征的發(fā)展中國家,農(nóng)業(yè)部門客觀存在的大量剩余勞動力以及農(nóng)業(yè)部門、工業(yè)部門在勞動生產(chǎn)率、工資率方面的差別都為中國的二元經(jīng)濟結構作注解。但是,中國二元經(jīng)濟結構具有自身的特殊性,表出明顯的結構剛性,農(nóng)業(yè)剩余勞動力非農(nóng)化轉移速慢,農(nóng)業(yè)勞動力的就業(yè)轉換速度嚴重滯后于產(chǎn)值的結轉換速度。
二、中國二元經(jīng)濟結構剛性的表現(xiàn)與原因分析
中國正處于二元經(jīng)濟結構轉換的過程中,且二元結構很穩(wěn)定,結構差距依然嚴重,轉換過程并不順利,特別是進入20世紀90年代以來,二元經(jīng)濟有進一步拉大的趨勢。為什么會出現(xiàn)這種情況,可能有以下原因。
一是就業(yè)結構的轉換嚴重滯后于產(chǎn)值結構的轉換。中國三大產(chǎn)業(yè)的產(chǎn)值結構與就業(yè)結構變動的方向基本上是一致的,但三大產(chǎn)業(yè)的產(chǎn)值結構與就業(yè)結構存在著較大的差異,表現(xiàn)出就業(yè)結構的轉換嚴重滯后于產(chǎn)值結構的轉換,這在第一產(chǎn)業(yè)中表現(xiàn)得最為突出。從改革開放以來到1985年以前,農(nóng)業(yè)就業(yè)結構滯后于產(chǎn)值結構的程度在減輕,而后卻在波動中逐步提升,表明農(nóng)村剩余勞動力的轉移越來越困難。從工農(nóng)業(yè)產(chǎn)值構成看,到20世紀80年代末,中國的工業(yè)已占國內生產(chǎn)總值的3/4,已基本實現(xiàn)了農(nóng)業(yè)社會向工業(yè)社會的轉變。然而從就業(yè)結構來分析,到2002年,中國的第一產(chǎn)業(yè)就業(yè)人員仍占勞動力份額的1/2,基本上還是一個以農(nóng)民為主體的農(nóng)業(yè)社會。就業(yè)結構與產(chǎn)值結構的嚴重偏離,說明勞動力在社會各個產(chǎn)業(yè)之間的轉移還存在著較大的障礙;同時也表明不同產(chǎn)業(yè)間的勞動生產(chǎn)率水平還存在著較大的差距(尤其表現(xiàn)為農(nóng)業(yè)部門勞動生產(chǎn)率提高緩慢)。
二是第三產(chǎn)業(yè)發(fā)展嚴重滯后于經(jīng)濟發(fā)展。除日本以外的大多數(shù)發(fā)達國家的經(jīng)濟結構轉換,都表現(xiàn)為由第一產(chǎn)業(yè)向第二產(chǎn)業(yè)、第三產(chǎn)業(yè)依次漸進的結構演變模式。發(fā)展中國家與發(fā)達國家相比,則表現(xiàn)為第三產(chǎn)業(yè)的超前發(fā)展。錢納里等人的多國模型表明,在發(fā)展中國家的經(jīng)濟結構轉換過程中,“工業(yè)就業(yè)的增加,遠遠低于農(nóng)業(yè)就業(yè)的減少,因此,勞動力的轉移主要發(fā)生在農(nóng)業(yè)和服務業(yè)之間”。與此相反,中國二元經(jīng)濟結構轉換過程中存在著第三產(chǎn)業(yè)發(fā)展嚴重滯后的特點。中國產(chǎn)值結構中第三產(chǎn)業(yè)所占的比重,不僅遠遠低于中等收入國家的水平,甚至低于印度等低收入國家的平均水平。而中國就業(yè)結構中第一產(chǎn)業(yè)就業(yè)份額過高,又和第三產(chǎn)業(yè)就業(yè)份額過低直接相關。
三是城市化發(fā)展嚴重滯后于工業(yè)化進程。從歷史上看,城市化與工業(yè)化是一個相互影響、相互推動的發(fā)展過程。在一國的工業(yè)化發(fā)展過程中,勞動力、資本和技術等生產(chǎn)要素不斷向第二、三產(chǎn)業(yè)轉移。與此同時,在空間結構上則不斷向區(qū)位條件相對優(yōu)越的地區(qū)聚集,這種伴隨著工業(yè)化而產(chǎn)生的人口聚集效應是城市化發(fā)展的根本動力。錢納里發(fā)展模式表明,在低收入?yún)^(qū)內,城市化率超過工業(yè)化率,但差異不大。在人均大于300美元時,城市化率明顯高于工業(yè)化率。在中國經(jīng)濟發(fā)展與結構轉換過程中,工業(yè)化與城市化相互關系表現(xiàn)出與上述城市化發(fā)展規(guī)律完全不同的特征:中國的城市化進程嚴重滯后于工業(yè)化水平。從1952—1978年,中國城市化率低于工業(yè)化率的差距不斷擴大,到1978年城市化率低于工業(yè)化率達到26.4個百分點;1978年后的改革開放使得1978—1990年的這一差距不斷縮小,但就是在差距最小的1990年,城市化率仍低于工業(yè)化率10.6個百分點;1990年后,這一差距一直穩(wěn)定在10個百分點以上。
四是限制勞動力轉移的制度性阻滯。劉易斯對二元經(jīng)濟結構的分析是以農(nóng)業(yè)勞動力自由流動,或勞動力市場的完全開放為前提的,而中國農(nóng)業(yè)勞動力的流動受到以戶籍制度為代表的城鄉(xiāng)分割制度的限制,勞動力的流動并不順暢,完全統(tǒng)一的勞動力市場尚未形成。因此,中國二元經(jīng)濟結構的轉換尚不具備劉易斯二元經(jīng)濟結構轉換前提,也就難以沿著劉易斯路徑實現(xiàn)消解。以戶籍制度為基礎制定的勞動就業(yè)制度、人事制度、社會保障制度等形成了限制勞動力轉移的無形壁壘,使勞動力轉移帶有明顯的制度烙印導致中國二元經(jīng)濟結構的轉換具有復雜性、長期性,并可能出現(xiàn)反復強化,從而呈現(xiàn)一定的剛性。
三、中國二元經(jīng)濟結構的軟化與消解
軟化和消解過大的二元經(jīng)濟結構強度,除了必須減少制度性障礙,清除不合理的制度,解決制度不公和失當?shù)膯栴}等“軟件”改革外,還必須增強農(nóng)業(yè)投資幅度、強化國家對農(nóng)業(yè)的支持和保護力度等“硬件”的投入力度,還要采取推進城鎮(zhèn)化,發(fā)展鄉(xiāng)鎮(zhèn)工業(yè)等措施。
一是提升農(nóng)業(yè)勞動力人力資本水平。農(nóng)業(yè)勞動力轉移能否順利推進,不僅與城市化、工業(yè)化發(fā)展所提供的就業(yè)吸納能力有關,更取決于農(nóng)業(yè)勞動力自身的素質。隨著中國經(jīng)濟由外延式發(fā)展向內涵式發(fā)展的轉變,對勞動者的素質提出了越來越高的要求,勞動力就業(yè)的素質門檻逐步提高,那些只靠體力而缺乏智力的勞動者的就業(yè)渠道越來越窄。為此,中國必須強化義務教育的政府責任,堅持“規(guī)范、公平、效率”的原則,加大對農(nóng)村義務教育的財政投入。
二是加快改革戶籍制度我國長期實行的戶籍制度是限制農(nóng)業(yè)勞動力轉移的本原性制度,其他的制度、政策多是以其為基礎制定的。因此,改革戶籍制度,消除無形壁壘,對農(nóng)業(yè)勞動力的轉移,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作用。戶籍制度改革的方向,應是將其變成一種純粹的人口登記制度,剝離其福利、特權含義。 三是農(nóng)業(yè)自身的發(fā)展是根本。費景漢、拉尼斯曾指出,“在勞動力剩余型的欠發(fā)達經(jīng)濟中,農(nóng)業(yè)中的技術變革是提高農(nóng)業(yè)勞動生產(chǎn)率的主要潛在源泉。”鄧小平在20世紀80年代也曾明確指出:“將來農(nóng)業(yè)問題的出路,最終要有生物工程來解決,要靠尖端技術。”所以,大力發(fā)展農(nóng)業(yè)技術是提高中國農(nóng)業(yè)勞動生產(chǎn)率,促進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自身發(fā)展的一條根本途徑。這對增強中國農(nóng)業(yè)加入WTO后的國際競爭力,緩解當前主要農(nóng)產(chǎn)品供大于求的矛盾大有益處,同時還將促進我國農(nóng)業(yè)比較勞動生產(chǎn)率的提高,從而有利于中國二元經(jīng)濟結構的演化與改進。
四是大力發(fā)展城市經(jīng)濟,促進農(nóng)業(yè)富余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大力發(fā)展城市二、三產(chǎn)業(yè),特別是發(fā)展勞動力密集產(chǎn)業(yè),實現(xiàn)全社會的充分就業(yè)應該成為中國城市經(jīng)濟體制改革過程中的產(chǎn)業(yè)政策選擇。要使農(nóng)業(yè)富余勞動力轉移城市,與城市先進生產(chǎn)要素相結合,成為城市經(jīng)濟發(fā)展中不可缺少的推動力,一方面要使之參與城市二、三產(chǎn)業(yè)的建設、生產(chǎn)和發(fā)展,對城市經(jīng)濟發(fā)展作出“要素貢獻”,另一方面也要使農(nóng)村富余勞動力轉移到城市消費者,使他們的消費行為又對城市經(jīng)濟發(fā)展作出“市場貢獻”。最終有利于社會政治經(jīng)濟協(xié)調發(fā)展和共同富裕的社會經(jīng)濟目標的實現(xiàn),是一個多贏的格局。
業(yè)科學.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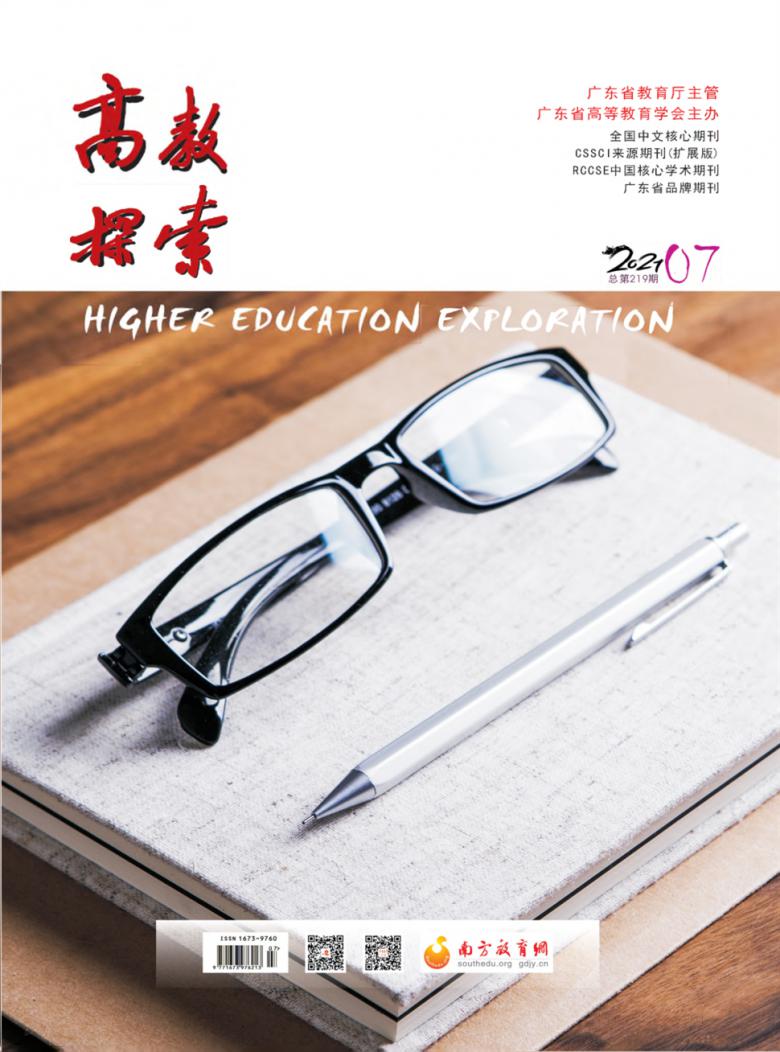

貿(mào).jp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