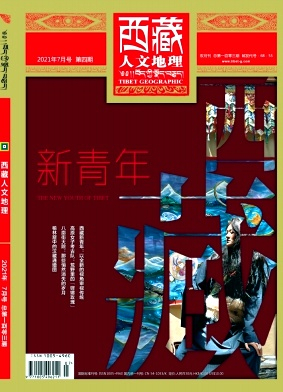對唐宋社會經濟制度變遷的再思考
謝元魯
內容提要:唐宋之際發(fā)生了重大的社會經濟變遷與發(fā)展。首先,從唐代中期至北宋在土地制度、手工業(yè)和商業(yè)各個領域中出現了產權結構明晰化的長期趨勢;其次,社會商業(yè)信用新體系的逐步形成與完善化,社會資本利率的不斷下降,市場交易方式的變遷等因素,使社會交易成本逐步降低;再次,科舉制度出身的官僚集團缺乏對規(guī)模日益增大,市場日益復雜的商品經濟的管理能力,導致國家權力對唐宋之際隨著商品經濟發(fā)展出現的新興經濟部門,尤其是金融業(yè)和工商業(yè)控制能力薄弱,使其獲得了發(fā)展的空間;最后,隨著宋代人口的增長而出現的市場規(guī)模擴大及耕作技術提高,以及由于部分傳統(tǒng)手工業(yè)部門投資收益的相對降低,使農業(yè)和金融業(yè)、商業(yè)等部門的投資收益相對增加,引起社會資本向這些部門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它們的發(fā)展。
關鍵詞:唐宋社會經濟變遷 產權結構 社會交易成本 國家控制能力 唐宋之際發(fā)生了對中國歷史影響甚大的社會經濟變遷,已成為學界的共識。宋代的農業(yè)生產無論是在墾田面積的擴大、糧食作物產量的提高、經濟作物品種的增加與種植區(qū)域的擴大方面,都較唐代有顯著的發(fā)展。而手工業(yè)方面的成就也遠遠超過唐代,無論在生產規(guī)模和分工上,還是在新興手工業(yè)的種類上,宋代都堪稱中國古代史上的高峰,如火藥、雕板印刷、航海等,均在技術上出現重大的突破。而最大的突破是在商業(yè)與金融領域。這一社會經濟的變遷,主要是從唐代安史之亂以后開始的。 從制度經濟學的角度來看,發(fā)生上述變革與發(fā)展的主要原因,在于唐宋之際,出現了一個產權結構逐步明晰化,社會經濟領域交易成本下降,以及國家權力對某些新興經濟領域控制相對薄弱的長期過程。首先,是唐宋之際出現的產權結構逐步明晰化過程。美國經濟學家李伯克(Gary D·Libecap)認為,“產權是政治制度。在配置對資源用途的決策權力以適應新的經濟環(huán)境上,產權同時也規(guī)定了財富和政治權力的分配。……不同的產權安排不僅有不同的生產效應,而且有不同的分配效應。”①從土地制度的變遷來看,唐代前期承襲北魏以來實行的均田制。在均田制之下,農民所從國家得到的土地,包括口分田和永業(yè)田,除了擁有使用權外,并沒有完整的所有權。國家干預土地的轉讓買賣,名義上仍是國有土地制度。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九月敕說:“天下百姓口分永業(yè)田,頻有處分,不準買賣典貼。如聞尚未能斷,貧人失業(yè),豪 --------------------------------- ① Gary D·Libecap:《產權合同中的分配問題》,(新制度經濟學),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258頁。 富兼并,宜更申明處分,切令禁止。若有違犯,科違敕罪,”①此外在均田制下仍然存在相當數量的私田。但這些私田往往充作口分田,其權利仍然受到國家的干預。②正因為如此,在均田制度下土地的產權是不明晰的。安史之亂前后,由于土地兼并、人口增加、以及賴以還授田地的國有荒地逐漸減少,均田制逐漸崩潰了。兩稅法實施后,國家不再禁止土地兼并,取代均田制的,是以莊園制為代表的私人土地所有制。唐憲宗元和十四年(819)敕說:“如聞諸道州府長吏等,或有本任得替后,遂于當處買百姓莊園舍宅。或因替代情弊,便破定正額兩稅,不出差科。今后有此色,并勒依元額為定。”③這道敕令實際上是承認了官吏所購買的土地,只要按原額交納賦稅,即為私有。這意味著較為完全的土地所有權開始由國家轉入私人手中,這是土地產權明晰化第一步的標志之一。除此以外,從唐代后期開始,以土地和房宅等為主的不動產可以進行自由買賣和質典,在質典后原主人可以在相當長的時間內保持收回的權利,由此可見唐代后期對于產權中的物權與債權已經有較為明確的規(guī)定。④傅筑夫指出,自從唐代天寶以后,隨著均田制的廢棄,土地買賣不再有任何限制,成為地權轉移的社會公認正常形式,也是法律承認的唯一方式。除了農民經常賣掉土地外,擁有大莊田的權貴豪門,也常常因為揮霍浪費或其他特殊原因,而將莊田賣掉,也成為民間地權轉移的又一基本方式。而宋代的土地制度,不僅是唐代后期的繼續(xù),而且是唐代的進一步發(fā)展。⑤ 從唐代后期到宋代,土地產權明晰化的進程繼續(xù)發(fā)展。宋代初年即已規(guī)定“墾田即為永業(yè),官不收取其租。”⑥宋太宗至道元年(995)6月詔說:“應諸道州府軍監(jiān)管內曠土,并許民請佃,便為永業(yè),仍免三年租調,三年外輸稅十之三。”⑦在真宗與仁宗朝亦再次頒布過類似的詔令。實際上,上述土地制度變化的趨勢與土地產權的明晰化過程,正是在自唐代中期以后到宋代土地所有權的頻繁轉移中逐步實現的。漆俠認為,“兩宋三百年土地兼并之不斷發(fā)展,與土地占有、買賣政策的自由、放任有著密切的關系。當著土地兼并尚不算多么嚴重,國家賦役還在一定范圍內增加之時,宋代土地政策或多或少地有利于自耕農經濟的發(fā)展,對一部分客戶的轉化乃至上升為自耕農也具有積極的意義。從北宋客戶比數下降,自耕農比數增長的這一事實中,就說明了這一點。”⑧唐宋之際,國家土地所有制繼續(xù)衰落,土地私有制則得到更進一步的發(fā)展,并居于絕對優(yōu)勢的地位。 --------------------------- ① 《全唐文》卷30。 ② 楊際平:《唐令·田令的完整復原與今后均田制的研究》,《中國史研究》2002年第2期。③ 《唐會要》卷83《租稅上》。 ④ 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第1卷《唐代不動產的“質”》,第230--232頁。 ⑤ 傅筑夫:《中國經濟史論叢》上冊,三聯書店1963年版,第13s一144頁。 ⑥ 《宋史》卷173《食貨上一·農田之制》。 ⑦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38。 ⑧ 漆俠,前引書,第235、339—344頁。 唐宋之際,不僅僅是在土地制度方面出現了產權明晰化的趨向,在手工業(yè)的許多部門中同樣也是如此。張澤咸指出,唐代的銅鐵業(yè)沒有廣泛實施官營,各地鐵礦在一定條件下聽任百姓開采,設鹽鐵使收稅,西北邊沿地區(qū)出于政治原因不許私自設冶及采煉,朝廷在少數產鐵地置官管理的官營鐵冶。由此可見,凡由朝廷直接經營的屯田、牧監(jiān)等所需鐵器統(tǒng)一由官府冶鑄供應,全國眾多民戶所需鐵器,基本上出自各地私營冶鑄者手中。而到宋代,私人冶鐵業(yè)的規(guī)模更大,徐州地區(qū)的“冶戶皆大家,藏鏹巨萬,常為盜賊所窺。”①可見這些私人礦冶資力之雄厚。②除此以外,即使是唐宋時代受到國家最嚴格控制,關系國家財政收入的鹽業(yè)與茶業(yè)中,同樣也出現了私人產權進入的過程。唐代中期以前,鹽主要由私人生產。中唐以后,鹽的生產由官府嚴格控制,但“煎販之徒,無由止絕”,③可見眾多的私人鹽業(yè)生產,在厚利的驅使下,仍無法禁絕。從宋代開始,除了解州、安邑池鹽的生產,仍由國家機構直接通過勞役制進行外,在四川井鹽和兩浙、淮東海鹽的生產中,大多已通過井戶與亭戶進行經營。四川井戶均為當地富豪,約有三四百家,自己出資,雇用鹽工鑿井及汲鹵煮鹽。而海鹽亭戶,則自己擁有鹽田,以及犁、牛等工具。④而在茶業(yè)中同樣如此。根據北宋神宗熙寧時知彭州呂陶的記載,彭州九隴縣的私人茶園中,業(yè)主管理茶樹和采摘茶葉,均通過“雇召人工”的方式來完成的。⑤漆俠指出,宋代的大茶園主還可以把自己的茶園分租給無茶園或茶園甚小的茶農。⑥可見在這樣的私人茶園中,產權關系是十分明確的。在其他手工業(yè)領域中,如紡織業(yè)、造紙業(yè)、雕版印刷業(yè)、制瓷業(yè)中,這種情況同樣在唐代至北宋出現。如《朝野僉載》中記載:“定州何明遠大富,主宮中三驛,每于驛邊起店停商,專以襲胡為業(yè),貲財巨萬,家有綾機五百張。”⑦反映唐代已有產權較明晰的私人手工業(yè)作坊。而宋代則在造紙、雕版印刷等新興行業(yè)中出現大量私人作坊。宋代的成都府百花潭側,“以紙為業(yè)者家其旁。”⑧五代后蜀宰相毋昭裔開始大規(guī)模私人雇工雕板印刷《文選》、《初學記》等書籍,他的子孫在宋代以售書致富。賈大泉指出,宋代四川私家刻書風氣很盛,“宋時成都辛氏、臨邛韓醇、蒲江魏了翁、眉州蘇林、三臺劉甲,都是有名的刻書之家。廣都費氏進修堂、廣都裴宅、西蜀崔氏書舍、眉山程舍人、眉山萬卷堂、眉山書隱齋,都是著名的坊刻印書之所。……各刻書之家的競爭日益激烈,為了保護自身的信譽和發(fā)行圖書的商業(yè)利益,他們還呈請官府保護,禁止翻版和另刻。”可見從唐代到宋代的四川地區(qū),不僅在出版業(yè)中出現大量私人作坊,而且還出現明確的版權意識。⑨ 除了產權的明晰化趨勢外,唐宋之際出現的另一個經濟變遷趨勢,是社會交易成本的逐步降低。美國經濟學家弗魯波頓和德國經濟學家瑞切特指出,所謂交易成本,是指“要建立、使用和保障一項制度需要耗費實際資源。很明顯,為了使社會和經濟機制運行肯定要發(fā)生成本。……現在,制度經濟學更廣泛地把交易成本定義為包括所有與(1)制度或組織的建立或變遷,和(2)制度或組織的使用有關的成本。”⑩因此,在本文中論述的社會交易成本,主要是指制度和組織建立、變遷和運行所產生的成本。社會交易成本的高低主要取決于市場規(guī)模的大小與 -------------------- ① 蘇軾:《東坡奏議》卷2《上皇帝書》。 ② 張澤咸:《唐代工商業(yè)》,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39頁。 ③ 《冊府元龜》卷494。 ④ 漆俠,前引書,第814—823頁。 ⑤ 呂陶:《凈德集》卷1《奏為官場買茶虧損園戶致有詞訟喧鬧等狀》。 ⑥ 漆俠,前引書,第755頁。 ⑦ 張鷟:《朝野僉載》卷3。 ⑧ 袁說友:《箋紙譜》。 ⑨ 賈大泉:《宋代四川經濟述論》,四川省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16H一164頁。⑩ EirikG·Furubotn、Rudolf Richtcr:《新制度經濟學:一個評價),《新制度經濟學》,上海財經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3、 種類,市場交易的機構與方式變化,交易信息的獲取便利程度,商業(yè)合同的談判和履行程度,商業(yè)信貸利率的高低等因素。美國經濟學家克萊德.里德認為,16至17世紀西歐各國,如英國、荷蘭經濟的增長與法國和西班牙經濟的停滯,與其交易成本的降低與上升有密切的聯系。① 唐宋之際社會交易成本的降低,首先表現在社會商業(yè)信用的新體系逐漸形成與逐步完善化。在金融貨幣業(yè)方面,唐代后期,長安、揚州等商業(yè)發(fā)達城市中,豪商巨賈為便利貨幣的存取,已出現了許多專營錢幣存取與貸出的金融機構柜坊,官吏豪商在柜坊中存錢,少則數萬貫,多則至數百萬貫。②同時,為解決錢幣的遠距離兌換問題,還出現了由藩鎮(zhèn)設在長安的諸道進奏院和有勢力富商經營的“飛錢”,實行貨幣匯兌業(yè)務。《新唐書·食貨志》載:“時商賈至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卷乃取之,號‘飛錢”’。柜坊和飛錢的出現,顯示唐代后期的社會商業(yè)信用正在逐步形成。到北宋時期,社會商業(yè)信用體系更進一步發(fā)展,出現了種類繁多的信用票據和信用貨幣。繆坤和認為,宋代在社會經濟活動中涌現出大量信用票據,主要包括如茶引、鹽引等期票類交引,和交子、會子、便錢等匯票類兌換券兩種類型。③加藤繁指出:“無論柜坊制度,或者飛錢制度,都是信任營業(yè)者,把錢物寄托給他們;而賒的制度,則信任對方,在收代價之前,先交付貨物。……從飛錢、賒,以及因為賒而造成的種種票據的盛行看來,可以承認:在唐、宋,尤其在宋代,商界已經建立了信義,足以作為征象和證明的票據已經正在發(fā)達起來。”④ 社會商業(yè)信用新體系的建立,除了上述唐宋之際出現的錢幣匯兌外,北宋時紙幣交子的產生,正是社會商業(yè)信用建立的集中體現。從具有實際價值的金屬貨幣銅錢,到僅僅是由民間富商在印刷圖案的紙上簽名題號,就可將其作為與銅錢同等價值的貨幣流通,必須是社會商業(yè)信用相當發(fā)達的產物。除金融貨幣方面的變遷外,在普通的商業(yè)交易中,唐宋之際也是商業(yè)信用上升的時代。加藤繁指出,商業(yè)消費信用與生產信用,在宋代已經盛行。蘇軾在哲宗元祐七年(1092)知揚州時的奏議說:“商賈販賣,例無見錢。若用見錢,則無利息。須今年索去年所賣,明年索今年賒,然后計算得行,彼此通濟。”⑤在宋代的布帛、茶、鹽等重要商品的大宗交易中,商人之間,尤其在客商與鋪戶之間相當盛行賒買和賒賣。“消費信用不過是為了緩和生活的窮迫,而生產信用能夠增大資本的效力,促進物資的流轉等,和一般的經濟發(fā)展有密切的關系。”⑥由于商業(yè)信用的發(fā)展與廣泛運用,北宋乾興元年(1022)六月還以詔令的形式,制定丁關于賒買賒賣的法律,規(guī)定必須簽訂契約文書、規(guī)定支付現錢期限,要有擔保人等,這是唐宋對商業(yè)信用的最初立法。商業(yè)信用的發(fā)展,大大提高了資本的利用率。法國經濟史家布羅代爾說:“整個商業(yè)體系的存亡取決于信貸,一旦信貸停止,發(fā)動機就會卡殼。關鍵在于,這是一種為商業(yè)體系固有的并由該體系產生的信貸,一種‘內在的’和‘不計利息’的信貸。笛福認為這種信貸的蓬勃發(fā)展正是英國經濟繁榮的秘密。”⑦唐宋之際的商業(yè)信貸當然尚未達到16—17世紀的歐洲水平,但相對于前代已經有相當的發(fā)展,這必然會激勵商業(yè)經濟走向繁榮。 --------------------- ① 克萊德·里德:<交易成本和十七世紀西歐的有差別增長》,轉引自《經濟發(fā)展辭典》,四川辭書出版社1989年版,第190頁。 ② 見《太平廣記》卷16《張老》、卷243《竇義》。 ③ 繆坤和:《宋代信用票據研究》,云南大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12一14頁。 ④ 加藤敏:《中國經濟史考證》第2卷,商務印書館1963年版。第5頁。 ⑤ 蘇軾:《東坡奏議》卷11。 ⑥ 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第2卷,第182一l88頁。 ⑦ Femand Broudcl:《15至18世紀的物質文明、經濟和資本主義》第2卷,三聯書店1993年版,第411—412頁。 交易成本的降低,還從唐代中后期至北宋時的金融業(yè)之中表現出來。李劍農指出,整個唐代的資本利率呈下降趨勢,由唐代初年的100%逐漸下降到武宗會昌時的40%,雖然這里是指官本利率,但私人利率的降低,應是大抵相同。“此種利率逐漸降低之事實,自可認為商業(yè)資本逐漸增多之表征。”①實際上,從唐代到北宋,資本利率繼續(xù)下降,到北宋神宗王安石實行青苗法與市易法時降到20%左右。青苗法規(guī)定“以常平耀本作青苗錢,散與人戶,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斂。”在市易法中,規(guī)定讓商賈以田宅或金銀作為抵押,向國家的市易務貸款,同樣“出息十分之二。”②而當時民間的資本利率最低亦降到20—30%。③由此可見,從唐代后期到北宋,資本利率進一步下降,使資本的借貸成本逐漸低廉,這是唐宋之際社會資本總額增加和商業(yè)發(fā)展的重要因素。“資金投入經濟生活決定著息率的變化,息率則是表現經濟和貿易的健康狀況的重大指標之一。息率在十五至十八世紀的歐洲幾乎不斷下跌,……這主要因為積累增加了資本總額,由于通貨充沛,借貸利息相應下降。”④這里指15至18世紀的歐洲資本市場上利息率的下降,使商品經濟得以活躍起來,這種情況同樣在唐宋之際發(fā)生了。實際上,宋代的商人擁有的商業(yè)資本遠遠多于唐代,如北宋開封“資產百萬者至多,十萬而上比比皆是。”⑤“兼并豪猾之徒,居物逐利,多蓄緡錢,至三五十萬以上,少者不減三五萬。”⑥可見當時社會資本之富足。宋代商人的財力是十分雄厚的,如蜀商、南商、北商等都是當時有名的地方商人,其占近世中國商業(yè)界中堅的山西商人、徽州商人,也大體在這時開始顯出身手。① 紙幣的出現,是社會交易成本降低的重要例證。宋仁宗時的益州轉運使張若谷和知益州薛田說:“川界用鐵錢,小錢每十貫重六十五斤,折大錢一貫重十二斤。街市買賣,至三五貫文,即難以攜持。自來交子之法,久為民便。”由于唐代中期以后長期出現的錢荒,導致流通的銅錢數量不足。長期的通貨緊縮,使商業(yè)的發(fā)展受到許多限制。宋代雖然重視這一問題,北宋時平均每年的銅錢鑄造額達到唐代后期的20—30倍左右,但通貨仍不能適應商品經濟發(fā)展的需要,尤其對一些經濟發(fā)達地區(qū)如四川等,制約更為嚴重。宋政府把四川地區(qū)作為鐵錢流通區(qū),但鐵錢幣值較銅線低,使用和攜帶極為不便,造成交易費用大幅度上升。宋神宗時,“自陜府般鐵錢一萬貫至秦州,計用腳錢二千六百九十余貫。”⑧由陜府(今西安市)到秦州(今天水市)距離約300公里,鐵錢的運費竟占了本身價值的四分之一還多,可見其交易成本之高。交子的出現,不僅使鑄幣流通不足的問題得到部分緩解,而且使川陜地區(qū)商業(yè)交易的成本大幅度降低,對于促進商品經濟的發(fā)展起到巨大作用。實際上,以唐代的“飛錢”、宋代的“便錢”為代表的錢幣匯兌業(yè)的發(fā)展和逐步完善化,同樣降低了商業(yè)交易成本。《宋史·食貨志》說:“先是,太祖時取唐飛錢故事,許民人錢京師,于諸州便換。其法:商人人錢左藏庫,先經三司投牒,乃輸于庫。開寶三年,置便錢務,令商人人錢詣務陳牒,即輦致左藏庫,給以券,仍敕諸州凡商人赍券至,當 ------------------------- ① 李劍農,前引書,第237—238頁。② 《宋史》卷327《王安石傳》。③袁采:《世范》卷3.④ Femand Braudel,前引書,第413頁。⑤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85,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乙已條。⑥ 宋祁:《景文集》卷28《乞損豪強優(yōu)力農札子》。⑦ 傅衣凌:《明清時代商人及商業(yè)資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頁;《宋朝事實》卷15《財用》。⑧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334,神宗元豐七年三月癸丑條。 日給付,違者科罰。至道末,商人人便錢一百七十余萬貫,天禧末,增一百一十三萬貫。至是,乃復增定加饒之數行焉。”①可見商業(yè)性貨幣匯兌業(yè)的發(fā)展,使商人在遠程商業(yè)貿易中,大大節(jié)省了為長途搬運沉重的銅鐵錢金屬貨幣的費用,使商業(yè)交易費用也大大降低。 市場交易方式的變遷也同樣起到降低交易成本的作用。唐宋之際的市場交易方式變遷,首先是坊市制的崩潰及街市商業(yè)的興起。唐代市場的設立與管理同樣有嚴格的制度,州縣以上的市一般有規(guī)定的商業(yè)區(qū)域,在這些區(qū)域內設有許多同業(yè)商店的街區(qū),市的周圍同樣有圍墻,也與坊一樣四面開門,市門同樣實行朝開夕閉。唐代的商店一般只能設于市內,同時禁止市場夜間營業(yè)。②可見唐代前期對市場管制的嚴密。直到唐文宗開成年間,還規(guī)定“京夜市宜令禁斷。”③可見直到唐代后期,還禁止市場在夜間進行交易。因此,商業(yè)交易無論從時間上還是在地域上,都受到較為嚴格的限制。這種嚴格的管理制度,自然加大了商業(yè)的交易成本。但是,這種對商品交易場所和時間的嚴格限制,到唐代后期已經松弛,到北宋前期,事實上已沒有限制。加藤繁指出,“到了宋代,作為商業(yè)區(qū)域的市的制度已經破除,無論在場所上,無論在時間上,都沒有受到制限,商店各個獨立地隨處設立于都城內外。”④商店可以和居民區(qū)混合設立,沿著大街開設。商業(yè)交易而且出現了夜市,延長了營業(yè)時間。根據《東京夢華錄》的記載,北宋開封商業(yè)街區(qū)中的交易數量非常龐大,僅潘樓街附近的“金銀綵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壯,門面廣闊,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聞見。”⑤可見隨著市場交易形式的變化,交易成本也隨之而下降,從而促進了商業(yè)的繁榮。其次,唐代中期以后,在農村地區(qū)草市和鎮(zhèn)市的大量出現,也為商業(yè)交易費用的降低起了重要作用。張澤咸指出,唐以前,華北地區(qū)不見草市記載,自中唐至五代,華北的草市已是為數不少,五代時更是成批出現。而長江流域及其以南地區(qū),中唐以后草市亦是為數眾多。這些草市的出現,突破了商品交易的法定區(qū)域范圍。⑥如宋代四川南部戎州與瀘州沿邊地區(qū)的居民,由于難以購買日用品與農具,請求設置草市。招募商人前來開店營業(yè)。宋神宗熙寧十年(1077)四月乙巳詔說:“戎瀘州沿邊地方,蕃漢人戶所居,去州縣遠,或無可取買食用鹽茶農具,人戶愿于本地分,興置草市,,招集人戶住坐作業(yè)者。”⑦可見由于興置草市可以大大減少當地居民的交易費用,所以當地人戶才向官府作出設立草市的請求,并得到準許。 除此之外,唐宋時代降低交易成本的市場交易方式變化中,還包括商業(yè)貿易中介人一牙人制度的出現與普遍化。牙人在漢代即已出現,但張澤咸指出,牙人在唐代以前仍然較少介入商貿領域。從武則天時代起隨著商品經濟與邊境貿易的發(fā)展而興起,如安祿山與史思明二人即為互市牙郎。但牙人的大量出現是在中唐以后到五代十國時期,當時在商業(yè)交易中大量通過牙人。⑧如后唐明宗天成元年(926)十一月敕說,“在京市肆,凡是絲絹、斛斗、柴炭、一物以上,皆有牙人。”宋代商業(yè)交易中的牙人更為普遍。雖然牙人在交易中有時出現欺詐行為,但作為商業(yè)交易的中介人,牙人的出現,總的說來是增加了獲取市場信息的便利程度,提高了商品交易效率,應是降低了商業(yè)的交易費用。 ----------------------- ① 《宋史》卷180《食貨下二·錢幣》。 ② 加藤繁,前引書, 第26l一265頁。 ③ 《唐會要》卷86《市》。 ④ 加藤繁:《中國經濟史考證》第1卷,第302頁。 ⑤ 孟元老:《東京夢華錄》卷2《東角樓街巷》。 ⑥ 張澤咸,前引書,第236—242頁。 ⑦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281。 ⑧ 張澤咸,前引書,第341—345頁。 整個社會交易成本的下降,就是在唐代中期起為國家控制最為嚴密的鹽業(yè)中,也出現了這一趨勢。郭正忠指出,北宋前期的官賣解鹽,在民運官鹽的情況下,利潤率約在500—1 000%之間,其平均贏利倍數約在8—14倍左右,這一暴利是在官府把鹽的運費部分轉嫁到民間的條件下獲得的。但在宋政府實行解鹽通商政策后,由商人在京城、鹽池和邊地交納錢款,換取交引券買鹽,販往西路、南路等指定地區(qū)銷售。宋政府僅賣出交引券,不再承擔銷售的風險與費用,北宋真宗時出賣交引券的利潤率竟高達4 000%以上,獲利倍數達到60—65倍,到仁宗時利潤率再創(chuàng)7 000%的新高,獲利倍數竟高達88倍。所以郭正忠認為,由上述分析可見,“解鹽官賣在兩種情況下,即官付全部運費和一半運費的情況下,其利潤率均遠不如通商。”①也就是說,宋政府在不能完全強制民間百姓免費為官府運鹽的情況下,以出賣交引券的方式,使商業(yè)資本進入到鹽的運銷環(huán)節(jié)中,從而降低了交易成本,同時宋政府也從中獲得了更為豐厚的利益。漆俠認為,從唐代后期起到宋代,除設立國家稅務機構征收商稅之外,還設立針對商稅與酒稅的買撲制度,即把某一地區(qū)的商稅或酒稅,以固定的稅額承包給私人,以減少官府開支。②這種作法,其實就是為降低專賣和商稅征收的交易成本,讓民間分享一部分稅收利益的作法。當然,由于鹽、茶、酒等商品專賣的利益大多數為國家所占有,即使實行通商制或買撲制,這些專賣商品的交易成本降低的程度仍是遠不及非專賣商品的。 唐宋之際社會經濟發(fā)生重大變化的又一個重要原因,是國家權力對一部分新興的經濟部門控制力的薄弱。這里所說國家權力對不同經濟部門的控制力,主要指其通過征收賦稅或直接占有等方式獲取資源的能力。黃仁宇認為,唐宋王朝興衰的背后原因,是當時的官僚機構雖已相當成熟,但其行政效率并不高,經濟管理能力也十分粗疏,這是因為其缺乏現代商業(yè)組織的數字化管理技能,對數字無法作精密的核算。這種農業(yè)國家的行政管理,并不遵循經濟原則,所以在社會出現大的變動時,對社會資源無法進行合理的征集與分配。③此論有相當的創(chuàng)見,不過黃氏沒有認識到,正是由于唐宋王朝的官僚機構缺乏商業(yè)的數字化管理能力,因而唐宋王朝的國家權力對社會經濟部門的控制,只能限于傳統(tǒng)的農業(yè)和少數最重要的商品,如鹽、茶、酒的專賣方面。而對于新興的商業(yè)、金融業(yè)與作坊手工業(yè)等需要進行較精密的數字化管理的經濟部門,則缺乏進行管理的能力,唐宋時期科舉出身的官吏,極不擅長于此,唐代中后期對商業(yè)管理較為著名者,也僅劉晏一人而已。但這種情況的出現,反而為這些新興的經濟領域發(fā)展留下了回旋的空間。道格拉斯.諾思說:“國家的存在是經濟增長的關鍵,然而國家又是人為經濟衰退的根源;這一悖論使國家成為經濟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關于長期變遷的分析中,國家模型都將占據顯要的一席。”④此外,唐宋之際中央集權的衰弱與地方勢力的發(fā)展,在宏觀上也削弱了國家權力對工商業(yè)發(fā)展的限制。 ------------------------ ① 郭正忠:《宋代鹽業(yè)經濟史》,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686—694頁。 ② 漆俠,前引書,第1002—1003頁。 ③ 黃仁宇:《赫遜河畔談中國歷史》,三聯書店1992年版,第115、183頁。 ④ DouglaSS C·Nodh:《經濟史中的結構與變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0頁。 唐代國家對農業(yè)的控制極為嚴密,因為“軍國所資,咸出于租調。”①唐代前期實行均田制與租庸調賦稅政策,按史家的研究,唐代均田制下的授田實際遠不足百畝,在人口密集、經濟發(fā)達的狹鄉(xiāng),最多的在30畝左右,甚至不過5畝、10畝。②唐代中原地區(qū)的糧食產量,普通在1石左右。③如以實際授田30畝,每畝平均產量l石計,每個丁男每年可收糧食30石,納租2石,其田稅率大致為6.6%左右。但還要加上調與庸的稅收。唐代規(guī)定每個丁男每年交納的調與庸共為絹2匹,按開元天寶時期的粟米與絹帛價格,粟米平均每石約200文,絹帛平均每匹約550文。④依此折算,相當于農民每個丁男還要向國家交納5.5石糧食。這樣算來,人口密集地區(qū)每個丁男的納稅率實際上為25%左右。這里還沒有計算其它雜稅的負擔。唐德宗時以大歷十四年的稅額為準,實行兩稅法后,夏秋兩稅的稅率未見記載,但按照安史之亂以后國家財政開支日益增加,財政困難的情況來看,農民每個丁男的負擔不會低于實行租庸調法時。北宋的兩稅額,“大率中田畝收一石,輸官一斗”,⑤即大致平均為10%左右,而且兩宋時期并未有大的變化。這一稅率大致與唐代相當。但宋代國家財政經常處于困竭狀態(tài),對農業(yè)稅收的增加,主要是通過兩稅附加的雜稅、以及所謂折科、折變和支移等變相加稅的手段來進行,農民的實際負擔并不會比唐代低。 但唐宋之際對工商業(yè)者的稅收是較為優(yōu)惠的。從商稅征收的變化可以說明這一點。唐代前期的工商業(yè)者,除與一般民戶同樣交納按資產多少規(guī)定交納的戶稅與地稅外,并未征收商稅,其負擔已較農民為低。到安史之亂以后,因為財政困難,方開始征收商稅。到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實行兩稅法時確定為三十稅一,即3.3%左右,⑥遠遠低于農戶的負擔。到宋代的商稅額則比唐代有所降低,當時“行者賫貨,謂之過稅,每千錢算二十;居者市鬻,謂之住稅,每千錢算三十,大約如此,然無定制,其名物各隨地宜而不一焉。”⑦過稅相當于商品流通稅,住稅相當于營業(yè)稅,也就是說,宋代的商稅率,大致為3%和2%,比唐代后期降低了。顯示國家權力對商業(yè)的征稅力度,唐宋時期比農業(yè)要低得多。可見唐宋時期國家權力對農業(yè)的控制力,始終遠高于對工商業(yè)(除鹽、茶等專賣商品外)。由農業(yè)取得的財政收入,直到北宋初期,仍然在國家財政收入中占有最大的比重。 唐代中期以后,由于國家財政的困難,通過農業(yè)部門榨取的收入畢竟有限,遠遠不能滿足不斷增長的財政開支,于是對工商業(yè)收取的專賣收入與稅收,在國家財政收入的比重中不斷增大。安史之亂后對鹽實行專賣制度,當時“天下之賦,鹽利居半,宮闈服御、軍鑲、百官祿俸皆仰給焉。”以后對商品的專賣,又擴展到茶、酒、醋等方面。因此,國家權力對鹽、茶等商品的控制非常嚴密,所謂“茶、鹽之法益密”,私販鹽、茶在一定數量以上均處以死刑,而“茶商所過州縣有重稅。”⑧但是,即使是鹽、茶業(yè)中,仍有私人商業(yè)資本的空間,范仲淹說:“茶鹽商稅之人,但分 ------------------------ ① 《文獻通考·田賦考》四,歷代田賦之制。 ② 王仲犖:《隋唐五代史》上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43—244頁;朱大渭、張澤咸:《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2冊,齊魯書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433—434頁。. ③ 胡戟:《唐代糧食畝產量》,《西北大學學報》1980年第3期;吳章銓:《唐代農民問題研究》,臺北中國學術著作獎助委員會1963年;王仲犖,前引書,第373頁。 ④ 彭信威:《中國貨幣史》上冊,群聯出版社1954年版,第205—206頁。 . ⑤ 張方平:《樂全集》卷14《食貨論·賦稅》。 ⑥ 張澤咸:《唐五代賦役史草》,中華書局1986年版,第190—19l頁。 ⑦ 《宋史》卷186《商稅》。 ⑧ 《新唐書》卷54《食貨四》。 減商賈之利爾,于商賈未甚有害也。”①如宋代四川的私人井戶約有三四百家,雇用的鹽工有七八千人,其經濟力量十分雄厚。宋政府在四川之外的地區(qū)實行鹽鈔法后,許多鹽商仍因此而致富,有的人甚至家資巨億。”② 不過,在以上鹽、茶、酒等在國家權力嚴密控制的禁榷產業(yè)之外,唐宋之際的工商業(yè)得到迅速的發(fā)展。從唐代到北宋對由于商品經濟發(fā)展而產生的許多新興部門,包括金融、貨幣匯兌、票據交易、商品儲存與批發(fā)等,國家控制力較為薄弱,使得在這些部門中的市場規(guī)律得到較為充分的體現,促進了這些產業(yè)的迅速發(fā)展。如在農業(yè)生產領域中以新興的經濟作物果樹、甘蔗、蔬菜、花卉、棉花以及傳統(tǒng)經濟作物桑麻等,北宋均出現了大批經濟作物種植的專業(yè)戶,其商品化程度也較唐代為高,并出現了一批依托上述經濟作物發(fā)展起來的手工業(yè),如四川遂州的制糖業(yè)、遍及全國的麻紡織業(yè)與嶺南地區(qū)的棉紡織業(yè)。在手工業(yè)方面,有冶鐵業(yè)、井鹽業(yè)、造船業(yè)、制瓷業(yè)、建筑業(yè)、造紙業(yè)與雕版印刷業(yè)等,這些產業(yè)由于受國家權力的控制較弱,主要由民間工商業(yè)者經營,所以均得到迅速的發(fā)展。③漆俠認為,宋代從事絲織業(yè)的機戶,全國已達10萬戶左右,可見其規(guī)模之大。④宋代商業(yè)利潤最大的行業(yè),包括交引鋪、金銀彩帛鋪、邸店、停塌以及從事長途販運及海外貿易的大行商等,他們的“每一交易,動即千萬,駭人聽聞。”⑤這樣具有優(yōu)厚利潤的行業(yè),仍然主要由私人商業(yè)資本經營,可見國家政權缺乏對私人商業(yè)資本的控制能力,從唐代中期起雖然對鹽、茶、酒等幾種最重要的商品實行國家專賣制度,但科舉制度出身的官僚缺乏對規(guī)模不斷增大、市場日益復雜的商品經濟的管理能力,宋代官僚,經常以奉行“祖宗家法”為圭臬,正是缺少適應社會經濟變化管理能力的一種表現,這樣,就仍為私人商業(yè)資本的發(fā)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間。 除了對市場的控制日益松弛外,唐宋之際國家權力對金融的控制力也很薄弱。首先是對貨幣發(fā)行的控制,這是現代國家權力控制最為嚴密的領域。但唐代初年即曾把鑄造貨幣的部分權力賜給秦王、齊王等王公大臣,到武則天以后,天下“盜鑄蜂起,江淮游民依大山陂海以鑄,吏莫能捕。”到玄宗開元時,宰相張九齡與信安郡王李棉甚至建議允許民間鑄造錢幣,雖未能實行,而實際上已變相承認民間私鑄錢幣,“京師權豪,歲歲取之,舟車相屬。”私鑄錢幣仍然通行民間。到宋代,就連貨幣也未能統(tǒng)一,形成了銅錢區(qū)、鐵錢區(qū)與銅鐵錢兼行區(qū),這應是宋代官僚機構對金融貨幣控制力下降的表現。甚至紙幣的發(fā)行也是由成都民間富商首創(chuàng),在宋太宗淳化至道年間(990—997)開始出現交子,到仁宗天圣元年(1023)以前,民間交子的流通已發(fā)展為16家富商聯合擔保發(fā)行的制度。 國家權力控制薄弱的另一個金融領域,是貨幣的匯兌業(yè)。《新唐書·食貨志》載,唐憲宗時,“商賈到京師,委錢諸道進奏院及諸軍、諸使、富家,以輕裝趨四方,合券乃取之,號‘飛錢’。”可見唐代后期商業(yè)的發(fā)展,需要貨幣匯兌業(yè)。而唐政府對飛錢的出現,首先是禁止,“京兆尹裴武請禁與商賈飛錢者,搜索諸坊。”⑥但禁止貨幣的兌換引起了京城流通貨幣的減少,元和七年(812),戶部侍郎、判度支盧坦和鹽鐵使王播等上奏說,當時京城流通的現錢減少,“蓋緣比來不 ------------------------- ① 《續(xù)資治通鑒長編》卷14l,仁宗慶歷三年六月甲辰條。 ② 漆俠,前引書,第823、859頁。 ③ 陳智超、喬幼梅:《中國封建社會經濟史》第3卷,齊魯書社、文津出版社1996年版,第201一233頁。 ④ 漆俠,前引書,第644頁。 ⑤盂元老:《東京夢華錄》卷2。 ⑥ 《新唐書》卷54《食貨四》。 許商人便換,因茲家有滯藏,所以物價轉輕,錢多不出。臣等今商量,伏請許令商人于戶部、度支、鹽鐵三司,任便換現錢,一切依舊禁約。”①但這種官府的貨幣匯兌要增收百分之十的匯費,結果沒有商人前來匯兌,只好改為與商人“敵貫而易之”,即實行平價匯兌的辦法,方能維持下去。②可見唐代的中央政府對貨幣匯兌的控制能力,遠不及民間的富商。在這次國家與商人爭奪對貨幣匯兌主導權的斗爭中,商人取得了勝利。唐王朝自建立之初,就在中央和地方各級官府中設置“公廨本錢”,作為放高利貸的資本,利率竟達60—70%之多,其利息作為官吏俸祿的補充,直到唐代后期依然沿襲,成為唐代的弊政,可見唐王朝控制金融信貸領域手法的拙劣。北宋神宗時的王安石變法中,實行“青苗法”,由國家借貸貨幣給民戶,以奪取民間高利貸商人的信貸利潤。但當時即受到朝野各方的強烈反對。變法失敗后,青苗法罷廢,宋政府控制金融信貸領域的努力再次失敗。

.jpg)
科學學報.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