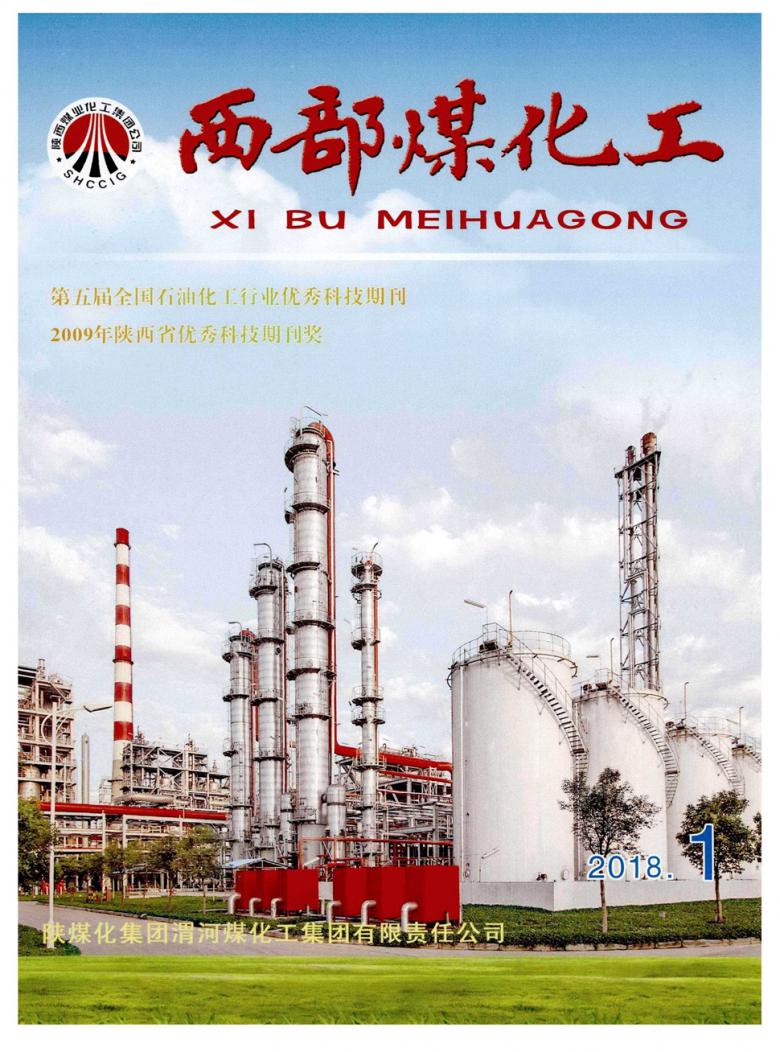試析從污點證人的角度看行賄人的司法處理
張耀軍
論文摘要為了重點打擊國家工作人員的腐敗行為,我國《刑法》對賄賂犯罪中的行賄人給予了“有條件從輕處理”的立法待遇。在司法實踐當中,也形成了“重查受賄、輕辦行賄”的辦案格局,然而這一辦案格局從長遠來看不利于有效打擊賄賂犯罪,而且司法實踐中對行賄人的處理方式也極不規范,難以納入偵查監督的視野,與現代刑事訴訟法律理念相悖。本文主要從有效打擊賄賂腐敗犯罪的角度出發,對行受賄犯罪中行賄人的處理方式進行探討,并認為將實踐中對行賄人的司法處理從程序法角度加以規范應是立法改進的方向,而進而明確給予行賄人以“污點證人”的刑事訴訟地位則是一個合理的選擇。
論文關鍵詞賄賂犯罪行賄人污點證人
在賄賂犯罪中,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在傳統的“國家工作人員”利用手中的公權力受賄的犯罪在新時期呈現出許多新特征的同時,市場交易中“非國家工作人員”為謀取私利而受賄的商業賄賂犯罪也愈演愈烈。 “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犯罪作為一種“權力尋租”的腐敗犯罪,對黨的威信和政府的公信力造成嚴重危害,從長期看會威脅黨執政地位的鞏固和執政使命的實現。商業賄賂則嚴重破壞商業信用與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若不有效打擊使之成為了不良的“商業潛規則”,會嚴重影響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健康發展。 賄賂犯罪作為一種“交易型”的對合犯罪,行賄人與受賄人由于都從這筆“交易”中獲取了一定利益,犯罪之后雙方即形成了利益共同體,恰如“一條繩子上的螞蚱”,這就使得賄賂犯罪變得極為隱秘不容易被發現,即使被發現也由于過于依賴口供使得案件不易突破。因此,賄賂犯罪一直是腐敗犯罪中的“痼疾”。
一、“重查受賄、輕辦行賄”辦案格局下對行賄人的司法處理
長期以來,賄賂犯罪雖然是典型的對合犯,但是由于受賄一方是公權力“尋租”的行為,所以一直是反腐敗打擊的重點。加之出于諸多法律層面和辦案策略的原因,以至在查處賄賂犯罪時形成了“重查受賄、輕辦行賄”的辦案格局。大體來看,“重查受賄、輕辦行賄”辦案格局有以下幾個方面的成因。 首先,這乃是由賄賂犯罪的特殊性引起的。賄賂犯罪由于極為隱秘,還日趨復雜化和智能化,物證與書證極難獲取,這就導致查處賄賂犯罪對言詞證據尤其是口供的依賴性非常高。而由于賄賂犯罪往往當事人極少,一般只有行賄人和受賄人在場,行賄人和受賄人又因共同利益容易形成“攻守同盟”,要想獲取賄賂犯罪的口供極為艱難,“分化瓦解”便成了主要的策略。現實辦案中,從打擊腐敗行為的辦案重點出發,經常采取先突破行賄后突破受賄的模式,而突破行賄人口供時,為了解除行賄人的顧慮,給行賄人以免于處罰或者從輕處罰的“政策承諾”遂成了重要手段之一。 其次,這是由我國刑法實體法律的相關規定決定的。根據我國《刑法》第390條第二款的規定,“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這乃是刑法為了瓦解賄賂對合犯罪、鼓勵行賄人如實交代的重要規定,也是辦案實務對行賄人“從寬處理”的唯一法律依據。從另一個方面講,根據我國《刑法》第389條的規定,行賄人構成行賄犯罪,需要有“為謀取不正當利益”這一構成要件,而實踐中“不正當利益”的內涵與外延十分不易界定,容易引發分歧,從而影響對行賄罪的處理,這也是“輕辦行賄”的一個重要原因。
二、“輕辦行賄”及其方式的問題
就成因來看,“重查受賄、輕辦行賄”辦案格局的形成具有一定必然性,這乃是賄賂犯罪本身的特性決定的。但是就長遠來看,一味地“重查受賄、輕辦行賄”卻無法有效打擊賄賂犯罪,不利于遏制腐敗現象。畢竟賄賂犯罪是一種對合犯罪,只有對受賄方和行賄方都給予有效打擊,才能有效發揮法律的威懾功能。 而且在“重查受賄、輕辦行賄”的辦案格局下,偵查機關出于分化瓦解的考慮,以“政策承諾”的形式換取行賄人的口供并對行賄人直接作不立案處理,這種廣泛存在的處理方式也存在諸多問題。首先,偵查機關的“政策承諾”并無可靠的法律制度保障,是否兌現承諾具有較強的恣意性,這就使得行賄人對于“政策承諾”顧慮重重,分化瓦解的策略經常難以奏效;一旦偵查機關失信,從長遠來看也會影響查辦賄賂犯罪的辦案環境。其次,雖然根據《刑法》第390條第二款,如果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但是刑事訴訟法卻缺乏明確的程序性規定。根據現代刑事訴訟理念,只有法院才擁有定罪量刑權,那么如果對行賄人進行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理論上也應當由法院進行宣告,偵查機關直接對行賄人作不立案處理則與這一理念相悖。最后,偵查機關為換取行賄人的口供,而對配合調查的行賄人不予立案,有與行賄人進行“交易”之嫌;而且由于偵查監督制度的完善,偵查機關的這種行為需要接受偵查監督部門的立案監督,一旦偵查監督機關要求偵查機關對已經作出“政策承諾”的行賄人進行立案,偵查機關將面臨“有苦難言”的窘境。
三、《刑法》第390條第二款的“尷尬處境”
應該說,偵查機關在向行賄人進行“政策承諾”時,其法律依據主要是《刑法》第390條第二款。但是如前所述,偵查機關對行賄人配合調查交代行賄行為的行賄人直接作不立案處理,則有重大問題。如果肯定《刑法》第390條第二款的立法價值,那么對于這一實體法規定如何在程序法層面進行規范則是立法必須解決的一個問題。 根據我國《刑法》第390條第二款,“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可以減輕處罰或者免除處罰”,對其性質,在刑法修正案(八)頒布以前,學界存在不同見解。具而言之,主要包括以下三種:(1)特別自首論,這類見解認為,該條款是一項“提示性”條款,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其行賄行為實質上是就是“自首”情節,其可以“免除處罰”的功能也只有“自首”;(2)重大立功論,由于賄賂犯罪隱蔽性極強,行賄人主動交代自身行賄行為,實質上是對受賄人的檢舉揭發,屬于立功表現,其量刑幅度也與“重大立功”相同;(3)坦白制度論,行賄人在被追訴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實質上是被動到案后對自己犯罪行為的“坦白”,但是刑法修正案(八)頒布以前我國刑法中并無“坦白”這一量刑情節。
筆者認為,《刑法》第390條第二款不能籠統地認定為我國刑法規定的“自首”、“立功”和“坦白”(“坦白”系刑法修正案(八)所新增),而應進一步區分。《刑法》第390條第二款將行賄人主動交代自己的行賄行為的時間點定為“被追訴前”,那么無論是行賄人主動到案、被動到案只要最終交代了其行賄行為,那么均可以就該行為獲得“減輕處罰或免除處罰”。如果行賄人主動到案并如實供述了其行賄行為,那么構成“普通自首”;如果行賄人因其他犯罪行為被動到案,但是供述了司法機關未掌握的其行賄行為,則構成“特殊自首”;如果行賄人因為其行賄行為被動到案,后主動供述了其行賄行為的,則構成“坦白”。而由于賄賂犯罪對合犯罪的性質,行賄人無論主動到案還是被動到案,在其供述其行賄行為時雖然貌似也是對受賄人的檢舉揭發,但實質上均無法構成“立功”,因為究其實質如實交代自身行賄行為雖然相當于交代受賄人的受賄行為,但是一項行為在法律上卻不能重復評價。 因此,筆者認為《刑法》第390條第二款乃是專門針對賄賂犯罪中行賄人的一項特殊規定,就其“減輕處罰”、“免除處罰”的立法用語來看,其乃是一項量刑規定,但是其卻不同于刑法設置的“自首”、“立功”和“坦白”三類量刑情節。其立法初衷應旨在分化瓦解賄賂對合犯罪中行賄人與受賄人的“攻守同盟”,鼓勵行賄人“倒戈”,但是其關于“主動性”的規定頗顯理想化。加之該條款缺乏相應的程序性制度予以保障,最終導致了這一條款在司法實務中被偵查機關的“變相適用”。
四、結語:行賄人的“污點證人”地位應從事實進入規范
從某種程度而言,司法實務與法律規范之間應當存在一個良性的互動。雖然嚴格來說,司法實務作為法律規范實施的過程應當嚴格依照法律規范進行,這也是法治實現的基本保障,但是如果司法實務長期存在“脫法”現象,那么或許法律規范本身也應進行適度反思。正如哲人黑格爾所說,“存在的就是合理的”。當事實與規范長期脫節的時候,如果事實具有合理性,那么應當改變的必然是規范。 以此來看我國司法實務中“變相適用”,《刑法》第390條第二款這一現象,便能得到很多啟示。其實,司法機關對主動交代行賄行為的行賄人給予“不立案處理”后,行賄人在賄賂案件中的地位便是“污點證人”,而“污點證人”作為一個法律名詞在法律實務中也并不陌生。只是在法律規范和法學研究中,“污點證人”一直得不到承認,雖然它在法律實踐中廣泛存在。 細究之,“污點證人”之所以不被承認,從根本上講,仍是我國法律文化中“絕對正義”的理念在作祟。讓所有的犯罪都得到懲罰,這是法律嚴肅性的體現,其反映的刑罰必罰性也是刑罰發揮職能的關鍵。但是隨著法律實務研究的深入,任何一個理性務實的人都必須承認,“犯罪黑數”是大量存在的,絕對正義無論怎么看都是一個美好的理想。樹立“相對正義”的正義理念只是更為理性的選擇,承認“相對正義”并非就是對正義理想的背叛,也不會動搖對法律權威的確信。在“相對正義”的視野下,接受“污點證人”也就不會顯得那么困難。 退而言之,如果廣泛承認刑事司法中“污點證人”的存在仍有困難,畢竟實務中操作有被濫用的風險,那么承認賄賂犯罪中行賄人的“污點證人”地位則顯得十分可行,且對于懲治賄賂犯罪來講具有極大的制度價值。從法律規范層面講,我國《刑法》第390條第二款的規定本身已經體現了法律對賄賂犯罪特殊性的關照;從司法實務的角度看,當下打擊賄賂犯罪的司法實務也體現了這方面的制度需求。只有承認行賄人“污點證人”的可能性地位,才能彌合對行賄人司法處理方面司法實務與法律規范的緊張關系。 具體來說,筆者認為應當首先借鑒《刑法》第390條第二款的立法模式,即仍從實體法角度對被動到案后坦白交代自身行賄行為的行賄人給予特殊規定,但是特殊規定的性質應當進行修正。對于《刑法》第390條第二款規定的行賄人交代其行賄行為“主動性”的要求,應當刪去,淡化該條政策性質的倡導性,強化其作為法律規范的操作性。至于對《刑法》第390條第二款“量刑情節”的性質,也應當修正為直接對刑事責任的“審查性豁免”,其在效果上的差別是:如果是“量刑情節”,那么對行賄人就是定罪而免于處罰;如果是對刑事責任的“審查性豁免”,那么對行賄人即是由法院在審查后作無罪宣告。只有從實體法角度進行規定,才能免卻執法機關或者司法機關與行賄人就行賄人的刑事責任進行交易的嫌疑;只有直接對被動到案后坦白交代自身行賄行為的行賄人的刑事責任給予“審查性豁免”,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特別是在商業賄賂中,才能完全解除行賄人顧慮,從而最大限度發揮該制度分化瓦解的立法價值。 在實體法修正的基礎上,對現在司法實踐中“變相適用”法律的現象從程序法角度進行規范也顯得極為重要。這一方面體現在,偵查機關不能對被動到案后交代自身行賄行為的行賄人直接即作“不立案處理”,畢竟這與現代刑事訴訟理念相悖,而應由法院在對行賄人的行為進行評價后對其刑事責任作進行豁免,即“審查性豁免”。另一方面,對于被動到案后交代自身行賄行為的行賄人應當有相對特殊的刑事訴訟程序,保證其此次行賄犯罪行為不會被追究刑事責任、保證其可以享受證人的保護待遇,包括偵查機關特殊的立案程序、偵查終結、審查起訴時提請豁免其刑事責任的意見文書、對其作證的保護措施應該都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