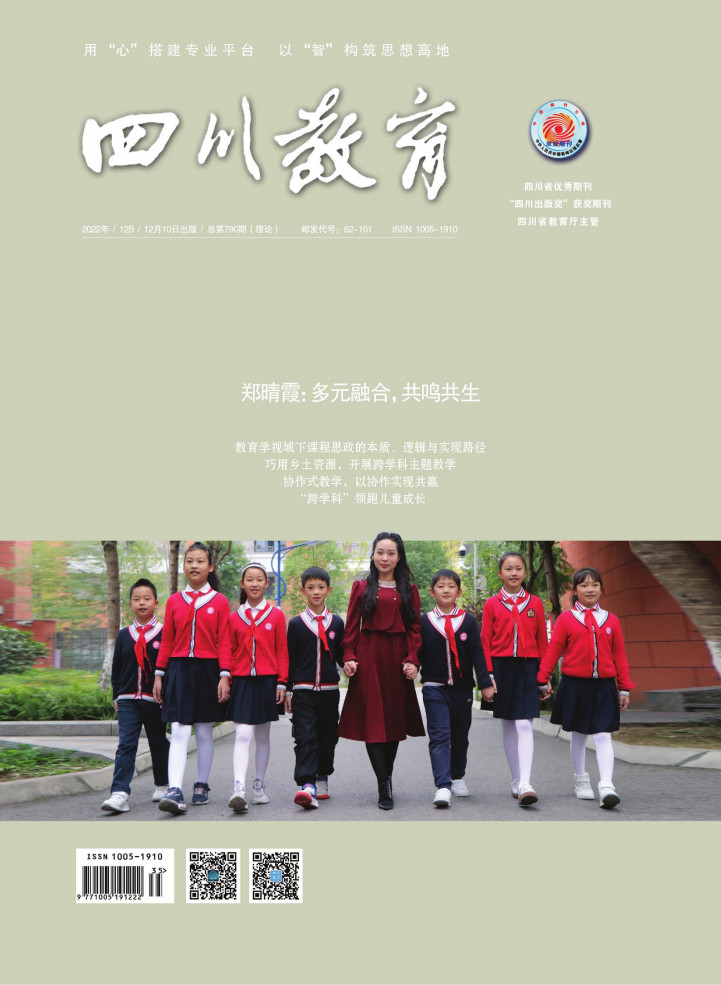國家介入與商會的“社會主義改造” ——以武漢市工商聯為例(1949—1956)
未知
【內容提要】1949年武漢解放之后,在接收改組原有商會、工業會的基礎上成立了工商業聯合會。新立的工商聯直接受新興政權之領導,在組織、人事及職能方面均已重新構建。與民國時期國家對商會的有限介入相較,共產黨領導下的新興人民政權對工商業聯合會采取的是全面強勢介入的政策。經改組重建后的工商聯在對資本主義工商業的政治、經濟改造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摘 要 題】共和國史研究
【關 鍵 詞】國家介入/工商聯/“社會主義改造”
【正 文】 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后,為確立“嶄新的”社會主義制度,對所謂“舊社會”進行了全面的介入與改造,民國時期普設的商會組織亦在其列。在整合原有各級商會、工業會的基礎之上,創建了全國性的工商聯組織體系。與民國時期的商會相較,工商聯可以說是商會制度的又一次重大轉型。新立的工商聯組織在黨和政府的直接領導之下,以私營工商業者為主要工作對象,成為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施管理及開展社會主義改造的重要組織基礎。不過,以工商聯在中國商會發展史中的轉折性意義,學界對其關注卻仍顯不足。在對晚清及民國時期的商會史研究已取得豐富成果之后,確有必要對1949年以后的商會史加以關注,如此才能將商會史研究延至當代,構建中國商會的完整歷史,也更能探究不同國家形態之下商會制度轉型的內在根源及其歷史作用①。本文擬以武漢市工商聯為例,運用武漢檔案館所藏的工商聯檔案資料,對這一問題稍作探討。
一、新國家的介入及武漢市工商聯的創建
武漢位居九省要沖,自古以來就為工商輻輳之地,在華中地區呈網狀輻射的商路格局中居于中心地位。武漢商人團體的發展有極為悠久的歷史,在明清時期來自全國各地的商民就在漢口建立了為數眾多的會館、公所。在晚清民初,武漢也成立了新式的商會、同業公會,漢口總商會是當時具有全國性影響的商會之一。至1934年,漢口市商會下屬工商同業公會共計159所[1] (p31)。至1947年,國民政府頒布《工業會法》,要求將工業行業從商會中分離出來另組工業會,漢口也成立了工業會。至1949年武漢解放前,漢口還設有工業同業公會11個,商業同業公會共82個,分屬市工業會及市商會管理[2] (p320—322)。以商會、同業公會為主體商人組織網絡在維護武漢商人的利益,推動行業自治,發展地方經濟等方面都發揮了重要作用。 在新中國成立之后,如何有效利用這一歷史性的制度資源,使之服務于國民經濟的恢復與社會主義改造,成為新政府首先要面對的問題。從政治上講,新國家的國體是無產階級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商會及工商同業公會代表的卻是“資產階級”的利益。在國民黨統治的時代,資產階級還曾與無產階級發生過激烈的沖突,資產階級正是利用商會以及同業公會的集團力量與無產階級抗衡,聯合政府壓制工人運動。但在另一方面,商會、同業公會又是最為普遍的商人團體,聯系著廣大的公司、行號和私營工商業者,其組織效能亦不容忽視。鑒此,中國共產黨在全國基本解放、人民政權初步穩固的政治形勢下,開始對商會進行全面干預與改組,以期將之改造為符合社會主義新生政權需要的工商團體。1951年7月,時任政務院副總理的陳云發表談話,就表示工商聯不同于舊商會,主要是私營企業利益的代表組織,但少數國營企業也可以作為團體代表參加;工商聯實行全國、省、縣三級制;同時,強調要加強黨對工商聯的領導[3] (p259)。這實是指明了商會改造的方向。 國家首先對商會重新進行了制度安排,在此基礎上構建了全國性的工商聯組織體系。1949年8月,中共中央發出《中央關于組織工商業聯合會的指示》,做出了將商會改組為工商業聯合會的正式決定。全國工商聯籌備會于1949年成立,各省市先后成立了工商籌備委員會。同年9月,武漢市召開第一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工商界建議成立新的統一組織。武漢市政府責成工商管理局于10月26日指導成立了市工商聯籌備會。籌備委員由武漢市政府遴聘,早期確立有70人。11月,籌備會接管了原漢口市商會、漢口市工業會、武昌市商會及漢陽縣商會,并在武昌及漢陽設立辦事處。會員代表包括私營工商業者、手工業者、行商、攤販,以及國營、公私合營、合作社的團體代表②。據1952年7月的統計,武漢市工商聯的私營企業會員共39950戶,占會員代表的絕大多數[4] (p312)。 就全國范圍內看,在1952至1953年間,完整的全國工商聯—省(市)工商聯—縣市(區)工商聯的三級體系就基本建立。1953年10月,中華全國工商業聯合會在北京正式成立,陳叔通任主任委員,會議選出執委209人[5] (p1)。武漢市工商聯的成立要稍早一些,在1952年11月武漢市工商聯第一屆會員大會召開,正式宣布成立,由陳經畬任主任委員,執行委員會90人,陳亦為全國工商聯之執委[4] (p306)。1952年10月至12月,硚口區、江漢區、江岸區、武昌區、漢陽區相繼召開會員代表大會,成立區工商業聯合會[6]。武漢市工商聯設置有執行委員會、監察委員會及組織、財經、稅務、企改、調解、文教等專門辦事機構。區工商聯在組織上屬市工商聯領導,在有關全市的問題上遵行市工商聯的決定和指示。各區工商聯亦根據業務需要設置有相關組織,如硚口區工商聯就設置了學習、組織、業務、稅務四個專門委員會,分別推行宣傳教育、組織設置、加工訂貨及稅收征稽等事項[7] (p16)。武漢市工商聯在直接吸收工商企業入會之時,也保留了原有的同業公會作為下屬的專業性行業組織,市一級同業公會接受工商聯之領導,在區一級也可設同業小組。武漢市工商聯、區工商聯及同業公會在職能上也稍有區分。據武漢市工商聯的報告,市工商聯在政治上經濟上起一般號召動員推動的作用,并集中反映工商界各階層的問題和意見,在經濟活動方面,其重點是全市性和通業性的活動;區工商聯主要是進行政治活動,并配合行業進行具體貫徹到戶的經濟性工作;同業公會以專業性工作調查統計協助研究任務改進為主[8]。不過,在實際運行過程中,很難嚴格加以區分。在市工商聯的統籌下,區工商聯及同業公會均承擔了政治改造及經濟改造的任務。 國家還對工商聯的人事安排及財務制度施加影響。武漢工商聯之組建雖然以黨政部門的直接領導為主,但不論是籌委會或者是正式成立之后的執監委會,其領導成員仍以工商界人士為主體。不過,這并非意味新政權仍然起用的是“原班人馬”。政府顯然非常重視這些人士在解放前活動及解放后的思想狀況,重點起用的是與共產黨具有一定歷史聯系或者在解放后能夠認同社會主義路線、思想覺悟較高的人士參加。在此,可稍對解放前夕漢口市商會的情況作一追溯。斯時,中共地下組織已與武漢工商界建立聯系,在中共主持的武漢市民臨時救濟委員會之中,就有賀衡夫、陳經畬、王際清、趙忍安等商界聞人參加,該會辦公地點即設在漢口市商會之內。在1949年5月人民解放軍進城前,漢口市商會、工業會還與地下黨組織聯合籌集救濟糧分送各維持治安部隊,維持社會秩序。在解放軍進城之后,商會還為軍隊籌借糧食[9] (p587)。曾任武漢棉布業同業公會執委的王際清回憶說,在臨近解放之時,中共武漢市委的宋洛和史林峰來到他家,代表中共中央中原局對他表示慰問,使之深受感動,“從此在共產黨的領導下,走上光明大道”[9] (p583)。王在武漢解放后頗受重用,先后擔任市政協主席、市工商聯副主委,而賀衡夫、趙忍安也分別擔任過武漢市工商聯籌委會的主任委員或者副主任委員,這自然與其在解放前就與中共存有歷史聯系切切相關[10] (p37)。 在國家建立之后,政府主要通過政治運動及思想教育對工商業者進行思想改造,并依其表現對之實施甄別與選用,武漢市工商聯籌委會之選定及改組基本按照這一原則進行。1951年底至1952年10月,黨在全國范圍內開展了“三反”、“五反”運動。武漢工商聯在此階段雖還處在籌備階段,但也參與其中,對于領導成員或者會員在運動之中的表現,也加以考查與評定。有認為不合要求的,則予以重點“關照”,或是撤除其職務。1952年3月,武漢市工商聯籌委會經議決撤銷了陳煥章所擔任的副主委職務,所請由市工商局批準,其原因就是在于陳煥章在“五反”運動中拖延抗拒,隱匿財物、拖欠物款,予以撤職嚴辦。籌委會常委兼副秘書長楊笛樓在“五反”中與人訂立攻守同盟,拒不坦白從前被本會停職反省又為法院傳訊的歷史,被撤職處分[10] (p32)。武昌區辦事處在改組為區工商聯之申請中就說,“本處經長時間籌備,但從未有一次徹底的改革,因此在各級負責人中進步力量太少,通過‘三反’、‘五反’運動以后,有些已被淘汰,同時又涌現了大批的積極分子”[6] (p3)。可見,各級工商聯籌備及重組的過程本身就是人員更進的過程。從總體上看,受到處分的工商聯領導成員及判刑的工商戶所占比例并不高,但由于“五反”運動是新政權建立之后首次發動的針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者的政治運動,開展范圍之廣、執行力度之大,均為此前所罕見。這種以意識形態與政治運動相結合的辦法給廣大私營工商業者包括工商聯之領導成員以極大的震動,其潛在的威懾作用自不容忽視。不少人由此轉變其思想認識,積極配合工商聯之工作。 在武漢市工商聯正式成立之后,工商聯領導成員的選拔仍遵循了上述政治性原則,且國營企業及部門領導列入工商聯領導層者有所增加。1952年11月28日,武漢市工商聯第一屆執監委中,陳經畬為主任委員,副主任委員包括申新紡織廠副經理華煜卿、市政府貿易局副局長沈以農、勝新面粉公司董事長王一鳴、公私合營后的市投資公司董事長余金堂、開明公司董事長林厚周、建新面粉公司經理王際清等人;1955年3月8日出任第二屆執監委的有主任委員陳經畬,副主任委員10人,在上述6人基礎上增加了人民銀行武漢分行行長李賜恭、公私合營民生總公司副總經理童少生、公私合營申新紗廠副總經理厲無咎、江漢綢布公司副總汪富謙;1957年4月第三屆主任委員王一鳴,副主委有所增減[11] (p32—110)。由此看來,工商聯領導成員中有私營工商業背景的仍占多數,但在思想上多能認同社會主義,接受黨的領導。 在經費方面,武漢市工商聯在初立之時,仍以會員繳納會費為主,收支自理。隨著社會主義改造的進行,逐步改為由市財政統一支出,領導層及職員之薪水也基本由財政支出工資。如江漢區工商聯的初期經費本是自籌自給,向工商戶收取,但1958年后,經費改為由國庫開支,工商聯的干部亦正式編為國家干部[12] (p1)。就全市范圍而言,在全市完成公私合營后,工商聯就停止收取會費。1959年1月起,市工商聯之經費收支納入國家行政預算,人員編制列入行政編制[4] (p309)。這意味著,工商聯領導的身份也逐步由工商業者轉變為“半公家人”。言其為“半公家人”,是因工商聯與政府部門尚存有性質上的差別,領導成員亦多另有企業本職。 新國家還明確限定,工商聯與舊商會在性質方面有重大差異,職能范圍亦有不同。1952年8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公布了《工商業聯合會組織通則》,規定:工商聯在性質上是各類工商業者聯合組成的人民團體。工商聯之基本任務包括領導工商業者遵守共同綱領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指導私營工商業者在國家總的計劃下,發展生產,改善經營;代表私營工商業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或有關機關意見,提出建議,并與工會討論有關勞資關系問題;組織工商業者進行學習、改造思想和參加各種愛國運動[3] (p259)。同月,負責起草通則的中央私營企業局局長薛暮橋在政務院第147次會議上作了進一步的說明。薛暮橋認為工商聯的建立主要是為了解決對私營工商業的組織領導問題。關于工商聯的性質及職能,他認為,“現在我們的工商業聯合會與過去的舊商會不同,它是新民主主義國家各類工商業者的組織,它擔負著兩方面的任務:一方面是領導工商業者遵守共同綱領及人民政府的政策法令,另一方面是代表私營工商業者的合法利益,向人民政府或有關機關反映意見,提出建議。”[13] (p3—4)薛暮橋的說明與陳云的講話共同傳遞的信息是,建立新的工商聯取代舊商會并非單純的組織替代,而是國家改造私營工商業者的一項重要舉措。工商聯承擔的任務不單純是舊商會所謂“通官商之郵”,而是更強調它的政治性和服務性。當然,文件之中也強調代表私營工商業者的合法利益,但這并沒有成為工商聯的工作重點。 國家對于工商聯政治屬性方面的規定在政治體制方面有所落實。各級工商聯要接受黨和政府的領導,服從各職能部門的管理。在各級工商聯建立之后,亦被作為工商界參政的代表組織納入到統戰及政協系統之中。武漢市工商聯作為私營工商業者及工商界的代表組織參加了市政協,并選派代表在政協任職,同時市工商聯的領導成員大多屬于民建的會員,也要接受市委統戰部的直接領導[11]。這些,都突出了工商聯的統戰性。不過,工商聯被定性為人民團體,又非政府機構,而是具有民間組織的象征意義。
二、工商聯與社會主義改造的推進
在新國家對商會進行了“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與國家性質相符合的工商聯體系之后,工商聯反過來又成為恢復國民經濟、對資本主義工商業實施社會主義改造的組織基礎。本文就從對同業公會的組織改造、對資本主義工商業者的政治改造及經濟改造等三個方面加以概括論述。 1. 工商聯與同業公會的組織改造 新國家對于原有商會和同業公會的改組在程序及方法上都有所不同。由于同業公會原為商會的基層組織,在商會的組織運作中有著不可替代的作用。工商聯在籌備期間及正式成立之后,都將改組同業公會作為其重要工作內容。不過,各地對于同業公會之改造政策又有所不同。青島等少數地區在初期將同業公會取消,不過后來又加以恢復。大多數地區如武漢一樣積極采取措施對同業公會進行整頓[14]。 在薛暮橋對《工商業聯合會組織通則》所作的說明之中,對同業公會實施組織改造的目的及其方針有明確的闡釋。《工商業聯合會組織通則》規定,市縣工商聯主要以企業或合作社為會員,但這并非要完全廢棄同業公會,而是要將同業公會的性質加以轉變。就他看來,“同業公會是工商界歷久相沿的組織,過去且是工商業聯合會的會員單位,它們具有更大的封建行會性。解放后有些同業公會得到了初步的改造,特別是‘五反’運動對同業公會的改造起著相當大的作用。但在組織上,同業公會仍然是各自獨立的組織,它代表本行業的各工商戶來參加工商業聯合會,其經費的收支和干部的任免,均不受工商業聯合會監督,這樣就破壞了工商業聯合會的統一性。”[13] (p3)“封建行會性”是政府對舊同業公會性質的認定,也說明它必須經改組方能被運用。說明還對同業公會之組織設置及其與市區工商聯組織的關系作有解釋,“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凡屬對國家經濟有作用的行業,可繼續保存同業公會的組織。……同業公會下可按業務相近,或按地區組織小組;區的行業小組受同業公會及區工商聯或區分會雙重領導”。在職能方面,“在有區一級組織的大中城市,同業公會主要應是在經濟方面的活動,如組織各種加工訂貨,執行產銷計劃,評議稅負,同業議價等。中小工商業者的一切政治性的活動,應該由區工商聯或區分會來領導。”[13] (p6) 武漢市對同業公會的整頓基本按上述原則進行。在市工商聯籌備會成立之后,即提出整頓同業公會的分類原則:工業同業公會與商業同業公會似以分開為宜;三鎮分別組織;同類性質組織一個同業公會;以本市為限,本市以外同業公會有分支機構在漢亦可加入;戶數太少可加入相近同業公會;公私均可加入。后推選出王一鳴等52人為市工商聯同業公會整理委員會委員,王為主任委員,調查各公會情況,擬訂整理方案,分批整理[15]。第一期自1949年12月—1950年2月,完成糧食業、百貨商業、化工工業、花紗商業、紡織染整工業、米面工業、綢布工業等七個行業的整理③。市工商聯正式成立之后,繼續對同業公會進行改組。到1953年3月重新提出改組同業公會的議案,該方案據“私營企業統一分類辦法”,計劃將漢口、武昌、漢陽三個地區現有的100多個同業公會(漢口79個公會,武昌23個公會,漢陽29個公會)調整合并為55個全市性的同業公會和同業委員會,并將公會內400多個名稱不一的自然行業小組,依照分類目錄的經營性質,統一調整為196個自然行業小組[8]。后繼改造基本按此進行。 自1950年開始,武漢工商聯就提出對同業公會進行統一管理,即行政、人事、財經統一,要求同業公會接受工商聯的垂直領導。具體來講,就是由工商聯對同業公會實行會費統一收支、干部統一調配、財產統一接管,并逐步實行集中辦公。這樣,就可改變了民國時期同業公會在會費支配及人事選派方面的自主權,將同業公會納入到了工商聯體系之中。此計劃至1954年方才正式實施。1954年,武漢工商聯以同業公會為單位,將業務相近者、依形勢發展,會員減少者、業務不多不須另組者、行業雖不同但屬同一國營企業單位領導者,前后分三批實行集中辦公。集中的內涵是相近行業辦公機構合在一起,集中辦公同業公會的職工由工商聯統一調配;財產由工商聯統一管理分配。以行業論,第一批有機制卷煙業、油脂業與米面業,竹木業與磚瓦、灰沙業,釀酒業與食品制造業,文具用品與紙張業,分別聯合集中辦公。以地區論,漢口為重點區域,亦分三批進行,第一批于6月22日動員了16個同業公會遷至7個地點集中辦公;第二批于7月3日動員了31個同業公會遷至12個地點集中辦公。截至7月21日止,第一批和第二批集中辦公的行業均已搬遷完畢。第三批則于7月21日起,分別動員24個同業公會遷至9個地點集中辦公[16]。在此基礎上,武漢工商聯仍適時對同業公會進行持續調整。1955年9月,武漢工商聯又專門成立了調整改組委員會對同業公會進行整頓,選取綢布業及茶葉業、醫藥三個行業公會作為試點[17]。改組后同業公會的委員會仍以私營企業主或其經理人員為主,也包括有國營企業人員,有的還是原任執委。武漢機器工業同業公會改組后,其原任執委就占相當比例[18]。大致上,工商業對同業公會的調整是以行業歸口改造及統一管理為組織原則的。 武漢市工商聯對同業公會之組織性質及地位有清楚認識,在其業務報告之中,工商聯認為同業公會是其領導下的一個專業性組織,在進行對私營工商業者的社會主義改造的過程中起統計監督協助政府教育同業。同業公會與區會并為市會之組織基礎,“區工商聯和同業公會像市工商聯的左手和右手,雖是一以企業的改造工作為主,一以人的改造為主,但又必須緊密配合,在市工商聯的統一領導下,分工合作,共同完成雙重改造的任務。”[19] (p49—50)就二者分工合作、上下共舉的組織關系而論,這一評論是相當精準的。
三、小結
1949年新中國成立,國家性質驟變,國家對于商會之制度需求有根本改變。新成立之工商聯為在黨和政府領導之下對私營工商業實施管理的人民團體,與原商會在組織形態、人員選派、職能范圍等方面均有明顯差異。武漢工商聯成為武漢市的工商界統一性組織,并在各區設立了分會,建立了與全國工商聯體系一致的地區體系。同時,武漢工商聯要接受武漢市委及市政府的領導,接受各部門的業務領導。工商聯作為私營工商業者的聯合性組織,亦被作為工商界的代表組織,參與新國家的政府體系。工商聯在組織設置、人事財務、性質職能等方面都要遵從新國家的安排。可以說,新國家對工商聯的全面介入的確使工商聯成為集統戰性、經濟性、民間性于一體的復合性組織。工商聯組織實施對同業公會的改組,參與到國民經濟恢復及社會主義改造的進程之中,為新國家各類政策的實施立下重要功勛。從協助政府的角度來講,工商聯的職能發揮基本上達到了政府的預期目標。 但問題是,武漢工商聯是否如《工商聯組織通則》所設定的是私營工商業者利益的維護者呢?依上所論,國家對工商聯進行了全面的介入,工商聯也將承擔政府所規定之管理職能作為主要任務,工商聯又如何獲得工商業者的支持并以推進種種政策呢?這就要從私營工商業者對工商聯的看法來加以分析。經過改造的工商聯雖然在人事上仍然保持了不少工商界的人員,但在部分私營工商業者的眼中看來,工商聯只是新國家的政府類組織,而并非工商業者自身利益的維護者。江漢綢布公司的一位私方人員說:“我們是工商聯公債推銷支會的會員,不是工商聯的會員,因為工商聯除公債外,沒有替我們做旁的事。”[20] (p31)工商聯一意以執行政府法令政策為己任,實際上在某種程度上忽視了對私營工商業者利益的維護。工商聯工作之獲得推動,其權力在相當程度上來自新國家的專政之威,而并非完全出自私營工商業者的自發認同。從這個角度說,工商聯的民間性已迅速退化。雖然這種觀念上的差異并未最終阻礙社會主義改造的實現,但卻增加了工商聯在推行有關政策時的難度。在社會主義改造徹底完成之后,工商聯的經濟性工作實際上也大為削弱,而統戰工作則成為其主要職責。
注釋: ①關于1949年后工商聯的研究還十分不足,較具學術性研究的論文有劉建中:《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廣州工商社團組織》,馬敏:《中國商會的現代演變》(第三屆中國商業史國際學術討論會論文)。在朱英主編的《中國近代同業公會研究與當代行業協會》(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一書中對1949年后同業公會的演變情況有所論述,亦涉及到工商聯的組織改造問題。 ②武漢市工商業聯合會編:《武漢市工商業聯合會成立大會匯刊》,1952年印刷,第142頁。 ③參見武漢市工商業聯合會編:《武漢市工商業聯合會成立大會匯刊》,第142頁。 ④參見新華社新聞稿:《全國工商聯發出通知普遍組織工商界討論憲法草案》,總第1482期,1954年第6期,第18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