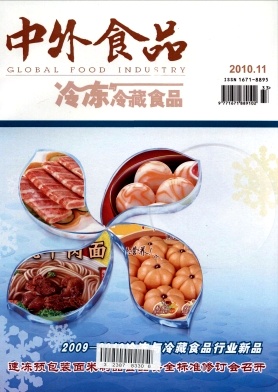商會史研究與新史學的范式轉換
馬 敏
【英文標題】The Study of Chamber of Commerce History and the Paradigm Change of New Historiography
【內容提要】近20年來,中國商會史研究越來越為中外學者所矚目,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熱點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城市史、經濟史、社會史、現代化史諸研究領域的進展。本文在商會史研究與新史學建構的相關層面上,深入探討了商會史研究在研究視角、歷史解釋、理論思維、范式突破諸方面對新史學建構的學術意義。在以上研究的基礎上,本文認為面向21世紀的新史學發展的基本方向乃是以新社會史為標志的“總體史”。
【摘 要 題】史家與史學
【英文摘要】The study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history has attracted more and more Chinese and foreign scholars’ attention in the recent 20 years,which also becomes one of the focuses in China’s modern history and studies as well as promotes the progresses in city history,economic history,social history,modernized history to the great extent.Based on the relevant aspects constructed in history research of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and new historiography,this paper probes into research angle,history explanation,theoretical thinking,and paradigm breakthrough respects in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hisctory study,which build the academic meaning of new historiography.On the basis of above studies,the paper thinks that the basic orientation of the development in new historiography on facing the 21st century,is"general history"signed the new Society history.
【關 鍵 詞】商會史/新史學/范式/總體史
the Chamber of Commerce history/new historiography/paradigm/general history
【 正 文】
近20年來,中國商會史研究越來越為中外學者所矚目,成為中國近代史研究的熱點之一,并在很大程度上促進了城市史、經濟史、社會史、現代化史諸研究領域的進展。換言之,商會史研究的開展是與改革、開放后新史學的構建相同步的,商會史研究中的突破體現了新史學所取得的進展。
之所以認為商會史研究的進展與新史學的進展有著內在關聯,乃是因為商會史研究能在不長的時間中異軍突起,取得較好的學術成果,首先便在于廣大商會史研究者能夠勇于解放思想,更新觀念,自覺地將社會學、社會心理學、法學、政治學等相關學科的理論及方法引入史學研究,從而帶來了研究視野的開拓和研究層次的提升。否則,“商會史研究只能是一種表象的陳述,而不能充分顯示商會史研究應具有的特色”[1]。
新史學的建構其實也才剛剛起步,還有許多新的領域需要拓展、許多新的問題需要研究。商會史研究亦如此。過去在理論架構上,商會史研究中主要運用的是社會學中結構—功能理論,并深受現代化理論的影響。在這種理論范式的支配下,比較注重商會的社會屬性、角色地位、組織結構、功能作用和商會中的現代性因素,卻相對忽略商會的復雜性和區域性特征,忽略其與傳統相聯系的一面。對引進的一些西方理論,如“公共領域”和“市民社會理論”,也多少有食洋不化之嫌。這些,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新史學建構中所存在的理論和方法上的問題。總之,本文擬在商會史研究與新史學建構的相關層面,深入探討商會研究在研究視角、歷史解釋、理論思維、范式突破諸方面對新史學構建的學術意義,而重點又將放在商會史研究中的范式轉換問題上。
一、緣起:范式與范式轉換
究竟什么是“范式”(paradigm,或譯規范、典范)?其實這一概念的發明者庫恩也從未給出明確的定義。從他對“范式”在科學革命中的作用的闡釋,大致可理解為某一科學群體在一定時期內基本認同并在研究中加以遵循的學術基礎和原則體系,它通常包括一門學科中被公認的某種理論、方法,共同的對事物的看法和共同的世界觀。庫恩認為,范式為科學共同體(科學工作者按同一規范組成的集體)所一致擁有,他們按照統一的規范從事科學研究活動,這就是科學。在從事科學研究中發現有些事實不能納入共同體的范式內,就形成反常。反常發展到一定階段就形成危機。在危機中逐漸產生了提出新范式的需要,于是開始了科學革命。科學的發展便是如此循環往復,以致無窮。
庫恩有關“范式”的理論,雖然主要是對自然科學發展規律的認識和歸納,但對人文社會科學(包括歷史研究在內)同樣具有指導意義。人文社會科學除各種各樣的理論主張外,似乎也同樣存在貫穿于各種理論之中,但又超脫于各種具體理論之上的研究“范式”。如有的研究者認為,政治史、文化史、社會史在某種意義上說也就是幾種不同的研究范式。也有的研究者提出,近現代史研究中所謂“革命”模式、“現代化”模式、“國家—社會”模式等分析框架,也就相當于庫恩所說的“范式”。
盡管有的研究者主觀上并不認可,但在史學研究中卻總是自覺或不自覺地在使用某種范式或受到某種范式的制約,這乃是不爭的事實。因為任何帶有概括性質的科學研究,不可能憑空產生,總是要受某些理論的暗中制約,總是要建立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之上。理論思維的前提性和非空白性特征,決定了“范式”總是客觀存在的。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理解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中“范式”的轉換?究竟存不存在范式的轉換?范式轉換對史學研究究竟有何實在的意義?應該說,這些才是史學從業者所關注的重點所在。
楊念群在評論德里克關于中國近代史研究中現代化史學取代革命史學的“范式轉換”時,提出相反的意見,認為“革命”模式與“現代化”模式之間不是范式轉換的關系,“而是復雜的重疊關系,由于各自處理的對象和范圍并不一致,怎么可能要求出現像自然科學那樣的范式轉換奇觀呢?”他還進一步認為,“歷史學可能根本就不存在自然科學意義上的‘范式轉換’的可能性,因為我們無法滿足庫恩所規定的那種徹底性要求,即在放棄一個范式之前必得先證明其無效,或者既能解釋支持舊范式的論據,又能說明用舊范式無力解釋的論據。”[2](p55)我想追問的是,如果真的根本就不存在“范式轉換”的可能性,那么“范式”概念的運用對歷史學究竟還有何實在的意義?庫恩所強調的似乎恰恰是“范式轉換”在科學革命中所起的作用,而不是范式本身。他認為,“一種規范(范式)經過革命向另一種規范逐步過渡,正是成熟科學的通常發展模式。”[3](p10)雖然“自然科學”的范式與“社會科學”的范式有所區別,后者較之前者可能會具有更大的主觀色彩,但這似乎并不能否定“社會科學”的范式之間仍存在哲學意義上的否定或揚棄基礎上的“范式轉換”,而這種范式轉換是否也恰是社會科學認識不斷走向進步的機制?正如有的研究者所指出,作為“新史學”出現的新社會史“絕不僅僅是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而是一個史學新范式,一個取代傳統史學的政治史范式的新范式。”[4]這里明顯地發生了范式的轉換。同理,我們似乎也可以認同德里克的假設,認為“革命”史學向“現代化”史學的轉變也就是庫恩似的“范式轉換”,是一種史學認識的突破和升華,盡管它無法在史學中構成一個唯一或主導范式,也不可能完全徹底地否定先前的“革命”范式。其實,即使在自然科學中,也很難有如此徹底的完全否定。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固然是對牛頓經典物理學的否定或揚棄,但這并不意味著牛頓的古典理論已毫無價值,在一定的層次上和一定的范圍內,它仍有自身的解釋意義。
我始終認為,在將庫恩的理論借用于歷史研究中時,最適宜于“觀其大要”,而不能拘泥于細節。這就是要認真去思考這一理論對于我們深化歷史思維的啟迪作用。而“范式轉換”對史學研究的啟迪作用,首先就在于對某些規范性認識的質疑。
黃宗智曾將中國經濟史研究中解釋框架的危機歸結為“規范認識”的危機,提出:“所謂規范認識指的是那些為各種模式和理論,包括對立的模式和理論所共同承認的,不言自明的信念。”他認為,這才是庫恩“范式”一詞的真正涵義。在黃氏看來,規范信念和規范認識比起任何明白表述的模式和理論來,有著更為廣泛、更為潛移默化的影響力。它們的影響還不僅僅在于引導人們去想什么,更在于不想什么。它們往往構成不同理論、模式間發生爭議時共同的前提和出發點。但不幸的是恰恰是某些不言自明的共同前提和出發點似乎發生了危機,即規范認識的危機。危機主要來自于實證研究所揭露的一系列悖論現象。而悖論現象則是指那些現有規范信念認定有此無彼的對立現象在事實上的同時出現。黃氏所列舉的悖論現象包括:商品化和經濟不發展同時存在;城市發展與鄉村過密化的同步發展;分散的自然經濟與整合的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