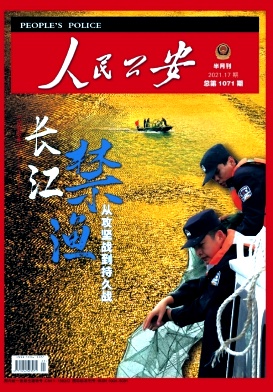從名士風度到圣賢氣象
朱漢民
今天我將和大家一起探討魏晉和宋明兩個時期的人格理想,也就是“名士風度”與“圣賢氣象”兩種不同類型的人格理想及其內在關聯。“名士風度”與“圣賢氣象”是士大夫們所追求的兩種理想人格類型,它們是魏晉與宋朝兩個不同歷史時期的產物,故而二者之間有著十分明顯的區別:魏晉名士往往是與不拘禮法、率性縱情、風流瀟灑、飲酒服藥的生活方式聯系在一起;而宋明理學家所追求的“圣賢氣象”則總是體現出一種憂患民生、兼濟天下、恪守禮教、修養心性的人生追求。
其實,這兩種理想人格類型均是作為“學者——官僚”的士大夫的精神投射。中國古代豐富的人生哲學、人格理想的學說,說到底均是一種士大夫精神的表達。士大夫是中國古代獨特的一種“學者——官僚”的社會階層,由于既從事社會管理又從事文化創造,故而形成了一種獨特的士大夫精神、人格理想。無論是“名士風度”還是“圣賢氣象”,其實均體現出古代士大夫的精神追求。
我們希望對這兩種理想人格類型形成的社會條件、文化資源、內在機制作一些探討,由此進一步思考它們在文化特質、思想形態、價值取向上的內在理路與相互關聯。
一、魏晉名士風度
魏晉名士風度的文化現象是與西漢以來出現的士大夫政治現象密切相關的,故而須從士大夫政治講起。應該說,西周封建制時代就有了宗法貴族的士大夫,并且也是兼及道藝與政事。但是,決定封建時代士、大夫身份的是他們的血緣關系,這與后來帝國時代由文化知識及相關的科舉制度來決定士大夫身份是不同的。西周的士大夫階層到了春秋戰國時期發生解體,其突出表現是政事與道藝的分離。在秦帝國時代,這種分離進一步制度化,出現了獨尊文法、專職行政的“文吏”與知識文化專業化的“學士”的不同社會角色的分立。但是,從西漢時期開始,隨著“禮治”與“法治”并舉,“儒生”與“文吏”開始融合,到了東漢后期,一種“亦儒亦吏”的社會階層完全形成,也就最終演生出了兼具行政功能與文化功能的士大夫。東漢時期完成的士大夫政治一直延續到中華帝國的末期,在傳統中國的社會政治結構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并產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
就在“士大夫”階層的演化、形成過程中,出現了一種對所謂“名士”推崇的現象。“名士”之所以能夠有名并受到推崇,當然首先在于他們作為文化知識占有者的學者身份,這是帝國時代士大夫們能夠成為居有高位的官僚身份的必要條件。所以,兩漢時期出現的大量“名士”,在主政者及民間社會的眼中主要是那些有才華、有品性、有學識的書生,并且許多往往還是不仕的民間學人。《禮記·月令·季春之月》中有“聘名士,禮賢者”的記載,而《注》云:“名士,不仕者。”《疏》在解釋“名士”時說:“謂王者勉勵此諸侯,令聘問有名之士。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在位者。”但是,到了合“學者——官僚”身份于一體的士大夫階層成型的東漢時期之后,人們指稱“名士”并不特別在意其“不仕”的身份,而是在意其士大夫特有的文化風貌、精神氣度。由于朝野的知識群體均普遍地追求這種士大夫所獨有的文化風貌、精神氣度,故而在東漢時期出現了一種推崇名士的社會風尚。這些士大夫們往往是“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之稱號。”
雖然都普遍表達出對士大夫的精神氣度的推崇和標榜,但東漢之末與魏晉時期的“名士”之標準卻發生了一個十分重大的變化,東漢黨錮之禍前后所標榜的是“風節名士”,“名士”往往通過“匹夫抗憤,處士橫議”的行為表現出一種積極入世、敢于與黑暗政治勢力抗爭的精神。
魏晉時期所標榜的“名士”,則轉型為“風流名士,海內所瞻”。魏晉所追求的“風流名士”風尚,正是這種灑脫活潑、自在適性的精神自由和個性表達,甚至許多與儒家禮教相悖逆的縱情率性行為,往往成為魏晉名士風度的標志。譬如《世說新語》載王孝伯所說:“名士不必須奇才。但使常得無事,痛飲酒,熟讀《離騷》,便可稱名士。”
魏晉時期風流名士的突出特點是個體意識的覺醒,這種個體意識的覺醒,使得魏晉名士全面關注、重視與感性生命、個體存在相關的一切價值:從追求外表的儀態容貌之美,到向往延年益壽的服食養性;從情色生活的縱情享受,到口吐玄言的哲理清談;從尋求歸隱山林、率其天性的精神自由,到“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時一杯酒”的及時行樂,總之,一切與個人肉體與精神生命有關的價值,諸如健康、長壽、美貌、智識、藝術以及精神享樂與肉體快感等都是魏晉名士所追求的。社會道德的“節義”不再是他們作為“名士”的人格標志。
“士大夫”畢竟是一種合“學者——官僚”為一體的社會階層。魏晉名士為了處理好個體價值與禮治秩序、精神自由與社會責任之間的關系,形成了魏晉名士所特有的雙重人格。
“學者——官僚”的雙重身份,轉化為自然與名教、隱逸與出仕、精神自由與恪守禮法、真情與文施、血性與世故的雙重人格。
譬如,有關出仕與隱逸的兩種人生道路選擇方面,他們的內心中一方面汲汲于功名利祿的追逐,向往廟堂之上的顯達、權勢與功名,盼望在經邦濟世的政治活動中施展自己的人生抱負;但另一方面他們又常常顯出對世俗權位、名教禮法的不屑一顧,表現出一種超脫世俗的生活追求,即向往山林之中的清逸、自在與閑適,盼望在竹林的清淡中獲得高雅的人生。所以,魏晉名士們總是在所謂“魏闕”與“江湖”之間充滿心靈的掙扎與精神的分裂。
其次,名教方面的神形分離而產生的雙重人格。他們在外在形體及行動中追求精神自由、個體價值的張揚,故而對約束自己的名教有諸多的貶抑甚至詆毀,另一方面他們在內心中又堅守名教,是禮教精神的堅定維護者。
唐宋時期,中國的政治社會結構發生巨大的變革,并使得士大夫的價值觀念與人格理念也發生重大變化。北宋初開始,士大夫們普遍倡導一種新的理想人格,這就是所謂的“圣賢氣象”。
二、宋明圣賢氣象
唐宋時期,中國的政治社會結構發生巨大的變革,并使得士大夫的價值觀念與人格理念也發生重大變化。魏晉以來的名士風度、雙重人格的思想與行為受到新一代士大夫的批評指責,一種新的人生價值觀念、人格理想普遍地受到主流士大夫們的向往和追求。北宋初開始,士大夫們普遍倡導一種新的理想人格,這就是所謂的“圣賢氣象”。“風度”與“氣象”意思接近,均是指一種精神人格的外在表現與流露,但“名士”與“圣賢”內涵則不同。魏晉的士大夫雖然也推崇周孔等儒家圣人,但他們從不把圣人作為自己追求、實踐的人生目標,而僅僅希望自己成為率性自由的風流名士。而宋儒則不同,他們不僅僅是推崇儒家圣賢,而且強調每個士大夫均要通過修齊治平的道路做圣賢,以圣賢的人格理想作為自己畢生追求、實踐的人生目標。
那么,宋儒所追求的“圣賢氣象”的內涵是什么呢?
首先,在宋儒眼中具“圣賢氣象”的士大夫,必須能夠關懷社會、心憂天下,具有“民胞物與”的博大胸懷,以社會和諧、國家富強、天下安泰為己任,積極參加治國平天下的經世濟民的活動。《宋史》:“士大夫忠義之氣,至于五季,變化殆盡……真、仁之世,田錫、王禹偁、范仲淹、歐陽修、唐介諸賢,以直言讜論倡于朝,于是中外搢紳知以名節相高、廉恥相尚,盡去五季之陋矣。”兩宋時期士大夫群體中這種心憂天下、名節相高的士林風習,促成了他們對傳統儒家人格理想——“圣賢氣象”的執著追求。
二程在教授弟子讀儒家經典時,強調要在孔子的人文關懷與道義承擔的精神中尋找“圣賢氣象”,他說:
孔子曰:“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懷之。”觀此數句,便見圣賢氣象大段不同。
其次,宋儒所推崇的“圣賢氣象”除了具有東漢“節義名士”及儒家傳統的救時行道、名節相高的社會道德內涵之外,同時還有魏晉“風流名士”以及老莊道家所追求的灑落自得、閑適安樂的個體人格及其精神超越。
兩宋開始,士大夫群體中盛行追求“孔顏樂處”。二程十四、五歲從學于理學開山周敦頤,周子并沒有向他們傳授什么深奧的哲理與經典的解讀,而是教他們“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據說后來程顥“自再見周茂叔后,吟風弄月而歸,有‘吾與點也’之意。”他顯然是從周敦頤那里領悟了“孔顏樂處”的深刻涵義。據《論語》記載,孔子曾自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另外,孔子還對弟子顏回贊揚說:“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在宋儒看來,孔子、顏子能夠在“人不堪其憂”的艱苦生活中感到精神上的快樂,具有十分深刻的思想內涵和人生指導意義。這一“圣賢之樂”正應該是他們深思的,也應是他們效法的。
孔顏之樂的深刻意義在哪里呢?其實它表達的正是“圣賢氣象”中追求個體精神灑落自得的一面。圣賢內心所達到“與物同體”、“天人合一”的精神境界,這一精神境界表現于外就是一種灑落自得、悠然安樂的“圣賢氣象”。這一點,在指導二程兄弟尋孔顏樂處的周敦頤那里,就表現得十分明顯。周敦頤是一個追求并達到這樣一個悠然自得的人生境界的人,據記載,周子“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這正是他的人生境界透露出宋儒所推崇的“圣賢氣象”,所以李侗贊嘆說:“此句形容有道者氣象絕佳。”可見,“孔顏樂處”與“圣賢氣象”有著深刻的聯系。
宋儒對“孔顏樂處”甚為熱衷。胡瑗曾以《顏子所好何學論》為題試諸生。二程兄弟從學周敦頤以后,就一直重視尋孔顏樂處及所樂何事。據《宋史·道學傳》記載,張載年少時喜談兵,“年二十一,以書謁范仲淹,一見知其遠器,乃警之曰:‘儒者自有名教可樂,何事于兵!’因勸讀《中庸》”。“名教可樂”是北宋學術的“問題意識”,這種問題意識“正是道學的萌芽”。由此可見,宋代士大夫們所推崇的“圣賢氣象”,不僅僅具有心憂天下、救時行道的一面,同時還有灑落自得、閑適安樂的另一面。他們總是借助于《論語》中的孔子、顏回、曾點等圣賢對“樂”的追求,而表達自己在自我的心靈世界中對自由、自在、自得、自樂的無限向往與追求。總之,北宋理學家們對“孔顏樂處”的追求和標榜,成為一種十分突出的文化現象。
宋明的“圣賢氣象”包括了上述兩個重要方面:社會責任與個人自在、憂患意識與閑適心態、道義情懷與灑落胸襟。宋儒希望“圣賢氣象”的理想人格在承擔社會責任的同時又有個人的身心自在,在具有深切憂患意識的同時又不能放棄閑適的心態,在堅守道義情懷的同時又具有灑落胸襟。
宋明儒家在中國思想學術史上的巨大貢獻,就是將“圣賢氣象”中社會關切和個體安頓奠定在一個以“天道”、“天理”、“太極”、“誠”為終極依據的哲學本體論基礎之上。名教與個體人格的終極依據均不是魏晉名士所說的“無”、“自然”,而是實際存在于社會之中與自我心性之中的“天道”、“天理”、“太極”。這時,社會憂患、經世情懷的價值依據不僅僅是人文關懷,而是與陰陽造化相關的宇宙精神;同樣,身心安頓、灑落胸襟的人道執著亦不局限于道德信念,也是由于對這個主宰浩浩大化的終極實體的精神依托。
在宋明理學史上,能夠列為著名道學家的重要學者,能夠成為理學名篇的代表著作,幾乎均是在建構宇宙本體論中統一社會關切與個人安頓,從而為“圣賢氣象”的理論體系做出了重大貢獻。理學家們發現,在推崇孔顏之樂、曾點之志時,如果過于強調個人身心的自在、閑適、舒泰、喜樂,使這種身心自在的追求與社會關懷、博濟事業分離開來,那就會落入魏晉名士、佛道宗教的價值虛無中去,從而背離周孔創立的圣人之學,而決不是周孔之教的“圣人氣象”!另一方面,作為一個儒家士大夫僅僅是講經世之業,而離開了天理的大本大根,同樣會因沾染政治功利之習而喪失圣賢氣象,盡管這種人十分有才干并做出了政治事業。《朱子語類》載:“圣人雖見得他有駁雜處,若是不就這里做工夫,便待做得事業來,終是粗率,非圣賢氣象。”朱熹認為那種能辦事、創造事業者如無道德心性工夫,仍無圣賢氣象。他強調的圣賢氣象必須建立在政治功業與從容灑落、堯舜事業與德性工夫相統一的基礎之上。
三、名士風度與圣賢氣象的內在關聯
無論是魏晉盛行的名士風度,還是宋明追求的圣賢氣象,它們均是中國文化史上一道亮麗的風景,為當時及后世的文人學者所景仰,被不同歷史條件、不同人生際遇的士大夫們所追求。應該說,這是古代士大夫的兩種人格理想類型,它們確實存在明顯的差別。但是名士風度與圣賢氣象決不僅僅是兩種不同類型的人格理想,這兩種人格是中國古代士大夫的人生哲學、人格理想發展中前后相關的兩個階段。名士風度與圣賢氣象之間不僅有著明顯的傳承發展的歷史關系,而且其問題意識也具有深刻的思想脈絡與內在理路。
我們著重對此問題作進一步分析。(一)士大夫主體意識的發展
魏晉與宋明時期的士大夫追求著“名士風度”與“圣賢氣象”的不同理想人格,但仍是深刻地體現出士大夫人生哲學與理想人格的思想邏輯脈絡與發展理路。
關于魏晉名士風度的思想特征及其評價,學術界一直有一個比較流行的看法,認為這是士大夫階層的一次思想解放與人的自覺,體現出士大夫個體自我意識的覺醒。
宋明士大夫追求一種“圣賢氣象”的人格理想,這種現象體現出士大夫群體價值意識的高揚。這種理想人格表達了以天下為己任的主體意識精神,但同樣包含并充分體現出魏晉名士風度中的個性化主體意識的內涵。如果說東漢名士體現出一種群體價值意識的精神,魏晉名士追求的是一種個體價值意識的話,那么,宋明士大夫推崇的“圣賢氣象”,則正是一種群體價值意識與個體價值意識的雙重弘揚。如果沒有魏晉名士有關個體生命、自我意識的覺醒,也就不會有宋明士大夫中有關“圣賢氣象”對理想人格的獨特追求與全面表達。
由此可見,從士大夫的主體意識角度來考察,宋明的圣賢氣象不僅包含和體現出士大夫的群體價值意識的覺醒,故而表現出他們憂患天下的人文關懷、經世濟民的社會責任;同時包含著士大夫的個體價值意識的兼容,從而表現出對個體心靈愉悅的追求,對自我精神安頓的關注。應該說,如果宋明的圣賢氣象只有前者或只有后者,那就與漢魏的士大夫精神沒有分別,體現不出士大夫精神人格的豐富發展與歷史演進。正由于“圣賢氣象”包括了上述的兩個方面,那么,它與魏晉風度的精神脈絡與內在理路關系就顯示出來。
(二)名教可樂的共同追求
在士大夫建構人生哲學與人格理想的過程中,名教與樂也是一個繞不開的問題。“名教”涉及群體生存的家國倫常、社會秩序,“樂”則涉及個體存在的生命意識、人生意義。然而,二者在現實中究竟是一種什么關系呢?歷代士大夫在各種歷史條件、社會處境中均能感到名教與樂之間的緊張關系。但是,他們無論是作為社會管理者還是文化創造者,均希望能夠將二者統一起來,也就是要在理論上、實踐中證實“名教可樂”的問題。
將“名教”與“樂”聯系起來,其“問題意識”源于魏晉名士。西晉樂廣提出:“名教內自有樂地,何必乃爾。”由于魏晉名士認為名教之樂歸本于名教中所依據的“自然”,其名教之樂就仍然只能歸因于自然,故而并沒有真正緩和名教與樂的緊張關系。從周敦頤、程顥、張載等宋儒在“尋孔顏樂處”中表現出“圣賢氣象”來看,應該說,他們確是從自己的內心深處領悟了這種名教之樂。魏晉名士的“樂”與宋明理學家的“樂”有相通之處,即在對世俗的得失、毀譽、是非、生死的超脫中獲得心靈自由、達到精神愉悅的境界。
但是,朱熹說:“曾子之學,蓋有以見夫人欲盡處天理混然,日用之間隨處發見,故其動靜之際從容如此。”朱子強調學者必須在合乎名教、追求仁義中達到“與道為一”的精神境界,這是宋儒解答名教可樂的最終答案。
(三)相通的性情結構
中國古代的人生哲學有自己的顯著特征,其思想的邏輯起點與最終結論不是人的知識、理性,恰恰是人情,原始儒家在思考社會與人生時,總是以“情”作為思考的起點和最終的目標。
和“情”密切相關的概念是“性”。先秦儒家總是把“情”作為其學說的起點,同時又把“性”作為“情”的內在依據,所以,性與情的關系就被視為一種密切相關的概念。
魏晉名士繼承了先秦儒學,在有關人格依據的探討中,肯定了“情性”是一切人的根本的觀念。正始名士王弼在注解孔子的“興于詩,立于禮,成于樂”時說:“夫喜、懼、哀、樂,民之自然。應感而動,則發乎聲歌。所以陳詩采謠,以知民志風。既見其風,則損益基焉。故因俗立制,以達其禮也。”“情”是一個經驗事實,而“性”則是一種價值取向和理論預設。儒家關注人的喜怒哀樂的“中節”與“不中節”,主張中節之情來之于性,不中節之情來之于物;而道家則更為關注人的情感的真實性,認為只有真實的情感才是來之于人的自然本性,而虛偽的情感則來之于人的外在機心。
魏晉名士的性情學說也體現出儒道兼綜的特色,他們認為“真情”源于人的自然本性,這樣他們通過引進道家自然的學說,從而使先秦儒家性情學說進一步演變成魏晉的性情學說。
從理論形式上來說,宋明理學的性情學說在貫通情與性,特別是以性統情的問題上繼承了魏晉玄學,從而體現玄學與理學之間的學術傳承與邏輯關聯。
當然,宋明儒者更為重視“情”對儒家仁義禮智信的“中節”與“不中節”,其性理已賦予儒家倫理的涵義。所以,宋儒必須對“性”作出新的詮釋,就是將“性”的內涵確定為儒家人倫之理。朱熹指出:“仁、義、禮、智,性也。”并進一步確定了性(也就是儒家倫理)對情的主宰者地位。朱熹說:“性,本體也;其用,情也;心,則統性情、該動靜而為主宰也。”“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以主宰者是理也。”
(四)性與天道相通的共同學理
道德與人生不僅需要現實起點,而且還需要確立終極目的;不僅僅應確立人的內在依據,而且需要確立一個超越的依托,這樣才能為理想人格及其人生境界建立起形而上的終極依據。
在關于性與天道的問題上,魏晉玄學標榜的名士風度與宋明理學所追求的圣賢氣象同樣表現出前后相承的思想脈絡與內在理路。
先秦儒、道兩家對性與天道的關系問題曾作出過一些闡釋。儒道兩家在“性—命”問題上各有卓見和不足,魏晉玄學與宋明理學均須綜合儒道兩家,從而將“性與天道”何以貫通的問題建立在宇宙本體論的基礎之上。
王弼所以主張以性統情的“性其情”的觀點,是因為此“性命”是自然本性,它與“天道”的自然本性在本質上是融通的。在郭象這里,“性”不僅是“情”合理性的內在依據,更重要的是,他認為天地萬物所必須順應的“自然之理”,其實均來自于它的“自然之性”。這樣,“性”與“天道”是一體貫通的。魏晉名士將人性的內涵、特質設定為一種“自然”的特性,又把自然之性歸結為天道自然,從而使人性與天道之間得以貫通,但這種貫通是建立在儒家以情為依據的名教與道家以天道為依據的自然之性相結合基礎之上的。
理學家們以儒家倫理為內涵,將人性與天道貫通起來。二程曾提出“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張載還提出“形而后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他們都是將人性與天道結合起來,使人性獲得了宇宙意義。這一點,朱熹作了十分哲學化的論述:“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于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仁義禮智的倫理準則既是主宰宇宙大化的“天理”,又是主宰人情的“性”,這種性與天道相通的理論為“圣賢氣象”的人格建立起形而上的終極依據。
今天我的主講就到這里,謝謝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