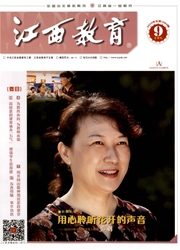監(jiān)獄法的法律地位及價值評估
佚名
[關鍵詞] 監(jiān)獄法,法律地位,價值所在,存在問題
1994 年12月29日,經第八屆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審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監(jiān)獄法》(以下簡稱《監(jiān)獄法》)。至此,歷時8年多的監(jiān)獄立法活動,以《監(jiān)獄法》的出臺作為取得階段性成果的重要標志。毫無疑問,中國第一部監(jiān)獄法典的出臺對中國法制建設有著深遠和重大的意義。正如1995年2月14日召開的全國監(jiān)獄工作會議的報告中所言:“《監(jiān)獄法》的頒布實施,是我國主義法制建設史上的一件大事,是監(jiān)獄史上的里程碑,是一件值得慶賀的盛舉。《監(jiān)獄法》是建國40多年來監(jiān)獄工作成就的結晶,是監(jiān)獄工作經驗的概括和,凝聚著廣大監(jiān)獄干警長期以來懲罰犯罪、改造罪犯的豐富經驗和解放思想、勇于探索、敢于創(chuàng)新的聰明才智,飽含著從事執(zhí)行刑罰和監(jiān)獄工作者的科研成果。《監(jiān)獄法》的實施,標志著我國監(jiān)獄工作進入了新的歷史時期。[1]” 然而《監(jiān)獄法》的出臺并非監(jiān)獄立法的功成名遂,相反,其正表示著我國系統(tǒng)的監(jiān)獄立法之開始。
從1994年到今年,正是《監(jiān)獄法》頒布與實施十周年,這是一個值得慶賀的日子。監(jiān)獄法實施10年以來,為我國建立中國特色的監(jiān)獄法制打下了良好和堅實的基礎,樹立了依法治監(jiān)的監(jiān)獄治理理念,為我國打擊犯罪、懲罰和改造罪犯,保障罪犯人權提供了法律保障。然而,根據(jù)這十年來《監(jiān)獄法》實施的狀況,監(jiān)獄法治所面臨的問題和形勢還是十分嚴峻的。“這些問題既有來自于中國社會文化發(fā)展客觀水平的局限,也有來自于國家刑事立法體系和刑事司法體制方面的制約;既有來自于監(jiān)獄外部社會環(huán)境方面條件的影響,也有來自監(jiān)獄內部自身的因素;既有來自監(jiān)獄立法體制的,也有來自監(jiān)獄法實施機制的;既有人的主觀方面的因素,也有物質的和制度或體制方面的因素。[2]”本文籍《監(jiān)獄法》頒布十周年,對《監(jiān)獄法》的法律地位及其所體現(xiàn)的價值作一評估。
一、《監(jiān)獄法》的法律地位
法認為,某部法律在整個國家法律體系中的地位一般是由該法制定的法律依據(jù)、其本身所具有的性質、及其調整的法律關系與法律調整所決定的。筆者認為《監(jiān)獄法》在我國法律體系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并非刑法、刑事訴訟法的附屬與補充,是我國刑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一)《監(jiān)獄法》具有獨立于《刑法》、《刑事訴訟法》的法律地位
《監(jiān)獄法》第1條開宗明義地講明:“為了正確執(zhí)行刑罰,懲罰和改造罪犯,預防和減少犯罪,根據(jù)憲法,制定本法。”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在中國法律體系中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和最高的法律權威,其他部門法都是由憲法所派生出來的。從《監(jiān)獄法》制定的法律依據(jù)來看是《憲法》,并不是其他法律,與《刑法》和《刑事訴訟法》并沒有法淵上的派生關系,盡管法淵上的不同,不能成為《監(jiān)獄法》獨立于《刑法》、《刑事訴訟法》的充分理由,但是,至少從法淵上排除了《監(jiān)獄法》與《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派生關系;從《監(jiān)獄法》的調整對象來看,其主要調整對象為刑罰執(zhí)行法律關系即行刑法律關系,這種特定的法律關系是監(jiān)獄在行刑過程中,發(fā)生在監(jiān)獄和罪犯之間的懲罰和被懲罰、改造與被改造的社會關系。這與刑法和刑事訴訟法調整的法律關系不同,《刑法》是規(guī)定犯罪與刑罰的法律規(guī)范,其并不調整刑罰的執(zhí)行活動,而《刑事訴訟法》是公、檢、法機關在當事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參加下,依照法律規(guī)定的程序,解決被追訴者刑事責任問題的活動規(guī)范,顯然《監(jiān)獄法》與《刑法》、《刑事訴訟法》各有不同的調整對象;從調整方法上來看,《監(jiān)獄法》與《刑法》、《刑事訴訟法》也不同,《刑法》的調整方法是采用刑罰制裁的方法來調整其保護的社會關系,而對于《監(jiān)獄法》來說刑罰制裁是其執(zhí)行的內容,而并非其調整方法;從法的性質和任務來看,《刑法》是規(guī)定刑罰的法,《刑事訴訟法》是確定刑罰的法,《監(jiān)獄法》是執(zhí)行刑罰的法,各具有不同的性質和任務。《監(jiān)獄法》具有獨立的法律地位,并不是刑法、刑事訴訟法的附屬與補充。
(二)《監(jiān)獄法》不是獨立的法律部門
有人認為:“監(jiān)獄法具有基本部門法律的屬性和特點。它與《刑法》、《刑事訴訟法》共同構成刑事法律的三個基本組成部分。三者相互銜接、相互支持,共同構筑我國刑事法律的基本框架,并呈”三足鼎立“之勢[3].”其實這種觀點有待商榷,現(xiàn)行《監(jiān)獄法》很難成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所謂法律部門,又稱部門法,是根據(jù)一定的標準和原則劃定調整同一類社會關系的法律規(guī)范的總稱。法律部門離不開成文的規(guī)范性法律文件,但二者并不是一個概念。并非所有的規(guī)范性法律文件都能成為部門法。劃分法律部門所依據(jù)的標準一般認為包括法律的調整對象和法律的調整方法,同時還必須遵守這樣幾個原則:粗細恰當原則、多寡合適原則、主題定類原則、邏輯與實用兼顧的原則。[4]在整個行刑法律體系中,《監(jiān)獄法》僅僅調整部分行刑法律關系,即對自由刑的行刑法律關系,其他具有同一性質的法律關系比如說拘役、罰金、管制和余刑在一年以下的有期徒刑等行刑法律關系并不在《監(jiān)獄法》的調整范圍,一個完整的法律部門應該能夠概括對同一法律性質的法律關系的調整,但從《監(jiān)獄法》所調整的法律關系來看,其并沒有調整全部的行刑法律關系,其只調整絕大部分的自由刑的行刑法律關系。很顯然《監(jiān)獄法》很難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當然,“從監(jiān)獄法律所具有的行刑法的實際意義來考察,確保刑罰實施和實現(xiàn)的行刑法,應當成為與刑事實體法和刑事程序法相同的國家基本部門法的地位,這是行刑地位和作用日益提高的客觀現(xiàn)實的反映和要求,也是刑法改革日益重視刑罰效益和行刑效率的反映和要求[5]”。刑罰的發(fā)展經歷了由生命刑、身體刑到流放刑直到當今以自由刑為主的發(fā)展形態(tài),刑罰的實際效益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因而行刑也受到了越來越多的關注,刑罰執(zhí)行日趨科學、民主、人道、平緩和謙抑,特別是在當今世界刑事司法領域,“非犯罪化、非刑罰化、非監(jiān)禁化”的行刑趨勢已經成為刑罰執(zhí)行的主題,把以《監(jiān)獄法》為主體的刑事執(zhí)行法律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這是與國際行刑理念相銜接的必然需求,也是真正實現(xiàn)懲罰和改造罪犯,預防和減少犯罪的立法目的的客觀需要。
(三)《監(jiān)獄法》是我國刑事法律體系的重要組成部分
刑事法律體系是規(guī)定犯罪與刑罰的知識體系,“犯罪”和“刑罰”是刑事法永恒的主題。二者具有天然的聯(lián)系,犯罪是刑罰的必然前提,刑罰是犯罪的法定后果,是整個刑事法律體系的中心內容。刑事法最根本的目的或作用是通過制刑、求刑、量刑、行刑等環(huán)節(jié),發(fā)揮刑罰對罪犯的懲罰、遏制、改造等功能,從而實現(xiàn)對犯罪的一般預防與特殊預防,最終達到減少和消除犯罪的目的。
有的論者認為,《監(jiān)獄法》調整的是監(jiān)獄的刑事執(zhí)行活動,監(jiān)獄由司法部即司法行政機關領導,因此,監(jiān)獄是行政機關,《監(jiān)獄法》是行政法的范疇,筆者對于這種觀點并不認同。一般來說法的性質主要由其調整對象和調整方法來決定,不受其實施機關或執(zhí)行機關的管理領導體制的影響。就《監(jiān)獄法》而言,監(jiān)獄執(zhí)行刑事判決,行使刑罰執(zhí)行權的刑事職能并沒有因為領導體制而改變,在活動的性質上仍然是一種國家刑事司法活動,而不是政府行政行為[6].比如說公安機關是典型的行政機關,但其在刑事訴訟過程中行使偵查權的刑事職能并沒有因為其管理領導體制而發(fā)生改變,否則規(guī)定公安機關行使偵查權的《刑事訴訟法》豈不是變成了行政訴訟法。總之,不論監(jiān)獄機關的領導體制如何,也不會改變《監(jiān)獄法》為刑事執(zhí)行法的法律性質。
按照我國《刑法》的規(guī)定,刑罰有五種主刑、三種附加刑。“自由刑判決在實踐中占審判機關整個刑事判決數(shù)量的90%以上。[7]”由此可見,徒刑在我國的刑罰體系中居于主導地位,是我國主要的刑罰方法。根據(jù)《監(jiān)獄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規(guī)定:余刑在一年以上的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緩期二年執(zhí)行的刑罰由監(jiān)獄執(zhí)行。由此可以看出,監(jiān)獄是我國主要的刑事執(zhí)行機關,在刑罰實現(xiàn)活動的過程中,監(jiān)獄發(fā)揮了主體性的作用。監(jiān)獄作為自由刑的執(zhí)行場所,在以自由刑為中心的刑罰成為了的刑罰體系的物化象征。“刑罰的動態(tài)運作機制告訴我們:在當今以自由刑為主的刑罰制度下,監(jiān)獄作為刑罰的執(zhí)行機構,作為自由刑的執(zhí)行場所,其行刑的功能發(fā)揮使其在刑罰機制運作中扮演一個十分重要的角色。行刑機制的運作與刑法、刑罰的發(fā)展從理論到實踐都處于一種深深互動關系之中。[8]”
國家運用刑罰治理犯罪,是通過刑罰權的分配和運行得以實現(xiàn)的。刑罰權一般可分為四項權能[9],即制刑權、求刑權、用刑權(又稱量刑權)和行刑權。制刑權,即國家立法機關創(chuàng)設刑罰的權力,包括設立、變更、廢止刑罰的權力;求刑權又稱追訟權或起訴權,是指請求對犯罪嫌疑人判處刑罰的權力;用刑權即對犯罪嫌疑人決定適用刑罰的權力;行刑權即對罪犯執(zhí)行刑罰的權力,是整個刑罰體系的最終環(huán)節(jié)。
行刑權是一項獨立的刑罰權能,它是指以監(jiān)獄為代表的刑罰執(zhí)行機關對犯罪分子執(zhí)行刑罰的刑事司法活動,是實現(xiàn)刑罰權的最終落腳點和關鍵所在。正如美國著名法學家戈爾丁所言:“對于一個普通公民來說,……他基本上是根據(jù)法律的刑事部門來認識法律的。在這一部門中,法律與法律實施似乎無可擺脫地糾纏在一起。法律的象征意義與其說是立法者,不如說是警官,后者的任務是預防犯罪、偵破案件和逮捕犯罪分子。然而法律的實施過程并不僅限于此,它的頂點是在審訊和定罪的復雜過程之后對犯罪所實施的刑罰。[10]”盡管這一論斷是針對整個刑事司法而言,但同樣說明了以監(jiān)獄為代表的行刑機關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