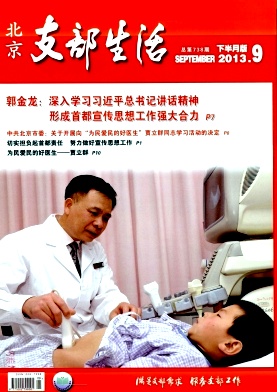漢代文學的趨同與模擬現象
未知
一、漢代文學中趨同模擬作品的繼承和發展
(一)漢賦的趨同模擬現象
西漢初年,漢代的統治者大多是楚人,因此對于“楚聲”十分愛好,他們創作了大量的楚歌,如劉邦的《大風歌》、戚夫人的《舂歌》、劉章的《耕田歌》等,形成了楚歌發展的一個新階段。據《漢書·藝文志》所載,西漢樂府所演奏的樂章,除漢高祖唐山夫人以“楚聲”為基礎創立的《安世房中歌》和武帝時的《郊祀歌》外,還有遍及黃河、長江兩大流域的各地民歌五十首。統治者的愛好,對當時的時代思潮也起了一定的引領作用。
在儒家思想尚未占據統治地位的時期,辭賦繼承楚辭的傳統,內容以抒發作者的政治見解和身世感慨為主。特別是以屈原的《離騷》為代表的騷體賦得到了迅猛的發展,出現了一大批模擬屈原創作的作品。如淮南小山的《招隱士》,其氣象、格調逼近屈宋,為漢代辭賦的佼佼者。賈誼的《吊屈原賦》和《服鳥鳥賦》,滲透著個人的身世感嘆,抒發了自己的政治抱負,特別是后者,在體制和寫法上,因顯示了由楚辭到漢賦過渡的痕跡,而被稱為“騷體賦”。還有許多作家則主要從藝術方面來學習屈原,他們仰慕屈原賦藝術上的“可與日月爭光”的成就,于是進行模擬。如賈誼的《惜誓》、王逸的《九思》等。對于這種模擬現象,宋代的朱熹批評到:“雖為騷體,然起詞氣平緩,意不深切,若無所疾痛而強為呻吟者。”但是這并不代表它們就無可取之處,賈誼的《吊屈原賦》在思想內涵和藝術特色方面就都是上乘之作。
漢賦發展到大賦階段,模擬現象則主要體現在了同代文人的作品中。據《史記·司馬相如傳》載“上讀《子虛賦》而善之,曰‘朕獨不得與此人同時哉?’”基于這種贊揚與認同,文壇上就掀起了一股強大的模擬之風。如楊雄,他對司馬相如極為欣賞,曾評說司馬相如的《上林賦》曰:“長卿賦不似從人間來,其神化所至也。”于是,他寫的《羽獵賦》《長楊賦》《甘泉賦》《河東賦》等都是學習的司馬相如的《子虛賦》和《上林賦》。雖然他模擬古人,其文學理論也主張要擬古,但是由于他知識淵博,又不受模式的拘泥,所以有自己的創建。而且他的這些模擬之作實際上也促進了文學及文學觀念的創新與發展,文學發展也只有在競爭中才能進步。
(二)散文的趨同與模擬現象
提到兩漢的散文,就不得不說《史記》和《漢書》,它們代表了史傳文學發展的高峰,其中仍不乏有模擬的現象。司馬遷著《史記》繼承了屈原的“發憤以抒情”而提出 “發憤著書”說。他把文學創作視為抒發抑郁之情的一種方式。魯迅稱之為“史家之絕唱,無韻之《離騷》”。稱之為“絕唱”,因為在當時“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情況下,作者能“不拘于史法,不囿于字句”(魯迅語),廣據見聞,獨抒己見,敢于直言,而成為“實錄”。稱之為《離騷》,因為作者更多的看到了歷史上的不公,人世間的不平,于是憤世嫉俗,憂思甚廣,不僅是個人的牢騷。可見,漢代的散文和楚辭也存在著趨同現象。后來班固作《漢書》以儒家正統思想為原則敘述了漢代王朝的發展史,同樣記敘了歷史的真實畫面,而且以史家的“實錄”精神為指導。其中的《司馬遷傳》還幾乎全部采用司馬遷的觀點,《武帝本紀》和《郊祀志》的觀點也與司馬遷一致。在體例上,《漢書》也繼承了《史記》的體例,并且使之更加完善。因此,成為后來人效仿的榜樣,后代史書的修訂基本上也以《史記》和《漢書》為準。
(三)文學對儒家命運論思想的趨同
漢朝建立初期,惠帝廢除了秦朝的挾書律,“大收篇籍,廣開獻書之路”(《漢書·藝文志》),加之戰國以來百家之學的影響,各地侯王也仿效戰國諸公子,招致各種人才于自己的門下。文人的命運就正如楊雄所說:“當涂者入青云,失路者委溝渠,旦握權則為卿相,夕失勢則為匹夫。”這種群體遭遇使他們對自身命運進行不斷的思索。董仲舒的《士不遇賦》就首倡此風。董仲舒提出 “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策略,確立了儒家的正統地位。但是,就是這樣一個對漢代王朝做出重要貢獻的人,最后也因寫災異問題來勸諫漢武帝而差點喪命。這對他自身和漢代的整個知識階層不能不說是一個打擊。司馬遷的《悲士不遇賦》與董仲舒的悲嘆并無二致,都是以“遇”和“不遇”為主題,悲嘆自己的生不逢時。到了西漢后期,文人對命運的感嘆更是加深了,正如楊雄所說“遇不遇命也”(《漢書·楊雄傳》)。對于文人地位變化及其原因的分析在東方朔的《答客難》和揚雄的《解嘲》中都有具體而全面的闡發,揭示了漢代文人命運的變化以及其內在的深層原因。這一類主題趨同的作品實際顯現的是同一時代氛圍作用于不同文人的結果。
二、 漢代文學的趨同與模擬現象產生的原因
(一)時代風貌對漢代文學趨同現象的影響
漢代文學是呈現多元化的發展趨勢的,但在這多元化的發展中也存在著趨同現象。漢朝的經濟繁榮,國力強盛,疆域廣袤,使那個時代的作家充滿了豪邁情懷。
反映在文學上就是:古往今來、天上人間的萬事萬物都要置于自己的關照之下,加以藝術的再現。司馬相如說過:“賦家之心,苞括宇宙,總攬人物。”(《西京雜記》卷二) 司馬遷稱他寫《史記》的宗旨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安書》)。一個是辭賦大家,一個是傳記巨匠,他們處于文學創作的不同領域,卻不約而同地提出了基本相同的主張,對作品都追求廣大的容量、恢弘的氣勢,欣賞那種巨麗之美。在大賦中,凡是能夠寫入作品的事情,都要囊括包舉,細大無遺。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創造出了與大漢帝國氣象一致的博大壯闊的體制,完成了謳歌時代的責任,成為海內漢賦第一人。漢代文學的巨麗之美,體現的是對大一統帝國輝煌業績的充分肯定,它的表現對象、領域和范圍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廣度。這種“以大為美”的審美要求是和漢代的時代特征分不開的。
(二)經學思想對漢代文學的影響
漢代的官學和私學都以講授儒家經典——五經為主,漢代經學的繁瑣解讀習尚也就形成,以致出現“一經說至百萬言”的事實,解釋經書上的五個字要用二三萬字。更有甚者,秦近軍解釋《尚書·堯典》標題兩字之義,竟至十萬言。他們在語言文字的運用上都是不厭其繁,多多益善,鋪天蓋地而來。這種繁瑣的風氣體現在文學上就形成了漢賦在表現形式方面的趨同現象。
兩漢文學思潮也很少超越經學的樊籬,而且很大程度上是經學的延伸和具體化,許多作家兼有經師和文人的雙重身份。《毛詩序》闡述的基本觀點,成為漢代文學思潮的靈魂和主調。漢代文學批評也主要以《毛詩序》的上述觀點為尺度,對各種文學現象作出判斷。即使像王充那樣富有批判精神的思想家,在評論各種文學現象的時候也經常以儒家經典為依據。可見,漢代經學對漢代文學思潮有很深的影響。
在傳授方式上,漢代經學重承襲,強調傳授先師之言。不依先師之言而斷以己意,就會被視為輕侮道術,受到學界的譴責。漢代文學情況相同,許多文人不但模擬前代的作品,而且同時代的文人也相互模仿。流行于漢代的大賦、騷體賦、七體、九體、體辭等,都留下了前后蹈襲的痕跡。
(三)儒家致用思想的影響
隨著中央集權的日益加強,在新儒學的掩蓋之下,漢武帝實行多欲政治,愛聽頌揚之詞,漢代的文人滿懷積極的入世之心。他們一方面要實現自己的理想,一方面又要避免殺身之禍,因而許多漢賦的寫作目的就是供上層統治階級閱讀,為他們服務。如司馬相如的《子虛賦》、《上林賦》是寫給漢武帝看的;楊雄的《羽獵賦》、《甘泉賦》是寫給漢成帝看的;班固的《兩都賦》同樣也是為帝王服務的。這些作品都有相同的寫作目的,雖然也有諷諫的意圖,但都只是委婉曲折地讓讀者自己去體會。此外,還有一些文人,為了實現自己的人生理想,忍辱負重,赴湯蹈火,甚至不惜犧牲自己的生命。他們胸襟開闊、思想恢弘,具有高度的時代責任感和歷史使命感。《左傳》記載記載穆叔的話說:“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這就指出了文人們實現自身價值的三種途徑。但是,這三種途徑根本上還是與他們輔佐君土實現安邦定國的理想有關。
總的來說, 漢代文學上趨同現象的出現,雖然在一定程度上造成繁瑣、重復的文風,不利于文學的創新。但是這種趨同現象,也在競爭中促進了文學技巧的進一步發展,使作家們對某些文學題材的性質有了一定的共同認知,積累了一定的文學經驗。在這種文學趨同現象經驗的積累下,出現了一大批的文學理論著作,為后世文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參考文獻:
[1]朱熹 《楚辭集注·楚辭辨證》上[M]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2]周勛初 《王充與兩漢文風》見于《古代文學理論研究》第二輯[M]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出版 第122~140頁
[3]班固 《漢書·揚雄傳》[M] 中華書局 2002
[4]尚學鋒 《中國古典文學接受史》[M]濟南教育出版社 2001
[5]郭預衡 《歷代散文叢談》[M]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
[6]袁行霈(主編)《中國文學史》第二版 第一卷[M]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7]劉黎明《中國文學·先秦兩漢卷》[M]四川出版社集團·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