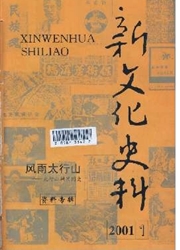關于現代漢語思維的中國當代文學
賀紹俊
了一次“新寫實”的潮流。“新寫實”強調零度情感,強調原生態。新時期文學的30年,現實主義基本上仍是文學的主潮。但現實主義經歷了一場自我解放的過程,在這之前,現實主義的意義闡釋達到了偏執的程度,于是現實主義敘述受到偏執意義的嚴重束縛。新時期文學從撥亂反正開始,撥亂反正的根本目的就是要改變意義偏執的狀況,但它并沒有改變現實主義敘述與意義之間的緊張關系。在后來的發展中,現實主義經歷了疏離意義、放逐意義、重建意義的螺旋往復的過程。中國在20世紀90年代以來社會大轉型帶來中國當代“新的現實”,則是重建意義的必要條件。“新的現實”是當代文學的重要資源,“新的現實”變幻莫測的生活萬象和前所未有的生活經驗對于當代作家來說確實也是充滿誘惑力的,但由此在對“新的現實”的敘述中也形成了越來越多的寫作模式和小說樣式。20世紀80年代,由知識分子政治精英話語建立起來的新時期文學撥亂反正宏大敘事與現實主義度過了一段蜜月期,但90年代的中國社會逐漸給市場化加溫,經濟幾乎成為社會的主宰,市場經濟的利益原則和自由競爭原則誘使文學朝著物質主義和欲望化的方向發展,這為現實主義與撥亂反正宏大敘事的親密關系的松動乃至瓦解創造了最合適的條件。但另一方面,現實主義擺脫意義約束之后,便朝著形而下的方向沉淪。 三當代文學的組織性和合目的性 中國當代文學是革命勝利者的文學,革命勝利者對它具有當然的領導權。中國革命理論中還有非常重要的一點,就是把文學看成是革命的武器和工具,毛澤東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指出,文藝應該是。整個革命機器的一個組成部分”。1949年初北平和平解放后,黨中央就召集一批文學藝術界名人在北平商議成立中華全國文藝工作者聯合會,即以后的中國文聯。1949年6月30日,第一次中華全國文學藝術工作者代表大會在北平正式召開,7月23日,正式成立中華全國文學工作者協會(簡稱全國文協,即中國作家協會的前身),全國文協的領導成員為:主席茅盾,副主席丁玲、柯仲平。丁玲為文協黨組組長,馮雪峰為副組長。全國文協在1953年召開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更名為“中國作家協會”,大會通過的章程規定:“中國作家協會是以自己的創作活動和批評活動積極地參加中國人民的革命斗爭和建設事業的中國作家和批評家的自愿組織。”但實際上它是國家領導和組織文學事業的特別機構,理論上說是群眾團體,實際上是被納入到國家正式編制中的執行國家文化政策的、具有行政性質的機構,其工作列人到國家決策計劃之中,是有國家正式編制和相應的政治待遇的。作家協會是社會主義國家的特殊產物,它不完全等同于其它國家內部的作家協會或作家同盟組織。在20世紀階級斗爭對抗的時代,社會主義國家都有相似的作家協會機構,隨著蘇聯東歐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解體,這些國家的作家協會也形存實亡,或者性質發生根本的變化。社會主義國家對待文學的態度,反映了在階級對壘分明的時代,無產階級要從資產階級手中奪回文化領導權的愿望。這一愿望對于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來說顯得更加迫切,因為中國的無產階級政黨是在東方專制文化土壤上開展的革命,缺乏資產階級文明的廣泛傳播和精英階層的集結,無產階級政黨以喚醒民眾的方式,將啟蒙與革命合為一體,這一切決定了當代文學的組織性和合目的性。如全國文協(即中國作家協會前身)成立不久,便創辦了文學刊物《人民文學》,時任主編的茅盾在創刊詞中是這樣闡述刊物的編輯方針的:“作為全國文協的機關刊物,本刊的編輯方針當然要遵循全國文協章程中所規定的我們的集團的任務。這一任務就是這樣的:一、積極參加人民解放斗爭和新民主主義國家的建設,通過各種文學形式,反映新中國的成長,表現和贊揚人民大眾在革命斗爭和生產建設中的偉大業績,創造富有思想內容和藝術價值,為人民大眾所喜聞樂見的人民文學,以發揮其教育人民的偉大效能。二、肅清為帝國主義者、封建階級、官僚資產階級服務的反動的文學及其在新文學中的影響,改革在人民中間流行的舊文學,使之為新民主主義國家服務,批判地接受中國的和世界的文學遺產,特別要繼承和發展中國人民的優良的文學傳統。三、積極幫助并指導全國各地區群眾文學活動,使新的文學在工廠、農村、部隊中更普遍更深入的開展,并培養群眾中新的文學力量。四、開展國內各少數民族的文學運動,使新民主主義的內容與各少數民族的文學形式相結合,各民族間互相交流經驗,以促進新中國多方面的發展。五、加強革命理論的學習,組織有關文學問題的研究與討論,建設科學的文學理論與文學批評。六、加強中國與世界各國人民的文學的交流,發揚革命的愛國主義與國際主義的精神,參加以蘇聯為首的世界人民爭取持久和平與人民民主的運動。”這一編輯方針更像是在完成一項政治思想任務,而這恰恰說明,當代文學從一開始就是被納入到國家的社會主義政治和經濟建設的宏偉規劃之中的,具有明確的政治目的。 但成立中國作家協會等相應的文學組織,只是國家全方位領導文學的方式之一,國家領導文學的方式是多方面的,還表現在國家文化政策的制定,文學制度、文學體制和文學生產方式的確立,等等。總之,國家通過多種方式使其領導和組織文學事業的意圖得以實現。這一切,給文學創作帶來深遠的影響,因此,要更為準確、全面地描述當代文學史,就不能忽略對文學制度的考察。不少學者已經注意到當代文學中的文學制度和文學體制問題,并將其引人到文學史的寫作中。洪子誠的《中國當代文學史》為我們率先做出了一個良好的樣板,他在這部著作中注重從文學制度入手去分析一些文學現象的成因,提出了許多新的見解。王本朝的《中國現代文學制度研究》則是國內第一本系統研究中國現當代文學史以來文學制度的專著。他在這部專著中闡述了文學制度的現代性意義。 相對于政治制度、經濟制度等社會制度,文學制度更為隱性,更多地通過一種社會習慣和精神指令加以實現。不同的社會形態具有不同的文學制度,文學制度是一個社會使文學生產獲得良性循環、文學能被廣大社會成員接納的基本保證。中國當代文學的文學制度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在于它是執政者對文學有著明確的政治要求,其文學制度是為了最大化地保證其政治要求的實現,通過相應的文學制度,將文學納入到政治目標中,這使得當代文學從一開始就具有明顯的組織性和合目的性。這樣一種文學制度從根本上說是與文學的自由精神相沖突的,因此文學制度與文學創作之間的內在矛盾就十分的尖銳,這導致了文學制度和文學創作雙方的相互妥協和調整。盡管當代文學制度最初明顯表現出與文學自由精神的沖突,不利于發揮文學的積極性。但我們在對待這一歷史現象時,不應該輕易地從否定文學制度的角度來總結歷史經驗,菲合爾·科勒克說過:“無一社會制度允許充分的藝術自由。每個社會制度都要求作家嚴守一定的界限”,“社會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過以下途徑:期待、希望和歡迎一類創作,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