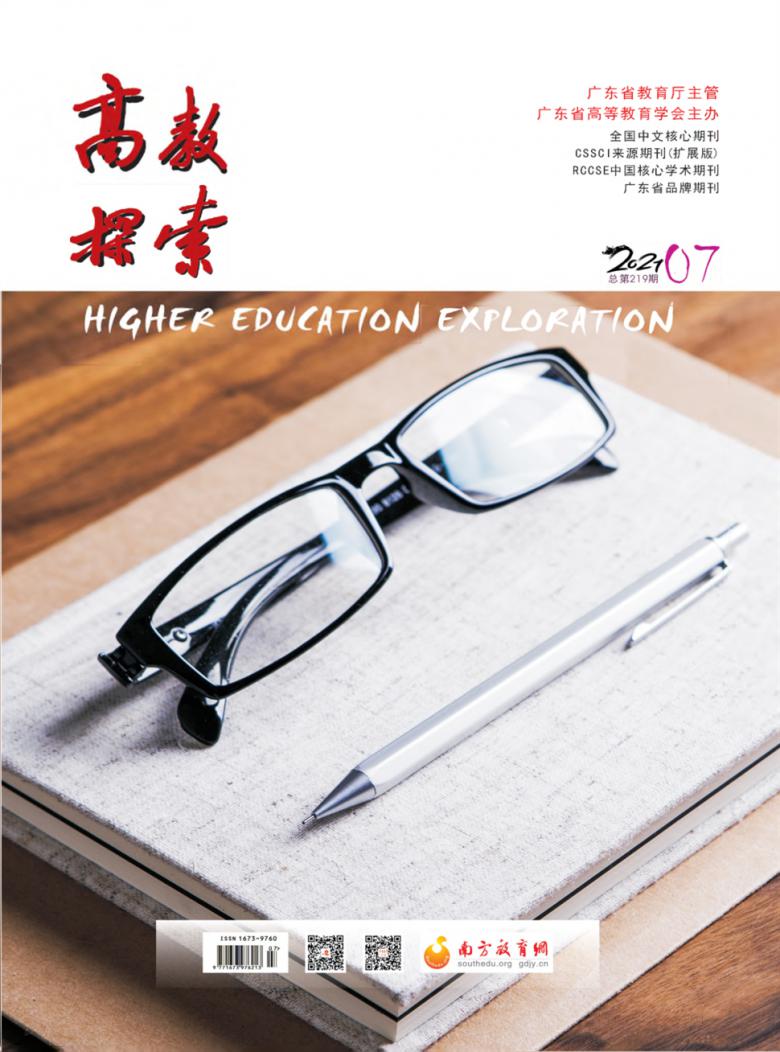關于魯迅文學創作對書畫技法的借鑒
朱鋒
論文摘要:魯迅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位拓荒者。在其文學創作過程中,自覺不自覺地履行了他“拿來主義”的主張,憑著自身深厚的藝術功力,融入書法藝術中的飛白手法,有意在作品中留下一點空白,使主題或形象更加突出。他還借鑒繪畫藝術中的黑白木刻技法和白描手法,使作品形象入木三分,形神兼備。這,自然得益于作家與書畫等多種藝術形式的藝術淵源。
論文關鍵詞:飛白;木刻;白描;藝術審美;藝術淵源
魯迅先生確實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位巨匠。早在1923年,茅盾就在自己所寫的《讀(吶喊)》中評論說:“在中國新文壇上,魯迅君是創造新形式的先鋒。《吶喊》里的十多篇小說,幾乎一篇有一篇的新形式,而這些新形式莫不給青年作者以極大的影響,必然有許多人們上去試驗。”(其實,不僅是小說,就其散文雜文等各種體裁的作品來看,魯迅先生巧妙地“拿來”,借書畫等藝術技法,左右逢源,鑄造自己的文學作品,為現代文學園地增添了朵朵奇葩。本文僅就其文學作品中借用書法、繪畫表現技法的特征,予以粗淺評析。
一、對書法藝術中飛白手法的借鑒
出于表達的需要,魯迅先生常常運用以虛襯實的語言,以達到“情到深處于無聲”的藝術效果,這種語言風格,人們稱之為“飛白”藝術。“飛白”本來是書法用語,指筆畫中露出一絲絲的白地,表面看好像是一種缺憾,但它使書寫顯現出蒼勁渾樸的藝術效果,使作品增加情趣,達到豐富畫面的視覺效果。文學作為藝術的另一種表現形式,有其相通的運用形式:描述或刻畫形象時,運用“一絲絲的白地”式的語言,使人產生意味深長的美感;它常因作者情感、社會背景或人物性格表達的需要,比實際描述或直接抒情更能突出主題的要義,甚至有“此時無聲勝有聲”的藝術效果。魯迅運用“飛白”式語言,尤為頻繁。
如《祝福》,文章對魯四爺家中的擺設作了一番細致描寫之后,突然一句“無論如何,我明天決計要走了”,兩個似乎毫不相干的語句聯在一起,留給讀者一塊空間和疑問:剛剛回來,為什么就要走呢?仔細對比分析才會發現,這何嘗不是“我”對此環境的厭惡之情而做出的無可奈何的選擇呢?在《為了忘卻的記念》中,當作者得到柔石等人遇害的確切消息后,用了獨立成段的“原來如此……”,省略號留下一個“令人不解”的空白,其中又凝結著作者多么濃烈的愛和強烈的恨!作者多是在“飛白”的語言中,表達出更加強烈的愛憎。
文學家在刻畫人物的復雜個性時,一般是通過人物的言行、肖像、心理的多種描寫來表現的,而魯迅,不僅如此,還巧妙運用語言本身所具有的“空間”來揭示人物性格。即運用飛白手法,襯托人物復雜的性格。《為了忘卻的紀念》寫馮鏗女士時,后面有一個“她的體質是弱的,也并不美麗”結句,有些同學奇怪這句為何不插入前文段落中。這段獨立,是抑是貶還是惡?只有填充此句的“空白”內容,改為“雖然她的體質是弱的,也并不美麗,但她的意志(精神)……”的句式時,其中的含意就迎刃而解,可見作者此句強調的,并非是她的身體、相貌,而正是她不易被人注意到的精神和毅力。作者不直接描寫她的性格,一方面是對她了解不夠,更重要的是給讀者留下了一個想象的空間。《阿Q正傳》第一章重筆寫一個自高自大卻又能自輕自賤的阿Q,末段突有一句“他睡著了”,看似閑著,卻是神筆,一個愚蠢、麻木的小人物就這樣又過去了一天。
此外,這種“飛白”藝術還可以節省筆墨并且使語意綿長。細細品味一下語句,可以深味其中的效果。《燈下漫筆》:“中國人向來就沒有爭到過‘人’的價格,至多不過是奴隸,到現在還如此。
《紀念劉和珍君》:“時間永是流失,街市依舊太平,有限的幾個生命,在中國是不算什么的”。這些語句語意空間很大,表達形式言簡意賅。“直露”中的“飛白”確實體現了一個文學家的完美的語言風格。
二、對繪畫技法的借鑒
在贊譽魯迅藝術手法高明時,人們常斷言他是一位高明的畫家。追根求源,這個高明的畫家在以文字為筆墨描繪形象時,是以什么畫種,什么方式來塑造形象的呢?我們只要對繪畫稍加了解就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魯迅是一位黑白木刻大師,那些人木三分的小說形象,就是他以犀利的文筆為雕刻刀刻畫出來的黑白木刻作品。
1.黑白木刻藝術手法
魯迅小說中的藝術形象分明地帶著濃郁的黑白木刻的神韻。其小說,黑白對比分明,線條清晰有力,注重勾勒而淡于敷彩——這正是黑白木刻的造型效果。這一顯著特色,構成了魯迅小說形象特有的風格。
繪畫藝術最基本的語言是色彩和線條。但黑白木刻在色彩方面,拋開了一切有彩色,只選擇最單純的黑白二色,利用黑與白強烈的明暗對比襯托或黑與白的協調過渡,來暗示大千世界的繽紛色彩;在線條的運用方面,則以刀為筆刻出的富有金石之味的各種粗線、細線、直線、曲線來勾勒形象,不輕浮,不單薄,骨法用筆,力透紙背,建構既抽象又具有表現力的空間。這種表現方式,以簡潔、概括、富有張力的形象給人強烈的視覺沖擊力,啟迪人們無窮的回味與想象。正基于此,魯迅的小說形象與黑白木刻有著異曲同工之美。用“刻畫”二字解說魯迅對小說形象的塑造,可謂恰如其分。
《狂人日記》《阿Q正傳》《祝福》《風波》《傷逝》《藥》等作品最為人稱道,其中人物形象深入人心。可以說,這些不可磨滅的藝術形象以及他們活動的背景,幾乎全由黑白二色構成。《狂人日記》通過“狂人”的獨特感知,描繪出一幅“吃人”社會的時代畫面。小說一開頭便是“今天晚上很好的月光”,這是令人叫絕的一筆,現實世界的一切在很好的月光籠罩之下消褪了原有的色彩,變成了黑、白以及黑白調和而成的灰色。作者借助月光搶先渲染了一種慘淡詭秘的氛圍,這是狂人特有的視覺心理感受,也是作者基于自己對那個世界深切的感知和理解。整篇小說沉浸在這樣一種色調之中:基調是黑,“黑漆漆的,不知是日是夜”,“屋里面全是黑沉沉的”,活動于其中的人物的臉色也一概是青的、鐵青的,真是黑暗到無以復加的地步。一片漆黑的基調之上又醒目地跳著白,除了有使黑暗更加陰晦凄厲的慘淡月光,還有“白厲厲地排著”的“吃人”的家伙的牙齒,“白而且硬”的黃魚的眼睛。漆黑的背景上,這些白的面積極小,卻因對比強烈而特別的刺激,令人觸目驚心。黑白的強烈對比,深刻揭示出黑暗社會的吃人本質。 除了色彩,魯迅先生還很懂得線的藝術魅力。心隨筆運,線隨墨出。在他的小說創作中鮮明地顯現著對線的表現力的把握與運用。他筆下的形象,如同簡筆勾勒后又用刀刻出來似的,勾勒準確傳神,刀法凝重老到。“阿Q赤著膊,懶洋洋的瘦伶仃的”,“在他頭皮上,頗有幾處不知起于何時的癩瘡疤”,還有常常被人揪住的“黃辮子”,就這么極少的幾筆,阿Q的基本輪廓就地凸現出來。阿Q“中興”回到未莊,“腰間還掛著一個大褡褳,沉甸甸的將褲帶墜成了很彎很彎的弧線”,這條弧線使阿Q的洋洋得意之態躍然紙上。其實,單單就魯迅先生給阿Q起的名字已令人叫絕了,一個橢圓形與一條小曲線構成的Q,不正是人物最傳神的寫照嗎?用藝術審美的眼光來看,像木刻刀中的圓口刀“擰”了一下的效果。
2.國畫里的白描手法
白描,屬于中國畫的一種技巧。這種畫法,不用色彩的烘染,只用黑線勾描物象。在文學創作上,白描指不加渲染、烘托,不用華麗辭藻,而以最經濟、最省儉的筆墨,勾勒出鮮明生動的形象。具體說來,就是抓住被描寫對象的主要特征,寥寥幾筆,形神逼肖。魯迅談及小說創作時,認為應該用“白描”的手法。在其小說創作中,他也大膽進行嘗試。《故鄉》開頭:“我冒了嚴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別了二十余年的故鄉去。/時候既然是深冬,漸近故鄉時,天氣又陰晦了,冷風吹進船艙中,從篷隙向外一望,蒼黃的天底下,遠近橫著幾個蕭索的荒村,沒有一些活氣。我的心禁不住悲涼起來了。/啊!這不是我二十年來時時記得的故鄉?”這里的白描,寥寥數語,將故鄉深冬陰晦天氣籠罩下的原野盡收筆下,字里行間又流露了作者內心的深沉的悲涼情緒。
短篇小說《藥》中,環境描寫也運用了白描。夏四奶奶、華大媽祭墳一段,不僅準確地勾畫出環境的凄涼、晦暗,而且用紅白相間的花環象征了先驅者不屈不撓的斗志,顯示出凄涼情景中的一束亮色。尤其最后一句l“他們走不上二三十步遠,忽聽得背后‘啞’的一聲大叫;兩個人都竦然的回過頭,只見那烏鴉張開兩翅,一挫身,直向著遠處的天空,箭也似的飛去了。”這一句用白描手法,勾畫出一只“箭也似的”飛向“遠處天空”的烏鴉,給人一種桀驁不馴、大膽抗爭的印象。“正如傳神的寫意圖,并不細畫須眉,并不寫上名字,不過寥寥數筆而神情畢肖。”這正是白描的魅力!
三、魯迅的書畫藝術淵源
按照常理,一個作家能夠諳熟并借鑒繪畫的技巧舞文弄墨,看起來好像是不可思議的。但真正全面地了解了魯迅,就不會再大驚小怪。魯迅原本就是一位頗有造詣的美術鑒賞家、收藏家、理論家,而且自己也能畫上幾筆。最早進入這個敏感的孩子的視野的繪畫作品,是在中國有著悠久傳統的木版年畫,這些年畫給了魯迅難以磨滅的印象,以至成年以后他還清晰地記得6歲時窗前貼著的“花紙”上的內容。后來,木版書籍的插圖,又引起他濃厚的興趣。當保姆找到讓他心里癢癢了好久的繪圖本《山海經》時,他激動得“似乎遇著了一個霹靂,全身都震悚起來”。對版畫的熱愛和收藏,幾乎貫穿了他的一生。中國的版畫,魯迅和鄭振鐸出版印行了《北平箋譜》、《十竹齋箋譜》等。他熱心倡導版畫的同時,還研究過漢代畫像。許壽裳說魯迅“搜集并研究漢魏六朝石刻,不但注意其文字,而且研究其畫像和圖案,是舊時代考據家鑒賞家所未曾著手的。”足見其藝術追求之廣、造詣之深。
作為藝術家,文學與藝術的共通,使他一只禿筆在握,如畫筆一樣揮灑自如,涂抹心中的色彩和情感,這當然也是順理成章水到渠成的事。而作為中國現代白話小說的拓荒者,能夠從借鑒西方小說形式,到借鑒詩歌、散文、音樂、美術、戲劇的藝術經驗創作小說,并試圖將它們熔為一爐,魯迅先生無羈的創造力和想象力是令人嘆而觀止的。因為他自身有著一種動力,有著一種使命感。因為他說過:“沒有沖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
魯迅先生作品中的“拿來”——對書畫藝術手法的借鑒,絕不只是個技巧問題,重要的是,它來自作者對社會生活深切地體驗,對人物性格特征準確地把握。借助于書畫等方面的藝術才華,才順理成章地表達出來、宣泄出來。作家神圣的社會責任感,厚實的藝術功力,使得作品行文如繪,一語通透靈魂,帶來神情活現、動人心魄的藝術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