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tái)灣現(xiàn)代詩西方用典的美學(xué)內(nèi)涵透視
邱冬梅
關(guān)鍵詞:臺(tái)灣現(xiàn)代詩 西方典故 歷史美 知性美 人性美 摘 要:西方用典在臺(tái)灣現(xiàn)代詩歌創(chuàng)作中表現(xiàn)出豐富的美學(xué)內(nèi)涵,如西方用典的歷史意識(shí)及現(xiàn)代性闡發(fā)呈現(xiàn)厚重的歷史美;其知性意識(shí)觀照呈現(xiàn)的知性美和理性美;以及生命意識(shí)及人性意識(shí)觀照呈現(xiàn)的人性美等等。運(yùn)用現(xiàn)代闡釋學(xué)的“視域融合”理論,從結(jié)構(gòu)主義符號(hào)學(xué)和文學(xué)修辭學(xué)的角度對臺(tái)灣現(xiàn)代詩西方用典之美學(xué)內(nèi)涵的闡釋,則將臺(tái)灣現(xiàn)代詩學(xué)納入跨文化、跨學(xué)科的比較詩學(xué)研究視域之中,拓展了研究空間。 西方用典是臺(tái)灣現(xiàn)代詩的一種普遍修辭手段。現(xiàn)代詩的西典并不局限于地理概念的西方,而是相對于中國典故而言的異質(zhì)文化典故,也就是通常所說的“洋典”。探究臺(tái)灣現(xiàn)代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西方用典,可發(fā)現(xiàn)其表征出鮮明的歷史意識(shí)、現(xiàn)代意識(shí)、知性意識(shí)和生命意識(shí),這諸種意識(shí)使臺(tái)灣現(xiàn)代詩具有厚重的歷史美、深邃的知性美和豐富的人性美。本文通過對臺(tái)灣現(xiàn)代詩西方用典之美學(xué)內(nèi)涵的闡釋,將詩歌的用典研究從實(shí)踐行為的概括進(jìn)一步拓展到理論的描述和詩學(xué)規(guī)律的總結(jié)。 一 用典往往與民族心理尚古崇經(jīng)意識(shí)有密切關(guān)系。西典大多脫胎于西方典籍和文學(xué)藝術(shù),而西方的悠久歷史與廣博的傳統(tǒng)文化自然而然形成一種巨大的向心力,使人們的思想意識(shí)不可避免向此傾斜,形成對西方先賢智慧的普遍敬仰和尊崇。因此,西典蘊(yùn)含著深刻的歷史內(nèi)涵,成為西方傳統(tǒng)文化的“原型”,隱含著深刻的民族群體的歷史記憶與文化選擇。 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這種歷史記憶如何選擇?西典作為一種構(gòu)建詩歌的語言符號(hào),從結(jié)構(gòu)主義符號(hào)學(xué)來看,其構(gòu)成以對等原則為基礎(chǔ),即通過典源語境和現(xiàn)實(shí)語境的相似或?qū)φ諄順?gòu)成。西典有兩個(gè)端點(diǎn),一端聯(lián)系當(dāng)代現(xiàn)實(shí),一端聯(lián)系西方歷史事件,西典在運(yùn)用中或?yàn)閺?qiáng)調(diào)今昔的類似,即歷史原型(人物或事件原型)的重復(fù),或?yàn)閺?qiáng)調(diào)今昔的對照,即今日與往昔的差異。于是,在兩個(gè)不同歷史時(shí)空語境的碰撞與交融中,西典表現(xiàn)出渾厚深沉的歷史意識(shí)。臺(tái)灣現(xiàn)代詩通過西方用典自然也就滲入了這種歷史意識(shí),呈現(xiàn)厚重的歷史美。 席慕蓉的詩細(xì)膩柔婉,純粹澄澈,詩中頗喜歡用龐貝古城的典故。如:“龐貝城里十六歲的女子/在發(fā)間細(xì)細(xì)插上鮮花/就在鏡前就在一瞬間/灰飛煙滅了千年堆砌的繁華”(《夏夜的傳說》),又如:“如龐貝的命運(yùn)/將一切最美的在瞬間澆鑄”(《夏日午后》),詩人藉古城陷落的歷史典故,感慨著時(shí)間的流逝和人生命運(yùn)的滄桑變化,這種懷古情愫纏綿悱惻,深沉細(xì)膩。 陳黎詩中的西典具有深沉曲折的歷史意識(shí):“華浦蘭語傳道書,西底雅語馬太福音/讓上帝的靈入福爾摩莎的肉”(《福爾摩莎 一六六一》),用史實(shí)典故追憶17世紀(jì)西方殖民者對臺(tái)灣的精神奴役,飽含著對屈辱歷史的憤慨和痛苦思索。 朵思的詩則借史實(shí)典故回憶戰(zhàn)爭如《(湖巖礁)湖下地行船》:“其實(shí),最純粹的黑暗/更純粹的,則是忘掉它正劃行在想象 /的拆卸和拼裝”,通過對二戰(zhàn)時(shí)期德國武器運(yùn)裝地遺址的緬懷,思索人類乖戾多舛的命運(yùn),這種歷史意識(shí)具有深刻的反思色彩。 西典作為西方文化的一種“原型”,其蘊(yùn)涵的文化內(nèi)涵在移植過程中,包含著作為創(chuàng)作主體的詩人超越自身存在的當(dāng)下視域去收覽彼時(shí)彼地的典源語境的意義,將之與現(xiàn)實(shí)語境互比互證,這形成一種“視域融合”;也包含著西典作為此在空間的“他者”對臺(tái)灣現(xiàn)代詩歌自我的觀照,這也形成另一種“視域融合”;此外還包含著作為闡釋主體的讀者的“前理解”與詩歌用典語境的觀照,這亦可視為一種“視域融合”。西典獨(dú)特的“視域融合” 形成了多元對話、開放性的臺(tái)灣現(xiàn)代詩歌語境。因此,通過西方用典,臺(tái)灣現(xiàn)代詩人通過對比或相似的時(shí)空聯(lián)想以今會(huì)古,以古襯今,闡發(fā)了新的現(xiàn)代性思想。 痖弦的詩用典新奇獨(dú)特,如:“更恨祈禱/因耶穌也是男子”(《棄婦》),圣經(jīng)中的救世主成為不愿祈禱的對象,傳統(tǒng)文化“原型”完全被顛覆。這種用典方式是對西方文化另辟蹊徑的攝取與吸納,典故的古今內(nèi)涵發(fā)生了質(zhì)的變化,而這種現(xiàn)代性闡發(fā)卻為人們提供了一種新的審美思維。痖弦的另一首詩則藉耶穌為救贖世人而獻(xiàn)身的典故,表達(dá)一種現(xiàn)代生存狀態(tài):“所有的靈魂蛇立起來,撲向一個(gè)垂在十字架上的/憔悴的額頭。/穿過從肋骨的牢獄里釋放的靈魂,/哈里路亞!我們活著。走路、咳嗽、辯論,/厚著臉皮占地球的一部分。”(《深淵》)以耶穌受難的“古”映襯被救贖者荒誕墮落的“今”,表達(dá)對現(xiàn)實(shí)的深切失望,具有現(xiàn)代主義的荒誕意識(shí)。 對現(xiàn)代都市罪惡蔓延、道德墮落的強(qiáng)烈憂思,余光中的詩也用典予以揭示:“罪惡在成熟,夜總會(huì)里有蛇和夏娃”(《芝加哥》),詩人抓住《圣經(jīng)》典故原型與現(xiàn)實(shí)語境的相似性,跨越時(shí)空進(jìn)行聯(lián)想,以今會(huì)古,在異質(zhì)文化中找到情感內(nèi)蘊(yùn)的觸媒點(diǎn)并加以闡發(fā),具有鮮明的現(xiàn)代性思想。 季廣茂在《隱喻視野中的詩性傳統(tǒng)》一書中指出:“典故是一種歷史化的隱喻……是在神話或歷史事件暗示之下感知、體驗(yàn)、想象、理解,談?wù)摦?dāng)下事件、情狀或環(huán)境的心理行為、語言行為和文化行為。典故對構(gòu)成隱喻的彼類事物和此類事物作出限制:隱喻中的彼類事物在典故中變成了神話或歷史事件,隱喻中的此類事物在典故中變成了當(dāng)下事件、情狀或環(huán)境。因此,典故能夠借助于歷史與現(xiàn)實(shí)在相似性基礎(chǔ)上相互映照表現(xiàn)一定的思想與情感,并能達(dá)到以少少許勝多多許的藝術(shù)效果。”①因此,西典體現(xiàn)了西方傳統(tǒng)文化厚重的歷史積淀,而臺(tái)灣現(xiàn)代詩人通過對西典故實(shí)的情感注入及創(chuàng)造性運(yùn)用達(dá)到了“以故為新”,襲故而彌新的境地,使西典獲得永久的生命力。 二 上世紀(jì)50年代,臺(tái)灣現(xiàn)代詩派的搖旗吶喊者紀(jì)弦先生旗幟鮮明地提出“知性之強(qiáng)調(diào)”的號(hào)召。研讀臺(tái)灣現(xiàn)代詩,就會(huì)發(fā)現(xiàn)大多意象繁復(fù)稠密,講究思想知覺化,主題多元化。西典作為臺(tái)灣現(xiàn)代詩的語言構(gòu)件和意義生成符號(hào),也成為其知性意識(shí)的表征。 這里的“知性”概念有別于西方古典哲學(xué)的理解。斯賓諾莎定義的知性是從方法論角度論述,即“知性憑借天賦的力量,自己制造理智的工具,再憑借這種工具獲得新的力量來從事別的新的理智的作品,再由這種理智的作品又獲得新的工具或新的力量向前探究,……直至達(dá)到智慧的頂峰為止”②。這種知性是邏輯學(xué)研究所指向的認(rèn)知理性。西典的“知性”則接近于康德的“審美知性”,即“想象力在它的自由中喚醒著悟性,而悟性沒有概念地把想象力置于一個(gè)合規(guī)則的游動(dòng)之中,這時(shí)表象傳達(dá)著自己不作為思想,而作為心意的一個(gè)合目的狀態(tài)的內(nèi)里的情感”③。這里的“悟性”即“知性”,是詩人、藝術(shù)家精神內(nèi)里的,與想象力、情感、意象融為一體,處在自由協(xié)調(diào)運(yùn)動(dòng)中的“審美知性”。 臺(tái)灣現(xiàn)代詩人和詩論家對現(xiàn)代詩及西典的“知性”特質(zhì)歷來頗為重視。杜國清先生在1989年提交給“臺(tái)灣暨海外華文文學(xué)國際研討會(huì)”的《新詩的再革命與現(xiàn)代化:論臺(tái)灣現(xiàn)代詩的特質(zhì)》一文中,指出臺(tái)灣現(xiàn)代詩的特點(diǎn)之一就是:“在詩質(zhì)上以主知的詩想取代感傷的詩情。”④在1991年提交的《宋詩與臺(tái)灣現(xiàn)代詩》一文中認(rèn)為“在中國的詩傳統(tǒng)中,臺(tái)灣現(xiàn)代詩的特質(zhì),也可以追溯到宋詩”⑤,即臺(tái)灣現(xiàn)代詩的知性意識(shí)與宋詩的講求理趣是一脈相承的。 洛夫先生則說:“我們所謂的知性或思想性,……是對生命本性的體認(rèn),生命真諦的探索,這種本性與真諦唯有在殘敗的生命情境中發(fā)現(xiàn)。”⑥他站在尋求詩人主體的生存意義與生存價(jià)值的存在主義哲學(xué)基點(diǎn)上來界定現(xiàn)代詩的知性內(nèi)涵,具有形而上的超越性。 覃子豪先生也提出自己的見解:“近代詩有強(qiáng)調(diào)古典主義的理性和知性的傾向。因?yàn)槔硇院椭钥梢蕴岣咴娰|(zhì),使詩質(zhì)趨于醇化,達(dá)于爐火純青的清明之境……最理想的詩,是知性和抒情的混合產(chǎn)物。”⑦他認(rèn)為知性在詩藝的運(yùn)作中,必須和情感、意象、哲理三者互相滲透,達(dá)致象中有理,理中有情、情中有象。
因而,臺(tái)灣現(xiàn)代詩人在創(chuàng)作中充分而敏銳地感應(yīng)到這種“審美知性”的召引,并通過西典運(yùn)用明晰地表現(xiàn)出來。
理.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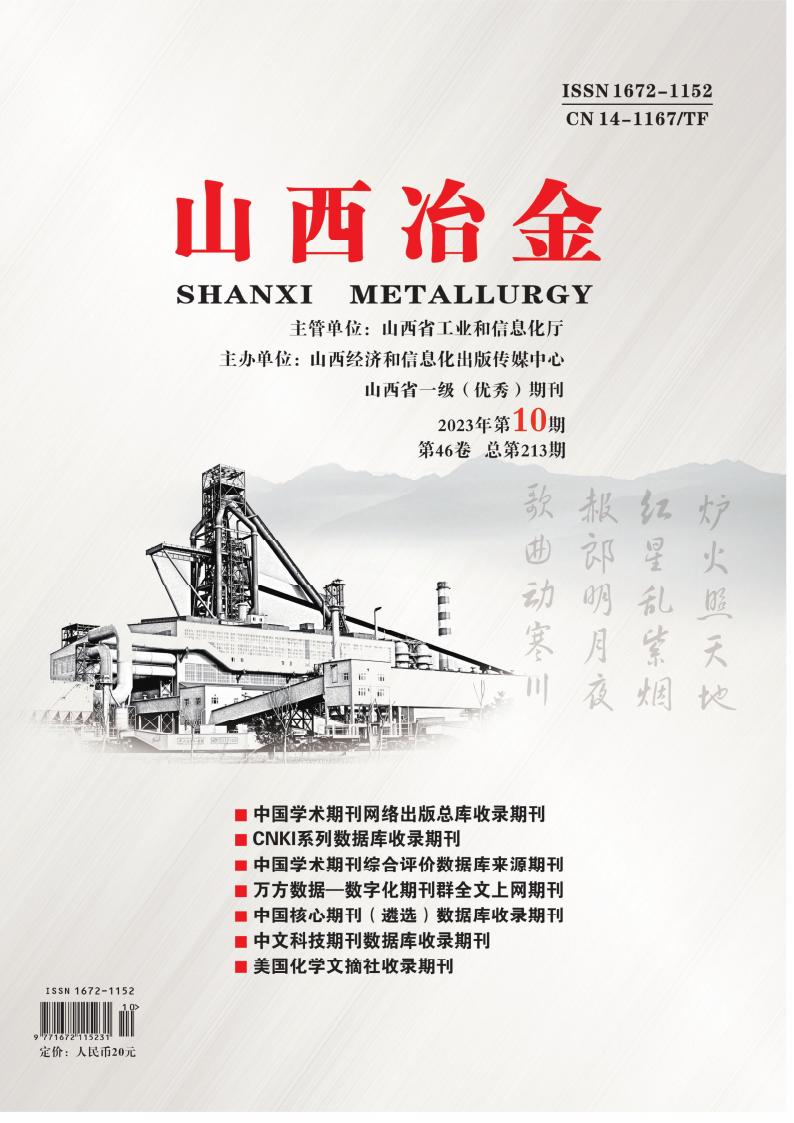
管理.jpg)
學(xué)院學(xué)報(bào).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