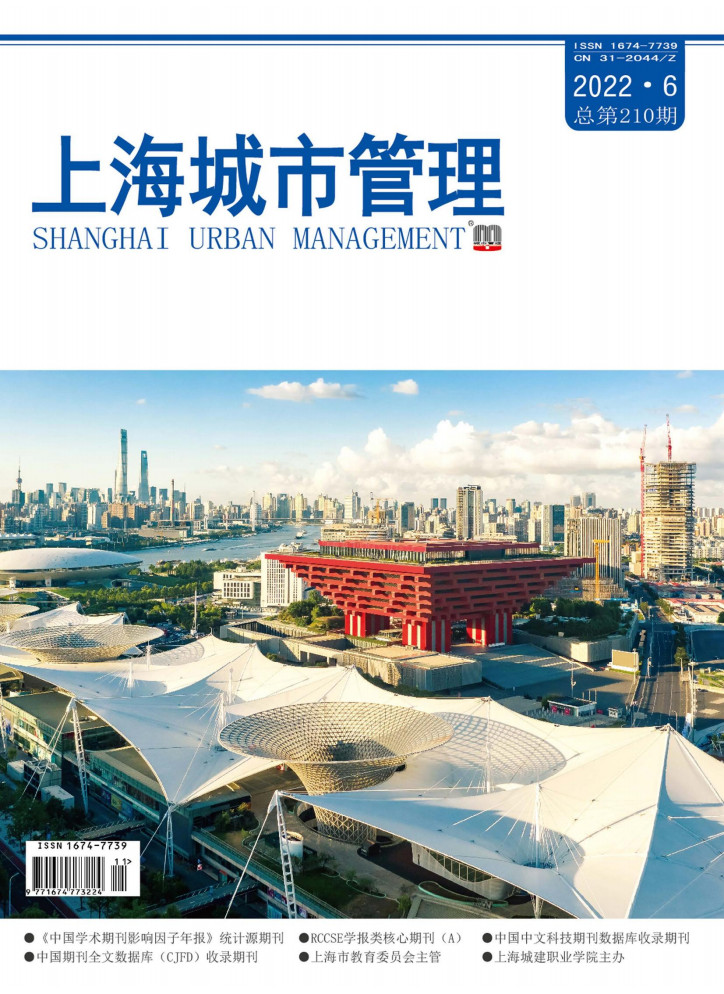文學創作中報人角色的凸顯——淺析張恨水以新聞思想編副刊
韋金艷
論文摘要:張恨水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一位小說大師,而事實上,新聞記者才是他的正業,他從事新聞工作長達30年,在整個報業生涯中,他的支撐點都落在報紙副刊上。目前,學界關于張恨水新聞思想的研究不多,本文著重探討張恨水在編輯副刊的實踐中形成的主要新聞思想,包括以小說反映社會新聞事實,予副刊以鮮明的新聞性;重視副刊的輿論監督作用;主張新聞自由等。
論文關鍵詞:張恨水 副刊新聞事實 新聞思想
提到張恨水,比較普遍的看法是:他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一位杰出的小說大師。在近半個世紀的寫作生涯中,他為讀者創造了100多部中長篇小說.總字數近2000萬言;同時,他還發表了各類散文,總字數約600萬言,詩歌約3000首。無疑,張恨水是文壇上的寫作能手,但說到他的新聞生涯,知道的人恐怕不多。張恨水自己也說過:“我的主要職業是做新聞記者.寫小說不過是性之所好。”事實上,寫作對于張恨水不過是“副業”,他的終身職業是新聞記者。從1918年在蕪湖《皖江日報》當總編輯正式開始記者生涯,到1948年辭去《新民報》的所有職務,張恨水從事新聞工作長達30年。曾任上海《申報》駐京記者、《益世報》助理編輯、蕪湖《工商日報》駐京記者、協助成舍我創辦聯合通訊社兼任北京《今報》編輯、任《世界晚報》和《世界日報》編輯、自辦《南京人報》、任《新民報》副刊編輯等,他的一生都和新聞事業緊密聯系在一起。是一位出色的報人.
也是新聞戰線上有名的“全手匠人”在幾十年的報人生涯中,張恨水的支撐點當落在報紙副刊上。在北平,他先后主編過《世界晚報》副刊“夜光”、《世界日報》副刊“明珠”、《新民報》副刊“北海”;在上海,他又主編《立報》副刊“花果山”;在南京,主編《南京人報》副刊“南華經”;在重慶,主編《新民報》副刊“最后關頭”等,他的生命光華及報人才情主要傾注在副刊上。而在幾十年的新聞實踐中,他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新聞思想理念。以小說反映社會新聞事實。予副刊以鮮明新聞性張恨水幾十年的副刊編輯實踐中.最突出的成就莫過于他在副刊上發表的連載小說:在20世紀20年代,他幾乎囊括了北平各大報的連載小說:30年代。他又包攬了中國南北報業中發行量最大的《申報》、《新聞報》的連載小說,包括《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緣》等,紅極一時,以至于當時的群眾為了追看當天張恨水的小說連載而在報館門口排隊等候買報。但是,這些小說不只是一個傳統文人對于風花雪月的吟詩灑淚.而是密切聯系當時的社會現實,把社會新聞集合到小說中,使小說與新聞事件緊密結合.反映社會的最新動態及現實生活中的世態百相、人情冷暖。
當時中國的社會現實,決定了中國新聞的非開放性.也決定了其不可能成為一個獨立的“公眾勢力”,來自由表達各種新聞與意念。因此,中國作家,尤其是近代以來的記者作家更愿意以小說這種虛擬的方式吸納、集合各種有趣的新聞,試圖借此表達自己對人生與社會的認識。張恨水正是這樣一位作家、報人。
張恨水作為報人的時期正是內戰頻頻的時期,政治生活缺少穩定的“游戲規則”,輿論環境極為嚴峻,報人稍有不慎,輕則失去飯碗,重則死于非命。在這樣的環境下,張恨水使用迂回曲折的方式表達其對生活的認識與評判,把大量的新聞事實、社會黑幕融人小說作品中,以避免因新聞的對號入座而明確樹敵,同時,免談或少談政治等敏感的話題,而將目光停留在文化、文學等軟性層面的問題上。
此外,張恨水還注重通過短評的形式來發表自己對社會新聞事件的見解。使副刊與社會新聞事件緊密配合,遙相呼應。他認為:“報紙上文字,是要配合時間的。…‘濟南慘案”發生時,張恨水在《世界日報》副刊上接連發表《恥與日人共事》、《亡國的經驗》、《中國不會亡國》等一系列短評,聲討日本帝國主義。他把重慶《新民報》副刊命名為《最后關頭》,1938年1月15日的發刊詞《這一關》中他這樣說道:
“最后一語,最后一步,最后一舉……我們只有絕大的努力,去完成這一舉.所以副刊的命名,有充分的吶喊意義包含在內。”他亮出了以抗戰為己任的鮮明旗幟。因此,他也為這個副刊規定了內容范圍:
1.抗戰故事(包括短篇小說);2.游擊區情況一斑;3.勞苦民眾的生活素描;4.不肯空談的人事批評;5.抗戰韻文。他以“關卒”的筆名,在副刊《最后關頭》上吶喊,不僅以詩文、小說作為武器,喚起民眾共同抗戰.而且還用漫畫等形式來諷刺揭露漢奸的丑態。對于新聞版面上不宜談的事.他的副刊文章往往旁敲側擊,卻能切中時弊:與此同時,他也直接描寫了抗戰.歌頌了可歌可泣的抗日英雄,促使副刊發揮了宣傳教育群眾、激勵民眾、打擊日寇的作用。 張恨水通過小說創作、短評寫作等.把社會新聞事實融人到副刊中.使副刊在具有文藝性的同時.也具有了鮮明的新聞性。重視副刊的輿論監督作用.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張恨水強調副刊的“輿論監督”作用。
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具體表現為對都市現存秩序、流行價值觀念的否定與顛覆.采取的方式是通過小說、短評等把都市人對權力、金錢等諸多事物的確信與追逐推向極致,從而使讀者感到這些確信無疑的觀念與信條的荒唐與可笑。張恨水認為即使是文史小品、雜文隨筆.也要針對當前的問題,有感而發:“我們正不妨下以一粟之微,上推宇宙之大。也不妨讀上古之禹,探今日之河流。”的副刊往往以敘為主,講究蘊藉含蓄,酸、甜、苦而不求辣的文風,顧時局而言他,斂鋒芒于笑談之中,但卻對當時的社會現實提出強烈的批判。
作為終生的職業報人,張恨水自然具有強烈的媒介意識,他的小說內容緊跟時代步伐.始終聚焦在紛繁復雜的都市社會生活上,通過描繪形形色色的人物.為讀者展示的是一個丑陋、畸形的都市社會,具有辛辣的批判意味。他是一位自由的批評者、監督者。
抗戰期間.他曾寫作了大量尖銳潑辣的雜文為抗戰鼓吹。如在1926年的《勢利鬼可起而為總長》、《官不聊生》等揭露了官場的腐敗、黑暗.揭示了官逼民反的社會現實;《免考入門券》抨擊了考場的舞弊營私勾當。但在當時嚴格的新聞檢查制度下.有的雜文都被剪掉。所以,張恨水更善于用小說來揭露、抨擊某些社會丑惡,把批判的鋒芒斂于小說的迂回中.以含蓄又不失尖銳的文章發揮副刊的輿論監督作用。主張新聞自由,當時的張恨水和成舍我一樣.主張“新聞自由”.敢于揭露黑暗。成舍我常常對編輯和記者說:“只要保證真實,對社會沒有危害,什么新聞都可以登。如果出了什么事,不要你們負責任,打官司、坐牢,歸我去。”作為成舍我的得力搭檔和一個堅決的新聞工作者.張恨水也極力主張新聞自由。他認為,報紙的言論應當完全受民意支配,應當代表民意.為人民呼吁,敢于講真話,敢于暴露社會的黑暗。他在編輯副刊期間,曾發表了大量的雜文、小說等來抨擊社會現實,為人民呼吁。然而,無論是在北洋軍閥統治時期.還是在國民黨統治時期,真正的“新聞自由”是沒有的。
新聞檢查文禁森嚴,報紙開“天窗”是常有的事。張恨水也有不少揭露腐朽、針砭時弊的文章被書報檢查官剪掉,在報紙上開了“天窗”。對于這種言論的不自由,張恨水在《世界上在談新聞自由》一文中寫道:“作新聞記者,是人生的不幸,一輩子沒有個自主的日子。想憑良心.這枝筆要替大多數人說話,就不免得罪少數人。……憑良心,這枝筆就要替極少數人說話。而這少數人,大概總不會是大多數人所喜的……這簡直是‘豬八戒照鏡子,里外不是人’。那末,不說話好了。請問,新聞記者在報紙上果然不說話,那又怎交待得過去?……”
在當時的黑暗統治下,缺失新聞自由,新聞工作者處于“應該說真話”而“無法說真話”的兩難境地中。張恨水“新聞自由”的幻想在現實中破滅.他感到新聞工作者實在難以為人.因而他甚至不愿自己的子女繼承自己這份“衣缽”。
張恨水不只是一位小說大師,更重要的是一位報人,他的小說創作是他報人生活的延續.他聚焦的核心永遠是堅實的社會而非浪漫的愛情。他身上也體現著作家與報人“雙重角色”的矛盾和融合:傳統文人的消極避世、獨善其身與現代報人的積極人世、干預生活,傳統文人取材于“情”及望月傷情的品格與現代報人聚焦社會現實以及冷峻犀利、縱橫恣肆的風格,雙重性格的沖突磨合。深刻影響了張恨水在創作及其新聞工作中的思想,使他在30年的報人生涯中形成不少閃光的新聞思想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