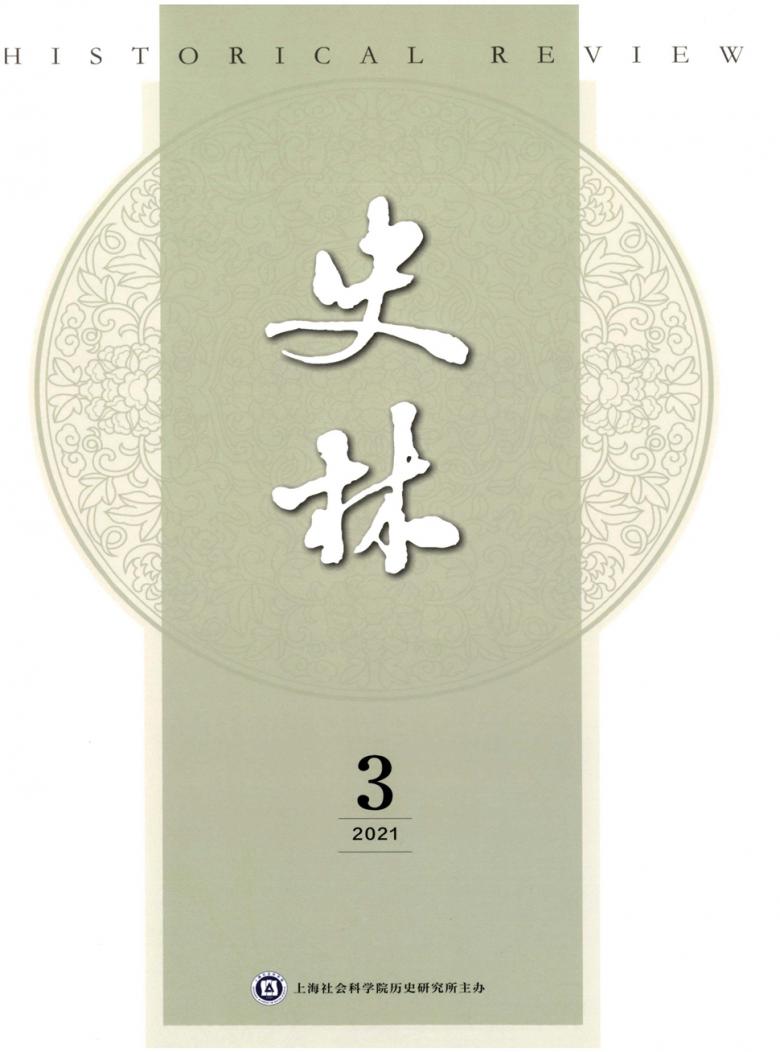關于淺說散文獨特的審美特性
呂彥福
真情,作為創作主體對生活的真切體驗與真誠態度,是形成一種文學樣式藝術真實的基礎,情感性歷來就被視為和形象性并列的文學基本因素。詩歌在抒發感情方面決不比散文遜色。小說表現的主題也既可大到國家大事、歷史題材,也可小到雞毛蒜皮、日常瑣事。語趣、理趣、智趣,在已經哲理化心理化知識化當代小說詩歌中也比比皆是,不足為奇。那么散文獨特的審美特征何在呢?也許我們可以從以下幾方面探知:
一、散文的“自我”性。
散文是創造主體性在文本表面上表現得最為強烈的一種體裁,文本的“自我性”是散文的一個基本的審美特征。文本中的作者必須是一個絕對真實的“自我“,“自我”成為散文主體的審美對象。絕大多數的散文總是讓作者這個“我”直接出現在文本中間,“我”必須在散文中出場。或者以“我”為中心敘寫“我”的所見所聞所感所想,或者面對一景一物而引出“我”的縷縷情思、綿綿絮語,從而宣泄、抒寫“自我”的生活經歷、情感體驗與哲理感悟。魯迅《從百草園到三味書屋》、朱自清《荷塘月色》等,就是以“我”為主的散文名篇。在這些作品中,“我”成為全文表現的主角。即使極少出現“我”的散文,作者的“自我”也往往活躍于文本的背后。不管是百草園、三味書屋也好,還是荷塘月色也好,始終都是作者眼中、心中的景物,始終以作者的眼睛與詩心去看、去體味。因為作者這個“我”直接出現在文本當中,所以散文一般都是以第一人稱“我”展開敘事,故散文文本敘事結構,或由“我”的所見所聞的物理時空順序來進行組織,或由“我”的意識流動的心理時空順序來予以安排,總之文本敘事因此而顯出整體性的“自我”言說與“自我”書寫,自始至終充盈著作者濃郁的主觀心理色彩。在這一點上,可以說散文追求的是一種“有我”之境,而非“無我”。
外在顯露的“自我”性這一特征,使散文在文本上與小說、戲劇和影視劇本劃清了自己的界限。相比較而言,小說、戲劇、影視劇本往往是通過人物之間思想性格的沖突、各類人物命運的發展以及情節故事的展開,來間接地表現小說家和劇作家的主觀思想感情和對生活的感想。“我”是不直接出場的,即使出場也是非常隱蔽的,往往是借助于作品中的人物事件來表達作家的主觀情感。作家的主觀性是隱蔽在人物與故事的背后,而且對優秀的作品來說,越隱蔽越好。也正是在這一方面,顯示了它們與散文外在顯露的“自我”性迥然有別的基本特征。在詩歌中,作者自我也是很少直接出現在文本當中的,往往是借助于景物、意象來抒發詩人的思想感情。
二、散文的非虛構性。
散文是非虛構性的文學,這是由散文的審美特質所規定的。文學是可以而且應該虛構的,而散文卻是不容虛構的文學“另類”。
散文題材內容的質料多種多樣,有作者直接從客觀生活中采擷的真人真事,有作者親身經歷的生活片斷、生活細節以及主觀的內心體驗,有間接從書本、報紙、雜志、影視等媒體中獲取的材料,但是,不管怎樣這些題材都要求是真實可靠、確鑿無疑的,尤其是,作家敘寫自己的見聞、親身的經歷以及那些借以抒寫內心思想與情感的客觀諸多事物,都應該絕對真實,是真實生活的真實“再現”。真實是散文的生命。在散文中,作者要絕對真實地抒寫自己的思想和感情,并且絕對真實地抒寫自己的內心體驗和對客觀事物的感悟與思考。散文中的真情實感不是淺薄的、虛假的、做作的情,而必須是作者內心世界的真實外現,必須是充滿“個性”的真情。 這種非虛構性,可以說是對中國古代散文文化基因的一種繼承,從《左傳》、《戰國策》到《史記》、《漢書》,其中不乏很多文史結合的美文,這些文章均是歷史實事的真實記錄。也正是這個原因,形成了我們民族長期以來的審美習慣與心理定勢,讀者總是把散文當作歷史來讀,當作作家(或他人)真實的生活史、個人史、心靈史來認識和評價。讀者相信散文是抒寫真實的,他們期待從散文作家敘說的真人實事中獲取“真”的感悟、“善”的誠信、和“美”的愉悅。因此,散文題材的非虛構性,是這種文體煥發思想力量與藝術魅力的一個關鍵性的基本特征。正是在這一點上,它與虛構性的小說、詩歌、戲劇、影視劇本等文學體裁,顯示了題材上質的區別。小說歷來強調其虛構性,往往是雜取眾人眾事而合成為一;戲劇、影視劇本的虛構性也比較突出。詩更是強調大膽的想象與夸張,也允許虛構與概括,追求避實就虛的空靈,常給人以“水中之月、鏡中之花”的美感。如果散文在題材上半實半虛、半真半假,甚至整個地虛構人物、杜撰事件、細節,那將不可思議,等于從根本上取消了散文的生命力與散文的審美原則。
三、散文的“隨”性,即無技巧性。
優秀的散文,不管作家們如何變幻筆墨,總會給我們一種“隨”的審美感受。那喜怒哀樂、人事物景,總好像是作家們隨心所欲、漫不經心地道出來的,全然不見匠心經營的痕跡,從而達到一種“無技巧”似的渾然天成的境界。散文理論家林非稱:“散文比起別的文學樣式來,最不講究技巧的,它不需要小說通常所具有的情節結構,戲劇通常所具有的場景沖突,詩歌通常所具有的節奏和韻律。”顯然,這是與其他幾種體裁比較之后而作出的一個正確判斷。而且從讀者對散文的審美要求看,他們通常期待散文作家在自然、平易、樸素的藝術表現中,達到“最不講究技巧”的那種境界。楊絳先生的散文《干校六記》,以其樸素、洗煉、平靜、通達、親切,以其舉重若輕的大家風范,詮釋了何謂樸素是一種高格的美,何謂“最高的技巧通常是無技巧”。張愛玲在評價蘇青時也講過類似的話:“有人批評她技巧不夠,其實她的技巧正在那不知不覺當中”。可見,真正的散文大家往往是追求無技巧的。實際上,在“最不講究技巧”的背后其實是最講究技巧的,這正是散文的又一個顯著的基本特征,即無技巧性的有技巧。散文文本表面看似自由散漫,不拘格套,顯示出作者“大可以隨便”、“與其防破綻,不如忘破綻”的自由瀟灑的作風。其實文本內里是十分講究立意、構思、剪裁、布局、結構、語言等諸多表現形式與藝術技巧的。———這正是散文文本構造的一個悖論,要在章法與技巧所制約的不自由中創造出文本的自由。
因此,我們可以說,散文最可貴的靈魂,乃是率真與灑脫。恍如天地間的赤子,一舉手一投足,一顧盼一回瞬,皆出隨意,一言以蔽之,即個性的充分展現,在其自身,也自有一份天然的美感與神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