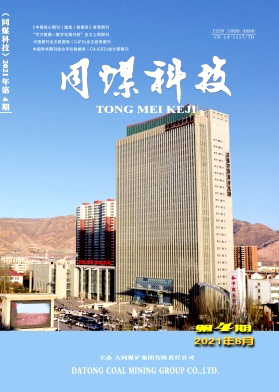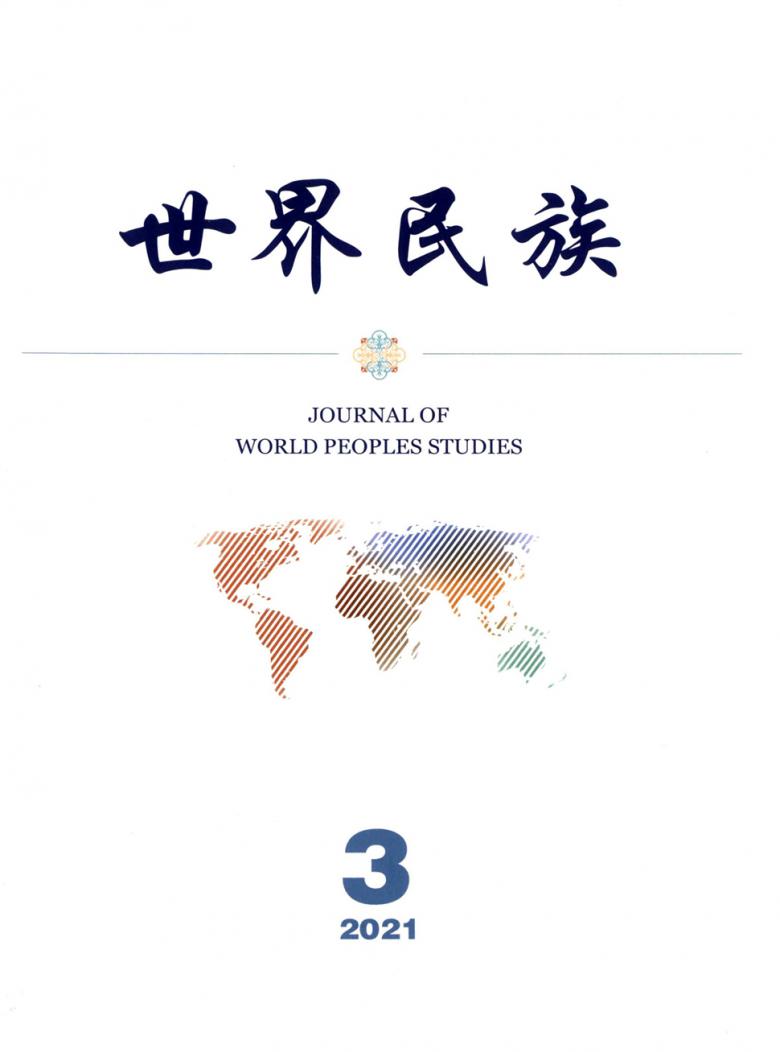《中國近代散文史》
謝飄云
撰寫過中國第一部文學史的東吳大學教授黃人在清帝遜位前一年刊布《國朝文匯》,這部五百卷的巨帙為清文的結穴劃上了一個圓滿的句號:自80年代初開始,錢仲聯教授著《清文舉要》授及門諸生,示以從入之途;謝飄云教授曾負笈吳門,從錢老受清代詩文,歸粵潛研十余載,終于結出碩果,向學術界奉獻了一部30萬言的《中國近代散文史》。面對優秀的清文及近代散文遺產,這三代學人都通過自己的探討作出歷史的回答,如果說,《國朝文匯》旨在存目傳人,《清文舉要》主要是傳授師法和家法,那么,《中國近代散文史》則重于描述晚清、近代散文的文化慧命,闡述中國散文的近代轉型。
美國史學家莫·曼德爾鮑姆在其《歷史中的客觀主義》中說:“任何一部專門歷史,如有一個中心題材,它就構成這部歷史所記載的各個事件的一種聯系形式。”在具有巨大的歷史和現實涵蓋面的近代散文中,這種意味的“聯系形式”至少有三層文化內蘊。
首先,作者極其重視文體發展過程的整體性研究,充分調動了“文體”本身具有的整合力。現當代許多綜合性的和專體性的文學史著作都不同程度重蹈古已有之的“文苑傳”式的寫法,往往體現為文學的“事件的總和”,而不是“過程的總和”(恩格斯《費爾巴哈與德國古典哲學的終結》語)。作者在寫作“近代散文史”時,不想將自己的筆約化為一根按時代先后機械串聯散文作家、作品的線條,他的研究視角與寫作重心已表現出富于哲理色彩的“轉移”:近代散文的近代化過程乃是中國散文必然的文化轉型,近代散文的發展史有如“多聲部”合鳴的氣勢磅礴的交響樂章,第一重奏為鴉片戰爭之前涌出現一批末世批判者,他們的散文洋溢著批判理性之光;第二重奏則是鴉片戰爭之后痛心疾首、力圖挽狂瀾于既倒的改革先行者們的探索,“睜眼看世界”的新風已不愜于古雅的形式了;第三重奏是維新派的文體創新,真正掀起了席卷全國的“文界革命”;第四重奏伴隨著民主革命的風起云涌而顯出驚濤拍岸的雄放,奠定了現代散文的美學原則。這四重奏所昭示的文體變革實質上乃是中國近代文化轉型的有機組成部分和內在表征之一,呈現為思想史意義上的同步嬗變。當然,作者并沒有將這一嬗變無限擴大為散文發展的全部,新美典的形成作為一個連續性的歷史過程,僅僅是先鋒型精英的創造,實有賴于更為廣闊的文學、文化基礎,在作者筆下,晚清時期在散文創作的數量和廣度上占有相對多數的傳統古文也是近代散文史上的動情和弦,傳統在與時俱進,傳統散文所抒寫的優美篇章恰恰為新美典的奠定營造了濃郁的精神氛圍,作者用較大的篇幅闡揚姚瑩、梅曾亮、吳汝綸、黎庶昌、郭嵩燾、嚴夏、林紓等人散文創作的積極因素,從中厘清并進而揭示出文化新變的邏輯起點和美學基礎。不難看出,作者試圖打破既往的“反撥”、“斗爭”的發展模式,重構一種更加個性化、更高境界的“長時段”內在關聯的整體發展模式。
其次,作者非常注重探討散文文體的創造尤其是散文語言的新美典的確立過程。作者認為散文的語言是主客體互相滲透的,既是內容又是形式,既是文學又是生活語言,不僅包括了作家的才華、智慧、思想、人格等因素在文學表達中形成的風格,而且蘊含著耐人尋味的韻味、情趣、色彩的語言,更明確地講,語言本身就是存在的詩意棲居,“亮敞”與“澄明”著個體化世界存在的最大可能性(海德格爾《荷爾德林與詩的本質》語),近代散文的語言漸漸拋棄程式化的古典語象而走向生命存在的本質,近代散文在這個意義上才具有一種真正的“近作姿態”。當中華民族被歷史性地推到世界舞臺的前沿時,近代散文家驀然發現自己和自己民族、國家的命運已不可能用傳統話語來表述了,例如黎庶昌、薛福成、王韜、馮桂芬等或走出國門親身感受西方文明或沐浴西學東漸之風,在行文過程當中不可避免地使用了代表新事物、新觀念的名詞,結構風格大大背離桐城義法,漸開一代新風;而梁啟超雜取西洋東洋名詞、文法,打破文言緊湊的結構,擴展句子長度,順應口語舒展的自然文氣,創造了風靡全國的“新文體”;民主革命者則采取較為純粹的口語寫作鼓吹革命的文章,以期其有效地喚醒民眾、推動革命,親隨著革命的成功而以政府行為的方式確立中語的合法性,這就為五四新文學運動打下了必然性的伏筆。近代散文語言逐漸走向白話的過程,完全不同于既往的和同時期的民間白話文學創作活動,也很難判別其與民間白話創作的因果關系,很大程度上是文化精英自覺尋找近代生命、情感和話語方式的完整凸現,其雄放、淺直與流暢的文體風格蘊涵著更深刻的散文的自覺,“近作姿態”不僅綜合了文化精英的創造與民間藝術活動的內在一致性,更重要的是初步實現中國散文與世界的理性接軌,中西文化交流使散文創作呈現雙向性發展,臻于“文言合一”的境界,作者對于文體轉型、語言文化創造的描述與論證精確入微,令人信服。
再次,作者將近代散文文體史的發展視為近代文化——審美心理流變的過程,更確切地說是“人的近代化”過程。近代中國的命運,充滿了苦難同時也充滿了希望,散文作家們無法容與地優游于純美的小天地之中,散文題材涉及古今中外幾乎所有的政治、社會、經濟、軍事、文化等諸多方面的問題,而主題則只有一個:改革與救亡成了近代散文中的主旋律。作者概括近代散文的時代意蘊有四點:一是充滿憂患意識和時代使命感;二是表現出強烈的救亡圖存的愛國熱情;三是向西方學習,求變的進取精神;四是對科學民主精神的弘揚。這樣的概括頗具深度,如龔自珍、魏源的散文就彌漫著濃郁的憂患意識,感時憂國,呼吁改革自救、解放個性,經世散文以雄豪犀利見長;打開國門、西風東漸之后,湘鄉派作家也在順應時代潮流,漸趨實用,走出“神韻”的窠臼;而后20多年間,恰如黃人所言:“中外一家,梯航四達,歐和文化,灌輸腦界,異質化合,乃孳新種,學術思想,大生變革。故其文光怪瑰軼,汪洋恣肆,如披《五會》之圖,如觀楚廟之壁,如喜馬拉山絕頂,遘天帝釋與阿修羅鏖戰,不可方物。”(《國朝文匯序》)國人的觀念在急劇地更新,文化視野從封建帝國內部拓寬到整個世界,政治一文化一審美心理已漸漸接近完成向近代化的轉型,散文家在充分認識到變革的必然性的同時,對散文審美趣味的追求則從“神韻”一變而為慷慨議論、元氣淋漓了,我們從中解讀到的不僅僅是散文文體的嬗變過程,也展讀了國人文化心態次第更新的驚心動魄的歷程,難道這不是一部活生生的近代思想文化史巨幅圖卷嗎?“文學是人學”,誠哉斯言!作者解讀近代散文的思想歷程,正是復原近代散文中的“文化場”,揭示近代散文轉型的奧秘所在。這是作者頗具手眼之處,也是本書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本書的顯著特點是冶哲理思致和優美的語言表述于一爐,頗見功力。近代散文所負載的歷史內涵往往超出純美之上,憂患、救國、改革、革命、文化建設等話題本身具有很厚重的歷史積淀和理論深度,卻是研究文體史必須面對的客觀現實,作者能以淺近的話語出之,沒有名詞的鋪排,怡然條鬯,舉重若輕,充分發掘出近代散文深層的個體心靈的性靈之美。本書作為第一部近代散文史,建構了文體發展的動態歷史,可謂精彩紛呈;當然,尚需張皇幽眇之處亦在所不免,這就有待于作者與有志者共同努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