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語絲》:現(xiàn)代散文文體自覺的代碼
未知
一
《語絲》周刊,它的命名帶有些游戲的色彩。主事者之一的周作人曾說:“刊物的名 字的來源是從一本什么人的詩集中得來,這并不是原就有那一句話,乃是隨便用手指一 個字,分兩次指出,恰巧似懂非懂的還可以用。”(注:長年(周作人):《<語絲>的回 憶》,收入賈植芳主編《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社團(tuán)流派》(上),江蘇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但正是這樣的一個刊物,成為中國現(xiàn)代散文發(fā)展史上的一個重要的生長點,一方使散文 成為亮麗風(fēng)景的苑圃。《語絲》文備眾體,詩歌、小說、戲劇等各種樣式都有刊發(fā),但 散文類的文字無疑占了其中的多數(shù)。《語絲》促成了散文的發(fā)展,而散文生成了《語絲 》的文學(xué)史價值。
如果說《新青年》于散文而言,主要在于它釀造孵化了生成散文現(xiàn)代性所需的某種精 神,具有某種精神性的意義,那么《語絲》就在整體上使這種散文成為一種可觀的實在 ,使精神性物化為一種具體可感的形態(tài),具有一種重要的實在性價值。《語絲》是促成 中國現(xiàn)代散文走向成熟的一個創(chuàng)作基地。它以規(guī)模化的散文創(chuàng)作的優(yōu)勢,充分顯示著新 文學(xué)運(yùn)動的實績。《語絲》的存在,表示散文由古典形態(tài)向現(xiàn)代形態(tài)轉(zhuǎn)型進(jìn)程的完成。 《語絲》集聚成一個規(guī)模相當(dāng)壯大的作家群體——“語絲派”。在《語絲》第3期中縫 曾標(biāo)示了撰稿的陣營:“本刊由周作人、錢玄同、江紹原、林語堂、魯迅、川島、斐君 女士、王品清、衣萍、曙天女士、孫伏園、李小峰、淦女士、顧頡剛、春臺、林蘭女士 等長期撰稿。”就實際情形看,如魯迅所說,所謂“語絲”社員并不十分固定,“中途 出現(xiàn)的人,則在中途忽來忽去”(注: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萌芽》第1卷第 2期,1930年2月1日。),由此可見與《語絲》有關(guān)的作家是相當(dāng)多的。他們中的許多人 ,由《語絲》時期的散文創(chuàng)作而使其成為現(xiàn)代散文史上的不可或缺的作家。1935年3月 由上海光明書局出版的《現(xiàn)代十六家小品》,入選對象與《語絲》作家有關(guān)者就有周作 人、俞平伯、朱自清、鐘敬文、魯迅、林語堂等。發(fā)表于《語絲》的散文作品《鳥聲》 (周作人),《執(zhí)政府大屠殺記》、《太湖游記》(鐘敬文),《論“他媽的”》、《再論 雷峰塔的倒掉》、《紀(jì)念劉和珍君》(魯迅)等被作為代表作錄入《現(xiàn)代十六家小品》中 。由趙家璧主編,于1935年8月初版的《中國新文學(xué)大系》,內(nèi)含兩集散文,分別由周 作人和郁達(dá)夫選編。入選作家33人,收錄作品202篇,其中半數(shù)作家與《語絲》有所關(guān) 聯(lián)。
《語絲》的創(chuàng)刊是一件偶然之中蘊(yùn)有必然之意的文學(xué)史事件。就其表象而言,帶有某 種偶然性。這種偶然性與孫伏園直接相關(guān)。對此孫伏園在《京副一周年》中曾有具體的 敘述。孫伏園任《晨報副刊》的編輯,魯迅“是由他個人來約,投些稿件的人”,因為 魯迅與孫伏園有著師生關(guān)系,所以魯迅“似乎也頗受優(yōu)待”,“稿子一去,刊登得快” (注:魯迅:《我和<語絲>的始終》,《萌芽》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1日。)。但1924 年10月間,因為已經(jīng)排成大樣的魯迅的《我的失戀》被抽掉,孫伏園“少年的火氣,實 在有些按捺不住了”,便與代理總編輯劉勉已發(fā)生沖突,由此,孫伏園“便辭去《晨報 副刊》的編輯了”(注:孫伏園:《京副一周年》,《京報副刊》合訂本第13冊。)。《 我的失戀》如魯迅所說:“不過是三段打油詩”,“是看見當(dāng)時‘阿呀阿唷,我要死了 ’之類的失戀詩盛行,故意做一首用‘由她去罷’收場的東西,開開玩笑的”(注:魯 迅:《我和<語絲>的始終》,《萌芽》第1卷第2期,1930年2月1日。)。
但《語絲》的創(chuàng)刊又是必然的。《語絲》可以視作知識分子建構(gòu)自己話語權(quán)力的一種 象征。現(xiàn)代作家與古代作家的價值生成方式有著諸多的差異。現(xiàn)代作家不再以一種藏之 名山,以俟來者的心態(tài)去寫作,求取自給自足式的寫作價值。媒體,報紙、期刊等,在 現(xiàn)代作家創(chuàng)作價值實現(xiàn)的訴求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言說,是知識分子身份的一種證 明,但這種言說并不是一種私語,其功能在傳播的過程生成。這樣,現(xiàn)代作家就特別需 要有一方適宜他們言說的論壇。五四是一個生風(fēng)起潮的年代,但風(fēng)潮漸息。這對于曾經(jīng) 思想過的或向往著自由思想的文化人而言,是一個難耐的時段。魯迅對此的體驗是非常 深切的。他說:“在北京這地方,——北京雖然是‘五四運(yùn)動’的策源地,但自從支持 著‘新青年’和‘新潮’的人們,風(fēng)流云散以來,1920年至1922這三年間,倒顯著寂寞 荒涼的古戰(zhàn)場的情景。”(注:魯迅:《中國新文學(xué)大系?小說二集導(dǎo)言》,良友圖書 公司1935年版。)《新青年》等報刊曾是知識分子放飛精神的居所,但社會演進(jìn)所產(chǎn)生 的引力使得它的同人朝著各自設(shè)定的方向行進(jìn),由此《新青年》也隨之解體。孫伏園主 持的《晨報副刊》對失去話語園地的文化人具有一種補(bǔ)償功能,但孫伏園的突然辭職, 使得這一種補(bǔ)償被擱置。這一事件在魯迅這里“心上似乎壓了一塊沉重的石頭”。這不 僅因為事關(guān)自己,自有一種歉意,而且更在于丟失了話語載體而致一種落寞。這種看似 尋常的事件,卻在當(dāng)事人與相關(guān)人心中造成了深度的震蕩。“這在20年代的中國文壇上 ,是件大事”(注:孫伏園:《京副一周年》,《京報副刊》合訂本第13冊。)。由此可 見,話語陣地的構(gòu)筑對于作家所具有的特殊意義了。
正因為這樣,魯迅、周作人他們在孫伏園辭職不久,就立即支持他創(chuàng)辦新的刊物。魯 迅表示“愿意竭力‘吶喊’”,周作人、錢玄同等直接參與了《語絲》的籌辦,孫伏園 、李小峰、川島則“夾著《語絲》沿街叫賣”。他們的這種熱情很大程度上來源于對“ 自辦”刊物的看重。因為言說自由本是現(xiàn)代作家的一種宿愿。孫伏園的辭職與其說是一 種遺憾,倒不如說是為作家走向獨立的主體創(chuàng)造了一種機(jī)遇。“在孫伏園辭去《晨報副 刊》的編輯以后,有幾個常向副刊投稿的人,為便于發(fā)表自己的意見不受控制,以為不 如自己來辦一個刊物,想說啥就說啥。于是由伏園和幾個熟朋友聯(lián)系,……決定出一個 周刊,大家寫稿,印刷費(fèi)由魯迅先生”與參與者分擔(dān)(注:川島:《說說<語絲>》,見 《和魯迅相處的日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就這樣,一個將對現(xiàn)代散文史 產(chǎn)生重要影響的刊物應(yīng)運(yùn)而生了。
二
《語絲》的創(chuàng)刊及其存在,表征著現(xiàn)代散文開始走向一個自覺的時代。《新青年》前 期新文學(xué)運(yùn)動的貢獻(xiàn)更多地在于對舊文學(xué)的破壞;充分顯示新文學(xué)實績的,則在1920年 以后,整體上的新文學(xué)建設(shè)由此發(fā)端。從語言工具而言,白話的運(yùn)用已為大家普遍接受 ,報刊相繼都改用了白話文。白話文學(xué)不僅在數(shù)量上相當(dāng)可觀,而且質(zhì)的提升也明顯可 見。“1921年以后的新文學(xué)作品,已脫出文學(xué)革命時期的粗造濫制,幼稚蕪雜,量的擴(kuò) 展已達(dá)到飽和,開始致力于質(zhì)的提高。可以說是順利成長的時期”(注:司馬長風(fēng):《 中國新文學(xué)史》(上),香港昭明出版公司1980年版,第12頁。)。單就散文一體視之, 這個時期現(xiàn)代的文體意識漸次生成。《語絲》時代,散文體的意識不再僅是少數(shù)“先覺 者”所具有,而為一定的群體所覺悟體認(rèn)。這不是我們的一種臆想,而由“語絲”派對 “體”的討論的史實而昭示的。“語絲社同仁對‘語絲體’展開了討論,這是在20世紀(jì) 里散文批評家第一次自覺地、有意識、有目的地圍繞現(xiàn)代散文的‘體’所進(jìn)行的批評活 動”。“對‘語絲體’散文的評論,表明了散文批評家的‘體’意識強(qiáng)化和對散文的尊 重……‘語絲體’散文的討論標(biāo)志著中國現(xiàn)代散文批評也進(jìn)入了自覺時代”(注:范培 松:《中國散文批評史》,第22頁。)。范培松先生的這種判定揭示了史實所蘊(yùn)有的史 意。需要指出的是參與“語絲體”討論的散文批評家,并不是局外的研究者,而是“語 絲體”的創(chuàng)建者。因此他們的討論不僅表示了現(xiàn)代散文批評進(jìn)入了自覺的時代,而且也 是現(xiàn)代散文創(chuàng)作走向自覺時代的一個重要標(biāo)志。批評家“體”的意識的自覺導(dǎo)源他們作 為散文作家對這一文類質(zhì)性獲得了深切感悟與體認(rèn)。批評的自覺基于創(chuàng)作的自覺。
“語絲體”的討論是由孫伏園引起的。他于1925年10月27日,也就是差不多在《語絲 》創(chuàng)刊一周年的時候,給周作人寫信提出“語絲體”的命題。信以《<語絲>的文體》為 題刊發(fā)于《語絲》52期上。孫伏園以編輯的職業(yè)敏感首先發(fā)現(xiàn)《語絲》雜志“體”的存 在。他認(rèn)為:“《語絲》并不是在初出時有若何的規(guī)定,非怎樣怎樣的文體便不登載。 不過同人性質(zhì)相近,四五十期來形成一種《語絲》的文體”,它“只是一種自然的趨勢 ”。孫伏園并沒有直接給出有關(guān)語絲體征的命名或描述,這大約是為展開討論留出足夠 的空間罷了。不過從其間透露出的信息,我們還是可以知曉孫伏園所體認(rèn)的《語絲》作 法的。他認(rèn)為,在《語絲》這里,“我們最尊重的是文體的自由,并沒有如何規(guī)定的” ,“我想先生的主張一定與我是一樣的。先生一定說:那一位愛談?wù)危阏務(wù)魏昧?,那一位愛談社會,便談社會好了;至于有些人以為某種文體才合于《語絲》,《語絲 》不應(yīng)登載某種文體,都是無理的誤會”。將孫伏園的這些表述作化簡處理并提煉其中 的要意,我們可以得知:自由隨意便是孫伏園認(rèn)知的“語絲”體征。
自由隨意的體征,在我看來,正是《語絲》同人實踐創(chuàng)刊初衷的一種結(jié)果。感受著不 自由之不快的創(chuàng)刊者,對自主自由的求取顯得特別的強(qiáng)烈。這從由周作人執(zhí)筆的《發(fā)刊 辭》中可以發(fā)現(xiàn)這一點。這一篇《發(fā)刊辭》就其大旨而言,無疑就是一群作家、文化人 發(fā)出的關(guān)于自由的宣言:
我們幾個人發(fā)起這個周刊,并沒有什么野心和奢望。我們只覺得現(xiàn)在中國的生活太是 枯燥,思想界太是沉悶,感到一種不愉快,想說幾句話,所以創(chuàng)刊這張小報,作自由發(fā) 表的地方。
我們并沒有什么主義要宣傳,對于政治經(jīng)濟(jì)問題也沒有什么興趣,我們所想做的只是 想沖破一點中國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濁停滯的空氣,我們個人的思想盡自不同,但對于 一切專斷與卑劣之反抗則沒有差異。我們這個周刊的主張是提倡自由思想,獨立判斷, 和美的生活。
由以上的申明可以知道,“自由思想”、“獨立判斷”、“美的生活”,正是《語絲 》同人對于理想中的人格與文體的一種設(shè)定和預(yù)約。“自由思想”與“獨立判斷”,反 映了經(jīng)過“五四”洗禮的知識分子,他們對自身現(xiàn)代性內(nèi)涵的理解與求取;“美的生活 ”則表明刊物對于文學(xué)藝術(shù)的親和,對于純?nèi)坏恼谓?jīng)濟(jì)話語的遠(yuǎn)離,對讀者提示著《 語絲》的性質(zhì)。這里最重要的就是對于自由的求取。
大體說來,“體”的生成表示著某種風(fēng)格的形成,或可認(rèn)為是一種文體成熟的標(biāo)志。 在孫伏園提出“語絲體”的話題后,周作人、林語堂隨即就作出了回應(yīng)。他們的表述自 然有著差異,但對“語絲體”的特質(zhì)——“語絲”精神的指認(rèn)卻是近似的。周作人在病 弱中回復(fù)孫伏園的來信。復(fù)信以《答伏園論“語絲”的文體》為題刊發(fā)于《語絲》第54 期上。他強(qiáng)調(diào)《語絲》的“目的只在讓我們可以隨便說話,我們的意見不同,文章也各 自不同,所同者只是要不管三七二十一地亂說”。周作人沒有從學(xué)理的層面上對“語絲 體”作出界定,而是以散文化的語言對其作出可以意會的描述:“《語絲》還只是《語 絲》,是我們這一班不倫不類的人借此發(fā)表不倫不類的文章與思想的東西,不倫不類是 《語絲》的總評,倘若要給他下一個評語。”周作人給出了“不倫不類”一詞論評《語 絲》之人之文。“不倫不類”其內(nèi)蘊(yùn)的意義就是不受矩yuē@①,隨心而為,因而它可以被“自由”一詞置換,其所意指的也就是“隨便說話”。周作人似乎并不關(guān)注“語絲體”的形式特征,他最為著意的是“語絲體”的內(nèi)在精神品質(zhì)。文體的精神品質(zhì)實際上也就是主體的精神品質(zhì)。周作人看重的是主體人格的獨立與由此生成的精神風(fēng)度。在周作人看來,主體只有稟持了獨立的人格,他在寫作時才會“大膽與誠意”。“大膽與誠意”是無所羈絆的散文作家具有的一種精神風(fēng)度。散文實際上是作家精神風(fēng)度的一種語言物化形式。
林語堂也參與了“語絲體”的討論,他在《插論<語絲>的文體——穩(wěn)健,罵人,及費(fèi) 厄潑賴》一文中,先引述周作人文章中的要點,表示對此的認(rèn)同,繼而“插說”自己對 “語絲體”的闡釋。對于“語絲體”體征精神的認(rèn)識,林語堂與周作人、孫伏園并無兩 致。他“插說”的要旨是分析《語絲》文體形成的“二大條件”,并由此強(qiáng)化文學(xué)個人 化的意義。林語堂以為刊物要成為作者得以自由言論的說苑,就應(yīng)該兼容作者種種的“ 偏見”。在他看來,“惟有偏見乃是我們個人所有的思想,別的都是一些販賣,借光、 挪用的東西。凡人只要能把自己的偏見充分地誠意地表示都是有價值,且其價值必遠(yuǎn)在 以調(diào)和折中為能事的報紙之上”。據(jù)此,他“主張《語絲》的朋友只好用此做充分表示 其‘私論’,‘私見’的機(jī)關(guān)”。林語堂將通常視作貶義詞的“偏見”反轉(zhuǎn)作褒義的處 理。“偏見”的褒義化,是林語堂從“偏見”中取出了“個人性”的內(nèi)涵。這里的“偏 見”表示著因自由而得創(chuàng)見,表示著話語主體對公共話語的規(guī)避,對私人話語的求取。 “語絲體”的隨意并不是從俗,而是意指作文的自出機(jī)杼,排拒庸言。因此,這一等值 于“個人性”的“偏見”,從一個獨特的角度解析了包括“語絲體”在內(nèi)的現(xiàn)代文學(xué)應(yīng) 具有的現(xiàn)代性品格。
除操守“偏見”外,林語堂認(rèn)為《語絲》文體形成的第二個條件就是“我們絕對要打 破‘學(xué)者尊嚴(yán)’的臉孔,因為我們相信真理是第一,學(xué)者尊嚴(yán)不尊嚴(yán)是不相干的事。即 以罵人一端而論,只要講題目對象有沒有該罵的性質(zhì),不必問罵者尊嚴(yán)不尊嚴(yán)”。林語 堂所示第二個條件與前者所謂“偏見”的條件之間有著內(nèi)在的關(guān)聯(lián)。偏見的稟具需要言 者有一個個人的立場;而個人立場的堅守就需要主體有一種我愛吾師,我更愛真理的理 性精神。只有破除了迷信、盲從的心理,言者才會取得屬于他個人的“偏見”。因此, 這種“偏見”應(yīng)是持之者由精神自主自由而得的一種結(jié)果。
魯迅是在《語絲》差不多自動停刊的時候,對“語絲體”特征作出歸結(jié)的。他寫有《 我和“語絲”的始終》一文,對這一刊物的起訖變化的情形進(jìn)行比較具體的敘述。論及 《語絲》的特色時,魯迅說:“這刊物本無所謂一定的目標(biāo),統(tǒng)一的戰(zhàn)線;那十六個投 稿者,意見態(tài)度也不相同……但同時也在不意中顯了一種特色,是:任意而談,無所顧 忌,要催促新的產(chǎn)生,對于有害于新的舊物,則竭力加以排擊。”“任意而談,無所顧 忌”這八個字是對“語絲體”特色所作的非常貼切的概括。魯迅的這一概括其要意和周 作人、孫伏園、林語堂所指認(rèn)的是一致的。由此可見,在這些《語絲》派同人的意域中 ,沒有比精神自主對于散文作家更為重要的了,他們對現(xiàn)代散文的基本精神有一種認(rèn)同 。我們之所以指認(rèn)《語絲》為現(xiàn)代散文走向自覺的標(biāo)志,是因為在我們看來《語絲》作 家普遍地具有一種明晰的現(xiàn)代散文觀念。
三
《語絲》作為作家的一個自由論壇,散文作為作家精神之流的一種載體,兩者是頗為 相得的。這種相得,使現(xiàn)代散文在《語絲》時期獲得了全面的發(fā)展。這種全面發(fā)展表現(xiàn) 在散文文體的類型方面,《語絲》建構(gòu)了現(xiàn)代散文的基本格局,雜感型態(tài)與美文型態(tài)成 為散文格局中的兩種主要的存在形式。《語絲》的《發(fā)刊辭》明確地表示:“周刊上的 文學(xué)大抵以簡短的感想和批評為主,但也兼采文藝創(chuàng)作及關(guān)于文學(xué)美術(shù)和一般思想的介 紹與研究。”由于《語絲》作家的積極實踐,雜感與美文同時得到了長足的發(fā)展。
《語絲》無疑是一份注重進(jìn)行社會批評和文化批評的周刊,所以,雜感一體的寫作自 然更為作家所重,《語絲》作家發(fā)表了大量的雜感,魯迅計有70多篇,周作人有100多 篇,林語堂、錢玄同、劉半農(nóng)、章衣萍、川島等也是《語絲》重要的雜感作家。魯迅所 說的“任意而談,無所顧忌”,指的主要就是雜感寫作。《語絲》上的雜感,在精神上 繼承了《新青年》的“隨感錄”,《語絲》對新事的催促,對舊物的排擊,對“一切專 斷與卑劣”的反抗等,無不承接了《新青年》的基本品格。這種承接對于《語絲》雜感 作者而言是十分自然的事情。因為魯迅、周作人、錢玄同、劉半農(nóng)等本來就是《新青年 》“隨感錄”的主要的或重要的作者。《語絲》對雜感的重視,體現(xiàn)在欄目的設(shè)置上, 可見它像《新青年》一樣也設(shè)有“隨感錄”一欄且設(shè)置的時間很長,始設(shè)于創(chuàng)刊時的第 2期,終刊前兩期,即第5卷第50期還發(fā)表隨感錄2篇。在“隨感錄”欄中發(fā)表的文章總 計230篇以上。此外,《語絲》還推出“我們的閑話”、“大家的閑話”專欄,分別刊 載本社同人和社外作者的雜感,另有“閑話集成”、“閑話拾遺”等。對于雜感的著力 倡導(dǎo),使這一體式的寫作頗成氣候。
作家對文體的擇取,并不只是對某種形式的選擇,它實際上關(guān)涉著作家對寫作價值取 向的認(rèn)定,對一定的意識形態(tài)的主觀傾向。從某種意義上說,作家選擇雜感(雜文)這一 文體,也就意味著他看重的是寫作的“覺世”功能,意味著他對現(xiàn)實意識形態(tài),特別是 主流形態(tài)持一種批評的態(tài)度。現(xiàn)代雜文文體的重要源頭應(yīng)是晚清風(fēng)行一時的“報章體” 政論,其時梁啟超親炙這一文體,寫作了大量的“別有一種魔力”的論評性文字,“開 文章之新體,激民氣之暗潮”。梁啟超通過這種寫作,宣泄著一個改良主義思想家的一 腔政治激情。《新青年》時期陳獨秀、魯迅等大量寫作“隨感錄”,以此表示著知識分 子對現(xiàn)實社會的關(guān)注,表示著對當(dāng)時社會主流意識形態(tài)進(jìn)行解構(gòu)的努力。由雜感的文體 流變史中,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這一文體已被附加了某種意識形態(tài)的質(zhì)性。
《語絲》作家充滿熱情地寫作雜感,這說明他們注意從寫作與社會的溝通關(guān)聯(lián)中實現(xiàn) 自身的價值。雜感之“感”從作者觀察社會、人生,思考現(xiàn)實、歷史中得來,寫作雜感 需要作者懷具一種社會責(zé)任感。雜感又不應(yīng)是一種包蘊(yùn)甜味的文體,文體的意義在作者 論議批評對象的過程中生成。它是一種應(yīng)有風(fēng)骨的文體。《語絲》的雜感作者與梁啟超 、陳獨秀、李大釗等有所不同,他們只是作家,是一群文化人,而不是政治家,或具有 政治激情的人。他們更多的是站在作家或者說人文知識分子的立場進(jìn)行社會批評、文明 批評,這種批評是個體的,而不是階級的、集團(tuán)的,是自由知識分子對社會作出的一種 自由言說。同時,因為是在寫作雜感,所以他們不能像藝術(shù)派作家可以遠(yuǎn)離政治,營造 個人藝術(shù)天地;作為社會派、人生派作家對社會政治進(jìn)行觀察、思考。政治往往是社會 現(xiàn)實存在中的結(jié)點,雜感作家往往有一種試圖打開這種結(jié)點的驅(qū)動力。
《語絲》雜感就取材題旨而言,約有社會批評、文化批評兩類。前者主要針對現(xiàn)實中 的政治性事件進(jìn)行論議,后者側(cè)重于對思想文化領(lǐng)域的情由作出批評。
作社會批評的雜感,體現(xiàn)了作者鮮明的反對封建主義和帝國主義的態(tài)度。錢玄同的《 恭賀愛新覺羅?溥儀君遷升之喜并祝進(jìn)步》,周作人的《致溥儀君書》等篇是就末代皇 帝出宮所發(fā)的議論,內(nèi)中洋溢著因反封建取得勝利而感覺到的喜悅之情。在他們看來, 溥儀出宮不只是他本人“回到自由的天地里去”,而更是封建政制終結(jié)的一個標(biāo)志,他 們與其說是恭喜“愛新覺羅?溥儀君從此超出帝籍,恢復(fù)他固有的人格和人權(quán)了”,毋 寧說是在慶祝反封建大業(yè)的成功。《關(guān)于反抗帝國主義》、《日本人的好意》等感觸的 也是政治話題。錢玄同有感于“五卅慘劇”的發(fā)生,為如何保國圖存而激揚(yáng)文字:
不愛中華民國,國必亡!甘愿托庇于“洋大人”之胯下,國必亡!守住已死的“鳥國粹 ”,國必亡!拒絕現(xiàn)代的文化,國必亡!要不亡國,除非由有腦筋的人們盡力去做“喚醒 國人”的工作,使國人把這種亡國的心理反過來。(注:錢玄同:《關(guān)于反抗帝國主義 》,《語絲》第31期。)
周作人對日人《順天時報》對李大釗烈士的惡意中傷加以駁誥。《順天時報》的短評 誣稱李大釗不肯“自甘淡泊”而“作非分之想”,結(jié)果“擔(dān)了許多的罪名,有何值得” 。李大釗與周作人曾是《新青年》的同人,周作人對李大釗被害自有一種痛悼之情,而 見烈士遭致污蔑,便有一股怒不可遏之氣了:“《順天時報》上也登載過李大釗身后蕭 條等新聞,但那篇短評上又有‘如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等語。我要請問日本人 :你何以知道他是不肯自甘淡泊,是作非分之想?如自己報上的記載是事實,那么身后 蕭條是淡泊的證據(jù),還是不甘淡泊的證據(jù)呢?日本人的漢字新聞造謠鼓煽是其長技,但 像這樣明顯的胡說霸道,可以說是少見的了”,“日本人不妨用本國的文字去發(fā)表謬論 或非謬論,但決用不著他們用了漢文寫出來教訓(xùn)我們”(注:周作人:《日本人的好意 》,《語絲》第131期。)。《日本人的好意》以嚴(yán)辭厲句直逼對象,體現(xiàn)出周作人作為 斗士一面的精神。論議的“無所顧忌”正是“語絲體”特色的寫照。周作人后來成為漢 奸為人不齒,但周作人也曾抨擊過日人的悖謬。
《語絲》作家對于專制的抗?fàn)帲顬榭扇牲c的篇章,是他們對于“三?一八”慘案 制造者段祺瑞執(zhí)政府暴行的批判。這是《語絲》作家的一次集體出場,張定璜的《檄告 國民軍》、林語堂的《悼劉和珍楊德群女士》、魯迅的《紀(jì)念劉和珍君》、《無花的薔 薇之二》、周作人的《關(guān)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新中國的女子》、朱自清的《執(zhí)政 府大屠殺記》,魯迅的《紀(jì)念劉和珍君》,陸晶清的《從劉和珍說到女子學(xué)院》等大量 的文章,彰顯犧牲者的品行,揭露專制者的殘暴,具有很強(qiáng)的戰(zhàn)斗性。在這些文章中, 作者與被害的烈士一樣表現(xiàn)得無所畏懼,把批判的矛頭直接指向?qū)V篇毑谜摺埗ㄨ?截了當(dāng)?shù)攸c出戕害年輕生命的兇手:“在首都里,在光天化日之下……潔白的青年飲彈 而死了,死在堂堂的中華民國國務(wù)院前面,死在中華民國政府的衛(wèi)兵手里!”林語堂指 罵統(tǒng)治者是“亡國官僚瘟國大夫”,朱自清則以激語表達(dá)一腔憤懣:“我們國民有此無 臉的政府,已何以自容于世界!——這正是世界的恥辱呀!”歷史事件本身似乎已被塵封 ,但《語絲》作家的這些文字所見證的一代知識分子守望正義批判邪惡的精神卻依然風(fēng) 采照人。
《語絲》雜感中,旨在進(jìn)行文化批評的占了多數(shù)。《語絲》原是一班文化人的天下。 文化人對于各類文化事象有一種職業(yè)性的敏感,他們所奉行的自由言說的主張,使他們 得以比較從容隨意地論說文化人物、文化事件。這足以體現(xiàn)出他們對文化的某種關(guān)懷精 神,而這種關(guān)懷對于當(dāng)時的文化界(知識界)來說是十分需要的。正如在場者林語堂所說 的那樣:“記得民國六七年,《新青年》時代,我們的知識界是一致革命的,不打算荏 苒十載,今日已是民國十五年,不但思想革命沒有弄成功,知識界方面自己軟了腿,一 方面講革命,一方面正在與舊勢力妥洽。”(注:林語堂:《討狗檄文》,收入《<語絲 >作品選》,人民文學(xué)出版社1988年版。)由這個背景可以看出,《語絲》同人對于文化 批評的執(zhí)著,是因為這些《新青年》時代的前衛(wèi)或受其時新思想洗禮過的知識者有意于 以推進(jìn)思想革命為己任。因此,文化批評類的雜感其基本主題就是對封建舊文化、舊道 德及其相關(guān)者的批判。
對封建文化的批判,在魯迅這里是一如既往的。發(fā)表在《語絲》創(chuàng)刊號的《論雷峰塔 的倒掉》是一雜文名篇。魯迅由雷峰塔倒掉的新聞?wù)归_聯(lián)想議論。作者巧妙地從民間傳 說的演繹中,提取出反對專制,倡揚(yáng)反抗的精神。《看鏡有感》一篇由“翻衣箱,翻出 幾面古銅鏡子來”的瑣事起興,從“海馬葡萄鏡”的由來,“遙想漢人多少閎放”的開 放求新的氣魄。魯迅以“鏡”作為回溯歷史的線索,展開歷史的情境并與現(xiàn)實的某些景 況相對照,其顯見的用意在于批評文化保守主義。當(dāng)時文化上的復(fù)古傾向觸目皆是。“ 許多雅人,連記年月也必是甲子,怕用民國紀(jì)元”。而在魯迅看來,“要進(jìn)步或不退步 ,總須時時自出新裁,至少也必取材異域,倘若各種顧忌,各種小心,各種嘮叨,這么 做即違了祖宗,那么做又像了夷狄,終生惴惴如在薄冰上,發(fā)抖尚且來不及,怎么會做 出好東西來。所以事實上,‘今不如古’者,正因為有許多嘮叨著‘今不如古’的諸位 先生們之故”。魯迅認(rèn)為應(yīng)該“放開度量,大膽地,無畏地,將新文化盡量地吸收”( 注:魯迅:《看鏡有感》,《語絲》第16期。)。
四
我們指認(rèn)《語絲》為現(xiàn)代散文文體自覺的代碼,這不僅在于《語絲》散文展呈了主體 自主自由的現(xiàn)代性的精神內(nèi)質(zhì),而且也因為《語絲》完整地建構(gòu)了現(xiàn)代散文的格局。《 新青年》時期散文以議論體為主,這大約是應(yīng)思想革命之運(yùn)而生的一種特點。現(xiàn)代散文 由議論體向敘事體、抒情體的發(fā)展,并形成多體共榮的局面,則表示著這一文類在現(xiàn)代 的完形。胡適在《五十年來中國之文學(xué)》中論及五四散文:“白話散文很進(jìn)步了,長篇 議論文的進(jìn)步,那是顯而易見的,可以不論。這幾年來,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發(fā)展,乃 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這一類的小品,用平淡的談話,包藏著深刻的意味, 有時很像笨拙,其實卻是滑稽。這一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 的迷信了。”(注:《胡適文存》二集卷二,上海亞東圖書館1924年版。)胡適對新文學(xué) 運(yùn)動中散文的成績給予了很高的評價,這大體上是符合文學(xué)史的實際情形的。周作人的 “美文”觀念及其實踐,在當(dāng)時獲得了初步的成功。但是我們可以注意到胡適的評價是 講究分寸的。“這一作品的成功,就可徹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話’的迷信了”這一 句使用的是假設(shè)性語式,“就可徹底打破”這一種委婉表達(dá),意味著當(dāng)時的美文(1922 年)已有卓然可觀的成績,但尚未獲得完全的成功。《語絲》的時代是一個美文的時代 ,許多報刊倡導(dǎo)這一體式,如《晨報副刊》、《小說月報》、《現(xiàn)代評論》等,而《語 絲》無疑是一個展示美文風(fēng)景的重鎮(zhèn)。
作為《語絲》主持者之一的周作人,是最早生成現(xiàn)代散文文體意識的。他于1921年6月 在《晨報副刊》發(fā)表了《美文》,首次將散文中“記述的,是藝術(shù)性的”一類的作品, 命名為“美文”,認(rèn)為這種美文“可以分出敘事與抒情,但也很多兩者夾雜的”。周作 人強(qiáng)調(diào)美文“須用自己的文句與思想”。由此可見,他已從文體之形之心兩端說明美文 的體征內(nèi)質(zhì)。這對后來散文作家文體意識的普遍自覺具有重要的啟發(fā)意義。在現(xiàn)代散文 文體的格局中,周氏兄弟是“雙柱”,分別代表了雜文(雜感)與美文創(chuàng)作的最高成就。 在《語絲》這里,是以雜感為主的,但美文類的寫作也頗受重視。魯迅《秋夜》等自稱 為“散文詩”的20多篇作品發(fā)表在《語絲》上,后來結(jié)集為《野草》。周作人不僅是美 文的倡導(dǎo)者,而且更是這一文類的實踐者。刊發(fā)于《語絲》的《烏篷船》、《喝茶》、 《鳥聲》等名篇,成為其美文創(chuàng)作的重要代表作。作為一方美文的天地,《語絲》同人 在大量寫作雜感的同時,也發(fā)表了很多敘事抒情性的散文,祖正的《山中雜記》、江紹 原的《小品》、綠漪的《我們的秋天》、繆崇群的《南行雜記》等,以連載的形式刊發(fā) 。韋素園有《春雨》,鐘敬文有《太湖游記》,向辰有《捕螢》,蹇先艾有《雨夕》, 章衣萍有《第一個戀人》、《暮春》、《夜夜曲》,評梅有《雪夜》,許欽文有《在湖 濱》、《石榴花下》,川島有《溪邊漫筆》等,一時美文的寫作蔚然可觀。
雜文與美文的寫作表示著現(xiàn)代散文作家精神存在的兩種不同的向度與形態(tài)。散文作家 之被冠于“現(xiàn)代”,主要在于他們成為思想獨立精神放逸的主體,其為文不是為了代言 釋道,而是為了寫心傾吐。他們寫作雜感,部分地體現(xiàn)著作為人文知識分子的本性,在 將寫作與社會的關(guān)聯(lián)中履行社會職志,實現(xiàn)自身存在的價值。他們寫作美文,則又體現(xiàn) 著他們作為文化人、知識者對本我生命的關(guān)注、尊重與某種意義上的自我肯定與欣賞。 這兩種存在并不矛盾,它們往往能在主體的寫作中得到統(tǒng)一。這種統(tǒng)一歸源于精神的獨 立自主,至于寫作形式的選擇,是雜感還是美文,這主要由作者寫作的社會需要與個人 趣味所決定。一般來說,選擇雜感,就意味著選擇對社會、對文化的批判;選擇美文, 則意味著對更多地通過對作家個體生活際遇情感流變等記敘,對自然的人文的風(fēng)情的描 寫獲得一種心靈的自適或自省。批判與自適都是需要的,魯迅主張雜文,但也寫美文, 周作人鐘情美文,而又不棄論議之好。這種情況,在《語絲》周刊上也得到了統(tǒng)一。這 種統(tǒng)一體現(xiàn)出《語絲》的兼容性。正是這樣的兼容,才成就了它的豐富。
《語絲》的美文有著自己的旨趣,是一種偏重于個人的文學(xué),其題材較多地關(guān)乎知識 者個人化的生活領(lǐng)域。與雜感的浮躁凌厲比,這里的美文有一種濃淡相宜的中和與雅爾 舒然的從容。這是作家將生活藝術(shù)化所得的一種成果。閑適是其中最為重要的滋味。周 作人的《喝茶》、《烏篷船》等可以視為美文的標(biāo)本,其取材題旨與現(xiàn)實社會保持著間 距,親近的是一種尋常的但具有文化味的生活。《喝茶》“所想說的,只是我個人的很 平常的喝茶罷了”。其中所寫是作者經(jīng)驗中的“茶道”:“我的所謂喝茶,卻是在喝清 茶,在賞鑒其色與香與葉,意未必在止渴,自然更不在果腹了。”“喝茶當(dāng)于瓦房紙窗 之下,清泉綠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飲,得半日之閑,可抵十年的塵夢” (注:《語絲》第7期。)。這種“茶道”中反映的是文化人的一種閑情逸致。《烏篷船 》一篇其精神與《喝茶》相通,這并不只是寫出一種文化味很濃的鄉(xiāng)俗,作者對烏蓬船 的敘寫實則反映出他對放達(dá)由性的自然境界的神往:“在船上行動自如,要看就看,要 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覺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樂法。天人合一,在人與自然和諧 的交響中,獲得一種生命的趣味:夜間睡在艙中,聽水聲櫓聲,來往船只的招呼聲,以 及鄉(xiāng)間的犬吠雞鳴,也都很有意思。”(注:《語絲》第107期。)這種交響不啻是一種 天籟。
論及這樣的美文,往往有內(nèi)容空疏,沒有多少社會意義之類的評語。這樣的評價差不 多是反散文的。散文作為反映作者精神存在的一種方式,對主體個人性的呈現(xiàn)是頗為重 要的。主體的個人性既展示在主體對現(xiàn)實社會觀察思考方面,同時也體現(xiàn)在他對自身存 在的關(guān)注與體認(rèn)方面。如果說雜文更多地給人以深刻的思想啟發(fā),那么美文更多地給人 以閑適的藝術(shù)享受。將美文置于現(xiàn)代散文演進(jìn)的歷程中觀察,我們更可發(fā)現(xiàn)這種“寫法 也有漂亮和縝密的”體式,顯示著“對于舊文學(xué)的示威”的價值,“在表示舊文學(xué)之自 以為特長者,白話文學(xué)也并非做不到”。美文的重要意義在于它以藝術(shù)的形制反映著散 文作家豐富心靈世界中的一個重要的存在。“漂亮”的形態(tài),顯示著美文無限的藝術(shù)魅 力。
《語絲》上的美文,作為一種藝術(shù)的文學(xué),它們最值得我們品賞的是作者善于運(yùn)用多 種筆調(diào)創(chuàng)造出各色的意境、情景。這種情景或意境有著一種極強(qiáng)的審美召喚力,令人留 連陶醉。周作人的《喝茶》、《烏篷船》的那種情景有這樣的魅力,鐘敬文的《太湖游 記》、石評梅的《雪夜》、徐祖正的《山中雜記》諸篇也各具心象相應(yīng)的意境。這是鐘 敬文筆下的黿頭渚的春景:
桃花方盛開,蔥綠若碧海,風(fēng)過時,樹聲洶涌如怒濤澎湃。渚上多奇石,突兀俯偃, 形態(tài)千般。我們在那里徘徊顧望,四面湖波,遠(yuǎn)與天鄰,太陽注射水面,銀光朗映,如 萬頃玻璃,又如一郊晴雪。(注:收入阿英編《現(xiàn)代十六家小品》,上海光明書局1935 年版。)
桃花,奇石,湖波,春陽,風(fēng)景如畫,令人心曠神怡。《雪夜》則呈現(xiàn)出“如夢似真 的藝術(shù)化的世界”。粉妝玉琢的街市,幽美清冷;“新栽的小松上,滿綴了如流蘇似的 雪花,一列一列遠(yuǎn)望去好像撐著白裙的舞女”。雪的世界伴奏著“悠遠(yuǎn)清靈的鐘聲”, 將作者的情思牽引得很長很長。這樣的文字顯示出的大約就是美文的風(fēng)致了。
美文著意將日常生活藝術(shù)化,以詩意洗滌庸常的鄙俗,營造一方作者自適的精神空間 。這樣的精神空間或表示與現(xiàn)實緊張的社會關(guān)系作消極對抗,是所謂“苦中作樂”之法 ;或體現(xiàn)散文作家稟具的一種自然無拘的心態(tài),美文成為現(xiàn)代散文作家放飛自我的彩色 的風(fēng)箏。
字庫未存字注釋:
@①原字左矢右蠖去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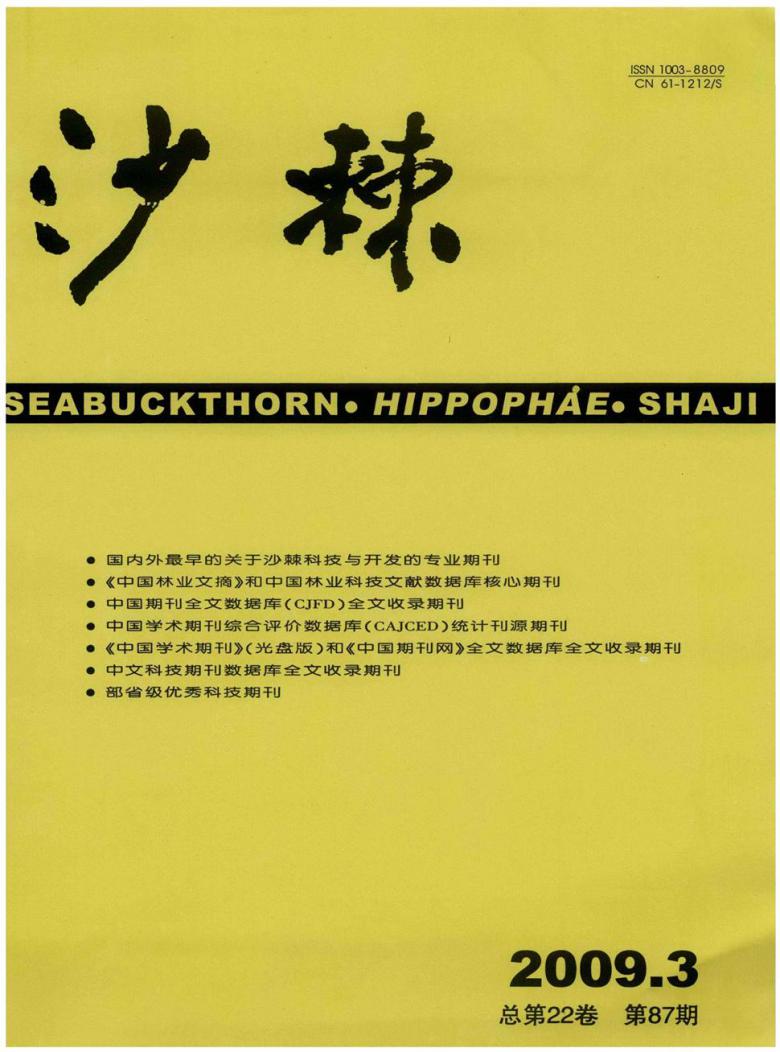
.jpg)
院學(xué)報.jpg)
科大學(xué)學(xué)報.jpg)
濟(jì)文匯.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