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中國古代詩文理論對書法創(chuàng)作的影響
戚榮金
論文關(guān)鍵詞:中國古代詩文理論書法創(chuàng)作中和緣情意境
論文摘要:中國古代詩文創(chuàng)作追求“中和之美”,強調(diào)“詩緣情”,注重意境的創(chuàng)造;中國書法創(chuàng)作則追求志氣平和、不激不厲,強調(diào)“書為心畫”、“達其性情”,中國古代詩文理論對書法創(chuàng)作的影響、滲透,使二者的審美精神和理念呈“同源”之勢。
任何一種藝術(shù)形式除按照自身的藝術(shù)規(guī)律發(fā)展外,還要受到其他藝術(shù)理論和創(chuàng)作實踐的影響。在中國古代藝術(shù)中,詩、書、畫三者的關(guān)系最為密切,它們都是在以儒、道、釋思想為主的哲學基礎(chǔ)和文化傳統(tǒng)的熏染之下形成的不同藝術(shù)門類,其審美精神和理念呈“同源”之勢。書與畫的淵源關(guān)系之密切自不待言,詩文理論對書法創(chuàng)作的影響也表現(xiàn)得十分突出。本文著重探討中國古代詩文理論中的一些重要觀點對書法創(chuàng)作的影響。
一、中和
“中和”是中國特有的傳統(tǒng)美學范疇和審美形態(tài),它涉及到各個藝術(shù)領(lǐng)域。《禮記·中庸》說:“喜怒哀樂之未發(fā)謂之中,發(fā)而皆中節(jié)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1](上冊P630)《左傳》曾記載了晏嬰對“和”的理解:“和如羹焉……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泄其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1](下冊P126)他們所說的“中”,就是事物自身矛盾雙方的互相依存和調(diào)和,“和”是矛盾雙方的互相交融、調(diào)和統(tǒng)一。可見,中國傳統(tǒng)的“中和”,既包括同一事物諸多因素的統(tǒng)一,又包括矛盾對立面的調(diào)和。孔子論詩樂也很重視“中和”之美,他在《論語》中說:“《關(guān)睢》樂而不淫,哀而不傷。”[1](上冊P275)這是他的中庸之道在文藝思想上的反映,這種思想直接導(dǎo)致了后來以“溫柔敦厚”為基本內(nèi)容的“詩教”的建立。“中和”廣泛而深厚的哲學內(nèi)涵,決定了它能被應(yīng)用于各個領(lǐng)域。“中和”之美是古代詩文的審美原則和審美追求。
書法創(chuàng)作則吸收了“中和”的思想,并發(fā)展成為最重要的創(chuàng)作原則。它要求書法家在創(chuàng)作時要“志氣和平,不激不厲”。唐代書法家孫過庭《書譜》中說:“數(shù)畫并布,各異其形,眾點齊列,為體互乖。一點成一字之規(guī),一字乃終篇之準。違而不犯,和而不同;留不常遲,遣不恒疾;帶燥方潤,將濃遂枯;泯規(guī)矩于方圓,遁鉤繩之曲直;乍顯乍晦,若行若藏。”[2](P59-60)“各異其形”追求的是對立統(tǒng)一,“眾點齊列”犯的是羅列之忌。因之,書法創(chuàng)作要在遲疾、燥潤、濃枯、顯晦、行藏的對立雙方之間做到“以他平他”,調(diào)和對立,不使任何一方過于突出。這是書法創(chuàng)作在用筆用墨上追求的“中和”之美。
章法結(jié)構(gòu)是書法創(chuàng)作要考慮的主要內(nèi)容,“中和”的理念對此也有重要的指導(dǎo)意義。書法作品的結(jié)構(gòu)美主要體現(xiàn)在漢字的筆畫組合和結(jié)構(gòu)形式上,正如劉綱紀先生所說:“書法的結(jié)構(gòu)之難,并不在機械地求得平衡對稱,而在從多樣的微妙的變化中求得平衡對稱。”[3](P270)這種平衡是一種動態(tài)的平衡,變化的平衡。清代書法理論家鄧石如說:“字畫疏處可使走馬,密處不使透風,常計白當黑,奇趣乃出。”[3](P278)劉熙載在《書概》中也說:“書之章法有大小,小如一字及數(shù)字,大如一行及數(shù)行、一幅及數(shù)幅,皆須有相避相形相呼相應(yīng)之妙。”[4](P271)這就是說,安排結(jié)構(gòu)要講疏密,恰當分布,有時讓字的筆畫左右伸展,突破行間空白,使之活起來;有時要把筆畫安排得有遠有近,有疏有密,黑白相間,參差不齊,使之具有生動活潑、亂中見整、整中有亂的藝術(shù)美,以追求結(jié)構(gòu)章法的“中和”之美。因此,“中和”理論影響了一大批優(yōu)秀書法家的創(chuàng)作,尤其是晉人書法,平和自然,含蓄委婉,剛?cè)嵯酀瑴匚男阊牛环Q為“中和”之美的典范。如天下第一行書《蘭亭序》,似“清風出袖,明月入懷”,被歷代書家奉為至善至美的法書寶典。當然,“中和”的原則在一定程度上也束縛了書法家藝術(shù)個性的發(fā)揮,限制了書法創(chuàng)作的表現(xiàn)領(lǐng)域。明清之際,隨著資本主義生產(chǎn)關(guān)系的萌芽,人們對思想自由和個性解放的追求,突破了儒家“溫柔敦厚”的傳統(tǒng)詩文理念,推崇“尚真求實”[5](P363)的文藝思想。這種思想同樣也影響了書法創(chuàng)作。明代晚期書畫家徐渭、清代康乾時期的“揚州八怪”等,他們的書法不遺余力地張揚個性,強烈地表現(xiàn)自我,無不受到當時的文藝思潮的影響。
二、緣情
中國古代詩文是主達情性的。《尚書·堯典》說:“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1](下冊218)孔穎達對“志”解釋為:“在己為情,情動為志,情志一也。”[6](P107)《詩大序》則認為:“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7](P75)這些詩論都肯定了“詩緣情”的特點。魏晉南北朝時期的陸機更明確地肯定了“情”在詩文創(chuàng)作中的作用,他在《文賦》中說:“詩緣情而綺靡。”[7](第一冊P171)劉勰在《文心雕龍》中指出:“綴文者情動而辭發(fā)”[7]。唐代的白居易在《與元九書》中則進一步鮮明地指出:“詩者,根情,苗言,華聲,實義”,“感人心者,莫先乎情”[7](第二冊P96)。唐以后凡重視詩文審美素質(zhì)的理論家都無一例外地肯定了情感在詩文創(chuàng)作中的地位與作用。
正是吸收了“詩緣情”的理論,書法創(chuàng)作才逐漸實現(xiàn)了由實用到藝術(shù)的發(fā)展。中國漢字在產(chǎn)生之初就已經(jīng)注意到了造字的情感問題,如人言為“信”,止戈為“武”,羊大為“美”等,都強烈地表現(xiàn)出人們內(nèi)在的思想情感和審美意識。就連象形文字“日、月、山、川、鳥、獸、蟲、魚”等,也都概括地描摹出客觀事物美的形象。即使非象形的文字也沒有失去形象性的特征,如魯迅所說:“今之文字,形聲轉(zhuǎn)多,而察其締構(gòu),什九以形象為本底”[8](P3)。這就是說非象形化的文字,其間架結(jié)構(gòu)乃至偏旁部首,仍有形象的因素,仍然同現(xiàn)實生活中的某些形象存在著聯(lián)系,同樣可以表達一種意象,使人產(chǎn)生一種美感。
作為抒情藝術(shù)的書法創(chuàng)作,其情感的抒發(fā)主要是由于書法家的內(nèi)在情緒同外界刺激發(fā)生共振和契合。這種情感的抒發(fā),一方面可以使人內(nèi)心積郁的情感通過書法創(chuàng)作得以渲泄,從而使心理情緒獲得平衡,精神得到陶冶;另一方面,書法家的情感變化也會使他的作品呈現(xiàn)出不同的風貌:“喜則氣通而字舒,怒則氣粗而字險,哀則氣郁而字斂,樂則氣平而字麗,情有輕重,則字之舒斂險麗,亦有淺深,變化無常。”[9]如唐代書法家顏真卿的《祭侄文稿》,這是他為追念在“安史之亂”中被殺害的侄兒季明所寫的祭文草稿。此稿為即興之作,從文稿的涂抹、推敲和修改,我們可以看出顏真卿的悲痛和沉吟。作品的章法從規(guī)整到凌亂,書體從行楷到狂草,這些變化映射出了作者“孤城圍逼,父陷子死,巢傾卵覆”的悲憤之情,表達了對安祿山叛亂的痛恨和對亡侄季明的深切懷念。而《流州帖》是顏真卿在獲悉兩處平叛取得勝利后寫的,帖上字跡流暢而又縱筆直下,一種欣喜若狂的心情,躍然紙上;《爭座位帖》則筆墨間透出怒氣;《中興頌》“宏偉發(fā)揚,狀其功能之盛”;《顏家廟碑》則“莊重篤實,見其承家之謹”[10](P169)。再如宋代文學家蘇軾被貶黃州后,面對茅屋、破灶、濕葦、野菜和寒食,百感交集,寫下了《黃州寒食帖》,把滿腹的哀怨、屈辱、激忿相互交織的復(fù)雜感情傾注于詩中。
同時又以錯綜變化的線條,勾畫出了他復(fù)雜的感情和痛苦的內(nèi)心世界。可以說,這些作品都無一例外地表明筆墨隨感情的起伏而跳動,表現(xiàn)了強烈的情感。詩文的抒情具體而直白,書法的抒情則抽象而含蓄。詩文的抒情主要通過言語對客觀事物的摹狀和主觀情感的直接抒發(fā)來實現(xiàn),而書法的抒情則更多的是通過抽象的符號和特殊的形式感來表達;詩文的抒情強調(diào)教化、感染,而書法則注重自娛即“自散懷抱”。書法家通常把書法創(chuàng)作當做一種抒發(fā)情感、修身養(yǎng)性的手段,而忽略了書法作為藝術(shù)對人的感染作用。盡管書法的抒情同詩文的抒情在方式方法上存在差異,但在通過一種藝術(shù)手段表達作者的主觀情感這一點上,書法創(chuàng)作與詩文創(chuàng)作二者是相互滲透和影響的。 三、意境
意境是中國古代詩文理論中一個重要的美學概念,它來源于魏晉南北朝時期的漢譯佛典。佛教的理論強調(diào)人的心理與精神作用,佛教徒竭力超脫一切物質(zhì)空間而回歸自己的心靈空間。于是漢譯經(jīng)者便借用表現(xiàn)地理空間、國土疆域的“境”或“境界”一詞來表述這種心靈空間和精神世界,尤其是表現(xiàn)佛理、佛法所能引導(dǎo)人進入的冥想的極致。“境”或“境界”的概念后來逐漸被引入詩文理論,它是“指作者的主觀情意與客觀物境互相交融而形成的藝術(shù)境界”[11](P270)。而真正大力標舉意境,并且深入探討意境涵義的是清代的王國維,他不僅注意到詩人主觀情感的一面,同時又注意到客觀物境的一面,必須二者交融才能產(chǎn)生意境。他認為意境是由真景物和真感情兩者契合而成,造境和寫境都是主客觀交融的結(jié)果,從而建立了一個新的詩歌評論標準,豐富了中國詩歌理論。
從這些理論可以看出,詩文創(chuàng)造的意境,必須同時具備“情”和“景”,并使二者有機融合。與此相比,書法創(chuàng)作的意境,也是由書法家的主觀情意與客觀物象相互交融產(chǎn)生的。它主要通過抽象的點畫來創(chuàng)造一種美的形式,從總體上反映客觀事物的感性形象,同時又滲透了書法家的某些情感,以一種特有的藝術(shù)形式創(chuàng)造一種意境的美。
書法意境的創(chuàng)造,首先要求書法家進入一種虛靜的狀態(tài),東漢書法家蔡邕說:“夫書,先默坐靜思,隨意所適,言不出口,氣不盈息,沉密神采,如對至尊,則無不善矣。”[12](P6)王羲之也認為,“夫欲書者,先乾研墨,凝神靜思,預(yù)想字形大小、偃仰、平直、振動,令筋脈相連,意在筆先,然后作字。”[12](P26)清代周星蓮說:“神凝則象滋,無意而皆意,不法而皆法。”[12](P726)只有進入這種“虛靜”的狀態(tài),才能擺脫各種名利雜念的影響,以便充分馳騁自己的藝術(shù)想像,在構(gòu)思中形成最優(yōu)美的藝術(shù)意象。其次,書法意境的創(chuàng)造是書家通過對自然現(xiàn)實中的一些現(xiàn)象的觀察和體驗,在其作品中抽象地映射出一種美的意境,從而使欣賞者產(chǎn)生一種與客觀感性形象相應(yīng)的聯(lián)想。如意境莊嚴的作品可以表現(xiàn)博大的情懷,使人聯(lián)想到高山瀚海、危樓深宇、忠臣義士,如顏真卿的楷書《大唐中興頌》、漢隸《乙瑛碑》;意境秀雅的作品行筆活脫輕盈,線條圓潤飄逸,結(jié)體疏朗空靈,章法舒斂自如,使人想到藍天白云、小橋流水、簪花仕女,如王羲之《蘭亭序》、褚遂良的楷書;意境粗獷的作品運筆奔放,結(jié)體開張,章法恣肆,動感強烈,使人聯(lián)想到迅雷驟雨、龍騰虎躍、駿馬馳奔,代表作如張旭《古詩四帖》、漢《石門銘》等等。我們欣賞王羲之《蘭亭序》時,總是給人一種平和自然的美感,這種美感又引導(dǎo)我們進一步體味詩人那詩酒集會的閑適、飄逸的情致,這種感受既不全是《蘭亭序》的作品本身,也不單是王羲之創(chuàng)作這一藝術(shù)作品時的情感,而是二者的結(jié)合、融徹后所生成的意蘊和情致,這就是書法藝術(shù)作品的意境所在。
從總體上看,中國古代詩文理論對書法創(chuàng)作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雖然這兩種藝術(shù)形式各有自己的發(fā)展規(guī)律,但從審美思想、創(chuàng)作方法和欣賞習慣上看,二者的交叉點很多。研究它們之間的互相關(guān)系,有助于我們把書法藝術(shù)放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藝術(shù)這個更為廣闊的空間去思考和探索,從而把握其創(chuàng)作規(guī)律,促進書法藝術(shù)得到更快更好地發(fā)展。
[1] 四書五經(jīng)[M].長沙:岳麓書社,1991.
[2] 馮亦吾.書譜解說[M].北京:國際文化出版公司,1992.
[3] 劉綱紀.書法美學簡論[M].武漢:湖北人民出版社,1979.
[4] 田連波.美學原理新編[M].開封:河南大學出版社,1988.
[5] 王忠閣,孫宏典.中國近古文學思潮[M].北京: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2000.
[6] 孔穎達.春秋左傳正義[M].北京:中華書局,1980年影印本.
[7] 郭紹虞.中國歷代文論選[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8] 魯迅.漢文學史綱要[M].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73.
[9] 劉鳴.試論書法藝術(shù)的審美本質(zhì)[J].安陽師專學報,1999,(1):78-80.
[10] 鐘明善.中國書法史[M].石家莊:河北美術(shù)出版社,2001.
[11] 袁行霈.中國詩歌藝術(shù)研究[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1987.
[12] 華東師范大學古籍整理研究室.歷代書法論文選[C].上海:上海書畫出版社,1979.


.jpg)
.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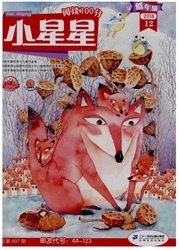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