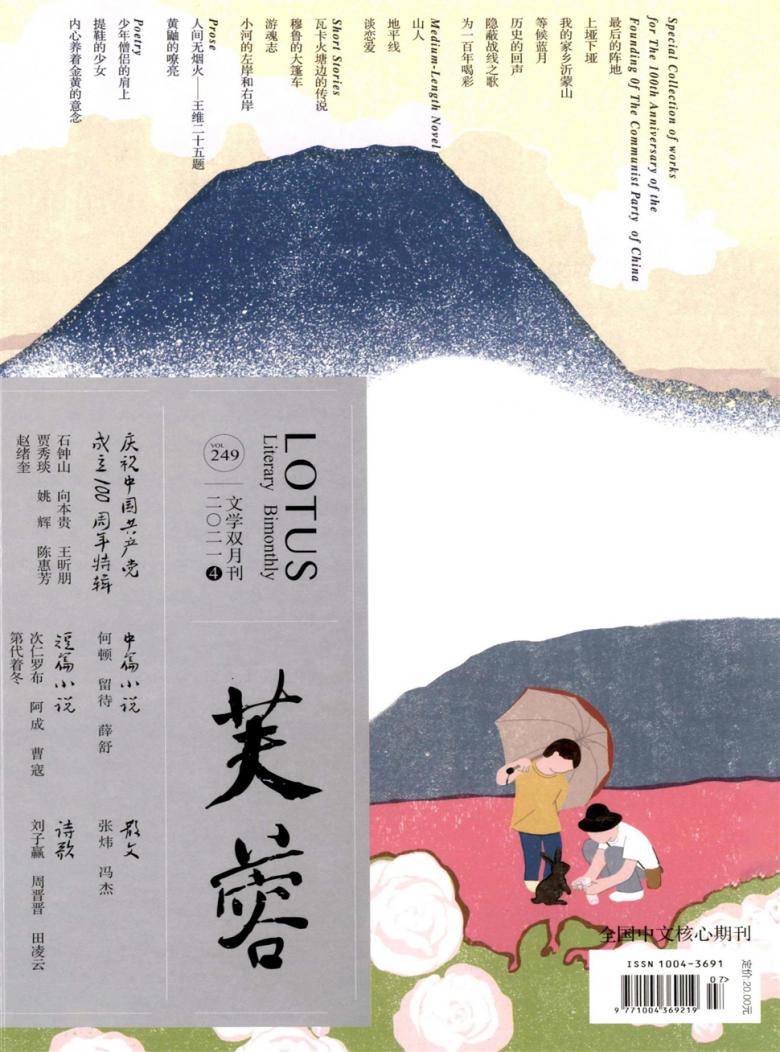《周易》的思維方式在中國畫發展中的特殊地位
李 巍
什么是“象”?《周易》又是通過怎么一套辦法來完成它的思維過程的呢?請看魏王弼的這樣一段話: “夫象者,出意者也。言者,明象者也。盡意,莫若象;盡象,莫若言。”(《易略例》)
王弼所說的“象”是《易傳》作者所賦予“意”的,通過爻辭所立的“言”以明其象,再由明“象”而嚴盡意”。從這個思維過程中,我們明顯看到“象”在其中的重要地位:立文字不是為了直接說事理而只是去說明“象”的。如乾卦以“龍”為象,借此來講述乾卦變化的道理。所用“取象之辭乃采取一種事物以為人事之象征,而指示休咎也,其內容較簡單者,近于詩歌中之比興。”(《周易古經今注》第49頁,高亨著,中華書局1984年3月版)即通過外物,景物來抒發、寄托、象征、表達觀念(“情”、“志”),使外物不再是自在事物的自身,而成為融合一定理解和想象后的客觀形象——“象”。這種思維形式以其理性的特點為中國傳統哲學與藝術的思維方式開出了先河。獨樹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中國書畫就是沿著這條道路走了幾千年之久。這里,我引用一段我們中國書畫家常說的一段話:“可以剛柔賅其情,動靜括其態。象之剛者,如龍威虎振’,松聳峰危是也。象之柔者,如鳥散萍開,柳舒花於是也。象之動者,如飄風忽起,驚鳥乍飛是也。象之靜者,如葉里紅花,云中白日是也。……掘絕俗念,凝神靜思,剛柔之情,動靜之態,得于心、應于手、發于毫、著于紙。”話中所說的“象”,它既不是外界事物的直接模擬,也不是主觀情緒的任意發揮。這種既非概念所能窮盡又非認識所能囊括的取象思維方式明顯是《周易》思維方式的繼承和發展,其本身具有很大聯想余地。由此我們可以看出,《周易》的內涵不確定的帶有模糊性的思維方式對藝術的發展較之哲學發展要顯得更有意義。
二
中國繪畫在世界繪畫史中,之所以與眾不同地獨立發展,其主客交融、主客合一的藝術主張不能不說是主要原因之一。以《周易》所建立起來的天人合一思想成了影響中國繪畫發展的哲學理論依據。
“《易》之為書也,廣大悉備,有天道焉,有人道焉,有地道焉,兼三才而兩之,故六。六者非它也,三才之道也。”(《系辭》) 作為世界觀的理論形式——哲學來講,大部分哲學派別對宇宙研究上,一般都是從整體出發的。然而在研究中把人和自然界看作一個互相對應的有機整體,并在這個整體中確定人的位置則不見于其它學派,即所謂六爻寓三才之道(天、人、地)是中國哲學,也就是《周易》所獨有的;經過幾千年的發展,其思想廣為中國務家學振吸收發展,孟子、莊子從不同角度發展了這種觀點。到宋明時期這種思想占據了主導地位。
人在考慮自身于天地之間的位置時,怎樣來校正自己‘的實踐呢?“與天地相似,故不違。知周乎萬物而道濟天下,故不過。旁行而不流,樂天知命,故不憂。”(《系辭》)“不違”、“不過”、“不流”是我們置身天地間行動約束的尺度。也只有順天‘應時,使人的思想和行為與自然界固有的規律同步發展,才能獲得人的真實存在。‘在這里我想重復一下,1957年8月間在墨西哥召開的《禪學與精神分析研討會》上日本禪學大師鈴木大拙發言中所舉的一個生動有趣的例子(文另錄)。莊子在《秋水》中說: “何謂天?何謂人?北海若曰::‘牛馬·四足,是謂天;落馬首,穿牛鼻,是謂人’。故曰:無以人滅天。” 按莊子的理解,天(客觀世界)是“牛馬四足”的自然生成的形態;而“人”則是“落馬首,穿牛鼻”的強加于自然的行為。這種有意識的活動、思慮、打算是對“道”的損害。《易傳》中提出“無思也,無為也,寂然不動。”為生活在天地間的“絕對自由”、“獨立自足”的“人”塑造了最初的原型,這也正是中國哲學家、藝術家在幾千年中所逐漸完善的中國理想的人格最初的外在化。由魏晉興起至宋明完成的在世界上有廣泛影響的中國文人畫,其所標榜的“簡”、“雅”、“拙”、“淡”、“奇”。“淡”的繪畫軌范的中心,就是出于這種哲學基礎。在中國畫“形”與“神”,“情”與“理”,“法”與“化”、“筆”與“墨”長期的討論中,“淡”是畫家、理論家所共同遵循的原則。“淡”就是順其自然,達到人與物化,物我為一的境界;正如清代胡琪在評明末中國山水畫大師石濤時說的:“世之知清湘(石濤)者,見其筆墨之高之古之離奇之創獲,以為新辟蠶叢,而不知其蕭然之極,無思也,無為也。”
中國繪畫在長期的發展過程中,從色彩豐富的青綠山水畫到否定色彩的水墨畫;從重視“形似”的院體畫到“似與不似之間”的文人畫;從效法天地陰陽的筆墨追求到“運墨如已成,操筆如無為”(《石濤畫語錄》)的筆不筆,墨不墨的自由揮灑境界,無一不是在追求著一個“淡”字。洗心退藏的,心態,將自我納入天地運行自然合順中,不帶任何后天“物欲”的心境在中國書畫作品中充分體現出來。難怪有人說:“中國書畫家多長壽者。”這種“寂然不動”的靜的心境是近代科學所證實為人生長壽的主要秘訣,中國書畫和中國書畫家皆得益于此,這也是當今世界由于物質發達而帶來的煩躁、不安的西方朋友,更多的人開始傾心于中國哲學和中國書畫的原因所在。
三
受著中國哲學深刻影響的中國藝術,所重視的“不是認識的模擬,而是情感的感受,……中國美學的著眼點更多的不是對象、實質、實體,而是功能、關系、韻律。從‘陰陽’、‘和同’到氣勢、韻味,中國古典美學的范,疇,·規律和原則大都是功能性的。它們作為矛盾結構,強調得更多的是對立面之間的滲透與協調,而不是對立面的排斥與沖突。作為反映,強調得更多的是內在生命意興的表達,而不在模擬的忠實、再現的可信”。(李澤厚《美的歷程》)使得中國繪畫走著與西方繪畫迥然不伺的實踐道路;因為中國確實存在獨立“內在生命意 興的表達”的特有的形式一書法。宋元以后,由于身兼哲學家、文學家、書法家的文人涉足于繪畫,中國畫也為之一變,書畫合一,圖字兼重使獨特的中國繪畫更具風采。
對藝術創作來說,在“如何表現”和“表現什么”這兩者當中,前者似乎顯得更為重要,它的美學價值不在于它所表達的“內容”,而在于它的表達“方式”。中國畫正是這樣舶。“松”、“竹”、“梅”、“蘭”是中國畫家喜歡選用的題材,而且歷久不衰,這在世界美術史中恐怕是絕無僅有的。其中主要原因可能要歸結前面所提到的“內在生命意興的表達”上了。這正是中國畫家借用某種內容(松、竹、梅、蘭)來發揮其獨立表現手段(書法》來完成自己的藝術創作。如元代畫家趙孟頫所說“石如飛白木如籀,寫竹還應八法通。”中國畫家在完成自己作品時多不稱之謂“畫”,而稱之為“寫”,其道理是不言自明的。
中國論述筆法的著作汗牛充棟,不能盡述,這里可舉漢代書家蔡邕一段話: “書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陰陽生焉。陰陽既生,形氣立矣。” 這段話說書法始于自然,取自然之象,效仿陰陽之性,剛柔之態,交錯變化以生無窮之形。明確地講出所說的“筆法”正是《周易》陰陽變化亦即矛盾變化的道理在書法中的運用。
《說卦》云: “觀變于陰陌而立卦,發揮于剛柔而生爻,和順于道德而理于義,窮理盡性以致命。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將以順性命之理;是以立天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故《易》六畫而成卦,分剛分陽,迭用柔剛,故《易》六位而成章。” 剛柔變化之理是中國書畫中筆墨的主要依據,我們常說:“書法有二,一曰疾,二曰澀。得疾澀二法,書妙盡矣。”
上面這些話中,有兩點必須注意。一是筆法中要陰陽(剛、柔);二是迭柔剛而成章。常聽有人說:“書法、繪畫要有筆力,要做到‘力能扛鼎’,‘力透紙背”等等。這里所說的“力”,其實只是一種陽剛之力,它和我們所說“迭用剛柔”之“力”有著根本不同。中國書畫一向反對只有剛力的“火氣”、“霸氣”。獨陰不長,獨陽不生,於是中國書畫中提出“棉里針”的柔中帶剛的最高要求,我們在較成熟的畫家作品中處處可以看到這種筆墨體現的。剛柔迭用的第二個意思,是每一幅成功的中國書畫作品中,大從滿幅小至一筆都要求有陰陽對比和陰陽的統一和諧,這往往是通過剛、柔,虛、實,方、圓,濃、淡,枯’、濕,開、合,平、奇等等諸因素,在滿幅畫中多層次“迭用”來完成的。簡單到可以用“陰”、“陽”二字;復雜到不可能盡述。歷代畫家以此獲得成功者實不乏其人。說小到一筆中也要講“陰、陽”,這也是西方所沒有的。我們中國書畫在最基礎單位的一個“點”時,也要有“落、起、走、住、疊、圓、回、藏” 八種剛柔不同的運筆之法,不可輕率一點了事。我們再來討論一下迭用剛柔而成章的問題(即《說卦》中“故易之六位而成章”),知道筆墨分剛柔是書畫家最基礎的知識,不是最終的目的;通過剛柔變化取得筆墨和諧將“內在生命意興的表達”得以陳述才是藝術家的使命。石濤在他的《畫語錄》中說:“夫畫,天地變通之大法也,山川形勢之精英也,古今造物之陶冶也,陰陽氣度之流行也,借筆墨以寫天地萬物而陶泳乎我也。”《周易》古經中以爻畫的形式組成八卦及其六十四.卦,在排列的結構不同中所出現的形與質的變異,來揭示宇宙萬物的變化。王弼說:“夫爻者何也?言乎變者也。”(《易略例》)
《周易》講陰由二氣交合為生成萬物的開端,也是書畫家創造出凈化了的筆墨審美趣味和理想。那么,創造這樣筆墨是否需要什么條件呢?小畜,是一陰與五陽的卦,它表示出陰弱陽盛難以交合,顯出一種不平衡。陰欲離去,陽則止陰而積畜,稱卦名《小畜》(畜,止也。)小畜的卦義,既為陽止陰使之不離去;又為一朗積畜自己的力量以逐漸達到與五陽平衡,實現對立相合而統一。在卦的《彖傳》中說廣密云不雨,尚往也。自我西郊,施未行也。”開始時,因陰陽力量不平衡難以相聚合呻陽氣往上升,不能與陰氣凝結而成雨。于是風將云“啟我西郊”吹向東,云雖密而時雨不至,萬物也就不能光大生息。后經初、二、三、四、五、上六爻的發展變化到達一卦終了時,陰氣畜而達到與陽氣平衡,實現了對立面的中和統一,二氣便凝結成雨,故上六云:“既雨既處”。從這一卦例看,《周易》通過卦爻的變化闡述陰陽二氣綱組交合的道理。所謂聚則生,離則死。《乾 彖》說:“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乃‘利貞”。;是我們的先哲在錯綜復雜的世界中所找到解決問題的根本方法。是我們賴以生存的世界最穩定的因素,也是中國丹青家苦思冥想的問題所在。
被稱為“群經之首”的《周易》對中國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的影響,以及對中國乃至東方文化形成所起的作用,愈來愈多地被人們所認識。在中國,從歷代和當代大量的書畫作品中,所傳留和感染著人們的思想、情感、觀念、意緒和中華民族幾千年來所形成的、心態一拍即合,正好表明了積淀在和體現這些作品中的情理結構,與今天的中國人的心理結構是相呼應的同構關系。因此,就不能忽視塑造這一偉大民族和其文化形成過程中的哲學,特別是《周易》的作用,這不單是一個歷史課題,本身具有鮮明的現實意義。本文只能是一個中國畫家在回顧這些古跡斑斑的歷史印痕中,對中國繪畫與《周易》的關系所做的一些鳳毛鱗爪的論述,請各位才華橫溢的思想家給以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