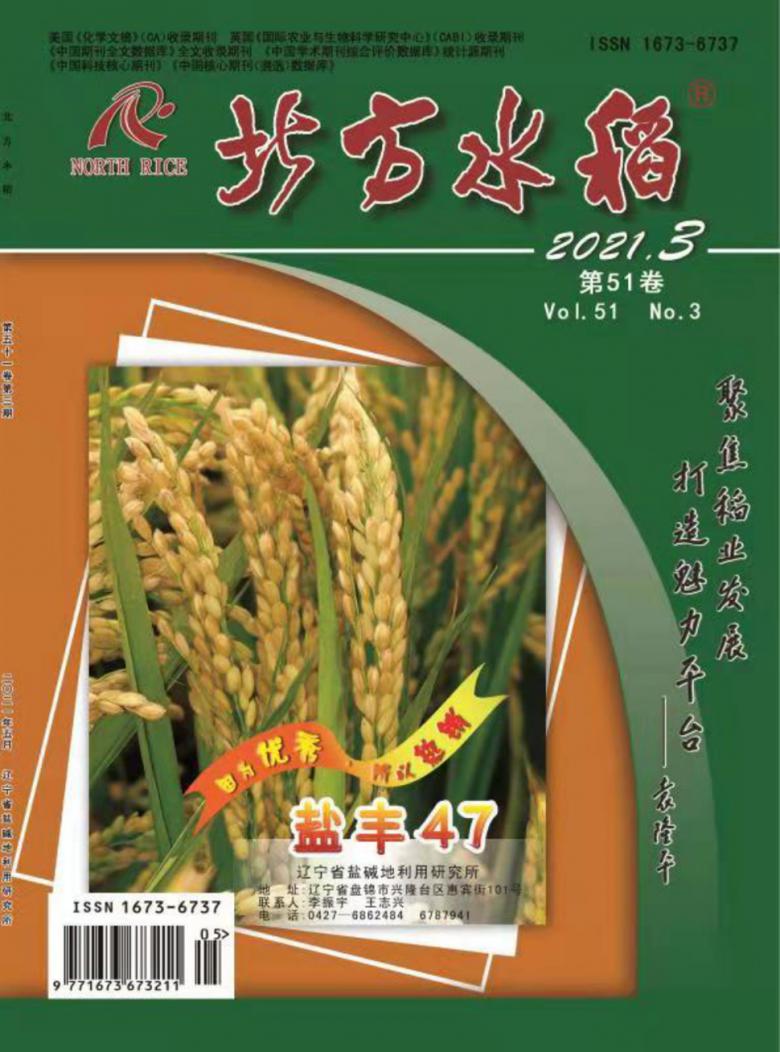關于油畫民族化與油畫民族性
羅石涌
20 世紀初,油畫的傳入給中國傳統的美術教育和傳統繪畫帶來了巨大的沖擊,出現了西歐學院制的畫室教學模式,并在當時引發了“油畫熱”。在具體的創作實踐中,為西方油畫新奇的藝術手法所吸引、所陶醉,長久的閉關鎖國下的中國人情不自禁地進行了借鑒與摹仿。借鑒、學習中,藝術表現力在不斷提高,伴隨而至的是如何準確闡釋中國文人自我身份——即油畫民族化成為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
油畫源于1 4 世紀的歐洲,為了追求文藝復興時寫實與再現的藝術理想,建立了一系列的繪畫法則和手法,形成了比較嚴密、完善的繪畫程序。隨后經歷了古典、近代、現代幾個時期,表現出不同時代的藝術思想和面貌。油畫始終根植于西方文化土壤,在自身規律下不斷演進。到了20 世紀,油畫進入一個探索自身語言的階段。
明朝萬歷年間,意大利傳教士利瑪竇為代表的“西學東漸”運動,可看作是油畫進入中國的序曲。而天主教耶穌修士、畫家兼建筑家意大利人郎世寧,則是帶著西方文化傳統而將西方油畫傳輸到中國的代表人物。中國人主動學習西方油畫是在19世紀與20世紀之交。正是在這個時期,中國的大批留學生來到西方學習油畫,并把油畫從西方引進中國。中國對油畫的學習從形式開始,起初,為其畫面的逼真典雅所震驚,從而簡單模仿西方畫家的圖形,繼而,開始脫離表面模仿,關注畫面背后深層次的文化精神,再到融入本民族感情的創作。在油畫藝術民族化的理論道路上,劉海粟1923年在《石濤與后印象派》中就提出了“油畫民族化”問題。在實際操作方面,20 世紀初,李叔同、李鐵夫、陳抱一、徐悲鴻、林風眠、劉海粟、顏文梁、常書鴻、呂斯百、潘玉良等畫壇學子紛紛出國學習,并將歐洲油畫技法引入中國。劉海粟、徐悲鴻、林風眠更是中西藝術融合的具體的倡導者和身體力行者,稍晚的羅工柳、董希文等人仍繼續前人油畫民族化的事業。
面對油畫這個異域文化的產物,我們大多只能憑借自身的文化傳統、思維方式和所熟悉的知識構成去解讀,而在探索油畫民族化的道路上,中西方文化間的誤讀始終伴隨其中。兩種文化間的交流似乎存在著必然的誤讀。誤讀在《韋氏新世界大學詞典》中的解釋是,“錯誤地閱讀,尤其是錯誤的闡釋或理解”(阿格尼斯,《韋瓦新世界大學詞典》,遼寧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P212),也就是說誤讀是一種錯誤的闡釋行為。 薩義德在他的《東方學》中說:每一文化的發展和維護都需要一種與其相異質并且與其相競爭的另一個自我的存在,每一時代和社會都重新創造自己的他者,因此,自我身份或他者身份決非靜止的東西,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種人為建構的歷史、社會、學術和政治過程。文化間的傳播(文化間的誤讀)必定是雙向的,文化誤讀必將貫穿于文化傳播之中。
我們總是會按照自身的文化傳統、思維方式和自己所熟悉的一切去解讀另一種文化。兩種不同文化間,當以他者的眼光觀察另一種文化時,只是站在一種文化的外部進行觀察,此時,他者的眼光會起一種過濾網的作用, 篩選出符合自己口味的東西,他者文化只是自己的言說。油畫民族化過程中嘗試用本民族語言去解讀外域文化產物——油畫——即可看作是文化誤讀。誤讀分為有意和無意,在油畫民族化的過程中充滿了自覺或非自覺的誤讀,構成了中國油畫民族性的重要特征。
油畫藝術作為源于歐洲的繪畫藝術,正式進入中國不過百余年歷史。回顧歷史,我們可以看到,作為異域文化的油畫,它進入中國就是它逐漸“中國化”的過程。只是在不同的階段,出現自覺或“非自覺”的試驗。早期油畫家李毅士、王悅之,在創作中一直追求中國文化韻味。稍后的林風眠、徐悲鴻一輩,從題材、色彩、氣韻等不同角度與中國文化連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的60 年,是中國油畫藝術得到前所未有的發展的60 年,也是油畫藝術迅速本土化的60 年。在各種外來藝術樣式之中,油畫藝術的本土化十分突出。從上世紀50 年代開始,中國美術界對美術門類有了統一的分類方式。如:中國畫、油畫、版畫、宣傳畫等等。其中,很重要的一個改變就是以“油畫”代替了過去沿用的“西畫”。這一改變不僅在客觀上突出了這類繪畫的技法、材料特色,淡化了“西畫”的文化背景和它在藝術觀念上不同于一般本土藝術的特殊性,但更為深遠的影響是藝術觀念上的變化,減少了中國油畫的“洋腔洋調”,增加了油畫在中國美術中的影響和分量。
在長期的藝術實踐中, 中國的油畫家們也逐漸認識到, 油畫的“民族化”或“民族性”的主要體現不在形式, 而在內容, 在精神。這是中國油畫學人能動意識和主動誤讀得出的結果。如果光在形式上做文章, 不在精神實質上下功夫, 油畫就談不上有真正的“民族化”或“民族性”。所謂內容、精神, 是由藝術家對所描繪現實的理解深度及其具有的民族文化藝術修養所決定的, 這是屬于藝術家的主體精神及人格力量范疇的東西。有社會責任感和民族文化自豪感、并對民族文化藝術有造詣的油畫家筆下的創作,必然會有時代的烙印、個性的面貌, 也會含有民族的風采。
有學人指出:油畫民族化時期,數代學者、畫家擁有的民族夢成為中國油畫民族化建構的自覺意識的動因。康氏強調中國畫寫神棄形,“衰弊極矣”,“宜取歐畫寫形之精,內合中西,以補吾國之短”。引進新學伊始,藝術與藝術家的社會責任、藝術活動與國民教育、藝術與改造國民性,便與強國夢想聯系在一起。在屬于維新思潮與外來文化結合的資產階級新文化的新學堂美術教育模式中,教育家沖破門戶之見,實行中國特色的、中西并行的雙軌制。其實,這種遠見也為未來中國油畫的民族屬性提供了傳統文化的浸淫氛圍,為之后的中國油畫美學、帶有民族文化因子的技法論埋下了伏筆。
徐悲鴻于1919年來到法國巴黎學習西方美術,先后師事費拉孟、達仰等人,師承西方19世紀古典學院派寫實主義傳統和“科學法則”,借鑒諸如比例、位置、解剖、構圖等形式技法,使用中國傳統筆墨工具和技巧來改造明清的寫意畫,重形似,追求惟妙惟肖、神形兼備的藝術效果,排斥印象派及印象派以后的現代藝術。徐悲鴻帶著用油畫改造中國繪畫的目的出國學習,十分重視藝術創作的社會功用性,追求的是藝術為時代、為社會、為大眾人生服務的功能,具有強烈的現實意義,在其代表作品《田橫五百士》中,我們不難看出他所推崇的藝術為時代、為社會、為大眾人生服務的社會功能,而且這是符合當時特定歷史時期需求的。這算得上是一個主動的文化誤讀,而類似于這樣的誤讀,是中國油畫先行者們自覺不自覺的共同的選擇。通觀中國油畫的百年,在審視中華文明的地脈和文脈中,用傳統藝術視覺、模式滋養油畫創作,對外來藝術觀念、手法予以反省、選擇和深化,立足本土的歷史語境對本民族的命運、生存狀態、心理和靈魂的嬗變做出時代性關照,是中國油畫家在構建民族化的過程中不自覺的共同選擇。如今,中國油畫形成了中國藝術家夢寐以求的民族藝術文化多元生態,但它在覺醒中對藝術絕對精神的追求才剛剛起步。實際上,油畫民族化是體現民族精神、民族性內涵的藝術追求和藝術創造的過程,追尋油畫藝術的民族精神、民族靈魂,才是建構民族化油畫的自覺意識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