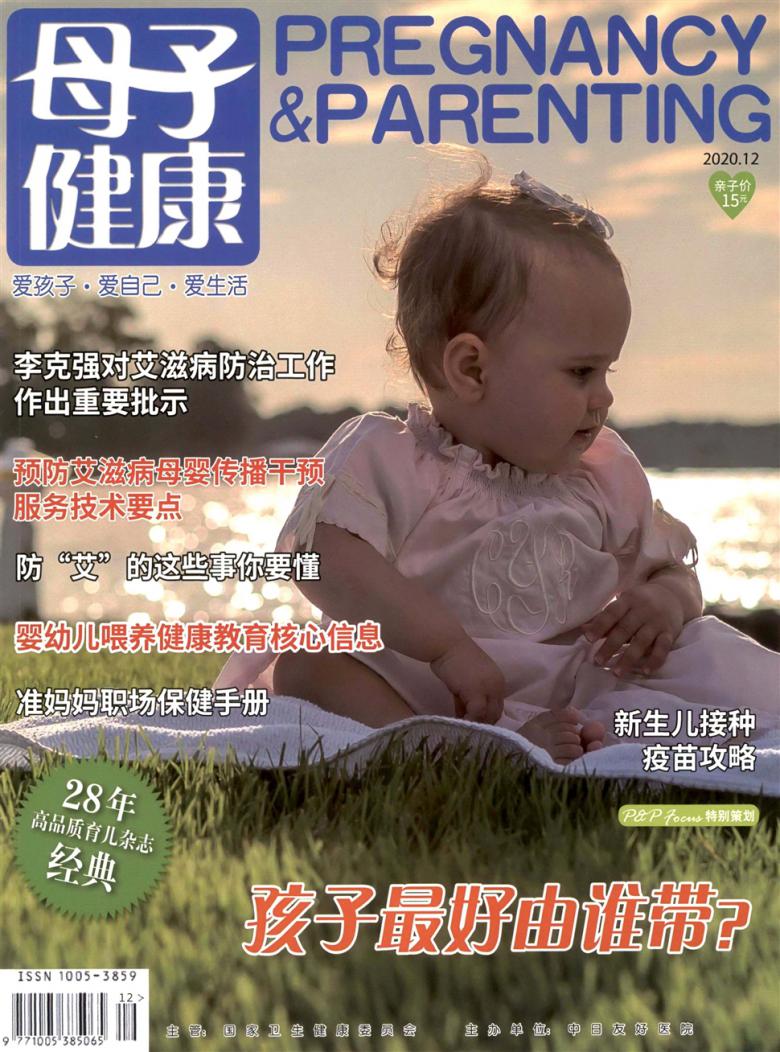油畫《開國大典》的成功與蒙難
艾中信
《開國大典》是新中國成立不久隨即和廣大群眾見面并博得廣泛稱譽的革命歷史畫。董希文精心設計的這件新穎的油畫也被藝術界人士所普遍推崇,成為他生平最重要的代表作,也是它的成名之作。董希文早已是我國著名的油畫家,但自從《開國大典》問世,這幅洋溢神州風采的油畫,使他在國際上也獲得了聲譽。
反映重大主題的繪畫作品,總是不同程度地維系于特定時代的,革命歷史畫更是直接和時代的命脈相聯系,和人們向往光明、進步的心態緊緊的扣在一起。人們熱情欣賞《開國大典》,正是因為它形象地揭示了光輝燦爛的中華民族新世紀,它不僅鼓舞了中國各民族人民自信心和自豪感,同時也震撼著世界人民的心坎,為新中國從此屹立宇東方而同心歡慶。人們喜愛《開國大典》無疑是受到了它的強烈藝術感染,沒有藝術性的繪畫是不可能令人矚目傾心的。然而,考察一件藝術品的成就如何,首先映著眼于它的社會效益,然后估計它的藝術價值,社會效益與藝術價值的統一是藝術品是否完美的標準。董希文的成功正在于藝術地完成了這一重大歷史任務,揭開了新中國美術史冊的第一篇章。
遺憾的是現在陳列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開國大典》并不是董希文的原作,而是由靳尚誼、趙域、閻振鐸根據原作同時參照印刷品臨摹的復制品。原作因在"文革"中蒙受不實之辭的連累,作了很大的改動,以后又不能恢復原貌,只能存放在中國革命博物館的畫庫里。為了紀念董希文完成這件重要創作近四十周年,現在我把所了解的有關情況作為美術資料記述下來,以供大家參考研究。
董希文接受這件創作任務時,正在北京郊區參加土改工作(1950年初)。他被調回城里后,遵照必須盡快完成的指示,只用了兩個多月的時間便交了卷。他雖然不習慣趕任務的創作方法,但以無比旺盛的創作熱情克服了許多困難,如在收集文字資料、形象素材進行構思的同時,還親自參與制作畫布(那時沒有現成的寬門面油畫布),以及籌劃做大型油畫的各種設施和所需的工具材料等。
決定《開國大典》的構圖,曾做了較長時間的推敲,在構草圖的階段,他身上經常揣著一張像明信片那樣大小畫在重磅卡片紙上的畫稿,凡遇到美術界及文藝界人士,便拿出來征求大家的意見。我就是從六郎莊土改工作隊回美院開會時第一次看到這張草圖的。草圖的設計很有創造性,他既根據1949年10月1日天安門城樓上舉行開國大典的莊重而喜慶的氣氛為基調,又不局限于再現當時的實際情況,采用了一種表現派和現實派相結合的手法,藝術處理很大膽。但是董希文當時并沒有把握,因為構圖上有幾個問題可能會引起爭議,甚至要被否定。他對我說:"能有機會創作這樣重大的革命歷史畫,是千年難逢的好運氣。可是照片和電影資料不合我的構思理想,只能用作參考。這幅草圖試圖把天安門廣場的群眾場面和城樓上的國家領導人聯系在一起,我認為不這樣不足以表現新中國成立這一歷史事件的宏偉氣概……這件作品必須集思廣益,否則難以畫好,限期又緊,我真有點著急呢!"董希文對油畫創作一向深思熟慮,同時又很虛心聽取別人的意見。在《開國大典》的創作過程中,特別在起草階段,更是虛懷若谷,不恥下問。據我所知這張畫在小卡片上的草圖,有不少北京美術界的同行曾經看到過,他也向一些年輕美術工作者征求過意見。一位很有威望的教授,在業務問題上表現出如此自覺的群眾觀點,是非常可貴而且值得稱道的。
這幅畫在不到十五平方英寸卡片紙上的草圖和原來定稿的構圖沒有多大出入,畫面的格局已經可以看出天安門廣場的開闊。人物的勾畫雖很簡單。但已經能看出主要國家領導人的身材特征。董希文所要征求的意見重點有兩個方面,首先是關于畫面上人物的布局安排。草圖上除了毛主席側身站立在畫面中間,其他的領導人都站在左邊大約三分之一的畫面上,形成左實右虛相差懸殊的布局。從一般的構圖規律來看,似乎失去了平衡。他特別擔心畫成大幅油畫以后,不知將是什么效果。其次是構圖上天安門城樓中間兩根廊柱之間的跨度大大放寬了,和實際的建筑構架也相差懸殊,可能會引起人們的非議。他所以要做這樣的構圖處理,都是為了顯出天安門廣場的明朗開闊,群眾場面的雄壯宏偉!使得國家領導人置身在這樣一個天地恢恢的氣氛中,從而體現出"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了!中國人民從此站立起來了!"的莊嚴宣言。
關于前一個問題,以為在主體性人物構圖上很少或者根本沒有見到過,驟然間大家感到很奇特。但是董希文告訴我,畫家中沒有提出異議,不少人還很喜歡。關于第二個問題,大多數同行認為很大膽,從表現天安門廣場和城樓的空間整體來看,加大兩柱之間的跨度是必須的,從視覺感受上說不畫右邊的柱子很暢快,畫上倒反累贅。李宗津當時在清華大學建筑系任課,他聽到梁思成說,這個構思是成功的。以精研古建筑的行家慧眼,梁思成指出,非但兩柱之間的跨度加大了好幾倍,而且從透視學的角度指出,畫面右方應該能看到的半邊柱子也沒有畫上去。他說,這在建筑學上是一個大錯誤,但是在繪畫藝術上確是一個大成功。他認為繪畫應該服從自身的藝術規律,對這樣大膽的構圖處理非常激賞。
傳聞董希文自己說過,他并沒有少畫一根柱子,只是少畫了一只燈籠。但梁思成指出這個問題時,董希文并未否認。那么他為什么又有這種說法呢?我想是因為少畫天安門城樓的一根柱子(有時說成"抽掉一根柱子"),容易引起牽強附會,有的人會覺得不吉利,所以想避免糾纏這個問題。何況人們從畫面上所得到的視象,只覺得天安門很寬暢亮堂,并沒有少了一根柱子的感覺。美術界的同行對這個問題之所以感到興趣,是因為董希文在這幅畫上創造性的運用了美術透視法則,他突破了什么時候都要用透視準繩去衡量的機械方法,使得構圖更符合繪畫空間造型的視覺效應。
另一個透視上的問題是畫面上的正陽門城樓坐落在畫面上垂直的子午線上,這和天安門城樓的方位稍有偏差。董希文對我說過,他要把正陽門城樓畫成正南北方向,也是為了使得廣場感到開闊。我覺得這個作用不大,但是他還是這樣畫了。《開國大典》上有這樣一些透視上的問題,可是愛挑毛病的透視學教授卻并沒有提出過非議,這也說明董希文的創作構思得到了大家的理解,而主要是畫面的感人效果說服力。如果畫面上看起來別扭,那是一定要責怪透視上的錯誤的。
為了1951年在印度舉辦新中國經濟文化建設展覽會,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和國家的領導人曾在當年五月審查一批美術作品。《開國大典》是其中的重要作品,審閱那天周揚帶著董希文同去,以便面陳創作情況,并準備回答詢問的問題。董希文心情十分激動。到中南海后周楊把他引見給毛主席,他卻老遠的站著退縮不前,直等到周揚高呼他的名字喚他前去,他才和毛主席握了手,感到無限溫暖、幸福。 毛澤東很欣賞《開國大典》,當時的談話就是對這件作品的確切評價。毛澤東一邊看畫,一邊說:"是大國,是中國。""我們的畫拿到國際間去,別人是比不過我們的,因為我們有獨特的民族形式"(引自1956年2月11日《光明日報》)。這個評價是高的,對董希文是最大的獎賞和鼓勵。毛澤東還說了一些風趣的話,他指著畫在周恩來旁邊、被朱德擋住只露出一點下巴和小胡子的董必武的臉說:你們看懂老被擠得差不多看不見了。附帶補一筆,畫面上的人物群體不是集體照相,既要考慮主次,又要疏落有致,董希文在安排領導人的位置和動態時,費了很多心思,領導人的儀表也描繪的各有特征。從半邊下巴和一片小髭就能看出董必武,也足以說明董希文對待創作的認真和造型工力的扎實。
絕對完美無缺的藝術品幾乎是沒有的,百分之百的一致贊同也不可能。《開國大典》也并不是沒有不足之處,也有美術家提出過一些藝術上的缺點。當這件作品剛剛完成之際,徐悲鴻看到了非常興奮,說董希文圓滿的完成了一項政治任務,應得一百分,但是要扣五分,因為缺少一點油畫特色。在油畫家中持這種觀點的人并不是個別的。朱丹當時是人民美術出版社的領導者,出版社很重視《開國大典》的問世,立即把它印成年畫和各種美術圖片,大量發行,印數達前所未有的高峰,對美術的普及工作貢獻極大。可是朱丹認為《開國大典》有點像宣傳畫,沒有充分的油畫特征。有些美術家雖然也欣賞《開國大典》,但是認為董希文的藝術道路從《苗女趕場》(1943)、《哈薩克牧羊女》(1947)、《迎接解放》(1949)后退了。他們認為上述三件作品更具有民族繪畫的特色。 我認為《開國大典》在油畫藝術上的主要成就是創造了人民大眾喜聞樂見的中國油畫新風貌。這是一種新型的油畫,成功的繼承了盛唐時期裝飾壁畫的風采,體現了民族繪畫特色。它既有利于油畫的普及,又是油畫朝著民族化的提高。董希文曾在敦煌研究傳統藝術多年,他在那里的最大收獲是在踏踏實實地臨摹壁畫的實踐中,深深的感受了傳統繪畫的審美薰陶,并且學到了形成這種審美情趣的傳統型手法。《哈薩克牧羊女》、《迎接解放》這兩幅作品也都受到了敦煌壁畫的影響,特別是前者,受北魏時期古樸渾厚的畫風薰染,生動的反映了蒼茫落漠的高原放牧風情。應當說,《哈薩克牧羊女》的民族風格比較鮮明,有些地方明顯的可以看到直接運用了傳統的繪畫技巧。同時,在這幅油畫上也可以看到歐洲現代油畫的某些表現手法,它和傳統技巧結合的很好。
然而,董希文對盛唐時期的敦煌壁畫印象更深,他認為這些至今還基本上保持原作本來面目的色彩富麗的壁畫,令人產生高昂的情操,是中國傳統繪畫的瑰寶。他對我說過:"試想當時石窟里的壁畫,在許多油燈和燭光的閃耀下,那富麗的色彩,何等輝煌,它充滿激情,牽動著人們的心靈。這是歷代無名化工所精心創造,經過長期的熏陶,便形成了人們對繪畫藝術的欣賞習慣,它就是廣大群眾所喜聞樂見得民族風格。"但是,怎樣吸收這種帶有宗教氣息的裝飾風格,用來表現新中國的盛大慶典,是必須有所選擇、改造,不能簡單的拿來套用的。董希文自己說過,他要"在帶有裝飾性處理的《開國大典》這幅畫里,盡力做到富麗堂皇,把風和日麗的日子里的一個莊嚴熱烈的場面描寫出來。""風和日麗"的描寫,在唐代壁畫上是少見的,"富麗堂皇"的描寫,也有時代和感情區別。怎樣繼承傳統的裝飾風格用以表現現代感情,這是要下一番消化、吸收、推陳出新的功夫的。他在《開國大典》上設計的是以大紅、金黃和碧藍相輝映的色彩裝飾效果,釀成崇高喜慶的情操,描繪出風和日麗而雄偉歡暢場景。他不采用傳統重彩繪畫的描金、貼金,也不用線描造型,因為這畢竟是一幅油畫,基本上運用油畫語言來表現一切,然而富麗堂皇的色彩裝飾效果和線描造型特征卻自在其中。有人說這是單線平涂的油畫,這是看了印刷質量差的印刷品所得到的印象,如果看了油畫原作,就會知道,這是畫的較為平薄的同時又很扎實的塊面油畫造型。從整個畫面來看,又有傳統的線描結構特征,所以說這是新型的油畫,民族風格的油畫。
回憶當年我在京郊做了兩期土改工作回到北京時,立即和馮法祀一起去看正在創作中的《開國大典》,地點是在西總部胡同的一座二層樓房的樓上。中央美術學院當時不能提供一間合適的畫室,但是這間接用的房間也不大,而且是狹長的。畫幅靠著南墻,為的是取得穩定的北光,這對畫油畫是理想的。畫室長度剛夠放這幅畫,但是寬度很窄,作畫時缺少退步余地,不能做較遠距離的觀察。墻角下鋪滿了顏色碟子,單是畫天空的藍色和劃柱子的紅色就各有很多碟,每碟的色調和深淺是不同的。他畫天空、廊柱等都用排筆和刷子做大面積鋪陳,從工具和畫法好像時在做重彩中國畫。董希文在色彩上一向強調物體的固有色,這并不意味著只用一種顏色(所謂本色),如這幅畫上的天空,好像是藍天、白云,其實這藍色是有各種變化的,靠近地平線的天空和高處的天空有著顯著的差別,只是整個天空是亮堂堂一片,和其他大面積的色片、色塊(如廊柱的紅、菊花和瓔珞的黃)相互對照,相映成暉,產生動人心魄的裝飾美。所謂光色效應。董希文本來就不大喜歡印象派的光色效應,認為它是色彩的自然主義,在這幅帶有裝飾性風格的大型油畫上,他所要考慮的是色塊對比產生審美情趣,當然不會去追求無助于表現主題的光色效應。
《開國大典》的創作進度很快,不到兩個月的時間,當我們第一次看到時,已經完成七八成,整個環境已經畫好,厚實的地毯既富麗又有份量,天安門廊前的琉璃瓦也很有質感,上了年代的漢白玉欄桿發出古樸的赭黃光彩,這一切使人感到裝飾性和現實性結合的很好。天安門城樓的建筑畫得規矩挺拔,廊前的鋼欄桿和麥克風等如同界畫一般周正。這個階段,畫面上的主要人物已塑造得相當完整、傳神,對宋慶齡、張瀾的服裝也作了精心設計,(宋慶齡帶著網花手套,張瀾的綢長袍看上去是特地熨平褶好,到大慶之日穿上的)。但是我們發覺毛主席的身材畫的不夠高,毛澤東本來身材高大,特別是在這個畫面上,不應受立足點造成的透視縮小所限制,覺得有必要加高幾分。董希文同意我們的意見,決定作修改、雖然加高不到一寸,但工程不小,為了使畫面不留痕跡,他用稀料謹慎地把原畫部分洗去,重新畫了一遍。
董希文對祖國的藝術遺產有豐富的知識和多方面的愛好,除了繪畫、陶瓷、玉墨等,兼及民間工藝品和器皿家具。他不是一般地愛好而是在研究傳統藝術優點和特征。三反、五反運動中,他被領導派到琉璃廠鑒定古文物,這個差使正投其所好,回來時高興得很,因為在工作中看見許多稀世珍品。平時一有空,也是到處轉,哪家寄賣行有好東西他先知道。我們剛到北平時,有一年春節,一起到廠甸觀光,回來時他買了一只螃蟹燈,我買了一只金魚燈,大家各自在宿舍里作靜物寫生。這些花燈的表面是刷上亮油的,我寫生如實描寫,他畫的螃蟹燈卻是粉樸樸的(他的口語)沒有光澤的。他說燈籠刷上亮油是為了透光、耐用,論美觀還是紙的本色味道醇。果然,他畫的螃蟹燈很像濰坊水印年畫的色調。由于去掉了锃亮油光現出又樸素又渾厚的造型美。他對這幅靜物很滿意,第二年暑假我們一起南返渡假時,他親自把它帶回老家去了,可見實在很心愛。
他從敦煌回來以后,所作油畫大多是粉樸樸的,如給當時的故宮博物院院長馬衡畫的肖像(這是一幅非常深入細致的寫實油畫),色調非常沉著淡雅。那時他畫人體也是粉樸樸的,作畫時還高度稱贊敦煌壁畫上的人體描寫,說這些藝人能用極其單純的色彩和線條,畫出肉體細膩的色調和彈性,實在另人折服。這個時期,他在油畫上追求敦煌壁畫和民間年畫的審美情趣,《哈薩克牧羊女》便是一件代表作。再看《苗女牧場》,它的表現手法手西方近代派的影響就多一點。我當時看到的"苗女"膚色畫得比較透明,也很好地表現出東方女子的美。
董希文對不同題材的創作,各有不同的設想,《哈薩克牧羊女》所采取的表現手法是適應描繪新疆那時的牧區風情的,《苗女趕場》、《沙漠駝影》、《瀚海》都有各自的風貌。他的油畫風格在各個時期都是變化著的,1954年所作的《春到西藏》則天朗氣清、繁花似錦,成功地反映了西藏自治區人民歡暢心境。《開國大典》是一幅政治歷史畫,畫面上出現許多國家領導人的形象,這就決定了應以現實主義為基調,同時利用色彩的裝飾效果以烘托慶典的氣氛。在這幅畫上,人物必須刻畫得惟妙惟肖,這也就決定了只有采取西法造型,才能做到萬無一失。董希文的素描功底非常深,他不過分依靠光影的作用,卻把形體塑造得非常充實肯定,落落大方。這手下工夫來自歐洲文藝復興時期的形體素描法(不同于以后強調光影法)有研究,同時也吸收了印象派之后如塞尚所強調的形體塊面轉折的造型法。(董希文對歐洲油畫的明確觀點是借鑒吸收早期文藝復興大師如喬托的典雅色彩和造型的印象派之后如塞尚的形體轉折、色彩堆移等手法)。在《開國大典》的人物塑造上,也可看出有些勾描受了敦煌壁畫的影響。雖然不明顯,但骨子里可以看出來。有一次我看到他正在畫郭沫若的頭部,是用淡赭色作線描,外輪廓和內輪廓結合(有時稱"復線線描",這些術語是他首先使用的)得很到家,形象生動自若,栩栩如生,使我感到如果畫上油色,反到可能會有所損傷。然而,在復線線描基礎上用油畫完成后的郭沫若,非常成功,這說明董希文對塊面素描和線描的結合運用是很有把握的。這種素描造型上的中西結合,可從細微處察覺。
董希文在收集《開國大典》的人物形象資料方面也頗費心思,寫生不可能,連速寫也做不到,只能放棄繪畫手段的第一手資料。唯一的辦法是收集照片和參考電影上的形象。董希文只希望能拍攝符合構圖所需的每個領導人的照片,他為此奔走了多次,結果在中南海只拍到了劉少奇的全身照片。朱德則說侯波那里有他的許多照片,可以任意挑選。大多數領導人就不可能完全符合構圖的要求。為了使這些照片化為他所需要的美術形象,董希文根據照片畫了不少簡寫(也是董希文的術語,意即比速寫深入、比寫生簡練的復線素描),使得本來有較強明暗關系的照片,轉化為處在平光上的美術造型形象,并以此求得所有人物在畫面上的統一和諧。這些簡寫是進行油畫塑造的過度形式,也可以說是油畫塑造的基礎,不但要畫得與本人肖似,更重要的是掌握神態氣度。董希文在這方面的探索追求做到了精微入化,無可挑剔。作品的成功是董希文不惜付出精力從多方面努力攀登的報償。
《開國大典》完成后只三年,不幸發生了高饒事件,革命博物館通知董希文把畫面上的高崗去掉。董希文說:這幅畫在構圖時,高崗就有擠在邊上的局促之感,去掉他對構圖倒有好處。但是為了使工藝上很講究的畫面不受損害,又專門研究了洗去油色的方法。他要對作品負責,絕不能草率從事。人們或許有一種誤會,以為油畫的涂改是很方便的。豈知油畫的覆蓋力強是一回事,而況《開國大典》近乎傳統重彩畫,油畫的肌理和麻布低層的制作工藝都是極其精致的,不經意的涂改必定會起破壞作用。董希文為這次改動作了種種實驗,終于保持了作品完美。沒有料到,"文化大革命"又一次使《開國大典》蒙受了更大的劫難,革命博物館通知董希文在畫面上去掉劉少奇。這個修改工程就更難了,因為不是簡單地去掉一個人,而且要另外補上一個人,還要牽動旁邊的人。更其為難的是,董希文此時已得了癌癥,手術后雖然情況尚好,但體力衰弱,實在難于負擔這樣繁重的精神和體力勞動。然而他仍然奉命抱病到博物館親自進行修改,在劉少奇的位置上改畫了董必武。很遺憾,等到劉少奇得到平反昭雪之日,董希文已于1973年7月8日因癌癥擴散不幸逝世,他再也不能親自在《開國大典》上恢復劉少奇的形象了,這幅杰出的油畫也只能存放在畫庫里不能和廣大人民群眾見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