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解放到迷茫——中國(guó)流行歌曲20年
佚名
那時(shí)候到處是高音喇叭,那時(shí)候沒(méi)有電視、沒(méi)有磁帶、沒(méi)有錄音機(jī)。喇叭聲從工廠、機(jī)關(guān)、學(xué)校、部隊(duì)大院的圍墻里傳來(lái),強(qiáng)大,嘹亮。這是很久很久以前,這是1978年。
1978年,或稍早,那個(gè)總是傳出決議、社論、訃告、樣板戲、毛主席贊歌的大喇叭里,有一天傳出了《洪湖水,浪打浪》,傳出了《花兒為什么這樣紅》,傳出了《劉三姐》,它們一天又一天在喇叭中重復(fù)著,百聽(tīng)不厭。大人們說(shuō),這都是些解禁了的歌曲。
中國(guó)的新時(shí)代就從解禁開(kāi)始了。那些因?yàn)檎味窢?zhēng),因?yàn)椴粔蚋锩蛘邇H僅因?yàn)閻?ài)情的歌曲,重新回到了人們的生活中。大人們克服了戲曲的障礙,一遍遍去觀賞越劇《紅樓夢(mèng)》、黃梅戲《天仙配》,一遍遍為林黛玉或者七仙女的命運(yùn)痛哭流涕,黑暗中他們的眼淚濕透了一張張手絹,濕透了中國(guó)的一家家電影院。就在這種哭泣聲中,愛(ài)情的知覺(jué),久違了的俗世的情感,不再被看作那么可恥的東西了。
80年代——一個(gè)電影插曲的時(shí)代在新的電影中伸延。半導(dǎo)體和晶體管,薄膜唱片和電唱機(jī),人們坐在新買進(jìn)家的收音機(jī)前,聽(tīng)著李谷一、朱逢博、關(guān)牧村、鄭緒嵐、關(guān)貴敏,聽(tīng)著《祝酒歌》、《吐魯番的葡萄熟了》、《年輕的朋友來(lái)相會(huì)》、《我們的生活充滿陽(yáng)光》、《潔白的羽毛寄深情》、《邊疆的泉水清又純》、《太陽(yáng)島上》、《浪花里飛出歡樂(lè)的歌》。充滿歡樂(lè)和陽(yáng)光的音符像雪后的泉水一樣四處流淌,它們歌唱著生活的甜蜜,社會(huì)主義大家庭的甜蜜,不關(guān)涉具體,也與每一個(gè)具體家庭的生活無(wú)關(guān)。別種滋味的歌是借著電影劇情出現(xiàn)的:《知音》、《雁南飛》、《心中的玫瑰》、《角落之歌》、《妹妹找歌淚花流》、《媽媽教給我一首歌》。與之同時(shí),城市青年在宿舍里偷聽(tīng)臺(tái)灣歌,喇叭褲戴著不撕商標(biāo)的太陽(yáng)鏡、提著最時(shí)髦的錄音機(jī),騎著車或者成群結(jié)伙地呼嘯而過(guò),把鄧麗君和張帝的歌聲一路灑在大街上。大人們望著他們的背影說(shuō):這些個(gè)小青年,這些個(gè)阿飛。
是的,這些個(gè)阿飛。中國(guó)人開(kāi)始渴望平常的日子,但極左時(shí)代的禁忌依然在骨髓中浸透著。在核心的意識(shí)形態(tài)里,除非輔之以革命、事業(yè)等崇高內(nèi)容,否則世俗情感、談情說(shuō)愛(ài)、個(gè)人悲喜,都是低級(jí)趣味的、不道德的、甚至是不正派的表現(xiàn)。鄧麗君、張帝、劉文正只能在“地下”流行,甚至欣賞者自己,都有一種道德上的不潔感:鄧麗君唱的是黃色小調(diào),張帝唱的是流氓歌曲,唱法本身就透著“黃”。不久,李谷一唱《鄉(xiāng)戀》用了氣聲,蘇小明唱《軍港之夜》又柔又綿,立即招致痛斥和批判,批評(píng)者聽(tīng)出了那聲音里的“黃”。
這是中國(guó)歌曲歷史上的“電影插曲時(shí)代”,又是一個(gè)“中間腔時(shí)代”——這一時(shí)代的“唱將”,同王酩、施光南、谷建芬、劉詩(shī)召、王立平、付林這些最主要的歌曲作者一樣,都是名門正派、正統(tǒng)出身,卻共有一種向世俗情感過(guò)渡的傾向。洋腔洋調(diào)和土腔土嗓漸漸退出主流,聽(tīng)眾喜好的對(duì)象,是那些美聲中帶點(diǎn)自然色的歌手,這是80年代前五年大部分受歡迎者的共同特征。很明顯,我們可以從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例如從解禁時(shí)代的王昆、郭蘭英、黃婉秋向李谷一的變化,從李谷一向朱逢博—鄭緒嵐—沈小岑—蘇小明的變化,從男女聲二重唱兩個(gè)時(shí)代的代表——張振富、耿蓮鳳向王潔實(shí)、謝莉斯的變化,看到美聲、民族唱法的逐漸下移。甚至,1984年春節(jié)聯(lián)歡晚會(huì)首次請(qǐng)來(lái)的兩位香港明星——張明敏和奚秀蘭,也是兩個(gè)“中間腔”——奚是民歌“中間腔”,張是流行“中間腔”。“中間腔”流行的背后,有意識(shí)形態(tài)的保守在暗中支配著。此時(shí),一方面意識(shí)形態(tài)從高調(diào)下移,一方面中心意識(shí)仍在起作用,這種作用甚至是整個(gè)大眾的,迷惘、失落、痛苦等生活中的正常情感,在主流價(jià)值中被視為資產(chǎn)階級(jí)腐朽沒(méi)落的情緒,反映個(gè)人情感的流行音樂(lè)則被視為靡靡之音,在接受上存在一種心理障礙。這時(shí),大眾意識(shí)處于一種政治中庸?fàn)顟B(tài)。
稍后,臺(tái)灣校園歌曲一下子流行了,《鄉(xiāng)間的小路》、《外婆的澎湖灣》、《踏浪》、《踏著夕陽(yáng)歸去》,它們被“中間腔”廣為翻唱,非政治的內(nèi)容既滿足了人們潛在的人性需求,其自然情趣和健康明朗,又與正統(tǒng)價(jià)值無(wú)傷。“中間腔時(shí)期”的壓軸大戲由唱著《軍港之夜》的蘇小明完成:它終于脫離電影歌曲的拼合,而有了歌曲專輯的概念;主題背景雖然不脫國(guó)家、集體、事業(yè),但抒情角度卻充滿人情味和世俗性;歌手的聲音不再高昂,是中音的、松弛的,最大限度地接近了美聲的底線,它伴隨著批判,也伴隨著歡迎。
積極、健康、正面等觀念支配著歌聲審美的狀況,大概一直持續(xù)到1989年左右,此前歌壇千變?nèi)f變,好嗓子的觀念一直不變,始終以清亮、純正為第一美學(xué)特征。
是1983年還是1984年?一個(gè)叫程琳的孩子出來(lái)了,稍后,一年更小的叫朱小琳的孩子出來(lái)了。孩子是天真的,孩子是無(wú)邪的,“小螺號(hào),嘀嘀地吹”,“媽媽的吻,甜蜜的吻”,同時(shí)她們會(huì)唱鄧麗君。在童稚的掩護(hù)下,鄧麗君公開(kāi)化了。沒(méi)有美聲血統(tǒng)的流行唱法登場(chǎng)。不是出身于正統(tǒng)的學(xué)院派,而是一批社會(huì)青年,女學(xué)鄧麗君,男學(xué)劉文正,磁帶風(fēng)行,走穴風(fēng)行,模仿港臺(tái)歌曲風(fēng)行,“翻唱歌曲時(shí)期”全面降臨。張行彈著吉他唱:“你到我身邊,帶著微笑,帶來(lái)了我的麻煩”,因?yàn)閻?ài)不能分享,因?yàn)槟惚人斑t到”。嘩,300萬(wàn)盒銷量;嘩,吉他成百倍地狂銷;嘩,吉他班在城市里鋪天蓋地。談情說(shuō)愛(ài)不再是禁忌,“月亮代表我的心”不再是黃歌,“愛(ài)你在心口難開(kāi)”不再是淫聲浪語(yǔ)。各種新星不知都從哪里冒出來(lái),都唱著港臺(tái)歌,都有人買賬。1985年,美國(guó)40多名歌星為非洲災(zāi)民義演,聯(lián)唱《天下一家》,第二年臺(tái)灣60位歌星聯(lián)唱《明天會(huì)更好》,中國(guó)一位磁帶編輯說(shuō):他們能做60名,我們能做100名,獻(xiàn)給世界和平年!
100名歌星,說(shuō)聚就聚,還有很多沒(méi)參加的,想想看,中國(guó)的歌星有多多吧。《讓世界充滿愛(ài)》,100名歌星穿上整齊劃一的演出服(多奇怪!),一方面亮出不同的聲音,一方面突出圣歌般的齊唱。中國(guó)人,甭管男女老少,都接受了,都激動(dòng)了。 這是一個(gè)轉(zhuǎn)折,這是1986年。因?yàn)橐皇状蟾瑁先藗儾辉俦M覺(jué)得流行歌“痞”,文化界不再對(duì)流行歌圍剿掃蕩。1986年,流行音樂(lè)獲得官方一個(gè)折衷式的稱謂——通俗歌曲。
有兩件軼事可以說(shuō)明中國(guó)這時(shí)的半就狀態(tài)。一件是:1985年底英國(guó)威猛樂(lè)隊(duì)在北京演出,勁歌熱舞折騰一個(gè)大勁,臺(tái)下的中國(guó)觀眾均端坐著不動(dòng),威猛走了大半個(gè)地球,哪見(jiàn)過(guò)這架式?傻了,第一次覺(jué)著自己像猴子。另一件是:郭峰初到北京,常抱著吉他在街邊唱歌,人們叫他“小流氓”;百名歌星演唱會(huì)后,當(dāng)他再一次抱著吉他在街邊唱歌,路過(guò)的人不禁對(duì)他指指點(diǎn)點(diǎn):“瞧,這就是寫《讓世界充滿愛(ài)》的作曲家,瞧人家多有藝術(shù)家的派頭!”
1986年之后,流行音樂(lè)并行出現(xiàn)了三條脈絡(luò)。崔健在百名歌星演唱會(huì)上唱出《一無(wú)所有》,從此搖滾在地下開(kāi)始蔓延流行,為首都青年所喜,為官方人士所罵;《信天游》引爆了“西北風(fēng)”,眾多歌曲創(chuàng)作均以北方民歌為素材,但是見(jiàn)歌不見(jiàn)人,大家都唱同樣的歌,寥寥數(shù)首名作成了“全國(guó)糧票”;以齊秦、蘇芮為開(kāi)端,港臺(tái)引進(jìn)版大舉登陸,原人、原唱、原作,使大陸的“翻唱歌曲”宣告滅亡。
1987年,《信天游》、《黃土高坡》、《我熱戀的故鄉(xiāng)》、《心愿》,中國(guó)人十分耳熟的民歌調(diào),唱著家鄉(xiāng)、土地、山溝溝,和著電聲樂(lè)隊(duì)、電子鼓擊、大嗓唱法,滿城轟鳴。1988年,電視臺(tái)每日播出《雪城》和《便衣警察》,“下雪了,天晴了”,“幾度風(fēng)雨幾度春秋”,劉歡的聲音每夜準(zhǔn)時(shí)響徹大街小巷。1989年,電影《紅高粱》,“妹妹你大膽地往前走,莫回呀——頭”。
呵,莫回呀——頭:民歌加架子鼓加鄉(xiāng)里腔加吼唱;之后“囚歌”——?jiǎng)诟姆傅母瑁恢筚邓字C謔歌曲大泛濫。是誰(shuí)在聽(tīng)它們?我不知道。
我知道另一種流行,港臺(tái)、歐美歌曲的流行。大學(xué)校園里在復(fù)制磁帶,城市的街頭在兜售拷帶。大街上能買到的公開(kāi)引進(jìn)版是《搭錯(cuò)車》,是《狼》,不能買到的便托人從海外購(gòu)進(jìn)、然后流入交換、翻錄、拷貝的渠道。到1993年,引進(jìn)版已經(jīng)全面化,大陸流行音樂(lè)市場(chǎng)全面開(kāi)放。王杰的心痛、姜育恒的憂郁、童安格的“其實(shí)你不懂我的心”,張雨生、庾澄慶、趙傳、小虎隊(duì)、鄭智化、四大天王;MTV、卡拉OK、追星族,音樂(lè)越來(lái)越新潮,歌迷越來(lái)越低齡。稍后又有歐美打口帶流進(jìn)城市,中國(guó),漸漸成為世界流行音樂(lè)統(tǒng)一市場(chǎng)中的一部分。
伴隨著這一統(tǒng)一化進(jìn)程,中國(guó)自己的造星運(yùn)動(dòng)隆重開(kāi)幕。1992年,唱著甜歌的甜妹子楊鈺瑩通過(guò)中央電視臺(tái)一舉傾國(guó),成為大陸第一位自制偶像。隨之,中國(guó)出現(xiàn)第三次新人輩出場(chǎng)景:上電視、拍MTV,推歌打榜,文字轟炸。潮流,潮流。歌曲越來(lái)越多,歌手越來(lái)越多,彼此間越來(lái)越相象。同期,搖滾樂(lè)唱片準(zhǔn)許出版,一直埋沒(méi)在地下的搖滾樂(lè)開(kāi)始全面出頭,搖滾不再是崔健一人,搖滾不再是禁忌,男人可以留長(zhǎng)發(fā),長(zhǎng)發(fā)可以上招貼。《無(wú)地自容》的黑豹火了,《夢(mèng)回唐朝》的唐朝火了,新音樂(lè)的春天的張楚、竇唯、何勇火了。鐵桿搖滾樂(lè)迷像沙漠中渴求水源一樣渴求著、尋找著搖滾樂(lè)。但當(dāng)各路知名樂(lè)隊(duì)和更多不知名的樂(lè)隊(duì)成批成批浮出地面,搖滾樂(lè)迷不再狂熱了,搖滾樂(lè)迷開(kāi)始深深地失望:搖滾樂(lè)不是賣著憤怒,便是賣著青春期的躁動(dòng)(多簡(jiǎn)單!),大家都太想快快成名。隨著中國(guó)全面進(jìn)入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時(shí)代,意識(shí)形態(tài)的對(duì)立局面被消解。潮流,潮流。搖滾樂(lè)的潮流也一撥連著一撥,隨著世界整齊地左轉(zhuǎn)、右轉(zhuǎn),齊步走,然后金屬了,然后另類了,然后朋克了。
1992年,《小芳》,知識(shí)青年和假知識(shí)青年在懷舊。
1993年,《濤聲依舊》:這一張舊船票,能否登上你的客船?
1994年,《同桌的你》,大學(xué)生未老先衰,感傷而回憶。
1995年,《艷陽(yáng)天》,搖滾樂(lè)像花朵縮進(jìn)琥珀里,懷想;《露天電影院》念起童年景色不再。
1996年,……
1997年,《心太軟》:OH,算了吧,就這么散了吧。
與這幾首最流行的歌曲相伴,是青藏題材的長(zhǎng)盛不衰,好像是另一個(gè)世界的呼喚:《回到拉薩》、《阿姐鼓》、《青藏高原》、《央金瑪》、《雪域光芒》;是俗歌的連連成功,好像在城市的變幻中穩(wěn)固著不變的舊色彩,接續(xù)著“西北風(fēng)”和“囚歌”的余緒:《大中國(guó)》、《纖夫的愛(ài)》、《天不下雨天不刮風(fēng)天上有太陽(yáng)》、《九月九的酒》、《大花轎》、《好漢歌》。在感傷懷舊、西藏情懷和大舊大俗的后面,則是整個(gè)社會(huì)的快速變遷。
從整體上看,城市情歌的泛濫已使流行歌變得膩味,北京樂(lè)隊(duì)的全面露臉已使搖滾樂(lè)的號(hào)召力徹底瓦解。這不再是一個(gè)短缺的時(shí)代,同時(shí)也不再是一個(gè)因?yàn)檎螇毫Χa(chǎn)生表達(dá)激情的時(shí)代。流行音樂(lè)的低潮隨之到來(lái)并延續(xù)到1998年。思想和情感禁區(qū)的不復(fù)存在,使表達(dá)真正成為一個(gè)問(wèn)題。中國(guó)流行音樂(lè)終于露出初級(jí)、幼稚和虛弱的真相,這時(shí)我們發(fā)現(xiàn),新的、城市的、豐富的、切身的生活,竟然還沒(méi)有得到多少真正的表達(dá)。業(yè)已存在的唱片商在狹隘的商業(yè)追求中老化,千篇一律的愛(ài)情只是一些虛假的套詞,搖滾的反抗只是一些口號(hào)和大話,空洞、淺薄而老套,它們是“我們的生活比蜜甜”的另一面的虛擬。
過(guò)去是政治的一統(tǒng)天下,現(xiàn)在是商業(yè)的一統(tǒng)天下。
你已有多久沒(méi)有聽(tīng)到刺痛你心肺的歌?
迷惘。但迷惘只是暫時(shí)。只要有生活,就會(huì)有生活的感受,就會(huì)有表達(dá)感受的歌。民間的多種音樂(lè)型態(tài)已經(jīng)發(fā)生,民間創(chuàng)作人士的遍地滋生已經(jīng)成現(xiàn)實(shí)。你看過(guò)個(gè)人網(wǎng)頁(yè)嗎?你聽(tīng)過(guò)小樣和自磁帶嗎?你讀過(guò)樂(lè)友之間交流的自辦雜志嗎?你知道你們那個(gè)城市的樂(lè)隊(duì)和演出嗎?如果你沒(méi)有聽(tīng)到豐富的聲音,那么你聽(tīng)。
而豐富的聲音這20年來(lái)一直沒(méi)有停止過(guò)生長(zhǎng),最近一年的生長(zhǎng)是:樸樹(shù)、尹吾、清醒、花兒、胡嗎個(gè)、《盤王之女》、《無(wú)能的力量》……還有許多我不知道的。如果這些聲音還不能讓你滿足,那也是這20年給你的饋贈(zèng),你遺憾了,你開(kāi)闊了,你自由了,你有福了。
科技.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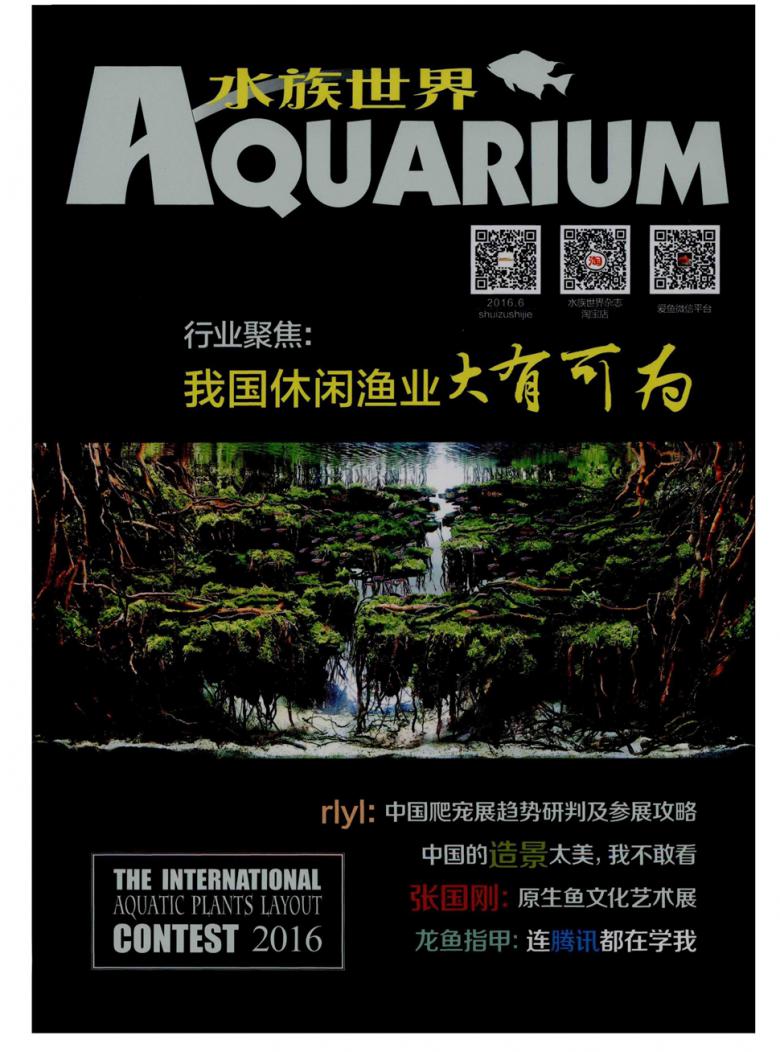
科大學(xué)學(xué)報(bào).jpg)

學(xué)報(bào).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