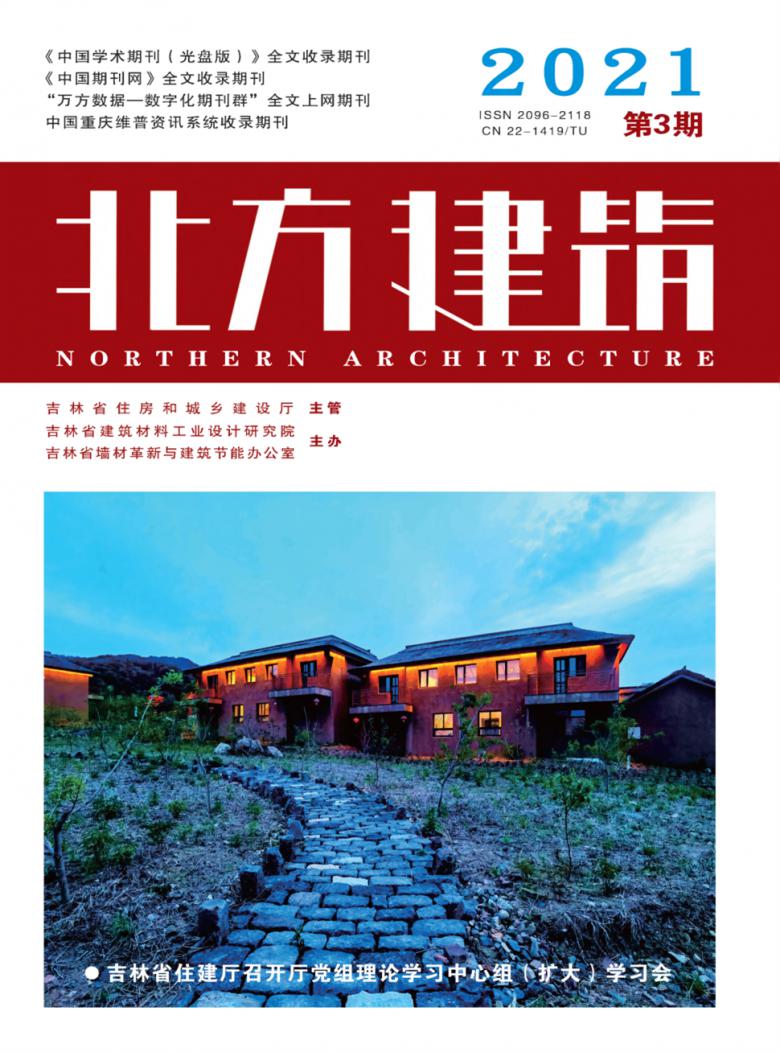新編京劇中蒙太奇手法的運用
張宏梁
摘 要:新編京劇中蒙太奇手法的運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話劇舞臺的改革創新推動的。蒙太奇手法在京劇舞臺上的運用已非個別現象,而且閃現出多種形式,使新編京劇增添了時空切換和形象拓展上的自由度,煥發出新的審美氣息。對于新編京劇中蒙太奇手法的運用,仍然需要以積極的態度給予支持。當然,蒙太奇手法在新編京劇中畢竟只是輔助手段,京劇更應該充分發揮自身所獨有的特長,以它特有的“唱做念打”來與影視抗衡。
關鍵詞:新編京劇;蒙太奇;輔助手段
Abstract:The application of montage in the new Beijing Opera is,to a large extent,promoted by the reform and innovation in the drama stage. Montage practice in the Beijing Opera stage is not unique,but has come out in various forms,added space-time switch and freedom of image expansion to the Opera,filling it with new aesthetic atmosphere. We should adopt a positive attitude towards it. Meanwhile we should also know that the montage practice is only a supplementary means,and to contend with the film,Beijing Opera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its ownunique traditional expertise singing,performing,explaining and martial arts.
Key words:new Beijing Opera;montage;supplementary means
一
新編京劇中蒙太奇手法的運用,在很大程度上是受話劇舞臺的改革創新推動的。
以影視為代表的物質技術力量的進步和發展的需要,使觀眾對話劇的審美也發生了變化,迫使話劇的創作和演出跳出某些傳統的圈子,展開一種全新的自由,正如俄國戲劇大師梅耶荷德所感嘆的那樣,舞臺從此就變成了“充滿了種種奇跡與魅力的一個世界,具有了令人喘不過氣來的樂趣和奇異的魅力”[1]。戲劇吸收多種藝術的長處并將它融為一體,為舞臺演出服務,已成為當今戲劇發展的一大趨勢,其中一個種類就是電影。早在上世紀20年代中后期,對電影情有獨鐘的梅耶荷德就對已確立了獨立藝術品格的電影贊賞有加,大膽提出了“戲劇與電影相結合”的口號,他在排演《森林》、《拿下歐洲》、《射擊》等劇時,都曾在戲劇演出的過程中直接穿插電影片段,包括在舞臺銀幕上配合劇情放映電影、采用電影字幕的表現手法等等。在1926年演出《欽差大臣》時,梅耶荷德更將電影里的特寫鏡頭、蒙太奇用來處理一些重要場面,這給舞臺形象帶來了饒有趣味的清晰性。與此相應,尤金·奧尼爾、布萊希特、田納西·威廉斯等人也都從電影藝術中吸取了大量技巧,極大地豐富了戲劇的表現力。戲劇要真正實現“電影式”的時空自由,而又不破壞觀賞感受,就得在時空切換時快速剪輯,以做到像布萊希特所說的那樣“迅速變換場景”。它可以采用“化入化出”形式,以電影化的速度出現在觀眾面前,也可以在視點上進行互無關系的畫面的突然結合,借助蒙太奇等電影手法創造出流暢的戲劇舞臺進程。
有學者認為,中國當代戲劇“電影化”的探索始于軍事題材的突破,其始創者是1980年北京軍區政治部話劇團演出的《平津決戰》和軍委總政話劇團演出的《原子與愛情》。它們在當時較為普遍的“高調”戲劇、“觀念”戲劇中,開始重視活生生的戲劇性格的塑造,力圖通過蘊涵悲劇精神的英雄主義情懷,詮釋一種道德崇高。它們對電影手法的借用,基本上處于不自覺的狀態,與題材本身的展示性特征密切相關。《平津決戰》直接在每幕(場)戲前插入電影片段,目的是幫助觀眾了解“平津決戰”的歷史背景;在《原子與愛情》中,銀幕的作用既體現在事件背景的解說上,也體現在誘發人物進入回憶,推出閃回鏡頭上。它們在空間上與戲劇的敘事空間拼接在一起,雖顯得有些突兀,但在當時卻也不失為大膽的創新。
話劇的演出除了直接加入銀幕(近年來利用舞臺上的大型電子顯示屏顯示時空變化的亦非少數)還廣泛運用特寫、閃回并間接使用疊化等電影技法,擴展話劇的感召力、增強故事的闡釋力和性格的揭示力。話劇的觀眾盡管還不很理想,但話劇界所做的努力,確實是艱苦卓著的。電影與戲劇相比,雖同為“直觀”,但電影語言有更強的可選擇性,更為自由,這也就是說,在“形象化”方面,電影作品有它特殊的審美心理對應。戲劇借鑒電影手法,正是為了擴大戲劇藝術的自由度。
“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戲劇中電影手法的運用,無疑是以話劇的改革為先行的。這種改革是藝術生產力和藝術生產關系之間矛盾運動的結果,以影視為代表的物質技術因素在這一過程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正如瓦萊里在《美學》中所言:“技術上驚人的進步,它們所達到的適應性和精確性,它們正在形成的觀念和習慣,確定無疑地使古代美妙的藝術面臨一場深刻的變化。在一切藝術中,有一種再也不能被慣常考慮或對待的物質成分,一種不能被我們時代的知識和力量所影響的物質成分。近20年來,無論是物質還是空間和時間,都不復是太古時代的那個樣子。我們將會有更偉大的革新以改造整個的藝術技巧并因而影響藝術創作本身,也許甚至實現一種我們在藝術見解方面的驚人改變。”[2]科技手段在藝術中的加盟,一個重要目的就是發展藝術的表現形式,擴大藝術的表現空間,讓觀眾獲得新的美的形式的觀照。有了這種藝術形式方面的自由度,才能更好地表達它的內容意義,使欣賞者的審美意識進入李澤厚所說的那種意味層。
話劇的改革也推動了長期固守自己程式規范的京劇的創作和演出。新編京劇中電影手法的運用使新編京劇增添了時空切換和形象拓展上的自由度,給觀眾新的審美享受。比如于魁智李勝素聯袂主演的大型新編歷史京劇《走西口》,在光影氛圍和照明切換上吸收了電影蒙太奇的手法,整個舞臺顯得撲朔迷離,渲染出人物命運的悲劇氣氛。中國京劇院根據《三國演義》中“諸葛亮七擒孟獲”的故事為素材改編的《瀘水彝山》,在場景的處理上,既有鮮明的程式,又有借鑒電影蒙太奇手法和時空交錯的舞臺調度。導演高牧坤對“火燒藤甲兵”的場面調度和武打、布景、設計、燈光均有新意。這場戲中,通過化用電影中的“平行蒙太奇”手法,表現出蜀軍與藤甲兵在同一時間里的不同空間中進行的多重廝殺,尤其是利用燈光映射出的火焚場面更是令人嘆為觀止。湖北省京劇院新編京劇《樊姬夫人》在一片聲色絢爛中拉開序幕,光影與布景融合了現實與想像、虛與實結合等多種手法,最特別的是場上6塊頗具楚文化風情的大盾牌,既是換場的“幕布”,又是表現劇情的背景,還成為了戰爭場面的道具。沈陽京劇院新編現代戲《法官媽媽》充分調動了戲曲藝術的表現手法,將唱、念、做、舞、翻與戲劇情節、情感的宣泄、人物的性格刻畫有機而較為完美地融為了一體。在布景、燈光的設計方面,則著力運用現代手法,創造出美輪美奐、引發深遠聯想的舞臺意境,十幾個場景變換自然,還在舞臺空間上使用了電影蒙太奇的手法。這些信息充分說明了新編京劇中運用蒙太奇手法,已非個別現象,這使京劇這種傳統的藝術煥發了新的生機。
二
追溯起來,京劇舞臺上運用蒙太奇手法早已有先例或雛形。
在一次關于京劇的研討會上,武漢大學教授鄒元江提出了“梅蘭芳不懂京劇美學”這個驚世駭俗的觀點,他舉了《汾河灣》中的一幕作為例子:薛仁貴(譚鑫培飾)在寒窯外面訴說往事,梅蘭芳演的柳迎春在里面傾聽,按照傳統的演法,梅蘭芳是背對著觀眾聲色不動的。然而,當時的劇評家齊如山看了十分不滿,寫信給梅蘭芳說,柳迎春應當配合薛仁貴的訴說做出各種表情。這顯然是把西方戲劇的標準強加給了京劇,因為中國的戲曲講究虛實相生,當譚鑫培表演的時候,是不允許梅蘭芳表演以分散觀眾的注意力的。但令人吃驚的是,梅蘭芳居然聽了齊的話,在以后的演出中加入了各種豐富的表情。
筆者認為,梅蘭芳吸取了齊如山的建議,確實打破了傳統的框框,使京劇表演中具有了兩個不同空間畫面的組接感覺。有專家認為:按照電影一般的拍攝手段,兩人對話,一般先來一個人的“正打”畫面,也就是先拍一段說話者之一的正面形象,接著便是另一個人的“反打”,以表示他(她)的反應,再接著是一個交代環境的雙人鏡頭。這種蒙太奇手段現在已經被電影廣泛運用,它的用意是很明顯的:第一個“正打”鏡頭是為了突出說話主體,此時的傾聽者往往只有一個背影或者干脆淡出畫面;而“反打”則是為了突出傾聽者。在這一正一反的組合中,電影通過空間的變化,把同一時間發生的事情切割成了先后發生,實質上是用技術來彌補人眼的局限,滿足了人類對于全方位了解“真相”的欲望。由此來反觀中國的戲曲,在《汾河灣》中,譚鑫培唱、梅蘭芳傾聽相當于一個“正打”鏡頭,“反打”被移到了下一唱段,同樣采用了對時間的解構—─這其中的微妙對應不是正好說明兩個藝術門類的一線相通嗎?觀眾不會運用所謂精確的思維,去責難寒窯里面的人如何能對寒窯外的人所進行的心理活動(這里不同于有意無意地、比較近距離地聽隔壁的人講話)作出表情反應。列夫·托爾斯泰曾說過,藝術家的任務不在于無懈可擊地解決問題,而在于促進人們熱愛豐富的永不枯竭的生活[3]。魯迅先生也說過,倘若苛求作品的事實真實,那不如去看通訊報道。列夫·托爾斯泰和魯迅先生的意思都是說明,藝術真實與生活真實是不能完全劃等號的。結合梅蘭芳在扮演柳迎春這個角色時的改革來看,這其實是使兩個人在不同區間的表演具有了背躬戲的味道。而京劇中的背躬戲與電影中的架話式蒙太奇,是具有相似因素的。梅蘭芳在寒窯里面對寒窯外的人進行的心理活動所作出的表情反應,不過是一種表情語言(態勢語言、身體語言、動作語言)。一些著名的背躬戲,比如《沙家浜》“智斗”中阿慶嫂、刁德一、胡傳魁三者之間的背躬唱,不就包含著應答、架話的形式嗎?他們三人站的是實的位置,背躬的心理應答空間則是虛擬的。上海京劇院新編京劇《貞觀盛事》中亦有一個蒙太奇畫面的處理,飾魏征者(尚長榮)所安排的位置則完全是虛擬的:魏征再諫后不被采納,李世民獨步庭院,心理正進行斗爭,后面出現魏征身影,這個身影完全屬于李世民心理上的聯想。舞臺燈光人員利用追光,使觀眾迅速意識到這是李世民進行心理斗爭時頭腦中涌現的形象。值得一提的是,在這場融入電影手法的背躬戲中,李與魏的“二重唱”中出現了“輪唱”成分。筆者在其他新編京劇中也偶或見過,這種包含著“輪唱”成分的唱腔,大大增強了人物心靈交錯的氣氛。正如匈牙利電影理論家貝拉·巴拉茲所說:“上下鏡頭一經聯結,原來潛藏在各個鏡頭里的異常豐富的含義便像電火花似的發射出來”[4]。
一些鄙薄京劇等戲曲的人,往往嫌戲曲節奏太慢,這實在有失偏頗。從情節進展來看,舞臺劇恰恰是最講究情節集中、緊湊的。當然,新編京劇也已注意盡量加快節奏,適應現代觀眾的觀賞心理。譬如沈陽京劇院的大型新編神話京劇《無底洞》,大膽借鑒了意識流、蒙太奇等手法,使戲劇節奏更加緊湊,避免了冗長拖沓的情節,多次于無形中完成了場次轉換。獲得高度好評的上海京劇院創作的京劇《廉吏于成龍》在編導上也是創意迭出,劇本采取的是“散點式結構”,只有中心人物(于成龍),沒有“起承轉合”的中心事件。這臺戲打破了場次的限制,在京劇舞臺上大膽運用了意識流、電影蒙太奇等手法,使戲劇結構很緊湊。普多夫金說:“凡是影片中斷的地方,凡是在需要連接的地方——無論這些片段是膠片的各個片段或是動作的各個部分,都必須考慮到節奏這個因素,這倒不是因為‘節奏’是一個現代的時髦用詞,而是因為受導演意志支配的節奏能夠是而且必須是一個有力的和可靠的造成效果的手段。”(注:普多夫金《論電影編劇、導演和演員》,轉自免費雜志在線閱讀《新聞愛好者》2007年第22期王紅霞《漫論影視節奏》。)而要造成效果,則又必須以觀眾的理解為驗證。 架話式蒙太奇等蒙太奇手段不僅可以使戲劇的情節變得更加緊湊,而且可能產生幽默機智、富有情趣等審美效果。湖北省京劇院演出的大型新編古裝京劇《曾侯乙》有這樣一場戲:曾侯乙為制造大型編鐘,與王后鐘玉及公主嫵女句均化裝成普通人,帶優丹(由武生飾矮丑)去找鑄鐘專家鐘穎。舞臺上,近臺邊處,優丹抓住一只鳥(以虛擬動作表示),問曾:“此是何鳥?”曾答:“是南方的一種鳥,叫玄鳥。把它放了!”而在舞臺另一頭,即舞美設置為上坡處,嫵女句正抓住鐘穎:“不能把他放了。”指的又是不能把鐘穎放了,構成了陰錯陽差的架話式蒙太奇,既顯出嫵女句活潑的性格,也增添了語言嫁接的特殊情趣。
在我國古典詩歌中常常運用到對比手法,比如在杜甫的詩中就有:“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富家廚肉臭,戰地骸骨白”等詩句,在電影蒙太奇中也有一種“對比式蒙太奇”。富與窮、強與弱、文明與粗暴、偉大與渺小、進步與落后等等的對比,在影片中是常見的。
在京劇《楊門女將》中我們似乎已經看到對比式蒙太奇。當天波府內喜氣洋洋,紅燭高燒映壽幛為宗保慶壽的時候,孟懷遠與焦廷貴卻送來了宗保元帥為國捐軀的噩耗,使舞臺氣氛形成了強烈的反差對比。在北京京劇院新編歷史京劇《武則天》中,通過權傾天下的武則天與文人駱賓王之間的一段恩怨來折射女皇的一生。全劇圍繞“討武檄文”的傳奇故事展開,以正說的姿態講述歷史,唱詞、念白具有盛唐氣象的詩化風格。劇中人的唱詞、念白和身段動作都融入了大量的新鮮元素,受到了戲迷觀眾的熱烈回應。武則天在要求詩人駱賓王為她篆寫墓志銘被拒絕的時候,才恍然明白原來她當了女皇依然不可能被社會世俗所承認。該劇出現了這樣一組畫面:武則天在臺前思考,為什么像駱賓王這樣的人要罵她、聲討她,社會上有很多人不能接受她;而在武則天扮演者的身后,在“橫線構圖”上展現出一組畫面,意圖則是表現結婚、豐收等方面的黎民生活。這里也包含著對比式蒙太奇的因素。
蒙太奇是叫板式蒙太奇。這種結構方法在故事影片中能承上啟下,上下呼應,而且節奏明快。有的資料上認為,叫板式蒙太奇就像京劇中的叫板或叫頭。這樣類比等同是欠妥當的。實際上,電影中的“叫板式蒙太奇”只是借用了戲劇中“叫板”這一名稱,其內涵則與京劇中的“叫板”有所區別。要解釋叫板式蒙太奇,最貼切的比喻是俗語“說到曹操,曹操就到”。京劇《武則天》中,有一場結尾處,武則天心理活動想到駱賓王,駱出,屬于心理想像,接下去一場即回到監獄場面,仍然是駱的表演。這里就構成了叫板式蒙太奇。
蒙太奇的設計,符合人的視覺感受規律。人在觀察事物時,根據視覺和心理的需要,總是不斷地調整視線和視點,將注意力依次集中在不同的空間范圍,以便全面地認識事物。有時候,甚至在同一時間內,人的視覺很可能同時注意到兩個不同方面。打個比方說,我們現在看電視,在注意到屏幕上主要畫面的同時,也可能注意到電視臺在屏幕下方所播放的“過條通知”。觀眾看戲劇或電影電視的時候,進入視野的雖然是整體畫面,而注意中心又常常是有所選擇的。如果觀眾有意注意某個人物,某個細部,則可能將其變成視覺上的“特寫”,而讓其他人物、景物、場面、畫面暫時變為注意邊緣。戲劇運用電影手法,強化了畫面的分割、切塊,將某些人物、細部同時特寫出來或分別特寫出來。電影蒙太奇的功能就是在鏡頭的組接中,使鏡頭之間產生連貫、轉接、對比、襯托、聯想等關系,賦予畫面以新的意義,增加電影的表現力。新編京劇《武則天》在這方面也較為典型,該劇利用眾多既古老又新鮮的元素打造了視覺聽覺盛宴。比如有一場戲,武則天、駱賓王、裴炎、上官婉兒4人4個位置,既是背躬戲狀態,也是畫面上的切割、疊化。再如京劇《梅蘭芳》中采用了電影蒙太奇手法,讓史實中本不在一個空間的人物相見、對話,虛與實都做到了極致,比如與武生泰斗楊小樓告別,與國畫大師齊白石的交往等等用時空概念來衡量都近乎荒誕,但這又都是梅先生親身經歷的,為他以后蓄須明志,息影舞臺做了鋪墊。這些電影手法的加入在傳統京劇中都是很難看到的。
三
法國電影理論家安德烈·巴贊認為電影一定會將取之于戲劇的一切,毫不吝嗇地奉還給戲劇。京劇的誕生固然早于電影,但電影吸收了戲劇某些特點后,又反過來推動了戲劇與電影的某些融合,京劇的創作當然也不能不與時俱進。這需要編劇、導演、演員、音樂、舞美、燈光等演職人員的通力合作。比如我們在新編京劇《華子良》中清楚地感受到利用燈光“暗轉”切換、淡出淡入而構成“蒙太奇”的效果。過去戲劇場次利用閉合開啟幕子或暗轉的時空轉接,有暗合蒙太奇的,但不多,一般也不明顯。而京劇《華子良》不僅頻率高,而且較為明顯。如有一場次結尾處,華子良跑步“淡出”,下面則是雙槍老太婆帶華鎣山游擊隊隊員跑步“淡入”,屬于“相似性蒙太奇轉接”;此劇還有其他幾處“蒙太奇”轉接值得研究,編導人員真的是把電影取之于戲劇的一切,毫不吝嗇地奉還給戲劇了。
京劇發展的過程是革新─規范─革新的過程。我們無疑需要強調京劇姓“京”,強調京劇的規范,強調其質的規定性。但也有些人借強調京劇的本質特點為名而對京劇的改革表示懷疑,對京劇中蒙太奇手法的運用也頗有微詞。他們認為,京劇有其程式,而且它的生命力更在于唱腔,運用蒙太奇等電影手法,就違背了京劇的本質特點,使這一國粹藝術變得不倫不類。
確實,電影電視可以更多地擁有“視覺合一”的效果,戲劇畢竟不同于影視,即使在新編京劇中,蒙太奇等電影手法畢竟也只是輔助手段,京劇更應該充分發揮自身所獨有的特長,以它特有的“唱做念打”來與影視抗衡。當然,京劇因為有自身的一些特點,也有些蒙太奇手法不宜生吞活剝地插入。比如電影中有“復現式蒙太奇”:從內容到性質完全一致的鏡頭畫面,重復出現(例如張藝謀執導的《我的父親母親》中復現“父親”生前在小學教書的鏡頭)以至反復出現(比如前蘇聯電影《鄉村女教師》中地球儀的多次轉動,表示時光的推進)叫做復現式蒙太奇。這種蒙太奇總是在劇情發展的關鍵時刻出現,意在加強影片主題思想或表現不同歷史時期的轉折。但反復出現的鏡頭必須在關鍵人物的動作線上,只有這樣,才能夠突出主題,感染觀眾。筆者認為,京劇里的人物回憶或補充交代過去的事情,大都通過唱腔或道白,由于要花大量的時間在唱念做打上,因此,一般說來,除了心理視像上再現某個人物外,很難安排重復性的具有情節因素的“閃回”場面,京劇的場面如開弓之箭,一般是有“去”無“回”的。
對于新編京劇中蒙太奇手法的運用,我們仍然需要以積極的態度給予支持。魯迅先生當年談到創作中新的嘗試時說:“因為在我們還算是新的嘗試,自然不免幼稚,但恐怕也可以看見它恰如壓在大石下面的植物一般,雖然并不繁榮,它卻在曲曲折折地生長”(注:魯迅《且介亭雜文》(草鞋腳)《<英譯中國短篇小說集>小引》,《魯迅全集》卷6第16頁。)。
京劇的特點也不應該神圣化。京劇的改革要符合規范,但這個規范是發展著的、變化著的規范,不應是凝固不變的規范。現代戲劇觀眾對舊的傳統模式可能產生審美疲勞,希望有新的技法,希望形象的豐富性,他們對于舞臺上一些新的手段的插入,視覺的敏感性及其識辨力、理解力已遠遠超過過去。
創造學的原理告訴我們,新的創造往往是根據信息的切割與結合來展開。在作為創造方法之一的創造工程理論中,戈登認為創造過程是由“把不熟悉的東西變成熟悉的東西”和“把熟悉的東西變成不熟悉的東西”兩部分組成的。前者重視分析,后者重視結合。在創造過程中,分析與綜合兩方面都是重要的,尤其是綜合更重要。創造是對可能性的挑戰。從通常的思考過程中飛躍產生的思想,一般來講是獨創的東西,也有的是深度思考的延長。創造是異質素材的新組合,是人類智慧行為的一種,通過對儲存的信息資料做出選擇和判別產生的有價值的東西。參照遺傳學的原理來看,戲曲改革是個“轉基因工程”。其中本質的特點是遺傳因素,但又有變異因素。在遺傳學上,變異是指同種生物世代之間或同代之間的性狀差異。變異有遺傳的變異和不遺傳的變異之分。前者必須通過遺傳物質的改變,包括基因突變和染色體畸變,一般是不定向的,稱不定變異。后者僅由環境條件直接引起的變化。新編京劇是從舊的價值體系向新的價值體系的變異,是將異質的信息或事物用至今未有的方法結合起來,產生新的有價值的東西的過程。好像阿爾米達(西方神話中的女巫之名)的魔杖,從不毛的荒野里召喚出一個花香鳥語的春天。
在我們這個價值取向和審美趣味更加多元化的時代,戲劇的改革也必然是不斷流動變化的。在改革發展過程中,存在著一個重要的推進力量,那就是人類審美觀的演變和科學技術的催化。一些新的藝術形式、新的表現手法、新的傳播媒介、新的藝術產品,有可能在它剛一出現的時候,就得到贊美和認可,也有可能從不太習慣逐漸變得習慣,轉而變為欣賞品味了。
參考文獻:
[1]J·L·斯泰恩.梅耶荷德論戲劇[M]//現代戲劇的理論與實踐:3.象禺武文,譯.北京:中國戲劇出版社,1989:116.
[2]許詩焱.影視時代西方戲劇的演變[J].藝術百家,2000(2):75.
[3]列夫·托爾斯泰.致彼·德·波波雷金[M]//文藝理論譯叢:第1期,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57:224.
[4]貝拉·巴拉茲.電影美學[M].北京:中國電影出版社,198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