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高師《西方音樂史》教學(xué)中音樂本體分析的重要性
張良寶
內(nèi)容摘要:文章通過對高師《西方音樂史》教學(xué)現(xiàn)狀的分析,論述了在高師《西方音樂史》的教學(xué)中滲透音樂本體分析的重要性。《西方音樂史》教學(xué)應(yīng)當(dāng)把音樂本體分析作為考察音樂歷史的立足點,通過對音樂本體的具體聲音結(jié)構(gòu)和技法層面的分析與探究,深入音樂的內(nèi)部去分析西方音樂本體形態(tài)嬗變的歷史。
關(guān) 鍵 詞:《西方音樂史》音樂本體音樂思維
《西方音樂史》是高師音樂院系音樂學(xué)專業(yè)的一門重要的音樂史論課程,它主要論述西方音樂中的各種音樂現(xiàn)象的發(fā)生、發(fā)展與演變過程,以及對這種演變過程的哲理性思考。在音樂各學(xué)科的相互交叉、相互滲透的發(fā)展趨勢越來越強化和深入的情勢下,《西方音樂史》在構(gòu)建合理的“音樂理論課程體系”方面扮演著重要的角色,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因此,學(xué)習(xí)《西方音樂史》,既是對學(xué)生已有的音樂理論進(jìn)行系統(tǒng)的補充、豐富并加以整合的過程,又是對西方音樂發(fā)展中的各種歷史現(xiàn)象進(jìn)行溯源、求證、提煉的過程,同時也是對西方音樂的發(fā)展進(jìn)行人文關(guān)懷的過程。
西方音樂史首先應(yīng)當(dāng)是西方音樂本體形態(tài)嬗變的歷史,是作曲手法演進(jìn)的歷史。學(xué)習(xí)和研究西方音樂歷史的目的是認(rèn)識和揭示西方音樂在發(fā)展中的各種現(xiàn)象,和在特定歷史階段的本質(zhì),在把握這種音樂現(xiàn)象自身發(fā)展的邏輯關(guān)系的同時,來探求它賴以產(chǎn)生的歷史環(huán)境以及它的發(fā)展與人、與社會發(fā)展的內(nèi)在聯(lián)系。音樂歷史的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于音樂自身發(fā)展的內(nèi)在邏輯。這種內(nèi)在的發(fā)展邏輯,具體體現(xiàn)在不同時代的音樂作品的表現(xiàn)形態(tài)和結(jié)構(gòu)形式——創(chuàng)作手法,即作曲家的作曲技法的演變上。可以這樣說,作曲手法是特定時代的作曲家的精神活動的結(jié)晶,它反映出音樂的具體物質(zhì)形態(tài)與物化的表象細(xì)節(jié)。因此,“在音樂史研究中,固然必須了解不同時期有關(guān)音樂體裁和風(fēng)格的某些史實,但更重要的是了解音樂本身。史實不過是干巴巴的骨架,只有音樂才能賦予骨架以生命和意義。”①音樂作品反映音樂歷史的本真面貌,或者說,真正的血和肉是音樂的本身。因此,我們在《西方音樂史》的教學(xué)與研究中,不能僅僅停留在對音樂史實的觀察、對音樂現(xiàn)象的“外圍性”考察,而應(yīng)當(dāng)深入音樂的內(nèi)部去分析。從根本上來說,對一部音樂作品或者一個時代乃至整個音樂發(fā)展的歷史的認(rèn)識與理解是離不開對音樂本體的具體聲音結(jié)構(gòu)和技法層面的分析與探究的。正如中央音樂學(xué)院的黃曉和教授所說的那樣:“研究音樂本體,無論如何,始終應(yīng)該是音樂學(xué)的核心的核心。”②因此,我們在《西方音樂史》的學(xué)習(xí)與研究中,如果想獲得音樂的完整印象和對音樂的深刻理解,就應(yīng)該把音樂本體的分析納入教學(xué)的重要、有機(jī)的組成部分,力求更多地從音樂本體的嬗變軌跡及其因果關(guān)系中找出并理清音樂發(fā)展的線索。以此證明在空間和時間上鳴響著、流動著的音樂,是怎樣作用于聽眾,怎樣發(fā)揮著它的藝術(shù)效應(yīng)和美學(xué)效應(yīng)的。況且,由于音樂自身缺乏語言藝術(shù)中的那種語義性和造型藝術(shù)中的那種具象性,因而在接觸音樂作品的內(nèi)涵問題時,是很難將內(nèi)涵與聲音形式這二者分割開來而完全采取二元化方式進(jìn)行闡釋的。由此可見,音樂藝術(shù)本身的特性也決定了我們在《西方音樂史》教學(xué)中必須以音樂為本,切實加強音樂本體分析在教學(xué)與研究中的重要地位。
具體說來,《西方音樂史》教學(xué)中的音樂本體分析,是對作曲家的作品從宏觀與微觀兩個維度所進(jìn)行的解構(gòu)性的分析。從宏觀的角度來說,是對作品本身的體裁、形式的認(rèn)識與判斷;從微觀的角度來說,是對音樂形式賴以產(chǎn)生和建立的“物質(zhì)材料”所進(jìn)行的再認(rèn)識,即:對作品的旋律特征、音的組織手段、和聲、結(jié)構(gòu)布局、織體、配器方法等進(jìn)行深入的認(rèn)識與理解。事實上,通過音樂本體分析,我們能夠?qū)崿F(xiàn)對作曲家創(chuàng)作過程及其創(chuàng)作手法的認(rèn)知與辨識,感受到作曲家的創(chuàng)作思維歷程。眾所周知,任何一位作曲家的藝術(shù)經(jīng)驗與技巧的成熟都需要有一個錘煉的過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音樂的發(fā)展正是無數(shù)作曲大師在對作曲手法進(jìn)行錘煉、創(chuàng)新與發(fā)展中而不斷發(fā)展的。而正是作曲家在創(chuàng)作中的不斷求異與創(chuàng)新,推動了音樂創(chuàng)作與音樂思維的不斷發(fā)展,最終推動了西方音樂文明的不斷發(fā)展。可以這樣說:“如果沒有音樂技術(shù)手段的充實,音樂本身的豐富多彩也就不可能想象。”③作曲技術(shù)不僅為創(chuàng)作者提供了音樂創(chuàng)作的技術(shù)手段,更重要的是,它為創(chuàng)作者提供了某種音樂創(chuàng)作的思維方式。作曲技術(shù)“具有一種相似于藝術(shù)思維的特性,或者說,技巧操作就是創(chuàng)作中藝術(shù)思維的一種具體方式。因此,運用技巧對經(jīng)驗進(jìn)行處理時,無異于如此這般地來感受、來體驗、來思考。”④作曲家的創(chuàng)作正是把他所處的特定歷史時代、特定歷史環(huán)境的情感,通過特定的音樂表達(dá)方式而加以表現(xiàn)。當(dāng)然這種特定的表達(dá)方式,是作曲家通過學(xué)習(xí)、繼承、借鑒、融合、吸收那一時代的特有的創(chuàng)作手法,并開拓出新的創(chuàng)作手法而以具體的音樂形式表現(xiàn)出來。因此,不管是作曲家的個人情感,還是他所采用的特有的表達(dá)方式,都深深地打上了鮮明的時代烙印。換句話說,音樂技法的特征從一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特定時代的觀念和思想。作曲家在具體的音樂創(chuàng)作過程中,除了彰顯出作曲家的個性和個人情感之外,同時也傳達(dá)出作曲家對于人、對于社會的諸多體驗與思考。偉大的音樂藝術(shù)家最能敏感地感覺到現(xiàn)實的苦難,并通過自己所擅長的藝術(shù)手段,表達(dá)出自己以及同時代人的心靈與嘆息。作曲家在創(chuàng)作中包容著深刻的苦難、絕望和悲泣,也創(chuàng)造出幻想、夢境、美好的天國,竭力以“希望”來彌補人們現(xiàn)實的“缺憾”。 人是歷史的人,也是社會的人,作曲家也不例外。在《西方音樂史》教學(xué)中進(jìn)行音樂分析的最終目的是關(guān)注音樂家以及他所處的時代的音樂觀念和思想。我們在對音樂作品進(jìn)行分析的同時,實際上是在有意識與無意識中走進(jìn)了音樂家的現(xiàn)實生活、實現(xiàn)了與作曲家面對面的交流與溝通,貼近并融入了音樂家的現(xiàn)實體驗與情感領(lǐng)域,同時也直接地觸摸到作曲家及其同時代人的心靈脈搏。從這個意義上來說,如果要從更高的層面上求得對于西方音樂歷史的認(rèn)識、理解與把握,不使音樂歷史的學(xué)習(xí)與研究成為“空中樓閣”,首先就應(yīng)當(dāng)立足于對音樂本體的充分認(rèn)識、理解與把握。究其根本,在學(xué)習(xí)西方音樂史的過程中,作品分析是觀照歷史的基礎(chǔ),是認(rèn)識和揭示音樂本真狀態(tài)的根本途徑,是實現(xiàn)人文關(guān)懷的最佳方式。
如果從加強音樂本體分析的角度來審視現(xiàn)今高師《西方音樂史》的教學(xué)現(xiàn)狀,情況卻令人擔(dān)憂。從教材來看,各地使用的高師《西方音樂史》教材大多使用的是“編年史式”的音樂史。這類教材是通過著作者的“一己之見”回答了音樂的“什么”,而對于其“為什么”卻缺乏邏輯分析與論述。這類教材對具體的音樂本身較少關(guān)注或漠不關(guān)心,因而,缺乏對音樂的情感體驗和歷史深度,其理論思考的結(jié)果就如同“海市蜃樓”。好的《西方音樂史》教材應(yīng)當(dāng)既有對史實的客觀描述,又要對作曲家的作品技術(shù)手段進(jìn)行邏輯分析與論證,并把作品放置在作曲家所處的時代、社會、政治及心智的范疇里去探究他的作品的時代意義,對這些史實與作品本身進(jìn)行理性的思考。音樂史不是音樂事件的記錄,它只能由音樂作品構(gòu)成,事件及其記載不能取代作品在音樂史學(xué)中的主導(dǎo)地位。從現(xiàn)實教學(xué)來看,一個普遍的教學(xué)模式也是停留在史實敘述的層面,這從很大的程度上反映出教師在這一學(xué)科的教育教學(xué)觀念的嚴(yán)重滯后。有的教師熱衷于向?qū)W生介紹作曲家的奇聞軼事,更有甚者干脆就照本宣科,著實把《西方音樂史》上成枯燥乏味的“閱讀課”。致使學(xué)生的思維停留于音樂知識的表層,其直接結(jié)果是阻斷了學(xué)生的自主思考與判斷力,扼殺了學(xué)生的認(rèn)識事物規(guī)律中的探究性思維,使學(xué)生最終遠(yuǎn)離了音樂,遠(yuǎn)離了西方音樂文化。
因此,在高師《西方音樂史》的教學(xué)中,教師應(yīng)該強化“以音樂為本”的教學(xué)觀念,把握音樂本體才是學(xué)習(xí)和研究西方音樂的“硬道理”,切實把教學(xué)重點與教學(xué)難點放在各階段的音樂自身特點的分析與歸納。這種教學(xué)方法會使學(xué)生對音樂本身“有極為豐富的感性知識,對不同時代、不同個性的作品能夠從直覺上去把握音樂,既能夠深入到音樂內(nèi)部從微觀上進(jìn)行分析,又能夠從宏觀上從史學(xué)、美學(xué)、社會思潮等方面進(jìn)行綜合考察。”如今,在大力提倡教學(xué)與科研齊頭并進(jìn)的高等教育中,作為培養(yǎng)未來音樂教師的搖籃和前沿陣地的高師音樂院系,要培養(yǎng)出注重“理論與實踐相結(jié)合”、對西方音樂十分敏感、熱愛西方音樂文化的未來中小學(xué)音樂教師,認(rèn)識到《西方音樂史》教學(xué)中“以音樂為本”“以人為本”的施教觀念是至關(guān)重要的。為穩(wěn)步提高高師《西方音樂史》的教學(xué)與科研,教師應(yīng)該帶領(lǐng)學(xué)生在音樂發(fā)展的歷史紛繁中,在不同時代、不同作曲家的樂譜和豐富的音響圖畫的編織中停駐,去尋覓、去思忖、去感悟,然后進(jìn)行純粹的感性體驗之外的深層思考。
注釋:
①(美)唐納德·杰·格勞特、克勞德·帕利斯卡著,《西方音樂史》,汪啟璋、吳佩華、顧連理譯,北京:人民音樂出版,1996年版,第37頁。
②黃曉和,《要關(guān)注音樂本體的研究》,原載于《中央音樂學(xué)院學(xué)報》,1995年第2期,第91頁。
③(德)格奧爾格·克內(nèi)普勒著,《19世紀(jì)音樂史》,人民音樂出版社,2002年版,第1頁。
④童慶炳主編,《現(xiàn)代心理美學(xué)》,中國社會科學(xué)出版社,1993年版社,第440頁。
參考文獻(xiàn):
[1]于潤洋著《西方史論新稿》,人民音樂出版社,2003年版。
[2]李應(yīng)華《對“基督教與西方音樂文化問題”的重新思考》,原載于《中國音樂學(xué)》,1991年第3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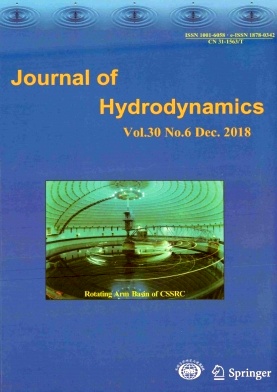
濟(jì).jpg)
導(dǎo)科學(xué)論壇.jpg)
生學(xué)報.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