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樂史寫作:藝術(shù)與歷史的調(diào)解
楊燕迪
《音樂史學(xué)原理》① 一書似乎只能出自德國(guó)學(xué)者之手——因?yàn)樗乃季S深度和力度,也因?yàn)樗囊曇皩挾群蛷V度。當(dāng)然,此書所關(guān)心的主題對(duì)象——音樂及其歷史——本來就是德國(guó)文化的精粹所在。而作者達(dá)爾豪斯(Carl Dahlhaus, 1928~1989)② 在觸及這個(gè)主題對(duì)象時(shí),論述角度又帶有濃重的哲學(xué)辯證色彩,這就進(jìn)一步加重了此書的“德國(guó)性格”。音樂圈中,時(shí)常聽到“德國(guó)式的演奏”與“德國(guó)式的音色”的說法。與此相仿,在本書中,我們就遇到“德國(guó)式的思辨”與“德國(guó)式的寫作”。 這種德國(guó)式思辨與寫作的特色之一是刨根問底:透視習(xí)以為常的現(xiàn)象,以洞察旁人未見的本質(zhì);剖析法定認(rèn)可的慣例,以追問心照不宣的前提。依照一般的看法,音樂的歷史,無非就是音樂發(fā)展歷程的記錄與解說,人物、作品的編年整理,風(fēng)格、流派的脈絡(luò)爬梳,外加時(shí)代精神、思想氛圍以及社會(huì)建制等等方面的編織架構(gòu),林林總總,錯(cuò)落有致,也就此可以宣告音樂史這個(gè)特殊學(xué)術(shù)寫作樣式的成立與成型。但在達(dá)爾豪斯這個(gè)具有典型“德國(guó)式頭腦”的學(xué)者眼中,事情遠(yuǎn)不是這么簡(jiǎn)單。在這本原來被命名為Grundlagen der Musikgeschichte的論著中,達(dá)爾豪斯從自己撰寫《十九世紀(jì)音樂》③ 一書以及多年從事音樂史研究的實(shí)際經(jīng)驗(yàn)出發(fā),對(duì)音樂史寫作過程中所遇到的問題和疑難進(jìn)行了非常德國(guó)式的根本性反思與哲學(xué)性論辯。德文Grundlagen一詞,原本即“基礎(chǔ)”、“基底”、“基位”之意,此書的英文版也將該詞直譯為Foundations(of Music History),意在指明此書的宗旨在于對(duì)音樂史寫作的基礎(chǔ)理念進(jìn)行刨根問底式的追究。但中譯本如果照字面意思將此書譯為《音樂史基礎(chǔ)》,由于“基礎(chǔ)”一詞在漢語中的文化聯(lián)想與德語的Grundlagen或英文的Foundations在各自語境中的意涵都相當(dāng)不同,弄不好會(huì)誤導(dǎo)讀者以為此書是一本介紹音樂史常識(shí)的入門讀物。出于上述考慮,就此書的實(shí)際內(nèi)容而論,譯者覺得《音樂史學(xué)原理》才是更為妥帖的書名。 “這是世界上所有語言中第一部針對(duì)音樂歷史哲學(xué)的透徹研究論著”——?jiǎng)虼髮W(xué)出版社1983年的英譯本封底上對(duì)此書這樣隆重推薦。但大有深意的是,這樣一本似乎全然屬于學(xué)理探究的“純學(xué)術(shù)”著作,其寫作前提卻依然帶有強(qiáng)烈的時(shí)代意識(shí)形態(tài)印記。此書的德文原著出版于1977年。我們應(yīng)該清晰記得,當(dāng)時(shí),東西方之間的“冷戰(zhàn)”對(duì)峙正處于膠著狀態(tài),緊張中帶有妥協(xié),敵視里含著理解。達(dá)爾豪斯作為“前西德”陣營(yíng)中最具聲望的音樂學(xué)界領(lǐng)軍人物,在與“前東德”的同行們面對(duì)面進(jìn)行學(xué)術(shù)爭(zhēng)論時(shí),自然不可能脫離當(dāng)時(shí)的思想成見與政治氣候。馬克思主義,作為社會(huì)主義陣營(yíng)的綱領(lǐng)性思想基礎(chǔ),當(dāng)然成為東歐國(guó)家集團(tuán)人文/社會(huì)科學(xué)的哲學(xué)/方法論前提。東歐國(guó)家中的音樂史學(xué),自然而然均屬于“馬克思主義”旗下的音樂史寫作。此外,以德國(guó)法蘭克福學(xué)派為代表的西方馬克思主義,在上世紀(jì)六七十年代可謂風(fēng)頭正健。達(dá)爾豪斯身處這樣的時(shí)代大背景中,如果要對(duì)音樂史學(xué)的哲學(xué)基礎(chǔ)進(jìn)行辨析和論說,他所遇到的第一個(gè)回應(yīng)對(duì)象,必然就是馬克思主義。 這就是為何達(dá)爾豪斯在此書的“作者序言”中,很快就公開亮牌,立馬開始對(duì)馬克思主義進(jìn)行評(píng)說。如果不了解上述時(shí)代背景,當(dāng)下的讀者很可能會(huì)犯糊涂——達(dá)爾豪斯為何偏偏對(duì)馬克思主義如此“耿耿于懷”。在此書的展開過程中,讀者也常常感到,馬克思主義的“幽靈”或隱或顯,幾乎從來沒有離開過論爭(zhēng)的戰(zhàn)場(chǎng)。不僅如此。達(dá)爾豪斯甚至專門動(dòng)用了整整一章(第八章)的篇幅來論述他所認(rèn)為的馬克思主義音樂史學(xué)中的關(guān)鍵性范疇:音樂史寫作中,如何處理音樂作為上層建筑與經(jīng)濟(jì)作為基礎(chǔ)支撐之間的關(guān)系。有意思的是,達(dá)爾豪斯自己也清楚地認(rèn)識(shí)到,他的這種姿態(tài),恰恰證明了馬克思主義意識(shí)形態(tài)批判所具有的尖銳性,確乎一針見血——“只要挑選一個(gè)課題,贊同或者反對(duì)某種立場(chǎng)已是不可避免……在馬克思主義者看來,明顯的偏見和潛在的偏見,兩者必居其一。”(中譯本,頁2——下同)看來,達(dá)爾豪斯針對(duì)馬克思主義的種種回應(yīng)以及在本書中的其他學(xué)理研究,恰恰無不反映出馬克思主義的這樣一個(gè)觀點(diǎn)的正確性——無論任何學(xué)者,不論從事貌似多么“純粹”的學(xué)術(shù)性研究,其背后都會(huì)有某種意識(shí)形態(tài)的基礎(chǔ)作為原因驅(qū)動(dòng),差別僅僅在于,學(xué)者對(duì)這種意識(shí)形態(tài)動(dòng)因是否具有清醒的自覺。 因此,似有必要提醒,達(dá)爾豪斯此書中的論辯口吻和爭(zhēng)論筆調(diào)其實(shí)是有針對(duì)性的。令人感慨的是,就在達(dá)爾豪斯逝世后(1989年)不久,時(shí)局大變,“冷戰(zhàn)”被“后冷戰(zhàn)”所替代。在東歐諸國(guó),馬克思主義不再作為國(guó)家意識(shí)形態(tài),而更多成為民間性的思想力量。由此,現(xiàn)在的西方讀者如果再來閱讀達(dá)爾豪斯這本書,感覺一定與七八十年代迥然相異。然而,對(duì)于處在當(dāng)前情境中的中國(guó)讀者,達(dá)爾豪斯這些針對(duì)馬克思主義學(xué)說的積極回應(yīng),盡管是在30年前,似乎依然具有直接的刺激感,鮮活而敏銳。畢竟,我們相信,處在中國(guó)的思想語境中,馬克思主義的文化學(xué)者都愿意聽到,也樂意看到,一個(gè)富有原創(chuàng)性思想的西方音樂學(xué)者是在如何應(yīng)對(duì)馬克思主義的質(zhì)問。 具體到音樂史學(xué)領(lǐng)域,達(dá)爾豪斯念念不忘的中心理論問題是,藝術(shù)與歷史之間,如何達(dá)成協(xié)調(diào),如何企及平衡。也就是說,怎樣寫作這樣一種音樂史,它能夠同時(shí)合法地處理音樂作為一種“審美藝術(shù)”的方面和音樂作為一種“歷史過程”的維度。這個(gè)問題當(dāng)然不是一個(gè)新問題,而是一個(gè)所有藝術(shù)史分支(包括文學(xué)史、美術(shù)史在內(nèi))都面臨的老問題。進(jìn)入近現(xiàn)代(Modern)以來,藝術(shù)中“現(xiàn)代性”(modernity)的表征之一,就是在“自律性美學(xué)”的理念指導(dǎo)下,將分離的、自足的作品視為藝術(shù)的中心范疇。卓越的藝術(shù)作品雖然產(chǎn)生于具體的歷史時(shí)空,受制于具體的文化條件,但它們最終超越自己的時(shí)代,針對(duì)每一個(gè)時(shí)代“說話”,從而具有了明確的當(dāng)下現(xiàn)時(shí)感。而歷史作為一種敘事寫作,它卻必須以線性的聯(lián)系和歷時(shí)的發(fā)展作為脈絡(luò),以敘述的連續(xù)和因果的邏輯作為前提。因此,在音樂史的視野中,藝術(shù)作品必須要被重新放回到它產(chǎn)生時(shí)的歷史環(huán)境和文化條件中去。于是,這中間就產(chǎn)生了在達(dá)爾豪斯的“德國(guó)式頭腦”看來問題嚴(yán)重的“二律背反”——“藝術(shù)”與“歷史”之間的緊張和矛盾: “音樂的歷史,作為一種藝術(shù)的歷史,似乎注定要失敗:一方面,音樂史受到來自‘審美自律論’的壓力;另一方面,音樂史遭到執(zhí)著于‘連續(xù)性’概念的歷史理論的攻擊。音樂史,要么不是‘歷史’,要么不是‘藝術(shù)’的歷史。”(頁37) 這也就是說,“寫作藝術(shù)史是一種自相矛盾的企圖,寫成歷史的只是藝術(shù)中那些根本不是藝術(shù)的方面”(頁45)。“歷史”與“藝術(shù)”之間的對(duì)立與調(diào)解這個(gè)復(fù)雜的課題,就像古希臘傳說中的達(dá)摩克利斯之劍,似乎一直高懸在達(dá)爾豪斯的頭頂,令他無法釋懷。他甚至在整本書中刻意貫穿性地使用了凸顯的斜體字(在筆者的中譯本中更換為楷體)來強(qiáng)調(diào)“歷史”和“藝術(shù)”(或“音樂”)兩個(gè)范疇在藝術(shù)史寫作中的矛盾關(guān)系,以期在行文中特別引起讀者的注意(見頁37、64、184、187、192、194)。 在達(dá)爾豪斯看來,由于馬克思主義的“左派”意識(shí)形態(tài)批判的質(zhì)疑,這個(gè)悖論無疑變得更加刺目。通過意識(shí)形態(tài)批判的透視鏡,“作品”、“審美”、“藝術(shù)”、“自律論”、“偉大人物”、“超越時(shí)代性”等等原本在傳統(tǒng)美學(xué)中都處于統(tǒng)治地位的概念范疇,一概都暴露出具有根深蒂固的時(shí)代局限,都受制于某種特定的歷史條件和環(huán)境。在這樣的觀念指導(dǎo)下,音樂史的天平開始劇烈搖晃起來。達(dá)爾豪斯于是感到深深的不安。 因?yàn)楦械綁毫Γ员仨氂瓚?zhàn)。達(dá)爾豪斯首先對(duì)傳統(tǒng)的音樂史寫作路數(shù)——“風(fēng)格史”——進(jìn)行發(fā)難(見頁26以后,不過達(dá)爾豪斯的相關(guān)論述語焉不詳,稍嫌簡(jiǎn)略)。隨后,在整個(gè)第二章中,以“歷史性和藝術(shù)性”點(diǎn)題,他從正面周詳觸及了上述的“音樂史悖論”問題。在對(duì)音樂歷史觀和音樂審美觀的具體關(guān)系進(jìn)行了一番思辨性的歷史考察和理論探究之后,達(dá)爾豪斯對(duì)“藝術(shù)”與“歷史”之間的調(diào)解與平衡進(jìn)行了理直氣壯的辯護(hù),并提出了自認(rèn)可行的理想方案: “調(diào)解審美自律性和歷史性,這種可能性一定存在。既不貶低音樂作品的歷史維度,也不違背音樂作品的審美維度;既不喪失陳述的連貫性,又不犧牲藝術(shù)的概念——在目前,藝術(shù)的概念遇到了危險(xiǎn),但近幾十年來的企圖并沒有從根本上動(dòng)搖它的地位。但是,審美和歷史之間的調(diào)解只能產(chǎn)生于這種詮釋——它通過揭示包含在作品本身之中的歷史,讓我們看到個(gè)別作品在歷史中的位置。藝術(shù)史的最終辯護(hù)來自于,歷史學(xué)家能在多大程度上從作品的內(nèi)在建構(gòu)中讀解到作品的歷史性質(zhì);否則,藝術(shù)史仍然只是一種做作的人工安排,從外部強(qiáng)加于藝術(shù)和藝術(shù)作品。”(頁49) 這是一段具有綱領(lǐng)性重要地位的宣言,值得細(xì)細(xì)品讀。顯然,在這個(gè)微妙的平衡狀態(tài)中,達(dá)爾豪斯作為一個(gè)音樂史家,他的重心仍然偏于“審美”/“藝術(shù)”一方——因?yàn)椤白髌贰钡臋?quán)重在這個(gè)調(diào)解過程中被置于更加重要的地位。音樂的歷史,如果它不違背自己的“審美”天職,它就必須“揭示包含在作品本身之中的歷史”,就應(yīng)該“從作品的內(nèi)在建構(gòu)中讀解到作品的歷史性質(zhì)”。這里的深層含義是,音樂史雖然是一種歷時(shí)性的敘事安排,但在其中,個(gè)別、具體的音樂作品卻不能僅僅被當(dāng)作時(shí)代風(fēng)潮中的一種陪襯,或僅僅被作為歷史過程中的一個(gè)環(huán)鏈。在前者,作品的獨(dú)立性質(zhì)被歪曲,因而成為背景式的“附庸”;在后者,作品的審美高度被降格,于是成為例證式的“文獻(xiàn)”。無論何種情況,達(dá)爾豪斯認(rèn)為,在這樣的音樂史寫作中,音樂的“藝術(shù)性”都遭到背叛。
科技.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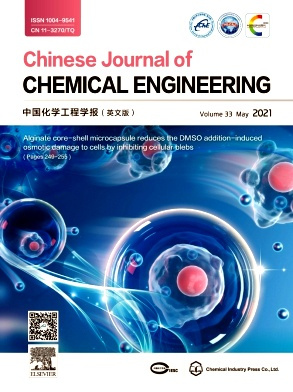
稅.jpg)
秀作文選評(píng).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