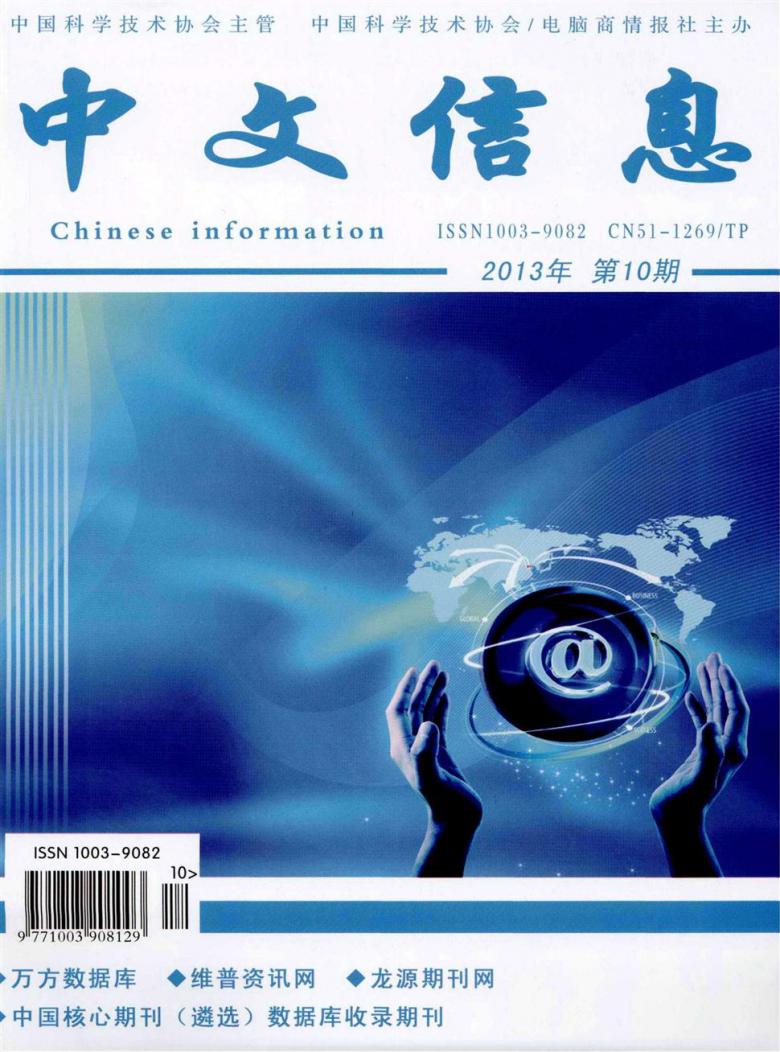淺論教育倫理學分析對象再認識
劉新春 呂志
論文關鍵詞:教育倫理學研究對象再認識
論文摘要:歐美、日本、前蘇聯(lián)教育倫理學研究對象可概括為道德教育、教師職業(yè)道德和教育的社會倫理基礎三種類型.我國教育倫理學一直未突破教師職業(yè)道德的研究框架。教育倫理學應當研究教育同經濟及其他社會現(xiàn)象的關系,不能把教育倫理學研究對象同教師倫理學、德育原理等學科研究對象相混淆。
教育倫理學是教育學和倫理學所構成的交叉學科,它是不是具有獨立存在和研究的價值,上世紀初人們對此展開了長時間的爭論。通過爭論,歐美、日本、前蘇聯(lián)等教育發(fā)達國家的學界同仁對獨立研究和發(fā)展教育倫理學、加強教師教育倫理學修養(yǎng)的必要性普遍給予了肯定。這一共識,對我國也發(fā)生了重大影響。從那時起,特別是最近二十多年來,我國相繼出版了一系列教育倫理學專著、教材,對教育倫理學開展了獨立的學科建設。但是,由于在研究對象問題上見仁見智,教育倫理學學科建設進展緩慢,不盡人意。
近幾十年來,國外教育倫理學在研究什么?20世紀上半葉,英國人B·諾曼妮和G·科蒙爾合著出版《教育倫理學》一書。該書依次討論了什么是兒童、胎兒的環(huán)境、早期家庭教育、性格和氣質、性別訓練、宗教信仰、理想的學校、學校指導等問題,未對教育倫理學研究對象給予明確闡釋。但從其體系和內容上看,其論述主要集中在人格發(fā)展這一主題上,可見他們所理解的“教育倫理學”實際上是“倫理教育學”,準確地說,是一種道德教育學或者說道德心理教育學。
美國對教育倫理學研究的關注點,一開始就集中在教師職業(yè)道德建設上。20世紀20一40年代,一批美國學者如卡他斯、韋伯斯等采用嚴格的實證研究方法,概括出了一名優(yōu)秀教師應具有的職業(yè)品質和行為特征。這些研究,有的是在征集有豐富經驗的教師的意見的基礎上進行的,有的是在對成功教師與失敗教師開展品德對比的基礎上進行的,有的則分析教師職業(yè)品質與教師成功之間的相關度。1948年,全美教育委員會所屬的師范教育委員會向全美教師發(fā)表了題為《我們時代的教師》的報告,對教師應當具備的職業(yè)道德品質提出了13項要求和指導;1968年,美國國家教育協(xié)會(NEA)正式制定了《教育職業(yè)倫理準則》。70年代,這一研究在美國得到了進一步深化和細化,專家們繼續(xù)以實證方法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分門別類地對“教師品質”進行研究,形成了教師職業(yè)內部不同專業(yè)的倫理道德準則,如美國大學教授聯(lián)合會的《職業(yè)倫理聲明》、美國心理學會的《心理學家倫理標準》以及人事指導協(xié)會的《倫理標準》等。
日本有培育優(yōu)良“教師形象”的傳統(tǒng),日本對于教育倫理學的研究也正是從培育“教師形象”開始的。20世紀初,日本師范教育改革家野口援太郎提出要培養(yǎng)人格主義的“理想”教師。二戰(zhàn)以后,廣大日本民眾從軍國主義的噩夢中驚醒,教育界提出培養(yǎng)民主主義的“現(xiàn)代教師”。1952年,日本教職員組織通過了《倫理綱領》,以此作為教師職業(yè)道德建設的指南。20世紀60年代以來,日本民間對教育倫理學的研究日趨增多,出版了一系列關于教師職業(yè)倫理和教師職業(yè)道德修養(yǎng)的專著和教材。如,日本當代著名教育家、原玉川大學總長小原國芳撰寫了《師道》一書,對于師道的本質、內容和發(fā)展條件等做出了有益探討。日本著名教育家、原廣島大學校長皇至道,出版了《人類教師與國民教師》一書,書中極力推崇瑞士教育家J·H·裴斯泰洛齊關于教師“愛”的品質。著名教育家、廣島大學教授新崛通則強調教師以身作則的精神,他在《現(xiàn)代教育講座》一書中說:“教師應當為人楷模,教師以身作則在道德教育中乃至整個教育過程中起決定性的作用。”長期以來,日本都以教師職業(yè)道德作為教育倫理學的研究對象,十分重視對師范生教師職業(yè)倫理道德的教學和教育,教育倫理學是日本師范生的必修課。
20世紀60年代,前蘇聯(lián)在《教師報》上開展了一場關于教育倫理的大討論,經過這場討論,教育倫理學取得了相對獨立的學科地位。1977年,·皮薩列恩科和·皮薩列恩科撰寫的《教育倫理學》出版,緊隨其后又出版了B·H·契爾那葛卓娃和H·H·契爾那葛卓夫的《教師道德》。前蘇聯(lián)十分重視教育倫理學研究,但總體上講其所確立的研究對象是教師職業(yè)道德。值得一提的是,前蘇聯(lián)在教育倫理學研究中,創(chuàng)制了“教育分寸”這一道德范疇。·科季格爾和·恰姆列爾在其所著的《教育倫理學》一書中,對“教育分寸”給予了教師職業(yè)道德的準確定位,該書認為:“‘教育分寸’的重要任務是促使在孩子身上樹立一個正面的心理背景,這個心理背景能正確接受教師的要求,而把這些要求轉變?yōu)樾袨榈膬刃膭右蛞彩潜匾摹S蟹执绲貙Υ龑W生,這意味著解決在教學過程中發(fā)生的矛盾和同時不再引起新的矛盾”。他們指出:“‘教育分寸’不是教師行為中一些個別的事情,這是行為風格。它必須使學生相信教師是友好的、體貼和善良的。這一特征大大加強了教師的道德立場,并成為學生公民覺悟的學校。”
從20世紀70年代開始,國外教育倫理學研究開始突破教師職業(yè)道德框架,出現(xiàn)新的視點。在美國,魯濱遜和莫爾頓合著的《高等教育中的倫理問題》,提出教育倫理學應研究教育內在的倫理和道德。該書分析了高等學校內部的矛盾沖突、倫理關系,提出了“公正原則”、“最大限度地實現(xiàn)利益的原則”、“普遍化原則”和“把他人當目的的原則”;剖析了學校與社會的關系、教師職業(yè)與共同職業(yè)的關系、教育中控制與維護的關系以及教學中的倫理問題、科研中的倫理問題、師資評價和教師聘用中的倫理問題。在英國,著名教育哲學教授波特斯出版《現(xiàn)代教育倫理學》,重點研究教育的社會倫理基礎,研究“正義”、“平等”、“自由”、“民主”等一般社會道德在教育過程中的體現(xiàn)。里斯·布朗也試圖從尋找正義、道德和教育的基本含義出發(fā),力求“為獨立的道德判斷提供一個倫理學基礎”,“為解釋教育中的不正義、不道德現(xiàn)象(如教育機會上的不平等)提供一個理性的基礎”。然而,從總體上講,這并非主流意識,而只是一種聲音或者說一種旁支流派。
在我國,教育倫理學研究初起于上世紀30年代,興盛于80年代。
30年代,丘景尼先生出版專著《教育倫理學》。先生認為,教育倫理學是關于道德教育的科學。教育倫理學與道德教育“二者之涵義,大體相同”,“其著重之點,不在道德本質之為如何,而在道德的人格如何養(yǎng)成”;二者之區(qū)別,僅在于“教育倫理學所討論的,大半屬于原理的問題,而道德教育所包涵的則大部分為實際的問題。”該著旨在探索道德教育原理,創(chuàng)立道德教育哲學。
1988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王正平主編、國內九所高等師范院校協(xié)作編寫的《教育倫理學》(以下稱《王本》),該書是我國建國以后出版的第一部《教育倫理學》。在教育倫理學研究對象問題上,《王本》明確提出,“教育倫理學是研究教師道德的學問”。具體地說,就是緊密結合社會教育職業(yè)勞動實踐,研究教育勞動中特有的道德意識,揭示教師道德的特點、本質和職能;研究教育勞動中的道德關系,闡明教師道德的原則、規(guī)范和范疇;研究教師職業(yè)道德的實踐活動,說明教師道德評價、教師道德修養(yǎng)以及教師職業(yè)品格形成發(fā)展的規(guī)律,從而為教師的職業(yè)道德實踐和自我道德提高提供理論與方法上的指導。在該書的《緒論》中,編者對教育倫理學的研究視域有一解釋,根據(jù)這一解釋,波特斯關于“教育的社會倫理基礎”包含在本書“道德意識”之中,但從其內容體系中考察,這一說明并未得到真正的體現(xiàn)。因此,(王本》關于教育倫理學研究對象的說明是現(xiàn)代的,實際操作是傳統(tǒng)的。其精彩之筆,在于研究了教育過程中豐富多樣的道德關系,具體地提出了教育行為規(guī)范并明確告訴教師哪些行為是善的,哪些行為是惡的。
1989年,上海科學普及出版社出版了施修華、嚴緣華主編的《教育倫理學》(以下稱《施本》),該書認為,“教育倫理學是關于教師及參與教育過程的其他人員的道德問題的一門科學,是研究教育過程中的道德現(xiàn)象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的學說。”同《王本》相比較,《施本》擴大了教育倫理學的研究對象范圍,將“教師”擴大為“教師及參與教育過程的其他人員”。進一步強化了“師德”在教育倫理學研究對象中的核心地位,他說:“如果離開了對教師道德現(xiàn)象的高度概括,如果離開了對教育過程中人與人之間道德關系的研究,就不可能建立科學的教育倫理學體系。”還提出了教育倫理學與教師道德思想的區(qū)別,他說:“教育倫理學同教師道德思想的關系是既有區(qū)別又有聯(lián)系的。教師道德思想的形成早于教育倫理學,最早的教師道德思想早在古代奴隸社會就已產生。而教育倫理學的創(chuàng)立,則是最近幾十年的事情。教育倫理學是……教師道德思想的理論化和體系化。古代社會雖然己有了教師道德思想,但都是零碎的、不完整的,有的甚至還是錯誤的。”
1990年,天津教育出版社出版陳旭光主編的《教育倫理學》(以下稱《陳本》)。《陳本》在《施本》的基礎上,進一步對教育倫理學的研究對象進行了擴充增容,把教育過程中廣泛涉及的教師學生、教學內容和教學手段都作為教育倫理學考察的對象。該書以人格教育為邏輯起點,系統(tǒng)地分析了教育過程中倫理因素對教師、學生人格完善的影響,揭示了教育倫理的形成規(guī)律,探尋了教育倫理的價值,闡明了教育倫理的三條原則。南京師范大學魯潔教授為該書作序,評價該書“具的一定的見解和特色。” 1993年,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出版了李春秋教授主持編寫的《教育倫理學概論》(以下稱《李本》)。該書認為,教育倫理學是研究教育的倫理道德價值和教師職業(yè)道德的科學。《李本》的重大貢獻之一,在于提出了廣義教育倫理與狹義教育倫理之分。他說,廣義教育倫理,即怎樣確立教育在社會生活結構中或體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評價人們對教育的態(tài)度以及社會應該賦予教育什么樣的性質和目標等等。狹義的教育倫理,即教育應包括哪些內容,德育在教育中占何種地位,教育應遵循什么樣的道德原則,教育過程能夠培養(yǎng)出具有什么樣品質、才能的人,作為教育工廠的工程師—教師應當具有什么樣的職業(yè)道德,作為受教育的學生抱什么樣的學習態(tài)度等等。對教育倫理學的研究對象,《李本》有兩處專門回答,大同小異,他說:“教育倫理學主要以教育過程參加者的道德關系為研究對象,并具體研究作為道德關系的反映和表現(xiàn)的教師道德現(xiàn)象。具體地說,就是……概括教師道德要求的內容、教師道德要求的內化以及教師道德行為的選擇等問題。”《李本》對教育倫理學研究對象的界定,明顯排斥了廣義教育倫理,只就狹義教育倫理做出了表述。
2000年,錢煥琦、劉云林教授收羅古今中外各家學說推陳出新所撰寫的一部學術專著《中國教育倫理學》(以下稱《錢本》)出版。這是一部視野開闊、力透紙背的新著作。是當前國內同類專著、教材中材料最新、信息量最大、可讀性最強的一部書。該著有“王者”風范,大有擺開集以往研究大成開一學術新時代的大架勢。在教育倫理學研究對象問題上,《錢本》在考察了中外b種不同學術見解的基礎上提出:“教育倫理學是研究包括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在內的教育教學過程中的道德關系的一門科學。”但《錢本》的內容結構大大超出了其所表述的研究對象范疇,既考察了教育倫理的實踐基礎、基本原則,考察了學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會教育的倫理規(guī)范,也考察了教育倫理評價和教育道德修養(yǎng),特別是把《王本》只作為道德規(guī)范范疇的“教育公平”、“教育威信”列為專章考察,在我國教育倫理學學科建設上第一次吸收了波特斯關于以“教育的社會倫理基礎”為研究對象的認知理念,體現(xiàn)了對西方當代教育倫理學研究新成果的借鑒。
綜上所述,中外教育倫理學研究,其研究對象可概括為三種類型:道德教育型、教師職業(yè)道德型和教育的社會倫理基礎型。道德教育型以B·諾曼妮和G·科蒙爾為代表,丘景尼先生對教育倫理學研究對象的認識,明顯地受到了B·諾曼妮和G·科蒙爾合著的《教育倫理學》一書的影響。這一認識,現(xiàn)已逐步淡出學術領域。這種“教育倫理學”,在我國已被《思想政治教育學》、《道德教育原理》、《德育原理》所取代。第二種類型最為普遍和典型,歐美、日本、前蘇聯(lián)以及我國的學術界,長期以來大多數(shù)學者都以教師職業(yè)道德作為教育倫理學的研究對象。2003年,北京師范大學教育學院教授檀傳寶在其所著的《教師倫理學專題》一書中仍對這一界說給予了解析與辨護,他說:“教育倫理學是一個比教師倫理學更寬泛的概念,但就學校教育而言,這兩個概念基本相似。”又說:“教師倫理學(或教育倫理學)是關于教育倫理智慧或教師道德及其規(guī)范的學問。就學科性質來說,它主要是一門規(guī)范和應用的倫理學。”筆者認為,這一認識雖然秉承了傳統(tǒng),但仍然是錯誤的。教育倫理學有別于教師倫理學,教育倫理學、教師倫理學甚至有別于教師職業(yè)道德方面的學問。
為說明這一問題,不妨先作一循名求實的學理研究。倫、理二字在中國古代很早就已出現(xiàn),《禮記·樂記》中說:“八音克諧,無相奪倫。”“倫”指和美樂章中的不同節(jié)奏或旋律,強調其不可混同的實然存在性。還有一種解釋,“倫者,輪也”。一輛車子有兩個輪子才能運轉,強調事物之間的協(xié)調。“倫者,綸也。”綸線貫穿方為布,可引申為關系。總之,“倫”是一種關系,是一種相互協(xié)調、和諧的關系,而這種關系是實然存在的。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倫”主要用于指稱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孟子》有言:“察于人倫”。趙歧在解釋孟子所謂的倫的含義時說:“倫,序……識人事之序。”東漢鄭玄在注《小戴禮記》時也說:“倫,親疏之比也。”在古代,人們以為人與人之間的關系是固有的、不可偕越的,因而孔子謂之“名分”。“理”是中國古代哲學的核心概念之一,莊子說:“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時有明法而不議,萬物有成理而不說。”如果說在中國古代文化中“倫”指一種實然,“理”則更向前跨進一步,具有濃厚的先驗性特征。以今觀之,倫理是一個客觀的關系范疇,是道德產生的基礎和道德修養(yǎng)的終極依歸;而不是道德原則、道德規(guī)范、道德評價、道德修養(yǎng)本身。因此,教育倫理學的研究對象應當是教育同經濟及其他社會現(xiàn)象的關系。其任務是解述教育同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宗教以及人類之間的實然、應然關系,求證教育的社會倫理基礎。
道德不是倫理學的研究對象。“道”者有同于“理”,春秋時謂之“道”,宋明時謂之“理”。“道德”之意不在“道”而在“德”,“德”者,“得也”。“得”有正負向度,背于“道”的負性之“得”不能謂之“德”;只有合乎“道”的正向之“得”方可謂之“德”。朱熹說:“德者,得其道于心而不失之謂也。”道德是道德學的研究對象,研究讓人“‘得’什么”,所要解決的問題是基于一定倫理而產生何種思想和行為要求、準則、規(guī)范。具體到教育倫理學研究對象的探討,可哄說教師道德不是教育倫理學的研究對象,而是教師道德學的研究對象。鑒于建國以來,不曾產生“道德學”這一稱謂,也不曾產生“教師道德學”這一稱謂,可以約定俗成以“倫理學”和“教師倫理學”代稱,但必須明白的是,這是“倫理學”的廣義泛用。特別值得注意的是,不能因為教育倫理學中納人了教師道德而將教育倫理學等同于教師倫理學,致使教育倫理學的主體即“倫理關系”完全被“道德要求”所取代。當前,國內也出版了一批《教師倫理學》專著、教材,如北京師范大學檀傳寶教授的《教師倫理學專題》、中南大學李建華教授的《教師倫理學》,雖體系迥異,但名實相符,很貼切也令讀來感到親切。其實,教師倫理是一個既有總原則又可以多層次、多方面、多維度、多視角分類的多學科集合體。美國近來出現(xiàn)的教師職業(yè)內部不同專業(yè)的倫理道德準則,較好地體現(xiàn)了教師道德研究的特性。
至于教師的職業(yè)道德修養(yǎng),這更不應當成為教育倫理學的研究對象,嚴格地說也不是教師倫趣學(教師道德學)的研究對象。職業(yè)道德修養(yǎng)是一個如何培育、如何內化、如何養(yǎng)成、如何熏染的教育教學方法論研究,是一個德育原理問題。如果用“倫”總概教育倫理學的學科特性,用“德”總概教師倫理學(教師道德學)的學科特性,則教師職業(yè)道德修養(yǎng)的學科特性可以一“明”字做總體概括。《大學》開篇即言:“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孟子》有言:“學則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倫也。”“明”涉及到一個途徑問題、一個方法問題、一個環(huán)境問題,更深層次的講,還有一個生理心理性內化機制問題,這些問題是《教師職業(yè)道德修養(yǎng)學》所要研究的問題。
基于以上分析,筆者認為,在中外教育倫理學研究對象的三種類型中,關于教育倫理學研究教育的社會倫理基礎的主張是科學的,有益于厘清教育倫理、教師道德、師德修養(yǎng)三個相互聯(lián)系,又相互獨立的理論和實踐范疇。有益于學科分類,推進教育倫理學的學科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