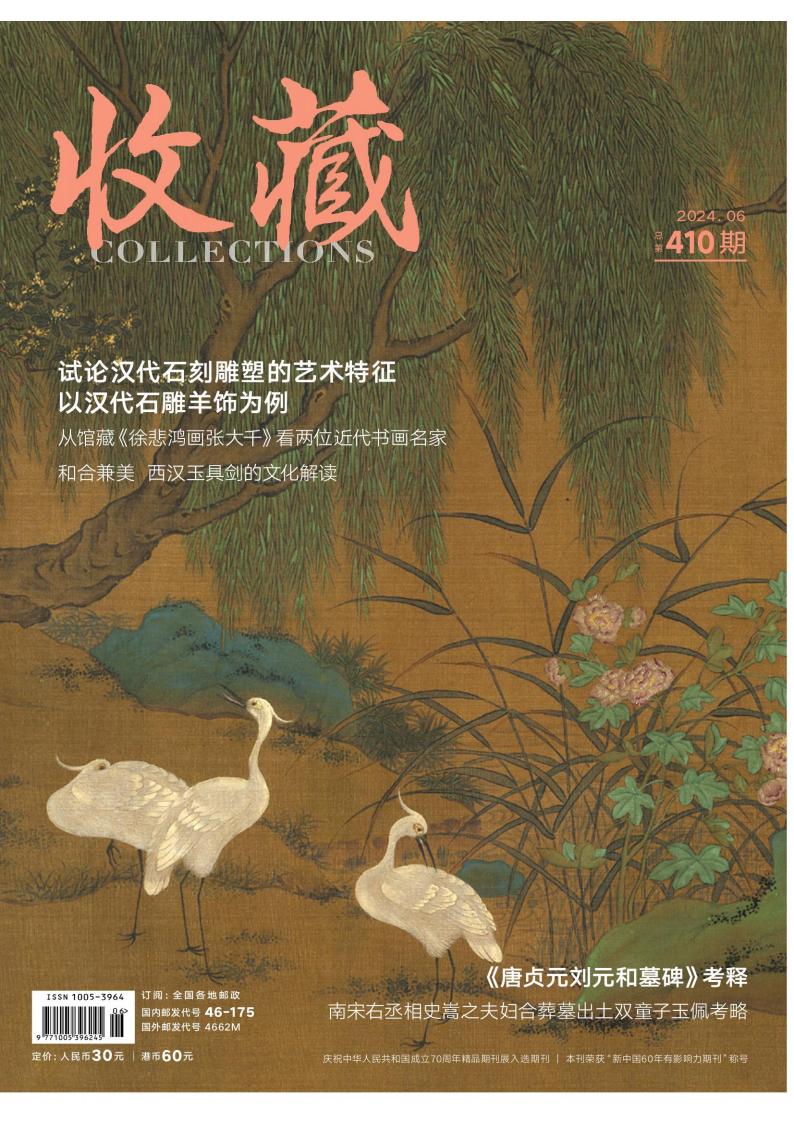二戰后美國聯邦政府干預高等教育的歷史演變
陳文干
[摘 要] 制定政策法規是美國聯邦政府干預高等教育的重要途徑之一。二戰后美國聯邦政府干預高等教育歷程大致可以劃分為四個時期:戰后初期至20世紀50年代末,是干預的謹慎時期;從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是干預的加強時期;從60年代末到加年代中期,是干預的減緩時期;從80年代中期以來,是干預的持續時期。本文分析了上述各個歷史時期主要的聯邦高教政策法規對高等教育的影響,并總結了聯邦政府通過制定政策法規干預高等教育的若干特點。
[關鍵詞] 聯邦政府 政策法規 干預 高等教育
美國聯邦憲法沒有賦予聯邦政府管理高等教育的權力,美國實行的是州管高等教育的制度,然而,聯邦政府不僅從其建立之初就開始介入高等教育事務,而且自二戰以來介入越來越深,聯邦政府通過制定政策法規等多種方式相當巧妙地對高校的發展予以重大影響。二戰后半個多世紀里,美國高校自治與聯邦政府的干預在動態平衡中推動高等教育長足發展,其經驗值得關注和研究。
制定政策法規是聯邦政府干預高等教育最常用的手段之一。在不同的歷史時期,聯邦政府結合當時的社會發展需要,制定相應的政策法規,將其意志滲透到各類高等院校,干預高等教育的發展進程。本文試圖從政策法規的角度來探索各時期聯邦政府對高等教育干預的歷史演變。
一、干預的謹慎時期(二戰后初期至20世紀50年代末)
二戰后,美國逐步擺脫了20世紀30年代經濟大蕭條,保持了一個歷史上比較高的經濟增長率,經濟實力的增強為二戰后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奠定了堅實的經濟基礎。二戰結束前夕到1958年,美國國會頒布并實施《國防教育法》,這段時期美國聯邦政府為了安置退伍軍人,維持社會安定,發展經濟、科技和教育,制定了一系列政策法規,其中二些對美國高等教育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由于聯邦政府管理教育沒有憲法基礎,并且美國高校自治問題向來甚為敏感,因此聯邦政府的干預是謹慎的,本文稱之為“干預的謹慎時期”。該時期的聯邦立法并非以高等教育為直接對象,聯邦政府制定涉及高等教育的政策法規主要以政府報告或政令的形式呈現。
1.頒布《退役軍人權利法》,讓退伍軍人上大學。
1944年美國國會通過的《退役軍人權利法》原本并非是以促進高等教育發展為直接目的的法案,而是安置退伍軍人的立法;聯邦政府頒布退伍軍人權利法,但無意卷入大學事務,大學管理者也不希望大學受到聯邦政府的監督。在該立法的激勵下,大批退伍軍人進入高等院校學習,引起美國高等教育的重要變化。戴維·亨利(David
Henry)認為,由于退伍軍人大批入學,對聯邦政府的決策者來說,高等教育已經非常明顯地成了實現國家目標的工具,這也為聯邦政府大規模介入、資助高等教育奠定了基礎;此外,資助學生成為聯邦政府以最低程度的控制介入高等教育的適當方式,也為高等學校樂于接受。根據該法案,大學從聯邦政府那里獲得了巨大的經濟收入,大學先前所存的疑慮也隨之減弱了。
2.發表政府報告,確立科技和高教政策。
該時期,聯邦政府促進高等教育發展政策的主要形式是發布政府報告,其中最有影響力的是1945年的《科學——無止境的疆界》和1947年的《為民主服務的高等教育》。前者被譽為美國第一份國家科技政策政府報告,確立了戰后美國“科學至上”的科技政策,對科學研究尤其是基礎研究和高校科學研究產生了重大影響。后者是總統高等教育委員會應杜魯門總統的要求而作,雖不具有法律性質,但卻充分體現了戰后美國聯邦政府的高等教育政策。報告中明確提出了改革美國原有高等教育結構和管理模式、擴大社區學院招生規模等建議。此后,在聯邦政府和各級地方政府的扶持下,公立社區學院迅速發展,并逐漸從以私立學院為主體轉變為以公立學院為主體。
3.發布政令,掀起對高校的過度政治干預。
由于當時正處于冷戰時期,有些政策法規也給高等教育帶來了麻煩甚至災難。1947年3月22日,杜魯門總統簽署9835號政令,由此掀起的麥卡錫主義(McCarthyism)一時間鬧得人心惶惶,大學這座象牙塔也失去了安寧。教師們或者被要求宣誓效忠,或者被要求宜稱與共產主義毫無關聯,拒絕者就有被解雇甚至被指控的危險。萊昂奈爾·劉易斯(Lionel Lewis)曾就58所高校做過調查和統計,在1947年至1956年,共有126名教授因麥卡錫主義而失去職位。許多州立大學董事會和校長迫于政府的要求和威脅,要求教師進行忠誠宣誓及遵從國會和州政府官員制定的行為規則。這種過度干預行為激起了一向熱愛學術自由的大學教師們的抵制,伯克利加州大學校長羅伯特·斯珀勞爾(Robert C.Sproul)擔心,清除所謂“不忠誠”的教授將會導致加州大學喪失在全國學術界的領先地位。
1947年杜魯門總統簽署的9835號政令并非;專門針對高等教育,但該政令掀起的反共狂潮卻嚴重干涉了高校自治和學術自由。當然,麥卡錫主義肆虐是冷戰時期的特殊事件,不能代表聯邦政府干預高等教育的普遍特征。
二、干預的加強時期(從20世紀50年代末到60年代末)
50年代初期,由于冷戰的加劇和退伍軍人的陸續離校,高校在校生數量一度出現連年減少的趨勢。直到50年代中期,由于下述因素的推動,新的大學生入學浪潮方才到來。這些因素包括:戰后經濟和科技的迅速發展迫切需要大量各級各類人才;中等教育的廣泛普及使得高中畢業生人數大量增加;自1940年以來,美國歷史上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兒童開始陸續步入高校;50年代中期興起的大規模“民權運動”使得高等教育民主化要求空前高漲;由于高校在二戰期間的重大貢獻以及戰后初期接受和培訓眾多退伍軍人所獲得的巨大成功,高校社會地位明顯提高。被公認為是對增強國家實力和解決社會迫切問題具有特殊重要性的機構;戰爭及空間領域的軍備競賽一度引起人們對教育和科技的廣泛關注。1957年蘇聯人造地球衛星上天,震驚了美國朝野,使教育問題成為舉國上下關心的中,從而揭開了此后十余年美國高等教育大變革和大發展的序幕。
在此背景下,美國高等教育迅速發展,高等教育大眾化得到了進一步推動,美國高等教育系統在招生、財政、機構等所有方面部擴張了。這些重要的歷史變化使高等教育成為國家層次上政策法規關注的焦點。從1958年頒布《國防教育法》后至1968年左右聯邦政府放棄優先發展高等教育的戰略之前,聯邦政府明顯加強了以立法形式對高等教育的干預。本文稱這一時期為“干預的加強時期”:在這一時期,聯邦制定了《國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高等教育法》Higher Education Act)等諸多法律法規。
1.頒布《國防教育法》,首次以立法形式直接干預高等教育。
1958年,為扭轉美國在空間技術領域落后于蘇聯的被動局面,國會通過了著名的《國防教育法》,這是二戰后聯邦政府干預高等教育的一個里程碑式的事件,是戰后聯邦政府通過立法形式直接干預教育的重要措施,有力地推動了美國高等教育的發展。《國防教育法》在美國歷史上首次將教育與國家安全聯系在一起,實質上是美國在50年代末和整個60年代高等教育發展的一個國家綱領,它的頒布實施標志著聯邦政府向高等教育大規模投入時期的到來,標志著高等教育在國家安全和國家政策上的戰略地位得到確立。在該法案及后來美國國會通過的一系列有關大學的立法推動下,聯邦政府對大學的影響和干預空前加強,以至人們認為出現了一個“大學的聯邦時期”。
2.頒布并多次修正《高等教育法》,不斷擴展聯邦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作用。
1965年,國會進一步擴展了聯邦在高等教育方面的作用,制定并通過了《高等教育法》。這部法令是美國歷史上聯邦政府第一部在高等教育方面最系統、最完善的立法。它首次明確規定丁聯邦政府要向公立和私立高等院校提供長期而全面的資助,并且要求每個州為高等教育建立一個協調性機構。后面的條款產生了強有力而又持久的影響,根據《高等教育法》1202條的規定,各州迅速建立各種治理或協調委員會,加強了對高等教育的治理與協調。
《高等教育法》的頒布實施表明聯邦政府對高等教育正式采取直接干預的強硬態度。前哈佛大學校長帕西曾評論1965年《高等教育法》,說它是由聯邦政府問心無愧地直接關心高等教育而制定的第一個法令。自此之后,聯邦政府就能夠較為輕松地將其意圖和政策滲透到高等教育中,直接或間接地決定著整個高等教育的發展方向與進程。聯邦政府每過幾年都要針對高等教育面臨的突出問題和發展趨向,對《高等教育法》進行重新修訂和補充。
3.制定其它重要立法,加強干預高等教育。
該時期聯邦政府還制定了其它涉及高等教育的重要立法。比如,把教育特別是高等教育當作對外援助和滲透的重要力量,為此制定了《富布賴特交流計劃》(Fullbright Exchange Program,1946年)、《國外援助法》(Foreign Assistance Act,1961年)、《共同教育與文化交流法》(Common Education and Culture Communication Act,1961年)和《國際教育法》(Intenational Education Act,1966年)等一系列政策法規,推動高校參與國際高等教育。1963年一些立法促使聯邦進一步介入高等教育事務,包括《職業教育法》(Vocatlpnal Education Act)、《高等教育設施法》(Hid,Education Facilities Act)等。 1964年的《公民權利法》(Civil Rights Act)和《經濟機會法》(Economic Opponu Act)的制定則促進高校擴大招生和教育民主化。1964年《公民權利法》實施以后,美國聯邦政府為促使高校貫徹該法案制定了“肯定行動”(Affirmative Action)計劃,規定高校在聘任教職員、招收學生、財政資助和宿舍空間分配等方面不得因為種族、膚色、性別和原國籍而對一部分人實行歧視政策。對于違犯這些規定的學校,聯邦政府將收回財政資助。肯定行動計劃在促進教育民主化前同時,對高校在招聘教職員、招收學生、財政資助等事務的自主權構成了明顯挑戰。
三、干預的暫緩時期(20世紀6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與持續時期(從20世紀80年代中期至今)
迫于越南戰爭和經濟危機等壓力及公眾對高等教育的信任危機的不斷加深,美國聯邦政府自1968年以后實際上已經放棄了優先發展高等教育的戰略,干預高等教育的勢頭也隨之有所下降,不僅大幅度削減教育支出,而且還減少了有關的教育法規。尤其是1980年里根總統上臺之后,政府推行“新聯邦主義”(New Federalism),反對聯邦政府干預教育。從60年代末聯邦政府放棄高等教育優先發展戰略到80年代中期制定各種關注高等教育質量的政策法規,這段時期可以說是一段“干預減緩時期”。
然而,70年代以來,第三次科技革命改變了美國的產業結構和生產方式,1983年美國農業生產總值只占GNP的3%,工業生產總值占34%,而服務業生產總值已經占到63%,生產過程的自動化日益取代幾十年前的機械化。新的工作領域和工作方式對高度熟練勞動者的需求急劇加大,要求美國高等教育對此作出回應。80年代以來,美國社會中存在許多社會問題,如犯罪、暴力、吸毒、離婚率居高不下、流浪者增多等等,美國朝野期望通過教育改革來克服這些社會問題和危機。這一時期,美國高等教育在鞏固大眾化成果的同時進一步向普及化方向發展,但高等教育的質量下降成了一個凸顯的問題。進入90年代以后,美國經濟發展到“新經濟”或稱信息經濟階段,大學被認為是這個信息時代經濟發展的“發動機”和“火車頭”。
隨著20世紀80年代中期特別是90年代以來美國經濟的好轉,聯邦政府干預高等教育的勢頭又有所回升并保持延續的狀態,本文稱之為“干預的持續時期”。在這一時期,聯邦政府在制定政策法規上除了通過發表政府報告、國會立法等形式外,還連續制定了全國性的對高等教育發展具有指導作用的戰略和規劃。
1.發表政府報告,關注高等教育質量。
針對高等教育質量下降問題,聯邦教育部及其下的“高質量高等教育委員會”(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Exce Hence in Education)分別在1983年和1984年先后發表《國家在危急中——教育改革勢在必行》(Nationat Risk:The Imperative for Educafional Reform)、《投身學習——發揮美國高等教育的潛力》(Improvement in Learning:Realizing the Potential of American Higher Education)兩份報告,在眾多關于高等教育質量問題的報告中影響最大。前者分析了高等教育教學質量下降的原因,并提出相關建議。后一報告著重指出了美國高等教育重視數量而忽視質量所引起的一系列嚴重問題,并提出具體改進本科生教育質量的27條建議。在聯邦政府的推動下,到20世紀90年代,美國高等教育質量下降的趨勢有所遏制。
2.修正高等教育法,加大監督和投入。
克林頓總統上臺后,積極嘗試一個范圍波及幼兒園到大學的重要改革。1992年制定的《高等教育法修正案》(Higher Education Amendment Act)提出兩項改革方案,即州中學后教育檢查方案和鑒定方案。這兩項方案成為聯邦政府監督美國高等教育的兩項重要策略。前者主要是針對那些營利性學校濫用學生貸款而制定的。該法規列舉了15項總體檢查準則,作為各州檢查高校的基本準則,從而擴大了政府對高校內部事務的監督權。后者明確提出要重視對高校的鑒定工作,是影響美國高等教育改革的一項重要法規。此后,克林頓政府繼1997年提出“教育行動綱領”(Call to Action)以加強信息化建設和提出補助學生新策略之后,又在1998年再次制定《高等教育修正案》,加大對高質量師資培養的投入。
3.制定教育戰略規劃,設立長遠發展目標。
這一時期聯邦比較重視制定全國性的教育戰略和規劃,而這些教育戰略和規劃往往是國會制定相應立法的前奏。喬治·布什(George Bush)擔任總統后即標榜自己是“教育總統”,十分重視教育的發展。1991年,他在《美國2000年教育戰略》報告中提出要制定關于中學英語、數學、自然科學、歷史等核心學科的全國統一標準,明確要求以這種新的學業標準作為衡量學生學業成就的基準,從而提高大學新生入學時的學業水準。此后克林頓總統簽署的《美國2000年教育目標法》(Goal 2000:Educate American Act,1993年)就是在該戰略的基礎上制定的,它規定了國家教育目標和標準、國家教育目標領導小組的職責和權力以及提出對州和地方教育體制改革的新設計等,使教育戰略規劃上升為立法,成為國家的意志。21世紀初,美國教育部相繼發表了《2001-2005年戰略規劃》(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trategic Plan 2001—2005)和《2002-2007年戰略規劃》(U.S.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trategic Plan 2002—2007),后者是在前者的基礎上為全面貫徹2002年《不讓一個兒童落后法案》(No Child Left Behind Act)而編制的。在后一個戰略規劃中,教育部設立了諸如加強中學后教育機構的問責制度等五個戰略目標,旨在提高大學生的學業成績與中學后教育機構的教育效能。
四、二戰后美國聯邦政府制定政策法規干預高等教育的特點
二戰后聯邦政府根據各個歷史時期的社會或經濟需要出發制定了許多涉及教育的政策法規,僅在1957—1958年間。85位國會議員提出了1500多個影響教育的法案,而國會至少實施了80個涉及教育的法律。然而,上文例舉的政策法規在反映聯邦干預高等教育的發展趨勢上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因此,我們仍可通過對這些典型例證的分析和總結,發現聯邦政府通過制定政策法規干預高等教育的若干明顯特點。
1.制定高教政策法規的歷程反映了聯邦干預總體上呈加強趨勢。
首先,涉及高等教育政策法規的增多是明顯佐證。其次,政策法規的呈現形式也反映了這一趨勢。在干預的謹慎時期,主要以政府報告的形式體現聯邦政府的意志,到了干預加強時期則直接通過立法來干預。在干預持續時期,持續制定了對全國高等教育發展具有指導作用的戰略和規劃,并往往上升為體現國家意志的法律。其三,有關高等教育的重大立法也顯示了聯邦干預不斷增強的趨勢:1958年的《國防教育法》是二戰后聯邦政府首次通過立法干預高等教育,1965年的《高等教育法》的頒布實施則表明聯邦政府采取直接干預的強硬態度,1992年《高等教育修正法案》提出的州中學后教育檢查方案使政府的影響深入到對高校內部事務的監督權上。聯邦干預的步步加強也意味著美國高校自治受到不斷挑戰,正如科爾(C.Kerr)和蓋得(M.Gade)所說的:“公共規章和制度在不斷取代大學的自主選擇。”
2.聯邦政策法規干預高等教育是雙刃劍。
總的來說,美國聯邦政府制定的有關高等教育的政策法規基本上反映了當時歷史時期社會經濟、政治及高教自身發展的要求,因而對推動美國高等教育發展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然而,如果處理不當,聯邦的政策法規也有破壞作用,如杜魯門總統簽署9835號政令掀起的麥卡錫主義嚴重侵犯了學術自由和大學自治,對高等教育發展造成了極大危害。看來,在制定政策法規干預高等教育時,政府需要考慮如何增強政策法規的促進作用而減少其阻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