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不能像德國(guó)那樣正確對(duì)待侵略歷史的七個(gè)原因
未知
日德兩國(guó)雖然同是二戰(zhàn)的侵略國(guó)、戰(zhàn)敗國(guó),共同對(duì)人類犯下了滔天罪行,但兩國(guó)政要對(duì)侵略歷史卻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態(tài)度:一個(gè)對(duì)侵略戰(zhàn)爭(zhēng)性質(zhì)和罪行坦率承認(rèn)、真誠(chéng)反省,一個(gè)遮遮掩掩、圖謀翻案;一個(gè)編撰合格的歷史教科書對(duì)下一代進(jìn)行正確的戰(zhàn)爭(zhēng)史觀教育,一個(gè)處心積慮篡改歷史教科書不讓下一代了解歷史真相;一個(gè)主動(dòng)向受害國(guó)受害民族支付巨額戰(zhàn)爭(zhēng)賠款,一個(gè)百般抵賴、拒不賠償。這主要是由以下七個(gè)方面的因素綜合作用所致。
1、兩國(guó)的文化思想底蘊(yùn)不同 德國(guó)是一個(gè)有著雙重性格的特殊國(guó)度:一個(gè)培育了歌德、黑格爾、馬克思等眾多文壇巨匠和思想巨子的偉大民族,卻一再挑起世界大戰(zhàn)、為禍人類。這完全是由戰(zhàn)前德國(guó)的精神世界與國(guó)家政治現(xiàn)實(shí)相脫節(jié)所致。當(dāng)這個(gè)國(guó)家強(qiáng)盛之時(shí),其思想精神總是遭受摧殘和涂炭;當(dāng)這個(gè)國(guó)家瀕臨衰亡之際,其思想精神又總是大放光芒,并數(shù)度引領(lǐng)本民族爬出災(zāi)難的深淵。換言之,因?yàn)榈聡?guó)是一個(gè)有著厚重文化思想底蘊(yùn)的國(guó)家,德意志民族是一個(gè)富于思想、善于思辨的偉大民族,德國(guó)知識(shí)分子又較之其他國(guó)家的知識(shí)分子更能深刻地剖析本民族的劣根性和冷靜而審慎地反思本民族的心路歷程及國(guó)家的行進(jìn)軌跡,因此這個(gè)曾以自己博大精深的思想睿智推動(dòng)了整個(gè)人類認(rèn)知世界和改造世界歷史進(jìn)程的偉大民族,也一定能夠?qū)o本民族和整個(gè)人類創(chuàng)下巨禍的法西斯思想及其引發(fā)的侵略戰(zhàn)爭(zhēng)進(jìn)行理性的思考。德國(guó)哲學(xué)家卡爾·雅斯貝斯曾在一次演說(shuō)中深刻指出:“如果沒(méi)有在深刻認(rèn)識(shí)罪行的基礎(chǔ)上經(jīng)歷一個(gè)凈化的過(guò)程,德國(guó)人就不會(huì)發(fā)現(xiàn)真理”。(注:潘俊峰等:《是總結(jié),還是翻案——兼評(píng)〈大東亞戰(zhàn)爭(zhēng)的總結(jié)〉》,軍事科學(xué)出版社1998年版,第319頁(yè)。)他希望德國(guó)人既要勇于正視痛苦的過(guò)去,更要正確把握民族的未來(lái)。 日本民族也是一個(gè)偉大的民族。然而,在自古積淀于大和民族心理潛層的神國(guó)觀念和天皇崇拜思想以及由此派生出來(lái)的島國(guó)集團(tuán)根性和愚忠盲從心理的久遠(yuǎn)影響下,在近代以降極端國(guó)家主義、軍國(guó)主義教育的灌輸毒化下,在當(dāng)年巨額的戰(zhàn)爭(zhēng)賠款和巨大的殖民地收益大大推動(dòng)了日本近代化進(jìn)程這一“利益”誤區(qū)的驅(qū)動(dòng)下,日本民族對(duì)戰(zhàn)爭(zhēng)是非的鑒別能力和反思水平受到了極大的限制和束縛,致使日本政要對(duì)侵略歷史的認(rèn)識(shí)非常短視,缺乏應(yīng)有的政治遠(yuǎn)見。這是導(dǎo)致日德兩國(guó)政要對(duì)侵略歷史態(tài)度迥異的文化思想方面的原因。
2、兩國(guó)的宗教信仰不同 德國(guó)人90%以上是基督教徒。基督教的基本教義之一是“原罪——認(rèn)罪——贖罪”的說(shuō)教。對(duì)基督徒來(lái)說(shuō),這是一個(gè)追求理性復(fù)歸的很自然的過(guò)程。他們不但認(rèn)為人生來(lái)就有可能犯罪,不但不把“認(rèn)罪”視為可恥,而且要求認(rèn)罪者必須真誠(chéng)“謝罪”,用行動(dòng)來(lái)“贖罪”。 日本民族信仰的主要是神道教。天皇是神,日本是神國(guó),國(guó)家至上,忠君愛(ài)國(guó),這是神道教的基本要求和主張。換言之,對(duì)神道教徒來(lái)說(shuō),天皇和國(guó)家從來(lái)都是正確的,按造天皇的意愿所作所為沒(méi)有什么錯(cuò)誤和悔罪可言,所以日本人普遍視“認(rèn)罪”、“謝罪”為恥辱。正因如此,戰(zhàn)時(shí)的部分日本國(guó)民曾盲從、協(xié)助了侵略戰(zhàn)爭(zhēng),并以能夠?yàn)樘旎实摹笆?zhàn)”效死疆場(chǎng)而倍感“無(wú)比榮幸”;(注:大島孝一:《戰(zhàn)爭(zhēng)中的青年》,巖波書店1985年版,第118頁(yè)。)同樣因?yàn)槿绱耍毡緫?zhàn)敗投降時(shí)不但有很多軍人為沒(méi)能打贏“圣戰(zhàn)”而紛紛剖腹自殺,以此向天皇謝罪,而且部分日本國(guó)民無(wú)論在戰(zhàn)爭(zhēng)中蒙受了多大的痛苦和犧牲,都拒絕批評(píng)“祖國(guó)”和天皇。這樣,戰(zhàn)后日本政要拒不承認(rèn)侵略戰(zhàn)爭(zhēng)性質(zhì)和罪行,拒不向被侵略國(guó)家和民族道歉、謝罪、賠償,也就不十分令人費(fèi)解了。
3、兩國(guó)的侵略戰(zhàn)爭(zhēng)歷史和兩國(guó)政要的個(gè)人經(jīng)歷不同 德國(guó)在20世紀(jì)上半葉曾兩次發(fā)動(dòng)世界大戰(zhàn),四處擴(kuò)張、瘋狂侵略,其結(jié)果不但沒(méi)有給自己帶來(lái)任何戰(zhàn)爭(zhēng)利益,反而把國(guó)家和民族推向毀滅的邊緣(國(guó)家分裂、支付巨額賠款、在國(guó)際上陷于孤立)。這一殘酷的事實(shí)教育了戰(zhàn)后德國(guó)領(lǐng)導(dǎo)人,使他們尤為深刻地感受到了納粹統(tǒng)治的極端危害性,認(rèn)識(shí)到靠發(fā)動(dòng)侵略戰(zhàn)爭(zhēng)來(lái)確立德國(guó)在世界上的地位的做法是代價(jià)極其昂貴的,而應(yīng)該選擇另外一條道路——和平發(fā)展之路。而日本則有所不同。在明治維新以后的半個(gè)多世紀(jì)中,日本挑起了那么多次對(duì)外沖突和發(fā)動(dòng)了那么多次侵略戰(zhàn)爭(zhēng),除最后一次戰(zhàn)爭(zhēng)失敗外,其他均以日本的勝利而告終。一方面,巨額的戰(zhàn)爭(zhēng)賠款和巨大的殖民地收益,曾大大加快了日本走向近代化的步伐;另一方面,即使最后一次戰(zhàn)爭(zhēng)失敗了,日本也未受到應(yīng)有的懲罰。這就使得充分嘗到了侵略戰(zhàn)爭(zhēng)甜頭而從未吃過(guò)戰(zhàn)敗苦頭的部分日本政要,很想重溫軍國(guó)主義老路。 就兩國(guó)政要的個(gè)人經(jīng)歷來(lái)看。戰(zhàn)后,聯(lián)邦德國(guó)的首任總理阿登納戰(zhàn)時(shí)曾遭受過(guò)納粹政權(quán)的迫害;而在波蘭猶太人紀(jì)念碑前“一跪泯恩仇”的勃蘭特總理,戰(zhàn)時(shí)也是一位堅(jiān)定的反法西斯戰(zhàn)士,積極從事反納粹活動(dòng),一度被希特勒政府剝奪國(guó)籍,亡命國(guó)外。即在德國(guó),當(dāng)年的法西斯戰(zhàn)犯已幾乎都被繩之以法,戰(zhàn)犯重新上臺(tái)執(zhí)政是根本不可能的事。然而,在日本,由于美國(guó)的庇護(hù)和扶植,不僅戰(zhàn)爭(zhēng)根源天皇制被保留和幾乎所有的戰(zhàn)犯被提前釋放,而且很多戰(zhàn)犯竟重返政壇、軍界執(zhí)掌了國(guó)家大權(quán)。像東條英機(jī)內(nèi)閣商工大臣岸信介、戰(zhàn)時(shí)鐵道總務(wù)局長(zhǎng)佐藤榮作、戰(zhàn)時(shí)內(nèi)務(wù)省特高課課長(zhǎng)奧野誠(chéng)亮等軍國(guó)遺臣當(dāng)上戰(zhàn)后首相、大臣者,司空見慣。而那些在戰(zhàn)后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新一代政治家的戰(zhàn)爭(zhēng)史觀所以也大成問(wèn)題,同樣與其個(gè)人經(jīng)歷密切相關(guān)。這些人雖然沒(méi)有親自參加過(guò)侵略戰(zhàn)爭(zhēng),但孩提或少年時(shí)代“舉國(guó)一致”盲從、協(xié)助侵略戰(zhàn)爭(zhēng)的狂熱氣氛和“軍國(guó)青年”決心為天皇的“圣戰(zhàn)”效死疆場(chǎng)的“感人情景”,不能不對(duì)他們的幼小心靈產(chǎn)生強(qiáng)烈而恒久的震撼,不能不久遠(yuǎn)而深刻地影響其未來(lái)的心理歸向和思想走勢(shì);加之戰(zhàn)后又沒(méi)有受過(guò)全面、正確的歷史教育,其戰(zhàn)爭(zhēng)史觀又怎能不成問(wèn)題呢?1996年7月29日, 時(shí)任首相的橋本龍?zhí)稍凇肮殹眳菥竾?guó)神社后“不無(wú)深情地”對(duì)記者說(shuō)道:“不能說(shuō)當(dāng)了總理大臣就讓我忘記了那些事。……五十多年前我在孩提時(shí)代時(shí),站在歡送出征人士的隊(duì)伍里。當(dāng)初人們是高呼著‘光榮回到靖國(guó)神社’的口號(hào)把他們送上了戰(zhàn)場(chǎng)的。今天我的參拜,僅僅是兌現(xiàn)孩提時(shí)代對(duì)那些英靈的承諾。”(注:肖季文等:《日本:一個(gè)不肯服罪的國(guó)家》,江蘇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頁(yè)。)戰(zhàn)后部分日本政要本身就是當(dāng)年的軍國(guó)主義分子或是戰(zhàn)后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沒(méi)有受過(guò)正確歷史教育的新生代政治家,靠他們?cè)跄苷嬲词∏致詺v史呢?
4、兩國(guó)反省戰(zhàn)爭(zhēng)的群眾基礎(chǔ)不同 戰(zhàn)后,由于德國(guó)政府重視對(duì)國(guó)人特別是下一代進(jìn)行正確的戰(zhàn)爭(zhēng)史觀教育,所以不論是親身經(jīng)歷過(guò)戰(zhàn)爭(zhēng)的成年人還是戰(zhàn)后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年輕人,基于對(duì)納粹罪行的深惡痛絕,他們不但主動(dòng)協(xié)助政府緝拿漏網(wǎng)戰(zhàn)犯,而且不斷舉行聲勢(shì)浩大的游行集會(huì)與右翼勢(shì)力進(jìn)行斗爭(zhēng)。據(jù)統(tǒng)計(jì),1979年時(shí)明確認(rèn)為當(dāng)年的納粹政權(quán)是一個(gè)犯罪政權(quán)的人占國(guó)民總數(shù)的71%。在反法西斯集會(huì)上,群眾高呼口號(hào)“我們不要戰(zhàn)爭(zhēng),永遠(yuǎn)不讓法西斯主義復(fù)活!”“外籍工人留下來(lái),驅(qū)逐新法西斯主義”。德國(guó)人民這一高度的政治覺(jué)悟和對(duì)新納粹勢(shì)力的不懈斗爭(zhēng),就使得德國(guó)政治家在反省侵略歷史時(shí)不但沒(méi)有孤立感,而且感到有著深厚的群眾基礎(chǔ)。 在日本,早在戰(zhàn)時(shí),部分日本國(guó)民在軍國(guó)主義教育的灌輸毒化等諸多因素作用下就盲從了統(tǒng)治階級(jí)發(fā)動(dòng)的侵略戰(zhàn)爭(zhēng)。在此,我們僅從侵華老兵東史郎日記中的一段記述便可略見一斑:“1937年9月1日,母親和弟弟重一來(lái)與我告別……母親很冷靜,重一也很冷靜。接著,母親說(shuō):‘這是一次千金難買的出征。你高高興興地去吧!如果不幸被支那兵抓住的話,你就剖腹自殺!因?yàn)槲矣腥齻€(gè)兒子,死你一個(gè)沒(méi)有關(guān)系’。接著,她送給我一把刻有文字的匕首。母親的話讓我多么高興啊。我覺(jué)得母親特別偉大,沒(méi)有比這時(shí)更知道母親的偉大了。于是,我在心中堅(jiān)定地發(fā)誓——我要欣然赴死!”(注:王奕紅等譯:《東史郎日記》,江蘇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38頁(yè)。)正是由于戰(zhàn)時(shí)的軍國(guó)主義毒素遠(yuǎn)未徹底肅清和戰(zhàn)后學(xué)校教育的人為誤導(dǎo),不僅當(dāng)年盲從侵華戰(zhàn)爭(zhēng)的部分日本國(guó)民遠(yuǎn)未走向覺(jué)醒,而且那些在戰(zhàn)后成長(zhǎng)起來(lái)的日本國(guó)民特別是青少年要么對(duì)過(guò)去的侵略歷史知之甚少,要么不肯為父輩參加的那場(chǎng)戰(zhàn)爭(zhēng)承擔(dān)任何道義上的責(zé)任,有的甚至產(chǎn)生了可怕的復(fù)仇心理。例如,中小學(xué)生們?cè)诳戳恕渡降ぶ贰ⅰ堵牐┗甑暮袈暋返确磻?zhàn)影片后,不但不從反戰(zhàn)方面來(lái)欣賞和理解,反而在自己的作文中情不自禁地恨恨寫道:“此仇必報(bào)!”“下次一定要打一場(chǎng)必勝的戰(zhàn)爭(zhēng)!”(注:巖崎昶著,鐘理譯:《日本電影史》,中國(guó)電影出版社1981年版,第244頁(yè)。)以致使仗義執(zhí)言的家永三郎、東史郎等進(jìn)步人士不僅受到政府的冷遇和右翼勢(shì)力的威脅,而且還要經(jīng)常忍受來(lái)自周圍不覺(jué)悟的民眾類似“賣國(guó)賊”的一些謾罵和諷刺。軍國(guó)主義思想潛存于部分民眾意識(shí)的底層和部分日本國(guó)民錯(cuò)誤的戰(zhàn)爭(zhēng)史觀,是日本政要否認(rèn)和美化侵略歷史的群眾基礎(chǔ)。
6、兩國(guó)的政權(quán)基礎(chǔ)不同 德國(guó)戰(zhàn)敗后,盟國(guó)吸取了一戰(zhàn)結(jié)束后戰(zhàn)勝國(guó)向戰(zhàn)敗國(guó)一味掠奪卻不去鏟除軍國(guó)主義禍根,致使德國(guó)再度為禍?zhǔn)澜绲某镣唇逃?xùn),認(rèn)識(shí)到在對(duì)德國(guó)進(jìn)行“非納粹化”改造之前,任何一個(gè)由德意志人自己建立起來(lái)的政府都不值得信任,于是盟國(guó)占領(lǐng)當(dāng)局擔(dān)負(fù)起徹底清算德國(guó)納粹殘余勢(shì)力和打碎舊的國(guó)家機(jī)器的歷史性工作。在1945年至1949年蘇美英法分區(qū)占領(lǐng)期間,不僅解除了德國(guó)武裝、取締了德國(guó)全部納粹黨團(tuán),而且徹底打碎了德國(guó)原中央政府機(jī)構(gòu),由“盟國(guó)管制委員會(huì)”作為占領(lǐng)期間德國(guó)境內(nèi)的最高權(quán)力機(jī)關(guān)行使中央政府職能。此間,盡管德國(guó)的一些舊的地方行政機(jī)關(guān)還在工作,但其原地方官多已出逃,所剩無(wú)幾。在此基礎(chǔ)上,1949年9月7日和10月7日分別成立了嶄新的德意志聯(lián)邦共和國(guó)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國(guó)。無(wú)論聯(lián)邦德國(guó)還是民主德國(guó),其政府官員基本上都是戰(zhàn)時(shí)遭受過(guò)納粹政權(quán)迫害的原抵抗運(yùn)動(dòng)成員、流亡民主人士等“歷史清白者”和“政治上無(wú)負(fù)擔(dān)者”,絕無(wú)舊納粹官僚置身其中,實(shí)現(xiàn)了新舊政權(quán)的一刀兩斷。這無(wú)疑有助于置身新政府中的德國(guó)新政要客觀審視和徹底反省前納粹政權(quán)的戰(zhàn)爭(zhēng)責(zé)任及其罪行。 反觀日本,戰(zhàn)后政府與戰(zhàn)時(shí)政府具有明顯的繼承性。日本戰(zhàn)敗初期,美國(guó)占領(lǐng)當(dāng)局為了確保日本不再成為美國(guó)的威脅和促使日本最終建立一個(gè)和平的負(fù)責(zé)任的政府,曾制定并初步實(shí)施了包括解除武裝、懲辦戰(zhàn)犯在內(nèi)的對(duì)日政策。但隨著冷戰(zhàn)開始,美國(guó)迅速將對(duì)日政策由“懲罰”改為“扶植”,不但重新武裝和釋放戰(zhàn)犯,而且?guī)缀踉獠粍?dòng)地保留了日本的戰(zhàn)時(shí)政治體制和統(tǒng)治機(jī)構(gòu):(1)二戰(zhàn)罪魁禍?zhǔn)自H侍旎屎蛻?zhàn)爭(zhēng)禍根天皇制被保留;(2)戰(zhàn)犯重返政壇、軍界掌控國(guó)家大權(quán);(3)戰(zhàn)時(shí)的多數(shù)政權(quán)機(jī)關(guān)戰(zhàn)后未經(jīng)裁撤和改造繼續(xù)統(tǒng)治著日本。這樣一來(lái), 與舊政權(quán)具有明顯承繼關(guān)系的戰(zhàn)后日本政府,必然因其統(tǒng)治核心、多數(shù)官僚和多數(shù)政權(quán)機(jī)關(guān)依舊而對(duì)戰(zhàn)時(shí)政府的戰(zhàn)爭(zhēng)責(zé)任及其罪行的反省受到極大的限制。
7、兩國(guó)所處的國(guó)際環(huán)境不同 戰(zhàn)后,德國(guó)所面臨的國(guó)際政治環(huán)境對(duì)德國(guó)政要正確對(duì)待侵略歷史具有積極的影響。表現(xiàn)在:(1)地處歐陸中心這一地緣政治環(huán)境的影響。波蘭、法國(guó)、荷蘭、比利時(shí)等深受納粹侵略之害的鄰國(guó)因長(zhǎng)期抱有“恐德心理”而一直在警惕地注視并不斷敲打著德國(guó),使德國(guó)領(lǐng)導(dǎo)人深知:欲使自己在歐洲站穩(wěn)腳跟,前提必須消除鄰國(guó)的“恐德心理”;而解除鄰國(guó)恐懼心理的最好辦法,就是不斷對(duì)本國(guó)的侵略歷史進(jìn)行深刻反省和真誠(chéng)懺悔,以表明德國(guó)不重走歷史老路和維護(hù)世界和平的堅(jiān)定決心。(2)盟國(guó)分區(qū)占領(lǐng)和鉗制的影響。戰(zhàn)后初期,德國(guó)被蘇美英法分割占領(lǐng), 國(guó)家命運(yùn)操諸于四大國(guó)手中;冷戰(zhàn)開始后,盡管美英的對(duì)德政策有所改變,但無(wú)論英國(guó)的“大陸均勢(shì)”政策還是美國(guó)試圖將德國(guó)重新武裝成為“遏制”蘇聯(lián)的前沿陣地的戰(zhàn)略構(gòu)想,都無(wú)法改變蒙受過(guò)亡國(guó)恥辱的法國(guó)和飽受德國(guó)法西斯侵略之害的蘇聯(lián)削弱德國(guó)的決心和政策。正因?yàn)橘頂撤▏?guó)和冷戰(zhàn)一極蘇聯(lián)的對(duì)德削弱、分割政策,使德國(guó)在歷史認(rèn)識(shí)等問(wèn)題上承受著巨大的壓力。(3)冷戰(zhàn)格局的影響。冷戰(zhàn)時(shí)期處于勢(shì)不兩立的北約和華約兩大軍事集團(tuán)夾縫中的德國(guó),被一幅厚重的“鐵幕”一分為二長(zhǎng)達(dá)40余年。兩大集團(tuán)若一旦開啟戰(zhàn)端,兩德勢(shì)必首當(dāng)其沖。尤其聯(lián)邦德國(guó),其國(guó)土東西長(zhǎng)不過(guò)453公里,南北寬只有83公里,幾無(wú)縱深可言。德國(guó)在戰(zhàn)后所面臨的這般國(guó)際政治環(huán)境,使其領(lǐng)導(dǎo)人凡事特別是在涉及鄰國(guó)民族感情的歷史認(rèn)識(shí)問(wèn)題上不得不謹(jǐn)慎處之;使之認(rèn)識(shí)到惟有如此,德國(guó)才能維持民族生存并最終實(shí)現(xiàn)國(guó)家統(tǒng)一。 戰(zhàn)后,日本所面臨的國(guó)際政治環(huán)境與德國(guó)迥然不同:(1)相對(duì)孤立的島國(guó)地理環(huán)境造成部分日本人視野狹窄和以日本為中心的思維方式。他們只看到原子彈轟炸給日本民族造成的傷害和念念不忘本國(guó)在戰(zhàn)爭(zhēng)中死去的310萬(wàn)人,卻視而不見其侵略戰(zhàn)爭(zhēng)給別國(guó)特別是中國(guó)帶來(lái)的創(chuàng)深痛劇的災(zāi)難,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受了島國(guó)地理環(huán)境的間接影響。(2)周邊不存在真正構(gòu)成威脅的強(qiáng)國(guó),客觀上為日本政要否認(rèn)甚至美化侵略歷史提供了寬松的環(huán)境。從盟國(guó)方面來(lái)看,戰(zhàn)后的日本由美國(guó)獨(dú)占,而不像德國(guó)那樣被多國(guó)分割占領(lǐng)。美國(guó)出于冷戰(zhàn)政策的需要, 一方面在扶蔣失敗后轉(zhuǎn)而扶植日本,對(duì)日本政要歪曲侵略歷史的言行置若罔聞,甚至默許和鼓勵(lì)日本軍國(guó)主義復(fù)活;另一方面,美日安保體制的建立,又使日本政要由于有了美國(guó)提供的安全保護(hù)而敢于在歷史問(wèn)題上忘乎所以、大肆“翻案”。從日本的周邊國(guó)家來(lái)看,亞洲多數(shù)國(guó)家雖然對(duì)日本的侵略深惡痛絕,但由于他們正忙于內(nèi)戰(zhàn)或民族獨(dú)立斗爭(zhēng)而大大降低了自己在對(duì)日問(wèn)題上的發(fā)言權(quán),因而處于不得不接受世界霸主——美國(guó)政府的意志之被動(dòng)地位,根本無(wú)法影響美國(guó)的對(duì)日政策。換言之,在遠(yuǎn)東存在著使冷戰(zhàn)一極的美國(guó)的全球戰(zhàn)略和國(guó)家利益得到不折不扣貫徹的國(guó)際環(huán)境,這與美國(guó)在德國(guó)問(wèn)題上的意圖和政策備受歐洲強(qiáng)國(guó)牽制的情形迥然不同;與此相關(guān)聯(lián),與德國(guó)首當(dāng)其沖成為美蘇冷戰(zhàn)政策最大、最直接的受害者截然相反,日本事實(shí)上成為美國(guó)冷戰(zhàn)政策最大、最直接的受益者。周邊無(wú)強(qiáng)國(guó)特別是幾乎不存在強(qiáng)烈要求懲罰戰(zhàn)敗國(guó)日本的國(guó)家這一特殊的國(guó)際政治環(huán)境,一方面使日本獲得了迅速發(fā)展經(jīng)濟(jì)的“天佑良機(jī)”,同時(shí)也深遠(yuǎn)地影響了日本政要對(duì)本國(guó)侵略歷史的自覺(jué)反省。 當(dāng)然,在以上七個(gè)方面的因素中,盟國(guó)對(duì)兩國(guó)的戰(zhàn)后處理和受害國(guó)對(duì)兩國(guó)的態(tài)度不同,特別是美國(guó)人為地保留天皇制、釋放日本戰(zhàn)犯、解除對(duì)軍國(guó)主義分子的“整肅”,是導(dǎo)致日本迄今不能像德國(guó)那樣正確對(duì)待侵略歷史最主要的原因。
.jpg)
械.jpg)
科學(xué)基金.jpg)
水稻科學(xué).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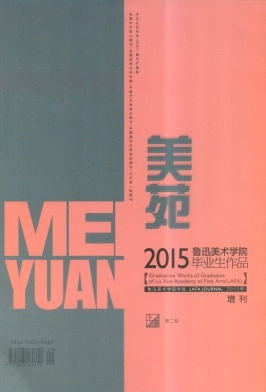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