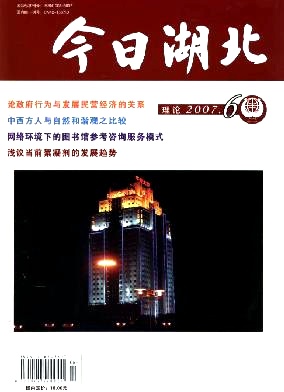孫中山的民權民主及共和之涵義
桂宏誠
【摘 要】本文論述的主旨在于說明孫中山和晚清時人相同,他們講「民主」時與現在使用「民主」一詞的涵義并不相同,而詞相同者則應該是「民權」。并且,孫中山所講的「共和」,是取自于中國古代「共和行政」之義,來詮釋國家應非世襲之一人所可獨治,故既不必然從「國體」與「政體」的二分概念來看待,也未必要以西方共和主義思想來加以評價。然而,孫中山講的「共和」除了是指廢除君主制而改為公舉國家元首外,還可能系取材自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在《聯邦主義者通訊》中所主張的「共和政府」理念。
【關鍵詞】孫中山、民權、民主、共和、專制 一、引 言
清末倡言民權之說者中,康、梁的「立憲派」主張維護萬世一系的君主,而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派」雖也主張「立憲」,但卻要推倒君主專制改以「共和」為前提。因此,若就「立憲」的主張而言,這兩派之間其實無甚差異,而最為能夠凸顯不同之處,則在于「革命派」還認為要推倒君主專制而改為「共和」。也因此,梁啟超等「立憲派」又較為關注「國體」與「政體」之分,認為萬世一系的「君主立憲」與推倒帝王的「共和革命」,此乃為「國體」上的區分,而無論「國體」為「君主」或「共和」,在「政體」上則皆可采用「立憲」。
需先說明的是,清末民初使用「憲政」一詞,乃為「立憲政體」的簡稱,而所謂的「立憲政體」或「立憲」,也即是指開議院或國會而言。梁啟超于1909年發表的〈各國憲法異同論〉中,對「憲政」一詞所下的批注為:「立憲君主國政體之省稱」,且他還認為英國是「憲政」之始祖[1]。所以,「憲政」之「憲」至少指的是「立憲」,而「憲政」之「政」則系指「政體」,故「憲政」也即是「立憲政體」的簡稱。此外,梁啟超于1908年發表的〈中國國會制度私議〉一文中即說過:「天下無無國會之立憲國,語專制政體與立憲政體之區別,其唯一之表識,則國會之有無是已」[2],由此可看出,康、梁等立憲派所稱的「憲政」或「立憲政體」,其根本之意即是指開議院或開國會而言的政體(參見本文附表之相關敘述的整理)。也因此,1915年梁啟超為反對袁世凱稱帝乃作〈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仍然強調了「夫立憲與非立憲,則政體之名詞也;共和與非共和,則國體之名詞也」[3],說明了梁啟超將「共和」視為國體的類型,而「立憲」則為「政體」之類型的看法并未改變。
盡管當前對「國體」與「政體」的區分已經失去了實際意義[4],但若拿西方「共和主義」(republicanism)思想來評價孫中山所講的「共和」,或是根據梁啟超的看法而認為他混淆了國體與政體之分,恐怕皆未盡公允與符合事實。然而,本文所要論述與澄清的主旨,并不在于說明孫中山講的「共和」與西方的「共和主義」或「共和」(republic)是否契合,而是要指出孫中山使用「共和」一詞時,除了取其意義于周厲王逃跑至彘而由周公與召公實行「共和行政」的歷史外,還可能另外取材自自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James Madison)的「共和政府」(republican government)理念。如果這樣的推斷并無錯誤,由于republic是被我們「理解」、「模擬」而翻譯成中文本有的「共和」一詞,故除了孫中山講的「共和」未必要以西方的共和思想為依歸外,本文還要指出麥迪遜在《聯邦主義者通訊》(Federalist Papers)第十號文件中所講的「共和」,原本也即是指「政體」而非「國體」。
此外,當梁啟超在區分「民權」與「民主」的不同時,也會把「民主」視為「國體」,而「民權」則屬于「立憲」的「政體」之說法(詳見以下)。換言之,從言論界天之驕子的梁啟超使用「民主」與「共和」詞匯時,同樣是用來指「國體」,而且還與指「政體」的「民權」有所不同,可見晚清時人使用「民主」一詞的涵義,便可能與我們現在所認知的democracy為不同的指涉。我們可以發現,英國在晚清時人的認知中是個「君主立憲」的國家,但卻不是一個「民主」的國家,這樣的表述即凸顯了晚清時代對于「民主」一詞的認知與現今乃有不同,因而有先予以厘清與說明的需要。 二、「民權」與「民主」涵義的辨析
根據大陸學者熊月之的考證,兩千多年前的《尚書》與《左傳》等經籍中,就已經多次出現了如「簡代夏作民主」、「天惟時求民主」及「其語偷不似民主」等的說法,但這里「民主」的意思是「民之主」,完全沒有近代意義上「民主」的含義[5]。臺灣學者陳鵬仁也曾指出:「『尚書』上的民主,是為民之主或替民作主的意思,它與我們現在現在所說的民主不但截然不同,而且完全相反」[6]。對于十九世紀六、七十年代的人們使用「民主」一詞時,是否都是近代意義上的「民主」而與中國經籍中的「民主」一詞本義完全無關?大陸學者謝放以《書經?多方》中「天惟時求民主,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與「簡代夏作民主」兩句話為例,再依據蔡沈《書經集傳》所注為:「言天惟是為民求主耳。桀既不能為民之主,天乃大降顯休命于成湯,使為民主」及「簡擇也,民擇湯而歸之」,而認為「民主」之本義固然是「民之主」,但這個「民之主」是由「天」來為民求得或由「民」擇而歸之。因此,謝放認為這里的「民主」一詞,其實還隱含了「民擇主」、「不世及」與「傳賢不傳子」之意。
另外,謝放還引據美國傳教士高理文(Elijah C. Bridgman,一譯裨治文)刊印的《美理哥國志略》與魏源的《海國圖志》,以及《萬國公報》等文獻中,就引介美國政治制度中的元首系由「公舉」產生的「民之主」,或因其為「傳賢不傳子」,認為在十九世紀鴉片戰爭前后起,傳教士或中國人在引介而使用「民主」一詞時,盡管仍多指的是「民之主」,但卻與《書經?多方》中隱含了「民擇主」與「傳賢不傳子」意義的「民主」,并非完全無關[7]。換言之,謝放所真正要說明與強調的,似乎是指中國古代經籍中的「民主」,除了「民之主」的本義外,原本即隱含有近代以來使用「民主」一詞所代表的涵義。所以,當引介美國元首為「公舉」、「不世及」與「傳賢不傳子」時,才選用中國古代經籍原已有的「民主」一詞。
然而,「民主」一詞在《書經?多方》中的本義為「民之主」自無疑義,且盡管此一詞匯原本也因隱含了「民擇主」、「不世及」與「傳賢不傳子」的意義,但既然稱之為「隱含」,自也不無是當代人以現代的「民主」觀念而對過去「民主」一詞追溯地賦予了新的意義。事實上,假托「天」來「為民求主」是中國傳統的民本思想,而「民擇湯而歸之」是強調民心歸趨于湯而使湯的新政權具有正當性,這也是民本思想的一種表達。再說,無論中國的儒家或法家思想中,君與民之間的關系基本上都是一君對萬民,民是集體存在的觀念而缺乏以個體的民來與君主應對的關系。就此來看,以個體人民身份表達擇君主之意向的「民主」(democracy),在中國傳統思想中并找不到落腳點。何況,中國古代經典如《尚書?周書?洪范》中有:「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的說法,這是把君、民關系放在人倫關系里來定其綱紀。所以,「民」不僅不是個體而為集體存在,且「天子」與「民」之間是父母與子女的關系,故除了靠假托天為「子民」另外擇「天子」外,在人倫關系又豈有子女可表達選擇父母之意向的余地?
從外文翻譯成中文的情況來看,外國傳教士丁韙良在1864年主譯的《萬國公法》中,就已曾多次使用「民主」一詞。例如,「若民主之國則公舉首領長官,均由自主,一循國法」[8],以及就遣使接使之職「在民主之國,或系首領執掌,或系國會執掌,或系首領、國會合行執掌」等[9]。丁韙良或許較無中國古典經籍之深厚背景,是就「君主」為「世襲之君為國之主」的意義上,在其對立面即為「公舉人民為國之主」之義而采用了「民主」一詞來代表。自此之后,中國的駐外使節對于「民主」一詞的認知,或許即是由此而來。例如,依其日記中所載,應屬中國最早使用「民權」一詞者的郭嵩燾,在他的日記中同樣也另外多次使用「民主」一詞。他寫到:「西洋立國,有君主、民主之分,而其事權一操之議院,是以民氣為強」[10],而黃遵憲在《日本國志》則稱:「有一人專制稱為君主者,有庶人議政稱為民主者,有上下分任事權稱為君民共主者」[11]。此處所引郭嵩燾與黃遵憲對于「民主」一詞的意義,深入來看則仍有所差異。基本上,郭嵩燾的「君主」與「民主」之分,強調的是「國體」上有「君主國」與「民主國」的區別,尚不涉及「政體」上的「專制」與「民主」之分。而黃遵憲則大至系依事權歸屬的政治體制角度來看,認為君主一人專制稱「君主制」,全由庶人議政者稱「民主制」,而君、民分任事權者便為「君民共主制」。
由上述可知,在1870年代后期中國人開始使用「民權」一詞以前,至少已有丁韙良以「民主之國」來介紹泰西各國的政治制度。并且,由于丁韙良對「民主之國」是以「則公舉首領長官」來界定,使得「民主」和「民權」二詞匯同時間為郭嵩燾與黃遵憲等駐外使節使用時,即已在意義上有所區分。其后,在他們這些提倡或主張「民權」之說者看來,「民主」主要被用來指稱國家元首由人民公舉產生,而「民權」則是在君主國的前提下,人民應該擁有議政及其它的權力或權利。到了1890年代末期,何啟與胡禮垣對于兩者詞匯意義的認識,仍大致沿襲了相同的區分,他們在《勸學篇書后?正權篇辨》中曾有明確的「民權」與「民主」仍有差異[12]: 民權之國,與民主之國略異。民權者,其國之君仍世襲其位;民主者,其國之權由民選立,以幾年為期。吾言民權者,謂欲使中國之君世代相承,踐天位勿替,非民主之國之謂也。 然而,當時并不是所有人對于「民主」一詞的涵義,皆能如同上述之認識,而仍有沿襲中國古代經籍中之涵義來使用「民主」一詞者。例如,《萬國公報》在1874年12月介紹美國的總統時,即有「公舉民主」及「美國民主曰伯理璽天德,自華盛頓始」的報導[13],而1881年2月時也有「民主曉諭」[14]的說法。這些對「民主」一詞使用的情形,或可說明中國知識分子觀察了泰西的政治制度或觀念后,較不會想到以「民主」一詞來概括的原因。另一方面,也說明了當「民主」的詞性日益轉變后,倡民權之說的改良派或維新派等,為何又苦于「民權」被誤解即為「民主」之義,而汲汲于辯解「民權」與「民主」實乃有所不同。例如,戊戌政變失敗后,1899年7月28日梁啟超在《清議報》上發表文章說:「夫民權與民主二者,其訓詁絕異。英國者,民權發達最早,而民政體段最完備者也,歐美諸國皆師效法,而其今女皇,安富尊榮,為天下第一有福人」 [15],1901年6月7日他在《清議報》上以〈立憲法議〉為題的文章中,更加闡釋了民權與民主之不同,他說[16]: 吾儕之昌言民權,十年于茲矣;當道者憂之、嫉之、畏之,如洪水猛獸然。此無怪其然也,蓋由不知民權與民主之別,而謂言民權者必與彼所戴之君主為仇,則其憂之、嫉之、畏之也固宜。不知有君主之立憲,有民主之立憲,兩者同為民權,而所以馴致之途,亦有由焉。凡國之變民主也,必有迫之使不得已者也。使英人非虐待美屬,則今日之美國,猶澳洲、加拿大也;使法王非壓制其民,則今日之法國,猶波旁氏之朝廷也。故欲翊戴君主者,莫如興民權。不觀英國乎? 從上述梁啟超的說法來看,他認為「民主」是以「民」取代「君」成為「國之主」,故「民主」講的是為「國體」。同時,他所講的「民權」僅指「立憲」,故為不涉及變更君主「國體」的「君主立憲政體」。因此,無論國體為「君主」或「民主」,只要行「立憲政體」就都是「民權」。并且,此處所謂的「立憲」若就剛歷經戊戌變法的失敗而言,自是以「開議院」而使人民有議政之權以通上下之情為要旨。總之,在戊戌前后期間,「民權」主要是指從君主專制權力中獲得解放而擁有參與議政的權力,但并不主張君主國體之變更;而「民主」則被理解為公舉不世襲的「民之主」,而具有取代君主的意義。根據孫廣德的考察結果也認為,在戊戌前后民主是指廢除君主,元首由人民直接或間接推選而言,而共和與民主的涵義略同;立憲則大多是指君主立憲而言,故民權略同于立憲或君主立憲。但有時他們也表示民主與君主都有立憲,當然也都實行民權[17]。 三、孫中山的「共和」觀與「民權」、「民主」之關系
如上所述,晚清倡言民權之說者的看法中,基本上是將「民主」視為廢除君主,而「民權」則意味著「立憲」。因此,熊月之認為孫中山于1905年11月26日在東京為同盟會機關報《民報》所撰的〈發刊詞〉,則是他第一次將反對專制主義的民主思想歸結為「民權思想」[18],尚須留意者是,熊月之此處所謂的「民主」思想是指democracy,但孫中山則是以「民權」一詞來表達。孫中山在《民報?發刊詞》里是這樣寫到[19]: 余維歐美之進化,凡以三大主義:曰民族,曰民權,曰民生。羅馬之亡,民族主義興,而歐洲各國以確立;洎自帝其國,威行專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則民權主義起。十八世紀之末,十九世紀之初,專制仆而立憲政體殖焉;……今者中國以千年專制之毒而不解,異種殘之,外邦逼之,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殆不可須臾緩。 由于反「君主專制」是反「專制」而未必即為反「君主」,此亦為梁啟超認為「夫民權與民主二者,其訓詁絕異」的理由。因此,若僅就上述孫中山的這段文字來看,尚難徑謂推倒君主的「民主」已含括在孫中山使用「民權」詞匯的涵義之內,而只能說明「民權」即意謂著行「立憲政體」。然而,孫中山在1905年以前便早已主張推翻君主的共和革命,他在1894年11月上書李鴻章未獲所納后,遂決意共和革命以推翻帝制而在檀香山創立了革命團體「興中會」。從他在《興中會章程》所附的秘密誓詞中,明確寫到了革命的目標為「驅逐達韃虜,恢復中華,創立合眾政府」來看,即表明革命的目標在于推翻君主以建立美國式的「合眾政府」。所以,在《民報》的〈發刊詞〉中所言的民權主義,姑且可視為已將梁啟超等人認知的「民主」之義,含括在他使用的「民權」詞匯之意義內。
然而,推翻君主世襲制度意義上的「民主」,固然可謂是孫中山之民權主張的內涵,但孫中山卻習以「共和」一詞來表達國家元首由公舉產生的政治。至于孫中山使用「民主」一詞時的涵義,則是與「君為一國之主」的「君主」相對立,而指的是由「人民」來當國家的主人或元首,亦即是「人民為一國之主」的意義。例如,孫中山在〈民權主義第五講〉中說[20]: 十三年前革命,仿效外國改革政治,成立民主政體,目的是在取法乎上,……,革命以后,舉國如狂,總是要拿外國人所講的民權,到中國來實行;至于民權究竟是什么東西,也不去根本研究。……
中國自革命以后,成立民權政體,凡事都應該由人民作主的;所以現在的政治,又可以叫作民主政治。換句話說,在共和政體之下,就是用人民來做皇帝。……。現在成立共和政體,以民為主,大家試看這四萬萬人是哪一類的人呢?……,現在民權政治,是要靠人民作主的,所以這四萬萬人都是很有權的。 從上述同一篇講詞中,我們發現「民權」與「民主」同時為孫中山所使用,此即意謂了孫中山使用「民權」與「民主」時,應是用以表達不同的概念。并且,我們還可發現,孫中山講十三年前「革命」是與「民主政體」相呼應,但革命以后要把外國人所講而拿到中國實行的,卻不是「民主政體」而為「民權」。故而,從語境上可以推知,革「君主」之天命而后所要建立的,乃為廢除「國之主」的世襲制度,并從此把「國之主」改為由「公舉人民」來擔任。再進一步來看,「民權政體」是與「由人民作主」相呼應,而這種政治則是「民為國之主」的「民主政治」,故「民為國之主」也即是用人民來做皇帝的「共和政體」。換言之,孫中山使用「民主」一詞時,乃著眼于國家元首由「民」來擔任而非世襲的「君」。也因此,他才繼續問到「以民為主」下的四萬萬人是哪些人?而講「民權政治」時則指出是要靠「人民作主的」。因此,我們可以得知的是,直到1924年孫中山逝世前一年,在他使用「民主」與「民權」的詞匯時,與democracy意義相當的是「民權」而非「民主」。
如果厘清了孫中山使用「民權」與「民主」詞匯所具有的涵義后,就能夠更清楚地了解他在1923年發表〈中國革命史〉中一段話的意義。他說[21]: 余之民權主義,第一決定者為民主,而第二之決定則以為民主專制必不可行,必立憲然后可以圖治。歐洲立憲之精義,發于孟德斯鳩,所謂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是已。 上述這段話里的「民主」一詞,其意義若是指democracy,則「民主專制」便成為「民主」與「專制」這兩個相反概念構成的復合詞,原本即因無存在之可能而也無所謂可行與否的問題。然而,若是把「民主」一詞的意義,理解為改由人民來擔任國家元首的「國之主」,則才進而發生選擇「專制」或「立憲」始可圖治的問題。我們可從梁啟超1906年在《新民》報上連載發表了〈開明專制論〉一文里,看到他對專制的國家又再區分為「君主的專制國家」、「貴族的專制國家」及「民主的專制國家」三種[22],再對照他在該文中多次提到的「民主專制」一詞,即可證明與孫中講的「民主專制」為相同的涵義,而都是指改由人民成為了一國之主與元首后,仍然可以存在著專制政體。換言之,此處所講的「民主」,僅是就民為國之主或國家元首的意義而言。
由此可看出,不僅戊戌前后對「民權」與「民主」兩詞匯間的混淆,已讓梁啟超發出了感慨,后來由孫中山為代表而興起的革命派,其等所提出以「共和」為口號的革命主張,也讓現代的研究者不得不再加以留意其意義。大體上來說,若就西方近代以來的「民主」意義為衡量,「民權」一詞原本即系中國人仿效西方議會之「民主」制度的過程中所產生,故「民權」的意義始終未脫人民有參與議政之權的涵義,而與人民具有參與議政之近代西方「民主」的涵義較為接近。另一方面,推翻君主世襲制度以使國家元首由公舉產生之意義上的「民主」,則反倒與西方近代意義上的「民主」涵義并無必然關系;因為,眾所皆知英國為君主世襲,但卻是老牌「民主」國家。
根據大陸學者方維規的考證,在十九世紀很長的一段時間里,西方的democracy和republic這兩個概念在漢語譯釋中并沒有嚴格區分。換言之,「民主」一詞既可能是democracy的漢譯,但也經常是譯自于republic,使得中文里講西方的「民主」時究竟是指democracy或republic?在許多情況下是很難斷定的[23]。然而,本文對于把democracy翻譯為「民主」,基本上則尚持存疑的態度。鑒于上述的討論,本文認為十九世紀時表達democracy概念的應是「民權」而非「民主」,至于republic也翻譯成「民主」的說法則應屬合理。依筆者的推測,當晚清時人及孫中山從西方文獻中認識了美國獨立與法國大革命的同時,他們也看到了republic這個字,并把其意義與廢除君主世襲改成「以人民為國之主」的現象聯系了起來。同樣地,他們也看到了美國及法國的統治者為不僅一人,故以中國歷史上的「共和行政」來比擬而也將之稱為「共和政體」。是故,republic翻譯成「民主」時是指「以人民為國之主」,而孫中山使用「民主」與「共和」的詞匯時,也經常同為表達republic的概念。但嚴格而論,孫中山所講的「共和」與「民主」仍有差別,其講「民主」時大多與梁啟超極力辨明的「民主」之義相當,都是指推翻君主世襲制度而改為由「人民」成為國家主人或國家元首。至于「共和」則指非一人專斷統治的「專制」,因而「民主共和」乃與「民主專制」亦可成一組對立的詞匯。 四、孫中山認知中的「國體」與「政體」
孫中山所講的「共和」其實還有另一層的意義,而這層意義論者則常以「國體」與「政體」的二分概念來做評價,并進而指出在他的民權主義思想中,未明「國體」(form of state)與「政體」(form of government)的概念應有所區分[24]。以西方政治學或公法學上的一般意義來說,「國體」是指國家的形式,若國家元首為世襲的君主則稱為「君主國」,如果國家元首無論是由直接或間接的民選產生,則稱為「共和國」。至于「政體」是指政府的統治型態,若是政府的統治型態為隨時基于國民之公意者,即稱為「民主制」;反之,則稱之為「獨裁制」[25]。若以此「國體」與「政體」區分的標準來看,孫中山講「民主」時系與世襲的「君主」相對立,故「民主」在他的語境中乃指「由四萬萬人民做皇帝」或民為國家元首的「國體」。同樣地,孫中山使用「共和」一詞時,經常系取義于中國歷史上的「共和行政」,故「共和」乃是與一人專斷獨裁之「專制」相對立的「政體」。
然而,當時或因「國體」在中文里本已有既定的涵義,故孫中山未必皆從政治或公法學上的意義來使用「國體」一詞,自然也無與「政體」一詞在概念上有所區分的需要。例如,孫中山在1894年的《檀香山興中會規條》的第一條中謂:「是會之設,專為振興中華維持國體起見。蓋我中華受外國欺凌,已非一日,皆由內外隔絕,上下之情罔通,國體抑損而不知,孑民受制而無告。……」[26],此處孫中山所欲維持的「國體」,當然不會是政治學意義上指稱「君主國」的「國體」。那么,孫中山所謂的「國體」該如何解釋呢?有研究者聯系了孫中山后來對所謂「國家為體,政治為用」的解釋,認為這里的「體」似可理解為國家的「物質型態」,故此處孫中山所謂的「國體」,可認為是指一個由人結合而成的共同體[27]。但這樣的解釋,似乎仍不無牽強之感。
光緒皇帝在1895年簽訂馬關條約之后,曾責問李鴻章曰:「身為重臣,兩萬萬之款從和籌措;臺灣一省送予外人,失民心,傷國體」[28]。對照1900年孫中山在〈致香港總督歷數滿清政府罪狀并擬訂平治章程請轉商各國贊成書〉中有言:「睦鄰遣使,國體攸關,移炮環攻,如待強敵,是謂戕使命」[29],以及1912年2月4日在〈覆中華國貨維持會論服制函〉中,對于民國成立后將改服制所引起外貨暢銷而內貨阻滯問題,在給「中華國貨維持會」的覆函中提及「而禮服又實與國體攸關,未便輕率從事」[30],從這些使用「國體」時的語境來看,則尚難謂必定直接與政治學或公法學上的意義產生關連。由此來看,光緒皇帝認為所傷的「國體」,以及孫中山所欲維持和改易禮服及睦鄰遣使均所攸關的「國體」,大致上應該具有相似相同的涵義與指涉。因此,這不僅說明了「國體」一詞在當時已有了特定的涵義,且其意義或許較接近于是指「國家的整體」或「國家的體面」。
孫中山在1912年8月13日的〈國民黨宣言〉中,則較為精準地從政治學或公法學的意義上使用「國體」與「政體」詞匯,他說[31]: 此消長倚伏之數,固不必論其國體之為君主共和,政體之為專制立憲,而無往不如是也。天相中國,帝制殄滅,既改國體為共和,變政體為立憲,然而共和立憲之國,其政治之中心勢力,則不可不匯之于政黨。 在這份宣言中,孫中山區分了「國體」與「政體」,也指出「君主」與「共和」為「國體」之別,而「專制」與「立憲」則屬于「政體」之分。然而,孫中山使用「共和」一詞時,卻又未必盡皆是在政治學意義上的「國體」來言說。孫中山較早提到「共和」的概念,在1897年8月和日本友人宮崎寅藏等人的談話中,對于宮崎寅藏問及他準備革命所持的宗旨與方法時所做的回答。在這篇談話的內容中,孫中山說出了他革命的宗旨在于「以人群自治為政治之極則,故于政治之精神,執共和主義」。他之所以提出共和主義為號召,是因為「共和者,我國治世之神髓,先哲之遺業也」,也就是中國人曾經歷過,至今仍然欽慕的「三代之治」,早已「實能得共和之神髓而行之者也」。而共和政治的精神,即為「彼等皆自治之民也」、「其它一切共通之利害,皆人民自議之而自理」。并且,「共和政治,不僅為政體之極則,且適合于中國國民,而又有革命上之便利者也」[32]。此處共和政治之所以具有革命上之便利者,大致上孫中山是以歷代易朝更迭,由于舉事者與為盟主者皆無共和思想,以致地方豪杰互爭雄長,亙數十年而使百姓受禍害,且盜賊胡虜居然可為全國之共主。因此,孫中山主張必須采取立即的革命為方法,且認為以共和政治有利于革命之號召。他還說[33]: 嗚呼﹗吾同胞之受禍,豈偶然哉!今欲求避禍之道,惟有行此迅雷不及掩耳之革命一法,而與革命同行者,又必在使英雄各竟其野心。竟其野心之法,唯在聯邦共和之名下,夙著聲望者,使為一部之長,以盡其材,然后建中央政府以馭之,而作聯邦之樞紐。方今公理大明,吾既實行此主義,必不至如前此野蠻,割據之紛擾,綿延數紀,而梟雄有非分之希望,以乘機竊發,殃及無辜。此所謂共和政治有革命之便利者也。 由上述可之,孫中山不僅認為共和政治為「政體之極則」,而且還顯然是以美國的「聯邦共和」為仿效的對象。因此,我們或可就其所敘述的內容來探究他的「共和」之義,不必先陷入「國體」與「政體」之分的框架內,而把問題意識指向了孫中山是否混淆了國體與政體之分。若能如此,我們或許即可理解1900年義和團事變期間,孫中山曾有意擁立李鴻章在兩廣成立獨立政府,盡管主政之人「或稱總統或稱帝王」聽由李鴻章,但這未必即可推斷為肇因于「對共和意義理解上的局限,導致孫中山在革命早期的某些時候,在共和理想上的搖擺」[34]。本文認為,即使孫中山真的曾有意擁立李鴻章在兩廣獨立稱王,但卻未必即與他的共和理想產生矛盾。這個道理就如同明、清之際的顧炎武在其〈郡縣論〉中主張恢復宗法封建制度,并認為地方官應改為世襲制度一般[35],卻不能因此便驟爾以為顧炎武乃支持滿清。
顧炎武的主張是他從明朝滅亡的原因中得到的體悟,認為明末地方官未將所轄視為「私產」,從而在任期內竭盡搜刮財富,當遇清兵入關則又諉棄守地與百姓。因此,若行宗法封建制度反而能使地方官在「私欲」的驅使下,捍衛封邑如同捍衛「私產」。然而,顧炎武的真正用意在于「異姓分天下」,以「地方分權」及「地方自治」來反君權的「家天下」,故日本學者溝口雄三即認為顧炎武〈郡縣論〉的基本點在「寓封建之意于郡縣之中」,但實質上則是假托封建以反君主專制的地方自治主張[36]。因此,盡管孫中山曾經有意擁立李鴻章在兩廣獨立稱王,但卻應該與顧炎武的〈郡縣論〉同樣是個策略性的主張。何況,孫中山講「共和」時應是從中國古代「共和行政」來理解,而他講「共和」所要反對的是一家一姓一人獨治中國,至于李鴻章若在獨立廣東稱王,此對廣東一地固為「君主」而非「民主」,但卻與其追求全中國的「共和」并未產生必然之沖突。
我們應特別注意孫中山的「而與革命同行者,又必在使英雄各竟其野心。竟其野心之法,唯在聯邦共和之名下,夙著聲望者,使為一部之長,以盡其材,然后建中央政府以馭之,而作聯邦之樞紐」這段話。因為,此一有革命之便利的共和政治,極可能是孫中山閱讀了美國憲法之父麥迪遜在《聯邦主義者通訊》第51號文章后的心得。
麥迪遜在《聯邦主義者通訊》第51號文章中,主要是對所欲建立之「共和政府」(republican government)的討論。麥迪遜認為,避免權力逐漸集中在某一部門(department)的最佳保障,就必須要再給每個部門抵抗其它部門侵犯的合法手段與動機,而且要使每個人的利益與其所在之處相結合。簡單說,就是「必須用野心來對抗野心」(Ambition must be made to counteract ambition) [37]。《聯邦主義者通訊》是所謂的聯邦黨人向脫離英國殖民的北美十三州(邦)(state,亦有主權國家之意)人民,主張應該批準聯合起來成為一個「合眾國」的憲法,而在報紙上刊載的宣傳文章。或許,孫中山從聯邦黨人的文獻主張與美國制度的實踐中,看到了美國首任總統華盛頓雖為獨立戰爭領袖,但仍須由各州為單位而所公舉出,使他想到了中國古代《國語》中記載周厲王被放逐,而由周公及召公共同執政的「共和行政」,而將《聯邦黨人文集》中的republic理解「共和」一詞來表達。同時,孫中山一樣采取了「用野心對抗野心」的策略,故需「使英雄各竟其野心」,并以「使其為一部之長」為「竟其野心之法」,但仍必須「在聯邦共和之名下」,并「建中央政府以馭之,而作聯邦之樞紐」。由此看來,孫中山的「共和」觀念可以說就是以美國的聯邦共和制為典范。所以,盡管他有意擁立李鴻章在兩廣獨立并接受其稱為「帝王」,但他的終極目標實是在于「聯邦」共和而非「一邦」,故其共和理想也未能因此而視為「動搖」。并且,在《聯邦主義者通訊》中常有republican government的詞匯,目前中文里也系將之翻譯成「共和政府」或「共和政體」;何況,麥迪遜所講的「共和原理」(republican principle),原本即是就政府體制的設計而言的。就此來看,孫中山對于近代美國的「共和」觀念未必即無掌握,且對他而言,既然仿效的是美國制度而宣揚「共和主義」,那么他所講的「共和」是否混淆了「國體」與「政體」之分?就美國立憲先賢在《聯邦主義者通訊》中闡揚的「共和原理」看來,這個問題已經不具有太大的意義了。
孫中山「共和」觀念之形成,是否還有證據可說明系從《聯邦主義者通訊》中獲得啟發呢?1916年7月15日在駐滬粵籍議員歡迎會上,孫中山針對「中華民國」的意義所作的演講中,似乎又可找到一個肯定的例證。他說[38]: 顧仆尚有一重大意志,欲白于今日者,諸君知中華民國之意義乎?何以不曰「中華共和國」,而必曰「中華民國」?此「民」字之意義,為仆研究十余年之結果而得之者。歐美之共和國,創建遠在吾國之前。二十世紀之國,當含有創制之精神,不當自謂能效法于十八九世紀成法,而引為自足。共和政體為代表政體,世界各國,隸于此旗幟之下者,如希臘,則有貴族奴隸之階級,直可稱之曰「專制共和」。如美國則已有十四省,樹直接民權之規模,而瑞士則全乎直接民權制度也。雖吾人今既易專制而成代議政體,然何可故步自封,落于人后。……。代議政體旗幟之下,吾民所享者,只一種代議權。若底于直接民權則有創制權、廢止權、退官權。但此種民權,不宜以廣漠之省境施行之,故當以縣為單位。……。如是數年,必有一莊嚴燦爛之中華民國發現于東大陸,駕諸世界共和國之上矣。 上述所引孫中山說明何以稱「中華民國」而不稱「中華共和國」的原因,是與他主張直接民權與間接民權之差異有關。簡單來說,孫中山想要凸顯的觀念是,「民國」是指「民權」之國,而真正的「民權」又是指「直接民權」,亦即我們目前所理解的「直接民主」。反之,「共和國」則是指采「共和政體」的國家,而「共和政體」即是「代議政體」,亦即「間接民權」或「間接民主」的意思。由此可看出,在孫中山的民權思想中,他的「民權」顯然已與近代意義的「民主」為相同的意義。然而,孫中山為什么說「共和政體為代表政體」或「代議政體」呢?這與他分不分得清楚「國體」與「政體」之區別未必有關,但卻可證明他受到了麥迪遜在《聯邦主義者通訊》第10號文章的啟發。
麥迪遜在《聯邦主義者通訊》第10號文章中,主要就是闡述他對「共和政體」的設計與理論。麥迪遜是就美國當時所普遍存在的「黨派」(faction)現象與發生原因,主張美國聯邦政府成立后,關于政府體制不該采取直接民主的「民主政府」,而應采取代議政府的「共和政府」。用麥迪遜的詞匯來說,就是采取「共和原則」(republican principle)所設計的「代議政府」(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來取代直接民主的政府型態(popular government)。并且,在麥迪遜所使用的詞匯中,democracy和republic是相對立的體制,而前者是指直接民主體制,后者則是指間接民主的代議體制[39]。盡管孫中山此時主張的是與麥迪遜相反的直接民權,但從他說明為何不采「中華共和國」為國名,且明確認為「共和政體」即是「代表政體」或代議政體來看,應可證明他的「共和」一詞是從《聯邦主義者通訊》中傳譯而來,而無論「共和國」或「共和政體」的概念,也是由此而受到啟發。 六、結 論
從清末到民國十幾年這段期間內,「君主」、「民主」、「共和」、「民權」、「立憲」、「國體」及「政體」等詞匯,彼此間在語境上當有一定的聯系、對應或對立關系。就孫中山而言,他所主張的「民權」指涉范圍最廣,可以用來指改「君主」為「民主」,也包括改「專制」為「共和」的「民主立憲」或「共和立憲」之政體。然而,或許自1919年五四運動高舉「德先生」與「賽先生」的「民主」與「科學」后,「民主」一詞已大致是用來表達democracy的意義,使「民權」與「民主」兩個詞匯都是在「由人民作主」的意義上而具相同的涵義,且還漸取代了「民權」一詞的使用[40]。
然而,我們發現孫中山在1924年演講民權主義時,他仍是在不同的涵義上來分別使用「民權」與「民主」的詞匯。基本上,如果要表達democracy的概念,孫中山使用的是「民權」,且體現「民權」的制度是「立憲」政體、「共和」政體或「代議」政體,以及后來因看到國會成為豬仔議員的腐敗現象[41],而主張直接「民權」的「全民政治」。其次,孫中山使用「民主」一詞時,則是與「君主」(亦包括與貴族)相對立,故其意義在于指統治者或國家元首是由「人民」(人民為集體而非個體之概念,亦即四萬萬人做皇帝)來擔任,并非由一家一姓之世襲所產生。至于他所講的「共和」是與「專制」為對立的概念,意味國家非一人之專斷獨治即為「共和」。但仍須注意而不另作說明的是,孫中山及晚清時人所講的「民權」,并非僅具有democracy的意義,還包括了「自由」(liberty)及「權利」(right)等概念在內。
附表 梁啟超對立憲、憲法、立憲政體及憲政的說明一覽表
內 容 出 處 要旨說明 世界之國有二種:一曰君主之國,二曰民主之國。設制度、施號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謂之政。世界之政有二種:一曰有憲法之政亦名立憲之政,二曰無憲法之政亦名專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國民謂之政體,世界之政體有三種:一曰君主專制政體,二曰君主立憲政體,三曰民主立憲政體。…。三種政體,舊譯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名義不合,故更定今名。 憲法者何物也?立萬世不易之憲典,而一國之人,無論為君主、為官吏、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為國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無論出何令,更何法,百變而不許離其宗者也。西語原字為THE CONSTITUTION,譯意猶言元氣也。蓋謂憲法者,一國之元氣也。 立憲政體,亦名為有限權之政體;專制政體亦名為無限權之政體。有限權云者,君有君之權,權有限;官有官之權,權有限;民有民之權,權有限。…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為專制之國言之耳。若夫立憲之國,則一治而不能復亂。……且君主之發一政、施一令,必謀及庶人,因國民之所欲,經議院之協贊,其有民所未喻者,則由大臣反復宣布于議院,必求多數之共贊而后行。民間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訴于議院更張而利便之,而豈有民之怨其上者乎?故立憲政體者,永絕亂萌之政體也。 問者曰:“然則中國今日遂可行立憲政體乎?”曰:是不能。立憲政體者,必民智稍開而后能行之。 1901年,〈立憲法議〉,《點校》,第二冊,頁920及922。 1.「民主之國」應系指透過公舉,而以民為「國之主」的國家。 2.所引省略之處,為梁啟超依序對君主專制、民主立憲及君主立憲三種政體之良窳做出評價,故舊譯為「君主」者為「君主專制」,舊譯為「民主」者為「民主立憲」,舊譯為「君名共主」者為「君主立憲」。 3.嚴復1906年在其演講〈憲法大義〉時,似系針對梁啟超的「憲法」及「立憲」觀念提出批評。他說:「按憲法二字連用,古所無有。以吾國訓詁言仲尼憲章文武、注家云憲章者近守具法。可知憲即是法,二字連用,于辭為贅」。又說:「吾國近年以來,朝野之間,知與不知,皆談立憲。立憲既同立法,則自五帝三王至于今日,驟聽其說,一若從無有法,必待往歐美考察而歸,然后為有法度也者,此雖五尺之童,皆知其言之謬妄矣。是知立憲、憲法諸名詞,其所謂法者,別有所指。…然究竟此法,吾國舊日為無為有,或古用而今廢,或名異而實同,凡此皆待討論思辨而后可決。故其名為立憲,而不能再加分別者,以詞窮也」。 3.立憲政體為有限權之政體,但此「限權」實質上為「分權」之義。亦即,從既有的「君權」及「官權」中再分出「民權」。而所謂的「民權」之體現與「永絕亂萌之政體」,皆是指開議院或國會的立憲政體。 4.因「立憲政體」系指開議院或國會,故乃有以民智稍開為行立憲政體之前提的問題。 本報論文最要之點:曰今日中國萬不能行共和立憲制。而所以下此斷案者:曰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共和國民之資格不一端,…。然吾檃括言之,吾所認為最重要者,則曰:“有能行議院政治之能力者,斯有可以為共和國民之資格”。 1906年,〈答某報第四號對于本報之駁論〉,《點校》,第三冊,頁1430。(按:某報指同盟會的《民報》) 1.梁啟超做此文前,已發表有〈開明專制論〉一文,其依「進化論」的思維,認為「野蠻專制→開明專制→君主立憲→共和立憲」為一演化的過程。他認為中國應以開明專制為立憲制的準備。 2.中國不能行共和立憲制的理由,在于中國國民尚未具備共和國民之資格。而尚未具備共和國民之資格最重要者,則是中國國民尚不具備行議院政治之能力。 3.尚不具備「行議院政治之能力」,就是戊戌變法時以「民智未開」而未開國會的同一理由。 4.國民具備行議院政治之能力為立憲制的前提,有「議院政治」始為立憲制。 天下無無國會之立憲國,語專制政體與立憲政體之區別,其唯一之表識,則國會之有無是已。 1908年,〈中國國會制度私議〉,《點校》,第二冊,頁967。 1.專制政體與立憲政體的區別,端視「國會之有無」而定。 2.有國會的國家才是「立憲國」,「立憲」即意味「有國會」。 憲法者,英語稱為Constitution,其義蓋謂可為國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故茍凡屬國家之大典,無論其為專制政體,舊譯為君主之國。為立憲政體,舊譯為君民共主之國。為共和政體,舊譯為民主之國。似皆可稱為憲法。雖然,近日政治家之通稱,惟有議院之國所定之國典乃稱為憲法。故今之所論述,亦從其狹義:惟就立憲政體之各國,取其憲法之異同,而比較之云爾。… 憲政立憲君主國政體之省稱之始祖者,英國是也。 1909年,〈各國憲法異同論〉,《點校》,第二冊,頁1056。 1.梁啟超此時對于「憲法」的認知,是從法律意義之角度來理解,故推衍致任何國家都有憲法的結論,而和自己以往的認識有所混淆需做批注。 2.惟「有議院之國所定之國典乃稱為憲法」。 3.「憲政」一詞是「立憲君主國政體之省稱」,且英國是行此種「政體」的始祖。但此處既以英國的「政體」為「立憲」始祖的表征,則所謂「立憲」自是指舊譯為「君民共主」的「議會制」。 政體之區別以直接機關之單復為標準。其僅有一直接機關,而行使國權絕無制限者,謂之專制政體;其有兩直接機關,而行使國權互相制限者,謂之立憲政體。…今就現世之君主立憲國而舉其特色,則有三焉:第一,民選議會。議會謂國會也,凡立憲國必有國會,…第二,大臣副署。凡立憲國君主之詔敕,必須由大臣署名,然后效力乃發生。…第三,司法獨立。凡立憲國皆有獨立之審判廳以行司法權。… 舉此三條件,規定于憲法中,而不許妄動,謂之立憲。立憲之制,首行于英國,…。 1910年,〈憲政淺說〉,《點校》,第二冊,頁957-958。 1.從將國權再予「國家直接機關權限分化」的角度界定「立憲政體」。 2.只要有「兩直接機關,而行使國權互相制限者」,即可謂之立憲政體,不以「三權分立」與「司法獨立」為必要條件。 學者言憲政之所以示別非憲政者有三:民選議院其一也,責任內閣其二也,司法獨立其三也。故語憲政之特色,實惟前二義。而議院與內閣,又必相倚而始為用,二義實一義也。…所謂君主立憲之異乎君主專制者,其在專制之國,則立憲(本文作者按:法?)與行政兩大權,皆由君主獨斷而躬行之。立憲國不爾,立法權則君主待議院協贊而行之,行政權則君主命大臣負責任而行之。質言之,則專制國之君權無限制者也,立憲國之君權有限制者也。立憲之與專制,所爭只此一點。 1911年2月,〈敬告國人之誤解憲政者〉,《點校》,第二冊,頁1078。 1.憲政與非憲政的差別有三,但其特色則為民選議院及責任內閣二義,且實際上僅屬一義,亦即開議院而行議會制度。 2.「其在專制之國,則立憲與行政兩大權」中的「立憲」兩字若無筆誤或誤印,則「立憲」當即指建立議會制度。 3.若是為「立法」之誤植,從「立憲國不爾,立法權則君主待議院協贊而行之」來看,立憲與否也是指「立法權」有無從行政權分離而言,故「立憲」仍意味了議會制度的建立。 4.立憲是指從君權中分離出了立法與行政兩權為表征,并非就「國權」相對于「社會」乃為有限度之constitutionalism的概念。 立憲政體,以君主不負政治上之責任為一大原則。其所以示別于專制政體者,惟在此點。… 1911年5月,〈立憲國詔旨之種類及其在國法上之地位〉,《點校》,第二冊,頁1062。 1.立憲政體以政治上的虛君元首為一大原則,故自是延續開議院或國會以行議會內閣制的思維,來界定立憲政體。 2.1905年同盟會成立后,革命派的言論較立憲派受到了廣泛支持,梁啟超繼主張開明專制后,又改變立場為虛君元首的議會內閣制。
內 容
出 處
要旨說明
世界之國有二種:一曰君主之國,二曰民主之國。設制度、施號令以治其土地、人民謂之政。世界之政有二種:一曰有憲法之政亦名立憲之政,二曰無憲法之政亦名專制之政。采一定之政治以治國民謂之政體,世界之政體有三種:一曰君主專制政體,二曰君主立憲政體,三曰民主立憲政體。…。三種政體,舊譯為君主、民主、君民共主。名義不合,故更定今名。
憲法者何物也?立萬世不易之憲典,而一國之人,無論為君主、為官吏、為人民,皆共守之者也,為國家一切法度之根源。此后無論出何令,更何法,百變而不許離其宗者也。西語原字為THE CONSTITUTION,譯意猶言元氣也。蓋謂憲法者,一國之元氣也。
立憲政體,亦名為有限權之政體;專制政體亦名為無限權之政體。有限權云者,君有君之權,權有限;官有官之權,權有限;民有民之權,權有限。…
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亂。”此為專制之國言之耳。若夫立憲之國,則一治而不能復亂。……且君主之發一政、施一令,必謀及庶人,因國民之所欲,經議院之協贊,其有民所未喻者,則由大臣反復宣布于議院,必求多數之共贊而后行。民間有疾苦之事,皆得提訴于議院更張而利便之,而豈有民之怨其上者乎?故立憲政體者,永絕亂萌之政體也。
問者曰:“然則中國今日遂可行立憲政體乎?”曰:是不能。立憲政體者,必民智稍開而后能行之。
1901年,〈立憲法議〉,《點校》,第二冊,頁920及922。
1.「民主之國」應系指透過公舉,而以民為「國之主」的國家。
2.所引省略之處,為梁啟超依序對君主專制、民主立憲及君主立憲三種政體之良窳做出評價,故舊譯為「君主」者為「君主專制」,舊譯為「民主」者為「民主立憲」,舊譯為「君名共主」者為「君主立憲」。
3.嚴復1906年在其演講〈憲法大義〉時,似系針對梁啟超的「憲法」及「立憲」觀念提出批評。他說:「按憲法二字連用,古所無有。以吾國訓詁言仲尼憲章文武、注家云憲章者近守具法。可知憲即是法,二字連用,于辭為贅」。又說:「吾國近年以來,朝野之間,知與不知,皆談立憲。立憲既同立法,則自五帝三王至于今日,驟聽其說,一若從無有法,必待往歐美考察而歸,然后為有法度也者,此雖五尺之童,皆知其言之謬妄矣。是知立憲、憲法諸名詞,其所謂法者,別有所指。…然究竟此法,吾國舊日為無為有,或古用而今廢,或名異而實同,凡此皆待討論思辨而后可決。故其名為立憲,而不能再加分別者,以詞窮也」。
3.立憲政體為有限權之政體,但此「限權」實質上為「分權」之義。亦即,從既有的「君權」及「官權」中再分出「民權」。而所謂的「民權」之體現與「永絕亂萌之政體」,皆是指開議院或國會的立憲政體。
4.因「立憲政體」系指開議院或國會,故乃有以民智稍開為行立憲政體之前提的問題。
本報論文最要之點:曰今日中國萬不能行共和立憲制。而所以下此斷案者:曰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共和國民之資格不一端,…。然吾檃括言之,吾所認為最重要者,則曰:“有能行議院政治之能力者,斯有可以為共和國民之資格”。
1906年,〈答某報第四號對于本報之駁論〉,《點校》,第三冊,頁1430。(按:某報指同盟會的《民報》)
1.梁啟超做此文前,已發表有〈開明專制論〉一文,其依「進化論」的思維,認為「野蠻專制→開明專制→君主立憲→共和立憲」為一演化的過程。他認為中國應以開明專制為立憲制的準備。
2.中國不能行共和立憲制的理由,在于中國國民尚未具備共和國民之資格。而尚未具備共和國民之資格最重要者,則是中國國民尚不具備行議院政治之能力。
3.尚不具備「行議院政治之能力」,就是戊戌變法時以「民智未開」而未開國會的同一理由。
4.國民具備行議院政治之能力為立憲制的前提,有「議院政治」始為立憲制。
天下無無國會之立憲國,語專制政體與立憲政體之區別,其唯一之表識,則國會之有無是已。
1908年,〈中國國會制度私議〉,《點校》,第二冊,頁967。
1.專制政體與立憲政體的區別,端視「國會之有無」而定。
2.有國會的國家才是「立憲國」,「立憲」即意味「有國會」。
憲法者,英語稱為Constitution,其義蓋謂可為國家一切法律根本之大典也。故茍凡屬國家之大典,無論其為專制政體,舊譯為君主之國。為立憲政體,舊譯為君民共主之國。為共和政體,舊譯為民主之國。似皆可稱為憲法。雖然,近日政治家之通稱,惟有議院之國所定之國典乃稱為憲法。故今之所論述,亦從其狹義:惟就立憲政體之各國,取其憲法之異同,而比較之云爾。…
憲政立憲君主國政體之省稱之始祖者,英國是也。
1909年,〈各國憲法異同論〉,《點校》,第二冊,頁1056。
1.梁啟超此時對于「憲法」的認知,是從法律意義之角度來理解,故推衍致任何國家都有憲法的結論,而和自己以往的認識有所混淆需做批注。
2.惟「有議院之國所定之國典乃稱為憲法」。
3.「憲政」一詞是「立憲君主國政體之省稱」,且英國是行此種「政體」的始祖。但此處既以英國的「政體」為「立憲」始祖的表征,則所謂「立憲」自是指舊譯為「君民共主」的「議會制」。
政體之區別以直接機關之單復為標準。其僅有一直接機關,而行使國權絕無制限者,謂之專制政體;其有兩直接機關,而行使國權互相制限者,謂之立憲政體。…今就現世之君主立憲國而舉其特色,則有三焉:第一,民選議會。議會謂國會也,凡立憲國必有國會,…第二,大臣副署。凡立憲國君主之詔敕,必須由大臣署名,然后效力乃發生。…第三,司法獨立。凡立憲國皆有獨立之審判廳以行司法權。…
舉此三條件,規定于憲法中,而不許妄動,謂之立憲。立憲之制,首行于英國,…。
1910年,〈憲政淺說〉,《點校》,第二冊,頁957-958。
1.從將國權再予「國家直接機關權限分化」的角度界定「立憲政體」。
2.只要有「兩直接機關,而行使國權互相制限者」,即可謂之立憲政體,不以「三權分立」與「司法獨立」為必要條件。
學者言憲政之所以示別非憲政者有三:民選議院其一也,責任內閣其二也,司法獨立其三也。故語憲政之特色,實惟前二義。而議院與內閣,又必相倚而始為用,二義實一義也。…所謂君主立憲之異乎君主專制者,其在專制之國,則立憲(本文作者按:法?)與行政兩大權,皆由君主獨斷而躬行之。立憲國不爾,立法權則君主待議院協贊而行之,行政權則君主命大臣負責任而行之。質言之,則專制國之君權無限制者也,立憲國之君權有限制者也。立憲之與專制,所爭只此一點。
1911年2月,〈敬告國人之誤解憲政者〉,《點校》,第二冊,頁1078。
1.憲政與非憲政的差別有三,但其特色則為民選議院及責任內閣二義,且實際上僅屬一義,亦即開議院而行議會制度。
2.「其在專制之國,則立憲與行政兩大權」中的「立憲」兩字若無筆誤或誤印,則「立憲」當即指建立議會制度。
3.若是為「立法」之誤植,從「立憲國不爾,立法權則君主待議院協贊而行之」來看,立憲與否也是指「立法權」有無從行政權分離而言,故「立憲」仍意味了議會制度的建立。
4.立憲是指從君權中分離出了立法與行政兩權為表征,并非就「國權」相對于「社會」乃為有限度之constitutionalism的概念。
立憲政體,以君主不負政治上之責任為一大原則。其所以示別于專制政體者,惟在此點。…
1911年5月,〈立憲國詔旨之種類及其在國法上之地位〉,《點校》,第二冊,頁1062。
1.立憲政體以政治上的虛君元首為一大原則,故自是延續開議院或國會以行議會內閣制的思維,來界定立憲政體。
2.1905年同盟會成立后,革命派的言論較立憲派受到了廣泛支持,梁啟超繼主張開明專制后,又改變立場為虛君元首的議會內閣制。
資料來源:作者自制
[1] 梁啟超,〈各國憲法異同論〉,引自梁啟超著,吳 松、盧云昆等點校,《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二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1056。 [2] 梁啟超,〈中國國會制度私議〉,引自同上注書,頁967。 [3] 梁啟超,〈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輯于《飲冰室合集》,4,專集之三十三(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頁88。 [4] 華力進,〈政體〉,見羅志淵主編,《云五社會科學大辭典第三冊:政治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5年12月,版7),頁212。張明貴,《Top 100憲政用語熱門榜》(臺北:書泉出版社,2005年),頁140-141。 [5] 熊月之,《中國近代民主思想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2年),頁8。 [6] 陳鵬仁,《孫中山先生思想初探》(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2000年),頁17。 [7] 謝 放,〈戊戌前后國人對「民權」、「民主」的認知〉,《二十一世紀月刊》,2001年6月號(總第65期),頁43-44。另可參閱 謝 放,〈“張之洞反對民權”說剖析—兼析19世紀后期中文詞匯“民權”與“民主”的涵義〉,《社會科學研究》(北京),1998年第2期,頁100-101。 [8] (美)惠 頓 著,(美)丁韙良譯,何勤華點校,《萬國公法》(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3年),頁72。 [9] 同上注,頁143。 [10] 郭嵩燾,《郭嵩燾日記》,第三卷(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頁535。 [11] 黃遵憲,《日本國志?國統志》一。 [12] 張之洞,何啟及胡禮垣撰,馮天瑜、蕭 川評注,《勸學篇?勸學篇書后》(武漢:湖北人民初版社,2002年),頁336。 [13] 《萬國公報》,第316卷,1874年12月。 [14] 《萬國公報》,第627卷,1881年2月。 [15] 梁啟超,〈愛國論三?論民權〉,《清議報》第22冊。引自梁啟超,〈愛國論〉,梁啟超著,吳 松、盧云昆等點校,《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二集(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頁668。 [16] 梁啟超,〈立憲法議〉,《清議報》第81冊。引自梁啟超,〈立憲法議〉,同上注書,頁921-922。 [17] 孫廣德,〈戊戌前后的民權思想(1894-1903)〉,輯于《中國近代的維新運動—變法與立憲》(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2年),頁29。 [18] 熊月之,前引書,頁402。 [19] 孫中山,〈民報發刊詞〉,輯于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二冊(臺北:近代中國出版社,1989年),頁256。 [20]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五講〉,《國父全集》第一冊,頁100-101及107-108。 [21] 孫中山,〈中國革命史〉,《國父全集》第二冊,頁356。 [22] 梁啟超,〈開明專制論〉,《飲冰室文集點校》第三集,頁1389。 [23] 詳參方維規,〈「議會」、「民主」與「共和」概念在西方與中國的嬗變〉,《二一世紀雙月刊》,2000年4月號(總第58期),頁54-56。 [24] 牛 彤,《孫中山憲政思想研究》(北京:華夏出版社,2003年),頁20。 [25] 參閱薩孟武,《中華民國憲法新論》(臺北:三民書局,1990年11月,9版),頁36。陳新民,《中華民國憲法釋論》(臺北:作者自版,1995年),頁61-68。 [26] 孫中山,〈檀香山興中會成立宣言〉,《國父全集》第二冊,頁1。值得留意的是,在本文所引據《國父全集》第二冊之版本另收錄了〈香港興中會宣言〉中,則為「以振興中華,維持團體起見」的文字,而將「國體」改為「團體」。據稱國民黨黨史會編之《國父全集》系作「國體」,但依原文及胡漢民編之《總理全集》均作「團體」。見頁2及頁4之注5。 [27] 牛 彤,前引書,頁18。 [28] 見《翁文恭公日記》,“光緒二十一年七月初九日”。轉引自湯志鈞,《戊戌變法史》(上海: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2003年,修訂本),頁473。 [29] 孫中山,〈致香港總督歷數滿清政府罪狀并擬訂平治章程請轉商各國贊成書〉,《國父全集》第二冊,頁5-6。 [30] 孫中山,〈復中華國貨維持會論服制函〉,前引《國父全集》第四冊,頁204。 [31] 孫中山,〈國民黨宣言〉,前引《國父全集》第二冊,頁33。該宣言應非出自孫中山手筆,丘桑主編之《護法使者—民國奇才奇文系列:宋教仁卷》(北京:東方出版社,1998年)將之收錄,以其為宋教仁所撰。 [32] 孫中山,〈中國必革命而后能達共和主義〉,前引《國父全集》第二冊,頁398-399。該一談話另附有內容互有出入的版本,題名為〈與宮崎寅藏之談話〉,頁399-400。 [33] 同上注,頁399。 [34] 牛 彤,前引書,頁29。 [35] 參閱顧炎武,〈郡縣論〉,《亭林文集》卷一,收于《四部叢書》(077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7年),頁10b。 [36] 參見,溝口雄三,〈中國民權思想的特色〉,輯于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編,《中國現代化論文集》(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1年),頁345-350。 [37] James Madison, Federalist, No.51, in Clinton Rossiter, ed., The Federalist Papers (New York: 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of World Literature, Inc.,1961),p.322. [38] 孫中山,〈中華民國之意義〉,前引《國父全書》第三冊,頁163。 [39] James Madison, Federalist No.10, op.cit., pp. 77-84. [40] 熊月之,前引書,頁12。 [41] 孫中山,〈民權主義第五講〉,頁102-1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