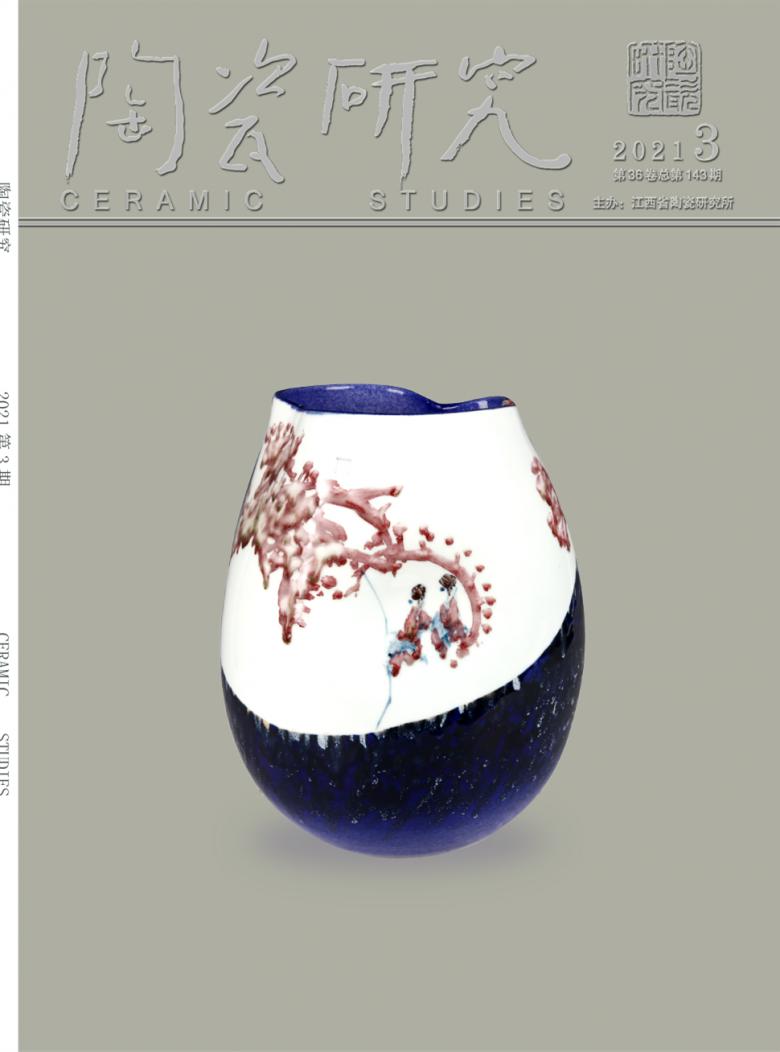從“述而不作”看儒家經典詮釋的理論特質
佚名
正如詮釋學所指出的,理解是人之基本的存在方式。而不同文化共同體之間之所以出現不盡相同的理解形態,又與各文化共同體所具有的不同的精神特質有著直接的聯系。本文擬從孔子倡導并身體力行的“述而不作”的敘述傳統入手,從一個側面對儒家經典詮釋的特質作一探討。
“述而不作”語出《論語·述而》,是孔子的自我評價:“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竊比我于老彭。”其字面意思是僅傳述既有而不進行創始性的工作。但事實上,正如孔子的有關工作所顯示的,在他對既有內容的傳述過程中實際上包含了創始性的義涵。正如朱熹所指出的:“述,傳舊而已。作,則創始也。故作非圣人不能,而述則賢者克及。……孔子刪《詩》《書》,定禮樂,贊《周易》,修《春秋》,皆傳先王之舊,而未嘗有所作也,故其自言如此。……然當是時,作者略備,夫子蓋集群圣之大成而折衷之。其事雖述,而功則倍于作矣,此又不可不知也。”(朱熹:《四書章句集注·論語集注》)這也就是說,孔子雖采取了“述”的形式,但卻有著“作”的內容。因此,也可以把這種經典詮釋方式稱作“以述為作”。也正因為此,雖然孔子的有關工作在文本上的確是“皆傳先王之舊”,但這并沒有妨礙他成為儒家文化的開創者,成為推進文化完成由原初階段向成熟形態轉進的中心開啟性人物之一。正是以“述而不作”的形式,孔子挺立了人的道德主體性,點醒了人們對作為自身內在本性的“仁”的自覺,為周初以來主要是作為外在行為規范的禮樂文化在人性本質的層面確立了內在根據,從而為中國文化成為以內在化的路向安頓人之生命意義為思想主題的成熟形態奠定了穩定的精神方向,實現了中國文化發展史上的根本變革[1]。
孔子所開創的這一傳統對日后儒家經典詮釋產生了重要。在一定意義上,“述而不作”成為了其后儒家經典詮釋基本的形式特征。換言之,孔子之后,通過“傳先王(賢)之舊”而進行傳述和創作成為儒家經典詮釋的基本形態。這一點在作為中國傳統學術之正統的儒家經學中得到了鮮明的表現。就文體而言,構成經學的著述可分為“經”和“傳”兩類。就其本意而言,“經”指原創性的經典,而“傳”則指詮釋經文的著述。但事實上,在經學發展演進的過程中,人們把某些儒家思想奠基的傳注之作也稱之為“經”。如《春秋》是經,作為解釋《春秋》的《春秋左傳》、《春秋公羊傳》、《春秋榖梁傳》則是傳。但至唐代,“三傳”已被視為經。正是有見于此,清代章學誠指出:“今之所謂經,其強半皆古人之所謂傳也。”(《文史通義·經解》)這也就是說,即使是對經而言,也有不少實際上是傳而非經。不僅如此,在數量上經本身是少之又少的,即使到有宋一代,算上《孟子》,才合稱“十三經”。而歷代的傳,則是成千上萬,堪稱汗牛充棟。可以毫不夸張地說,中國文化傳統中所謂經學,就是由一代又一代學人對為數極少的有限幾本“經”不斷加以傳注、詮釋而形成的。而傳注、詮釋的基本形態就是“述而不作”。這至少表現在以下幾方面。
第一,經學的存在是以對作為“經”的原初文本的不斷詮釋為前提的,離開了對原初文本的不斷詮釋,所謂經學就無從談起。
第二,盡管不能說在經學發展的過程中沒有新的范疇與出現,但就其基本范疇如理、氣、心、性、有、無、動、靜、名、實、知、行等和討論的基本問題如天人關系、心性之學、人性善惡、希圣希賢等而言,則堪稱幾千年來保持了顯明的一致性,從軸心時代這些范疇和問題開始出現,到19世紀中葉西方近代文化傳入中國之前,經學一直在圍繞這些范疇和問題展開自己的學理系統①
第三,“述”成為儒家經學的基本敘事方式。不僅經籍成為經學闡釋的先在文本、經學的基本范疇與問題一直與軸心時代保持了高度的一致性,而且“述”而非“作”構成了儒家經學一以貫之的基本敘事方式。儒者在進行經典詮釋時,往往是在經過“小學”功夫即對原典字詞的訓詁、考據之后,才進入義理的闡釋。而在義理的闡釋中,又往往要先溯其原始、再明其流變,并蒐集前此的各家注疏,最后才有所謂“斷以己意”。這就形成了儒者皓首窮經,為一字而釋數十萬言,但其中絕大部分篇幅都只是“述”,而“作”者即闡述釋經者自己意見的內容卻只有數千言、數百言乃至數十言的情狀。
第四,正如孔子之自述所表明的,在傳統經學中,即使對“作”而言,人們也要自覺不自覺地采取“述”的形式。這至少有以下兩種情況。其一,在歸根結底的意義上,無論是“述”還是“作”,立言的準則都是“以圣人之是非為是非”。作為陽明后學中頗具批評反省精神的李贄對此有著頗為清楚地描述:“前三代吾無論矣;后三代,漢唐宋是也。中間千百余年而獨無是非者,豈其人無是非哉?咸以孔子之是非為是非,故未嘗有是非耳。”(《藏書·世紀列傳總論》)這種狀況的結果是“人皆以孔子為大圣,吾亦以為大圣;皆以佛、老為異端,吾亦以為異端。人人非真知大圣與異端也,以所聞師父之教者熟也。師父非真知大圣與異端也,以所聞儒之先教熟也。儒先非真知大圣與異端也,以孔子有是言也。……儒先臆度而言之,你師沿襲而育之,小子蒙聾而誦之,萬口一詞,不可破也;千年一律,不自知也。”(《續焚書·題孔子像于芝佛院》)李贄的批評或有過激之處,但的確可以從一個側面窺見經學立言“以圣人之是非為是非”的情狀。其次,即使真有與先圣前賢不盡相同的“己意”,為了突顯其存在的合法性,人們也往往自覺不自覺地將之歸結為與先圣前賢的明確論斷或微言大義一致,從而事實上是給“作”披上了“述”的外衣。作為中國哲學史上重要發展階段的魏晉玄學和宋明的開創者之一,王弼和周敦頤顯然可以看作是中國哲學史中的“作者”。但其撰述卻是以《周易注》、《老子注》和《太極圖說》等傳注的形式出現的。從“理存于欲”出發將倡導“存天理,滅人欲”的宋明道學指認為是“以理殺人”的清儒戴震在儒學發展史上無疑有其思想的獨特性,但他確立自己有關觀念之合法性的方式卻是通過撰著《孟子字義疏證》而力圖證明自己的有關思想是符合孟子的“微言大義”的。也正因為此,在中國哲學史上,甚至出現了將自己撰著的書稿托名于古人的情況,由此而有如《列子》等被今人懸疑為“偽書”的一類典籍。
儒家經典詮釋的這一特征和西方文化與哲學在發展演進中所體現出來的詮釋傳統形成了鮮明對比。概而言之,如果說儒家經典詮釋更為注重“述”,那么西方詮釋傳統則更為注重“作”。不僅如此,在“作”的過程中,西方文化在不同思想家的理論系統之間不是更為注重相互之間的承繼關系,而是著力于突顯自身不同于其他思想系統的理論特質,甚至不惜為此而對其他思想系統在整體上作出否定性的評價。換言之,不同于在儒家經典詮釋傳統中,后起的學者為了謀求自身思想觀念的合法性而采取“以述為作”的方式以充分突顯其思想系統與前此相關思想系統的繼承性,在西方詮釋傳統中,后起的思想系統恰恰是要通過指證前此相關思想系統的局限性來反顯自身的革命性,以為自己確立存在的合法性與合理性。在這個意義上,可以把儒家經典詮釋傳統中后起思想系統與此前思想系統之間的關系比喻為一波一波緊緊相連的波浪,而西方詮釋傳統中后起思想系統與此前思想系統之間的關系則可以看作一座座突兀而起的山峰。黑格爾對西方哲學史演進歷程的描述,可以看作是十分典型地狀述了西方詮釋傳統的這一理論特質。黑格爾把哲學史比喻為一個“廝殺的戰場”:“全部哲學史就這樣成了一個戰場,堆滿著死人的骨骼。它是一個死人的王國,這王國不僅充滿著肉體死亡了的個人,而且充滿著已經推翻了的和精神上死亡了的系統,在這里面,每一個殺死了另一個,并且埋葬了另一個”。“這樣的情形當然就發生了:一種新的哲學出現了。這哲學斷言所有別的哲學都是毫無價值的。誠然,每一個哲學出現時,都自詡為:有了它,前此的一切哲學不僅是被駁倒了,而且它們的缺點也被補救了,正確的哲學最后被發現了。但根據以前的許多經驗,倒足以表明新約里的另一些話同樣地可以用來說這樣的哲學,----使徒彼德對安那尼亞說:‘看吧!將要抬你出去的人的腳,已經站在門口。’且看那要駁倒你并且代替你的哲學也不會很久不來,正如它對于其他的哲學也并不會很久下去一樣。”[2]
如果承認在儒家經典詮釋傳統中存在著上述理論特質,可以進一步討論的是:出現上述理論特質的原因何在?接下來本文就從一個側面對此試作進一步探討。關于這個話題同樣可以從孔子說起。前已述及,孔子在中國文化發展過程中的一個重要作用就是點醒了人們對“仁”的自覺,挺立了人的道德主體性,在順承三代文化特別是周文化的基礎上為其后以儒家為主導的中國文化的發展演進奠定了基本的精神方向,從而成就了承先啟后、繼往開來的事業。關于“仁”,孔子留下了不少論說,根據張岱年先生的觀點,下面一段話可看作是孔子的“仁之界說”:“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論語·雍也》)張先生在陳述了之所以將這兩句話看作是孔子所定仁之界說的三點理由后進一步解釋說:“‘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乃是仁的本旨。‘立’是有所成而足以無倚;‘達’是有所通而能顯于眾。自己求立,并使人亦立;自己求達,并使人亦達:即自強不息,而善為人謀。簡言之,便是成己成人。‘能近取譬’,則是為仁的,即由近推遠,由己推人;己之所欲,亦為人謀之;己之所不欲,亦無加于人。”[3]張先生的上述論斷的確從一個側面抓住了“仁”的基本意旨。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把“仁”理解為是一種從對自我生命的肯定的價值立場出發,在推己及人乃至及物的過程中所生發出來的對他人和他者生命的肯定和培護之情。而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和“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為基本內容的“忠恕之道”則是最為切近的“為仁之方”即行仁的方法。由此出發,孔子所開創的儒家要求人們在踐行自己的生命活動時,自覺地按照仁道原則行事,在處理人與他人、人與世界、人與超越的天地宇宙、人與傳統之關系的過程中,均自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