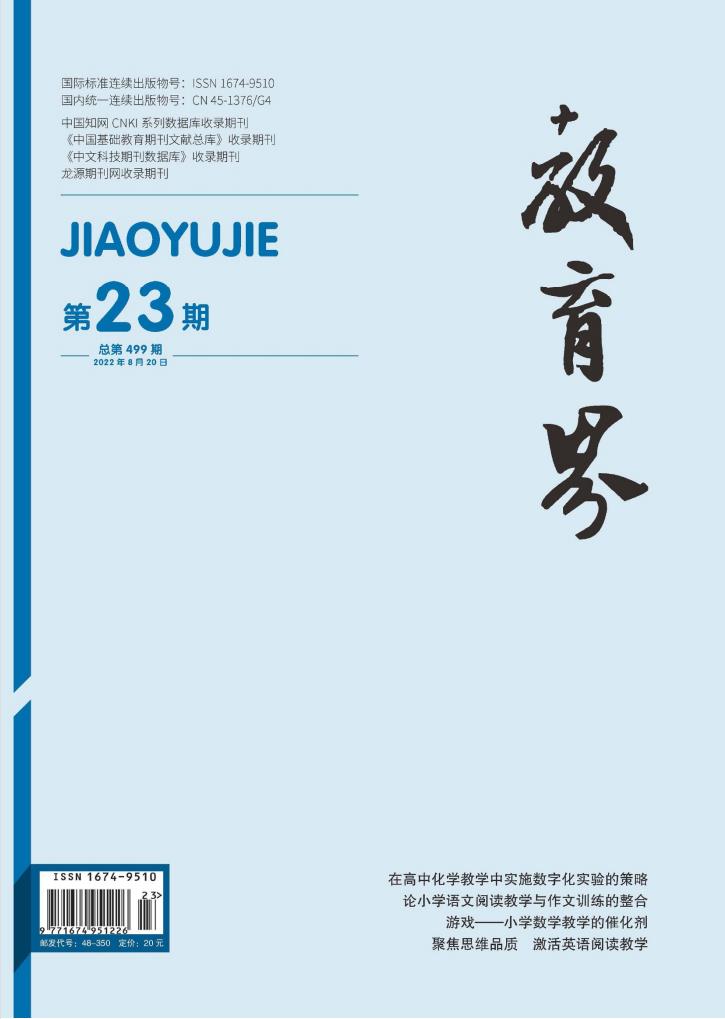從東亞儒家思想史脈絡論「經典性」的涵義
佚名
一、引 言 在不同的文化傳統中,「什么是經典」這個各有其不同的答案。關于「經典性」(canonicity)的不同定義具體地說明:各個不同文化傳統中的經典,除了經典的共同性質之外,更深具個別地域文化之特色,并受到各地域的與文化傳統的投影。我們可以說,所謂「經典」或「經典性」常常是在各地域的思想史或文化史脈絡中被定義的。 本文探討的中心課題是:在東亞儒家思想史脈絡中,「經典性」如何被定義?為了探討這個問題,我們除了運用儒家涉及經典之特質的直接史料之外,也想從東亞儒者解釋經典文本的言論之中,推敲他們心目中經典之所以為經典之特質。
二、儒家思想脈絡中「經典性」之三個面向 從東亞儒家思想脈絡來看,「經典性」至少包括三個重要內涵:(1)的內涵,(2)形上學的內涵,(3)心性論的內涵。我們引用儒者釋經的相關言論,依序加以論述。 (1)社會政治的內涵:儒家定義下的「經典性」,第一個組成要素就是經典必須具有社會政治的內涵,坐而言可以起而行,致天下于太平。這種特質源自古代政教不分之傳統,古代貴族以《詩》《書》《禮》《樂》等經書治理國家,統領眾庶,所謂「王官學」就是貴族之學。從《左傳》記載可見,春秋(722-481B.C.)的行人,在外交場合常引用《詩》《書》作為修辭之依據,甚至春秋各國在戰事場合中也常引《詩》以證成自己之立場。到了貴族凌夷,「王官學」沒落,「百家」之學大興,民間學者雜然紛起,而孔子(551-479B.C.)尤開其先河。 自孔子以降,經典之所以成為經典,最重要的特質就是經典必須通過批導現實世界進而改變世界。孟子(371-289B.C.)可能是最早提出這種看法的哲人,他說:「王者之跡熄而《詩》亡,《詩》亡然后《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孟子?離婁下》)。孟子認為孔子之所以因魯史而作《春秋》,乃是為了從史實中求史義,以致天下于太平。這種將經典視為社會政治之寶典的看法,幾為漢代人之共識,太史公司馬遷(145-86B.C.)解釋孔子作《春秋》之意說: 孔子知言之不用,道之不行也,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為天下儀表,貶天子,退諸侯,討大夫,以達王事而已矣。子曰:「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 從孟子到司馬遷所主張的「經典性」之社會學與政治學內涵,確屬言之有據,孔子早就說過:「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于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論語?子路》),從孟子以降許多儒者所定義的作為社會學與政治學的「經典」,確實與孔子的說法互相呼應。 經典作為社會政治運作之寶典,在兩漢時代不僅是「經典性」的重要定義,更是社會與政治運作的事實。誠如皮錫瑞(鹿門,1850-1908)所說,漢代政治實受經典之主導,「武宣之間,經學大昌,家數未分,純正不雜,故其學極精而有用。以〈禹貢〉治河,以〈洪范〉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治一經得一經之益也。」在兩漢時代,五經于施政的實例可謂不勝枚舉,具體的說明經典的政治學涵義在現實世界中的落實。 如果「經典性」是建立在經典的社會政治性之上,那么經典中的「道」就是一種批導并改變現實世界的具體原則與策略,誠如董仲舒(C.179-C.104B.C.)所說:「道者,所繇適于治之路也,仁義禮樂皆其具也。」這種經典中的「道」是徹底的「人道」而不是「天道」,這種「人道」并非不占時間與空間的、作為抽象范疇的形上學之「道」。在這種思想脈絡下,漢代人特別重視《春秋》這部經典,實在是理所當然,事所必至。 德川時代(1600-1868)的日本儒者也多半從社會性與政治性來定義「經典性」。從十七世紀古學派大師伊藤仁齋(維楨,1627-1705)以降,日本許多儒者都不滿朱子(晦庵,1130-1200)在「人道」之上另立「天道」,他們對宋儒之形上學傾向皆特加批判。他們多半主張儒家經典中所謂「道」,就是人倫日用之「道」,伊藤仁齋在《語孟字義》中的一段話,很具有代表性,他說: 道,猶路也,人之所以往來也。〔……〕大凡圣賢與人說道,多就人事上說。〔……〕凡圣人所謂道者,皆以人道而言之。〔……〕道者,人倫日用當行之路。 伊藤仁齋認為儒家經典中的「道」,就是「人倫日用當行之路」,因為: 人外無道,道外無人。以人行人之道,何謂知難行之有!夫雖以人之靈,然不能若羽者之翔,鱗者之潛者,其性異也。于服堯之服,行堯之行,誦堯之言,則無復甚難者,其道同也。故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若夫欲外人倫而求道者,猶捕風捉影,必不可得也。〔……〕天地之間,唯一實理而已矣。 仁齋所謂「實理」就是具體的社會政治事物,而不是超越的形而上的世界。 十七世紀伊藤仁齋以「人倫日用」之「實理」界定儒家經典中的「道」,也獲得十八世紀下半葉大阪懷德堂儒者中井履軒(名積德,字處叔,號履軒,1732-1817)的呼應。中井履軒解經,極力批駁朱子學,并強烈主張經典中的「道」的人間性格,他說:「道元假往來道路之名,人之所宜踐行,故謂之道也。所謂圣人君子之道,堯舜文武之道,皆弗離乎人矣。《易傳》諸書乃更假論易道天道,及陰陽鬼神莫不有道焉,并離乎人而為言矣。」中井履軒認為孔孟之「道」皆是「人倫日用」之「道」,他解釋《論語?述而》「子曰:志于道」一語說:「道,如君子之道,堯舜之道,夫子之道,吾道之道,此與人倫日用當行者,非兩事。……集注解道字,或云:『事物當然之理』,或云:『人倫日用之間所當行者』,如判然兩物,不知其義果經乎?竊恐不若用一意解之。」 德川儒者將儒家經典中的「道」從天上轉到人間之后,認為經典之所以為經典正是在于它能發揮「人倫日用當行」之社會性與政治性之作用。在對經典中的「道」的性格重新界定之后,德川儒者對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儒家經典?」也提出了嶄新的答案。伊藤仁齋主張《論語》、《孟子》二書是儒家思想的淵源,他推崇《論語》為「最上至極宇宙第一書」,而《孟子》則為「《論語》之義疏」,兩者之價值皆高出于六經之上。仁齋認為對儒家經典義理的解釋,應以《論語》與《孟子》為依歸。中井履軒對于「正統的」儒家經典,也提出一套看法,他說: 夫子晚年緒正六經,固非無垂教之意。然秦漢以降,禮樂已泯滅矣。詩書缺亡紛亂,無以見夫子之功。《易經》雖存矣,亦無功。《春秋》亦非孔子之筆,故傳孔子之道者,唯《論語》、《孟子》、《中庸》三種而已矣,皆后人之績,而非宰我所知。豈容據此等說哉?是故夫子垂教之績,皆泯于秦火,而后世無傳也。此頗吾一家之言,人或不之信,仍信用《易傳》、《春秋》者,則廑廑亦唯有是二事而已。學者是取《易傳》、《春秋》,通讀一過以評之,何處是傳堯舜之道者? 中井履軒認為:只有《論語》、《孟子》、《中庸》等三部經典,才能傳孔子之道,其余如《易傳》和《春秋》均不足為據。總之,德川儒者與孟子以降兩漢中國儒者,都將經典中的「道」解釋為充滿人間性格的「道」。在這種對「道」的理解之下,中日儒者所認定的「正統」儒家經典雖然互有不同,但是他們在以「社會性」與「政治性」界定「經典性」這點上,完全是若合符節。 (2)形上學的內涵:東亞儒者界定「經典性」的第二項特質是:經典必須有其形上學的內涵。關于從「形上學」界定「經典性」,應可上溯至戰國末期《禮記?經解》及《莊子?天下》等,但最具有代表性的可能仍是朱子。朱子在解釋他重訂的《中庸》第32章時,對「經」之涵義曾提出如下的解釋: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圣人之德極誠無妄,故于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后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于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于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于物而后能哉。 朱子上文中所說的作為常道的「經」之特征在于「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這種作為形上之理的「經」,是朱子心目中「經典性」的要件。 朱子從形上的「道」界定「經典性」,代表東亞儒者心目中「經典性」的一個重要面向。程頤(伊川,1033-1107)就說:「今之學者歧而為三:能文者謂之文士,談經者謂之講師,惟知道者乃儒學也。」宋人羅處約(思純,960-992)也說: 六經者,《易》以明人之權而本之于道;《禮》以節民之情,趣于性也;《樂》以和民之心,全天真也;《書》以敘九疇之秘,煥二帝之美;《春秋》以正君臣而敦名教;《詩》以正風雅而存規戒。是道與六經一也。」 在許多宋儒心目中,所謂「道與六經一也」的「道」,具有純粹的形上學性格。 德川時代日本儒者中,傾向從形上學界定「經典性」的多半是陽明學者,大鹽平八郎(中齋,子起,1794-1837)是一個代表人物。大鹽平八郎主張經典之特質在于其言「太虛」與「理氣」: 或曰:「于經明言虛,有乎?」曰:「有。《大學》曰:『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圣,其心好之,不啻若自其口出。寔能容之。』這兩個『容』字,心之量也。心之量,非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