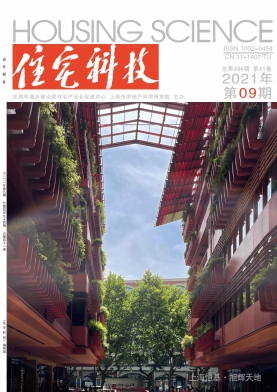明代縣衙規制與日常政務處理程序初探
未知
縣衙是明代縣級政府的辦公官署,可以說是一縣的政治中心。縣官、佐貳、首領等朝廷職官和六房書吏,按規定都要在縣衙中居住和辦公,大量的執事差役也在縣衙中聽候官吏差遣,縣級政府的刑名、錢谷等日常政務主要是在縣衙中完成的。此外縣衙內外還有監獄、倉庫、縣學、賓館、驛站、遞運所等相關機構和設施。考察明代縣衙的布局和結構,以及日常政務在其中的運行流程,對于我們理解明代縣級地方政府的實際運作當是極有助益的。(注:關于明代縣衙及其政務運轉的研究,此前主要有柏樺的《明代州縣衙署的建制與州縣政治體制》(《史學集刊》1995年第4期)、 《明代州縣政治體制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劉鵬九的《內鄉縣衙與衙門文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李志榮的《元明清華北華中地方衙署建筑的個案研究》(北京大學博士論文,2004年),及美國學者Thomas G. Nimick的博士論文《晚明的縣、縣官與衙門》(The County, the Magistrate, and the Yamen in Late Ming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1993)。以上成果對研究明代縣衙的建筑格局和衙門文化做出了重要的貢獻,但對明代縣衙的具體規制和政務運作流程還缺乏深入細致的說明。)
一、明代縣衙的規制
據學者的新近研究揭示,中國古代地方官衙的建筑格局到明代發生了一個顯著的變化,這就是明初太祖頒行了地方衙署建設應遵循的“范式”。這一規制與前朝的主要不同在于“府官居地及各吏舍皆置其中”。[1](P22) 洪武初王祎《義烏縣興造記》載:“今天子既正大統,務以禮制匡飭天下。乃頒法式,命凡郡縣公廨,其前為聽政之所如故,自長貳下逮吏胥,即其后及兩傍列屋以居,同門以出入,其外則繚以周垣,使之廉貪相察,勤怠相規,政體于是而立焉。命下郡縣,奉承唯謹。”[2](卷九) 這樣的建筑格局反映了朱元璋懲前元之舊弊,力圖整頓吏治的思想。《大明律·工律·營造·有司官吏不住公廨》規定,有司官吏必須居于官府公廨,不許雜處民間:“凡有司官吏,不住公廨內官房,而住街市民房者,杖八十。” 雖然明初頒布了地方衙署建設的規制,但明代縣衙的建筑格局還要受歷史遺留下來的衙署格局的影響。從文獻記載來看,許多在明初新修或重修衙署的格局的確遵循了新的規制,但也有些地方限于經濟條件或歷史格局的影響,并不完全符合新的規制,比如在一些地方吏舍并未被納入到縣衙之中。總的來看,明代縣衙根據所在地區地理位置和經濟條件的不同,有的較為宏敞,有的則較為簡陋,但大多數縣衙有兩個共同特點:一是封閉性,四周以高墻與外界相隔;二是形制四方規整,中間有一條顯著的中軸線。在這條中軸線上,依次排列著縣門、儀門、大堂、二堂、三堂等主要建筑。中軸線大致可分為三段:儀門之前主要是禮儀性的建筑;儀門至二堂或三堂為縣衙的核心區域,為知縣審案、辦公之所;二堂或三堂之后,為知縣內宅。中軸線上的院落一般遵守對稱的準則。中軸線兩側,則分布著佐貳官縣丞、主簿和首領官典史的衙門和宅邸,以及吏廨、監獄、倉庫等建筑。 以下試以隆慶《儀真縣志》所載儀真縣衙[3](國朝縣治圖) 為例,來說明明代縣衙的具體構造。 縣衙前有照壁一道,照壁后為牌坊,儀真縣衙牌坊上有匾額題“忠廉坊”。牌坊以里為大門,大門兩邊的墻呈“八”字形,所謂“八字衙門”即由此而來。八字墻上可張貼告示、榜文,公布科舉考試錄取結果等,有的加上頂棚和柵欄,稱“榜廊”或“榜棚”。牌坊以里,設有醫學、陰陽學,右側設有總鋪(急遞鋪),以便于縣衙公文的快速遞送。牌坊正北為鼓樓或譙樓,為兩層,是縣衙中最高的建筑,便于報時和瞭望。鼓樓外墻左右,分別建有申明亭、旌善亭,或申明在左、旌善在右,或反之,無一定之規。嘉靖《太平縣志》:“申明亭:在縣治門外,牧愛坊左。凡民有作奸犯科者書其名揭于壁,而耆民里長會斷民訟者亦于是云。旌善亭:在縣治門外,牧愛坊右。凡民間有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則書其行實揭于亭,以寓勸善之意云。”[4](卷四,公署) 進入鼓樓,也就正式踏進了縣衙的大門。有的縣沒有鼓樓或譙樓,而以縣門代之。 鼓樓之后,即是儀門。有的縣鼓樓之后還有一道二門,儀門為三門。儀門之左,一般設土地祠、衙神廟、寅賓館(或迎賓館),儀門右側為縣獄。儀門中間為正門,平時關閉,只有迎接上級或同級官員造訪時才打開,兩側開有角門。 儀門內為衙中最大的一進院落,院中樹立一座小亭,稱“戒石亭”。亭中石碑南面刻“公生明”三字,語出《荀子·不茍》:“公生明,偏生暗。”碑陰書“爾俸爾祿,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難欺”十六字。戒石碑下有甬道向北,到達月臺,臺上即是縣衙的核心建筑——大堂。大堂為知縣審案、辦公之所,一般建得高大軒敞,正中設桌案,堂前設柵欄,前有飛軒甃,其下為露臺,上有審案時供人犯下跪的跪石。大堂又稱“縣廳”、“正廳”、“治廳”、“琴堂”、“牧愛堂”、“親民堂”、“節愛堂”等。大堂兩側耳房可用作儀仗庫、鑾架庫[5] 等庫房。大堂左側或右側,有的還設有“典史廳”、“典幕廳”、[6](卷四,建制) “幕廳”、[7](卷二,署廨) “縣幕”[8](縣治之圖) 或“贊政亭”,[3](國朝縣治圖) 為幕官典史辦公之所。 應當說明的是,縣衙中幕廳的存在并不能被簡單地當作出現縣官幕友的證明。(注:柏樺在《明代州縣衙署的建制與州縣政治體制》(《史學集刊》1995年第4期)中曾認為:“明代州縣衙署正堂左廂修有幕廳,從各地方志的公署建筑沿革來看,這個幕廳修建時間最早的州縣是在洪武二十八年,說明在洪武末年,幕友制已在州縣中出現,從明代洪武以后各州縣相繼修建幕廳的事實來看,幕友是逐漸發展起來的,而在明中葉成為一種不成文卻也為時人公認的定規。”后在氏著《明代州縣政治體制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3年)中,對上述觀點有所修正,認為幕廳開始是典史廳,但仍認為明代中期后演變為知縣幕友的辦公場所。見該書第114~116頁,第119頁。) 幕廳實際上是典史廳,是典史幫助知縣處理文案的場所。首先,首領官在明代又被稱為“幕職”、“幕官”,(注:“幕職”、“幕官”的稱呼自唐宋以來就有,是協助行政主官參酌政務、處理文書的輔助性官職。在明代,首領官的職責與前代幕官類似,因此也被稱為幕官。) 主要掌文移出納,這正是典史的角色。其次,“典史廳”、“幕廳”在眾多不同的縣志上都出現在大致相同的位置——大堂的東西梢間,說明它們所指的應該是同一個東西,只是在不同的縣志編纂者那里使用了不同的稱呼而已。如果將這些名稱——“典史廳”、“典幕廳”、“幕廳”排列在一起,答案就更清楚了。再次,設有典史廳的縣衙同時還設有典史衙,這說明典史廳是典史于本衙辦公之外,協助知縣處理文卷的場所。典史廳設于大堂之側就是這個目的。[5](縣治之圖)[6](縣治之圖)[9](縣治圖) 又次,幕友屬于知縣私人雇傭,因而不宜出現于大堂之側。在清代,幕友協助知縣處理事務,都要在靠近內宅的地方進行。(注:如今存內鄉縣衙之“刑錢夫子院”,即刑名和錢谷師爺的辦公場所,乃位于二堂之后,內宅門之前。見劉鵬九《內鄉縣衙與衙門文化》所錄《內鄉縣衙全圖》,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 幕廳緊鄰縣衙大堂,屬于核心辦公區域,幕友到此辦公不合情理。最后,清代幕友制盛行后,佐貳官設置極少,也就是說佐貳官的職能大部分為幕友所取代,幕友是在佐貳官作用削弱之后取而代之的。而反觀出現“幕廳”字樣的幾幅縣衙布局圖,可以發現一般都有數處佐貳官衙宅,佐貳官的設置還相當多,承擔著很多行政事務,這至少說明即使出現了幕友,作用也必相當有限,此時在大堂之側公然出現幕友辦公的專門處所是令人難以想象的。雖然明代中后期的某些方志中有模棱兩可的記載,如嘉靖《太平縣志》卷四“公署”條:“治廳曰琴堂……左耳房為儀仗庫,籍冊藏焉,又其左為幕廳,幕僚居之。”李樂《見聞雜記》也說明后期縣官常自帶主文之類的私人助手上任:“近日友人作令,雇主文行者,十有四五。”[10](卷八,五十二) 但沒有證據將幕廳與之掛起鉤來。 大堂院內兩側廂房為吏員辦事之六房所在,左側為吏、戶、禮三房,右側為兵、刑、工三房,糧科(房)、馬科及承發房、鋪長司等也排列于左右廂房中。糧科(房)從戶房分出,二者的分工是:“戶房止是分派錢糧,收解俱是糧房。”[11](卷二) 馬科從兵房分出,“承發吏設管公文及管詞狀”。[12] 鋪長司為急遞鋪鋪長辦公之所。北直隸宛平縣大堂兩側廊房有多達15個房科。[7](卷二,署廨) 儲藏冊籍檔案的架閣庫、冊房,以及存放各種器具財物的鹵簿庫、帑庫、鑾駕庫(儀駕庫、鑾儀庫)等,也位于大堂附近。 大堂之后是二堂。二堂是知縣預審案件和大堂審案時的退思、小憩之所,又稱“退思堂”、“改絃堂”、“省觀堂”等。由于它是一個過渡性的建筑,因而相對較小,也叫“穿堂”、“川堂”、“過堂”等。二堂后一般有宅門,將南邊的外衙與北邊的內衙分開。宅門內為三堂和知縣廨,二者有時合而為一。三堂又稱“后堂”、“便堂”,在一些縣它是僅次于大堂的建筑;知縣廨又稱“正衙”、“知縣衙”。三堂是知縣接待上級官員、商議政事和辦公起居之所,有些事涉機密的案件和不便公審的花案,亦在此審理。內衙中一般還有住宅、書房、花廳、后花園等,為知縣的生活區。(注:也有的縣僅有兩個堂,如浙江新昌縣衙只有琴堂和后堂,后堂之后也不像一般的縣是知縣衙,而是縣丞衙,正衙(知縣衙)反而位于縣衙東北角。萬歷《新昌縣志·縣衙圖》,《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古籍書店,1981年。) 縣丞、主簿、典史的衙、宅,分布于縣衙后部中軸線兩側,一般典史衙只有一個,縣丞衙、主簿衙則可能有多個,視該縣所設佐貳官多少而定。 吏舍,即吏員的居所,也分布在縣衙中。明代規定,為防止吏員內外勾結舞弊,吏員平時要待在縣衙內,不允許擅自出衙。吏舍一般集中位于六房之東西側,或散布于官廨之間的空地。官吏都須按規定在縣衙內居住,一般不許雜處民間。然而由于吏員眾多,吏舍難以容納,許多人只好借住衙外民居。沈榜《宛署雜記》卷二“署廨”云:“吏廨無定所,時補各官廨之空地云。吏大半無廨地,僦借民居。”官舍和吏舍合稱“公廨”。關于公廨的規格和等級,弘治《句容縣志》卷二載:“知縣十間,縣丞八間,主簿七間,管馬主簿七間,典史六間,吏舍四十間。” 監獄是縣衙不可或缺的部分,一般占據了縣衙的西南角,故俗稱“南監”。分內監(關重犯)、外監(關一般犯人),男監、女監。附近還設有獄神祠或獄神廟。此外,縣衙中還有馬政廳、馬房、官倉、門房、里舍(里甲房)(注:里舍為到縣應役之里役所備的住所。嘉靖《應山縣志》卷上:“里舍:舊在治房東,亦久廢。知縣王朝璲、典史傅僾改建于申明、旌善二亭之南,各六間。”《天一閣藏明代方志選刊》,上海古籍書店,1982年。成化《內鄉縣志》卷二《公署略》:“里甲房,舊任知縣鄭時,嘗于城中隙地,蓋房若干間,區分所屬二十五保里長、老人、書手、甲首輪該應役者寓之,以便趨事。”后者轉引自川勝守《中國封建國家の支配構造——明清賦役制度史の研究》第83~84頁,東京大學出版會,1980年。) 等建筑。 以上所述是典型的縣衙,當然也有些縣衙不那么規范,比如山東淄川縣縣衙把一般建于縣衙之外的府館、布政分司、按察分司、養濟院、縣倉等都包含在縣衙中。[13](卷一,縣治圖) 臨朐縣的監獄、吏舍則與他縣不同,位于縣衙之外。[14](臨朐縣邑內圖) 縣衙之外還有其他官署和設施,亦為一縣行政之所需,計有縣學、社學、城隍廟、際留倉、祿米倉、預備倉、便民倉、養濟院(疏養孤老無靠之人)、漏澤園(收集埋葬無人認領的遺骨)、府館(府級官員到縣辦事駐扎之所)、布政分司、按察分司(省級兩司官員巡歷所至駐扎之所)、都察院(巡撫至縣駐扎之所)、察院(為巡按至縣駐扎之所)、公館(接待過往官員之所)、管河廳(理河廳)、巡捕廳、巡檢司、水馬驛、急遞鋪、遞運所、社稷壇、山川壇、邑厲壇、僧會司、道會司、稅課局、河泊所、工部分司等。
明朝政府規定了一些法定假日。“凡每歲正旦節,自初一日為始,文武百官放假五日。冬至節本日為始,放假三日”。[15](卷八○,節假) 洪武六年,太祖“命考古休沐假日,禮部以唐六典假日上,從之。令百官每月五日給假”。[16](卷五,洪武六年閏十一月壬辰) 宣德三年,又定于每年歲首旬休十日。[17](卷四十四,休假)(注:又萬歷《明會典》卷八○《節假》:“永樂七年,令元宵節自正月十一日為始,賜百官節假十日。”但查《明會要》本條知其為“賜朝參官元宵節假”,并不含地方官。又記:“弘治四年正月癸未,以修省,罷上元節假。”楊聯陞認為明清時期,每年冬季從十二月二十號前后開始,有一個月左右的“封印”時間,作為春假。見《國史探微》第48頁,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其所據為清末富察敦崇所著《燕京歲時記》“封印”條:“每至十二月,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四日之內,由欽天監選擇吉期,照例封印,頒示天下,一體遵行。封印之日,各部院掌印司員必應邀請同僚歡聚暢飲,以酬一歲之勞。”及“開印”條:“開印之期,大約于十九、二十、二十一三日之內,由欽天監選擇吉日吉時,先行知照,朝服行禮。開印之后,則照常辦事矣。”此言清末習俗,而明代已有歲首旬休,不當再有一月之假。) 此外,逢皇帝登基、壽誕、喪葬等,也要停止公務活動。 除政府規定的假日外,縣衙每日清晨即開始辦公,日暮時方才散衙。“凡官府皆須侵晨署事,日入方散”。[18](卷下,公座) 每日卯時,吏典、隸兵及各種雜役于承發房畫押報到,稱點卯;下午酉時,散衙歸家。“凡公門吏典、兵卒及里長人等,皆須置簿,付承發典吏收掌,每日侵晨于上畫卯,至暮畫酉”。[18](卷下,卯酉) 縣官每日升堂分為早堂(早衙)、中堂(中衙、午堂、午衙)、晚堂(晚衙)。各官對時間的安排,根據各地的不同情況和各自的性情能力,不盡一致。但“堂事須有定規,各役人犯方便伺候遵守”。若初仕者無經驗,“投文聽審,俱無定時,自朝至暮,紛紛擾擾,(吏役)終朝伺候”。[11](卷三,投文會客次序) 據載,早堂一般為卯時至辰時,“糧里長等各照都圖,挨次站立兩廊下,次第升堂,作揖聽發放出”。[12] “升堂后皂隸報門,陰陽報時,同僚揖,首領(注:原文此處有一“一”字,疑誤。) 揖,六房揖,門庫參見,始將公座簿以次僉押。內外巡風、灑掃、提牢、管庫等各報無事,自吏房起先將一日行過公文或申或帖或狀,依數逐一稟報點對,各房挨次僉押用印”。然后“放里老挨圖入見”,[19](公座) “比較里老,催辦公事”。[20](坐衙) 中堂為巳時至未時,主要是“問理詞訟,干辦公務”。[19](公座) “聽訟在午、未時,則白晝了然”。[11](卷四,審訟勿夜) 晚堂為申時至酉時,繼續清理詞訟,審錄獄囚,總結一天公務,然后擊鼓散堂。 知縣一天處理事務總的次序是處理公文、比較錢糧、問理詞訟。《官箴集要》稱處理公文的順序是:“其申達上司公文,早衙僉押;其平關牌帖并批牌等項,中衙僉押。”[18](卷上,六房) 大堂上每日設值堂吏和值印吏各一名,“直堂吏一名,專一在堂掛號登記上下公文,并拘勾人犯牌票,以便揭查。直印吏一名,置簿填寫某房公文幾件,用印幾顆,至晚遞不致違誤,結狀以防奸弊”。[21](立定規) 其余吏典于各房辦事,非傳喚不得上堂。每晚又派巡風吏一人巡視衙門各處,以防奸盜。
三、日常政務的處理程序
縣衙中的人員分為官、吏、役三等,在數量上呈金字塔形。在政務上的分工大體為:官主決策,吏理文書,役供差遣。知縣、縣丞、主簿、典史即正官、佐貳、首領,為朝廷命官,數量極少。知縣總管一縣之政務,佐貳、首領則分別分工負責勸農、水利、清軍、巡緝等某一方面的事務;吏員為在吏部注冊的公職人員,主要在六房、糧科、馬科等各房科中辦事,處理公文賬冊;衙役則司職站堂、看管、守衛、催科、抓捕等事,聽候官吏差遣。 縣衙中的公務文書主要由各房科的吏書草擬。與清代縣官文移主要倚仗師爺不同,明代吏書在公文的處理中還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縣官一應文移,本應親自為之,但實際上多派相應房科起稿。《大誥三編·農吏第二十七》曾規定:“今后諸衙門官,凡有公事,能書者,務必喚首領官于前,或親口聲說,首領官著筆,或親筆自稿,照行移格式為之。然后農吏謄真,署押發放。”[22] 但后期普遍的情形卻是縣官“申上司文移,先令該吏起草”。[21](慎申呈) 由于明代中期以后吏典買充者多,素質普遍降低,通文移者日少,多由各房主文、書手代筆。縣官“凡承上發下文移,只問該房取稿,不必管他央何人作,只要好便罷”。[21](遠主文) 吏典、首領官對公文應及時辦理,不得稽延。《大明令·吏令》規定:內外衙門公事,“小事五日程,中事七日程,大事十日程”。[23] 《大明律·吏律·公式·官文書稽程》規定:“凡官文書稽程者,一日,吏典笞五十,三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首領官各減一等。”《讀律瑣言》卷三《吏律·官文書稽程》注云:“諸衙門文書,小事五日程,中事十日程,大事二十日程。” 遇有公事,六房吏典向上稟報,須自上而下進行,即首先秉明知縣,再赴分管佐貳、首領處商議;簽押文書時,則遵從自下而上的順序,先由下面的吏典首領等官開始,最后至知縣處用印施行。“該房該吏凡遇稟復公事,自上而下;僉押文書,自下而上”。[18](卷上,六房) “遇有大小事務,該吏先于長官處明白告稟,次于佐貳官處商確既定,然后當該吏典幕官書卷,才方自下而上以次僉押訖,正官下判日子,當面用使印信,隨即施行”。[18](卷下,僉押) 這樣做的目的, 可能一方面是為了保證信息上達長官的渠道通暢,不致被中途截斷;同時政務處理意見先由下面的該管官吏議定,最后由縣官決斷施行,也可以減輕知縣的理政負擔,使各級官吏各負其責。 刑名、錢谷為知縣最重之事。縣官受理百姓詞訟稱為“放告”,受理詞訟的日子稱為“放告日”,每隔三五日一次。一般是逢三、六、九日放告。(注:《新官軌范》:“告示眾告狀之人,每月三六九日方許遞狀。”蔣廷璧《璞山蔣公政訓·清詞狀》:“凡三六九日受過詞狀……”吳遵《初仕錄·嚴告訐》:“放告明開告示,或三或六或九,每放告牌出,挨圖逐里進入。”) 也有五日一放告的,更有“民淳事簡之地”,只在每月初二、十六放告兩次。[11](卷四,準狀不妨多) 在農忙時節,為不妨農時,還要止訟幾個月。如四至七月農忙時,除人命、強盜等大案外,其他案件不予受理。放告之日,縣官升堂后,出“放告牌”,原告捧紙依次遞進縣衙。凌濛初《拍案驚奇》卷十《韓秀才乘亂聘嬌妻吳太守憐才主姻簿》:“到得府前,正值新太守吳公弼升堂。不逾時,抬出放告牌來,程朝奉隨著牌進去。”[24] 狀紙遞進后,由承發房吏接下掛號。(注:《新官軌范》:“承發吏,設管公文及管詞狀。”蔣廷璧《璞山蔣公政訓·清詞狀》:“凡詞訟,先令承發科掛號。”) 縣官接狀后為慎重起見,往往并不立即審理,而是退堂后一一細覽,第二天再與發落。(注:吳遵《初仕錄·審詞狀》:“公堂事冗,日亦有限。所收狀,俱俟退堂細看。”《新官軌范》:“將狀子不分有理、無理,俱各接下。省令告狀之人,俱各明日來朝聽審。當夜用心將狀逐一參看,可受理者,緊關去處紅筆標下,次日只在紅筆去處審理。如無理者,將狀扯毀趕出。”《居官格言·放告》:“示仰一應告狀人等,除人命強盜重情不拘日期,其余戶婚、田土、斗毆等項,俱照后開日期遞狀,次日聽審。”《居官格言·遞狀日期》:“初三日初四日聽審初六日初七日聽審初九日初十日聽審十三日十四日聽審十六日十七日聽審十九日二十日聽審二十三日二十四日聽審二十六日二十七日聽審二十九日三十日聽審。”) 不準狀的退回,準狀的再傳原告、被告、證人三方細審。 錢糧完納不及時,或差役辦差逾期,縣官則用刑求、監禁的辦法催督,稱為“比較”。“凡差人解軍、解錢糧,限定日期。如不完批回繳者,即拿的親家屬監候,輪日比較,則事易完”。[21](慎差人) 征比錢糧時,先比較糧長、里老等役,使之催督欠納戶,若再不完,則征比花戶。 縣官除點視橋梁圩岸、驛傳遞鋪,踏勘災傷,檢尸、捕賊、抄札等事外,不得輕離縣衙,有事則以信牌差遣吏役。《大明律·吏律·公式·信牌》規定:“凡府、州、縣置立信牌,量地遠近,定立程限,隨事銷繳。違者,一日笞一十,每一日加一等,罪止笞四十。若府、州、縣官遇有催辦事務,不行依律發遣信牌,輒下所屬守并者,杖一百(按謂如府官不許入州衙,州官不許入縣衙,縣官不許下鄉村之類)。其點視橋梁圩岸、驛傳遞鋪,踏勘災傷,檢尸、捕賊、抄札之類,不在此限。”信牌又稱“牌票”、“票”、“硃票”,為紙質,上面用墨筆寫明所辦事情,限定日期,用硃筆簽押,并蓋官印。關于信牌名稱及形制,顧起元《客座贅語》卷一《辨訛》云:“票,一作慓,疾也,急疾也。今官府有所分付,勾取于下,其札曰‘票’。”[25] 《醒世恒言》卷三十九《汪大尹火焚寶蓮寺》:汪大尹“當晚在衙中秉燭而坐,定稿申報上司,猛地想起道:‘我收許多兇徒在監,倘有不測之變,如何抵擋?’即寫硃票,差人遍招快手,各帶兵器到縣,直宿防衛。”[26] 《三刻拍案驚奇》第二十七回《為傳花月道貫講差使書》,記錢生員偽造官府“紙牌”詐財之事。[27] 《型世言》第二十七回《貪花郎累及慈親利財奴禍貽至戚》,寫奸徒商德、錢流偽造官府牌票,商寫牌,錢用硃筆簽押。[28] 吏役事完須將牌交回,稱“投牌”、[29](P292) “銷牌”。差點差役時又使用簽筒,筒中置簽,上寫各役姓名,差點某役,則抽其名簽付之,事完差役將簽交回。《治譜》云:“在縣呼喚各役,非抽簽叫者不許應。出入時須以簽筒自隨……如在家或轎上,或催夫馬或叫人,系緊急事,袖中宜置小簽,抽一與門子,門子照名以大簽給之,彼事不完,簽不得入。……(行刑時)須簽上本人用刑。”[11](卷二,置簽抽簽法) 但牌票亦不可輕給,以維護牌票的嚴肅性。“凡有小節公事,只可用言語分付催辦完結,不必出票。如有大事不能結絕,或各樣差使不完,方才出票拘勾。不可泛濫一概出票,致使小民輕易不懼官法。及票俱用縣印一顆”。[12] 諸役多有借牌票詐害百姓者。“差人持糧票下鄉……黑夜排闥,就床擒鎖,舉家驚惶,設酒送饋。及去,衣服雞犬一空。假如欠銀五兩,此番所費二三兩,手頭愈空,錢糧愈難完辦。及帶至縣,該差又與商通,雇人代杖而出。一番追呼,始終皆為差人生意,而官逋如故”。[30](卷二十三,御吏) 有的串通吏書,私寫牌票,不蓋官印,持“白頭”牌票下鄉欺詐百姓。“吏書欺官討錢,每于開征(錢糧)之日,一甲寫一催票,謂之押差,或謂之總催。每一快手一二十兩,賄買戶書寫就。……蓋快手借票催糧,原非為催糧計,不過借印票在手,無端索害鄉人。農民多不識字,又多良善之人,彼即有完票在家,快手欲無端害之,幾十里外向誰分訴。……一張票,乃一快手幾年生活也”。[11](卷五,摘差總差之殊) 牌票是替官府辦差的憑證,可發與差役,也可發給在縣聽差的值年里長,使之勾攝公事。“追會錢糧、軍需、刑名、造作,大小公事,不得差人下鄉,止是遣牌勾辦”。[18](卷下,銷繳信牌) 審案時,縣官還可將牌票交與原告、干證, 令其持票拘傳被告。明初以后里長多在縣“承符呼喚”,聽領錢糧詞狀牌票,回鄉催征錢糧,勾攝人犯,或措辦供應。《海瑞集》上編《興革條例·戶屬》:“舊例里長逐日在縣應卯,違卯則罰。”[31] 袁黃《寶坻政書》卷四《申道報撫臺減糧公移》:“自卑職到任,凡見年里長,皆放歸農。”[32] 說明萬歷十六年袁黃任寶坻知縣前,該縣值年里長須至縣聽差。不但里長,甲首也須隨里長到官聽差,或出“應卯銀”(注:海瑞《海瑞集》上編《禁約》:“一、禁甲首不許與里長戶輪當里長,每一官丁許出銀三分與里長以償應役之勞。仍舊多取應卯銀兩者,甲首不時首告。”) 補貼里長勞費。徐學聚《國朝典匯》卷九十《賦役》:“(嘉靖)四十年正月,御史潘季馴巡按廣東,倡行均平里甲之議。……其里長止于在官勾攝公務,甲首悉放歸農,廣人便之。”[33] 說明廣東在潘季馴改革前甲首須隨里長到官。 縣官有事傳喚鄉民,應盡量差遣里長,以免差役下鄉生事勒索。“凡勾攝公事,不可差皂隸、快手、機兵人等下鄉生事害人,致生不虞,負累不便。止許差各里里長轉令甲首拘與”。[10] “有等在官人役,有因公差下鄉,狐假虎威,虛張聲勢,指官誆詐,擾害良民。明知鄉農少入城市,怕見官府,只得受其凌虐,雞犬為之不寧。有本差一人,有幫二三人者,一至其家,勢如餓虎,不滿其心不休也”。[34](卷下,刑類) 以上所論述的是明代縣衙中比較常見或一般的運作方式,其中一些材料來自明代的官箴書。官箴書作為明代官員初入仕途的為官指南,反映了當時官場行事的慣例。參以其他資料,可以大體了解明代縣衙的實際運作情況。由于明朝疆域遼闊,歷時200余年,各個地區、各個時期的情況會有所變化,其間的差異性及其與縣政的關系,有待于進一步的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