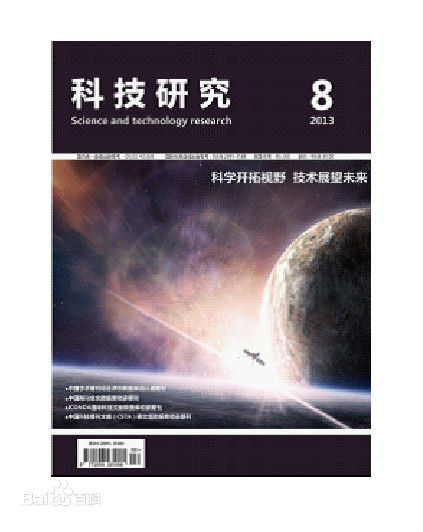明代皇帝崇奉藏傳佛教淺析(之二)
未知
二
明代皇帝為何多崇奉藏傳佛教?我們結合藏傳佛教的教義及修持特點,試作如下分析。 第一,藏傳佛教宣揚“即身成佛”是明代皇帝多崇奉藏傳佛教的重要原因。藏傳佛教形成于10世紀后半期至13世紀的后弘期,有許多教派。盡管他們在傳承與修持方法上有所差別,但“信仰的教義內容則是一致的,都屬于佛教大乘空宗和密宗”(注:丁漢儒、溫華等:《藏傳佛教源流及社會影響》,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26頁。)。大乘空宗(顯宗)的教義,大體上就是佛祖釋迦牟尼的創教學說, 如四圣諦說、因緣說、業力說、無常說、無我說等,與漢傳佛教基本一致。藏傳佛教尤重密宗,密宗是其主要內容和鮮明特色。其教義認為,世界萬物、佛和眾生皆由地、水、火、風、空、識“六大”所造。前“五大”為“色法”,屬胎藏界,“識”為“心法”,屬金剛界。色、心不二,金、胎為一,兩者賅宇宙萬有,而又皆具眾生心中。佛與眾生體性相同,本無差別。眾生根據宗教導師(喇嘛)的秘密傳授,通過設壇、供養、誦咒、灌頂等種種儀式,嚴格依法修行,身結印契(“身密”),口誦真言(“語密”),意觀本尊(“意密”),就能使身、口、意“三業”清凈,受到佛陀“三密”的加持,佛與眾生三密相應,融和無間,此身即可成佛。與顯宗(除禪宗以外)的須經三大阿僧祗劫、修六度萬行始得證佛果相比,密宗的僅修三密妙行即可現生成佛更為簡易快速(注:參閱《佛光大辭典》(新版、電子版),“密宗”、“三密加持”條。)。這也是藏傳佛教吸引民眾信仰、崇奉的重要原因。明代皇帝多皈依、崇信藏僧,接受灌頂,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無不反映他們對藏傳佛教教義的接受,對即身成佛觀念的信持。 第二,藏傳佛教重視儀式巫術,強調男女“雙修”的修行方法,是吸引明代皇帝多崇奉藏傳佛教的另一重要原因。由于記載缺乏,明代居京藏僧所屬的宗派大多不很清楚。不過,重視儀式巫術、強調男女雙修是藏傳佛教密宗各派的共同特點,這對明代最高統治者來說,不僅神秘而且新奇,頗具吸引力。藏傳佛教“本身具有令人畏服的神秘色彩”,通過“侈設儀式,講究修法,演習咒術等”(注:黃玉生等:《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史》,西藏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44頁。),廣作法事,據說可以溝通神佛世界與人間,驅邪避兇。而一些藏僧“熟悉魔術,擅長咒語和誑話”(注:丁漢儒、溫華等:《藏傳佛教源流及社會影響》,第133頁。),作法多著“靈驗”。明太祖請來惺吉堅藏等結壇作法,“廣施濟度”,據說有“天雨寶花”、黑氣聚散開合等異象,“似此者七晝夜,妖氣始滅,不復作矣”(注:《金陵梵剎志》卷一七,釋道果《雞鳴寺施食臺記》。)。明代在宮中舉行的“跳步叱”(藏語稱為跳“恰穆”,蒙語稱為跳“布扎”),就是藏傳佛教的跳神儀式,藏地一般在年終舉行,“表示除去舊歲的鬼崇和不祥,迎接新年,平安如意”(注:弘學:《藏傳佛教》,四川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29頁。)。明代皇帝之所以多崇奉藏傳佛教,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很大程度上因為它們據說能夠溝通神佛世界與人間,驅邪避兇。 另外,藏傳佛教中摻雜有大量的醫占歷算知識,藏僧往往精通醫占歷算,可能也是明朝皇帝崇奉藏傳佛教的不可忽視的原因。如釋迦也失用醫藥和傳授灌頂為成祖治好了重病,為成祖所崇信,就是一個例證。 第三,宮廷中濃厚的藏傳佛教信仰之風也對后朝皇帝崇奉藏傳佛教產生一定影響。如前所述,明代從成祖開始,在宮中設立番經廠,作為準藏傳佛教寺院,宦官接受專門培訓者成百上千,經常舉行藏傳佛教法事。宮中英華殿、隆德殿、欽安殿,也是供奉藏傳佛教佛像、舉行藏傳佛教法事的場所(注:《酌中志》卷一六《內府衙門職掌》。)。再如大善佛殿,“內有金、銀佛像并金、銀函貯佛骨、佛頭、佛牙等物”,世宗評曰“朕思此物,聽之者智曰邪穢,必不欲觀”(注:《明世宗實錄》卷一八七,嘉靖十五年五月乙丑。),可知它們也是藏傳佛教佛像法物。甚至乾清宮梁栱之間也“遍雕佛像,以累百計”(注:王譽昌:《崇禎宮詞》,載《明宮詞》,第81頁。)。從小在宮廷中成長的太子、皇子,耳聞目睹隨處可見的藏傳佛教佛像及頻繁舉行的藏傳佛教法事,不時接觸入宮藏僧,并與為數眾多的受過藏傳佛教法事訓練的宦官朝夕相處,不能不受影響。一旦他們繼位為帝,便會像其父、祖一樣,迅速走上崇奉藏傳佛教的老路。 第四,藏傳佛教提倡喇嘛崇拜、皈依四寶,是明朝皇帝大量封授和供養藏僧、為其建寺造塔等的根本原因。藏傳佛教特別注重師徒傳承,宣揚喇嘛是救度眾生的宗教導師,眾生不依喇嘛的引導,不會知有佛教;不從喇嘛的教誨傳承,不能入佛、成佛;皈依喇嘛,然后才能皈依佛、法、僧三寶。因此,喇嘛“包括了佛、法、僧三寶的全部”,“積聚善根的主要方法,也就是供事喇嘛”。藏傳佛教提倡皈依喇嘛,并對喇嘛僧團也絕對皈依崇拜,“須竭盡一切的財物來供奉喇嘛”(注:釋圣嚴:《西藏佛教史》,第125—129頁。)。明朝皇帝不能不受此影響,因此大量封授和供養藏僧、為其建寺造塔等也就毫不足奇。
三
明朝統治集團中,崇奉藏傳佛教者主要限于皇帝個人,而不像元朝那樣包括皇帝、后妃乃至廷臣等整個蒙古貴族統治階級上層;明朝皇帝不再封授帝師,在京法王等不能凌駕于皇權之上,藏僧在內地沒有干預政治的權力;宮中、京中雖然不斷舉行法事,但規模、次數都大大遜于元朝;明帝雖為藏僧修建寺院等,但數量及耗費錢財也與元朝無法相比;明朝統治者基本上不再對內地藏僧、寺院大量賞賜土地、佃戶等,這與元代也大相徑庭。但是,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的皇帝崇奉藏傳佛教,仍對當時政治、經濟、文化產生不小的影響。 首先看其消極影響。 第一,明代尤其是明代中期的皇帝在京師大量封授藏僧,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崇信藏僧,加劇了明朝政治的黑暗腐朽。 明代中期以后,皇帝多昏庸怠政,宦官間或專權,大臣不斷爭斗攻訐,明朝政治日益黑暗腐朽。而各朝皇帝崇奉藏傳佛教,在京師大量封授藏僧,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崇信藏僧,又大大加劇了這一趨勢。 大量封授藏傳佛教僧人,嚴重破壞了官員的選拔和升用制度,造就了龐大的無關于國計民生的官員隊伍。我們知道,明代選官,主要有科舉、薦舉、學校等幾個途徑。在京藏僧的封授,皆由恩幸得官,與上述幾途無涉,這破壞了正常的官員選拔制度。在京藏僧有法王、西天佛子、灌頂國師、大國師、國師、禪師等名目,其中灌頂國師為二品,大國師為四品,國師為五品,禪師為六品(注:《明宣宗實錄》卷一四、一五,宣德元年二月戊寅、三月庚子。),法王、西天佛子的官品則更高。封建官吏的職責是輔君治民,協助皇帝治理天下。而在京藏僧基本上“與烏斯藏本土關系不大”,“不具政治內容”(注:伊偉先:《明代藏族史研究》,民族出版社2000年版,第217頁。),無補于國計民生。成化年間,即有官員說,“當今號佛子、法王、真人者,無片善寸長可采”(注:《明憲宗實錄》卷七七,成化六年三月辛巳。),“在京番僧既無化導番人之功”,“實濫恩典”(注:《明憲宗實錄》卷二二六,成化十八年四月丙午。)。藏僧的升授,按制由吏部題奏、皇帝批準。但明代中期,皇帝往往直接派宦官傳奉圣旨,封授藏僧等。吏部官員得旨后,“則次日依例于御前補奏”。到成化年間,“僧、道官傳奉寖盛”,吏部尚書尹旻等“無旬日不赴左順門候接傳奉”。最后連傳旨宦官也嫌煩,“諭令勿復補奏,至廢易舊制而不恤云”(注:《明憲宗實錄》卷一五九,成化十二年十一月癸卯。)。大量封授藏僧,“幸門大開”,“濫誤名器”(注:《明孝宗實錄》卷二,成化二十三年九月丁未。)。 明朝皇帝花費大量時間與精力,頻繁舉行藏傳佛教法事,而對上朝聽政、出席經筵日講等卻多持消極態度。如,憲宗“頗留意佛事”,經常召藏僧入內。他迷戀“秘密教”,即房中術,荒淫廢政,“十五六年未嘗與群臣相見”,“上下否隔,朝政日非”(注:趙翼:《陔余叢考》卷一八《有明中葉天子不見群臣》,商務印書館1957年版。)。孝宗日從事于“燒煉齋醮”,“視朝漸晏”,章奏“或稽留數月,或竟不施行,事多壅滯,有妨政體”,經筵進講“每歲不過數日”(注:《明史》卷一八一《徐溥傳》。)。武宗以藏僧自居,時與藏僧混處狎昵,“異言日沃,忠言日遠”,“用舍之顛倒,舉措之乖方,政務之廢弛,豈不宜哉”(注:《明武宗實錄》卷一一七,正德九年十月甲午。),朝政更加黑暗腐朽。 一些藏僧利用皇帝的崇信,橫行恣肆于內地。如,成祖時,有西寧藏僧張答里麻,為僧錄司左覺義,“恩寵日厚”,“遂驕蹇放恣”,甚至“招納逋逃為僧,交通西番,侵奪各寺院山園田地”(注:《明太宗實錄》卷二一○,永樂十七年三月辛酉。)。正統年間,崇國寺楊禪師“視君上如弟子,輕公侯如行童”(注:《明英宗實錄》卷一八三,正統十四年九月戊子。)。憲宗時,藏僧“服食器用僭擬王者,出入乘棕輿,衛卒執金吾杖前導,達官貴人莫敢不避路”(注:《明憲宗實錄》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武宗時,藏僧領占綽節兒、綽供札失回藏,“輜重相屬于道,所過煩費,行道避之,無貴賤,皆稱兩人國師云”(注:《明武宗實錄》卷一二一,正德十年二月戊戌。)。武宗遣藏僧領占、札巴等往西藏封闡化王,他們“科索無厭,州縣驛遞俱被陵轢。至呂梁,群毆管洪主事李瑜瀕死。其縱恣如此”(注:《明武宗實錄》卷一六四,正德十三年七月丙午。)。 第二,明代皇帝大量征召、供養藏僧,頻繁舉辦藏傳佛教法事等,浪費了大量的財力物力,加劇了明代中期以后的財政危機。 明代皇帝在京師供養大量藏僧,為他們提供豐厚的酒肉飯食,是一筆不小的開支。宣德年間,京中藏僧的每日酒食,“俱系光祿寺支待,有日支酒饌一次、三次,又支廩餼者,有但支廩餼者”(注:《明英宗實錄》卷一七,正統元年五月丁丑。)。景帝時,對藏僧“逐日光祿寺酒肉供給,所費頗繁”(注:《明英宗實錄》卷一八六,正統十四年十二月己未。)。成化年間,藏僧札巴堅參、札實巴等“服食器用僭擬王者”(注:《明憲宗實錄》卷五三,成化四年四月庚戌。)。后因官員們要求驅遣藏僧,憲宗下令“供給俱省其半”(注:《明憲宗實錄》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不僅如此,在京藏僧還有相應的人夫供役使。如,正統年間,京師大慈恩等寺分住國師、禪師、喇嘛等三百四十四人,占用會同館夫二百一十三人,以至外國及邊境少數民族使至,會同館“乏人供應,不得已而雇覓市人代之”(注:《明英宗實錄》卷七九,正統六年五月甲寅。)。成化年間,京中供養藏僧達一千二百余人,“光祿寺日供應下程并月米,及隨從館夫、軍校動以千計”(注:《明孝宗實錄》卷四,成化二十三年十月丁卯朔。),以至“廩餼、膳夫供應不足”(注:《明憲宗實錄》卷二六○,成化二十一年正月己丑。)。而武宗為迎取噶瑪噶舉派黑帽系第八世活佛彌覺多吉,耗費物力、人力更是不可勝計。據實錄記載:“(劉允等)以珠琲為幡幢,黃金為供具,賜法王金印、袈裟,及其徒饋賜,以巨萬計,內府黃金為之一匱……又所經略,帶鹽、茶之利,亦數十萬計。允未發,導引相續。已,至臨清,運船為之阻截。入峽江,舟大難進,易以覯艫,相連二百余里。至成都,有司先期除新館,督造旬日而成,日支官廩百石,蔬菜銀亦百兩。錦官驛不足,旁取近城數十驛供之。又給入番物料,估值銀二十萬,鎮巡爭之,減為十三萬。取百工雜造,遍于公署,日夜不休。居歲余,始行,率四川指揮、千戶十人,甲士千人俱西。逾兩月,入其地……番人夜襲之,奪其寶貨、器械以去,軍職死者二人,士卒數百人,傷者半之。”(注:《明武宗實錄》卷一三一,正德十年十一月己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