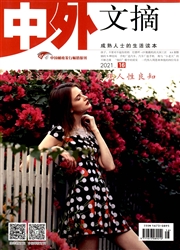論清代前期我國國內市場
佚名
在論明代國內市場的時候,我是從三個方面來觀察流通的和市場性質的變化的:(1)商運路線的增辟和新的商業城鎮的建立;(2) 主要商品的長距離運銷;(3)大商人資本的興起。[1]①清代,則已有可能以鴉片戰爭前國內市場的商品量和商品值作一粗略估計,因此,對(1)(3) 兩項我只在第一節中作簡略概述,對(2)項亦只糧和布兩種主要商品,以省出篇幅,留作量的。
關于本文國內市場的目的和對我國封建各級市場的看法,都已在論明代市場一文中詳述。這里從略。
一 國內市場的擴大
前文曾提過,明代國內市場的開拓主要是在南北貿易方面,尤其是大運河的利用,這是受。清代商運路線有更大的擴展,則基本上是發展的結果了。
清代東西貿易有重大突破,尤其是長江一線。上游(即宜賓至宜昌段)商運主要是清代開拓的,這和四川的移民和開發是分不開的。川江主要支流嘉陵、沱江、岷江都在糧食和棉、糖、鹽產區,匯流而下,集中宜賓、瀘州、重慶。乾隆初,為運云南銅礦,還在宜賓以上疏鑿險灘,開通金沙江船路一千三百余里,瀘州更成商貿重鎮,惜不久淤塞。
長江中游(即宜昌至漢口段)的貿易也是清代才大發展的,這主要是由于洞庭湖流域的開發,長沙成為四大米市之一,而岳陽成為湘江等水的貨運中轉站。同時,由于陜南山區和鄂北丘陵地帶的開發,唐以后陷于停滯的漢水船運重新活躍起來,襄、樊成為商業城市。于是,除糧食為大宗外,川陜的木材、江漢平原的棉花、湘蜀的絲、茶以主南北土產,都匯入長江。
長江上中游商運發展的結果,出現漢口鎮這樣大的商業城市。漢口原一荒洲,屬漢陽縣,明嘉靖時,整個漢陽縣人口不過二萬余,到清乾隆時,單漢口鎮即達十萬,成為華中和東南貿易樞紐,號稱“九省通衢”。不僅長江上中游商貨匯集于此,淮鹽、蘇布、東南洋廣雜貨也在此集散;鴉片戰爭前年貿易額在一億兩左右。[2]①
其余東西方貿易,最有發展的是南方的珠江水系,尤其是西江船運。又東北的黑龍江、松花江,原限于軍船,康熙時始有商船,但隨即出現吉林、失馀、嫩江等商業城市。惟中部淮河船運,仍受黃河干擾,無何進展。
南北貿易方面,清代對大運河的整治遠不如元、明,只是修修補補。康熙時開中河,避去一部分黃河之險,出現清江浦(今淮陰)這樣的商業城市,乾隆后期人口達五十四萬。乾隆末,中河淤廢;道光初,寶應高郵段全淤,大運河的利用就更差了。
長江以南的南北原有兩條干線:一由江西贛江南行,過庾領,經北江到廣州。此路明代即商運繁盛,清代續有發展。尤其福建茶大量出口后,清廷禁海運,均由此路運廣州,沿途船夫、挑夫、客店、小販以十萬計。另一路由湖南湘江南行,過桂林,沿西江到廣州。此路明洪武雖重修靈渠,但是軍事目的。到清代,隨著沿庭湖流域的開發,湘江商貨日繁,始成為重要商路。尤其廣州一口通商后,絲茶在湘潭裝箱南運;洋貨亦先集湘潭,再分運內地。中經南風嶺,人力肩挑,不下十萬人。
清代南北貿易的重要發展,是沿海北洋船線的開通。由上海繞山東半島到天津的北洋船線,辟于元代,但基本上官漕;明代廢海漕,航道幾乎湮滅。清康熙重辟,并由天津延至營口,與遼河聯運。每年沙船運北方豆、麥、棗、梨等到江、浙;運布、茶、糖等南貨去華北、不北,成為南北一大干線。至于南洋沿海航線,與明代無殊。貿易則頗有發展。
到鴉片戰爭前,我國的內河航運路線,大體已具有近代的規模,內河航程在五萬公里以上,沿海航線約一萬公里。事實上,鴉片戰爭后的發展,主要是一部分航程改用輪駁船而已;直到鐵路興建,才發生重要變化。
清代的大商人資本,有進一步發展。徽商、山陜商、海商之外,有粵商、寧紹商、沙船商和經營國際貿易的行商興起。原來販運商人屬于客商,到交易城市須投行。明代大商幫興起,已不盡是客商,而常挈著在交易城市占籍。入清以后,他們就大多在所到城市設立莊號,乃至批零兼營;于是商人會館林立,反映長距離販運貿易的發展。北京、蘇州都有商人會館三、四十處。商人會館按地區分幫,競爭激烈,幫分裂,會館也分裂,同時,又有全行業性的會館出現。嘉慶以后,會館逐漸為工商業公所所代替,公所則大多是全行業性的組織了。到清末,蘇州有公所一百余處,上海有六十余處。
清代的大商人資本,仍以與封建政權關系密切的鹽商最為顯赫,鹽商仍以徽商為主,八個總商中徽商常占其四。但是,如后民說,鹽在清代市場上已是退居第三位的商品了,布、茶、絲等傳統商品都有發展,并逐步擺脫封建勢力;新的品陸續加入市場,并有洋貨和廣雜貨成為一大行業、嘉慶以后,鹽商衰落,行商(廣東十三行)勢力已凌駕鹽商。不琿,行商與另一非商品性的大行業山西票商,其與封建政權的關系也是極其密切的。
前文曾提到,明代大商人的資本組織還限于家族范圍。清代,則已有信貸發展。康熙時,徽商“雖挾資行賈,實非已資,皆稱貸于四方大家,而償其什二、三之息。”[3]①明代大商人資本還是銀五十萬兩級、最高百萬兩水平。清代,則數百萬兩已屬常見,進入千萬兩級。淮鹽商人’辦運者百數十家,有挾資千萬者,最少亦一二百萬。”[4]②“淮商資本之充實進以千萬計,其次亦以數百萬計。”[5]③山西巨商“元氏號稱數千萬兩”[6]④。廣州行商伍怡和的資本有二千六百萬元,其他大的行商亦在千萬兩左右;和坤單當鋪的資本即達二千萬兩。這說明市場積累貨幣資本的能力大大提高了。當然,這時大商人資本的積累還多少帶有封建權力因素,不完人是經濟手段,和坤之流尤其如此。他們的積累,除擴大商業外,也主要是用于購買土地,甚少投資生產。盡管如此,據我們考察,清前期我國資本主義萌芽的發展,仍然主要是依靠商人資本,僅少數是由小生產者分化而來。[7]⑤
二 鴉片戰爭前國內市場的
為探討清代前期市場擴大的程度及其性質,我利用盡可能得到的資料,對鴉片戰爭前(以1840年為基期)市場上主要商品量和商品值作一估計,如表一。事實上,這時我國并無調查,該估計主要是用間接救是,當然很粗糙。但它總可以給我們一個比較全面的印象,反映大致的比例關系,比那種單純概念來論證的方法為好。
表一 鴉片戰爭前主要商品市場估計[8]①
種類|商品量|商品值(銀:萬兩)|比重(%)|商品量占產量(%)
糧食|245.0億斤|16,333.3|42.14|10.5
棉花|255.5萬擔|1,277.5|3.30|26.3
棉布|314,517.7萬匹|9,455.3|24.39|52.8
絲|7.1萬擔|1,202.3|3.10|92.2
絲織品|4.9萬擔|1,455.0|3.75|——
茶|260.5萬擔|3,186.1|8.22|——
鹽|32.2億斤|5,852.9|15.10|——
合計|——|38,762.4|——|——
注:棉布按標準土布計,即每匹重20兩,合3.633平方碼。凈進口棉花60.5萬擔、凈進口棉布(折標準土布)267.3萬匹,未計入。出口絲1.1萬擔、出口茶(折干毛茶)60.5萬擔,包括在內。
表列是只七種商品,已足代表整個市場結構。其余商品,最大宗者為鐵、瓷器、銅。鐵在嘉慶后減產,我們估計年產量在四百萬擔左右,按每擔一兩半計,約合六百萬兩,瓷器,景德鎮當時產量約三十萬擔,按每擔十五兩計,合四百五十萬兩;全國計亦不會高出太多。銅,當時朝野十分重視之滇銅,年產值不過六十萬兩;全國計可能有一百萬兩。其他商品就恐怕不會有超過一百萬兩的了。表一所列,則都是以千萬兩計的。
表一商品值是消費市場價格,一般是批發價,不是生產者所得價格。依表,流通總額年約三億八千七百萬兩,人均近一兩,已經不算小了。
對于這個數值,還應作些調整,才好分析其交換。如前文所說,每年都有相當數量的農產品單向運出,而沒有回頭貨與之交換。造成這種情況的主要因素有三:(1)政府的征課;(2)城居地主引入城鎮的地租;(3)商業、高利貸資本得自農村的利潤和利息。后兩項無法計量。第(1)項即政府征課占最大數量。清代的征課大都已折色,生產者將賦額(農產品)賣給商人運出,而實際并非商品。我們也僅就這一項來進行調整。
清政府的征課,是大項目是田賦,占歲入四分之三以上,鴉片戰爭前實收約三千二百萬兩,棉田、桑田、茶山的地丁在內。此數約合表一糧、棉、絲、茶商品值的百分之十四點六,而地方實征還多些。因將表中四項商品值各減百分之十五,作為調整數。
征課的另一大項是鹽課,鴉片戰爭前已缺額,實收不到五百萬兩。鹽課由鹽商繳納,原屬商品流通稅性質,但鹽場也有課。且鹽為專賣品,表一是按各銷區批價(每斤一分二厘至三分不等),偏高。因無出場價,只好將該項商品值減除五百萬兩,作為調整數。
其他征課如常關稅、海關稅、牙稅、茶課等,均屬商品流通稅性質,不再調整。但應加入進出口因素,以修正流通總額。調整結果見253頁表二。
表二 鴉片戰爭前主要商品流通額(調整)
種類|國產商品流通額(銀:萬兩)|比重(%)|凈進口+凈出口-(銀:萬兩)
糧食|13,883.3|39.71|——
棉花|1,085.9|3.11|+ 302.5
棉布|9,455.3|27.04|+80.2
絲|1,022.0|2.92|-225.2
絲織品|1,455.0|4.16|-已計入絲中
茶|2,708.2|7.75|-1,126.1
鹽|5,352.9|15.31|——
合計|34,962.6|——|——
這些商品之間怎樣流通和交的換,是很復雜的。但從主要流向看,大體是糧農出售糧食,換取布和鹽;而經濟作物區棉、絲、茶等生產者作換取布和鹽外,還要同農換取部分糧食。因此,可凈這些商品分為三大類,其相互交換關系如圖(見下頁)。圖中略去了絲織品、進口棉布和出口部分的絲、茶,因為這些商品是城市消費或出口國外,不參與圖中的流通。這部分的總值,不過占全部流能額的百分之八。
從圖解中可以看出:
第一,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市場交易是在Ⅰ類與Ⅱ類之間進行的。尤其是糧與布,是市場上最大量的兩項商品,市場上最大量的交換也就是糧與布的直接或間接交換。其次是糧與鹽的交換。
第二,布和鹽雖屬品,但實際都是農村生產的。這時的商品布,基本上還是農民家庭生產;鹽民也是農民。因此,絕大部分市場交易,實際是農民小生產者之間的交換,不過是通過商人和地主之手而已(商品糧多來自地主的租谷)。
第三,Ⅰ類的布鹽,若減除城市人口(約占全人口百分之五)的消費,幾乎與Ⅱ平衡了。這說明,商品之銷往城市是很少的(一百八十四萬兩即不足二百萬石),城市用糧主要是由上述農村向城市的單向輸出(超過二千萬石)來解決,這是沒有交換的。Ⅲ類中的絲、茶主要是銷往城市,但也不過二千余萬兩。這就是說,城鄉之間的交換不大。也說明,鴉片戰爭前雖然城市手工業(包括絲織業)已有一定的,但其產品主要是供城市消費,很少與農村進行交換。
第三個特征,構成了鴉片戰爭前我國市場結構的基本模式。它是一種以糧食為基礎、以布 (以及鹽)為主要對象的小生產者之間交換的市場模式。
下面進一步考察一下糧、布這兩項主要商品的流通。
三 糧食和棉布的流通
在上述市場結構中,差不多所有商品都是直接或間接與糧食相交換。因而,在一定意義上,有多少米食可以運出,就成為市場大小的一個界限,也是作物和手能有多大的一個界限。同時,農村出售多少糧食,也直接改變著農民的生活方式。所以糧食商品率又可作為農村經濟解體的一個指標。
然而,如所周知,市場上的糧食一般并不是作為商品來生產的,而是農民已生產出來的東西,由于商人資本的運動而變成商品。商人收購的糧食,又主要不是直接生產者的余糧,而多半是地主出售的,即作為地租形態的糧食。這又是以糧食來觀察市場變化的局限性。
糧食反映商品經濟的發展,不是它在地方小市場上的交易,也主要不是它在區域內市場上的流通,而是指長距離販運貿易。這種貿易,基本上都是與手工業品或經濟作物相交換的。
明代,據作者前文考察,糧食的輸出區主要只有安徽、江西兩省,長距離販運發于長中中下游和福建、廣東,年約一千萬石;除漕米(非商品)外,當時沿毋需南北調。清代情況就有很大不同了。河北、山東已有部分地區缺糧,山西、陜西也缺糧,都非本區域可以調劑。廣東原有余糧,這時則缺糧食嚴重。同時,余糧地區也增多了,尤其是四川、湖南的開發,東北的放墾,的經營,都成為糧食基地。因而,調運頻繁,路程也加長,由北而南,總計有十條主要路線:
(1)米麥經大運河北運京畿、山西、陜西。南方六省漕糧,實際多在江蘇采辦,連同河南、山東賦額及耗羨,年在五百萬石以上。官漕私帶和商人販運的,也是“由江淮溯〔運〕河而北,聚集豫省河南、懷慶二府。由懷慶之清化鎮進太行山口,運入山西。由河南府之三門砥柱運入潼關”①,供應陜西。官商兩項,總計由大運河北運者,為估為六百萬石。
(2)奉天麥豆海運天津、山東。奉天是清代開拓的糧食產區,其麥豆運往天津,始于乾隆初,“以前不過十數艘,漸增至今,已數百艘”[9]①。這種海船每艘能裝五百——一千石,共約數十萬石。運山東者接濟東部缺糧區,乾隆十三年,除領票商人“照數裝運外,尚有余糧二十萬石”,亦令裝去[10]②。故兩地共可估為一百萬石。
(3)奉天豆麥海運上海。這是清代新興的一項大宗貿易,即北洋航線的沙船貿易。據包世臣說:“自康熙二十四年開海禁,關東豆麥每年至上海者千余萬石。”[11]③又謝占壬說:“凡北方所產糧豆棗梨運來江浙,每年不下一千萬石。”[12]④是單就糧食說,恐不足一千萬石。但關東系用大石,謝占壬說:“海關〔東〕石計倉斛二石一斗有零”[13]⑤;或謂“關斛一石,合蘇斛二石四斗二升。”[14]⑥我們按糧食一千萬江南通用石計,不會是高估的。
(4)河南、天津麥梁運山東臨清。臨清州“地產麥谷不敷用,猶取資于商販,從衛河泛舟東下者豫省為多;秫梁則自天津溯流而至。”[15]⑦其數未詳。這里缺糧,主要由于是舟車輻輳的通商碼頭與山東東部之由于經濟作物發展不同,大約數十萬石已足。
(5)漢口麥谷經漢水運陜西。這大約是湖北德安、襄陽、安陸一帶麥產區的余糧,據說雍正十一年有糧船一千五百只[16]⑧。此種河船載重三百至五百石,估計共約六十萬石。
(6)安徽、江西米運江蘇、浙江。江浙是缺糧最多的省份。江蘇的太倉、松江、通州、海門等府廳缺米,是由于棉田金于稻田。蘇州府九縣原是稻的高產區,年產米達二千二百萬石,但因工商業發達,外省“客米來售者歲不下數百萬石”[17]①。浙江西南部溫州、處州,所產米“不足供本地食米之半”[18]②。北部杭、嘉、湖原是高產區,但因桑蠶發達,“每歲產米不敷數月口糧”[19]③。故這兩者缺米有重要經濟意義。明代,即由安徽北部、江西南部的余糧接濟,略加湖北米,已足補缺。清代,則運有未足,要依靠上述之關東麥豆和下述之湖南、四川米大量濟運了。安徽、江西人有余糧,并形成蕪湖、九江兩大米市,惟其運江、浙數未見記載;只好參酌明代情況,估為五百萬石左右。
(1)湖南、四川米經長江運江蘇。湖南、四川都是清代新發展的糧食基地。湖南米產區主要在洞庭湖流域,筑堤墾田尤多商品糧,其米集中漢口,再東運。全漢升先生根據雍正十二年湖廣總督邁柱所奏情況,估算該年自湖廣運江浙的食米為一千萬石[20]④。其數應指湖南米,因湖北清代主要發展是北部麥產區,漢陽、黃州一帶余米因漢口鎮的消費,輸出條件反不如明代。乾隆以后,論者常言湖南米谷緊張,蓋因當時糧價陡漲,地方官有要求多儲本省之意。實際運出數量,比雍正時當有增無減;包世臣曾說漢口存糧多至二千萬石[21]⑤,或許夸張,到近代,湖南輸出米年尚有四百萬石。至于四川,產米頗豐,或謂居各省之冠[22][22]⑥;但運出數量無考。不過,四川米都是在漢口落岸,所謂“江浙糧米歷來仰給于湖廣,湖廣又仰給于四川”[23]⑦。所以上述一千萬石數字,已包括四川米在內。這些米多是運到蘇州楓橋,再由各地商人運銷浙江、福建。
(2)江浙米由上海運福建。福建是經濟作物和手工業發達較早的地區,在考察明代市場時,我曾說它是唯一出現自然經濟解體的省份。其缺糧主要在泉州、漳州兩府,明代曾由廣東大量接濟;到清代,廣東自顧不遑,就主要依靠江浙和臺灣米濟運了。惟江浙米運福建多少,無考[24]①,我們并入下項總算。
(3)臺灣米海道運福建。福建所需米,恐怕更多仰仗臺灣。臺灣“一年豐收,足供四五年之用”,雍正初令每年濟閩八萬三千石[25]②,這屬官運;實際輸福建者,每年約有四、五十萬石[26]③。雍正后無記載。至近代,福建年約缺米二百萬石。參照人口,估計嘉道時浙江和臺灣米運銷福建者,不會少于二百萬石。
(4)廣西米經西江運廣東。清代廣東商品經濟發展甚速,成為嚴重缺糧省份。其米主要來自廣西。雍正時有人說,廣東“即豐收而乞糴于〔廣〕西省者猶不下一二百萬石”[27]④,似有夸大。但也可能能包括湖南運來之米,因湖南經湘江到廣東的干線即過廣西桂江。另一南北干線是由江西贛江到廣東,江西也是米輸出地,但只“運去米谷甚多”[28]⑤,不詳數量。乾隆后,廣東尚有進口洋米,但為量不多。總看廣東由廣西、湖南、江西運進之米,每年大約有二百萬石也就夠了。
總計以上十路,年約三千六百萬石,除去漕糧,亦在三千萬石以上,與明代的長距離運銷比,已三倍之。
但是,在糧食的總商品量中,長距離運銷所占比重仍屬有限。以三千萬石計,合四十五億斤,占表二調整后商品糧(二百零八億二千五百萬斤)的百分之二十一點六,這還未包括墟集貿易的調劑。并且,這種長距離運銷,并不都是為了與手工業品或經濟作物相交換。例如,由于北方缺糧,南非要南糧北調,但北方甚少工藝品供應南方,以致糧船回空。由于東南缺糧,東北有大批豆麥海運上海,而回頭貨即東南的布、茶、糖等,卻常不滿載,需以泥壓艙。川、湘每年有大量糧米接濟江、浙,后者以鹽、布、廣雜貨等作為補償。但這些工業品在長江上游并無多大市場,后來川、湘來米少了,淮鹽也滯銷。就是說,這種長距離運銷,主要是由于某些地的缺糧引起的,而不是因手工業擴大商品生產引起的。這就反映了當時市場的狹隘性。
再看棉布的流通。糧食雖然重要,但在市場上起主導作用的不是糧食,而是工業品。正因工業(這時是手工業)一個個從農業中分離出來,市場商品量才能擺脫自然條件的限制,無限擴大。工業的部門的結構,決定市場的結構;工業的布局,決定商品的流向。貨幣資本的積累,也主要是靠工業品的貿易,明清以來的大商人資本如徽商、西商、粵商等,都是靠鹽、茶、布、絲等起家,沒有經營糧食起家的。有多少工業品流通,是衡量市場最重要的量度。
在明代以前,大約市場上陽大量值的工業品是鹽,其次是絲織、鐵器等。到清代,棉布代鹽在市場上占主導地位,這是一個進步。因為鹽的產銷,僅決定于人口數量;布,則與經濟的發展密切相關。
這時,布還是農民家庭生產的,所謂“男耕女織”。但并非家家織布,據《江南土布史》編寫組調查,大約織布戶最多時(1860年左右),也不過占全國總農戶的百分之四十五,鴉片戰爭前,有些地區還是基本上不織布的。所以,布的商品率是很高的,經常占產量的一半左右(表一)。但是,市場上的商品布,絕大部分是農家自用有余的布,只有在棉布的集中產區,才有為市場而生產的織戶,也只有這種商品布,才有一定的規格品種,才能進入長距離運銷。
在明代,還只有一個這樣的棉布集中產區,即江蘇省的松江一帶,主要品種是標布和棱布(后稱稀布),進入長距離運銷的,年約一千五百——二千萬匹。(另如福建的北鎮布、湖北的咸寧布,也有遠銷,但為數甚小。)到清代,這個產區擴大了,包括松江布、常熟布、無錫布,統稱蘇松產區。另外,在北方和華中雙出現幾個小的集中產區。布的長距離運銷增多了,總括起來,也有十路:
(1)松江布。北銷東北及河北,南銷福建、廣東并出口南洋。有人說:“松之為郡,售布于秋,日十五萬焉。”[29]①據《江南土布史》考證,十五萬匹超過該地區織機設備能力,近代調查,大約最多日十萬匹。秋,布旺季,一百八十日,得一千八百萬匹,全年最多三千萬匹。
(2)常熟布。“常、昭〔文〕兩邑,歲產布匹,計值五百萬貫。通商販鬻,北至淮、揚,及于山東;南至浙江,及于福建。”[30]②此時(道光二十年左右)銀價每兩約一千五百文,五百萬貫合銀三百三十余萬兩,布價每匹銀三錢,合一千余萬匹。
(3)無錫布。“坐賈收之,捆載而貿于淮、揚、高〔郵〕、寶〔應〕等處。一歲交易,不下數十百萬。”[31]③所稱數十百萬,似亦指銀兩,以百萬計,約有三百萬匹。此外還有太倉、嘉定一帶和浙江嘉興,都屬蘇松布產區,惟量未詳。蘇州為染布中心,胚布主要來自松江、常熟,信少量自織;主銷北方,并銷漢口。總計蘇松地區年產布約四千五百萬匹,其進入長距離運銷的總也有四千萬匹。
(4)直隸灤州、樂亭布。灤州布,“用于居人者十之二三,運于他鄉者十之七八”[32]①。樂亭“地近邊關,邑之經商者多出口貿易”,“布則樂為聚藪,本地所需一二,而運出他鄉者八九”[33]②。是該產區布主銷關外,惟數不詳。
(5)直隸元氏、南宮布。元氏“郡近秦壟,地既宜棉,男女多事織作,晉賈集焉”[34]③。南宮,清初有“湖廣商黃姓,以數千金市布”[35]④。又較晚記載:“其輸出,西自順德以達澤潞,東自魯南以達徐州”;縣有建成村,所產布“西達太原,北至張家口,而郝家屯布店尤多,自古北口輸出內外蒙古”[36]⑤。其布是以銷西北為主。
(6)山東歷城、齊東、蒲臺布。歷城布“有平機、闊布、小布三種”,“平機棉線所織,人所常服。小布較闊布稍短,邊塞所市。闊布較平機稍粗而寬,解京戌所需。”[37]⑥齊東,“民皆抱布以期準集市場,月凡五六至焉,交易而退,謂之布市。通于關東,終歲且數十萬計”[38]⑦。蒲臺“布有數種,……商販轉售,南赴沂水,北往關東”[39]⑧,說明這一帶的布也是大量銷往東北。僅知齊東是數十萬匹。
(7)河南孟縣布。“孟布馳名,自陜甘以至邊墻一帶,遠商云集”[40]⑨。銷于西北。
(8)河南正陽布。這是豫南布,又名陡布,產陡溝店者最出名,“商賈至者每挾數千金。……東達潁毫,西達山陜”[41]①。也銷西北。
(9)湖北布。產布在中部漢陽、孝感、應城一帶。漢陽布,“四方來貿者,輒盈千累百”[42]②;較晚記載云:“遠者秦、晉、滇、黔賈人爭市焉”[43]③。孝感布,“西賈所收也”[44]④。應城布,“行北路者曰山莊,行南路者名水莊”[45]⑤。又云夢,“凡西客來楚貨布,必經云城捆載出疆,……故西商于云立店號數十處” [46]⑥。大約這個布產區,行銷西北者以云夢為集中地,捆載北去,行銷西南者以漢陽為中心,溯江而上。又湖北南端的監利,產布也銷西南,“蜀客貰布者相接踵”[47]⑦,后擴大銷區,“西走蜀黔,南走百粵,厥利甚饒。”[48]⑧
(10)湖南布。湖南布產區在巴陵,質較粗糙,稱都布。“吳客在長沙、湘潭、益陽者,來鹿角市之。……歲會錢可二十萬緡”[49]⑨。鹿角在巴陵南沿庭湖畔,吳客所販似沿湘江運廣西。二十萬緡,當有四十——五十萬匹。
此外,山西榆次、四川新津等也有布外銷。二省皆缺布,外銷恐少。
以上十路,除蘇松四千萬匹外,多無數據。直隸東西二區,山東沿黃河三地,河南南北二區,大體均可估一百萬匹,湖北當亦不下一百萬匹。這樣,進入長距離運銷的布共約四千五百萬匹。與明代比,約增加一倍半。
然而,四千五百萬匹只占表一布的商品量的百分之十四點三。就是說,到清代,布雖已是占第二位的商品,也已有了全國性市場和出口,但長距離運銷還是很有限的,布的市場還是狹隘的。
還不在此。如前所述,商品布絕大部分是農家自用有余的布,拿來和不織布換取口糧。這是屬于自然經濟中有無調劑的性質,實示是小農業和家庭手工業結構的另一種形式,難說是商品經濟。即使在集中產區,為市場而生產的織戶,也還未從農業中分離出來,他們也是為買而賣,以換取糧食、日用品,或繳租還債。即在蘇松地區,織戶亦是“僅足糊口”,“賴此營生”。靠織布發家致富者,尚屬罕見。所以,盡管有了較大市場,并未能促進生產關系的改變。
但是,布的運銷,對棉布加工業即染坊業和踹坊業,卻有作用。青藍布幾乎是蘇、松二地壟斷,這兩地的染坊、踹坊,也都有了資本主義萌芽。
表一中其他商品,都有長距離運銷。到清中葉,茶市場迅速擴大,并大量出口;絲和絲織品也比明代有所發展;棉則不超過明代規模;鹽因人口劇增而增加。又清代經濟作物有較大發展,農產品加工也漸繁盛,煙、豆油、豆餅可視為新商品,均有遠銷。手工業范圍擴大,陶瓷、糖、紙遠銷俱增,鐵器形成廣闊市場。礦產品中,煤為新興商品,山東博山煤沿運河北上,竟行銷甚遠。
四 簡短的結論
從以上考察可見,由明到清,國內市場顯著擴大了,市場結構也力量也略有變化。這表現在:
(1)商運路線增長,水運已具近代規模;商業城鎮增多,并有漢口、廣州等大埠及若干大米市同現;大商人資本量增大,由五十萬兩級增至百萬兩級以至千萬兩。
(2)長距離販運貿易品種增多,貿易量增大,以糧、布而論約為明代的二、三倍;經營逐漸專業化,并開辟東北、西南市場。
(3)布代替鹽,成為市場上占主導地位的品,市場上工業品總值超過農產品。整個市場已是以小生產者之間的交換為主,傳統的勞動產品與封建收入(地租轉化形態)的交易已退居不重要地位了。
這些變化反映真正的商品的,它的作用是不容否定的。據我們考察,到鴉片戰爭前,已在二十個手工行業中有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的萌芽稀疏地出現,它們的產品,差不多都有長距離運銷;農業方面,也已見資本主義經營的端倪,主要是在經濟作物中。
但應看到,直到鴉片戰爭前,我國國內市場,還是一種以糧食為基礎、以布(以及鹽)為主要對象的小生產者之間交換的市場結構。在這種市場模式中:
(1)主要商品,即糧和布,還都是農民家庭生產的,并且,糧基本上沒有商品生產,布也主要是農家自用有余的布;
(2)糧和布的長距離運銷在它們的商品量中只占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比重,而絕大部分仍是區域內的和地方小市場的交換;
(3)這也就使得農民保持著耕織結合,使基本上仍處于經濟狀態。
(4)還應看到,作為第一位商品的糧食,它的長距離運銷,主要是由于若干地區嚴重缺糧所引起的,主要不是由于手工業和經濟作物區擴大商品生產所推動的。
這就造成了市場的狹隘性和長距離貿易的局限性。這種市場狹隘性和局限性,又是資本主義生產關系發展遲緩的原因之一。
這里再對農村市場補充幾句。前文在對明代市場的考察中,曾對一些新興的絲織業(以及鐵器業)村市給予高度重視。清代販運貿易的發展,曾使某些地方的墟集專業化,出現絲墟、布市、豬市、葉(桑)市等名稱,以米谷稱者尤多,反映地方小市場向初級市場過渡。但以手工業馳名的鎮市,記載并不甚多。清代農村市場雖有變化,但僅限于少數地方。一般仍是“蔬粟布帛雞豚酒果之屬,……趁墟貿易”[50]①;或“非定期不集,非集不得貿易,且花布雞豚糧草果蔬之外,無他奇貨。”[51]②廣大農村,基本上仍是自然經濟;農民出賣糧食,部分是稅債所迫,所謂“江南民俗,每因納糧而糶”[52]③。因賦稅普遍征銀,有的地方已超過市場發展程度,“窮民小戶有谷帛而無售主,有雞豚而待市販”[53]④。在估計清代市場的擴大時,這種情況亦應考慮在內。近年來國外常有人申論,清代農村已是市場經濟,看來非是。
注釋:
[1]① 見本書《論明代國內市場和商人資本》。
[2]① 范植清:《鴉片戰爭前漢口鎮商業資本的》,《中南民族學院學報》1992年第2期。
[3]① 康熙《徽州府志》卷八,蠲賑。
[4]② 王贈芳:《謹陳補救淮鹽積弊疏》,《經世文續編》卷五十一。
[5]③ 李澄:《淮鹺備要》卷七。
[6]④ 徐珂:《清稗類鈔》。
[7]⑤ 參看本書《資本主義的萌芽導論》。
[8]① 此表的估計比較復雜,將專文載入即將出版的《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史》第一卷第四章(中國所編),這里僅作簡介。
糧食:產量依傳統辦法按四億人口計,人均占有量五百八十斤。商品量:非農業人口二千萬人,人均五百斤;經濟作物專業區五千萬人,人均二百五十斤;釀造、上漿用糧二十億斤。價格主要據《漏網喁魚集》及《一斑錄》,并按“米一谷二”折原糧,每石一兩。
棉花及棉布:產量采用徐新吾同志及《江南土布史》估計,是參照近代產棉量,調查人均棉布和絮棉消費量,調查紡織戶比重,自給部分與商品部分,再用進出口記錄修正。棉價,主要據《一斑錄》,評為每擔五兩。布價,主要據海關及英商記載,評為每匹三錢。
絲、絲織品和茶:產量據徐新吾同志及《江南絲織史》、《上海華商國際貿易業史》的估計。絲是根據江南織戶、織機估算紡織用絲,根據廣州出口記錄估算外銷絲,產量即銷量。價格是以出口絲價每關擔三百五十元為基數,內銷絲評為每關擔二百四十五元,綢緞價評為每關擔五百元。茶按人均消費量半斤計(比傳統估計為低),出口按廣州及鋨國記錄,銷量即產量。價格以上海出口價為基數(廣州太高),每擔二十兩七錢,內銷價評為十兩三錢。
鹽:官鹽采用簡銳同志的估計,系根據十一個產區戶部額定引數,按不同配鹽數計算銷量,銷量即產量。價格按各銷鹽區發售價,均據各區《鹽法志》。私鹽產量按四川、兩淮情況,估為官鹽的三分之一,價格為官鹽平均價的三分之二。
這幾項估計總商品值為三億八千七百萬兩,比過去有人按厘金推算數(不到一億兩)大得多,比最近美國珀金斯氏按海關土產轉口統計推算(六——七億兩)又小。厘金、海關統計均為一八七0年或一八八0年以后之事。
《江南土布史》、《江南絲織工業史》、《上海華商國際貿易業史》均為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將陸續出版。
[8]① 朱軾:《軺車雜錄》下,康熙六十年序。
[9]① 同治《續天津縣志》卷六。
[10]② 《高宗實錄》卷三三九,乾隆十四年四月乙未。
[11]③ 《海運南漕議》,《安吳四種》卷一。
[12]④ 《古今海運異宜》,《皇朝經世文編》卷四十八。
[13]⑤ 《水腳匯籌》,《皇朝經世文編》卷四十八。
[14]⑥ 齊學裘:《見聞續筆》卷三。
[15]⑦ 乾隆《監清直隸州志》卷二,市衢。
[16]⑧ 引自D. H. Perkins,Agricul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1969年,第148頁,稱系據湖廣總督報告。
[17]① 高晉:《清海疆禾棉兼種疏》,《皇朝經世文編》卷三十七。
[18]② 清《高宗實錄》卷三一四,乾隆十三年五月乙酉上諭。
[19]③ 清《高宗實錄》卷八十二,乾隆三年十二月丙戍戶部議。
[20]④ 全漢升:《中國經濟史論叢》第二冊,1972年版,第573頁。
[21]⑤ 《籌楚邊對》,《安吳四種》卷三十四。
[22]⑥ “臣查各省米谷,惟四川所出最多,湖廣、江西次之。”《石朱批諭旨》,雍下地五年十二月初三日浙江總督李衛奏。
[23]⑦ 《石朱批諭旨》,雍正二年八月二十日四川巡撫王景灝奏。又稱:“秋收之后,每日過夔[州]關大小米般或十余只不等,源源下楚。”
[24]① 雍正五年春起,有福建官員來蘇州辦米二次,商人販米六次,到四月十一日“閩省已搬運三萬石”(《石朱批諭旨》,雍正五年四月十一日蘇州巡撫陳時夏奏)。以比,全年不過十余萬石,恐怕太少了”
[25]② 《石朱批諭旨》,雍正四年七月二十六日閩浙總督高其倬奏。
[26]③ 連璜:《通史》上冊,頁四十四,引雍正七年詔書。
[27]④ 《石朱批諭旨》,雍正八年四月二十日閩廣總督鄂爾泰奏。
[28]⑤ 《石朱批諭旨》,雍正四年六月初四日江西巡撫裴率度奏。
[29]① 欽善:《松問》,《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十八。
[30]② 鄭光祖:《一斑錄·雜述》卷七。
[31]③ 黃印:《錫金識小錄》卷一。
[32]① 嘉慶《灤州縣志》卷一。
[33]② 乾隆《樂亭縣志》卷五。
[34]③ 光緒《元氏縣志》卷一,引乾隆《正定府志》。
[35]④ 道光《南宮縣志》卷十。
[36]⑤ 民國《南宮縣志》卷三。
[37]⑥ 乾隆《歷城縣志》卷五。
[38]⑦ 嘉慶《齊東縣志續》。
[39]⑧ 乾隆《曹州府志》卷七。
[40]⑨ 乾隆《孟縣志》卷四。
[41]① 嘉慶《正陽縣志》卷九。
[42]② 乾隆《漢陽府志》卷二十八。
[43]③ 同治《續輯漢陽縣志》卷九。
[44]④ 光緒《孝感縣志》卷五,引順治舊志。
[45]⑤ 光緒《應城縣志》卷一,引康熙舊志。
[46]⑥ 道光《云夢縣志》卷一。
[47]⑦ 光緒《荊州府志》卷六,引乾隆舊志。
[48]⑧ 同治《監利縣志》卷八。
[49]⑨ 吳敏樹:《巴陵土產說》,《樣湖文集》。
[50]① 乾隆《東安縣志》卷一。
[51]② 乾隆《齊河縣志》卷二。
[52]③ 《乾隆諭折》抄本,乾隆七年九月漕運總督顧忱奏。
[53]④ 趙廷臣:《請定催征之法疏》,《皇朝經世文編》卷二十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