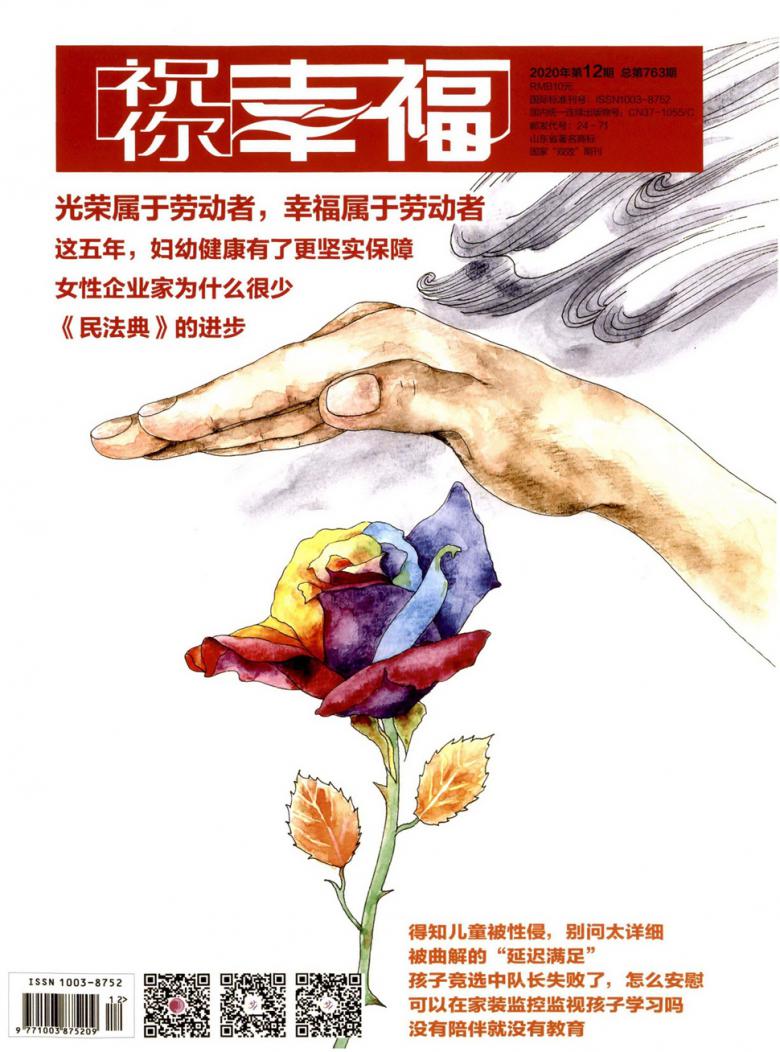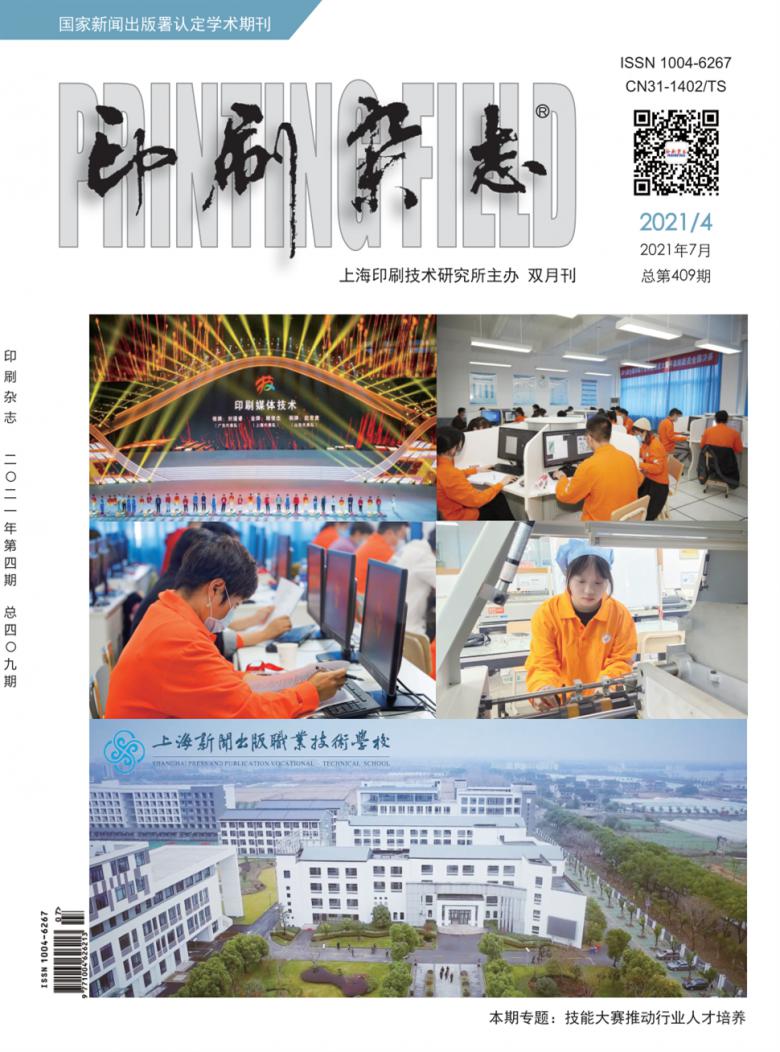民國前期內地城市工人生活研究——以成都為例
未知
【內容提要】工人階層是民國時期城市社會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成都作為內陸城市,其工業與社會發展都呈現出了與其時工業較為發達的沿海、沿江城市迥然不同的風貌,從而使得工人生活也具有了鮮明的內陸城市特征。
【摘 要 題】現代史專論
【關 鍵 詞】成都/工人生活/民國前期
【正 文】 民國以來,隨著社會經濟的變遷,城市社會結構發生了相應地變化,新的社會力量開始出現。工人群體開始崛起并逐步發展壯大正是這一時代的產物。對工人這一近代城市中的重要社會階層的相關研究已有很多,然多集中于近代工業較為發達之地區,對近代工業發展相對落后和緩慢的內陸地區則涉及較少。成都作為重要的內陸中心城市,民國以降,其城市社會經濟的發展和社會階層的變遷亦自有其特色。本文即欲對抗戰前成都工人群體的生活狀況作一個初步考察,以期能從一個側面反映出其時廣大內地城市中工人們的生活狀況及其對城市現代化進程所產生的影響。
一、抗戰前成都工業發展與工人構成
成都的現代工業雖然從晚清時期就已經開始起步,但成都因遠離技術源、資金源和人才源,又非工業原料生產地,興辦工業難度較沿海城市為大;由于受到資金、技術、市場以及社會環境等因素的制約,成都的工業發展非常緩慢。而從民國初年到30年代中期,四川戰亂頻繁,更是嚴重影響到成都工業的發展,故在此20余年間,成都的現代工廠寥若晨星,到30年代中期亦不過70余家,而真正有一定規模者僅17家。據統計,成都市17家規模較大的工廠共有職工1864人,僅占全市人口的0.41%,占第二產業人數的3.18%,第二產業從業人員的90%以上是手工業者[1]。由此可見,直至20世紀30年代中期,成都工業仍集中于規模小、技術落后的傳統手工業,現代機器工業十分稀少。手工業占絕對優勢乃是其時成都城市產業結構的一大特色。基于上述因素,本文中所述之“工人”并非僅限于現代機器大生產條件下的產業工人,而是一個包括產業工人、傳統手工業者、傭工乃至苦力等在內的廣泛的工人群體。這可能也更為符合時人對“工人”的界定。在1936年進行的一項成都各業工人統計中,統計者即將其按職業工會分為了七大類,即:機械工人、手工業工人、交通工人、運輸工人、制造工人、傭工工人和雜業工人[2]。而他們皆為本文的研究對象。根據1934年的一項調查顯示,其時成都市共有工人205954人[3]。而當年成都市人口總數為440859人[4]。這樣,其時成都市工人就占了全市總人口的46.72%,如果除去失業人口和非勞動人口,工人在成都市的勞動人口中所占比例就更為可觀。因此,對工人階層的生活狀況進行考察,或許可以一窺其時成都城市社會中最廣大人民的生存狀況。
二、工人的工作狀況與收入
其時成都各業工人主要來源于農村破產農民和城市貧民。前者多從事苦力,如人力車夫、運輸工、傭工等,后者則多分布于手工各業。抗戰前的四川,由于拉丁派款,天災人禍所造成了農村經濟的破產,而城市則因其擁有的較多的從業機會而吸引了大量破產農民的涌入。據1936年中央農業實驗所所作的調查可知,在全川64縣中,有154837戶農民離鄉遷移,占總農戶的6%。其中,遷往城市(包括逃難、做工和住家)的農民占全部遷移戶的61.1%[5]。作為省會城市的成都自是首當其沖。從1939年所進行的成都市牙刷業工人調查中可以看到,在141名職工和學徒中,其籍貫為成都的僅有38人,占總人數的26.95%,其余人員則來自省內其它地區[6]。此外,在1935年所進行的一次成都市人力車夫生活調查中的309人中更只有23人的籍貫為成都,其余均為省內其他市縣[7]。以上兩例或可以從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成都對于省內各地勞動者所具有的吸引力。另一方面,由于其時成都城市工商業發展較為緩慢而使得它對勞動人口的消化和容納能力有限,出現了大量過剩的勞動人口。這樣,無論是由農村來的破產農民,還是原來的城市居民,廣大的工人群體為了生存,不得不接受低廉的工資待遇而從事各種繁重的工作,以求溫飽,并隨時面臨著失業的危機。 1931年成都市各業工人工作時間與工資一覽表 業別 每日工作時間 平均月得工資 業別 每日工作時間 平均月得工資 (小時)(元)(小時) (元) 兵工廠1020 造幣廠 1110 機械廠1114 棉織業 11 7 綢緞長機 11 7 生縐業 10 6 綾紗業10 7 紡織業 12 4 成衣業10 7 理發業 10 7 金銀飾1012 服裝 1010 茗工 10 5 泥工 10 6 木工 10 6 雕工 10 7 油漆 10 7 懈工 10 6 石工 10 6 廚工 10 7 屠案 10 7 錫工 1010 牛骨業10 5 飯店業 11 7 面食業12 6 筆業 11 7 印刷 1114 色染業 1010 治銅業11 6 絲煙業 10 8 制帽業10 8 制革業 10 8 靴鞋業1010 制花業 10 6 鐵貨業10 5 紙柴業 10 6 錢紙業10 6 刀剪業 10 6 機關雜役 11 7 平均 10小時30分弱 8元弱 (資料來源:《苦矣成都市的工人》,《社會導報》第1卷第6期,第25-28頁,1931年6月15日。) 從上表中可以看到,工人們的工作時間長達10小時,甚而長至12小時,其平均工作時間為10小時30分,其勞動時間之長,工作之艱辛可見一斑。而工人們如此辛勤地工作所換來的工資待遇卻是十分低下的。上表中也有統計,工人們的平均工資尚不及8元。而1931年成都市食米的平均價格維持在每石30元左右,由此可見工人工資水平之低微[8]。雖然工人們多由資方供給膳食,或許亦為工資的一部分。而從當時的印刷業調查中可知,“伙食普通多每日兩頓,三頓者,僅有一二家”,由此可見,此部分回報實為有限[9]。而根據1929年上海市社會局對全市21個行業中285700名工人工資的調查,其中男工平均月工資為17.52元[10]。又如1930年國民政府工商部對全國29個城市工資調查,男工每月平均工資為15.43元[11]。可見成都工人的工資水平不僅遠低于上海等發達地區,甚而還低于全國各城市的平均水平。雖然成都地處素有天府之國之譽的四川,物價水平較低,然1932年間,一名成都平民“每日生活費,亦在三角以上”[12],以一家四口計,以成都工人的工資水平,單憑其一人之力顯然是難以養家糊口的,因此,普通工人家庭不得不依靠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職業人口的收入來勉強維持,同時,由于收入的低下,一般普通工人家庭往往不得不讓未成年的子女去當童工、報童、小販,甚而從事苦力勞動。在1939年所進行的成都市牙刷業工人調查中,年齡在14歲以下者占了總人數的52.48%[13]。這主要是因為包括工人家庭在內的廣大下層勞動者家庭出于生計的需要而不得不把年幼的子女送去當學徒。而1932年的成都《平報》更曾報道稱市內各人力車公司多招用幼童出外拉車,最小者只有10歲,故市政府特訓令工務局,嚴禁15歲以下之幼童拉車,違者則會追究各公司,以維人道云[14]。工人階層生活之艱辛躍然紙上。 此外,工人們還要面臨著失業的威脅。如據成都《新新新聞》1935年的記載,當年入春以來,成都商業極其疲滯,手工業多緊縮范圍減少雇工,工人失業者甚多。棉織與絲織兩業失業工人已達五千人以上,縫紉業失業亦不下四五百人,其他如染房街之骨貨工人,東御街之銅貨工人,亦多無工作可作,鐵路公司三倒拐鞋鋪,全街鋪戶一百余家除學徒外,雇用工人不及十人,由此可見一斑,其他行業工人失業者更不知若干[15]。由于其時成都工商業發展的不景氣,商號、工廠之裁員與倒閉時有所聞,工人們亦自是朝不保夕,時時面臨失業的危機了。
三、工人家庭生活
工人們的家庭生活也相當困苦。如前所述,工人收入的低下決定了他們的家庭規模不會過大,且生活是極其貧困的,其家庭的消費水平也是極低的,“他們的工作不外乎求溫飽而已”[16]。 家庭規模通常指家庭人口的容量。據1928年內政部的調查,21個主要城市的平均戶規模為5.14人[17]。另一方面,“經濟收入狀況是決定家庭結構和人口多少的一個主要因素”,收入相對低下的工人等城市社會階層的家庭規模也就相應較小[18]。據近代社會學者的調查,中國幾個主要都市中貧民家庭的平均人口都在4-5人之間(注:根據《成都市牙刷工業與工人生活概況調查》中對其時北平、上海、天津、南京等都市中貧民家庭的相關統計可知。)。成都工人家庭規模也大致如此。 1934年成都市勞動負販界之人口數目與家庭大小表 業別 小貿 車夫 棉織 長機 成衣 理發 木工 泥工 金工 飯食 茶工 平均 平均每家人口 4.5 3.1 7.6 7.2 4.7 5.1 3.6 3.3 8.1 6.6 3.2 5.18 平均每家成年 3.5 2.45 6.46 5.83 3.66 4.26 2.82 2.63 6.20 5.37 2.52 4.15 男子單位數目 (資料來源:楊蔚:《成都市生活費之研究》,第8頁,第1表,金陵大學農學院出版研究叢刊第五號[19]。) 上表或可對我們了解其時成都各工人家庭規模大小提供一定幫助。不過,由于上表中家庭人口統計,除親族外,尚包括雇工在內,而棉紡、長機等手工業作坊中多雇傭工人,故其數據所反映并非完全為平常意義上之家庭,而諸如小貿、車夫者因無需雇傭工人,故被統計的家庭人口應多為一般意義上之家庭成員。綜合多方面的考察,我們可以推測其時成都工人家庭規模以4人左右者居多。而其時成都商賈店主界和軍政教育界的家庭規模則分別為6.52人和6.47人,皆高于工人家庭。同時,上表中還反映出其時成都工人家庭中成年男子比例極高,這應“因為收入低微的家庭中不能生產者或不必要居留城市者,均居留鄉間,以省開支”之故。這電是近代城市中出現的一種家庭小型化的新趨勢。
(資料來源:楊蔚:《成都市生活費之研究》,第26頁,金陵大學農學院出版研究叢刊第五號。) 從其中食物類消費高達63.34%可以看出,其時成都工人階層的生活水平是極為低下的,廣大工人往往“只求一啖飯地,以暫維生,于愿已足”[23]。因收入有限,工人們的大部分開支均用于基本衣食所需,甚至連衣服費用都很少,絕大部分都用于食品與燃料。 據調查,1929年上海工人家庭生活費開支中食物、房租、衣著、燃料和雜項等所占比例分別為53.2%、8.3%、7.5%、6.4%和24.6%[24]。根據恩格爾定律:生活水平直接與食物、房租、衣著、燃料、娛樂教育等雜項這五類支出比例有關。食物費所占的比例隨收入的增高而遞降;房租衣著與燃料的比例,不隨收入的增減而變化;娛樂教育等雜項費支出的比例隨收入的增高而遞升。從成都和上海工人家庭生活費的比較中不難發現,上海工人家庭生活費中食物費所占比例遠低于成都工人家庭,而雜項費用比例則接近為成都工人家庭的兩倍。上海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顯然遠高于地處內陸的成都工人家庭,他們更能享受到都市現代化進程中所帶來的對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的提升。 從各類雜項消費中則可以一窺其時成都工人家庭的生活觀念和消費方式。 1937年成都市勞動負販界每成年男子單位雜項消費價值之百分比 類別日用嗜好 教育 娛樂 交際 醫藥 其他 共計 百分比 12.11 16.17 6.05 0.84 7.51 16.93 40.39 100 (資料來源:楊蔚:《成都市生活費之研究》,第46頁,金陵大學農學院出版研究叢刊第五號。) 從表中可以看到,在日常雜項的消費中日用、醫藥等滿足生活必需的項目占了較大比例。而雜項中的另一項較大的花費為“嗜好”,即指煙、酒、賭博等不良習慣,這主要是由于工人們生活苦悶,加之他們多迫于生計而失去上學的機會,文化水準普遍不高,缺乏正當的娛樂以消解疲乏所致,當然也與其時不健康的社會風氣密不可分。根據《國民公報》1931年所援引的成都市工會的統計,全市工會會員中“工人識字者僅占五分之一稍強,而吸煙者竟達五分之二以下”[25]。而在雜項中教育所占比例僅為6.05%也反映出他們對教育的重視是顯然不足的,這在他們的子女教育中也有所體現。在1935年對成都市校工生活狀況的調查中可見,在被調查的校工子女中,學齡兒童108人,而其中未入學者達49人,占了總人數的45.37%[26]。總之,貧困及對教育的忽視使得工人子女的受教育程度也往往偏低,這不僅會對其時成都的人口素質形成影響,也使得廣大的工人子弟在將來的擇業及社會流動中也往往會重復父輩的道路。
四、結語
通過對抗戰前成都市工業的發展和工人的數量、工人的工作狀況與收入、工人的家庭生活等多方面的考察,可以看到,其時成都城市社會經濟發展的滯后使得工人的工作環境惡劣而收入則極為低微,受其所限,工人家庭的生活水平也是十分低下。其時成都工人們的生活狀況應該代表了最廣大勞動群體的生存狀態。他們一方面成為了城市經濟發展所需的廉價勞動力,另一方面,生存的壓力以及對社會不公平的激憤的累積也使得他們容易產生變革的呼聲。從要求改善生活待遇的自發式的斗爭到建立自己的組織,成都市的工人運動經歷了一個發展的過程。廣大的工人階層也成為了革命的群眾基礎,成為了推動社會變革的積極力量。總之,民國前期成都市工人階層開始崛起并逐步走上社會的政治舞臺,為成都城市現代化進程帶來了重大而深刻的影響。這也是民國前期廣大內陸城市工人階層生存狀態和發展軌跡的一個縮影。
【參考文獻】 [1]四川統計月刊第1卷[J]. 1939,(1). [2]本市各業工人統計[J]. 四川經濟月刊第6卷,1936,(6). [3]成渝兩市之勞動人口統計[J]. 民間意識,第3年第2、3、4期合刊,1936,23-24. [4]施居父. 四川人口數字研究之新材料第4卷[M]. 成都民間意識社,1936. 6. [5]農情報告[J]. 1936,(7). 173-178. [6][13][16][21]成都市牙刷工業與工人生活概況調查[N]. 成都市政府周報,1939,(22),(23). [7]成都市人力車夫生活概況調查報告[J]. 華西協和大學社會學系期刊,1935. [8]吳虞. 日記中物價摘錄(1912-1947)[M]. 近代史資料,總60號(1986年). [9]成都印刷業調查[J]. 四川經濟月刊第5卷,1936,(1). [10]上海特別市社會局編. 上海特別市工資和工作時間(1929年)[M]. 商務印書館,1931. 124. [11]第二次中國勞動年鑒上冊[M]. 北平社會調查所,1932. 29. [12][23]十年來成都市生活之變遷調查[N]. 國民公報,1932-01-01. [14]禁止幼童拉車[N]. 平報. 1932-05-26. [15]新新新聞[N]. 1935-03-31. [17]陳正謨. 我國人口之研究[J]. 統計月刊,1933. [18]羅澍偉. 近代天津城市史[M]. 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 596. [19]楊蔚. 成都市生活費之研究[J]. 金陵大學農學院出版研究叢刊,(22). [20]成都快報[N]. 1932-08-10. [22][26]鄧士華. 成都市校工生活狀況調查報告[J]. 華西協和大學社會學系期刊,1935. [24]上海市政府社會局. 上海市工人生活費指數[M]. 中華書局,1932. 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