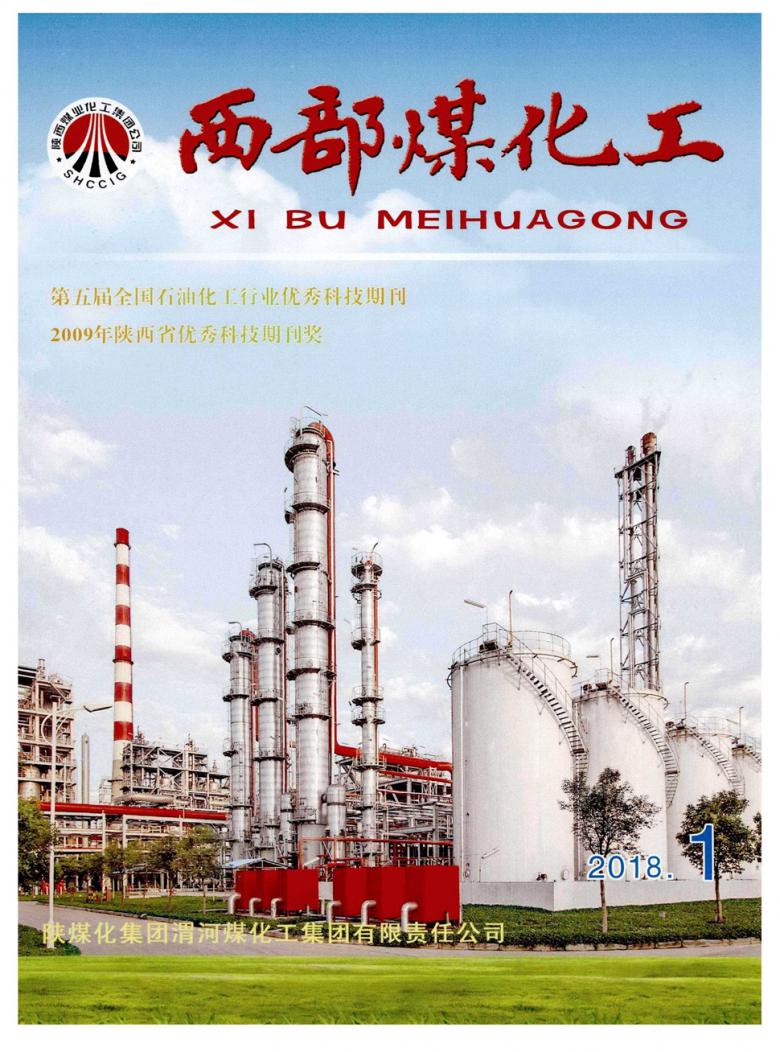試析中原文化背景下當代河南作家的文化品質
劉渝霞
論文關鍵詞:河南作家鄉土文學平民意識文化批判文化品質
論文摘要:中原文化浸潤下的河南作家,選擇鄉土文學作為創作的載體,注重文學的社會價值,對文化與生存關系進行思考,展示與剖析了國民靈魂,深入地揭示了當代農民心理上的種種痛疾和障礙;關注對鄉土的文化理性批判,展現了河南地域文化的新品質。
特定的地域,有著人類不同的活動形態、地理特征、文化傳播走向和行為系統,不同的地質條件會產生不同的勞動方式、生活方式、風俗風情和審美意向,這些都使作家在文學創作的總體風貌和細部描摹中產生深刻的印記。
當代河南作家的創作離不開孕育它的文化背景—中原文化。中原文化悠久、堅韌、豐富和渾厚的個性,中原文化所具有的生命力和穩定性特征以及其文化思維和生存觀念,是河南作家的精神財富;無論是人生哲學、審美情趣、藝術思維方式,乃至題材選擇、語言運用等方面,中原文化都對河南作家的成長起著潛移默化的作用,從而使我們可以在作品的文化生存環境下體味其具有的河南特色。
當代河南作家多是出身于城鎮的書香門第,或其本身就是農民,或是農民的兒子,或即使非土生土長,但由于上山下鄉等原因,也有著長時間的鄉村經歷。農村、田野在他們的世界觀、思維邏輯乃至情感判斷上打上了深刻的烙印,以河南為中心地區所構成的中原文化生態空間,對河南作家的影響最為突出。同時,河南長期以來以農為主的生存狀態使同宗同姓的自然村落長期保存,許多古老的傳統習俗得以保留,濃厚的傳統倫理于農民既是一種美德,同時又是一種狹隘。在這樣的創作背景下,鄉土就成為河南作家最初始情感與深刻理性結合的一種文化形態,他們選擇鄉土文學作為自己創作的載體,表現了濃郁的中原情結,對故鄉的熱愛和冷靜的分析,體現出鮮明的中原傳統文化蒼勁、雄厚和悲苦的情懷。
1注重文學的社會價值,表現平民化的文學意向
20世紀80年代以后崛起的河南中青年作家,背負著振興中原文化的歷史重任,決定著中原文化圈整體文學品質的未來。但是中原文化的振興,裹挾著歷史的厚重、蒼勁、執著、理性,同時還有權欲、保守、奴性、自卑等劣根性。皇天后土的中原文化和新的時代文化相交織,形成了河南地域文化的新品質。
李佩甫的《羊的門》演繹和再現了這種文化品質,它集中展現了中原人文化心靈史。書中的人們具有保持生命的本能,又對他人的生死麻木漠視;既因充滿生的苛求而馴服,又內含無知的反抗和愚昧的自尊。主人公呼天成就是在中原文化的背景下塑造的、兼有中原文化的優點和局限的形象。這一形象寄托著作者李佩甫對養育他的中原大地和中原文化的熾愛,對中原鄉村智慧的首肯,同時也體現了作者對呼天成所外化的中原文化的困守與封建特性的深刻批判。
中原文化深受儒家文化的影響,當代河南作家在中原文化的浸潤和儒家理想的濡染下,作品中情不自禁地保持了儒家的生態哲學、生存追求及社會理想,注重文學的社會價值,創作風格大氣,文風雄渾而壯闊。他們緊跟時代,表現現實,關心政治。政治文化在他們的作品中有比較集中的體現,儒家的憂世憂生精神轉化為一種終極人文關懷。李佩甫的《學習微笑》等作品直接關心國事民虞,表現社會主潮問題,引起讀者強烈的共鳴;柳建偉的《沖出重圍》通過和平年代的一次軍事演練,暴露出軍隊建設的一些非常深刻、關鍵的問題,揭示了科技強軍的緊迫性,表現了作者沉重的憂患意識,在恢弘的時空中所包含的軍旅生活的豐富性、反思性和前瞻性是空前的;周大新的具有“史詩”之謂的《第十二幕》,立足于故土南陽,以尚家三代發展絲綢業的家族史為經線,編織出了20世紀中國民族工業酸甜苦辣的發展史,對中國百年掙扎圖強的抗爭史給予了個人性的藝術透視,這些都表現了作家強烈的憂世與憂生精神。
當代河南作家的作品,在文化意象上表現在他們的平民化立場、民間化傾向,具有可貴的平民意識。作品中蘊涵了沉重的歷史文化內涵,文學的主角由英雄改為世俗平民,追求“現代精神”和“現世關懷”。二月河的“清帝系列”小說所展示的社會風俗和人文景觀,使它具有“史詩”的規模和品格。作品中的中心人物雖為歷史上的風云人物,但他們走出了“正史”或者是“政治史”,作者與作品中的人物進行靈魂的對視,他們的七情六欲、喜怒哀樂一一展現,經過原生歷史到心理歷史到審美歷史的轉變,實現了人的還原。張宇的《軟弱》等,把寫作的筆觸深人到城市平民小人物的生存境況中;《曬太陽》雖寫的是一縣之長的人生經歷,但作品所采取的第一人稱的敘事方法,更容易表現縣長楊潤生作為一個普通的“這個人”的思想。劉震云《故鄉天下黃花》從普通村民的角度,審視馬村半個世紀以來的風云變幻,認為從民國初年、抗日戰爭、解放戰爭直到改革開放這么長的歷史進程中,一幕幕爭權奪利的鬧劇,每次遭殃的都是最普通、最無辜的村民。這些作品都表現了強烈的平民精神。
2關注鄉土文化理性批判,展示剖析國民靈魂
以回顧和反思歷史為主的鄉村小說,包含了對文化與生存關系的思考,從不同方面塑造出“鄉土中原”的立體形象,已經成為河南小說創作的主要內容。田中禾的《匪首》、李佩甫的《李氏家族的第十七個玄孫》、《羊的門》等,這些作品是對近百年農村歷史的重新認識,作家把“生之沉思”寄托在這“重新認識”之上,完成了農民形象“從精神意義的放逐、形象意義的消解到文化意義的整合”。《羊的門》被稱為“是一部改變了50年來鄉農文學面貌的作品。” 喬典運、周大新、閻連科等的鄉土小說,展示與剖析了國民靈魂,把目光投向農村畸形的關系和丑陋的人生,吸納繼承了“五四”以來問題小說“為人生”的主題,深人地揭示了當代農民心理上的種種瘤疾和障礙。這些作品立意厚實,“把筆觸伸延到對人性、人生、人的梳離與孤獨等現代意識的強烈的揭露和展示”,表現出小說家勇于“直面人生的勇氣和強烈的憂患意識”。喬典運的小說創作一直致力于國民性的探索,“對鄉土文化負面價值進行集中思索和表現的巨眼大手應當首推喬典運。其整個80年代小說主要視點是基于這樣一個發現:鄉土文化的負面影響已深人農民群體中,形成文化心理疾患,成為習焉不察的無意識,成為根性。一是長期封建文化,一是極左毒害,已轉為與現代化格格不人的根本障礙。改變的前提是必須認識它。喬以細節的寫實,整體語言式的現作,運用抽象、象征、變形、夸張、隱喻等手段,把他對鄉土文化心態即中國魂靈的深思熟慮,進行藝術強化。”他的《問天》、《換病》、《滿票》、《村魂》等一系列鄉村小說,以審丑的眼光關注社會現實,深刻地揭露蘊藏在農民心靈深處的頑癥:自私自利、麻木不仁、恃強凌弱、愚昧嫉妒等深層文化心理。周大新也是以探討國民性問題而見長,無論是對社會學意識上的人的描寫,還是對人的本性的探索,無論是表現農民的樸實、善良、樂觀為懷以及深藏在他們血脈中的旺盛的生命力,還是表現某些農民的殘酷無情、蝙狹固執、報復心理等丑陋之處,都反映了作家對人性矛盾深沉的思索。作家這樣寫的目的并不在于揭露傷疤,蘊涵在其中的是作家的強烈的社會責任感和歷史意識,希望這樣做能呼喚出健康的人格,呼喚出強大的國民靈魂。這無疑是繼承了魯迅農村小說重塑民族性格的創作意旨。
對鄉土世界的否定性價值判斷已經不約而同地成為河南作家的文化認同,形成了占主導地位的文化品格。在古老土地經受內外危機改造的時代,那些不安的靈魂先是“從器物上感到不足”,繼而“從制度上感到不足”,最終深化為“從文化根本上感覺不足”,并由此引發對傳統文化的價值解構。如果說對鄉土文學的理性批判精神來自對現代化正面價值的認同,那么,對鄉土文學負面價值的回歸意識,則產生于對現代化負面效應的認識和反撥。
當代河南作家關注對鄉土的文化理性批判,鄉土苦難和文化積重得到了空前的審視,體現出深重的悲劇精神。張宇《曬太陽》、李佩甫《無邊無際的早晨》、劉震云《塔鋪》等,把農民哲學表現得微妙而殘酷,捕捉了鄉土政治與文化的魂靈。作家的憂思和痛苦足可以顯示出文化結構破損的程度。劉震云后期的故鄉系列是超越土地的非功利審視,在創作立場上,他站在農民文化的內部對歷史和歷史觀念進行了重新的審視。他以高級文明形態的目光俯視農民的傳統文化心理,形成居高臨下的反諷語勢,在戲謔性的嬉笑怒罵中透出深切的關注。村莊里不存在倫理與政治的結合,也沒有民族與階級的沖突,只有對權力的世俗理解以及對世俗權力的強烈認同。權力崇拜釀就權力萬能,而權力無孔不人又支撐著權力崇拜。這些原本生活在最底層的鄉民,一生的智慧與勇力、狡黯與殘忍都在權力角逐中被激發出來,遍嘗人生的酸甜苦辣。這種陋習頑強的生命力說明了人性中的權欲本能在現代文明面前的勢力和可怕。
中原文化的熏陶和影響造就了河南作家,同時,與中原文化頑強生命力相伴的頑固的保守性,因循守舊的歷史觀念,也制約了當代河南作家的創作。
河南作家多是因為后天工作的緣故才走人城市的,他們在創作的起始階段以鄉土為題材,在隨后的創作中才慢慢轉人城市生活領域。他們的生活經驗主要集中在農村,藝術視野不夠開闊,寫作資源不能多方獲取。當有限的生活素材和情感體驗消耗之后,創作就失去了底氣,因此顯得后勁不足,難以創作出底蘊豐厚的作品。張義曾說過,“鄉土情結既是優勢,又可能成為負擔,在有些作家的作品里,鄉土定位已遮蔽了創作視野,面對城市化的沖擊,他們表現情不自禁的反感、退避、偏見情緒,一個作家可以終身描寫農村,但在今天他若不能了解城市化帶來的全民族生活的變化,就會固步自封。”許多作品在塑造代表著現代農業發展方向的新型農民形象方面用力不夠。河南作家在寫作視野的拓展方面還有待于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