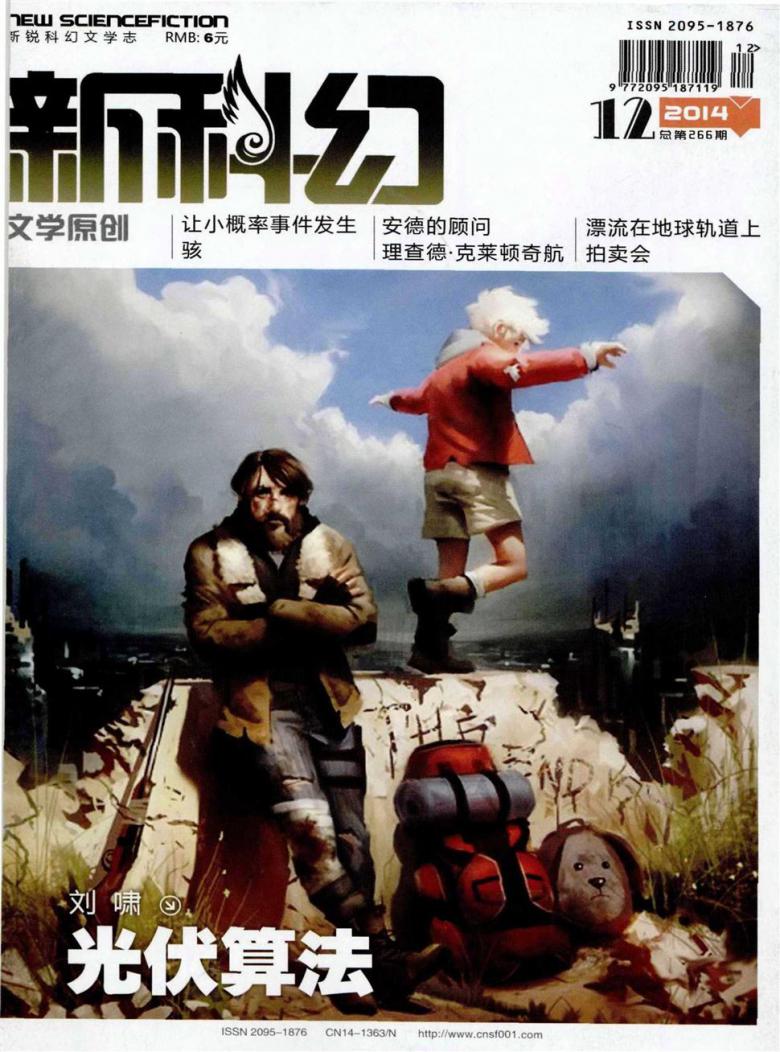試析當代中國場域中的大眾文化批判—評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
羅小青
論文關鍵詞:大眾文化法蘭克福學派伯明翰學派
論文摘要:大眾文化批判是法蘭克福學派的中心話語,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進行了全面的批判,其批判有不少合理之處,但是也存在不少局限,它片面強調大眾文化與社會的對立,忽視大眾文化本身特性,從而帶來了理論上的偏差。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在當代中國仍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有效性。
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批判是法蘭克福學派社會批判理論的一個核心話題,在一定的層面上,要研究和了解大眾文化的批判,必先對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判有所了解。
可以說,法蘭克福學派一直就是把大眾文化批判當作其批判理論的中心,從1936年霍克海默的《利己主義和自由運動》提出的“肯定文化”概念到1942年他與盧旺塔爾在通信中所提出的“大眾文化”概念,再到1944年他與阿多諾合著的《啟蒙辯證法》一書所使用的“文化工業”一詞,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及其危害作了細致的分析和論述。這些分析和論述對后來的文化研究產生了極大的影響,從現實文化評論中我們也可見一斑。
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根據于深厚的近現代歐洲大陸哲學文化傳統之中,其理論深受歐陸哲學文化的影響。其思想既受盧梭、歌德、席勒等人的宗教化色彩的救贖思想影響,又受人文主義者伏爾泰、柏格森、叔本華、尼采、海德格爾等人的啟迪。而且,早期西方馬克思主義者盧卡奇、柯爾施、葛蘭西對馬克思思想的誤解也成為他們對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的口實—把馬克思描繪成一個活脫脫的人本主義者,更有甚者,他們把黑格爾的辯證法思想以實用主義態度對待—強調其“否定”性,而拋棄其“同一”性。這樣,我們不難發現,法蘭克福學派在進行對大眾文化抨擊的同時,必然顯示出片面性、局限性。正視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判理論,同時結合當代中國實際,我們會找到正確面對大眾文化的鑰匙。
一、大眾文化以及對大眾文化的批判
在法蘭克福學派那里,“大眾文化”與“肯定文化”和“工業文化”有共同的含義。
何謂大眾文化?
在法蘭克福學派看來,大眾文化最顯著的特征是它使文化、藝術產品商品化,他們認為,當代資本主義或晚期資本主義的發展為文化、藝術的各個主要部分的商品化創造了條件,即科學技術進步、經濟和行政管理的集中化使這種商品化成為可能。他們達成如下共識:當代資本主義所遇到的再生產越困難,它利用一切可利用的手段來維持現狀的一般趨勢就越強大;現有的權力和財產分配的主導者使用經濟的、政治的和文化的手段來維持現狀。結果大部分文化生活領域被吸收并轉變控制個人意識的方面;同時,文化變成一種工業,利潤動機轉變成文化形式,越來越多的藝術產品變成商品,它們與工業產品一樣可以銷售和交換。即然藝術家靠出賣自己勞動為生,那么藝術家也就擁有這種文化形式的各個方面。阿多諾認為,大眾文化是一種標準化、陳腐老套、保守主義、虛偽、滿足浮化幻想的受操縱的文化工業產品為標志的文化,它致力于勞動階級的非政治化,維護社會的統治權威,制造大眾的虛假需求,是欺騙群眾的統治工具。現在“文化產品是徹頭徹尾的商品”(阿多諾)。廣告確立了新的美學標準,即使在那些文化工業不直接地為利潤而生產的地方,它的產品也是由這種新美學所決定的。快速與高比率的投資回收的經濟必然性,要求有吸引力的包裝物的生產,—或者為直接的銷售設計,或者為創造一種銷售氣氛。文化工業必須出賣特殊的新產品;或轉變成公共關系。法蘭克福學派將大眾文化或工業文化作為當代資本主義社會總體性的一個方面或維度,斷言“在壟斷下大眾文化是一致的,它們的結構都是由工廠生產出來的框架結構”,“文化工業的每個產品都是經濟上的巨大機器上的一個標本”。
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的批判主要集中在以下幾個方面:第一,批判大眾文化的欺騙性。霍克海默和阿多諾認為:“文化工業通過娛樂活動進行公開的欺騙。這些文娛活動,就像宗教界經常說教的,心理學的影片和婦女連載小說所喋喋不休地談論的,進行裝腔作勢的空談以便能夠更牢靠地在生活中支配人們的活動”。同時文化工業又通過許愿來欺騙群眾,給予他們一個暫時的滿足,但又隨時讓他們跌人冷酷的現實生活。由于大眾文化所具有的這種欺騙性,使得人們形成了得過且過的思想。“文化工業把日常生活描繪得像天堂一樣。擺脫和逃避日常生活就像私奔出走一樣,從一開始就決定了一定會回到原先的出發點,享樂促成了看破紅塵和聽天由命的思想”,正如馬爾庫塞所描繪的那樣,這種欺騙性還顯示出溫柔的一面—即“一種舒舒服服、平平穩穩、合理而又民主的不自由,在發達的工業文明中流行。”f=JN}第二,批判大眾文化對民眾的控制性。這一方面與前一方面有緊密的聯系。文化工業的最大功效就是對大眾進行控制,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提出了文化操縱(Culturalma沖ulation)這一概念,他們認為,在資本主義社會中,文化工業就是藝術作為操縱的過程。霍克海默在《藝術與大眾文化》一文中指出,“大眾娛樂”和“文化工業”的中介就是“操縱”。“文化工業的操縱功能已滲入經濟社會生活的每一個部分,并產生了無時不在的影響。更深一步看出,文化工業已完全控制了人們的精神思想,實現了對大眾的意識形態的操縱。文化工業使精神生活的所有部門、都以同樣的方式影響人們傍晚從工廠里出來,直到第二天早晨為了維持生存必須上班為止的思想,文化工業令人嘲笑地貫徹了粗陋的人格主義哲學家所反對的統一文化概念”。第三,批判大眾文化作為意識形態的工具。這方一面與前面兩點有密切的連貫性,因為欺騙性和控制性本身就是意識形態的特征。在霍克海默和阿多諾看來,文化工業及其娛樂的真正意義是“為社會進行辯護”;“在文化工業中,批判與敬畏都消失了,機構鑒定取代了批判的職能,’;“文化工業的每個運動都不可避免地把人們再現為社會需要塑造的那種樣子”;“現在的藝術拒絕反映下層人民事業,反映真正的普遍性,輕視認真地反映存在的苦難和壓迫”;“工業文化所描述的,是人們只能忍受的殘酷生活熬煎”。法蘭克福學派認為,作為為存在制度辯護的意識形態,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是通過對大眾心理意識進行操縱來實現的。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正是這樣履行意識形態的控制職能。一方面,文化活動失去了為人們提供娛樂的消遣和給人們的精神享受的作用,變成了外世界的擴展,勞作的延申,旨在恢復精力的應付下一次工作,阿多諾在《論流行音樂》中對流行音樂的這種作用作了這樣的說明:“音樂節目的消遣者自身就決定了流行音樂生產的同一機構的產品,他們的閑暇時間只是用來再生產他們的工作能力。欣賞音樂不是目的,而只是手段”。另一方面,文化工業決定娛樂商品的生產,控制規范著文化消遣者的需要,成為支配人的閑暇時間與幸福的力量,從而成為極權主義、法西斯主義控制大眾輿論、操縱人們的心理意識的強有力手段。第四,批判大眾文化扼殺個性和創造性。法蘭克福學派指出,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的標準化,劃一性扼殺了個性和創造性。所謂標準化乃是影響作品的一般特征和細節的過程,文化工業按照一定的標準、程度,大規模生產各種復制品,如電影拷貝、唱片、照片錄音帶等;而結構的類似性作為文化上業技術的結果產生于文化的形式,通俗作品或一個成功的新作品是大商業的機構急于賺錢的命令下而生產的,文化工業所崇尚的是模仿,內容的風格被堵塞或凍結,然而,對舊風格更新的作品必須維持創新型和獨創性的外表。因此偽個性在標準化自身的基礎上賦予大眾文化的生產一種自由選擇或開放市場的光環,每個產品影響一種個別的氣氛,這與其它產品的差別是微乎其微的。在《啟蒙辯護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諾根據文化工業產品對風格的否定來分析這些產品,認為他們很少顯示出不同于傳統形式的新形式,文化藝術生產脫離現實,文化工業的風格扼殺了風格自身。它的產品不反映實在的本質,并沒有真正的內容,它們從本質上說是一種模仿。盡管在電影、無線電廣播,流行音樂和雜志中有某種激情存在,但這僅僅是關于整體與部分、形式與內容、主體與客體同一的激情。文化工業的產品的模仿,標準化,偽個別性扼殺了藝術的生命、藝術的創造性和個性。
法蘭克福學派看到了當代資本主義社會文化領域出現的新變化和新特點,力圖揭示當代資本主義或發達工業社會與自由資本主義社會不同的文化模式;指出了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文化日益商品化的趨勢,以及這種趨勢所帶來的對文化事業的危害。他們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當代資本主義文化的局限性,揭露壟斷資產階級把文化變成為現實和統治辯護的意識形態工具,指出了由此產生的種種消極異化現象。的確,隨著科學技術的發展,當代資本主義的大眾傳媒迅速發展,使文化工業迅速成長為資本主義的一個重要的生產部門,文化藝術的商品化趨勢不斷加強。在晚期資本主義社會,文化的標準化、模式化、商業化、單面化,操縱性的強制性已成為當代資本主義文化的明顯特征,從而使之具有壓抑主體意識、個性、創造性、想象力和壓抑自由創新、自由選擇的消極功能,成為資產階級為維護統治辯護、壓抑或平息人民大眾反抗的意識形態的工具。應該肯定,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的批判,對它的涵義、特征和危害的分析是有獨創之處的,并包含有合理成份。很明顯,西歐北美在上世紀60年代末掀起的那場“反文化”運動,不能不說是受到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的影響。
但是,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的批判具有片面性和缺陷的。第一,法蘭克福學派站在舊的文化貴族市場,以文化精英自居,強調人與社會,人性與科技,文化藝術與時代的對立,以先念的道德倫理價值觀來衡量文化藝術和文化生產,因而使理論嚴重落后于實際。馬克庫塞的一個基本命題是在發達工業國家,技術和科學不僅成為一種和平和令人滿意生產力,而且也已變成一種新的意識形態。他認為科技的發展必然造成人性的墮落。法蘭克福學派還強調和夸大人與現實社會的對立,認為現在社會的發展導致了人的異化,人日益異己化,邊緣化,成為工業文化文明的奴隸。文化工業對人的精神的剝奪、控制,欺騙使得人失去了對現在社會的批判能力,而只能成為文化產品幸福的享樂者。法蘭克福學派在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之間挖出了一條壕溝,故意抬高精英文化而打擊和蔑視大眾文化。我們應該看出,大眾文化在沖擊精英文化的同時,也給精英文化展現出一片新的空間。為了應付現代工商業的需要,精英文化逐漸走出了世代棲息的藝術殿堂,脫離了傳統社會空間的局限從貴族城堡走向了大眾社會,從精英舞臺走向了大眾傳媒,在大眾社會找到了新的生存方式和生存空間,精英文化與大眾文化互滲已是不爭的事實,法蘭克福學派早已衰微,而大眾文化仍舊興盛并遍及全世界,這充分說明了大眾文化存在的歷史必然性和合理性。事實上,60年代后,隨著西方社會現代化進程的進一步發展及整個社會結構和形態的變化,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工業”,“大眾文化”理論影響力越來越小,倒是那些對大眾文化持積極態度的批判家日益受到重視。例如興起于20世紀五六十年代的英國文化研究,特別是1964年成立的“伯明翰當代文化研究中心”即伯明翰學派,他們不滿于法蘭克福學派那樣站在精英主義立場來研究文化方式,特別是他們所認為的本真大眾文化,即底層的工人階級文化,力圖從精英文化傳統中走了出來。早期他們以《新左派評論》為陣地,發展出一種“文化主義”理論,擴大了文化的內涵,反對高雅文化與低俗文化的劃分,取消文化產品中審美的首要地位。可以說,伯明翰學派是以嚴肅的方式對待大眾文化,同時也堅持文化研究的批判維度,意圖將大眾文化放在與社會相關聯的政治框架中加以分析。這個學派的影響力目前越來越大。 第二,把對納粹的仇恨和恐懼帶進文化工業理論研究活動中,使理論視角出現偏差,形成了對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的偏見。阿多諾曾說過:“奧斯維辛之后寫詩是野蠻的”。足見納粹暴行對這位猶太裔的法蘭克福學派成員的精神傷害有多么深切。法蘭克福學派其他主要成員如霍克海默,馬爾庫塞、弗洛姆等人都具有猶太血統,對納粹的精神迫害、納粹所借助的宣傳機器所展開的反猶太宣傳對他們有切膚之痛。所以為什么法蘭克福學派對文化工業或大眾文化特別反感。正因為法西斯的非理性的極端荒謬的宣傳活動;民眾受納粹意識形態的控制及納粹暴政統治等現實,正是通過具有文化工業的意識形態統治功能統一起來,以理解社會控制問題。他們完全站在科技文明和大眾文化的對立面,理解和評價文化工業或大眾文化。法蘭克福學派這種對納粹的仇恨和敵意的情緒必然會影響他們對文化工業或大眾文化的偏差和敵意。
第三,在對文化工業的批評中,忽視了大眾的審美共性、接受性和創造性。法蘭克福學派在20世紀40年代轉移到美國,更驚訝于美國社會生活中的文化商業化以及交換價值在這個國家所占的主要性,他們發現,合理化和標準化已廣泛深人到大眾媒體之中。于是這一學派高舉文化捍衛的旗幟,站在精英文化立場,以貴族守舊意識對抗資本主義文化的異化。重點批判決定娛樂商品的生產、控制和規范消費者的文化精神需要的文化工業,以及文化工業所表現出來的標準、模式化、商業化、操縱性、強制性,偽個性化等等。法蘭克福學派的文化批判理論一直強調人的價值、情感,人的解放自由,看似十分重視人本身,但是,他們卻忽視了文化工業的產品的受眾在消費這些產品時,每個個體的審美感方面的共性;同時也忽視了每個個體在接受這些產品時,由于各方面的不同而產生的獨特審美感受和審美差異,忽視了各個個體在接受同一類作品時會有不同的審美想象、審美領悟、審美創造等方面的藝術創造性,而一味地強調文化工業的物質化、平庸化、非個性化,這樣帶有偏見的研究和在此基礎上形成的理論,必然只講對立,而忽視同一性。對于法蘭克福學派關于大眾文化是大眾被強制和被欺騙的文化平庸形式,遭到了伯明翰學派的反對。多米尼克·斯特里納蒂說得很明白:“不能把通俗文化理解為一種強加于人們思想和行動的文化。無論這種強加被說成是資本主義生產和消費要求獲利和市場的結果,是資本主義或父權制實行意識形態控制的結果,或者被說成是一種普遍精神結構支配的結果,都是理解通俗文化的不適當方法。根據平民主義的看法,除非把通俗文化看成是對于民眾聲音或多或少的真實表現,而不是一種強加,否則就不可能理解它。”
伯明翰學派拋棄了高雅與粗俗文化之分,通過關注媒介文化的產品,打破了法蘭克福學派研究中的某些局限性。實際上,法蘭克福學派的早期代表人物班雅明已經開始了對大眾文化的研究,他也看到了大眾文化解放的潛力,并提出了主動觀眾的可能性的觀點。在他看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進步,自上世紀末開始,人類進人了一個機械復制的時代,文化也成了“技術復制文化”。技術復制文化的首要象征是喪失了傳統文化的“光暈”,而“光暈”的喪失則意味著改變了以往使藝術遠離群眾,成為少數人的天地的局面。本雅明是懷著贊賞的態度談論復制藝術取代“有光暈藝術”的,在本雅明看來,機構復制藝術更符合現代人的需要。他曾指出:“技術復制能把原作的摹本帶到原作本身無法達到的地方”看來,本雅明是站在正面市場看待文化工業或大眾文化的。
二、大眾文化批判理論與當代中國現實
前面我們分析法蘭克福學派大眾文化批判理論的特點以及所存在的片面性和局限性,聯系到中國實際,我們認為有現實的啟發和借鑒意義。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深人和市場經濟體制的不斷完善,我國的文化事業進步被推向市場,文化、藝術的商品化成了一種不可避免的趨勢。這既給我國文化事業的發展帶來生機與活力,又產生了一些令人困惑的問題。如何對待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或文化工業批判,這是我們不能不去思考的問題。
(一)中國仍然需要法蘭克福學派的大眾文化批判理淪。
1.我國目前的大眾文化是一種商業文化,它以利益為主要追求目標,以娛樂消遣為主要功能價值,以低俗為主要藝術特征,所以大眾文化的消極意義是無法否認的。這就決定了法蘭克福學派的批判理論在當代中國還具有合理性和有效性。
2.我國文化研究和批評還需要法蘭克福學派文化批判理論的某些精神。法蘭克福學派的某些具體觀點和表述可能已經過時了,但其中體現出的某些精神還是非常有價值的,也是值得借鑒的。比如關注和研究新的文化現象的精神和胸懷,關注大眾立場等等。雖然法蘭克福學派對大眾文化的態度是否定的,但該學派把大眾文化納人關注和研究的視野本身就反映出開放的學術視野和寬廣的理論胸懷。反觀我國學界,當大眾文化已經在我們文化生活中立穩腳跟后,還有不少學者和作家對大眾文化嗤之以鼻,他們中不少人甚至不看一眼大眾文化的產品,更不去對之進行研究,甚至對大眾文化采取簡單粗暴的方式否定,這不但缺乏客觀的科學研究精神,而且還缺乏開放的學術意識和寬容的學術胸懷。對比法蘭克福學派,筆者認為該學派的學術視野和理論胸懷值得我們借鑒學習。
(二)走出法蘭克福學派的批評模式。
我國當前的大眾文化雖然存在商業化、模式化等特點,總體看還沒有達到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程度,還沒有形成戶大的文化工業體系,在一定程度上還具有文化藝術性。更仁一況,在“二為”的文化方針指導下,我國的大眾文化還不僅是謀利益的工具。大眾文化具有為大眾的特點,不單是具有強制性和欺騙性。從總體上,我國的大眾文化是反映大眾的聲音的。同時,我國還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沒有經過像資本主義長達好幾個世紀的思想啟蒙(從文藝復興到19世紀),所以,我國還不能一味批判大眾文化,大眾文化是啟蒙大眾的重要文化資源,我們要盡量消除其反面效應,充分發摘其iE面效應。北京大學著名文藝評論家張頤武先生有一句話值得我們深思,他說:“要像重視孔子一樣重視章子怡,”“世俗文化是低端、豐富的文化資源,傳統文化要通過大眾文化的出口才能流傳出去。”這句話至少指明了目前中國文化處于兩難境地:高端,中華文化的普遍價值沒有被充分認知,低端,大眾文化的競爭力還遠遠沒有和經濟成長的現狀相適應。
我們要從中國實際國情出發,對大眾文化進行準確地定位和引導,要正確認識大眾文化,堅持歷史的、辯證的實事求是的方法,任何人為的障礙設置都是要不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