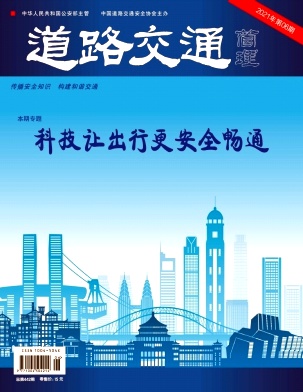“和而不同”:中華民族精神中的政治文明精髓
虞崇勝
【內容提要】中華政治文明的精核可以歸納為“和而不同”。從一定意義上講,把握了“和而不同”的精神實質,就是把握了中華民族精神中的政治文明精髓。“和而不同”,意思是說要承認差異(不同),在“不同”的基礎上形成的“和”才能使事物得到發展。也就是說,“和”是目的;但“和”的前提是“不同”,是多樣性的存在;沒有“不同”,沒有多樣性,就無所謂“和”。“和而不同”堪稱人類文明特別是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
【關 鍵 詞】和而不同/政治文明/文明沖突/多樣性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發展,弘揚民族精神已經成為不同國家和不同民族的共同呼聲。何謂民族精神?張岱年先生指出:“在中國思想史上,一種思想能夠滿足兩個條件才能稱為民族精神:一個是具有廣泛的影響,被許多人所接受,還有一個是它能夠促進社會發展。”[1]民族精神是一個歷史范疇,隨著歷史的發展和時代主題的轉換,民族精神也會不斷地發展和躍遷。中華民族精神博大精深,其中內涵著豐富的政治文明因素。這是一份寶貴的政治文明資源,值得我們深入發掘。我以為,“和而不同”應該可以被看做是中華政治文明的精髓。之所以如是說,是因為中華政治文明的發展盡管源遠流長,內涵豐富,但其精核則可以歸納為“和而不同”四個字。從一定意義上講,把握了“和而不同”的精神實質,就可以把握中華政治文明的精髓。
一
政治文明是人類政治智慧的結晶。中華民族精神作為中華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動力,包含著豐富的政治文明因素。2002年5月28日,李瑞環同志在英中貿易協會舉行的歡迎午宴上作了題為《和睦相處,和諧共進》的演講。他在演講中回顧了中華民族傳統文化形成和發展的歷史,引述了3000多年來歷代大思想家們關于“和”的思想,認為:“‘和’的思想,強調世界萬事萬物都是由不同方面、不同要素構成的統一體。在這個統一體中,不同方面、不同要素相互依存、相互影響、相異相合、相反相成。由于‘和’的思想反映了事物的普遍規律,因而它能夠隨著時代的變化而不斷變化,隨著時代的發展而不斷豐富其內容。現在,我們所說的‘和’,包括了和諧、和睦、和平、和善、祥和、中和等含義,蘊含著和以處眾、和衷共濟、政通人和、內和外順等深刻的處世哲學和人生理念。”[2]2002年10月24日,江澤民在美國喬治·布什圖書館的演講中也談到:“兩千多年前,中國先秦思想家孔子就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的思想。和諧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相互沖突。和諧以共生共存,不同以相輔相成。和而不同,是社會事物和社會關系發展的一條重要規律,也是人們處世行事應該遵循的準則,是人類各種文明協調發展的真諦。”他還說:“大千世界,豐富多彩。事物之間、國家之間、民族之間、地區之間,存在這樣那樣的不同和差別是正常的,也可以說是必然的。我們主張,世界各種文明、社會制度和發展模式應該相互交流和相互借鑒,在和平競爭中取長補短,在求同存異中共同發展。”[3]從以上論述中可以看出,“和而不同”的思想實則包容著深刻的政治智慧。
所謂“和而不同”,意思是說首先要承認“不同”,在“不同”的基礎上形成的“和”(和諧、和合),才能使事物得到發展。如果一味追求“同”,忽視或不尊重“不同”,不僅不能使事物得到發展,反而會使事物衰敗。這也就是說,“和”(和睦相處、共同發展)是目的;但“和”的前提是“不同”,是多樣性的存在;沒有“不同”,沒有多樣性,就無所謂“和”;“和”不是“同”,因為“同”泯滅了事物個性,是不可能達到“和”的境界的。由是可知,“和而不同”堪稱人類文明特別是政治文明的最高境界。
人類政治生活中之所以要特別強調“和”,是因為政治生活總是在一定的共同體中進行的,而共同體的存在本身就蘊含著和合的精神。如果沒有“和”,不同階層、不同膚色、不同信仰、不同傳統的人是不可能集合在一起的。正如布克勒所言:“構成任何共同體的東西與其說是各個個人的同質性,倒不如說是屬于一個既定的自然復合體內的許多個人力量集合。”[4]不僅如此,“和”還是政治發展的強大動力。沒有“和”,就不可能形成互惠,沒有互惠,就不會有政治發展。“互惠在各種政治發展形式中的重要性在于,確保發展使有關的人和共同體都相互受益。沒有互惠,政治就成為零和競賽。在這種情況下,有些人就使用政治的手段來損人利己。長此以往,其結果就很容易成為‘其和為負’,從而導致貧困、暴力和革命的逐步升級。”[5]
毫無疑問,在人類政治史上,到處都充滿了斗爭和沖突,在一定的歷史時期里甚至是你死我活的斗爭和沖突,但正如萊斯利·里普森在《政治學的重大問題》中所指出的:總的看,競爭的時間遠遠少于合作的時間。“因為競爭制造分裂,而合作產生團結;競爭具有破壞性,而合作是建設性的。競爭導致自我與他人對立,而合作使自我與他人和諧相處。事實上,甚至為攻擊他人而結合起來的團體也有內部的合作措施。因此,競爭的需求導致一些合作,但后者從不將人們引入競爭。所以,對于人類及其政治而言,合作行動是最重要的。”[6]
從政治文明的基本特性來看,“和”是政治文明產生和存在的基本前提。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中談到國家起源時指出:“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承認: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又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于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這種從社會中產生但又自居于社會之上并且日益同社會相異化的力量,就是國家。”[7]這就是說,國家存在的條件就是“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以內”;換句話說,就是國家的存在是以“和”為前提的,沒有“和”,不能將沖突限制在一定的范圍之內,就不可能有國家的存在和發展。因此,在政治領域,保持一個相對和諧的局面是十分必要的。
二
中華民族精神中“和而不同”思想的精妙之處在于,它在強調“和”的同時,堅持“有異”(不同)的存在,“和”是包容了“異”的“和”,而不是排斥“異”的“同”。作為追求和諧之美的儒學,歷來十分強調“和為貴”,強調多元共處,但同時也強調“和而不同”。孔子所說的“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已經明確地區分了兩種不同的理想境界:真正有德行的君子是善于協調、能夠與人和睦相處的,但又不是一味地、盲目地茍且求同;而無德行的小人則只知茍且求同,不顧不同主體間的差別,從而難以達到真正和諧。另外,孔子在回答子貢的問話時,還表達了“君子亦有惡”的觀點。他說:“唯仁者能好人,能惡人。”[8]這也就是說,做不到愛憎分明還算不上真正的仁者。因此,人們在交往特別是在政治交往中,不能無原則地遷就別人。與此相類似,《周易》中也曾提出過“物不可以茍合而已”的觀點,強調了世間萬物不能強求一律。不同政治文明間又何嘗不是如此呢!在未來的人類社會政治文明格局中,和睦相處必然是主旋律。但是,在和諧的大背景下,由于諸多政治文明之間的差異的存在,一定范圍的沖突也在所難免,這種沖突有時還會以激烈的形式表現出來。不過,只要這種沖突不突破一定的度,就不會危及到諸種政治文明的協同演進。甚至從某種意義上可以說,這種沖突的存在有時還是有益的。如果我們把人類政治文明看成一個大系統,那么組成這個大系統的諸種政治文明(即各國的政治文明)就是一個個的子系統。諸子系統之間的沖突必然引發各個子系統內部結構的變化,系統結構的變化又必然促使系統功能的變化。這樣,各個子系統就在這種變化中不斷實現質的飛躍。而各個子系統的質的飛躍又必然促使諸種政治文明資源的重新組合,并在政治文明資源的重新整合中實現人類政治文明的發展和進步。
“和而不同”的思想表現在國家關系上,就是倡導“協和萬邦”的理念,強調國家間應當親仁善鄰、講信修睦、禮尚往來,不能以大欺小、以強凌弱、以富壓貧,國際爭端要通過協商和平解決,各國之間應在平等相待、互相尊重的基礎上發展友好合作關系。表現在各種文明的關系上,主張“善解能容”,各種文明都是人類文明的組成部分,都對人類文明做出了貢獻,不應當相互排斥,而應當彼此尊重、保持特色、共同進步。這就是說,“和”是一種有機的契合,是一種質的提升,是通過和合達到一種新境界;而相對來說,“同”則是無原則的混合,只是一種量的相加,泯滅了各自的特性。因此,和諧不僅不消滅差異,而且鼓勵差異的合法存在,通過差異的比較和交融,以達到新的和諧。和諧不是靜止,而是通過和解和化合而獲致新的進步。如果表面上一團和氣,內里卻是一潭死水,那也是不符合“和而不同”精神的。
“和而不同”的思想就其精神實質來說,體現了一種政治寬容精神。2002年12月,在香港浸會大學召開的第二屆中華文化世界論壇上,澳洲國立大學榮譽教授柳存仁提出了“中華什么物事美”的題目。他認為,中國歷史上民族間的調和、互助,正是中華物事最美的地方。他還引用《國語·鄭語》中的話說:“‘講以多物,務和同也。聲一無聽,物無一聞,味無一果,物無一稱。’我們能夠明白事物的兩面,這是中華民族積了幾千年寶貴的、有時甚至是痛苦的經驗。有了這樣的文化,這樣的思考方式和深度,這樣在國際間、各民族間的認識和了解,是大家對我們中華民族能夠有的自覺。”來自美國威斯康辛大學的周策縱教授進而提出,很難想象,未來的理想世界會只有同而沒有異,這會是一個死寂的境界,也是不能長期存在的世界。因此,我們要建立的新文明、新文化,要統一并存,決不歧視“異”,這樣才能消泯可能因文明沖突而引起的戰火,保障永久的和平。[9]
幾十年前,周一良先生曾說過他最推崇這樣一幅對聯:“海納百川,有容乃大;壁立萬仞,無欲則剛。”季羨林先生也說過:“我個人覺得中國文化的特點可以歸納如下:唯求實用,不尚玄虛,貌似淺顯,實亦深密,整體思考,枝葉兼及,允執厥中,不務偏愛激,最大的特點還在有極大的包容性。大海能納百川,所以能成其為大。古人說:‘有容乃大’,說的也是這個道理。”[10]費孝通先生在90歲時也說過:“十年前在我80歲生日那天在東京和老朋友歡敘會上,我曾展望人類學的前景,提出人類學要為文化‘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做出貢獻,這里特別意味著人類學應當探討怎樣才能實現文化的自我認識、相互寬容和并存及‘天下大同’的途徑,這正是我提出‘文化自覺’看法的背景和追求。”他強調:“在新國家的建設當中,我們必須注意民族與民族之間、文化與文化之間的那種‘和而不同’的關系。‘和而不同’是世界上成功的文明體系的主要特征,這樣的文明體系與歐洲式的民族國家體系很不同,也有著它自身的優點。”[11]對于這些論述,我們不能僅僅看成是思想大家們的人生體悟或心靈感應,而應視為是對中華民族精神的精確把握和對人類社會政治文明發展規律的深刻揭示。
展開而論,不僅政治生活離不開寬容精神,即使是法律規范也是離不開寬容精神的。從一定意義上講,只有內涵了寬容精神的法律才是可以長久的。因為在人類社會歷史上,過于偏狹的法律,沒有幾部是能夠長久發生效力的。應該說,政治寬容精神在當代中國政治生活中得到了較好體現,比如我國實行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體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政體,以及多黨合作、政治協商、民族區域自治、“一國兩制”等等基本政治制度都是充分體現了政治寬容的精神的。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政治寬容不僅是一種政治精神,而且還是一國經濟和文化強盛的重要體現。孔子在談到民族關系和國家關系時,曾說過一句名言:“禮之用,和為貴”。在中國歷史上,大凡繁榮昌盛的年代,基本上都是遵循或體現了這一原則的。在長期的歷史和文化研究中,季羨林先生總結出了一條非常可貴的經驗:在我們國力興盛、文化昌明、經濟繁榮、科技先進的時期,比如漢唐興盛時期,我們就大膽吸收外來文明,從而促進了文明的發展和生產力的提高;到了見到外國東西就害怕,這也不敢吸收,那也不敢接受,這往往是我們國勢衰微、文化低落的時代。應該說,季老總結的這條經驗比較確切地反映了中國歷史的實際,值得我們再三深思。
翻開人類文化史隨處都可以看到,一種文化之所以能夠吸收他種文化,往往是在兩種或多種文化交往中體現“和而不同”思想的結果,而不是“同而無棄”的結果。歐洲文化在自身發展中吸收了各種各樣的不同文化傳統的因素,但它不僅沒有因此失去歐洲文化的特色,反而大大豐富了自身文化的內涵,這無疑是符合“和而不同”原則的。中國文化曾經大量吸收印度的佛教文化,并對其作了很大的發展,但中國文化仍然是中國文化,并沒有變成印度文化,這也是中國人較好地運用“和而不同”原則正確對待印度文化的結果。因此,要真正做到尊重政治文明的多樣性,必須弘揚“和而不同”的政治大智慧。
三
在經濟全球化的今天,世界變得越來越小,不同文明間的矛盾和沖突可能會比歷史上的任何時代來得更加彰顯和激烈,這就是美國學者亨廷頓提出“文明沖突論”的原因所在。然而,解決文明沖突的途徑并不是以暫時處于優勢的某種文明去同化或消滅其他文明;相反,文明沖突的消解只有在尊重文明的多樣性,保證不同文明的協同發展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實現。因此,在當今世界,倡導“和而不同”的政治文明觀就顯得十分重要。
在當今世界,盡管仍然有人幻想以一種超越一切時空的普世文明來統一世界,但是人類歷史上真實存在過的卻是沒有等級之分的多元文明,在世界文明之樹上開出的從來都是五彩繽紛的花朵。可以預計的是,未來的世界文明仍然是多種文明的和諧并存,而不會是什么普世文明的一統天下。因為這是人類文明發展的定律,誰也不能改變的。試圖以一種普世文明去框定人類豐富多彩的生活,那只不過是霸權主義者的一廂情愿,不可能成為事實。正確的態度,應是尊重多元文明的客觀存在,不要拂逆人類文明發展的客觀規律。正如費孝通先生所說,不同文明應在“多元文化的世界里確定自己的位置,經過自主的適應,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長補短,共同建立一個共同認可的基本秩序和一套各種文化能和平共處,各抒所長,聯手發展的共處原則。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12]。這就是說,未來的文明重構既不是東方文明化,也不是西方文明化;既不是以東方文明之柔克西方文明之剛,也不是以西方文明之剛克東方文明之柔;既不是東風壓倒西風,也不是西風壓倒東風。對此,即使是以文明沖突論而著稱的美國學者亨廷頓也注意到,以一種文明完全置換另一種文明是不可能的。他說:“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有時企圖擯棄本國的文化遺產,使自己國家的認同從一種文明轉向另一種文明。然而,迄今為止,他們非但沒有成功,反而使自己的國家成為精神分裂的無所適從的國家。”[13]
值得欣慰的是,“和而不同”作為中華民族精神中的政治文明精髓,正在受到越來越多的中外進步人士的關注,并且日益顯示出其強大的生命力。正如美學家陳望衡教授所指出的:“作為古典哲學的命題‘和而不同’,它的生命力是永恒的,它在今天的價值需要我們進一步挖掘。在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政治,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偉大事業中,‘和而不同’的魅力越來越放射出光輝。一個高度文明的國家,必然是一個法治的國家,同時也是一個民主團結、生動活潑、安定和諧的國家,必然是一個倫理充分發揮調節作用但審美又必然極為活躍的國家。‘和’既聯系著人與自然的血緣關系,又聯系著情與理的血緣關系。在法治不到的地方,有倫理的‘中和’在調控,在倫理不到地方,有審美的‘和融’在調控。依法治國,以德正人,以美和心。我們的社會必將越來越文明,越來越美好。”[14]
當代中國共產黨人關于文明多樣性的認識和看法,是中華民族精神中“和而不同”思想的具體體現,也是中華民族精神中政治文明因素的發揚光大。這種認識和看法由于正確地反映了人類政治文明發展的基本規律,因而得到了包括西方進步人士在內的世界所有進步力量的普遍贊同和支持。“尊重文明的多樣性”,“倡導和而不同的政治格局”——這些反映人類政治文明發展內在要求的正義呼聲,正日益成為進步人類推進政治文明發展的基本價值取向。有理由相信,只要切實尊重政治文明的多樣性,堅持“和而不同”的政治文明觀,人類政治文明一定能夠在新的世紀里獲得前所未有的發展和繁榮。
[1]張岱年:《炎黃傳說與民族精神》。載《中華炎黃文化研究會會刊》第1期。
[2]李瑞環:《和睦相處,和諧共進》。載《人民日報》2002年5月29日。
[3]《人民日報》2002年10月25日。
[4]轉引自[美]貝恩·J·辛格:《實用主義、權利和民主》,上海譯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93頁。
[5]國際經濟增長小組編:《制度分析與發展的反思》,商務印書館1992年版,第119頁。
[6][美]萊斯利·里普森:《政治學的重大問題》,華夏出版社2001年版,第32頁。
[7]《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0頁。
[8]《論語·里仁》。
[9]轉引自《中國文化報》2002年12月27日。
[10]季羨林:《20世紀中國學術大典》序。載《光明日報》2002年10月27日。
[11]費孝通:《文化自覺,和而不同》。載《民族研究》2000年第3期。
[12]費孝通:《反思·對話·文化自覺》。載《北京大學學報》1997年第3期。
[13][美]塞繆爾·亨廷頓:《文明的沖突與世紀秩序的重建》,新華出版社1999年版,第12頁。
[14]陳望衡:《論“和而不同”》。載《湖北日報》2003年4月10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