淺談孝道回歸與農(nóng)村家庭養(yǎng)老保障的再定位
王文娟 馬國(guó)棟
論文關(guān)鍵詞:農(nóng)村;孝道回歸;家庭養(yǎng)老保障
論文摘要:隨著農(nóng)村社會(huì)的變遷和發(fā)展,孝道在經(jīng)歷了功能錯(cuò)位、缺位后逐步回歸到家庭倫理道德規(guī)范的本位。國(guó)家相關(guān)養(yǎng)老保障政策的實(shí)施,農(nóng)村孝道的階層化現(xiàn)象,于女分擔(dān)的養(yǎng)老模式以及老人自我養(yǎng)老意識(shí)的強(qiáng)化等,都推動(dòng)了農(nóng)村孝道的回歸。本文旨在以孝道養(yǎng)老功能的回歸為出發(fā)點(diǎn),探討農(nóng)村家庭養(yǎng)老保障的再定位問(wèn)題,指出家庭養(yǎng)老保障必然是我國(guó)農(nóng)村當(dāng)前及今后相當(dāng)長(zhǎng)的時(shí)期內(nèi)的主要養(yǎng)老方式。
一、孝道與農(nóng)村家庭養(yǎng)老保障的研究概述
在中國(guó)農(nóng)村,幾千年來(lái)都有著養(yǎng)兒防老的傳統(tǒng)理念,并且通過(guò)家庭養(yǎng)老這種形式表現(xiàn)出來(lái)。孝道是中國(guó)傳統(tǒng)社會(huì)所形成的家庭倫理道德規(guī)范和社會(huì)基本行為規(guī)范,自從1949年以來(lái),農(nóng)村的孝道觀念在遭遇了功能錯(cuò)位、缺位之后,開(kāi)始逐步回歸到家庭倫理道德規(guī)范的本位。學(xué)界對(duì)孝道與農(nóng)村家庭養(yǎng)老的關(guān)注較多,但只是探究農(nóng)村孝道衰落的根源和對(duì)策研究,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有郭于華、閻云翔、陳柏峰、賀雪峰和聶洪輝等人的論述。郭于華(2001 )通過(guò)對(duì)河北省農(nóng)村養(yǎng)老的調(diào)查,強(qiáng)調(diào)指出中國(guó)人的代際關(guān)系是遵循付出與報(bào)償相衡的公平邏輯。正是上下兩代對(duì)孝道理解出現(xiàn)差異,親子之間付出與回報(bào)的均衡交換關(guān)系被打破,農(nóng)村的孝道就崩解了。閻云翔(2006)在對(duì)黑龍江省下呷村的調(diào)查基礎(chǔ)上宣稱,農(nóng)村孝道的衰落是個(gè)人權(quán)利意識(shí)的增長(zhǎng)、無(wú)效的法律、公眾輿論失去約束力等原因所致。對(duì)皖北李好村進(jìn)行實(shí)地調(diào)查后,陳柏峰(2007)指出,孝道衰落是農(nóng)民生活價(jià)值的外在體現(xiàn),孝道衰落是家庭關(guān)系日益理性化,農(nóng)民價(jià)值世界倒塌所致。賀雪峰(2008)則認(rèn)為,在農(nóng)村孝道衰落的背景下,代際間關(guān)系重新平衡應(yīng)建立在代際交換減少、期望值下降和情感減少等基礎(chǔ)之上。聶洪輝和揭新華(2009)的觀點(diǎn)是,信仰和價(jià)值觀的倒塌是孝道衰落的催化劑,法律只能保底的兩難困境成為“無(wú)效的法律”的尷尬,最終使傳統(tǒng)的孝道失去作用并衰落下去。由此可見(jiàn),學(xué)界大多持有這樣的觀點(diǎn):農(nóng)村孝道觀念正在衰落,其對(duì)農(nóng)村家庭養(yǎng)老的保障功能逐步削弱。筆者則以孝道養(yǎng)老功能的回歸為出發(fā)點(diǎn),探討農(nóng)村家庭養(yǎng)老保障的再定位問(wèn)題,以期對(duì)促進(jìn)農(nóng)村養(yǎng)老保障事業(yè)發(fā)展,加強(qiáng)農(nóng)村和諧社會(huì)的建設(shè)作出思考。
二、農(nóng)村家庭養(yǎng)老保障中的孝道回歸
新中國(guó)成立以后,由于孝道文化在農(nóng)村有一定的歷史積淀,在廣大的農(nóng)村,民眾在一定程度上繼承弘揚(yáng)傳統(tǒng)孝道精神,人們的家庭生活依然遵循著傳統(tǒng)孝道。從上個(gè)世紀(jì)50年代到60年代的中期,由于政治生活中“左”的錯(cuò)誤對(duì)農(nóng)村孝道的不良影響,以及所有制的改變對(duì)家庭關(guān)系產(chǎn)生的重大影響,青年人對(duì)孝的踐行出現(xiàn)了一定程度的錯(cuò)位現(xiàn)象。1966-1976年的10年浩劫讓人們磨滅了“孝”字,中斷了孝文化的傳承,以致于人們對(duì)孝道襟若寒蟬,談孝色變,孝道的合理性和繼承性被完全否定。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huì)以后,經(jīng)濟(jì)利益原則漸次成為主導(dǎo)農(nóng)民行為的標(biāo)準(zhǔn),農(nóng)村社會(huì)出現(xiàn)了家庭利益關(guān)系的倒置現(xiàn)象。青年人多以自身利益為重,代際之間利益和情感分離,孝道倫理逐漸淡化。隨著農(nóng)村家庭模式的現(xiàn)代性轉(zhuǎn)變,維系家庭關(guān)系的紐帶變?yōu)榍嗄攴蚱拗g的愛(ài)情和三口之家的天倫之樂(lè)。這種家庭生活方式給了年輕一代極大的自由和幸福,但卻造成了老人晚年的孤苦和寂寥。現(xiàn)代孝道所要求的對(duì)老人的“敬”這種精神慰藉功能很難實(shí)現(xiàn)。到了90年代以后,由于儒家文化的影響力在農(nóng)村進(jìn)一步衰微,孝道觀念更為淡漠,農(nóng)村老人的生活處境更為艱難。中國(guó)農(nóng)村家庭養(yǎng)老在現(xiàn)代社會(huì)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困境,孝道傳統(tǒng)在中國(guó)農(nóng)村一度出現(xiàn)了危機(jī)。
有研究者指出,由于農(nóng)民價(jià)值世界的倒塌,他們?nèi)找骊P(guān)注的只是赤裸裸的現(xiàn)實(shí)利益,農(nóng)村的孝道正在日益衰落。如果照此推論的話,1949年以來(lái),孝道的地位在農(nóng)村一步步衰落,時(shí)至今日,農(nóng)村社會(huì)幾無(wú)孝道可言,但這并不符合廣大農(nóng)村社會(huì)的現(xiàn)實(shí)情況。誠(chéng)然,孝道淪喪的情況在2000年之前比較嚴(yán)重,但自2000年以后,那將只會(huì)是少數(shù)情況。“農(nóng)村舊貌換新顏”已然不再是一句政治口號(hào)。進(jìn)入21世紀(jì),國(guó)家意識(shí)到在道德生活領(lǐng)域,不能選擇“國(guó)退民進(jìn)”的方略,讓農(nóng)村的“市民社會(huì)”在道德滑坡中生長(zhǎng),必須要適時(shí)、積極地進(jìn)行引導(dǎo)和干預(yù),國(guó)家政治生活又一次深刻地影響了農(nóng)村。農(nóng)村養(yǎng)老迫切需要國(guó)家、社會(huì)、家庭等多方力量的匯聚和高度關(guān)注。近年來(lái),由于國(guó)家相關(guān)養(yǎng)老保障政策的實(shí)施,農(nóng)村孝道的階層化,子女分擔(dān)的養(yǎng)老模式以及老人自我養(yǎng)老意識(shí)的強(qiáng)化,都大大促進(jìn)了農(nóng)村孝道的回歸,促使農(nóng)村孝道最終向著社會(huì)主義新孝道倫理的方向發(fā)展。社會(huì)主義新孝道倫理包括兩個(gè)方面:一是要贍養(yǎng)父母,關(guān)心父母的身體健康狀況,即“奉養(yǎng)”,二是讓父母在精神上能夠得到慰藉,即“誠(chéng)敬”,兩者缺一不可。
(一)國(guó)家推行的相關(guān)養(yǎng)老保障政策與農(nóng)村家庭養(yǎng)老保障
在我國(guó)二元化經(jīng)濟(jì)的現(xiàn)實(shí)情況下,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水平還比較落后。因此,由政府出面把社會(huì)保障和社會(huì)發(fā)展與家庭養(yǎng)老結(jié)合起來(lái),尤其是逐漸擴(kuò)大政府的財(cái)政責(zé)任,將有助于孝道的回歸,有利于家庭養(yǎng)老的繼續(xù)發(fā)展。“保護(hù)耕地、增加農(nóng)民收入”的政策,為農(nóng)村家庭養(yǎng)老提供了最基本、最有效的社會(huì)保障。 2009年9月,在農(nóng)村開(kāi)展的新型農(nóng)村社會(huì)養(yǎng)老保險(xiǎn)規(guī)定:中國(guó)農(nóng)民60歲以后都將享受到每月55元的國(guó)家普惠式養(yǎng)老金,“新農(nóng)保”還規(guī)定,參保人從男年滿60周歲、女年滿55周歲的下月開(kāi)始,根據(jù)養(yǎng)老保險(xiǎn)繳費(fèi)金額大小、繳費(fèi)年限長(zhǎng)短確定養(yǎng)老金領(lǐng)取標(biāo)準(zhǔn)。這些政策在一定程度上減輕了農(nóng)村青年的負(fù)擔(dān),解決了老人的養(yǎng)老問(wèn)題。“新農(nóng)保”試點(diǎn)覆蓋面僅為全國(guó)10%的縣市、區(qū)、旗,2020年之前才能基本實(shí)現(xiàn)對(duì)農(nóng)村適齡居民的全覆蓋。加之現(xiàn)在我國(guó)已提前進(jìn)入“未富先老”的老齡化社會(huì),當(dāng)一個(gè)國(guó)家邁入老齡化社會(huì)的門檻之后,經(jīng)濟(jì)保障、服務(wù)照料和精神慰藉就從個(gè)人和家庭的需求轉(zhuǎn)化為社會(huì)的需求,老年人的需求更應(yīng)得到關(guān)注。為營(yíng)造一個(gè)和諧的老齡社會(huì),在社會(huì)政策方面要建設(shè)一個(gè)“可持續(xù)、求適度、行得通”的社會(huì)保障制度。當(dāng)前,社會(huì)還不能完全承擔(dān)起養(yǎng)老的任務(wù),孝道的養(yǎng)老功能日益突出。所以,國(guó)家在推廣“新農(nóng)保”政策的同時(shí),大力弘揚(yáng)孝道文化,并建立一定的法律作為保障,同時(shí)對(duì)貧困的養(yǎng)老家庭給予一定的補(bǔ)助,這也是我國(guó)農(nóng)村經(jīng)濟(jì)發(fā)展和社會(huì)進(jìn)步的必然要求。
社會(huì)主義新農(nóng)村建設(shè)所要求的“做個(gè)有道德的新型農(nóng)民”正在國(guó)家與農(nóng)村輿論的宣傳和監(jiān)督下成為農(nóng)村社會(huì)的“共識(shí)”,絕大多數(shù)人都不愿意成為不孝的“另類”。外出務(wù)工的農(nóng)村青年工,經(jīng)過(guò)經(jīng)年的積累,家庭經(jīng)濟(jì)收入穩(wěn)步提高,經(jīng)濟(jì)狀況明顯改善。有了物質(zhì)支撐,他們的家庭價(jià)值觀念開(kāi)始逆轉(zhuǎn),他們身在“流動(dòng)”,心系“家庭”。孝道之“養(yǎng)”和“敬”的觀念在緩緩生長(zhǎng),孝道的地位重又回歸到家庭倫理道德規(guī)范的本位。因?yàn)樾⑹侵袊?guó)家庭養(yǎng)老的內(nèi)在動(dòng)力,其歷經(jīng)數(shù)千年的發(fā)展,已發(fā)展成為廣大人民群眾的心理需求結(jié)構(gòu),成為人們選擇家庭代際關(guān)系模式的基本價(jià)值尺度。
(二)農(nóng)村孝道的階層化與農(nóng)村家庭養(yǎng)老保障
處于不同階層地位的青年農(nóng)民,其經(jīng)濟(jì)收入存在差異,孝道觀念不盡相同,導(dǎo)致了孝道階層化現(xiàn)象的出現(xiàn),這一現(xiàn)象在農(nóng)村社會(huì)已經(jīng)相當(dāng)普遍。處于貧困階層的農(nóng)村青年,像農(nóng)業(yè)勞動(dòng)者、雇工等,主要是以物質(zhì)援助父母為主,他們理解的孝道就是讓老人有飯吃,有衣穿,有房住,但是他們很少顧及到老人的精神需求,或者是對(duì)老人的精神需求視而不見(jiàn)。富裕階層的農(nóng)村青年,如鄉(xiāng)村干部、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管理者、私營(yíng)企業(yè)主等,往往喜歡給老人購(gòu)買高檔生活用品,過(guò)奢侈壽宴,讓老人感到風(fēng)光無(wú)限,以為這樣就是盡了最大的孝道。他們平常忙于賺錢,很少陪老人聊天,基本上不能和老人一起生活,老人的精神需求也很難得到滿足。居于中間階層的農(nóng)村青年,如亦工亦農(nóng)勞動(dòng)者、知識(shí)分子、個(gè)體工商業(yè)主等,他們雖然沒(méi)有充裕的物質(zhì)基礎(chǔ),但也不會(huì)為了生計(jì)問(wèn)題而煩惱,他們注重的往往是“養(yǎng)”和“敬”并舉,既關(guān)注老人的物質(zhì)需求,又盡可能顧及到老人的精神需求。其實(shí),農(nóng)村老人對(duì)養(yǎng)老的要求并不高,只要衣食無(wú)憂,兩代人之間和睦相處,其樂(lè)融融,就是最大的滿足了。中上層農(nóng)村青年的孝道履行方式有著示范和帶動(dòng)作用:一是直接影響了下層農(nóng)村青年的盡孝行為,大家都盡孝,我不能不盡孝;二是喚醒了農(nóng)村各階層青年農(nóng)民的感恩意識(shí),他們?cè)陴B(yǎng)育孩子的過(guò)程中才真正體會(huì)父母養(yǎng)育自己很不容易,想在父母有生之年好好盡孝;三是面子問(wèn)題,不盡孝就等于沒(méi)有面子,很多人不愿意成為沒(méi)有面子的“另類”,不管是在村里也好,還是出去打工也好,都“混”不下去。當(dāng)然有個(gè)別“另類”現(xiàn)象出現(xiàn)也在所難免,但從總體上看,農(nóng)村孝道的主流還是積極健康、蓬勃向上的。 (三)子女分擔(dān)的養(yǎng)老模式與農(nóng)村家庭養(yǎng)老保障
隨著農(nóng)村社會(huì)流動(dòng)的加劇,外出務(wù)工的青年人越來(lái)越多,有的甚至“舉家遷徙”。這種人口流動(dòng)雖然對(duì)農(nóng)村養(yǎng)老產(chǎn)生了一定影響,但是隨著孝道功能的回歸,農(nóng)村青年逐漸意識(shí)到父母的不易,能夠做到心系父母,給予父母物質(zhì)保障和精神慰藉。子女整天和父母生活在一起,難免有些磕磕碰碰,但是如果由子女輪流照顧老人,共同分擔(dān)贍養(yǎng)費(fèi)用,不管從時(shí)間還是空間距離講,都能夠減少不必要的摩擦,減少農(nóng)村青年的養(yǎng)老成本,主要是老人的衣食住行和醫(yī)療費(fèi)用,從而減輕了整個(gè)家庭的經(jīng)濟(jì)負(fù)擔(dān),這深受廣大農(nóng)村青年的歡迎。在廣大農(nóng)村,成年子女對(duì)老年父母的贍養(yǎng),首先是一個(gè)道德問(wèn)題,其次才是一個(gè)法律問(wèn)題。子女分擔(dān)的養(yǎng)老模式強(qiáng)化了子女的養(yǎng)老責(zé)任與養(yǎng)老義務(wù),有助于農(nóng)村孝道的回歸,作為居家養(yǎng)老的重要補(bǔ)充,它延續(xù)了幾千年,在現(xiàn)代社會(huì)也將掀起中國(guó)農(nóng)村養(yǎng)老模式的又一次革新。政府財(cái)政力量有限,對(duì)農(nóng)村老人的補(bǔ)助力度較小,國(guó)家制度化的養(yǎng)老安排已不能真正適應(yīng)農(nóng)村養(yǎng)老的需要,農(nóng)村子女分擔(dān)養(yǎng)老模式的功能極大地凸顯出來(lái)。
(四)老人的自我養(yǎng)老意識(shí)與農(nóng)村家庭養(yǎng)老保障
隨著社會(huì)老年人生活質(zhì)量的不斷提高,老年人不僅有生存問(wèn)題,而且有發(fā)展問(wèn)題,不僅有物質(zhì)生活需求,而且有精神生活需求,老有所養(yǎng)、老有所醫(yī)、老有所學(xué)、老有所為、老有所樂(lè)正在進(jìn)入現(xiàn)代老年生活范疇,養(yǎng)老功能也分解為經(jīng)濟(jì)贍養(yǎng)功能、生活照顧功能、精神慰藉功能等。作為農(nóng)村勞動(dòng)者,大多數(shù)未享受退休養(yǎng)老金,無(wú)論自養(yǎng)還是他養(yǎng)都是家庭、個(gè)人與社會(huì)共同運(yùn)作的。在經(jīng)過(guò)一系列的經(jīng)驗(yàn)和教訓(xùn)之后,農(nóng)村老人開(kāi)始注重自身的安全意識(shí)、獨(dú)立意識(shí)和自強(qiáng)意識(shí)等自我養(yǎng)老意識(shí)的強(qiáng)化,在進(jìn)入老年前或老年后會(huì)進(jìn)行必要的經(jīng)濟(jì)儲(chǔ)備、健康儲(chǔ)備和情感儲(chǔ)備,以預(yù)備應(yīng)對(duì)有可能不期而遇的“風(fēng)險(xiǎn)”,為養(yǎng)老做好準(zhǔn)備,保障晚年充分享受老有所養(yǎng)的權(quán)利。父母與子女之間相互理解,相互尊重,相互親愛(ài)的情感基礎(chǔ)由此產(chǎn)生,有助于傳統(tǒng)孝道的回歸,從而在代際公正的基礎(chǔ)上實(shí)現(xiàn)了家庭內(nèi)部的和諧,有效地解決了農(nóng)村老人的養(yǎng)老保障問(wèn)題。
三、農(nóng)村家庭養(yǎng)老保障的再定位
學(xué)界有關(guān)孝道研究的主流觀點(diǎn)大多只是停留在孝道為什么會(huì)衰落,應(yīng)該采取什么樣的解決對(duì)策這些方面。如聶洪輝、揭新華認(rèn)為,孝道的工具化和家庭的奴化教育,使得孩子缺乏理性精神,結(jié)果,子女在掌握家庭權(quán)力后又走向不孝。必須將平等意識(shí)、協(xié)商精神、參與意識(shí)和權(quán)利意識(shí)引入家庭,將父母對(duì)子女尊重、民主平等作為親子關(guān)系的基本準(zhǔn)則,形成新的家庭文化。誠(chéng)然,1949年以來(lái),農(nóng)村的孝道觀念遭遇了功能錯(cuò)位、功能缺位,經(jīng)歷了一系列波折,但是,已開(kāi)始逐步回歸到家庭倫理道德規(guī)范的本位,最終向著社會(huì)主義新孝道倫理的方向發(fā)展。一直以來(lái),農(nóng)村的家庭養(yǎng)老保障都是我國(guó)多數(shù)農(nóng)民的首選。根據(jù)有關(guān)部門統(tǒng)計(jì),目前,我國(guó)農(nóng)村家庭養(yǎng)老模式仍占養(yǎng)老保障總數(shù)的90%以上。 需要生活上照料的老人95%以上住在家庭,即使是比較富裕的農(nóng)村老人入住養(yǎng)老院,他們?nèi)噪x不開(kāi)家庭,也需要家庭成員生活上的照料和精神上的安慰。這說(shuō)明,很多老人不能接受在養(yǎng)老院終老天年的方式,他們選擇的是在家庭度過(guò)自己的垂暮之年。在物質(zhì)文明發(fā)展到較高階段時(shí),人們更需要精神文明,需要家庭的互助,不僅是經(jīng)濟(jì)上的互助,還需要精神上的慰藉,感情上的交流,生活上的關(guān)心,各方面優(yōu)勢(shì)上的互補(bǔ),親人間內(nèi)心世界的敞開(kāi)和交流。老人隨著年齡的增加,對(duì)家庭的依賴性會(huì)更強(qiáng),他們更渴望得到子孫的尊敬和關(guān)懷。目前,在農(nóng)村,家庭還是基本的生產(chǎn)單位或消費(fèi)單位,家庭養(yǎng)老有助于實(shí)現(xiàn)老有所養(yǎng)、老有所終,滿足每個(gè)家庭成員生活各個(gè)方面的需要,促進(jìn)家庭的和諧與安定。在農(nóng)村積極倡導(dǎo)尊老、敬老、助老的傳統(tǒng)美德,充分發(fā)揮孝道文化在農(nóng)民養(yǎng)老保障中的作用是客觀現(xiàn)實(shí)的必然選擇,家庭養(yǎng)老必然是我國(guó)農(nóng)村當(dāng)前及今后相當(dāng)長(zhǎng)的時(shí)期內(nèi)的主要養(yǎng)老方式,一定會(huì)在農(nóng)村取得良好的成效。
四、余論
孝道之所以能夠歷經(jīng)幾千年流傳至今并在今天仍有強(qiáng)大的生命力,影響著人們的思想行為,是因?yàn)樗谥袊?guó)養(yǎng)老實(shí)踐活動(dòng)中起著基石的作用。養(yǎng)老制度化、法制化正是一個(gè)國(guó)家文明進(jìn)步的重要要求和主要標(biāo)志之一。因?yàn)榉杉扔杏布s束,又有軟約束,它往往要比單純的道德教育更直接、可操作性也更強(qiáng)。家庭保障畢竟是一種非制度化、非社會(huì)化的保障形式,農(nóng)村家庭養(yǎng)老保障要想發(fā)揮更好的作用,當(dāng)然離不開(kāi)國(guó)家政策、法律的保障。國(guó)家應(yīng)該大力提倡宣傳孝道文化,出臺(tái)相關(guān)的法律法規(guī),約束所有子女都不能輕易逃脫養(yǎng)老的責(zé)任,使養(yǎng)老保障真正做到有法可依,讓家庭養(yǎng)老由倫理走向法制,讓法的硬約束為農(nóng)村老年人口提供強(qiáng)有力的外在保障。
實(shí)際上,在許多情況下,人們之所以這樣做而不那樣做,并非出自對(duì)法律的畏懼,而是出自對(duì)同伴輿論的畏懼。在農(nóng)村老人養(yǎng)老問(wèn)題上,離開(kāi)社會(huì)輿論的導(dǎo)向、監(jiān)督和強(qiáng)化作用,很難確保老年人晚年生活的質(zhì)量。要通過(guò)新聞媒體等多種輿論工具,大力宣傳遵循孝道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強(qiáng)化人們尊敬父母的自覺(jué)意識(shí)。我國(guó)75%的老年人集中在鄉(xiāng)村,家庭養(yǎng)老仍是農(nóng)村養(yǎng)老的主要形式。我們要明確家庭養(yǎng)老在農(nóng)村社會(huì)保障制度建設(shè)中的基礎(chǔ)性地位和作用,同時(shí)要在家庭養(yǎng)老文化的視角下,探索多層次的養(yǎng)老保障體系。
作為家庭養(yǎng)老的重要補(bǔ)充,我們應(yīng)在繼續(xù)鼓勵(lì)家庭贍養(yǎng)的基礎(chǔ)上,努力擴(kuò)大社會(huì)養(yǎng)老保險(xiǎn)覆蓋面,逐步建立覆蓋農(nóng)村所有人口的養(yǎng)老保險(xiǎn)體系。走出一條家庭養(yǎng)老和社會(huì)養(yǎng)老互為補(bǔ)充、相互完善的農(nóng)村養(yǎng)老保障之路。農(nóng)民是社會(huì)中的弱勢(shì)群體,農(nóng)村老人更是弱勢(shì)群體中的弱勢(shì)群體,農(nóng)村老年人的權(quán)益應(yīng)當(dāng)?shù)玫匠浞种匾暎r(nóng)村老年人的養(yǎng)老問(wèn)題應(yīng)當(dāng)?shù)玫匠浞直U稀T谵r(nóng)村倡導(dǎo)和建立現(xiàn)代孝道,構(gòu)建融洽的家庭親子關(guān)系與和諧的農(nóng)村社會(huì),從而從根本上推動(dòng)社會(huì)、政治、經(jīng)濟(jì)、文化的的協(xié)調(diào)可持續(xù)發(f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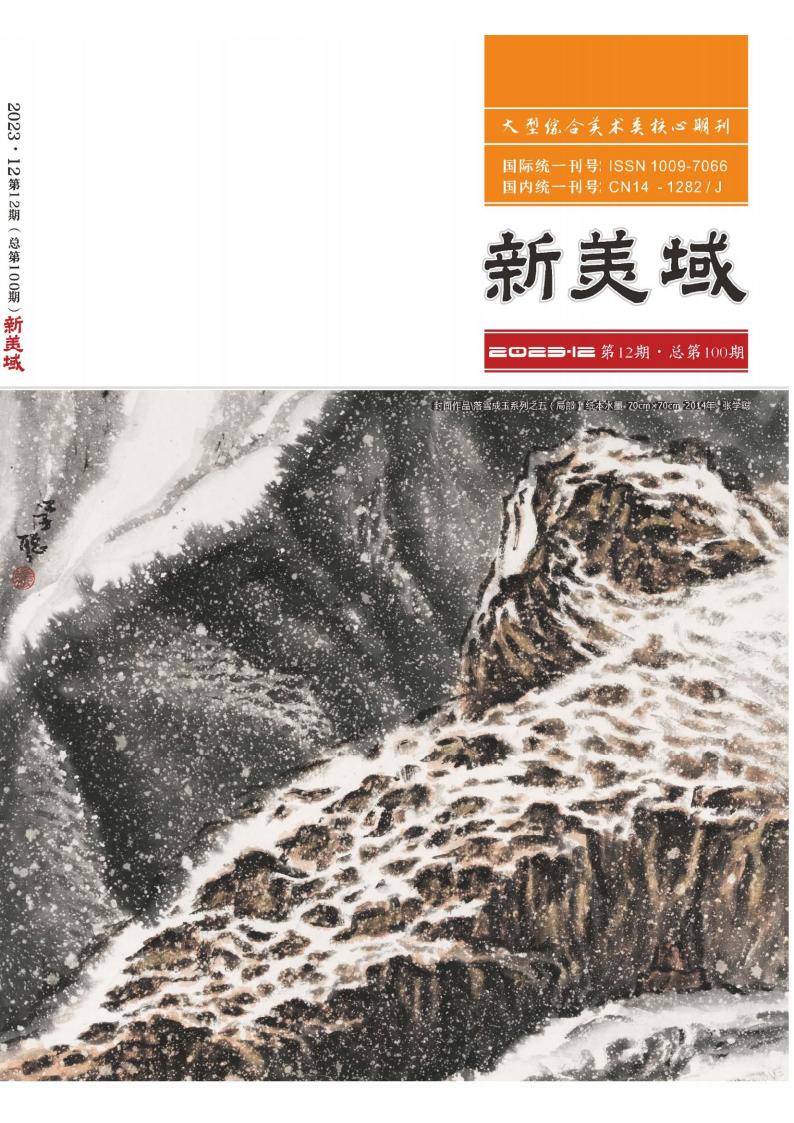
境與人.jpg)
市人民政府公報(bào).jpg)
與光化學(xué).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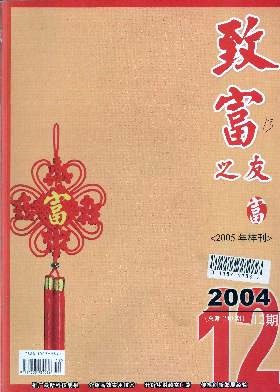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