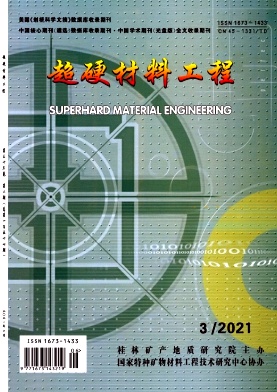法律技術與戶籍制度困局
佚名
提要:我國和戶籍制度有關的是一團亂麻,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以最大的耐心注意的技術。本文提出了對上書全國人大請求對《戶口條例》進行違憲審查這種解決方式的疑問;通過現實中的一些具體事例的,說明戶籍制度所涉及問題在的復雜性和法律技術的重要,表明籠統地談論廢除戶籍制度無法實際上減輕弊端,甚至有適得其反的后果;討論了基于居民和非居民身份的區別待遇、以居民身份或定居期限為享有某些權利前提條件問題的美國案例,也在于說明類似問題在美國的復雜性和法律技術的必要,強調在具體案件中精致的法律概念和運用區別與分類管理的技術;了怎樣逐步消除戶籍制度的僵硬性和弊端。
關鍵詞:法律技術 戶籍制度 中國問題 美國案例
中國的許多不公平和弊端都和戶籍制度有關系。那么一個問題提出來:通過法律手段——立法、司法和《立法法》第90條、91條規定的違憲、違法審查辦法,如何能夠在實際上減輕其弊端。我強調是要減輕弊端,而不是造成新的禍害。本文最初步的發現,我國和戶籍制度有關的問題是一團亂麻,絕不是僅憑人權的抽象道德就可以解決,我們需要以最大的耐心注意法律的技術。
中國的戶籍制度,有狹義、廣義之分。
1958年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通過并以國家主席令形式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該條例以國家法律的形式對戶籍管理的宗旨、戶口登記的范圍、主管戶口登記的機關、戶口簿的作用、戶口申報與注銷、戶口遷移及手續、常住人口與暫住登記等方面都作了明確規定,標志著全國城鄉統一戶籍制度的正式形成。狹義的戶籍制度是指以1958年頒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為核心的限制人口流入城市的規定以及配套的具體措施。廣義的戶籍制度還要加上定量商品糧油供給制度、勞動就業制度、醫療保健制度等輔助性措施,以及在接受、轉業安置、通婚子女落戶等方面又衍生出的許多具體規定。它們構成了一個利益上向城市人口傾斜、包含生活多個領域、措施配套、組織嚴密的體系。政府的許多部門都圍繞這一制度行使職能。
北京某大學教授于2004年的11月9日,上書全國人大,遞交違憲審查建議書(《對二元戶口體制及城鄉二元制度進行違憲審查的建議書》),聲言現行戶籍制度有悖《憲法》。[1]該教授上書全國人大常委會要求進行違憲審查的主要目標就是1958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戶口登記條例》。該《建議書》中指出:《戶口登記條例》第三條、第四條、第十條、第十三條等不僅違背了憲法關于保障公民遷徙自由的條款,而且也涉嫌違背現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戶口登記條例》違反了《憲法》第三十三條規定“凡具有中華人民共和國國籍的人都是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第三十七條“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以及第三十八條、第四十五條、第四十六條等規定”。該教授認為,正是由于二元戶口制度及其附加功能的不斷強化,才導致農民在教育、醫療、社保、稅費、甚至選舉權等方面都受到種種的歧視和不公平對待。最突出的就是在就業和受教育兩方面,如有的城市規定:某些行業和工種必須持有所在城市的戶口才能被錄用;教育方面也是如此,許多持農業戶口者的子女沒有所在城市的戶口,不得不交納一定的借讀費,平等受教育的權利由于“戶籍制度”而失去。
單單從規定本身看,《戶口登記條例》本身僅僅是用來記錄一個人是什么地區的,那么很難談到違憲與否的問題。確實,因為登記條例的存在,可以方便地區別不同地區的居民、農村和城市的居民。但是,一提戶籍制度,就不得不將范圍推廣得非常遙遠,推到無數的法律規則當中去。所謂的戶籍制度在我國是由一系列不同的規則構成的,在各個地方規則又都不相同,我們事實上無法定義什么是戶籍制度——除了在理論上抽象之外。在理論上所進行的抽象和理論判斷并不能直接用在現實當中,不能要求全國人大常委會或法院判斷并認可一種抽象的權利理論和學理論,這既無必要,也和現實問題的解決沒有直接關系。如果說要對這千千萬萬的規則進行法律意義的判斷和審查,那么將是一系列具體的判斷,而不是抽象的判斷。
我們是否要消除一切區別對待?在具體的事例中,我們將發現,公民基于上述區別形成的某些不同對待、享有的不同權利,不能廢除,其存在有合理性。例如,“高考移民”問題;農業戶口同時也意味著農村集體的成員資格,意味著某種財產權利等等。并不是所有對公民的區別對待都是不合理的,比如一個其他城市的居民到本城市來,由于他不給這個城市繳稅,所以當他使用本城所提供的某些公共品時,就要付費,這一點沒有人認為是不公平的;某地給了本地居民一些特殊的優惠,比如美國上州立大學本州居民和他州居民的不同學費比例也是合理的。
要分別考慮各種具體的區別對待,各種具體的區別對待在我國是一種附加的制度,和《戶口登記條例》之間并沒有一種必然的聯系。改革戶籍制度需要解決的不是一個語義分析或者純邏輯的問題,沒有一般的抽象原則可供推理得出結論,這是在充分了解現實情況和不同規則下的社會后果后進行審慎判斷和權衡的問題。審慎的做法是在那些附加的制度當中看看哪些是最不可取的,可以相對平穩地廢除,并且這種廢除和其他規則之間并不產生一種嚴重紊亂的后果。改革戶籍制度需要發展法律技術。
“高考移民”問題
我國實行各省、市、自治區分別進行評卷和劃定高考錄取分數線的政策。部分考生利用各地存在的高考分數線的差異及錄取率的高低,通過轉學或遷移戶口等辦法到高考分數線相對較低、錄取率較高的地區應考,這被稱為“高考移民”。與沿海省份及其他教育發達省份相比,西部省區的高考錄取分數線一般會低幾十分,甚至上百分。因而,每年高考報名時,教育發達地區的許多考生便想方設法移入新疆、西藏、寧夏、青海、貴州、云南等教育欠發達的西部省區應考。這就打破了各省高考原有的政策規定和分省定額錄取的格局,產生了很多新的社會問題。
國家教育部和一些中西部省份均采取了較為嚴厲的措施杜絕“高考移民”現象。教育部在《2003年普通高校招生工作規定》中規定:以虛報、隱瞞或偽造、涂改有關材料取得錄取資格的,應由高校取消其入學資格。海南省曾經規定,考生本人及其法定監護人在本省要有戶籍;考生本人高中階段后兩個學年要在海南就讀;考生本人小學或者初中在海南畢業且畢業時戶籍在本省。另外,考生本人在海南有戶籍且其法定監護人屬駐瓊部隊現役軍人或者屬省人事部門確認引進的優秀人才,也可在海南省報名參加普通高等學校招生。不符合以上條件之一,但戶口在海南的考生限定報考本科第二批和專科(高職)學校。2005年海南省出臺了更嚴苛的《海南省普通高等學校招生報考條件規定》,以“入住三年,讀書三年”為基本要求。吉林、廣西、寧夏、貴州、青海等地也相繼出臺了類似政策。
能否廢除一切對“高考移民”的限制?這個問題卻是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知道了平等受教育權和遷徙自由權的原則,并不意味著在現實中找到了穩妥地減輕弊端的答案。既然我們的高等教育體制還沒有改變,是否可以設想,取消本省和外省戶口的一切區別?如果這么做,會帶來什么樣的后果?
類似的問題古已有之。[2]中國古代(宋、明、清)采取的是鄉試、會試取中名額按地區分配,并禁止“冒籍”行為。例如,康熙五十一年(1712年),以各省取中人數多少不均,邊遠省份或致遺漏,因此廢去南北卷制度,代之以分省取中辦法,按各省應試人數多寡,欽定會試中額。從此,分省定額取士制一直延續到科舉被廢。這項措施的實施是希望通過對錄取名額分配的控制,照顧文化不發達地區,平衡地區利益。各地區有固定的取中名額,這就使得教育發達地區的考生向邊遠地區流動,導致了“冒籍”現象的產生。明清兩代,“冒籍”問題尤為嚴重。明清兩代對“冒籍”問題的解決對策一般是根據戶籍限制其報考,一旦發現有“冒籍”行為,即對當事人及相關人員進行懲處。考試公平與區域公平的矛盾(即古代傾斜的“高考分數線”問題),是一個自宋代以后就爭論不休的千古難題。考試公平是指完全依據考試成績來公平錄取考生,區域公平是指通過區域配額來調控各地區之間考中人數的懸殊差異,在中國這么一個幅員遼闊、人口眾多的大國,這是一個古今大規模考試都會遇到的棘手問題。本文不能夠提出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只能說這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需要平衡兩種平等原則在具體實踐中的沖突,需要考慮到國家的穩定和整合(古代云、桂、黔無人中進士,今天青、新、藏無人考到北京來上北大、清華,都是或會引發這些問題)。
農業戶口與財產權資格
“農轉非”在上個世紀計劃經濟年代曾經是農民可望不可及的夢想。一出農門便身價倍增,農民們通俗地把農轉非、吃商品糧稱為“吃國家糧”。到上世紀80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期,我國不少地方出現“農業人口轉非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