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guó)傳統(tǒng)建筑的文化反思
葉廷芳
世界上的建筑(這里主要指大型的、屬于藝術(shù)范疇的公共性建筑),從形式上劃分,基本上有兩類:一類主要用石頭建造的,叫“石構(gòu)建筑”,流行于世界絕大多數(shù)地區(qū);一類主要用木頭建造的,叫“木構(gòu)建筑”,流行范圍很小,主要以中國(guó)為主的東亞地區(qū)。兩種形式的建筑各自都有深厚的文化淵源,各有不同的風(fēng)格和藝術(shù)特色。就藝術(shù)而言,各有不同的價(jià)值觀和審美取向,很難分出高低。這篇演講,僅從反思的角度,著重談?wù)勎覀兊慕ㄖ幕心切┲萍s著我們發(fā)展的、值得我們認(rèn)真思考和克服的負(fù)面現(xiàn)象。
縱向承襲的慣性思維中國(guó)人總習(xí)慣于“摸前有”,而西方人則善于“探未知”。兩種不同的文化心態(tài)導(dǎo)致兩種不同的結(jié)果:一個(gè)不斷重復(fù)前人,不思突破;一個(gè)則不斷推陳出新,向前跨越。
我們的木構(gòu)建筑至少已有兩千多年的歷史,那“覆壓三百里”的阿房宮可資證明。在這漫長(zhǎng)的過(guò)程中,從形式到風(fēng)格都只是單一的發(fā)展,沒(méi)有發(fā)生過(guò)質(zhì)的變化,可謂“兩千年一貫制”。而歐洲人的石構(gòu)建筑,僅自古希臘羅馬時(shí)期開(kāi)始,其風(fēng)格上的更新?lián)Q代至少在一打以上:古希臘風(fēng)格、古羅馬風(fēng)格、拜占庭風(fēng)格、羅馬風(fēng)格、哥特風(fēng)格、文藝復(fù)興風(fēng)格、矯飾風(fēng)格、巴洛克風(fēng)格、古典主義風(fēng)格、浪漫主義風(fēng)格、折中主義風(fēng)格、現(xiàn)代主義風(fēng)格、“后現(xiàn)代”風(fēng)格……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之一恐怕是:我們習(xí)慣于承襲思維,總愛(ài)向前人看齊;以前人的水平為坐標(biāo),以前人的成就為榮耀。而歐洲人就不是這樣,他們不管前人有多大成就,也不高山仰止,而設(shè)法超越他們,努力向前探索。正如魯迅當(dāng)年所概括的:我們中國(guó)人總習(xí)慣于“摸前有”,而西方人則善于“探未知”。兩種不同的文化心態(tài)導(dǎo)致兩種不同的結(jié)果:一個(gè)不斷重復(fù)前人,不思突破;一個(gè)則不斷推陳出新,向前跨越。
縱向承襲思維近年來(lái)的一個(gè)突出例子表現(xiàn)在,到處熱衷于搞仿古建筑,其中“重修圓明園”的呼聲堪稱其最高音響。說(shuō)是為了“再現(xiàn)昔日造園藝術(shù)的輝煌”,殊不知,美是不可重復(fù)的!若是可以重復(fù),則今天世界上的藝術(shù)品早就沒(méi)有地方可堆了。何況圓明園是極為重要的國(guó)恥紀(jì)念地,是入侵強(qiáng)盜的“作案現(xiàn)場(chǎng)”,重修意味著對(duì)“現(xiàn)場(chǎng)”也就是對(duì)文物的破壞。
建筑作為藝術(shù)的一門和審美的載體,它的生命在于不斷創(chuàng)新,因?yàn)槿说膶徝酪庾R(shí)是不斷變遷的,而且這也是歷史發(fā)展的客觀要求。
從19世紀(jì)下半葉起,從世界范圍看,隨著生產(chǎn)力的發(fā)展,新的建筑學(xué)理論和新的建筑材料的誕生,建筑開(kāi)始了一場(chǎng)嶄新的革命。中國(guó)的木構(gòu)建筑作為農(nóng)耕時(shí)代的產(chǎn)物,也已走完了它的歷史進(jìn)程,面臨著蛻變。然而,中國(guó)歷史的發(fā)展,整個(gè)兒講就慢了西方一大拍,即少了一個(gè)工業(yè)時(shí)代。西方思潮作為強(qiáng)勢(shì)文化迅猛地涌入我國(guó)。這意味著,客觀形勢(shì)已不允許中國(guó)建筑從自己的娘胎里孕育出自己民族的建筑新胚胎,我們一邊招架,一邊接受;來(lái)不及細(xì)嚼,難免囫圇吞棗,就是說(shuō):簡(jiǎn)單仿效。這在開(kāi)始階段是不可避免的,對(duì)于異域的人類文明成果,先要“拿來(lái)”,而后才能進(jìn)行鑒別、挑選和借鑒。但如果一味“拿來(lái)”,或“拿”的時(shí)間過(guò)長(zhǎng),這就值得注意了。吸收別人的長(zhǎng)處,畢竟不能代替自己的創(chuàng)造。學(xué)別人,如果只學(xué)其表面,即形式和風(fēng)格,而不學(xué)其本質(zhì),即創(chuàng)造精神,那就是舍本逐末了。整個(gè)20世紀(jì)我們?cè)诳傮w上就未能跳出西方建筑的窠臼,既沒(méi)有創(chuàng)造出屬于我們自己民族個(gè)性的東西,也沒(méi)有在世界新思潮中取得令人矚目的地位。結(jié)果,到世紀(jì)末一看,缺少自己的東西,沒(méi)有進(jìn)行必要的反思,馬上又求助于老祖宗,把前人留下的那些遺產(chǎn),即把“大屋頂”風(fēng)格當(dāng)作中華民族永恒不變的建筑美學(xué)法則和藝術(shù)模式,到處用鋼筋水泥搞復(fù)古。
應(yīng)該說(shuō),作為民族遺產(chǎn),適當(dāng)?shù)亍⒃鷮?shí)實(shí)地重建一點(diǎn)古建筑是無(wú)可厚非的,但鋪天蓋地的搞,甚至借“弘揚(yáng)”之名,“一窩蜂”地大貼“古建符號(hào)”,就有違歷史規(guī)律了。
技術(shù)傳授的滯后性師傅教給徒弟的除了與建筑直接相關(guān)的純技術(shù)知識(shí)外,一般沒(méi)有相關(guān)的科學(xué)常識(shí)和必要的基礎(chǔ)理論知識(shí)。這樣學(xué)出來(lái)的徒弟只能算是個(gè)懂技術(shù)的匠人,而不可能是個(gè)有文化的“知識(shí)分子”或建筑藝術(shù)家。
正如公元前四世紀(jì)希臘人亞里士多德在總結(jié)古希臘戲劇(悲劇和喜劇)的基礎(chǔ)上成為雄踞歐洲兩千年的理論泰斗一樣,羅馬人早在公元前一世紀(jì)就有了維特魯威的《十建筑書(shū)》,它不僅在希臘羅馬豐富的建筑實(shí)踐基礎(chǔ)上,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建筑技術(shù)和藝術(shù)作了詳盡的記載,而且作了理論提升,成為世界上第一部較完備的建筑理論著作。文藝復(fù)興時(shí)期,歐洲人又有了帕拉提奧的《建筑四書(shū)》,阿爾伯蒂的《論建筑》(又稱《建筑十篇》),維尼奧垃的《五種柱式規(guī)范》等。它們根據(jù)歐洲建筑的發(fā)展,從不同方面,在不同程度上對(duì)歐洲建筑理論作了認(rèn)真而詳盡的梳理和闡發(fā),對(duì)爾后的歐美建筑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至于現(xiàn)代和“后現(xiàn)代”他們也有多種經(jīng)典性理論著作廣泛流傳。
相比之下,作為木構(gòu)建筑水平最高、經(jīng)驗(yàn)最豐富的國(guó)家,我們?cè)谶@方面的建樹(shù)就要遜色得多。直到漢代我們才有了一部屬于政策、法規(guī)一類的《考工記》。之后過(guò)了上千年,到五代至北宋才有了一部《木經(jīng)》,元代有過(guò)《經(jīng)世大典》和《梓人遺制》,但都不完備,而且多半失傳。比較完整的是宋代李誡寫的《營(yíng)造法式》和清代的《工部工程做法則例》,這是我國(guó)建筑遺產(chǎn)的精華,尤其是前者。但它們都著重在建筑材料、施工技術(shù)和管理方面的記述,理論升華和美學(xué)探索仍很缺乏。
西方建筑的美學(xué)觀念一直以來(lái)都是建筑在造型和裝飾基礎(chǔ)上的。隨著新的建筑材料如鋼筋、水泥、玻璃等的誕生,在現(xiàn)代主義建筑思潮中人們拋棄了這一傳統(tǒng),轉(zhuǎn)向?qū)Y(jié)構(gòu)的重視。這時(shí)許多人發(fā)現(xiàn)中國(guó)建筑的長(zhǎng)處,因?yàn)橹袊?guó)建筑的藝術(shù)奧妙和美學(xué)特征主要就體現(xiàn)在結(jié)構(gòu)上。作為現(xiàn)代建筑扛鼎人物之一的美國(guó)建筑師賴特就曾對(duì)中國(guó)建筑大加贊賞。可惜我們自己很少有人發(fā)現(xiàn)這一契機(jī)。只有梁思成看到了中國(guó)傳統(tǒng)建筑與西方現(xiàn)代建筑之間的這一機(jī)緣。可是由于眾所周知的原因,他的宏圖悲劇性地落了空。
知識(shí)的更新與進(jìn)步,技術(shù)的提高與發(fā)展都需要合適的環(huán)境,至少要有信息傳遞和交流的渠道。知識(shí)的傳授與人才的培養(yǎng)尤其需要這樣的條件。古羅馬建筑的發(fā)達(dá)跟它在這方面的領(lǐng)先很有關(guān)系。他們?cè)缭诠兰o(jì)就有了建筑工程技術(shù)學(xué)校,開(kāi)始以集群和規(guī)模的方式培養(yǎng)人才。然而我國(guó)歷代的人才培養(yǎng)主要是通過(guò)師徒相授或家族傳授的途徑。這種方式的狹隘性與局限性是顯而易見(jiàn)的:沒(méi)有橫向聯(lián)系,缺乏信息交流;容易坐井觀天,難有競(jìng)爭(zhēng)雄心;看不到差距,少有抱負(fù);即便是恩師,最后還要留一手“絕招”,以防后生搶了自己的飯碗。在這種封閉的條件下,很難出得了人才。即使是天才,恐怕也難成氣候。因?yàn)橐曇蔼M小,心理封閉,很難獲得奇想的靈感。即使獲得這種靈感,也很難拿出推陳出新的勇氣,因?yàn)閹煾狄话悴辉S徒弟越雷池半步,更不愿看到他超越自己。為什么我國(guó)的建筑藝術(shù)和建筑風(fēng)格始終不能更新?lián)Q代,而只能在原來(lái)的基礎(chǔ)上作漸進(jìn)式的改進(jìn)和提高?我想這與我們的人才培養(yǎng)方式有很大關(guān)系。
這種傳授方式還決定著傳授內(nèi)容的片面性與有限性:師傅教給徒弟的除了與建筑直接相關(guān)的純技術(shù)知識(shí)外,一般沒(méi)有相關(guān)的科學(xué)常識(shí)和必要的基礎(chǔ)理論知識(shí)。這樣學(xué)出來(lái)的徒弟只能算是個(gè)懂技術(shù)的匠人,而不可能是個(gè)有文化的“知識(shí)分子”或建筑藝術(shù)家。我國(guó)歷史上的人才制度從根本上說(shuō)是一種培養(yǎng)官僚的制度,即所謂“學(xué)而優(yōu)則仕”,只有走仕途,才能有出息,有前途。學(xué)技術(shù)到頭來(lái)還是個(gè)體力勞動(dòng)者,是匠人,是“工匠”,而不是建筑工程師或建筑藝術(shù)家。須知,匠人的習(xí)性是重復(fù),藝術(shù)家的天性則是創(chuàng)造!不難想象,這種教育制度決定了我國(guó)建筑學(xué)的命運(yùn)。它使我國(guó)的建筑的形式和風(fēng)格陳陳相因,代代相傳,長(zhǎng)期停留在單一的局面,形成了一種“超穩(wěn)定結(jié)構(gòu)”。
忽視建筑的藝術(shù)屬性從建筑師的地位與影響來(lái)看,我們的古代建筑師不管成就多大,一律被置于“工匠”地位,因而被載入史冊(cè)的很少,能被老百姓叫出名字來(lái)的更少。
建筑自從擺脫了遮風(fēng)避雨這一最基本的原始功能以后,它就與美學(xué)結(jié)下了不解之緣。在保證功能需要的前提下,如何把房屋蓋得更好看,成為建筑師的主要追求。建筑美學(xué)的基本特征就表現(xiàn)在技術(shù)與藝術(shù)的結(jié)合。因此建筑的藝術(shù)屬性在國(guó)際上早已形成公論。在歐洲,“藝術(shù)”或“美術(shù)”這一概念向來(lái)就包括繪畫、雕塑、建筑這三大門類。然而中國(guó)古代始終把建筑排除在藝術(shù)之外,直到現(xiàn)在仍有不少人甚至包括少數(shù)建筑師持這種觀點(diǎn)。
建筑的藝術(shù)屬性至少包括下列五個(gè)方面:建筑具有韻律的美。它既是空間的藝術(shù),又是時(shí)間的藝術(shù),故被譽(yù)為“凝固的音樂(lè)”。建筑具有雕塑的美。這不僅表現(xiàn)在建筑物所附屬的那豐富的浮雕和雕塑陳列品,就是建筑物本身的輪廓和造型也具有這種雕塑的特性,有其獨(dú)立的審美價(jià)值。建筑具有結(jié)構(gòu)的美。建筑的美不僅表現(xiàn)在外部造型,而且也表現(xiàn)在內(nèi)部空間。在這里,力學(xué)與美學(xué)難解難分。建筑具有裝飾的美。建筑物的裝飾猶如人的服飾。“人恃衣裳馬恃鞍”,建筑亦然。建筑具有詩(shī)意的美。這主要體現(xiàn)在建筑與環(huán)境的關(guān)系中。海德格爾那句所謂“詩(shī)意的棲居”幾乎成了“后現(xiàn)代”建筑的座右銘。
建筑的以上藝術(shù)屬性古今中外皆然,只是程度不同而已。問(wèn)題在于,兩千多年來(lái),我們的建筑只對(duì)一種形式和風(fēng)格進(jìn)行了追求,并使之達(dá)到極致。但在這方面所表現(xiàn)出的毅力和所投入的智慧總量而言,我們是不如西方人的。
首先,從建筑物所投入的時(shí)間和力量來(lái)看,我們的大型建筑在古代一般只花幾年、十幾年,而人家一般須花幾十年,甚至幾百年。其中有名的如圣。彼得大教堂前后花了121年;巴黎圣母院經(jīng)歷了139年;科倫大教堂甚至斷斷續(xù)續(xù)搞了600余年!現(xiàn)代人高迪設(shè)計(jì)的巴塞羅那圣家族教堂已經(jīng)123年了,至今仍與腳手架相伴。即以最近落成的歐洲首屈一指的柏林火車站來(lái)看,以德國(guó)的經(jīng)濟(jì)和技術(shù)力量,竟然用了11年!
其次,從建筑師的地位與影響來(lái)看,我們的古代建筑師不管成就多大,一律被置于“工匠”地位,因而被載入史冊(cè)的很少,能被老百姓叫出名字來(lái)的更少。而歐洲的老百姓,誰(shuí)不知道米開(kāi)朗基羅、貝爾尼尼、辛克爾、賴特、格羅皮烏斯……這些如雷貫耳的名字?我國(guó)20年前自己編寫的《中國(guó)大百科全書(shū)》被單獨(dú)列為詞條的中國(guó)建筑師一共只有16名,其中古代的占8名。這8名中,只有1名有生卒年,2名只有生年,而無(wú)卒年。可這兩人分別是我國(guó)重要建筑理論著作《營(yíng)造法式》和《木經(jīng)》的作者!另5名生卒年都不詳!而這5人中多數(shù)都是明清時(shí)期的。而中國(guó)古代文學(xué)家被單獨(dú)列為詞條的約有1050余位;中國(guó)古代美術(shù)家被單獨(dú)收入的也有300多位。
第三,從建筑理論的總結(jié)、建設(shè)與影響來(lái)看,如前所述,西方是領(lǐng)先于我們的。
第四,從統(tǒng)治者的意向來(lái)看,從來(lái)都是強(qiáng)調(diào)功能而忽視藝術(shù)。我國(guó)的帝王們?yōu)榱藱?quán)力和享受需要宏大的宮殿和豪華的園林,但對(duì)建筑本身,幾乎沒(méi)有人表現(xiàn)出特別的興趣,不像外國(guó)的君主們常常以建筑為尚、為榮。古羅馬皇帝奧古斯都曾自豪地說(shuō):“我接手的是磚頭的羅馬,我留下的是大理石的羅馬”。至于法國(guó)凡爾賽宮的首建者路易十四對(duì)于建筑的追求更是殫精竭慮。這一傳統(tǒng)在當(dāng)代的蓬皮杜、密特朗等法國(guó)總統(tǒng)身上依然可見(jiàn)。
第五,從宗教建筑與世俗建筑的比較看,在西方,最輝煌、藝術(shù)成就最高的建筑是教堂和廟宇,而在中國(guó),最輝煌的建筑卻是皇宮和皇陵。耐人尋味的是,世界上凡是供人享受的皇家建筑遠(yuǎn)遠(yuǎn)超過(guò)供神使用的宗教建筑的國(guó)家,后來(lái)都衰落了。
值得反思的“墻”文化我們幾乎歷朝歷代都在筑墻,我們一直以來(lái)都在“防”,到頭來(lái)卻是防不勝防。
自奴隸制時(shí)代起,中國(guó)統(tǒng)治者那種君臨一切的自我意識(shí)就是非常強(qiáng)的。這種無(wú)上至尊的威權(quán)需要一種象征,這象征需要一種載體,最好的載體莫過(guò)于建筑了。正如漢初奉命建造未央宮的蕭何所說(shuō):“天子以四海為家,非壯麗無(wú)以重威。”于是我們有了世界上最宏偉的宮殿,最壯觀的陵墓。而老百姓的房屋則是一片低矮和灰暗。這種巨大的反差,必然要在國(guó)民的心理上造成負(fù)面影響,即壓抑感和窒息感。近年來(lái)許多地方的政府大樓蓋得越來(lái)越輝煌,而且往往占據(jù)城市的“制高點(diǎn)”,讓老百姓望而生畏,這種狀況值得反思。
中國(guó)的墻之多為世界之最。你看:國(guó)家有萬(wàn)里長(zhǎng)城,城市有城墻,單位有圍墻,家庭有四合院,現(xiàn)在甚至發(fā)展到幾乎每家每戶都有防盜門。如此層層包圍,不能不說(shuō)是一種世界奇觀。與“墻”相聯(lián)系的是“門”。我們的建筑物的門表面看起來(lái)固然不算少,但能讓你走的門是極少的。究其理由,都說(shuō)“為了管理方便”,而不是“為了群眾方便”。這是“官本位”與“民本位”的顛倒。
這種以“防”為特征的“墻文化”的負(fù)面效應(yīng)是顯而易見(jiàn)的:其一,反映了中國(guó)歷代統(tǒng)治者“一勞永逸”的茍安思想。他們?yōu)榱耸朗来舶卜€(wěn)穩(wěn)地“坐江山”,不惜一切代價(jià),不顧人民死活,動(dòng)輒進(jìn)行浩大工程,一味進(jìn)行物質(zhì)上的消極防御,而不是從精神上培養(yǎng)人民的反抗意識(shí)和斗爭(zhēng)意志,進(jìn)行積極自衛(wèi)。
其二,造成國(guó)民心理的單純防守性。我們幾乎歷朝歷代都在筑墻,我們一直以來(lái)都在“防”,到頭來(lái)卻是防不勝防:想打進(jìn)來(lái)的都打進(jìn)來(lái)了。一種見(jiàn)兇就躲的國(guó)民,再堅(jiān)固的防衛(wèi)墻、防盜門、防盜欄,能從根本上解決問(wèn)題嗎?
其三,造成國(guó)民心理的自我封閉性。我們世世代代被無(wú)數(shù)的墻團(tuán)團(tuán)圍住,眼界越來(lái)越狹小,以致坐井觀天,夜郎自大,自以為處于世界的“中央之國(guó)”,盲目排外。封閉的環(huán)境不便橫向聯(lián)系,可使老百姓消息閉塞,安分守己,不易接受外來(lái)的“危險(xiǎn)思想”。封閉的環(huán)境可以造成封閉的心理,而封閉的心理有利于養(yǎng)成對(duì)統(tǒng)治者的馴服習(xí)慣,有利于適應(yīng)封建主義輕易而穩(wěn)固的統(tǒng)治。
盡管如此,我們還是要將勞民傷財(cái)建造的“墻”與作為歷史文物的“墻”加以區(qū)分。動(dòng)用巨大的人力物力去建造規(guī)模宏大的國(guó)墻、城墻,盡管在軍事上也許能起一時(shí)的防御作用,但對(duì)當(dāng)時(shí)的生產(chǎn)力發(fā)展無(wú)疑是一種阻礙或抑制。而從實(shí)踐過(guò)程看,所有的墻最終都未能起到城防、國(guó)防的根本作用。但作為古代中國(guó)人的一種思維方式和行為過(guò)程,這些“墻”卻是一種極為重要的歷史證物,它確鑿地證明中國(guó)人在意志和力量上能夠做到什么。因此,對(duì)于這些遺產(chǎn),我們應(yīng)該作為國(guó)寶予以充分的尊重和珍視。這是祖先們用無(wú)比巨大的血汗代價(jià)換來(lái)的啊。
走出“繼承傳統(tǒng)”的誤區(qū)“繼承”成為抵制革新的擋箭牌,尤其抗拒“反傳統(tǒng)”的要求和努力。殊不知,反傳統(tǒng)是藝術(shù)革新的推進(jìn)器。
由于“縱向承襲”的思維慣性,“繼承傳統(tǒng)”或“弘揚(yáng)傳統(tǒng)”的口號(hào)在我們這里頻率特別高,幾乎與當(dāng)年西方人“反傳統(tǒng)”的口號(hào)同樣響亮。問(wèn)題是,傳統(tǒng)具有兩重性,既有積極的、正面的部分,又有消極的、負(fù)面的部分。而有些人由于“過(guò)去”的情結(jié)過(guò)重,繼承的背后往往掩蓋著負(fù)面的東西。表現(xiàn)在建筑方面的主要是:“繼承”成為對(duì)前人的形式和風(fēng)格的單純模仿和重復(fù)。近20余年來(lái),大量仿古建筑的出現(xiàn)就是有力的說(shuō)明。這種“西裝加瓜皮帽”的“假古董”,使我們的許多城鎮(zhèn)變得不倫不類,變成一堆堆充斥著“建筑垃圾”的大雜燴。
“繼承”成為抵制革新的擋箭牌,尤其抗拒“反傳統(tǒng)”的要求和努力。殊不知,反傳統(tǒng)是藝術(shù)革新的推進(jìn)器。反傳統(tǒng)的人并不是不要傳統(tǒng),他只是不想重復(fù)前人有過(guò)的東西而已。魯迅就是一個(gè)既善于繼承傳統(tǒng),又敢于反對(duì)傳統(tǒng)的“大呼猛進(jìn)”的偉大斗士。
繼承傳統(tǒng)的實(shí)質(zhì)是學(xué)習(xí)前人的創(chuàng)造精神。凡是具有現(xiàn)代意識(shí)的藝術(shù)家都以重復(fù)為恥:即既不重復(fù)前人的,也不重復(fù)他人的,甚至也不重復(fù)自己的。因?yàn)椤澳7履耸亲顩](méi)有出息的文學(xué)教條主義和藝術(shù)教條主義”(毛澤東)。藝術(shù)貴在原創(chuàng),而原創(chuàng)都是一次性的。
總之,無(wú)論是繼承傳統(tǒng),還是反傳統(tǒng),其結(jié)果都應(yīng)該是發(fā)展并豐富傳統(tǒng),進(jìn)而推進(jìn)今天的建筑事業(yè)更快更好地發(fā)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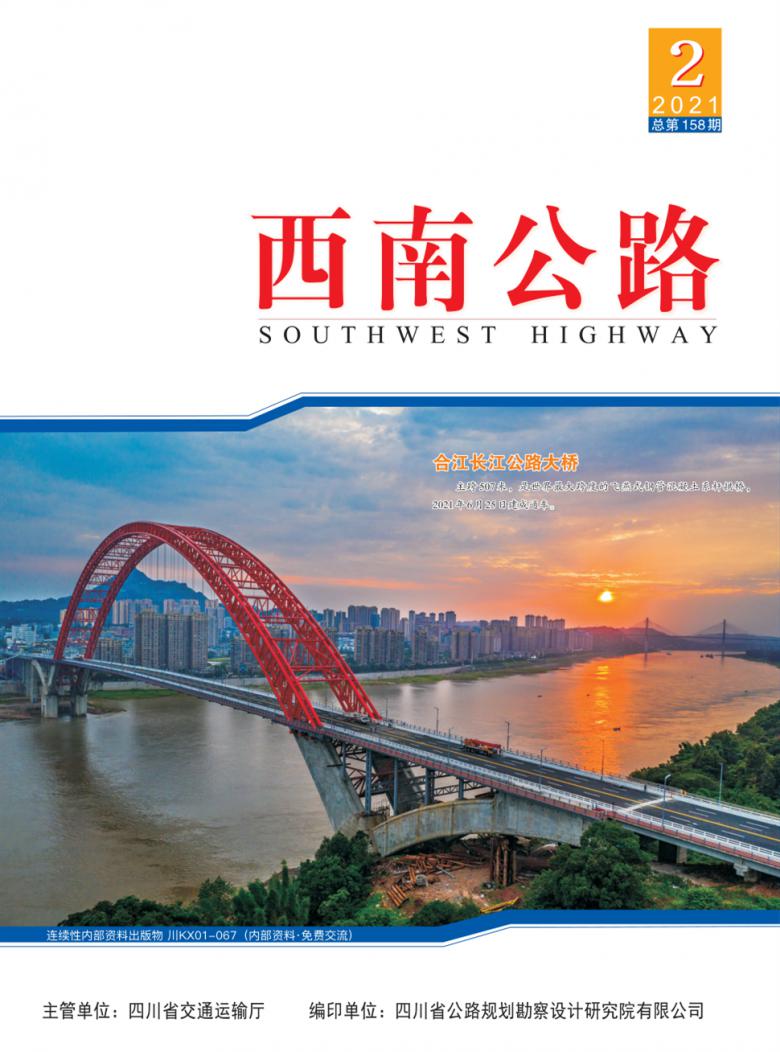
微生物.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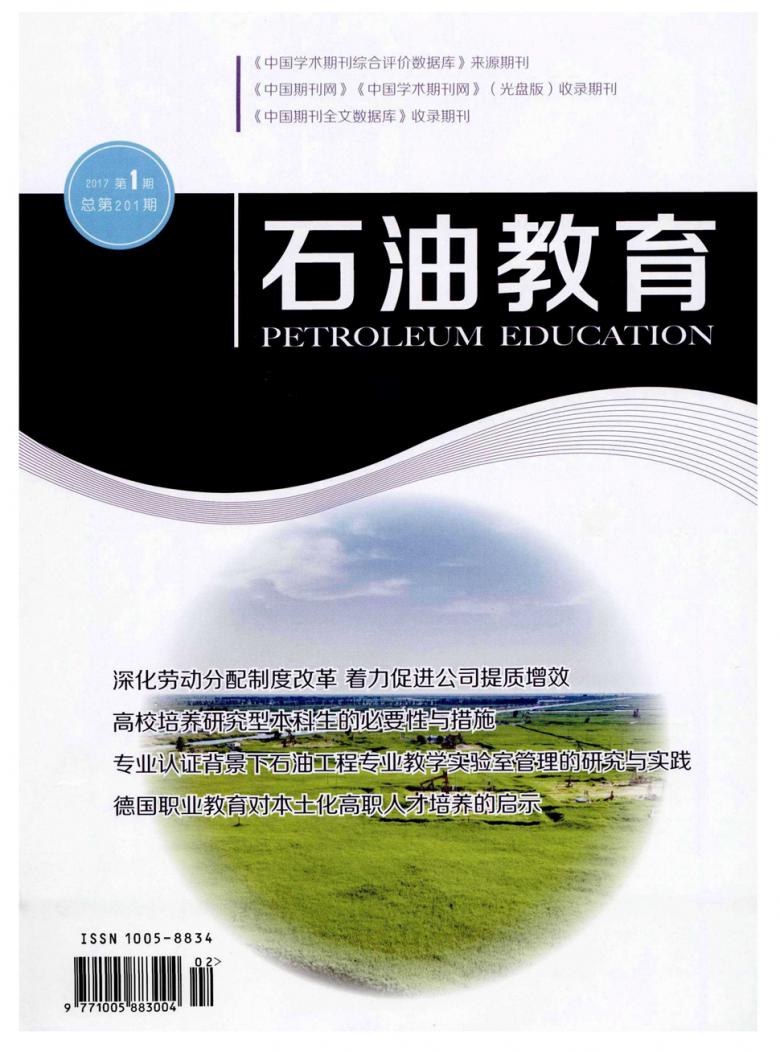
濟(jì)研究.jpg)
學(xué)報(bào).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