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較優(yōu)勢(shì)理論和產(chǎn)業(yè)發(fā)展戰(zhàn)略
本站會(huì)員
靜態(tài)比較優(yōu)勢(shì)和動(dòng)態(tài)比較優(yōu)勢(shì)
關(guān)于對(duì)外開放和我國(guó)產(chǎn)業(yè)發(fā)展的關(guān)系問題,目前理論界明顯存在著兩種不同傾向性意見。對(duì)此筆者大體歸納如下:
第一種意見認(rèn)為,應(yīng)充分發(fā)揮我國(guó)勞動(dòng)密集型產(chǎn)業(yè)的比較優(yōu)勢(shì),融入國(guó)際分工體系,以解決就業(yè)問題;要盡可能利用外資,學(xué)習(xí)國(guó)外先進(jìn)技術(shù)和管理技術(shù);民族產(chǎn)業(yè)是次要問題,只要在中國(guó)土地上生產(chǎn)、納稅、增加就業(yè)既可;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優(yōu)化問題應(yīng)主要由市場(chǎng)決定,主張搞“產(chǎn)業(yè)政策”是沿襲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思路。
第二種意見:強(qiáng)調(diào)在開放條件下保持民族經(jīng)濟(jì)獨(dú)立性;主張適度開放,吸引外商投資也要適度,注重經(jīng)濟(jì)(產(chǎn)業(yè))安全;需要國(guó)家實(shí)施積極的產(chǎn)業(yè)政策;有必要在戰(zhàn)略性產(chǎn)業(yè)領(lǐng)域中爭(zhēng)取趕超。
上面兩種不同傾向,實(shí)際上隱含著對(duì)國(guó)際環(huán)境、國(guó)家發(fā)展戰(zhàn)略、經(jīng)濟(jì)體制改革中政府和市場(chǎng)的作用等等一系列問題的判斷的分歧。
筆者的基本觀點(diǎn)是:我們必須堅(jiān)持改革開放的方向,因?yàn)榻裉靽?guó)有企業(yè)和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很多問題,根源還在于舊體制改革不徹底和新的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秩序沒有完善。但對(duì)在國(guó)際競(jìng)爭(zhēng)面前要不要堅(jiān)持自己的產(chǎn)業(yè)獨(dú)立性、要不要保護(hù)和扶持民族戰(zhàn)略產(chǎn)業(yè)的問題上,筆者不能同意第一種意見。
很多文章傾向于用“全球化”、自由貿(mào)易代替經(jīng)濟(jì)發(fā)展,好像只要“放開”搞自由貿(mào)易、按比較優(yōu)勢(shì)論辦事,發(fā)展中國(guó)家就能走上健康發(fā)展之路,好像這就是發(fā)展戰(zhàn)略的核心。而貿(mào)易保護(hù)、產(chǎn)業(yè)發(fā)展政策,都是“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余毒”,是保護(hù)落后。
我們應(yīng)該承認(rèn),自由貿(mào)易和比較優(yōu)勢(shì)原則,有相當(dāng)大的合理性,在很大程度上,對(duì)后進(jìn)國(guó)家的發(fā)展有指導(dǎo)意義。但是這個(gè)理論的缺點(diǎn)是“孤立地、靜止地、片面地”對(duì)待發(fā)達(dá)——不發(fā)達(dá)經(jīng)濟(jì)之間的分工問題,所以是“靜態(tài)的比較優(yōu)勢(shì)”理論。它解決不了長(zhǎng)期經(jīng)濟(jì)發(fā)展問題(比如說,解釋不了為什么日本韓國(guó)的高科技產(chǎn)業(yè)發(fā)展這么快)。靜態(tài)比較優(yōu)勢(shì)論實(shí)際上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理論武器。按照這個(gè)理論,在全球化條件下,后進(jìn)國(guó)家就沒有追趕和后來居上的可能,只能宿命地被動(dòng)服從于“客觀規(guī)律”,即現(xiàn)有的世界分工格局。
工業(yè)化的拉美式道路和日韓式道路
汽車工業(yè)界有人提出:世界各后進(jìn)國(guó)家發(fā)展汽車工業(yè),有“拉美式”和“日韓式”兩條路線。實(shí)際上這可以推廣到整個(gè)工業(yè)政策。在全球化條件下,后進(jìn)國(guó)家的產(chǎn)業(yè)發(fā)展有兩種可選擇的道路:拉美道路和日韓道路。
拉美道路的特點(diǎn),就是敞開大門,鼓勵(lì)各跨國(guó)公司進(jìn)來合資合作、設(shè)廠競(jìng)爭(zhēng),不追求“民族汽車品牌”。而“日韓式”則強(qiáng)調(diào)國(guó)家發(fā)展自主汽車工業(yè)(自主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自有品牌),不傾向于合資,高度重視引進(jìn)消化,重視自有品牌。為保護(hù)自己的汽車工業(yè)不惜搞市場(chǎng)壁壘,通過與跨國(guó)公司合作打入國(guó)際市場(chǎng)。
拉美式道路,是遵循“國(guó)際自由競(jìng)爭(zhēng)”和“比較優(yōu)勢(shì)”論的、政府放任自由的產(chǎn)業(yè)發(fā)展道路。“日韓式”道路是政府強(qiáng)烈干預(yù)市場(chǎng)的(國(guó)家確定產(chǎn)業(yè)發(fā)展目標(biāo)、實(shí)行市場(chǎng)保護(hù)和傾斜支持)發(fā)展道路。
拉美式道路證明,出讓國(guó)內(nèi)市場(chǎng),換取國(guó)際投資,可以增進(jìn)居民福利,可以節(jié)省技術(shù)研發(fā)耗費(fèi),減少投資風(fēng)險(xiǎn)和市場(chǎng)風(fēng)險(xiǎn)。其代價(jià)是阻礙了自己的技術(shù)研發(fā)和創(chuàng)立品牌的前景,本國(guó)的汽車產(chǎn)業(yè)和汽車市場(chǎng)被跨國(guó)公司所控制,成為依附型產(chǎn)業(yè)。
日韓式的發(fā)展道路,要付出購(gòu)買、消化技術(shù)的金錢和努力,要冒技術(shù)引進(jìn)失敗或消化不力、掉進(jìn)“引進(jìn)陷阱”的風(fēng)險(xiǎn)。但這是不受外國(guó)資本控制、發(fā)展中國(guó)家振興民族產(chǎn)業(yè)、縮小與國(guó)際先進(jìn)水平差距的唯一途徑。[1]
可以看到,所謂日韓道路,和我們過去的封閉型計(jì)劃經(jīng)濟(jì)的區(qū)別在于:不僅強(qiáng)調(diào)技術(shù)引進(jìn)消化、也強(qiáng)調(diào)國(guó)際市場(chǎng)導(dǎo)向,是“外向型的自立自強(qiáng)”工業(yè)方針。而和拉美道路的區(qū)別在于,政府起到了強(qiáng)有力的產(chǎn)業(yè)發(fā)展導(dǎo)向作用。
選擇什么道路,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國(guó)家的戰(zhàn)略取向和精神狀態(tài)。一般地說,拉美式的產(chǎn)業(yè)發(fā)展道路,固然也促進(jìn)了GDP的穩(wěn)定增長(zhǎng),但經(jīng)濟(jì)體系擺脫不了對(duì)強(qiáng)國(guó)的依附(拉美自來有“美國(guó)后院”之稱),最終影響國(guó)家獨(dú)立行動(dòng)的能力。其實(shí),我們的不少產(chǎn)業(yè),已經(jīng)在走拉美化的道路了。
所謂產(chǎn)業(yè)政策,就是在一定程度上,不按市場(chǎng)經(jīng)濟(jì)原則,不按靜態(tài)比較利益走。而不論發(fā)達(dá)國(guó)家還是發(fā)展中國(guó)家,沒有哪個(gè)國(guó)家極端地放棄產(chǎn)業(yè)政策的(拉美也在搞自己的民族產(chǎn)業(yè),如巴西的飛機(jī))。事實(shí)上,現(xiàn)今發(fā)達(dá)國(guó)家在早期都是靠高度的貿(mào)易保護(hù)才發(fā)展起本國(guó)工業(yè)的。日本韓國(guó)經(jīng)濟(jì)后來居上的案例中,可以看到后進(jìn)國(guó)家通過高強(qiáng)度引進(jìn)技術(shù)和本國(guó)化,促進(jìn)產(chǎn)業(yè)迅速升級(jí)的成功可能性。這是一定程度的貿(mào)易保護(hù)和“產(chǎn)業(yè)政策”的成功,也就是發(fā)揮動(dòng)態(tài)的比較優(yōu)勢(shì)。
比較優(yōu)勢(shì)理論,可以是后進(jìn)國(guó)家經(jīng)濟(jì)政策的一個(gè)基本出發(fā)點(diǎn),但由于這個(gè)理論有著很大的片面性,無法作為制定發(fā)展戰(zhàn)略的根據(jù)。經(jīng)濟(jì)發(fā)展戰(zhàn)略要解決的是長(zhǎng)期追趕問題,要兼顧多重目標(biāo)、不能簡(jiǎn)單抽象掉各種重要因素。筆者認(rèn)為,國(guó)家的經(jīng)濟(jì)發(fā)展戰(zhàn)略,以下幾個(gè)因素是不能不考慮進(jìn)去的:技術(shù)發(fā)展的累積性和不確定性、國(guó)家安全和國(guó)際關(guān)系、我們已有的產(chǎn)業(yè)基礎(chǔ)。
技術(shù)發(fā)展的累積性和不確定性
動(dòng)態(tài)地、歷史地看,我們今天具有比較優(yōu)勢(shì)的傳統(tǒng)產(chǎn)業(yè),曾是發(fā)達(dá)國(guó)家昨天的“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如紡織業(yè)。今天某些國(guó)家的高新技術(shù)產(chǎn)業(yè),可能較快地?cái)U(kuò)散到發(fā)展中國(guó)家,利用本地高素質(zhì)的勞動(dòng)力和其它有利因素,形成新的比較競(jìng)爭(zhēng)優(yōu)勢(shì)(如臺(tái)灣的半導(dǎo)體制造業(yè)、印度的軟件業(yè))。當(dāng)然,并非所有國(guó)家都必然能承接先進(jìn)國(guó)家的產(chǎn)業(yè)轉(zhuǎn)移。
所以,一國(guó)產(chǎn)業(yè)的興衰,并非完全遵從靜態(tài)的、決定論的“必然規(guī)律”。這首先是因?yàn)榧夹g(shù)因素在現(xiàn)代產(chǎn)業(yè)生產(chǎn)率的比較和變動(dòng)中的作用越來越重要,技術(shù)進(jìn)步(多樣性、不確定性),決非李嘉圖式的“葡萄酒和紡織品”的比較模式能容納。
當(dāng)今產(chǎn)業(yè)的技術(shù)含量不斷提高,產(chǎn)品生命周期縮短,這構(gòu)成“動(dòng)態(tài)比較優(yōu)勢(shì)論”的論據(jù)。
關(guān)于相對(duì)技術(shù)差距:隨著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的不斷升級(jí),比較優(yōu)勢(shì)來自于技術(shù)差距,而技術(shù)差距是前一個(gè)階段投資和學(xué)習(xí)的結(jié)果。“比較優(yōu)勢(shì)”不是天然的,而是歷史上的投資形成的,是可以培養(yǎng)并不斷變動(dòng)的。我國(guó)在許多領(lǐng)域已經(jīng)形成的技術(shù)積累,本身就是比較優(yōu)勢(shì)(如我國(guó)已經(jīng)具備的大型運(yùn)輸機(jī)設(shè)計(jì)制造能力,連日本也不具備,在性能價(jià)格比上很可能有潛在的比較優(yōu)勢(shì))。
關(guān)于學(xué)習(xí)效應(yīng):生產(chǎn)要素的生產(chǎn)率并非天生,而更多地取決于生產(chǎn)的歷史,取決于人們?cè)趯?shí)踐中的學(xué)習(xí)和鍛煉。企業(yè)生產(chǎn)同種產(chǎn)品越多,效率越高,生產(chǎn)成本也就越低(如美國(guó)航空界的經(jīng)驗(yàn):飛機(jī)制造廠產(chǎn)量每增加一倍,成本降低20%)。發(fā)展中國(guó)家生產(chǎn)“新產(chǎn)品”少,相對(duì)的生產(chǎn)率低,成本高。所以適度的市場(chǎng)保護(hù)是獲得學(xué)習(xí)效應(yīng)的必要條件。如追求短期經(jīng)濟(jì)效益,就永遠(yuǎn)得不到學(xué)習(xí)效應(yīng)。[2]
科學(xué)技術(shù)的運(yùn)行發(fā)展有自己的規(guī)律。科學(xué)研究有基礎(chǔ)科學(xué)、應(yīng)用科學(xué)和具體技術(shù)研發(fā)各層次,不能簡(jiǎn)單用“經(jīng)濟(jì)效益”指標(biāo)衡量科研機(jī)構(gòu)的業(yè)績(jī)。科研要求相對(duì)寬松的內(nèi)部環(huán)境和團(tuán)結(jié)協(xié)作的團(tuán)隊(duì)氛圍。科研項(xiàng)目有連續(xù)性,不能隨便中斷,研究隊(duì)伍運(yùn)作和經(jīng)驗(yàn)需要長(zhǎng)期積累過程。一個(gè)科研項(xiàng)目的運(yùn)行有自己的節(jié)奏和周期,要有長(zhǎng)遠(yuǎn)規(guī)劃和靈活應(yīng)變機(jī)制,現(xiàn)在的五年計(jì)劃和科技管理方式,有很多不適應(yīng)科研客觀規(guī)律的地方。
我國(guó)電子工業(yè)是50年代起步的,初期發(fā)展勢(shì)頭非常好,比起美國(guó)日本差不到哪里去。文革失去了10年,中外技術(shù)水平差距陡然拉大,再要追趕,談何容易。航空工業(yè),一個(gè)新的飛機(jī)型號(hào)的研制一般要8-10年(隨著電子技術(shù)的發(fā)展周期可能會(huì)縮短)。為了10年、20年后能與發(fā)達(dá)國(guó)家在民用飛機(jī)上競(jìng)爭(zhēng),今天就要起步。空中客車,各國(guó)財(cái)政支持,賠了20年錢才養(yǎng)大到足以挑戰(zhàn)美國(guó)波音的地步。
科研團(tuán)隊(duì)是技術(shù)進(jìn)步和獲得知識(shí)產(chǎn)權(quán)的核心力量,需要經(jīng)過多年科研實(shí)踐的鍛煉和磨合。一旦骨干散失,就再難成氣候(就是有技術(shù)資料,也難以發(fā)揮作用),還要重起爐灶慢慢聚合力量,和國(guó)外的差距就會(huì)突然拉大,很可能再也難追上。對(duì)自己已經(jīng)形成的科技研發(fā)機(jī)構(gòu)和隊(duì)伍。必須珍惜愛護(hù),善于發(fā)揮科學(xué)家的積極性創(chuàng)造力。
總之,沒有自己的科技儲(chǔ)備,就無法和國(guó)際高新產(chǎn)業(yè)界對(duì)話,就抓不住未來的商機(jī),將來連引進(jìn)和合資的資格都沒有。我們的高素質(zhì)低成本人才隊(duì)伍的“潛在比較優(yōu)勢(shì)”,就永遠(yuǎn)發(fā)揮不出作用。在這方面,我們的苦頭吃得太多了。
我國(guó)早在20世紀(jì)60至70年代,在原子能、航天技術(shù)方面大幅度地縮短了和發(fā)達(dá)國(guó)家的差距(比印度至少領(lǐng)先20年),在航空領(lǐng)域,我國(guó)是少數(shù)具有設(shè)計(jì)制造百噸級(jí)噴氣運(yùn)輸機(jī)的國(guó)家(連日本也沒有這樣的能力),這已經(jīng)形成了我們的“比較優(yōu)勢(shì)”。
當(dāng)代科技日新月異,新興產(chǎn)業(yè)層出不窮,市場(chǎng)千變?nèi)f化,商機(jī)無窮。但是,機(jī)遇只屬于有準(zhǔn)備的企業(yè)、行業(yè)和國(guó)家。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必須兼顧“今天和明天”。為了抓住明天的發(fā)展機(jī)遇,今天就必須在關(guān)鍵的基礎(chǔ)制造業(yè)、部分高科技產(chǎn)業(yè),在國(guó)力允許的范圍內(nèi),不懈努力打好技術(shù)的、產(chǎn)業(yè)組織的、體制的基礎(chǔ),這才可能逐步縮短差距。“走一步看一步”,只顧眼前的發(fā)展思路,差距就會(huì)越拉越遠(yuǎn)。
&nbs
化學(xué).jp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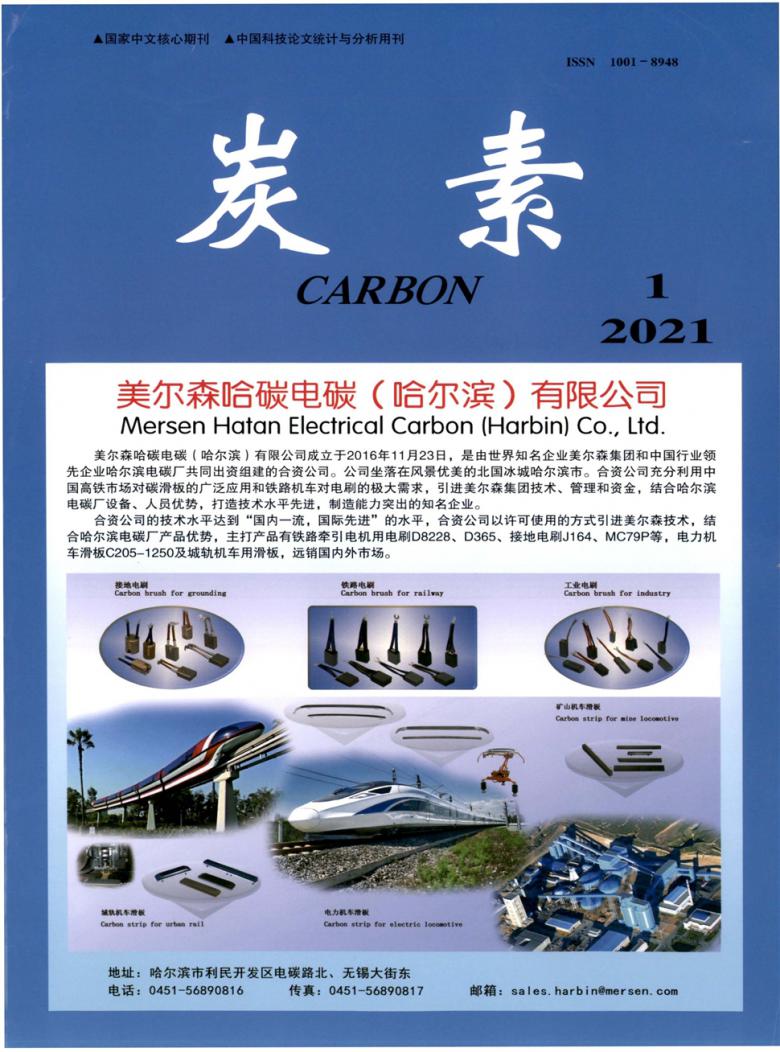
絡(luò)科技時(shí)代.jpg)
教育網(wǎng)絡(luò).jpg)
學(xué)報(bào).jpg)
于我們.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