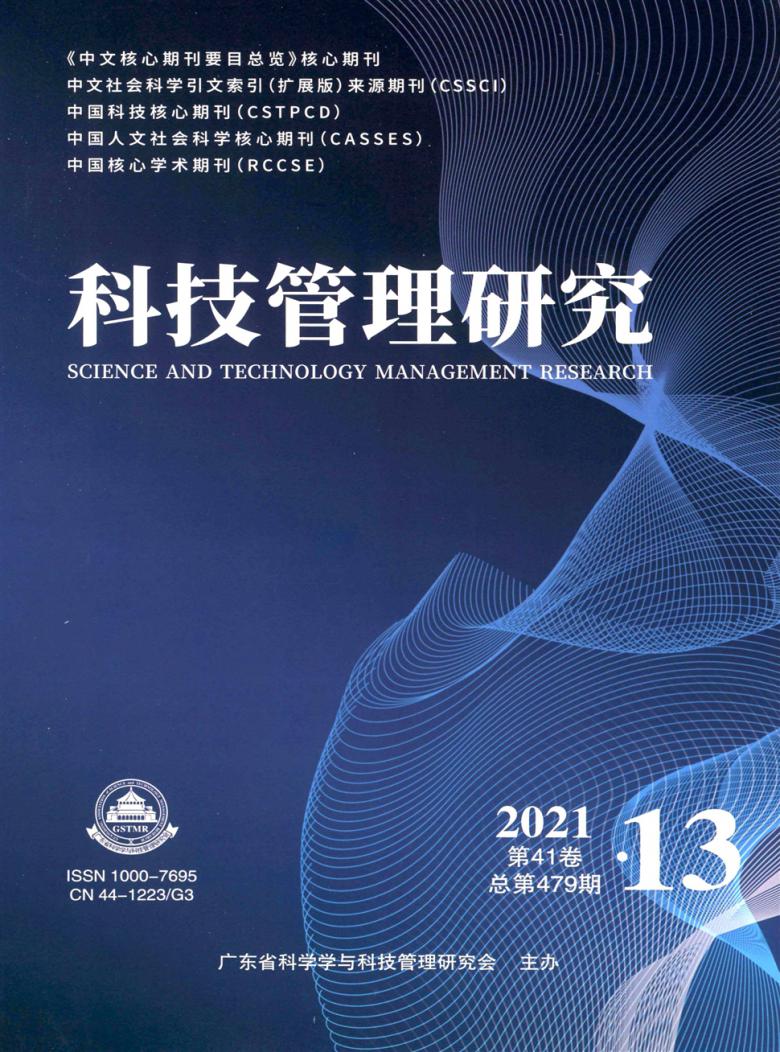國際貨幣體系與金融危機
黃梅波 熊愛宗
當今的國際貨幣體系仍然屬于美元本位制。一方面,美元通過經常項目失衡向世界輸出大量美元,這造成了國際貨幣體系外圍國家的流動性過剩。另一方面,美元通過外圍國家對美國金融資產的購買回流到美國,美元擴張的最終結果又會造成美國國內的流動性過剩。這造成了危機不斷在外圍國家與中心國家發生。如果當前國際貨幣體系下國際儲備資產的流動不發生根本改變,未來金融危機爆發的風險依然存在。
關鍵詞:國際貨幣體系;流動性過剩;金融危機
一、導言
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后所形成的牙買加體系,被稱為“無體系”的國際貨幣體系。之所以被稱為“無體系”,是因為與先前的國際貨幣體系相比,在這一體系下出現了匯率制度選擇的多樣化、國際收支調節手段的多樣化以及儲備資產的多元化。但是,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從本質來說仍然是美元本位制。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在國際貿易中美元仍然是最主要的標價與結算貨幣
三、國際貨幣體系與金融危機——外圍國家視角
新興市場經濟體通過持續的貿易盈余(以及資本盈余),積累了規模巨大的外匯儲備,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流動性壓力。以東亞為例,大部分經濟體雖然在金融危機后施行了相對靈活的匯率制度,但是在實際上又大都回到了釘住美元制。為維持本幣匯率穩定,在外匯儲備增加的情況下,中央銀行不得不投出本幣進行干預。盡管東亞各央行通過各種手段進行了一定的沖銷,但成本越來越大,且越來越缺乏效力。因此,在外匯儲備激增的情況下,外匯占款的增多必然帶來貨幣供給的增加,當貨幣供給超過實體經濟的需求數量時,泡沫將不可避免地產生。
(一)日本的經濟泡沫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出現持續的貿易盈余,1986年達到了整個80年代的頂峰。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日本的外匯儲備開始激增,從1985年到1989年,日本的外匯儲備增加了2.6倍。而當這些外匯儲備無法被中央銀行沖銷干凈的情況下,它們就會進入銀行體系,從而象高能貨幣一樣進行無限的信用創造。從1980年到1990年,日本的國內廣義貨幣供給和國內信貸分別增加了125%和127%,國內信貸占GDP的比例從1981年的200%上升到1989年的265%。貨幣增長刺激了日本房地產價格和股票價格的暴漲。從1985年到1989年底,日本股票價格大約上漲了3倍,而不動產價格和土地價格上漲更為厲害,在1990年初,按當時的價格,用東京可以買下整個美國,而用日本皇宮一帶的土地則可以買下整個加拿大。為了阻止泡沫的進一步膨脹,日本央行在1988年5月開始提高利率,到1990年6月份,貨幣市場利率重新攀升到8%的水平,泡沫迅速破裂,從而將日本帶入到“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
(二)中國股市與房地產市場繁榮
進入21世紀,隨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歸于平靜,中國的對外貿易開始迅速發展,突出的表現就是經常項目順差和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從2000年到2007年,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從205億美元擴大到3718億美元,而外匯儲備則從不到1700億美元增加到1.53萬億美元,8年間增長了800%多。
由于直到2005年7月之前,人民幣一直實行的是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因此隨著外匯儲備的增加,中國人民銀行必須不斷投放基礎貨幣,以維護人民幣匯率的穩定。雖然央行進行了頻繁的沖銷干預,我國的外匯占款仍然增長迅速。2000年,我國金融機構外匯占款大約為1.43萬億元人民幣,而2007年增長到12.8萬億元,也增長了近800%。
同時,國內的貨幣供應也在迅速增長。盡管這段時期我國一直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2002年初開始加息一直到2008年),從2002年開始,我國的貨幣供給(M2)增速一直在15%以上,從2000年到2007年,我國的貨幣供應增長了200%,而國內信貸也增長了186%。
然而,在貨幣供給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我國并沒有出現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形勢,這說明大量的資金并沒有進入實際的生產與消費領域,而是進入了資產投資渠道,這推動了中國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的繁榮。從2005年到2007年,中國的房價大約上升了20%,而中國股市在最高點則上漲了370%(圖3),中國的房地產尤其是股票市場已經出現了嚴重的泡沫,正當中國政府著手進行治理之時,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從而使這場泡沫還未成型便自行消散。
四、國際貨幣體系與金融危機——中心國家視角
美國具有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而美元又居于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地位,這使美聯儲充當起世界中央銀行的角色,向世界提供低風險、低收益、高流動性的資產,這被戴高樂(DeGaulle)稱為美元的“過度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
由于大量資金的流入,美國的長期利率和實際利率不斷走低。在上一次的加息周期中(2004.6—2006.6),盡管聯邦基金利率不斷提高,但是美國的長期利率如10年期國債收益率卻不升反降,這造成了長期利率與短期利率的倒掛,被稱為格林斯潘之謎(Greenspan’s Conundrum),盡管聯邦基金利率經歷不同的升降息周期過程,但是長期利率和短期實際利率卻不斷降低,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從1990年的8.55%降到2000年的6.03%,再進一步降低到2007年的4.63%。短期實際利率雖然波動較為激烈,但是整體水平已經是相當的低,且具有一定的下降趨勢,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后(1997/98)。毫無疑問,實際利率的降低說明了美國國內資金的充裕,而這部分來自于國際資金向美國的涌入。
國外資金的充裕供給使得對金融資產的需求越來越多,這必然造成美國金融資產的相對供給不足,這將引起兩方面的后果。第一,對美國資產的過分追逐,容易造成相關金融資產價格的上漲;第二,在需求過旺的刺激下,美國金融資產供給質量將會下降。
首先,流動性過剩造成資產價格上漲。在互聯網泡沫破裂之后,為了刺激經濟增長,美聯儲從2000年6月開始到2003年7月,短時間內把聯邦基金利率從6.5%迅速降低到1.0%。在美聯儲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刺激下,同時國際資金不斷涌入美國金融市場,造成了美國資金利率的降低和貨幣供應量的過度膨脹。從1990年到2007年,美國基礎貨幣(M0)和廣義貨幣(M2)分別增加了180%和127%,國內信貸增長了200%。從貨幣和信貸占GDP的比例來看,盡管從1990年到2007年,基礎貨幣占GDP的比例只增加了1%,但是國內信貸卻經歷了急劇的擴張,尤其是在1997年之后,國內信貸占GDP的比例增加了24%,在2007年已經超過100%。
大量學者研究了流動性過剩和資產價格之間的關系,得出的結論比較一致,那就是流動性過剩將會造成資產(房地產和股票)價格的上升,并具有一定的國際溢出效應。從近10年來看,美國經歷了兩次較為激烈的資產價格上漲。第一次是2000年左右的互聯網泡沫,這主要表現在股票價格的上漲上,從1997年到2000年,納斯達克指數大約上漲了157%。這主要是因為亞洲金融危機后,隨著美國“新經濟”的興起,使得國際資本重新回流到發達國家。第二次的資產價格上漲轉移到了房地產市場,互聯網泡沫破裂促使美聯儲施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時國際資本也從股票市場轉移出來,尋找新的投資渠道。這直接催生了房地產市場泡沫,從1997年到2007年,美國住房價格大約翻了一番,同時股票市場也出現反彈(圖4)。
流動性過剩意味著過多的資金追逐有限的金融產品,這一方面必然造成相關資產價格的上升(圖4),另一方面,在需求過旺的情況下,容易引發資產供給質量的下降。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可以很好的說明這一點。在房產價格上升的情況下,住房抵押貸款機構開始放松貸款人的借貸條件,這就造成了大量的次貸產品,然后再經過資產證券化變為次債產品(住房抵押貸款債券,RMBS),并衍生出其他金融產品。而在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次債及其相關產品的銷售不成問題。因此,在流動性的支持下,房地產價格不斷上升,同時,所創造出來的次債產品也完全被市場吸納干凈,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下去,直到流動性發生逆轉。為了易于銷售,大部分次債產品往往再次進行資產證券化,變為擔保債務憑證(CDO),CDO經過不同的變種(典型過程如在CDO的基礎上再CDO(CDO2)……,理論上可以無窮),將借貸人存在的違約風險無限的放大與擴展。從需求方來看,在美國國債產品收益下降的情況下,國際投資者開始傾向于購買這種高收益的結構產品。從2005年一直到次貸危機爆發,美元CDO發行幾乎翻了兩番。
由于金融結構產品(如CDO)具有明顯的信息非對稱性特點,這使得投資者不能對這些金融產品的風險收益狀況做出合理有效的判斷,一旦條件發生逆轉,投資者便會迅速將這些產品拋售以降低損失,如果市場上所有參與者都這樣做的話,這就發生了流動性的逆轉。
2004年6月美聯儲開始提高聯邦基金利率,幾乎就在同時房產價格止穩回落,這直接刺破了房地產泡沫,并使市場的潛在風險完全顯露出來,最終促成了次貸危機的爆發。次債產品供給(如CDO)開始大幅回落,同時次債市場的支持資金(如資產支持商業票據(ABCP))大幅減少。但是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危機逐漸從次債領域蔓延到良債領域,并發展成為金融危機,美國大批金融機構紛紛倒閉,全球五大知名投行已經集體從華爾街消失,同時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造成致命打擊。
但是我們注意到,在這次流動性逆轉過程中,外國投資者流入美國的資金在危機發生前后并沒有太大的變化(圖5)。外國投資者對于美國政府債券與票據和長期機構債的每月凈購買一直維持在200億美元上下,雖然一直存在著較為劇烈的波動,但是在危機發生后,并沒有出現明顯且持續的下降趨勢。這說明在美國國內出現流動性緊縮的情況下,來自國際社會的流動性并沒有減少的跡象,這再一次說明了全球“資產短缺”和美元“過度特權”的影響。因此,在美國國內情況發生好轉的情形下,這些來自國際社會的流動性仍會像以前一樣,推動下一個泡沫的產生。
五、總結
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本質上仍屬于美元本位制。由于美元供給的限制條件不復存在,這使得美聯儲在不考慮美元國際外部性的情況下傾向于擴大美元供給。同時,牙買加體系下由于不存在金本位體系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國際收支自動調節機制,這就更容易出現全球經濟失衡現象。以上兩個因素相互影響,共同造成了全球美元供給的迅速增長,并為儲備貨幣吸收國帶來巨大的國內流動性過剩壓力,蘊含下巨大的經濟風險。
然而在另一方面,全球美元資產必然要回流到美國,因此全球美元的過多供給在最后必然要表現為美國國內貨幣的過多供給,同時,伴隨著美聯儲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國國內的流動性開始泛濫。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剛剛經歷了股票市場價格泡沫,充足的流動性便集中到了房地產市場上,這推動了房產價格的急劇上升。在房價上升,同時國際社會對于金融資產的強烈需求下,這使得金融機構可以放心大膽地創造與房地產相關的金融衍生產品。而金融資產質量下降成為流動性逆轉的誘發條件,一旦條件改變,市場的過度反應將會造成整個市場的崩盤。
由于擔心通貨膨脹,美聯儲在2004年6月開始加息,這加劇了次貸相關者的還貸成本,次貸的風險開始累積。在房地產價格下降的情況下,風險終于在2007年夏天完全釋放出來。危機首先造成次債產品的崩盤,并傳染到優良債券市場,進而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同時危機的爆發也引起了全球性的流動性緊縮。從美國國內來看,流動性緊縮源于美國貨幣供給的減少(美聯儲加息),同時國內相關的金融機構和投資者貨幣需求的增加(盡管后期美聯儲降息增加貨幣供給),但是從外部情況來看,外國投資者(特別是官方)對于美國市場的資金注入并沒有減少,它們仍然在美國尋找著新的投資機會,因此一旦美國經濟情況發生逆轉,它們將會為下一場泡沫的產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美國次貸危機再一次向我們啟示,盡管泡沫的產生與破裂主要是由于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造成的,但是當今國際貨幣體系所造成的金融狀況失衡也是個中原因之一。解決之道除了要大力發展各國的金融市場之外,就是要改革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否則危機的爆發只是國家的不同與產業的差別。
[1]張明,覃東海,國際貨幣體系演進的資源流動分析[J1,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12):61—66。
[2]張明,流動性過剩的測量、根源和風險涵義[J],世界經濟,2007,(1):44—55。
[3]王洛林,余永定,李薇,日本的通貨緊縮[J],世界經濟,1999,(2):32—38。
,在國際儲備資產中,美元仍占據著最重要的位置,世界大部分國家都不同程度地實行釘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同時美元也是大多數國家進行本幣干預的對手貨幣。
但是,在牙買加體系下,美元供給已經不再受到黃金供應量的限制,而是服務于美國國內的經濟目標。因此,美聯儲在未考慮到美元作為國際貨幣而帶來的外部性時,必然會造成美元的過多供給,這造成了全球儲備資產的迅速擴張。據IFS和COFER的數據,1948年到1969年布雷頓森林體系崩潰前夕,全球儲備資產大約只增加了160%,而從1969年到1989年,全球儲備資產則增加了1386%,而從1969年到2007年則近乎增加了10000%。
同時,在現行的美元本位制下,由于缺少像金本位體系以及布雷頓森林體系下國際收支的自動調節機制,這使得一國的國際收支更容易出現失衡現象。而正是通過這種失衡,國際儲備資產得以成倍創造,并從貨幣體系的中心國家(儲備貨幣發行國)不斷向外圍國家(儲備貨幣的需求國)輸出。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的經常項目逆差逐漸擴大,同時伴隨著對外直接投資的增長,大量美元涌入世界各地,這帶來了全球性的流動性過剩,同時大量美元最終又回流到美國,這相應造成了美國國內的流動性過剩。這正是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所爆發的幾次危機的共同背景(包括拉美的債務危機、日本的經濟泡沫、亞洲金融危機、美國互聯網泡沫以及最近的美國次貸危機等)。
二、美元本位下的國際貨幣體系
Dooley等人指出,在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下存在著三大功能區:貿易賬戶區、中心區和金融賬戶區。貿易賬戶區主要包括亞洲國家,他們主要以美國為出口市場,同時維持匯率低估,積累了大量的貿易盈余與外匯儲備,但是這些儲備又大部分以購買美元債券的形式重新回流到美國。金融賬戶區主要包括歐洲、加拿大以及拉丁美洲等,這些地區的國家一般實行浮動匯率制度,國際收支基本平衡,外匯儲備變動不大。但是這些國家的私人投資者大量購買美國的股票、債券等金融資產,因此他們對美國保持著金融賬戶逆差。而中心區的美國則處于國際貨幣體系的支配地位,由于有來自貿易賬戶地區的外匯儲備回流和金融賬戶地區私人資本流人的支撐,這使得美國的經常賬戶逆差得以維持,且規模越來越大。張明和覃東海將以上三個地區之間的資源流動模式表示為圖。
通過圖1,我們可以大致了解現行國際貨幣體系存在的兩個特征:
第一,通過經常賬戶赤字美國向世界輸出了大量美元,而貿易盈余地區則積累了大量的美元資產。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美國的經常賬戶開始惡化,除了在1991年經歷短暫的盈余狀態外,大部分年份經常賬戶差額都處于逆差狀態,在1998年突破2000億美元之后,美國的經常賬戶迅速惡化,在2006年達到了歷史的高點近8000億美元。同時,經常賬戶逆差占當年GDP的比例也在不斷上升,從1998年的3.24%上升到2006年的5.98%。雖然2007年這一趨勢稍有好轉,但是經常賬戶差額仍有7312億美元,占當年GDP的5.3%。通過經常賬戶逆差,美國向世界輸出了大量美元。2007年全球的美元儲備資產接近2.6萬億美元,這約是1995年的4.3倍,是2000年的2.4倍。
與美國經常賬戶逆差形成鮮明對比的是另一些經濟體持續的經常賬戶順差,這主要來自新興市場經濟體以及一些石油產出國。亞洲的新興市場經濟體在出口導向型經濟發展戰略指導下,對外貿易尤其是出口貿易得到了迅速發展,亞洲金融危機后大部分經濟體經歷了持續的貿易順差,這其中尤以中國為最。在1996年之前,中國的經常賬戶盈余有限,且部分年份處于逆差狀態,即使到2001年中國的經常賬戶盈余也只有174億美元,占當年GDP的比例也不過1.3%,但是隨后經常賬戶順差開始成倍增長,到了2007年,經常賬戶順差已達到3718億美元,占GDP的比例也上升到11.3%。同時,由于近年來石油價格的上升,主要的石油產出國的經常賬戶順差也急劇擴大。以中東地區為例,2007年整個地區的經常賬戶順差為2570億美元,這幾乎是2001年的6.5倍。
伴隨著經常賬戶順差的增加,新興與發展經濟體和石油產出國的外匯儲備規模不斷擴大,2007年這兩組經濟體的外匯儲備分別為3.11萬億SDR與3120億SDR,這分別是他們2000年水平的3.47倍和3.05倍。從東亞來看,從1990年到2007年,亞洲7個經濟體(中國香港、印度尼西亞、馬來西亞、菲律賓、新加坡、泰國和越南)的外匯儲備從829億美元增加到6093億美元。中國的外匯儲備增加則更加驚人,1990年中國的外匯儲備只有286億美元,2007年這一數字為1.53萬億美元,而到了2008年12月份已經達到1.95萬億美元。石油產出國的外匯儲備也在迅速增加,如俄羅斯的外匯儲備在2007年底已達到4655億美元。
第二,外圍國家所積累的大量美元必然要重新回流到美國。但是對于貿易賬戶區和金融賬戶區美元回流的表現形式又不太相同,東亞官方儲備積累的美元資產主要以美元國債的形式回流到美國,他們不太注重贏利性,而強調安全性與流動性。而經由歐洲等金融賬戶區回流的美元主要通過私人投資完成,他們追求金融資產良好的風險收益回報,投資的資產更傾向于公司股票、企業債券等。
表1是外國投資者持有美國債券的資產構成,我們按地區歸屬依次說明。首先是來自亞洲地區的日本和中國,他們是持有美國證券最大的兩個外國投資者,在持有證券的構成上,主要以國債和長期債券為主,分別占到了各自投資比重的65.3%(日本)和91.4%(中國),在其他資產上投資則相對較少。其次是來自歐洲地區的國家如英國、盧森堡以及加拿大(我們將開曼群島也歸為此類),這些國家對美元股權資產以及企業債券的持有比例明顯大于亞洲地區,其持有比例大都在70—90%不等。最后,來自中東地區的石油出口國的投資組合則介于以上兩個地區之間。
Bracke等人將大量美元資產回流美國這一現象稱為金融失衡,它和貿易失衡一起構成全球經濟失衡的全貌。從20世紀90年代開始,外國投資者對美國資產購買迅速增加,1990年外國投資者在美國的資產共計2.4萬億美元,而到2007年已經增加到20萬億美元之多。同時,從20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美國的國外資產凈額由正轉負,這意味著美國由債權國轉變為債務國。從2000年開始,流入美國的資金凈額首次突破1萬億美元,到2007年流入美國市場的外國凈資金規模近2.5萬億美元(圖2)。
Caballero等認為金融狀況失衡的原因是由于全球金融資產供給短缺造成的。新興市場經濟體由于國內金融市場發展滯后,所以資金無法在國內尋找相應的投資渠道,這就表現為這些經濟體的高額儲蓄,并造成資本的大規模外流。美國、歐洲和日本都存在著發達的金融市場,但是由于歐洲和日本的增長前景相比于美國遜色,使得它們的金融資產相比于美國并沒有那么強的吸引力。因此金融資本源源不斷地流入到美國。
貿易失衡與金融失衡相互影響,他們共同組成了整個國際貨幣體系的美元流通循環。首先,美國通過貿易失衡向世界提供了大量美元,這造成貨幣體系外圍國家的外匯儲備增加和貨幣供給的擴張,直接催生了這些國家的經濟泡沫,并引致危機發生。其次,通過金融失衡,大量美元最終要回流到美國,因此,美元擴張的最終結果必然要造成美元國內的流動性過剩,這同樣會刺激出美國的經濟泡沫。因此,以下兩個部分我們就分別從外圍國家和中心國家視角來探討美元流動循環所造成的幾個危機。 三、國際貨幣體系與金融危機——外圍國家視角
新興市場經濟體通過持續的貿易盈余(以及資本盈余),積累了規模巨大的外匯儲備,面臨著越來越大的流動性壓力。以東亞為例,大部分經濟體雖然在金融危機后施行了相對靈活的匯率制度,但是在實際上又大都回到了釘住美元制。為維持本幣匯率穩定,在外匯儲備增加的情況下,中央銀行不得不投出本幣進行干預。盡管東亞各央行通過各種手段進行了一定的沖銷,但成本越來越大,且越來越缺乏效力。因此,在外匯儲備激增的情況下,外匯占款的增多必然帶來貨幣供給的增加,當貨幣供給超過實體經濟的需求數量時,泡沫將不可避免地產生。
(一)日本的經濟泡沫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日本出現持續的貿易盈余,1986年達到了整個80年代的頂峰。也正是在這一時期,日本的外匯儲備開始激增,從1985年到1989年,日本的外匯儲備增加了2.6倍。而當這些外匯儲備無法被中央銀行沖銷干凈的情況下,它們就會進入銀行體系,從而象高能貨幣一樣進行無限的信用創造。從1980年到1990年,日本的國內廣義貨幣供給和國內信貸分別增加了125%和127%,國內信貸占GDP的比例從1981年的200%上升到1989年的265%。貨幣增長刺激了日本房地產價格和股票價格的暴漲。從1985年到1989年底,日本股票價格大約上漲了3倍,而不動產價格和土地價格上漲更為厲害,在1990年初,按當時的價格,用東京可以買下整個美國,而用日本皇宮一帶的土地則可以買下整個加拿大。為了阻止泡沫的進一步膨脹,日本央行在1988年5月開始提高利率,到1990年6月份,貨幣市場利率重新攀升到8%的水平,泡沫迅速破裂,從而將日本帶入到“失去的十年”(Lost Decade)。
(二)中國股市與房地產市場繁榮
進入21世紀,隨著亞洲金融危機影響歸于平靜,中國的對外貿易開始迅速發展,突出的表現就是經常項目順差和外匯儲備的迅速增長。從2000年到2007年,中國的經常項目順差從205億美元擴大到3718億美元,而外匯儲備則從不到1700億美元增加到1.53萬億美元,8年間增長了800%多。
由于直到2005年7月之前,人民幣一直實行的是釘住美元的固定匯率制度,因此隨著外匯儲備的增加,中國人民銀行必須不斷投放基礎貨幣,以維護人民幣匯率的穩定。雖然央行進行了頻繁的沖銷干預,我國的外匯占款仍然增長迅速。2000年,我國金融機構外匯占款大約為1.43萬億元人民幣,而2007年增長到12.8萬億元,也增長了近800%。
同時,國內的貨幣供應也在迅速增長。盡管這段時期我國一直實行穩健的貨幣政策(2002年初開始加息一直到2008年),從2002年開始,我國的貨幣供給(M2)增速一直在15%以上,從2000年到2007年,我國的貨幣供應增長了200%,而國內信貸也增長了186%。
然而,在貨幣供給不斷增加的情況下,我國并沒有出現比較嚴重的通貨膨脹形勢,這說明大量的資金并沒有進入實際的生產與消費領域,而是進入了資產投資渠道,這推動了中國房地產市場和股票市場的繁榮。從2005年到2007年,中國的房價大約上升了20%,而中國股市在最高點則上漲了370%(圖3),中國的房地產尤其是股票市場已經出現了嚴重的泡沫,正當中國政府著手進行治理之時,美國次貸危機爆發,從而使這場泡沫還未成型便自行消散。
四、國際貨幣體系與金融危機——中心國家視角
美國具有高度發達的金融市場,而美元又居于國際貨幣體系的中心地位,這使美聯儲充當起世界中央銀行的角色,向世界提供低風險、低收益、高流動性的資產,這被戴高樂(DeGaulle)稱為美元的“過度特權”(Exorbitant Privilege)。
由于大量資金的流入,美國的長期利率和實際利率不斷走低。在上一次的加息周期中(2004.6—2006.6),盡管聯邦基金利率不斷提高,但是美國的長期利率如10年期國債收益率卻不升反降,這造成了長期利率與短期利率的倒掛,被稱為格林斯潘之謎(Greenspan’s Conundrum),盡管聯邦基金利率經歷不同的升降息周期過程,但是長期利率和短期實際利率卻不斷降低,美國10年期國債收益率從1990年的8.55%降到2000年的6.03%,再進一步降低到2007年的4.63%。短期實際利率雖然波動較為激烈,但是整體水平已經是相當的低,且具有一定的下降趨勢,尤其是亞洲金融危機之后(1997/98)。毫無疑問,實際利率的降低說明了美國國內資金的充裕,而這部分來自于國際資金向美國的涌入。
國外資金的充裕供給使得對金融資產的需求越來越多,這必然造成美國金融資產的相對供給不足,這將引起兩方面的后果。第一,對美國資產的過分追逐,容易造成相關金融資產價格的上漲;第二,在需求過旺的刺激下,美國金融資產供給質量將會下降。
首先,流動性過剩造成資產價格上漲。在互聯網泡沫破裂之后,為了刺激經濟增長,美聯儲從2000年6月開始到2003年7月,短時間內把聯邦基金利率從6.5%迅速降低到1.0%。在美聯儲擴張性貨幣政策的刺激下,同時國際資金不斷涌入美國金融市場,造成了美國資金利率的降低和貨幣供應量的過度膨脹。從1990年到2007年,美國基礎貨幣(M0)和廣義貨幣(M2)分別增加了180%和127%,國內信貸增長了200%。從貨幣和信貸占GDP的比例來看,盡管從1990年到2007年,基礎貨幣占GDP的比例只增加了1%,但是國內信貸卻經歷了急劇的擴張,尤其是在1997年之后,國內信貸占GDP的比例增加了24%,在2007年已經超過100%。
大量學者研究了流動性過剩和資產價格之間的關系,得出的結論比較一致,那就是流動性過剩將會造成資產(房地產和股票)價格的上升,并具有一定的國際溢出效應。從近10年來看,美國經歷了兩次較為激烈的資產價格上漲。第一次是2000年左右的互聯網泡沫,這主要表現在股票價格的上漲上,從1997年到2000年,納斯達克指數大約上漲了157%。這主要是因為亞洲金融危機后,隨著美國“新經濟”的興起,使得國際資本重新回流到發達國家。第二次的資產價格上漲轉移到了房地產市場,互聯網泡沫破裂促使美聯儲施行寬松的貨幣政策,同時國際資本也從股票市場轉移出來,尋找新的投資渠道。這直接催生了房地產市場泡沫,從1997年到2007年,美國住房價格大約翻了一番,同時股票市場也出現反彈(圖4)。
流動性過剩意味著過多的資金追逐有限的金融產品,這一方面必然造成相關資產價格的上升(圖4),另一方面,在需求過旺的情況下,容易引發資產供給質量的下降。美國房地產市場泡沫可以很好的說明這一點。在房產價格上升的情況下,住房抵押貸款機構開始放松貸款人的借貸條件,這就造成了大量的次貸產品,然后再經過資產證券化變為次債產品(住房抵押貸款債券,RMBS),并衍生出其他金融產品。而在流動性過剩的情況下,次債及其相關產品的銷售不成問題。因此,在流動性的支持下,房地產價格不斷上升,同時,所創造出來的次債產品也完全被市場吸納干凈,這種情況一直持續下去,直到流動性發生逆轉。為了易于銷售,大部分次債產品往往再次進行資產證券化,變為擔保債務憑證(CDO),CDO經過不同的變種(典型過程如在CDO的基礎上再CDO(CDO2)……,理論上可以無窮),將借貸人存在的違約風險無限的放大與擴展。從需求方來看,在美國國債產品收益下降的情況下,國際投資者開始傾向于購買這種高收益的結構產品。從2005年一直到次貸危機爆發,美元CDO發行幾乎翻了兩番。
由于金融結構產品(如CDO)具有明顯的信息非對稱性特點,這使得投資者不能對這些金融產品的風險收益狀況做出合理有效的判斷,一旦條件發生逆轉,投資者便會迅速將這些產品拋售以降低損失,如果市場上所有參與者都這樣做的話,這就發生了流動性的逆轉。
2004年6月美聯儲開始提高聯邦基金利率,幾乎就在同時房產價格止穩回落,這直接刺破了房地產泡沫,并使市場的潛在風險完全顯露出來,最終促成了次貸危機的爆發。次債產品供給(如CDO)開始大幅回落,同時次債市場的支持資金(如資產支持商業票據(ABCP))大幅減少。但是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危機逐漸從次債領域蔓延到良債領域,并發展成為金融危機,美國大批金融機構紛紛倒閉,全球五大知名投行已經集體從華爾街消失,同時金融危機對實體經濟造成致命打擊。
但是我們注意到,在這次流動性逆轉過程中,外國投資者流入美國的資金在危機發生前后并沒有太大的變化(圖5)。外國投資者對于美國政府債券與票據和長期機構債的每月凈購買一直維持在200億美元上下,雖然一直存在著較為劇烈的波動,但是在危機發生后,并沒有出現明顯且持續的下降趨勢。這說明在美國國內出現流動性緊縮的情況下,來自國際社會的流動性并沒有減少的跡象,這再一次說明了全球“資產短缺”和美元“過度特權”的影響。因此,在美國國內情況發生好轉的情形下,這些來自國際社會的流動性仍會像以前一樣,推動下一個泡沫的產生。
五、總結
現行的國際貨幣體系本質上仍屬于美元本位制。由于美元供給的限制條件不復存在,這使得美聯儲在不考慮美元國際外部性的情況下傾向于擴大美元供給。同時,牙買加體系下由于不存在金本位體系與布雷頓森林體系的國際收支自動調節機制,這就更容易出現全球經濟失衡現象。以上兩個因素相互影響,共同造成了全球美元供給的迅速增長,并為儲備貨幣吸收國帶來巨大的國內流動性過剩壓力,蘊含下巨大的經濟風險。
然而在另一方面,全球美元資產必然要回流到美國,因此全球美元的過多供給在最后必然要表現為美國國內貨幣的過多供給,同時,伴隨著美聯儲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國國內的流動性開始泛濫。在這種情況下,由于剛剛經歷了股票市場價格泡沫,充足的流動性便集中到了房地產市場上,這推動了房產價格的急劇上升。在房價上升,同時國際社會對于金融資產的強烈需求下,這使得金融機構可以放心大膽地創造與房地產相關的金融衍生產品。而金融資產質量下降成為流動性逆轉的誘發條件,一旦條件改變,市場的過度反應將會造成整個市場的崩盤。
由于擔心通貨膨脹,美聯儲在2004年6月開始加息,這加劇了次貸相關者的還貸成本,次貸的風險開始累積。在房地產價格下降的情況下,風險終于在2007年夏天完全釋放出來。危機首先造成次債產品的崩盤,并傳染到優良債券市場,進而引發全球性的金融危機。
同時危機的爆發也引起了全球性的流動性緊縮。從美國國內來看,流動性緊縮源于美國貨幣供給的減少(美聯儲加息),同時國內相關的金融機構和投資者貨幣需求的增加(盡管后期美聯儲降息增加貨幣供給),但是從外部情況來看,外國投資者(特別是官方)對于美國市場的資金注入并沒有減少,它們仍然在美國尋找著新的投資機會,因此一旦美國經濟情況發生逆轉,它們將會為下一場泡沫的產生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美國次貸危機再一次向我們啟示,盡管泡沫的產生與破裂主要是由于美聯儲的貨幣政策造成的,但是當今國際貨幣體系所造成的金融狀況失衡也是個中原因之一。解決之道除了要大力發展各國的金融市場之外,就是要改革目前的國際貨幣體系,否則危機的爆發只是國家的不同與產業的差別。
[1]張明,覃東海,國際貨幣體系演進的資源流動分析[J1,世界經濟與政治,2005,(12):61—66。
[2]張明,流動性過剩的測量、根源和風險涵義[J],世界經濟,2007,(1):44—55。
[3]王洛林,余永定,李薇,日本的通貨緊縮[J],世界經濟,1999,(2):3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