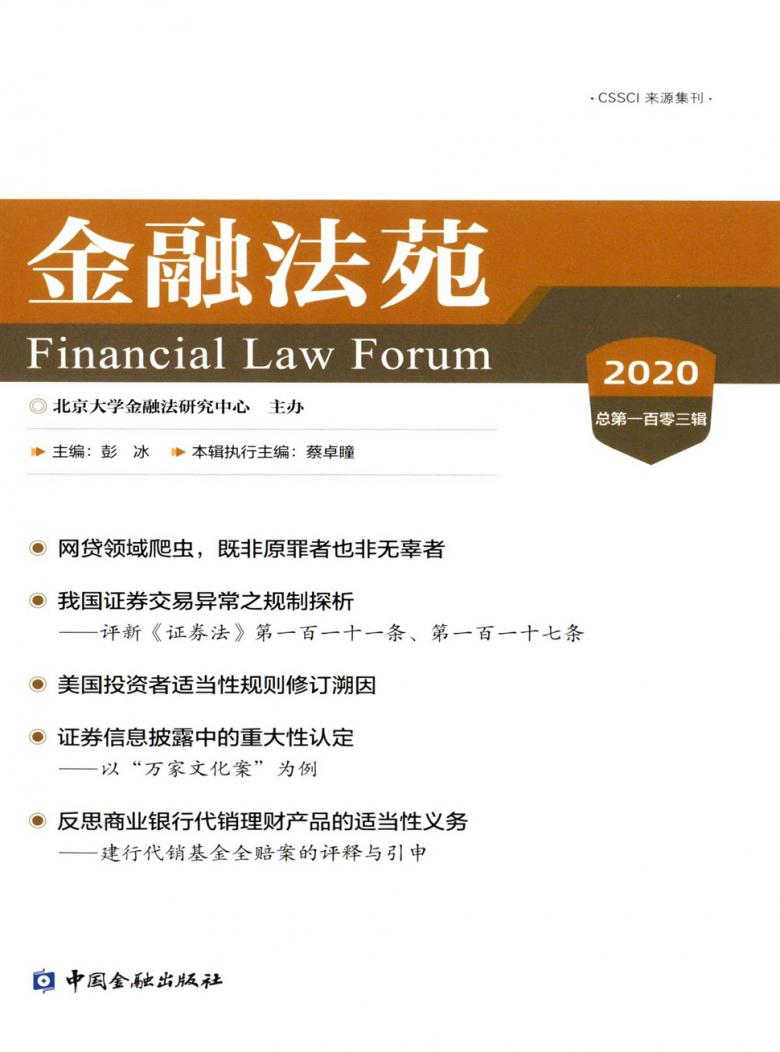英國法對自殺者的懲罰與寬宥——福柯刑罰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擴展
黃永鋒
關鍵詞: 自殺/英國法/刑罰政治經濟學
內容提要: 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指出,一部刑罰史就是一部國家權力對個體征服、控制和利用的歷史。英國法對自殺者的懲罰和寬宥,一方面可以用福柯的刑罰政治經濟學來解釋,另一方面又擴展了刑罰政治經濟學的視野。英國法的歷史表明,從中世紀到資本主義興起時期,國家權力通過懲罰或寬宥自殺者而對活著的個體進行威懾、控制和利用,與此同時權力也自我調整,從而使個體的存在和發展與國家權力的轉型和發展相契合。
一、福柯的刑罰政治經濟學
對于人類社會中刑罰方式的變遷,許多人都樂于將其概括為一個“從野蠻走向文明”的過程,并由此而贊美“啟蒙和人性發現”的偉大。但對于以冷酷思想和銳利思維而著稱的福柯(Michel Foucault)來說,這種溫情脈脈、似是而非的人道主義論調顯然是不夠深刻的。因為據他考證,在歐洲近代刑罰史上,從酷刑轉向監禁的過程相當短暫。雖然公開的酷刑在17世紀還非常盛行,但進入18世紀特別是中期以后,往昔熱鬧非凡的公開處決幾乎都銷聲匿跡了,那種慘烈壯觀的斷頭臺場景再也難覓蹤影。為什么在短短的幾十年間,刑罰會發生如此重大的變化?這種轉變意味著什么?除了“啟蒙”和“人性”之外,還有沒有更深刻的原因?這正是福柯在《規訓與懲罰》[1]一書中所要解決的一個重大歷史問題。
為了回答上述問題,福柯根據許多不引人注目且少為人知的邊緣史料,細致地梳理出了三種刑罰權力運作機制:“酷刑展示與公開處決”模式、“傳播懲罰符號表象”模式、“監禁”模式。他指出,在18世紀晚期,人們面對著“酷刑展示與公開處決”、“傳播懲罰符號表象”和“監禁”三種組織懲罰權力的方式,它們分別以舊式君主制度、懲罰表象和強制制度為基礎。在君主制度中,刑罰是君權在眾目睽睽之下制造強烈恐怖效果的一種報復儀式,是君主及其權力的物質表現,但這種權力不連貫、不規范,總是凌駕于自身的法律之上。在懲罰表象中,刑罰被視為使人重新獲得權利主體資格的程序,其采用一系列被編碼的符號和表象,并使之在民眾之間得到迅速和廣泛的傳播,從而阻斷犯罪。而在監獄制度中,刑罰則被視為對人實行強制的技術,其以一種特殊刑罰管理權力的建立為先決條件,通過在習慣、行為中留下痕跡而訓練肉體。
這三種模式分別對應著不同的權力策略和技術:第一種模式基于舊式專橫的君主制度;第二種模式基于懲罰的符號技術;第三種模式基于教養所的強制制度。通過闡述和分析三種刑罰模式之間的轉換過程,福柯向人們展示了他從眾多史料中提煉出來的刑罰政治經濟學———在刑罰日益寬松的現象背后,并非溫情脈脈的“人性和啟蒙”,而是刑罰作用點的微妙轉換,即從“鮮血淋淋的肉體”到“精神和觀念”再到“馴順的肉體”。這種轉換的實質是刑罰權力策略和權力技術的轉變,是國家權力對個體的征服和控制方式的轉變;并且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一部刑罰史就是一部國家權力對個體征服、控制和利用的歷史[2]27-34。
毋庸置疑,福柯對刑罰史的這一發現和概括是驚世駭俗的,并且犀利睿智。但是,除了活著的個體外,福柯的刑罰政治經濟學并沒有涉及國家權力對自殺者的態度。而在歐洲,尤其是英國,有大量歷史事實表明,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國家權力的觸角甚至還延伸到了自殺者的尸體和財產。這應作何解釋?在發掘和梳理相關史料的基礎上,本文認為,這一問題同樣可以用福柯的刑罰政治經濟學來進行解釋,而且在一定程度上還擴展了刑罰政治經學的視野———從中世紀到資本主義的興起,權力通過懲罰或寬宥自殺者(尸體和財產)而對活著的個體進行威懾、控制或利用,與此同時權力也進行自我調整,從而使個體的存在和發展與國家權力的轉型和發展相契合。
二、英國法中自殺者的罪與罰
英國法中出現禁止自殺的規范最早可以追溯到中世紀的普通法,但直到封建制度瓦解后,普通法才代替了教會法和其他宗教規范對自殺進行懲罰。由于最早反對自殺的法律是以普通法的形式出現的,因此很難明確這類法律的起源時間;但可以肯定的是,直到14世紀,自殺才被認為是重罪[3]253。14世紀中期以后,自殺在普通法中已被普遍當作謀殺罪,認定該罪的兩個前提是行為人已成年和神智正常,這同時也是認定自殺未遂罪(被視為輕罪)的部分要件。除了所涉及的法律要件外,自殺罪還有一個特別的名稱,“felo-de-se”,意思是“恥辱的自殺者”。從詞源學上來看,“felo”指的是仆從破壞其與主人之間信任關系的一類犯罪;“felon”則是指實施前述犯罪的行為人,在以家臣制度(vassalage)束縛仆從的時代,這是一個被普遍使用的詞匯;“felony”是對“最惡劣且無法彌補的犯罪”(具體案情見Hales v。 Petit (1565), 1 Plowd, 253, 260。)的稱呼,一般認為其派生于拉丁文“fell”(“惡毒”的意思)。由于在時間上,懲罰自殺的各種刑罰要早于禁止自殺的法律出現,因此,英國普通法在界定“felonies”這類犯罪時,更多的是從法律后果方面著手(例如會導致財產喪失),而較少涉及其實體內容[4]139。
從13世紀到18世紀期間,懲罰自殺主要有兩類刑罰。一類涉及對自殺者尸體的懲罰,另一類涉及對自殺者財產的懲罰。在第一類刑罰中,根據教會法,那些自殺或者自殺未遂的人被認為是“不名譽”的,不得舉行基督教葬禮[5]87。這些規則后來為英國的普通法和成文法所采納,效力一直延續到19世紀上半葉。對于自殺者的尸體,英國的傳統作法是在夜間將其放置于十字路口并用木棍穿刺而過,此外還用石頭壓住死者的臉面,以此表征自殺者的“恥辱”。據考證,這種對尸體的懲罰源自非洲部落和澳大利亞原著民的原始宗教儀式[6]115。總體而言,公開褻瀆尸體的實踐意在給公眾強化這樣一種印象———自殺行為具有異教性,并以此威懾其他有自殺傾向的人;此外,這種實踐還反映了一種鬼神信仰,即要用針將自殺者的鬼魂扎住,使其無法從墳墓中逃脫,這非常重要。
第二類刑罰是沒收自殺者的財產,大約在1221年以普通法的形式出現,脫胎于一系列神智正常的人實施的自殺案件。13世紀一位著名的法學者布萊克頓(Bracton)區分了針對不同自殺者而應當實施的沒收財產的刑罰,認為:一個人若是為了逃避被判罰極刑而自殺,就應當剝奪其財物和土地;若是普通的自殺,則只須沒收其財物[7]97。但布萊克頓并沒有明確被沒收的財產應當歸屬于誰。另一位同時期的法學者威廉姆斯(Williams)則認為,“自殺者的動產應當與重罪犯人的動產等同對待”[8]102,不過他沒有提及土地。在英國的司法實踐中,盡管自殺者的財物常常要被沒收,但沒有證據顯示自殺者的土地也要被沒收。根據司法規則,沒收自殺者的財物必須經過調查詢問的程序,只有認定自殺者為“felo-de-se”(意為“恥辱的自殺者”)之后,才能沒收其動產。由此,如果調查官員寬恕自殺者,認定其自殺是出于神智錯亂或者其他可減輕罪過的情節,不構成“felo-de-se”,那么就可以避免自殺者的財物被沒收。
在懲罰自殺的普通法出現之前,被認定為“felo-de-se”的自殺者的財產歸屬于其領主(Lord)。而到了中世紀晚期,自殺者的財產則開始成為國家的財政收入來源[9]273。為了達到把自殺者的財產從其領主那里轉移到國庫的目的,國家唯一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將自殺定為重罪。因為根據英國的法律傳統,重罪犯人的財產是要收歸國王的。與普通法上的其他犯罪一樣,將自殺定為犯罪要經歷一系列緩慢、零碎的司法程序,要建立在法院判決、傳統和慣例的基礎之上,而非以成文法的形式加以規定。哈里斯訴貝蒂特(Hales v。 Petit〔1565〕)案也許是這當中最為重要的一個案件。本案中,針對有爭議的沒收自殺者財產這一問題,布朗大法官(Mr。 Justice Brown)認為:“自殺是違反大自然的罪犯,是最為恐怖的事情。其不但因為違反戒律而背叛了上帝,而且因為導致國王喪失臣民而背叛了國王。”(具體案情見Hales v。 Petit (1565), 1 Plowd, 253, 260。)這種觀點的最后一部分尤為重要,因為其暗示了一種還沒有發展成熟的國家理論,即認為在一個國家中,國王是首領,而民眾是臣屬。在政治國家開始從封建秩序的灰燼中建立起來的時期,這種對國家的關注儼然成為了法官在司法過程中所要完成的重要“政治任務”。此外,從功能主義的角度來看,將自殺確定為犯罪還有助于現代政治國家的確立。原因在于:一方面,由于自殺者被視為重罪犯人,因而其財產要被沒收并上繳國庫,這增加了國家的財政力量;另一方面,確立一個新的罪名,能夠使在具體層面上的司法權力和在總體層面上的國家權力,都擴展了各自相應的干預范圍,從而在相當程度上強化了國家對社會的控制。
當然,這兩方面的功能與更大層面的國家政治經濟體制是分不開的,而且只有將其置于從封建主義向重商主義轉變的社會發展進程中,才能夠得到更好的理解。懲罰自殺的法律之所以規定要將自殺者的財產收繳國庫,是因為一種基于土地所有和領主-仆從關系的制度(a system of land tenure and lord-vassal relations),已經被另一種基于商業和商人-政治國家的制度(a system of merchant-state relations)所取代。國家政治經濟環境的變革,使得針對自殺的刑罰也發生變化:在封建制度中,將自殺者的財產收歸領主,目的在于補償領主因喪失在封地內勞作的仆從而發生的損失,同時從經濟后果上也對潛在的自殺者構成威懾,警告其不得自殺,否則就會拖累家人;而在重商主義制度中,將自殺者的財產收繳國庫,一方面也會對潛在自殺者產生威懾力,另一方面還從源頭上增加了國家的財富,強化了國家的權力。畢竟在以“自由”和“平等”標榜的重商主義制度中,財富的基本形式表征為財物(goods),而非對人身的控制。
三、英國法對自殺者的寬宥
盡管自殺在普通法中被界定為一種犯罪,但在英國,從14世紀到18世紀,都少有自殺者被逮捕、起訴、定罪或判刑。而負責執行這類法律的、最常見的刑事司法官員就是驗尸官。為什么驗尸官沒有嚴格執行法律懲罰自殺者呢?要理解這一點,首先需要指出的是,英國驗尸官這一職位早在1194年就已被完全確立下來,而且一直到18世紀,驗尸官都被賦予了廣泛的權力。當發生非自然死亡的案件時,尤其是引發刑事責任的死亡案件(例如自殺、他殺以及其他暴力致人死亡的案件),首先要由驗尸官負責進行調查。此外,驗尸官最初的一個名稱就是“國王的保稅官”(guardian of the king s revenue),要通過執行刑事法律來保障國王的財政收入。驗尸官甚至還被授權逮捕和沒收重罪犯人的財產。當發現自殺者的尸體后,驗尸官的主要職責就是進行調查并判定死亡的原因。如果無法確定自殺者死亡的地點,就如其他重罪案件一樣,要全案移交治安法官(justice of the peace)來調查,或者交由王座法院(the Court of the King’s Bench)來處理。通常,自殺者的死亡地點都可以確定,因此驗尸官就成為了第一個調查涉嫌“felo-de-se”(恥辱的自殺者)案件的人。
協助驗尸官詢問證人和收集其他證據的是一個陪審團,其成員由12到30個與自殺者同等的人(peers)構成,而且全都是來自離事發地最近的四個鄉鎮。這些陪審員不但聽審證據,而且還憑借個人知識或者所獲悉的傳聞,就自殺者如何以及為何自殺等問題,協助驗尸官進行分析[10]47。驗尸官要記錄在調查中所發現的事實,以便為陪審團作出終局裁決提供依據。如果陪審團認定自殺者在自殺時“神智正常”,自殺者就不能獲得基督教的葬禮,并且其財產也要被沒收。相反,如果陪審團認定自殺者在自殺時“神智錯亂”,自殺者就無須承擔刑事責任,并且其家人也不會因此而負擔懲罰性的后果。實踐中,“因一時神智錯亂而自殺”,是陪審團最為經常作出的認定結論。從14世紀中葉到19世紀,隨著自殺案件的不斷增多,這類裁決也不斷增加。到了18世紀末,已經少有自殺者被認定為神智正常的人。例如,據記載,從1780至1888年間,肯特郡(the county of Kent)的驗尸官在580例自殺案件中,只認定了15例案件當中的自殺者構成“felo-de-se”(恥辱的自殺者)[11]157。 然而,驗尸官和陪審團在處理自殺案件中所表現出來的慈憫,受到了18世紀一些重要法學者和史學者的尖銳抨擊。布萊克斯通爵士(Sir William Blackstone)就指責陪審團在“道貌岸然地作偽證”,利用“神智錯亂”這一托詞來幫助自殺者逃脫刑罰制裁。根據布萊克斯通的說法,如果驗尸官在調查過程中發現了任何顯示自殺者精神焦慮并有可能誘發自殺動機的證據,就會宣告正是這種焦慮“擾亂”了自殺者的神智;如果驗尸官找不出自殺的動機,就會把自殺行為本身作為“神智錯亂”的證據[12]324。同時代的霍金斯(William Hawkins)也批評了“每個自殺者必定是精神失常的”這種觀念。他指出,這種推理的危險在于,一個殺害了孩童的人會據此而爭辯自己當時已“神智錯亂”,因為一個神智正常的人永遠都不會做出這樣的事情來[13]66。盡管存在這些批評,但判定自殺者“神智錯亂”的裁決還是普遍存在。這種裁決不但可以使自殺者能夠獲得一個體面的葬禮,避免財產被沒收,而且還可以使其撫養/扶養的人能夠從保險公司那里領取保險收益。人們普遍認為判定自殺者“神智錯亂”的裁決反映了英國社會草根階層(the grassroots level)民眾的意見,這種裁決的效果也許正是陪審員所預見和期待的。顯然,大多數普通民眾都不希望自殺法中那些嚴厲的刑罰被施加到自己朋友和鄰居身上。而且事實上,正是這種強烈的情感使得民眾在司法實踐中,通過陪審團阻止了自殺法的完全實施。
廣泛抵制自殺罪還是19世紀英國法律改革運動的一個組成部分。這場運動由羅米利爵士(Sir Samuel Romilly)發起,吊詭的是,他本人后來就是以自殺的方式來了結生命的。羅米利認為,正是刑法當中那些極度嚴厲的刑罰導致其自身難以實施。尤其是,他重申了布萊克斯通所說過的一個觀點,即由于刑罰嚴厲程度與行為違法性之間的比例嚴重失調,從而使得陪審員自己都卷入了偽證罪,常常違反證據作出裁決。羅米利還進一步指出,將重罪犯人的財產收歸國家是封建壓迫制度的殘渣余孽,應當被廢除,因為其總是導致無辜的人因為犯人的罪行而被剝奪本應可以享受的物質財富[6]211。在羅米利與其他改革者一起領導的這場運動中,自殺法發生了翻天覆地變化,其中兩個最為重要的成果就是:1823年的《安葬權利法》(Right to Burial Act)賦予了自殺者獲得宗教葬禮的權利; 1870年《廢除沒收財產法》(Abolition of Forfeiture Act)廢除了個人因犯罪而被沒收財產的刑罰。此時,盡管自殺仍被視為“felo-de-se”,是一種犯罪,但法律已不再懲罰自殺者的尸體或財產。到19世紀末以后,與自殺有關的就只有三類行為會受到法律懲罰:自殺未遂,教唆自殺和在自殺過程中導致他人死亡。
在宏觀層面上,自殺法改革的根源,可以追溯到19世紀英國的社會結構和社會進程。一個重要的事實是,自殺法的重大改革在時間上與繼承法的改革相重合。這一吻合實質上顯示了,針對自殺的刑罰改革在源頭上與重商社會中的物質主義(materi-alism)是相通的。財產繼承是資本積累的一個重要渠道,對于早期資本主義經濟的擴張尤為重要。然而在工業資本主義的早期,代際財產繼承卻受到長子繼承制和其他封建法律制度的阻礙,迫切需要變革。為此,資產階級興起后,從19世紀初開始,英國的繼承法就陸續發生了一系列重大變革,許多新法律得到頒行,例如1833年的《繼承法》(Inheritance Act)、1856年的《遺產統一分配法》(Uniformity in Distribution of Estates Act)、1890年的《非遺囑財產繼承法》(Intestate sEstate Act)和1925年的《遺產管理法》(Administration of Estate sAct)。顯然,這些法律清除了諸多封建主義對遺產繼承的限制,有助于其對資本財富的積累。由此可見, 1870年廢除沒收自殺者財產這一法律變革,與上述指向財產的制度改革和其他服務于資產階級利益的改革,是相契合的。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只需認識到,從資產階級的立場出發,沒收自殺者的財產實質上就是一種阻礙財富流轉的封建制度。因此,沒收自殺者財產這種刑罰也就理所當然地成為了資產階級改革者手中“柳葉刀”所要剖解的對象,正如資產階級要迫切地解構封建土地法一樣。與此同時,對于19世紀的政治國家而言,懲罰自殺者的刑罰已經變得不重要了,因為沒收自殺者的財產已不再是一種重要的財政收入來源。導致這種情況主要有兩個原因:一是,公眾對自殺法的抵制極大程度地限制了國家所能獲得的財物和金錢;二是,相比于中世紀,此時國家已有更多其他途徑來獲取財政收入,例如國內稅、關稅等。
四、結語
在理論上,對刑罰的解釋歷來存在著報應論和功利論兩種視角。報應論認為,“刑罰之所以應該存在,原因不在于懲罰可以帶來有益于社會的結果,而在于作為懲罰之前提的犯罪是一種道德上或法律上錯誤的行為”,即“為懲罰而懲罰”;功利論則認為,“刑罰之所以應該存在,不是因為懲罰本身具有某種值得追求的內在價值,而是因為它具有服務于有益于社會的目的的工具價值”,即“為社會目的而懲罰”[14]2-3。圍繞著報應論與功利論,有人將“刑罰進化”的主要原因歸結為“人類對刑罰理性的不斷發現與追求”,甚至斷言“一部刑罰進化史,實際上也就是一部刑罰理性的發現和完善史,亦即以刑罰體制的更迭為表征的刑罰理性進化史”[15]8-9。與此形成強烈反差的是,福柯在《規訓與懲罰》中另辟蹊徑,從功能意義上對刑罰的歷史變遷進行理解和闡釋。在福柯看來,刑罰既有報應的因素,也有其他目的;無論何種刑罰機制,對于決定其是否能夠繼續存在的根本原因,都要從刑罰的制度性功能與社會結構的關系中去尋找;只有當一種刑罰所發揮的制度性功能契合了社會結構、滿足了社會結構的要求,這種刑罰才能獲得正當性并得到貫徹。
遵循福柯的這一分析視角,我們就可以看到,英國法對自殺者的態度轉變,不僅僅是“文明”和“理性”的進步,毋寧說是國家權力技術的一種革新。起初之所以懲罰自殺者,是因為在人身依附性極強的封建社會中,因懲罰尸體和沒收財產所起到的威懾力,一方面能夠有效地減少封建領主勞動力的損失,另一方面還能夠補償甚至增加封建領主的財產性收入。而后來之所以寬宥自殺者,則是因為懲罰自殺者的尸體首先在政治上遭到了民主司法的抵制,而且沒收財產從根本上不利于新興資產階級原始資本的積累,無益于資本主義制度的確立。因此,就英國法對自殺者的懲罰與寬宥、英國自殺法的變革而言,我們首先要認清其所處的大背景是社會結構和權力架構正從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轉變,這是由經濟力量所左右的,并且服務于那些控制著生產和積累財富的利益集團。由此,從英國法對自殺者態度的轉變過程中,我們看到了一種作用于死者(尸體和財產)的國家權力技術,一種在福柯分析基礎上擴展了的刑罰政治經濟學。
注釋:
[1]米歇爾?福柯.規訓與懲罰[M].劉北成,楊遠嬰,譯.北京:三聯書店, 1999.
[2]黃永鋒.歷史變遷中的刑罰政治經濟學[J].海南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07, (1).
[3]Rosen, G..History[C]∥S. Perlin (ed. ) A Hand Book for the Study of Suicid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4]Pollock, F. , F. W. Maitland. The History of the English Law (2nd Ed. )[M].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5]Guernsey, R. S.. Suicide: History of the Penal Laws[M].New York: L. K. Strouse, 1883.
[6]Fedden, H. R.. Suicide: A Social and Historical Study[M]. New York: Benjamin Blom, 1972.
[7]Bracton, H.. On the Laws and Customs of England (S.E. Thorne, trans. )[M].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
[8]W illiams. F.. The Sanctity of Life and the Criminal Law [M].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57.
[9]Holdsworth, W. S.. A History of English Law ( III)[M]. London: Methuon and Co., 1909.
[10]Moley, R.. Politics and Criminal Prosecution[M].New York: Arno Press, 1974.
[11]Moore, C. A Full Enquiry Into the Subject of Suicide[M]. London: P. N. K., 1790.
[12]Blackstone, W.. Commentaries on the Laws of England(4th Ed.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770.
[13]Hawkins, W.. A Treatise of the Pleas to the Crown(6th Ed. )[M]. Dublin: Eliz. Lynch, 1972.
[14]邱興隆.關于懲罰的哲學[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0.
[15]邱興隆.罪與罰演講錄:第1卷[M].北京:中國檢察出版社, 2000.